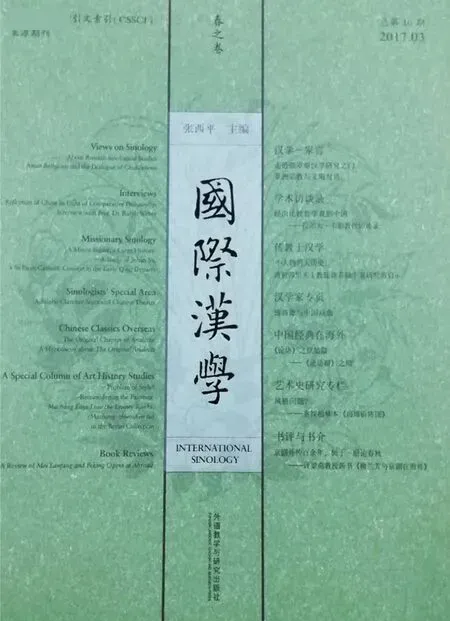近二十年来新加坡汉学研究之现状及特色—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为例*
□
引言
在海外汉学研究中,①关于“汉学研究”概念的界定,学界多有论著,在此不一一赘述。可参见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的地位相当特殊。纵然与中国大陆相隔千里,复杂的历史渊源却在两国间串联起了牵丝扳藤的紧密联系。早在宋元时期,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带来了南来北往的中国商船。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曾涉足时称“淡马锡”的新加坡。清朝末期,为躲避战乱谋求生计,大批华人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迁徙至马来半岛。从1836年开始,新加坡当地华人人口逐步超过马来原住民总数。②新加坡统计局网站(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人口与人口结构,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browse-bytheme/population-and-population-structur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5月1日。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各族人口比例中,华族占74.1%③同上。,是全球范围内除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外,唯一以华人为主体并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新加坡华人与我们同宗同族、同文同种,是一衣带水的近亲。这种情感预判,使我们在审视新加坡汉学研究时容易进入一种思维误区,即新加坡华人是中华文化天然的亲近者,应当对中国怀有一份血浓于水的别样认同;新加坡庞大的华人社群基础,能够保证汉学在新加坡得到充分重视乃至热烈追捧,并成一门“显学”。然而,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所言:“国人对新加坡存在着不少认识错误和‘美丽误解’……这种认同经常显得一厢情愿。”④王江雨:《“新加坡模式”深思明辨》,《财经》2013年第10期,第1页。此类预设并不一定契合近二十年新加坡汉学研究的现状,甚至有可能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
尽管时至今日,在全球范围内,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仍以历史悠久、影响深厚著称,华人族群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与之矛盾的是,从新加坡的近现代历史沿革可以看出,虽然该区域华人和华裔人口众多,但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形成主体意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为不同的力量所牵引。新加坡的现代华人社群从教育背景、职业目标,到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在长达百年的冲突、裂变、杂糅和自我塑造中,为各种文化类型所陶染。如王赓武教授在2015年发表的言论:“新加坡华人不会盲目跟随中国。事实上,新加坡华人自国家独立以来的转变是值得注意的。”⑤王赓武:《中国崛起与新加坡的“华人困境”》,载《联合早报》,2015年6月5日。这种转变如何影响了近二十年来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当代新加坡汉学研究的主流角度和价值观显现出怎样的“西方”特质,抑或“中国”特色?在种族与国家的多层次关系间,新加坡的汉学界如何看待中国?新加坡的汉学研究未来会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本文将从新加坡汉学研究群体的认识策略与情感认同出发,以东南亚汉学研究的核心重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为例,结合新加坡官方与民间对汉学研究的多重态度,重新解读近二十年,尤其21世纪以来,新加坡汉学研究的现状与特色。
一、研究现状
1.逐渐“边缘化”的地位
关于近二十年新加坡汉学研究的现状,首先需要从1980年后该国推行的语言政策开始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加坡的国民教育英校和华校两个系统并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推行“去华校”政策,英语作为通行教学语,为事实上的“第一语言”,华文降级为按照学生各自种族出身选修的“母语”,与泰米尔语、马来语等并列。各级别华校被逐步裁汰。
经过30多年政府行政手段的强制推动,①推行英文教育作为新加坡的基本国策之一,政治领袖们不断公开强调英文的重要性,鼓励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学好英文。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表示:“我们学习英语是为了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联合早报》1999年8月16日报道李光耀内阁资政15日在丹戎巴葛选区的国庆晚宴上致词)前总理吴作栋认为英语“是我们同世界各地沟通的工具。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不讲英语,而我们能掌握英语,那我们就占了上风”。(《联合早报》1999年8月29日报道吴作栋总理28日在马林百列选区国庆晚宴上致词。)而今的新加坡,英语已成为本地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医疗等领域的强势语言,未来还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不断蚕食使用华语的人口比例。1980年后接受教育的新加坡人,与中华文化的疏离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根据新加坡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0年,新加坡华族家庭中,5—14岁的儿童51.9%在家讲英文。15—24岁的青少年中,这一比例则为40.7%,均远高于55岁以上老龄人士的19.2%。②新加坡统计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教育与文化 ,http://www.singstat.gov.s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ndpapers/population#education_and_literacy,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5月1日。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加坡华族家庭常用语言,在祖孙三辈的代际交替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华文迅速易位于英文,呈现出明显的“脱华入英”趋势。根据语言濒危程度(Degree of Language Endangerment)的定义,当一种语言只在老年人群,而并非年轻群体中通用,表示该语言已进入弱化/病态(Weakening/Sick)的时期。虽然自独立以来,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华人依然是整个新加坡社会的主体。但绝大多数在新加坡接受教育的年轻华人,成为了“被动双语者”(passive bilingual)。他们更容易接受第二语言英文的信息,对于“母语”华文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系统的学习。因此从基础的以华语交流,到中层的以华文书写和阅读,再到更高层面的汉学研究,都不能称之为当代新加坡的主流。
新加坡目前共有四所公立大学,③分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南洋理工大学(NTU)、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SUTD)和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其中只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设有中文系,均为该校人文暨社会科学院下属学系之一。其中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于2004年7月开办研究生课程,2005年7月开始招收本科生,首批招生人数只有70人,从办学规模到历史积淀,都尚显青涩薄弱。与之相比,1980年成立,并于1994年专门开设汉学研究中心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资质则更胜一筹。2007/2008学年,该系教师人数为26位,各年级本科生人数合计1 011名。然而从整体来看,新加坡国立大学现阶段共有28 000余名本科生,2 400余位专职教师。中文系的师生,分别只占全校总数的约1%和3.6%。两所公立大学的中文系作为新加坡汉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机构,其规模尚且如此,新加坡汉学研究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和学术界中的“非主流”身份可见一斑。
式中: Q—两相邻舱室之间的补气量;A—两相邻舱室之间的补气面积;P1—压力较高的舱室内的舱压;P2—压力较低的舱室内的舱压;T1—压力较高的舱室内的舱温;R—气体常数;K—绝热指数。
2.全球化的研究团队
由于官方政策导向等现实原因,新加坡的汉学研究,规模较小且在本土的地位较为尴尬。但这并不代表新加坡汉学研究的整体质量存在很大问题。事实上,重视教育是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基本国策之一,新加坡教育部是仅次于国防部的第二大财政开支部门。从2000到2013年之间,新加坡教育经费占政府开支的平均比率为20.1%,据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列全球第34位。①参见世界银行网站“教育作为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支出”(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as % of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所公布的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XPD.TOTL.GB.ZS/countries/HT-XJ-XM?display=default,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5月1日。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1889—1962)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②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新加坡的公立大学为任课教师提供了极富国际竞争力的薪酬与福利。③新加坡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不仅领先于东南亚诸国、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甚至高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普通大学。不仅如此,新加坡国立大学还在纽约和伦敦等地设立了专门负责教师聘任的办公室,广泛接触代表各领域前沿思想的知名学者,以优厚条件邀请他们赴新加坡任教。
在坚持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策略指引下,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不仅亚洲领先,也在一路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16年QS发布的世界大学(QS University Rankings: 2016)排名,新加坡国立大学勇夺亚洲第一,世界第12宝座,南洋理工大学紧随其后。虽然新加坡基础教育的“去华校”政策一直存在争议乃至备受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公立大学对师资队伍的高标准、严要求,也同时为新加坡汉学研究组建了高品质、小而精的全球化研究团队。
2016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共有专职教授15位,其中有13位在欧美顶尖名校取得博士学位,如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背景,不单只是“血统”或噱头,它实实在在地保证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汉学研究品质。从2003到2007年,该系教师出版专著31种(不包括专著中的部分篇章),发表学术论文135篇。与此同时,国际化的研究团队还帮助新加坡汉学研究打破语言疆界,增加了中西对话的可能。从2008至201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世界各国联办的学术专题研讨会有“辞赋理论、语言修辞、与文类研究—国际赋学研究会学术论坛”“清代理学国际研讨会”等。同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汉学研究机构建立交流与合作,为新加坡的汉学研究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群。
3.民间力量的支持
相较于新加坡政府更为重视英文教育的官方态度,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和热忱支持是新加坡汉学研究呈现出又一独特现状。
不同于部分研究者所认为的:“汉语语言文化的逐渐消亡,与其说是英美语言和文化的侵略,不如说是在华族自身无可奈何又略带感伤的放弃。”④韩雨:《多语环境下的语言接触和汉文化变迁浅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29期,第87页。即便新加坡系统的华文教育已被取缔三十多年,却并未彻底磨灭华人华侨的文化认同感。如张西平教授所言:“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⑤张西平:《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尝试》,《中华读书报》,2016年5月4日。在移居海外的华人群体中,尽管与中国的接触相对减少,但在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和向心力的影响下,仍然保留了中华文化的诸多核心成分,譬如方言、习俗和宗教信仰等。虽然这种文化维持会受政府导向影响,并随时间和人口更替而发生变化与衰减,但到目前为止,在新加坡华人群体中,中华文化仍具有深厚的影响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现阶段可供申请的奖助学金,绝大部分并非来自新加坡教育部,而是得益于民间团体或个人的慷慨捐赠。⑥包括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中文系奖学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中文系论文研究奖学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中文系游学(田调、交换生)补助金、孔子基金会奖学金、新加坡道教学院国大文学院中国宗教研究生奖学金、云茂潮中文系主修奖学金、云茂潮中文系研究生奖学金、新加坡福建会馆华文教学奖学金、林金山纪念奖学金。例如曾由爱国华侨陈嘉庚族侄陈六使担任主席的新加坡福建会馆,一直以保存和推广中华语言和华族文化为宗旨。其设立的华文教学奖学金,意在鼓励优秀的中学生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深造,并于毕业后留新加坡任教,传承中华文明。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则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合作,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表现突出的个人提供奖励。因此不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可以获得这些华族社群的帮助,而且现今的新加坡汉学研究界也得到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内,多名专任教师“身兼数职”,如李焯然副教授兼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组主任,王昌伟副教授任南洋孔教会学术副会长等。
二、研究特点
1.西方化的研究途径
作为新加坡汉学研究主体的国立大学中文系教师群,主要来自新加坡与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虽然地区有所不同,他们的成长和求学经历却存有诸多相似之处。绝大部分研究人员早期接受了系统的华文初级教育,出生于中国的教师不必赘述,本国培养的学者们,目前也全部属于新加坡最后一代华校生。②其中最年轻的徐齐雄副教授,小学阶段也曾在新加坡淡滨尼地区传统华校育民小学就读。但是,他们并未被纯粹的“中华文化”范畴束缚。青年时代走出国门、负笈海外,所修读的欧美名校博士学位,是他们赢得国立大学中文系教职最重要的“敲门砖”。
本文将这些学者定义为“离散华人”群体,即他们本身都为华族,却是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或因为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成为了移民的第一代。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又兼具现代欧美教育背景。出生和成长经验赋予了他们对中华文化原生的体验与认知,而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又在严谨科学的训练下,向他们灌输了西方的思想体系及价值框架。
后殖民理论巨匠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将“在欧洲内部有特殊身份,但一直在为局外人代言”的群体定义为“文化两栖人”(cultural amphibians)。③Patricia Clare Ingham, Michelle R.Warren, Postcolonial Moves: Medieval Through Modern.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96.同样,“离散华人”并非一直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由单一文化类型和社会力量塑造出自身的特质及认同。反之,他们接触了广泛、多元的社会文化,学贯中西的同时跨越了种族、空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意味着他们构建个体文化身份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新加坡汉学研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质,首先来源于研究者的认识策略与叙述方式,它并不完全与作者本身的母语和出生地相连,而是呈现出西方化的研究途径和文化的多视角性。
首先是批评手段的“西方化”。用西方的理论工具和批评方法来解释中国问题,是这种跨文化视野中最显著的特质。在不同文化类型杂合、碰撞、挤压的动态趋向中,西方中心的话语权力在“离散华人”批评家和研究客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潜在关系。
王润华教授堪称个中旗手。他祖籍广东,194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1962年从台湾政治大学开启留学生涯。1968年赴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师从周策纵教授(1919—2007)主修中国文学,辅修比较文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任教于国立大学中文系。从2000年的《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到2011年发表的《探索“存在的遗忘”:浪子、橡胶树、榴莲、铁船、鱼尾狮—新加坡的移民、后殖民、边缘、魔幻写实、多元文化的书写与世界文学》,王润华将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后殖民主义,广泛运用到新马华文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中,借后殖民的“杯酒”,浇胸中之块垒。他借鉴了一系列后殖民批评话语,解构我们原本熟稔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从西方理论的视角,关怀文学里中国的历史与悲欢。在探讨帝国主义和东方文化的相关课题方面,显示出与英美批评家基本一致的方向。
其次是东亚研究的整体化。打破中国研究的界限,引入亚洲其他国家作为参照系,从更广阔的视域理解中国文化,也是新加坡汉学研究全球化视野的一部分。
在大多数位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大学里,中文系都是一个单独开设的系别。①或称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系/国文学系。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及文化等。但反观欧美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情况却截然不同。极少有学校独立开办中文专业,汉学研究一般和日本研究、韩国研究等一起,共同纳入东亚研究学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的范畴内。②东亚研究是以整个东亚为研究区域(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和朝鲜),从跨学科的方向关注东亚地区的语言及文明。其主要方向涵盖人类学、考古、历史(包括艺术史、经济史和法律史)、语言学、文学、哲学、政治、宗教和社会学等。
对于曾在欧美东亚语言及文明系学习的研究者而言,超越国界的研究条件开启了多元的研究视角。相比单纯的中文系背景,他们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更广泛的了解,具备跨文化、跨学科阐释中华文化的能力。如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及文化系(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s)的许齐雄副教授,其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明清思想史和宋明理学等方面,但他同时积极拓展新的研究范式,在比较文化研究的框架下,引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作为汉学研究的“镜子”,在多重客体的映照下,加深对中国思想的理解。代表论著如《事大至诚—从十六世纪末“昭雪国疑”和“壬辰请援”看朝鲜李朝政治核心对中国的想象和期许》《传统的开展与再生:沟口雄三的中国近代社会观评析》(与李焯然合著)。
再次为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接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专业训练、精通中英文、能够同时以双语进行教学和研究,是新加坡汉学研究社群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些在中西间沟通交流无障碍的汉学研究者,于跨语际的汉学实践中表现得更为得心应手。除了研究途径和方法能够和西方接轨外,他们用流利英文写作的论文发表于各类国际期刊,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同时也能够充当东西文化沟通的桥梁,为东方读者翻译引介海外中国研究的新成果。
总而言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网站所宣传的“贯通东西学术、涵容多元视角”,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网站,http://www.fas.nus.edu.sg/chs/chines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5月1日。国立大学中文系所代表的新加坡汉学研究之国际化视野和西方化研究途径,增进了不同语言、不同种类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激发了跨地域、跨学科学术方法的使用,促成了一系列与世界文化研究脉络贴近的新兴汉学研究课题,并且提升了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在本埠及国外学界的重要性和可见度。
2.文化母国的想象回归
在一些反映当代欧美国家汉学研究现状的论著中,作者不约而同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在“西方中心主义”导向下,国外汉学研究普遍存在偏重实用性的趋势,正如何培忠所分析:“对美国而言,研究中国并不是对其存有文化想象或向往,而是区域研究的一环。”④何培忠:《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2页。而据关山《德国汉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统计:“汉学则被纳入社会科学的领域,相比之下更注重对现代中国的研究。老一代汉学家离开汉学界后,从60年代中期始,几乎没有人再以中国古代作为教研的课题。”⑤关山:《德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61页。
作为新加坡汉学研究主体的“离散华人”学者群体,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都相当微妙。东方成长背景和西方教育训练,为两种不同文化力量所牵引。因此新加坡的汉学研究,不止涉及单纯的学术问题,还关乎海外华人群体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个人的文化情感和国家的集体意识,在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群体中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割裂”。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团队,虽然身处独立的国家社会结构中,出生地和国籍也有所不同,但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看,他们更接近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由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中华文化相互连接。对中华文明的原乡记忆,让他们在熟练使用西方理论工具的同时,主动抑或被动地呈现了对文化中国的回望,使得他们的研究,往往存在融入和析出的冲突,个人与集体的对撞。无论彰显或隐藏,华人性常常透过文本浮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中华文化既是新加坡汉学研究的入口,也往往是它的终点和精神归宿。这种徘徊于“文化母国”与“祖国”之间的“身份认同”,构筑起新加坡汉学研究自身“亦西亦中”的价值观和特质。
当西方的汉学研究者们对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寻求与中国的“相处之道”时,新加坡汉学研究界却带着它深刻的中华文明烙印,回溯中国古典文化。在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系统中,对中国古代文学、文论、思想、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是其中一大重要领域。与欧美、日韩等地区的域外汉学研究者有所不同,基于“根基性情感联系”的族群认同,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群体在身份上有了更多的能动性。“离散华人”的多重背景,加之工作场域和研究资料的辅助,使得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研究中,获得了更加有利的文本诠释位置。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六个研究群队分别为东南亚华人研究组、汉语语言学研究组、明清研究组、印刷及大众文化研究组、中国宗教研究组、古典文学与思想研究组。原则上每个研究群定期举办学术活动,对内包括国大中文系师生的座谈会、研讨会、读书报告会、田野心得报告会;与本地民间学术团体,如新社、南洋孔教会、潮州八邑会馆等合办学术活动。对外则有访问学者的演讲和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从组群设置到研究方向,均展示出不同于海外其他区域汉学研究的、鲜明的本地特色。
例如2013年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休的萧驰副教授,本科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早年曾以《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一书引起广泛关注。他于1987年赴北美深造,先后入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修读比较文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任教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萧驰副教授研习中国古典诗学三十余年,尤善船山诗学。1999年在台湾出版专著《中国抒情传统》,被誉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滥觞北美后回流亚洲之“中国抒情传统”①1971年旅美学人陈世骧在美国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认为“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该论点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逐渐成长为一门“显学”。代表学者还有高友工、孙康宜、张淑香等。文艺思潮中一位重要学者。2003年,论文集《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研究员盛赞该书:“将王夫之诗学的阐释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②蒋寅:《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第180页。同时对大陆学界对新加坡汉学研究成果重视不够的现状不无遗憾,认为:“目前我们对海外清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了解得很不够,今后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学术交流和沟通。”③同上。
同样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苏瑞隆副教授,1984年自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师从西方汉赋专家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教授。苏瑞隆副教授早年就与大陆的辞赋研究界展开了合作,例如1999年与中国赋学泰斗龚克昌先生合著《司马相如》,成为中国与海外汉学研究界跨界合作的成功范例。可以说作为中西交流的“中转站”和“关键点”,苏瑞隆副教授串联起了中美学界对中国辞赋的研究,增进了双方的合作与沟通。
④ 王润华、杨松年主编:《新马汉学研究—马大国大中文系研究状况探讨研讨会论文集》(内部流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出版,2002年,第119页。
在国立大学中文系史学研究方面,明清研究蔚为专长,较为薄弱的上古、中古历史,尤其先秦研究也自20世纪90年代起取得了突破。据2001年国立大学中文系史学组的统计数据,中国史研究中思想文化类的论文一枝独秀。①同上,第117页。反之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单薄。这种汉学研究计划的制订,不单只是研究人员个人好恶的问题,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新加坡汉学研究界对中华思想文化所怀有的特殊情感及认同。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于2002年所做的研究成果汇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汉学研究,明显带有海外华人的情感意识。换言之,研究者首先是以海外华人或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的身份或情结,去研究、探讨华人的历史与文化。”②劳悦强:《学与术之取舍—新加坡近二十五年来汉学研究之发展》,见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合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马来西亚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结语 新加坡汉学研究展望
对于新加坡汉学研究在新世纪的未来,海内外均有研究者持乐观态度。“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和新加坡之间交往趋于密切,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新加坡汉学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③吴原元:《略述新加坡汉学的历史与现状》,载《社科纵横》2009年第6期,第127页。“目前,新加坡全国上下似乎万众一心,鼓励国民重视华文,并且积极学习中华文化。”④罗兆强:《华文退出新加坡舞台》,摘自新加坡文献馆网站,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6560,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5月1日。
同时,也有学者在冷峻反思后,对新加坡中华文化传承表示忧虑。“新加坡政府推行的杂交文化导致年轻人面对文化断层的问题,到了90年代已经出现明显的病症……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在杂菜语言及杂交文化的腐蚀下,新加坡年轻一代基本上面对文化断层带来的困境。”⑤吴了了:《李光耀的中国结》,载《镜报》(香港),2015年5月25日。
这种焦虑感其实不无道理,尽管2016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中,新加坡本地老师有四位,为各地区之最。但作为最后一代华校生,他们的教育经历在现今的新加坡已呈不可复制之趋势。1996年9月21日,《海峡时报》刊登名为《认同感:危机与机会》的文章:“我同情老一代,我了解他们,今天我拥有的一部分,是他们留下来的。但我知道必须跟他们不同,因为我没有他们所负担的心理与历史包袱。”⑥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一批“双语新生代”步入社会,这一群在20世纪80年代华文教育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才入学就读的青年,代表了与先辈们完全不同的新加坡华人。他们中的部分人,即便对中华文化仍保有温情及敬意,有勇气和志向投入汉学研究的阵营。但是,氛围同教育的缺失,不断消解了文化传承所必需的底蕴与尊严。
未来的新加坡汉学研究,也许仍然可以凭借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吸引海外一流学者,保证其研究质量,但是只有新加坡当地学者才能代表的本土汉学研究与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沿袭等方面,却面临人才储备的不足。从2000年开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入学的本科新生中,新加坡本地学生的数量呈逐年递减的趋势,折射出新加坡本土汉学“后继无人”的潜藏危机。新加坡海外华人社群中,中华性的继承与认同,在强势的“自我西方化”环境中,还能持续多久。这种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承会在汉学研究中得到怎样的体现,值得我们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