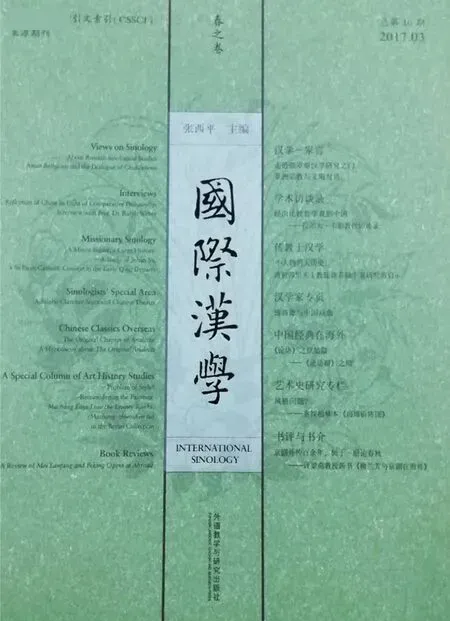折射的他者:吴历《三巴集》中的西方形象*
□
在吴历(1632—1718)生活的年代,亲自到过欧洲、实地观察过西方习俗的中国人寥寥无几。1681年跟随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由澳门赴欧洲的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 1657—1692)是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之一。沈福宗之后则有1702年随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nonne, 1655—1713)至欧洲并在法国度过余生的黄嘉略(Arcade Huang, 1679—1716)。不过这两人均英年早逝,留下的中文著述(黄嘉略有《汉语语法》《汉语字典》以及一部记于1713年10月19日至1714年10月2日之间①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9页。的私人日记)不多,直接描写西方的更少。清人樊守义(1682—1753)1707年随法国传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62—1720)出使罗马,居意大利九年,他的《身见录》(约1721年)被视为最早的西方游记(原稿藏罗马图书馆,阎宗临校注,1941年刊)。相比而言,吴历是较早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澳门这一“界外”地域描绘西方的中国文士之一。齐皎瀚(Jonathan Chaves)指出,在澳门时,吴历“尽管身处中国国土,却是以一名目击者的身份准确描绘西方风俗的第一位中国诗人”②Jonathan Chaves, Singing of the Source: Nature and God i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Painter Wu Li.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p.55.。
1680年,吴历和陆希言作为赴罗马教廷的中国司铎候选人来到澳门,后未前往欧洲,而是留在澳门三巴静院学道。澳门“界外”之称,见于陆希言所撰《澳门记》最后一段:
乃有摈而为界外者。因存其本国之风,衣冠犹在,语言犹在尔。若吾不以为外,而以孔孟之书、周鲁之礼化之,一道同风。……以如是之地,如是之人,如是之道,如是之学,如是有功于吾国家者,而又视为外夷,摈为界外,不亦深可慨也夫,抑为不知究也夫?③吴历撰,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97页。文中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1680年,当吴历他们来到澳门,葡萄牙人在此定居已达一百多年,澳门独特的葡人文化已逐渐成型。引文中的“外夷”即指当时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外”指外国。陆希言在《澳门记》中客观描绘了澳门这一“界外”之地的异“国”风情,力写对澳门之被摈为“界外”、被视为“外夷”的不满,“内”“外”之截然对立,当时“界内”对澳门的成见之深,可以想见。那么,作为陆希言在三巴静院同时期修道的同学,吴历对于这片“界外”土地及其生活又是如何描绘和应对的呢?在吴历眼里,西方这一他者在“界外”澳门折射出的形象究竟如何?这需要到吴历主要创作于澳门修道期间的“天学诗”集—《三巴集》(包括前帙《澳中杂咏》30首和后帙《圣学诗》82首)中去探究。
吴历的“天学诗”,即以基督宗教为主题的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被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专家、美国汉学家齐皎瀚称为“以前所未有的大胆进行实验性创造”,是吴历“真正的独创性”所在①Chaves, op.cit., “Preface,” p.xii.,无论对中国诗歌发展史还是基督宗教在华史的研究而言,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三巴集》作为吴历天学诗的重要部分持续受到中西学者的关注和研究。2010年,徐晓鸿在中国基督教杂志《天风》上发表一组文章《吴历及其“天学诗”》(一至六),介绍和解读吴历的天学诗创作。
比较文学继承了法国比较文学的系统教育,肯定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法国比较文学家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倡导形象学甚力,他对形象学论述中关于他者相异性的书写以及对待他者的基本态度或象征模式两部分内容尤其中肯②巴柔著,孟华译:《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形象》,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152页,第153—184页。。巴柔指出,比较文学形象学关心的是对相异性和关于相异性的书写,即以文本所存储的能够直接或间接传播他者形象的词汇作为形象的原始构成成分。巴柔所说的词汇可以扩展到句子、语段、语篇;对于本文所分析的对象文本《三巴集》来说,这些书写往往是诗句或一整首诗。第二个重要内容即对待异文化的基本态度或象征模式,巴柔区分了四种态度:狂热、憎恶、亲善以及第四种可能:一个新的统一整体,可以说是一种世界主义的开放而宽厚的态度。本文运用巴柔的形象学原理,梳理《三巴集》对他者相异性的书写,以此呈现其中的西方形象,同时表明作者对这个西方他者的态度,最后总结《三巴集》所呈现的西方他者形象对于当时中国人的意义。
一、《澳中杂咏》:西方他者的异地映射
1.澳门风物志
吴历将他在澳门观察到的地貌、经济、风俗习惯等写入诗歌,《澳中杂咏》构成吴历在澳门这一17世纪下半叶带有鲜明西方影响痕迹地区的西式生活图景,类似于一种游记文学。齐皎瀚指出,吴历的30首《澳中杂咏》很可能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细致描绘西方风俗的诗歌创作”③Chaves, op.cit., p.50.,充分展现了直接由葡萄牙商人给澳门带来的新风新貌,比如海上商业盛于农业:
海鸠独拙催农事,抛却濠田隔浪斜。地土纵横五六里,隔水濠田甚瘠。居客不谙春耕,海上为商。(其二)
在这里,有“疍”以海上捕鱼为业,以海为家,好群聚饮酒的生涯:
夜半蛋船来泊此,斋厨午饭有鲜鱼。(其三)
海气阴阴易晚天,渔舟相并起炊烟。疍人放舟捕鱼,以海为家,终岁不归。(其五)
晚堤收网树头腥,蛮疍群沽酒满瓶。(其八)
有使用橄榄油的西式烹调法:
鱼有鲥鰡两种,用大西阿里袜油炙之,供四旬斋素。(其三)
食材、调味品中,有来自南洋群岛的胡椒:
小西船到客先闻,就买胡椒闹夕曛。(其十八)
有来自西方欧洲报时准确的自鸣钟:
但听钟声不听鸡。昏晓惟准自鸣钟声。(其十九)
有葡萄牙人黑人仆役的居所、关于美丑的特殊俗尚及其善舞的特征:
黄沙白屋黑人居,门柳如菼秋不疏。黑人俗尚,深黑为美,淡者为丑。(其三)
黑人舞足应琵琶。黑人歌唱舞足,与琵琶声相应,在耶稣圣诞前后。(其二十七)
居客异于内地的着装风俗:
俗喜短毳衣衫,两袖窄小,中间四旁纽扣重密。……(其六)
葡萄牙商人妇不事农桑、好锦衣打扮的生活:
少妇凝妆锦覆披,那知虚髻画长眉。夫因重利常为客,每见潮生动别离。(妇)全身红紫花锦,尖顶覆拖,微露眉目半面,有凶服者用皂色。(其七)
西人与中国人相异的免冠礼:
来人饮各言乡事,礼数还同只免冠。发有金丝拳披者,矜重戴黑多绒帽。帽式如笠,见人则免之为礼敬。(其九)①以上吴历诗作均引自《吴渔山集笺注》,下同。
通过《澳中杂咏》对澳门的描绘,澳门的西式生活风貌跃然纸上。在这里,这个西方形象就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实,吴历对此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诧和不安,而是欣然观察,以欣赏和赞美的笔调描绘澳门的西式生活风貌。显然,澳门为吴历打开了观察新世界、了解新事物的一道门窗,而吴历乐在其中。顾彬(Wolfgang Kubin)曾指出,《澳中杂咏》最惊人的是吴历克服对欧洲任何偏见的能力以及对东西方差别的幽默描绘。②Wolfgang Kubin, “Crossing the Border, Breaking with the Past: Wu Li’s Iconoclasm,” Cultur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and His Inner Journey.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6, p.333.吴历在面对“他者”时,不仅看到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别,而且还知道外国人也可能将他视为不同的。③Ibid., p.328.齐皎瀚指出,与同时代其他中国文人诗文中对外国风俗的描写相较,《澳中杂咏》具有惊人的“移情性”(empathetic),表明吴历面对异国风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恐外症(free of xenophobia)④Chaves, op.cit., p.58.。由巴柔的四种基本态度考量,吴历对澳门生活画景的态度应是第三种,即亲善或友善。
另外,《澳中杂咏》对澳门的书写不仅突出了他者相异性,同时也融入了他者和自我的相似性、相同性。吴历在面对澳门异于中国内地的西风异俗时,在敏锐地观察到二者相异的同时,也隐含着对二者之同的体认。如见面礼俗之不同,仅在于表现形式—西方人以入室脱帽为敬礼,而中国人没有这个礼,形式不一,但两种不同形式所表达的礼仪内容本身是相同的;服装问题亦如是。吴历对东西之异同给予同样的关注,表明吴历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实在是比较“开放而宽厚”的,是近似于巴柔所谓世界主义的第四种态度。
2.“大西”“海外”:吴历想象的西方
吴历所在的圣保禄学院是一所由天主教耶稣会创立于1594年的传教士学院,办学经费主要由葡萄牙商人提供。当时尽管身处多葡人居住、深受葡萄牙文化影响的澳门,在《澳中杂咏》中,吴历却甚少直接提到葡萄牙这个具体的欧洲国家,而一般以“大西”“西”来指称广义的西方欧洲,如“大西阿里袜油”(其三)、“计程前度大西去”(其十)、“西字如蝇爪”(其二十六)等。此外,还有一次以“海外”来指称地域上的西方欧洲,即“性学难逢海外师”(其二十五)。“海”字意味深长。客观上,澳门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海”字密不可分。在《澳中杂咏》所描绘的澳门风物志中,“海”字出现频繁,大部分都是实指澳门濒临大海:“海鸠”(海鸠独拙催农事[其二])、“海气”(海气阴阴易晚天[其五])、“以海为家”(其五)、“海浪”(无风海浪似雷霆[其十七])等。
首先,吴历在诗中不直言葡萄牙而以“西”“大西”指称西方欧洲,表明他是将欧洲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对待的,因此对葡萄牙这个具体的欧洲国家并不特别留意。相较而言,清修《明史·外国传》中将“佛郎机”(即葡萄牙)刻画为一欧洲强国,突出其强大、可怕的异国形象(《佛郎机传》云:“其人……好经商,恃强陵轹诸国,无所不往”“自灭满剌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蕃无敢与抗者”。),吴历《澳中杂咏》与此不可同日而语。吴历在圣保禄学院修习神学,以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为总的精神指导,故而对欧洲有此全体的概念性认识。吴历的这种认识突出了宗教之统一对于欧洲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重要意义。
其次,“海”字在诗中的频繁出现表明吴历似乎对这个字有着特殊的偏爱。事实上,“海”字对吴历而言绝非仅仅意味着作为物质实体的大海,“海”与“大西”联合在一起代表吴历内心对于海上远航、对于西方“绝域”的向往。在渔山生活的年代,海上航行对渔山并不陌生。在渔山早年相过从和往来的诗画文友人中,有一位遗民文人朱舜水。朱舜水(1600—1682)参与复明事业,曾于1647年奉命赴日乞师。1659年,复明事业失败,舜水再至日本,先后居长崎和江户,服明衣冠,讲学授徒二十余年,直至去世。在朱舜水赴日之际,吴渔山作《送朱舜水之日本》二首为之送别:
征帆出海渺无津,但见长天不见尘。
一日风波十二险,要须珍重远游身。
春风日日送行旌,谁送天涯九万程?自古无情是杨柳,今朝攀折昨朝生。
“征帆出海渺无津,但见长天不见尘”“谁送天涯九万程”,对于扬帆万里的海上旅途,渔山一方面为朋友担着心,折杨柳为朱舜水送别,希望他“珍重远游身”,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和对他远游旅途的祝福,同时,诗里行间又流露出诗人对远方旅途的憧憬。在那个社会动荡、经历巨变的年代,渔山身边朋友的不同命运和遭际可以说是拓宽渔山视野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澳门学道时,吴历又作了如下两首诗,分别是《澳中杂咏》第16首:
虹见来朝狂飓起,吞舟鱼势又纵横。
不知九万风涛去,归向何人说死生?
(谓罗先生到大西矣。)
和第29首:
西征未遂意如何?滞澳冬春两候过。
明日香山重问渡,梅边岭去水程多。
(柏先生约予同去大西,入澳不果。)
第16首是渔山为怀念返回欧洲的耶稣会士“罗先生”而作,第29首是渔山为自己未能陪同柏应理前往欧洲,只好滞留澳门学道之事而感慨。前者描绘了诗人想象中海上旅程的万般险难,表达了诗人对“罗先生”经历这番险象环生的海上航程的担心和挂念,同时也透露出渔山对这种海上航行带有一种新奇的想象。这里的“大西”指西洋欧洲。“九万风涛”与前面的“天涯九万程”同义,均指旅途之遥,超乎想象。吴历在澳门学道时,与西洋教士朝夕相处,身边不乏往来于中土和西洋之间的教士,那么他对欧洲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的旅程远近以及所需的时间,不可能毫无所知(“计程前度大西去,今日应过赤道旁”,《澳中杂咏》其十);对于远行日本和远行大西,吴历均以“九万”路程描摹之,可见这只是诗人对海上旅途的一般描绘,并不反映其对二者地域距离中国远近的认知。吴历的好奇心在于,“不知九万风涛去”之后,吴历继续发问,“归向何人说死生?”他想象罗先生到达欧洲之后,会向什么人讲述基督宗教对生死问题的解答?后者则表达了渔山对自己未能如愿前往西方欧洲的遗憾心情。这两首诗都表明事实上吴渔山向往大海另一边的那个未知的新世界。他没有将眼光局限于“中华帝国”之“界内”,而是敢于放眼未知的地区和领域,具备探索未知新世界的好奇心和勇气。
二、《圣学诗》:西方他者(基督宗教)的形象
《圣学诗》作为《三巴集》主要的天学诗,记录了吴历在三巴静院的修道生涯,体现了他对西方基督宗教的感悟和认知,构成了吴历在三巴静院所认识的“西方他者”。具体而言,这个西方他者主要包括对人生终极问题的解答、对待西圣和基督宗教教义三方面的内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最有特色,能解答吴历之所以皈依天主教的问题。
吴历少年时代经历明清易代之变,持守遗民气节,无意于仕途,终生不仕;跟随明遗民学者陈瑚学儒、随钱谦益习儒、向王时敏学画、向陈岷学琴,试图通过对艺术的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思想上早已有出世倾向,在行为实践上一度亲近道教风俗习气。在家乡常熟虞山一带,青年渔山曾一度崇尚绮黄,吟咏和描画采芝,多画采芝图,如为虞山处士张春培岑蔚居而作的《岑蔚居产芝图》(1659)、《采芝图》(1664)、《九芝图》等。“采芝”主题隐含对长生不老药的寻求。这正是当时包括渔山儒学师陈瑚在内常熟一批明遗民的癖好。采芝图表明青年吴历对以道教方法寻求长生之术具有兴趣①Yao Ning, “The Painting Fungus Growing at the Cenwei Residence 岑蔚居产芝图 (1659) of Wu Li (1632—1718) and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His Early Years,” accessed November 2, 2016, http://www.doc88.com/p-2002062548786.html.。渔山母亲1662年卒,渔山禅友默容和尚和儒学之师陈瑚分别于1672年和1675年离世,渔山之妻亦亡于17世纪70年代。正在吴历至亲师友相继去世的17世纪70年代,吴历与欧洲耶稣会士柏应理和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交往,后皈依天主教,在澳门三巴院的学道经历则更坚定了吴历的天主教信仰。宗教信仰的转变使吴历首先对自己早年梦想长生不老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驳。这体现在《澳中杂咏》第13首诗中:
浪绕三山药草香,如何得误几君王?秦时采剩今犹绿,药自长生人自亡。
不仅如此,信奉天主教之后,吴历自觉地将自己早年对长生的追求转向了对基督宗教天国的企望。《圣学诗》中,有17首诗的诗句中提到或隐含、描绘了天国,如:
“从今帆转思登岸”(《佚题》十四首其二)
最高之处府潭潭,眷属团圆乐且耽。”
(《诵圣会源流》十二首其八)
“最高之处府潭潭,眷属团圆乐且耽”,由这些诗句对天国的描写,再联系《澳中杂咏》“归向何人说死生”的诗句,显然,对吴历而言,基督宗教教义的天堂论,即对死生问题的解答是吸引吴历入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能解答他长期以来对死生问题的思考和困惑。
17世纪80年代正是礼仪之争兴起的年代,当时一些中国天主教徒与欧洲在华传教士讨论中国古籍中“上帝”“天”之名,严谟为此撰有《帝天考》(据钟鸣旦考证,《帝天考》约成书于17世纪80年代①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台北:光启出版社,1998年,第17—21页。)。而当时正在澳门学道的吴历,似乎并未直接介入这场讨论,《圣学诗》中屡屡出现“主”字汇,“上帝”则无;可见吴历关心的重点或许并非天主之名,而是基督宗教所允诺的那个永福之地—天国。利玛窦(Metteo Ricci,1552—1610)说,“夫天堂大事,在性理之上”②利玛窦:《畸人十篇》,载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2页。,列出天堂六福:圣城、太平域、乐地、天乡、吉界、寿无疆山。吴历的诗所描绘的天国之抽象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
吴历相信人最后必将受到天主的审判:“万罪从来不足怜,经言恶表判尤严”(《佚题》十四首其七),只有“从今帆转思登岸,摧破魔波趁早风”,离开“世海”,离开尘世,破除魔鬼设下的障碍,扭转驰向地狱的方向,“头回向九天”,奔向基督宗教宣扬的天国,才可能享受到永恒的福祉:“永福在高天,人生非漫然。”得升天国之永福之地犹如回到故乡:“梓里原来永福庭”;也只有在这个天国,人才能脱离尘世的牵绊和魔鬼的魔障,做到“一身由我主,谁遣受拘牵?”(五绝二首其二)表明吴历在归信天主教之后,在天国允诺中找到了解答人生终极问题的答案,自觉地将早年对长生的追求转向对基督宗教天国的虔信和企望。
总而言之,《三巴集》显示西方他者形象的产生主要基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或者说是他者形象源与他者形象塑造者这二者的原因。客观上,西方他者的形象源—澳门深受葡萄牙文化影响,异于内地的风物志、远西地域(尽管只是想象中的)、基督宗教这三者对吴历来说均为“异者”,超出吴历本人旧有的经验和知识范围之外,因此作为他者形象的材料来源被诗人写入诗歌。主观上,西方他者形象的塑造者—吴历首先在心理上具备纳故迎新的精神;其次,作为一名神学院的神学生,吴历具有为这一西方他者塑形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必要性。同时,吴历拥有高超的文学创作才能,故能撷取以上三者之异而创作新诗,在这些天学诗中塑造了鲜明的西方他者形象。
三、《三巴集》所描绘的西方他者形象的意义
吴历在澳门不能直接描绘他从来没去过的西方,所以《三巴集》里的诗歌反映的只能是吴历眼中经过当时澳门这一中西文化交会的前沿地“折射”了的西方(《澳中杂咏》),以及他通过在澳门三巴静院学道之后对天主教的初步认识(《圣学诗》)。前者的“西方”形象呈现的是部分的西方外形,后者的西方则是书斋里宗教修士对西方精神内核所做的理解和想象,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澳门学道时期吴历对他所经历和理解的西方的描绘,就是《三巴集》笔下的西方形象。这各个部分看似零散、杂糅,却又是一个统一体,代表17世纪晚期一个心灵开放的中国人睁眼看外部世界时对“西方”的初步概念和印象,当他从澳门将这个西方形象带回中国内地时,会在他所属的江南教区进一步引起回音和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