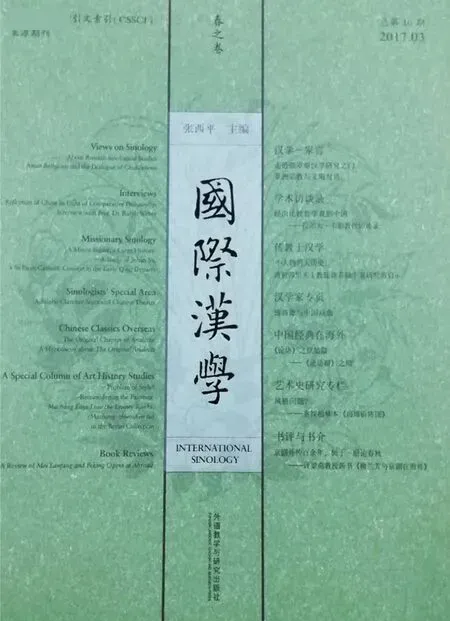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基督教情结与中西宗教比较研究*
□
引言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43年来到香港以后,自1861年至1876年的16年时间里,他先后翻译了儒家十三经中的十经。1875年,理雅各受到语言学和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Fredrick Max Müller, 1823—1900)的邀请,到牛津大学担任首席汉学教授,讲授汉语及中国典籍②Helen E.Legge, 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p.243.。后又应缪勒的邀请,编译《东方圣书》(The SacredBooksoftheEast)系列中的《中国圣书》(TheSacredBookofChina)。《东方圣书》是缪勒为研究世界各国宗教而主编的一套世界宗教系列丛书,按缪勒的要求,其《中国圣书》卷要收集中国本土宗教经典的英译文,于是理雅各决定在《中国圣书》中编入《尚书》《易经》《诗经》《礼记》的部分译文,并增加《孝经》《道德经》《庄子》的全译文。自1877年至1879年两年间,他陆续完成了《中国圣书》的编译工作。理雅各之所以在《中国圣书》中增加《易经》《道德经》《庄子》,无疑是出于译介中国道教的考虑;在《中国圣书》中选编《书经》,当是为了通过书中的“天”“帝”“上帝”等神祇,来追索我国先民的至上神以及多神信仰,选编《礼记》与《孝经》,则是为了从其中对王室及平民宗族祭祀的风俗礼仪中,窥视儒教教义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实践状况;而至于《诗经》,理雅各认为,这不仅是一部关于社会、道德的儒家经典,同时又是一部真实描绘中国先民信仰状况的宗教经典,起码《颂》中的诗篇即是如此。1879年,理雅各分别选取了1872年《诗经》全译本的《风》《雅》《颂》部分内容,并将其以《诗经:其中所有的诗篇都说明诗篇作者及其时代的宗教观和宗教习俗》(TheShihKing orBookofPoetry:AllthePiecesandStanzasinItIllustratingtheReligiousViewsandPracticesofthe WritersandTheirTimes)之书名编入《中国圣书》。《中国圣书·诗经·商颂》部分的前言认为,《诗经》中的《颂》明显是宗教性的①James Legge, “Preface to the Ode to the Temple and the Altar,” The Sacred Book of China.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79,p.299.,而《风》《雅》中也有宗教内容。综观理雅各整个中国典籍翻译历程,不难见其高度的宗教自觉性。其1876年前的儒家九经翻译,总的特点是为了认识古代中国和证明“上帝”在中国古代宗教中的存在,以服务于其传教目的;后因受到缪勒科学宗教观的影响,其宗教态度有所变化,开始对中国宗教的认识尽量“不带有译者的任何个人色彩”②James Legge, Preface to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79, pp.xxiii—xxiv.。但是,客观地看,其所浸润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宗教态度和目的是一贯的,其基督教至上的宗教观念也始终没有改变。在理雅各看来,儒家典籍实质上就是宗教经典,翻译儒家典籍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西方介绍儒教,利用儒教证明基督教教义。1789年,理雅各编译《中国圣书》时于其中保留《书经》《易经》《礼记》《孝经》,删除《春秋》和《诗经》的《国风》《大雅》《小雅》的大部分内容,而增添《道德经》《庄子》,其选材标准表现出了较明显的学科性质,宗教态度趋向客观。但这在名义上是受缪勒之托进行的中国宗教研究,本质上则是两人在中国宗教研究上的“合谋”;表面上编译《中国圣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世界宗教比较研究,但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突出基督教一神论的优越性。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中的宗教目的进行分析。
一、于中国原始宗教中植入基督教教义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宗教目的。他在1847年5月5日的一则日记中说,“原则上,在这个国家(本文作者注:指中国)的不同宗教和伦理体系……(儒教、道教和佛教)必须全部揭开……其教义必须得到揭示,这些教义就是他们的原则。其中的真理必须与谬误分开……远古时期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值得研究的宗教和伦理?儒教究竟是什么样?道教究竟是什么样?我要彻底、准确地弄清楚这些问题”。③Lauren Psfister, Some New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James Legge: Part I.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1990, XII, p.33.可见,寻求中国本土宗教及其教义,反过来为传教服务,是其中国经典翻译的根本宗旨。杰拉特(Norman J.Girardot)认为,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过程,实质上是在东方寻求上帝存在的过程,其基本观点是反东方宗教的④Norman J.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235—240.。综观其整个翻译过程,理雅各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证明上帝在中国本土宗教中的存在。在《中国圣书》第四卷《诗经》译本的前言部分,他对“帝”的英文译名做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帝’就相当于希伯来语的‘埃洛希姆’(Elohim)和希腊语的‘神’(Theos),因此应该翻译成英文的‘God’。”⑤James Legg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London:Henry Frow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rehouse, Amen Corner, E.C.(1939年伦敦会香港影印所影印本),Vol.IV—Part I,Part II: p.132.他把“帝”和“God”等同,意欲向英国读者提供“God”无处不在的证据,这对巩固西方民众的基督教信仰,无疑是有益的。他对《诗经》中的“上帝”的崇高性和无上权威性做了大量的介绍和分析:
(中国的)上帝似乎是专门统治人类和世界的。他为所有的人指定粮食为食物。他还特别监视被称为‘天子’的各国君王的行为。如果君王敬仰上帝,并出于对他的敬畏而笃行其职,践其志,法其道,上帝就会保护他们,他就会乐于闻君王的祭品的馨香,并保佑君王及其臣民富裕兴旺。如果君王对上帝不敬,政治上玩忽职守,他就降罚于他们,夺其位而另命他人。⑥Ibid..
有时,上帝似乎很可怕,天意因此改变。天灾被认为是由上帝引起的,因此,天被认为无同情心。但这是他的奇异行为,是他的裁决,他是想借此让人们悔罪。他并不憎恨任何人,引起灾祸的实际上并不是他,而是因为人们抛弃了古人正确的统治方法。上帝在给人生命的同时,也给了人善良的天性。(同上)
“悔罪”的说法听起来很像是基督教的布道,把中国经典中的“帝”和“上帝”说成像“God”一样,是奖善惩恶的,这对宣扬God崇拜,强化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是有利的。本着“帝”“上帝”就是“God”这样的认识,理雅各在翻译中把二者一律做了等化处理。《诗经》中“帝”共出现43次,其中《国风》中出现1次,《雅》《颂》中出现42次。除了《国风·君子偕老》中的“帝”被译作goddess之外,《雅》《颂》中42处全部被译作大写的“God”或小写的“god”。有时候,译者还禁不住把《圣经》语言直接用在了译文当中。例如,《大雅·大明》和《鲁颂·閟宫》中的“上帝临女”这一诗句,本来是武王鼓励三军将士的话,指的是周室先王(上帝)已经到来,正在高天之上俯瞰着将士们,在冥冥中监视和保佑着他们。理雅各却将此译作“God is with you”。其实“God is with you”与“上帝临女”二者的文化内涵相差很大。前者意思是说,一个信仰基督的人,就会成为上帝的选民,他的灵魂就会得到救赎,上帝会永远和他在一起,给他指引和帮助。这句译文足以使英语读者误认为《诗经》当中有本来属于他们的“God”和基督教教义。
1876年,语言学和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委托理雅各翻译属于《东方圣书》一部分的《中国圣书》,这使理雅各有机会对《尚书》中“帝”和“上帝”的翻译进行修改。虽然《东方圣书》的编纂宗旨是科学地研究东方宗教,理雅各却在《中国圣书》的编译中,更多了些基督教刻意的成分。1865年他在《中国经典·书经》译本中,把“帝”字都是按对尧舜的尊称译作“emperor”,这是公允的,这次《中国圣书·书经》编纂过程中,他却趁机把其中77处“帝曰”的“帝”字全部改译成“Tî”。例如,《益稷》:“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1865年译本作:
Yü said, “Oh! Be careful, O emperor, of the manner in which you occupy the throne.”The emperor said, “Yes.” Yu said, “Find your rest in your resting-point.Attend to the springs of things, study stability; and let your assistants be upright:—then will your every movement be greatly responded to, as if the people only waited for your will, and you will brightly receive gifts from God.Will not Heaven renew its appointment of you, and give you blessing?”《东方圣书》改译为:
Yü said, “Oh! carefully maintain, O Tî,the throne which you occupy.’ The Tî replied,‘Yes;’ and Yü went on, ‘Find your repose in your (proper) resting-point.Attend to the springs of things; study stability; and let your assistants be the upright:—then shall your movements be grandly responded to, (as if the people only)waited for your will.Thus you will brightly receive (the favour of) God;—will not Heaven renew its appointment of you, and give you blessing?”
他在《东方圣书》的前言中说:
在把“帝”和“上帝”改译之前,我曾考虑是否把《书经》中的“帝”及其尊称“上帝”全部都翻译成“God”(《诗经》也做同样处理)……二十五年多以前我就认定,汉语的“帝”就相当于我们的“God”,“上帝”亦复如是,只是多用了一个“上”字,即“至高无上”的意思。因此迄今为止翻译和出版的《中国圣书》的各书中我把这两个名称都应该翻译成“God”,我的这一观点从未改变。①Preface to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p.xxiii.
我现在之所以不再把所有的“帝”都译作“God”,是考虑到,以我的理解,《东方圣书》的编纂宗旨是不把这些译本都染上译者个人观点的色彩。(同上)
在此,理雅各实质上是在借用科学比较宗教学的名义,暗中进一步在中国经典中植入基督教成分。他心里明白,通过在前言中言明“帝”和“上帝”都是“God”,尽管正文中把“帝”翻译成“Tî”,读者仍认为“Tî”就是“God”。因此《中国圣书·书经》的翻译实际上是更加基督教化了,其客观性竟不及1865年的首译本。
其实“帝”与“上帝”和“God”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区别是赫然分明的。
“帝”和“上帝”本来是我国典籍中原有的概念。这在《尚书》中写得十分清楚。《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尚书·舜典》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至此尧舜被并称为“帝”。“上帝”是商代的至上神。《尚书·汤誓》:“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这里的“上帝”很像是天的主宰。古人以地推天,认为地上有人帝主宰人间事物,天上则有上帝主宰自然万物,上至日月星辰、风云雷电、阴晴雨雪、四季轮回、寒暑交替,下至山川河流、万物生死,等等。秦汉时期,国家所祭祀的上帝有五位,即黄帝、炎帝、青帝太昊(伏羲)、白帝少昊和黑帝颛顼。有的学者认为,上帝就是古代君王的祖宗神。“上帝”开始未必是“天上”的帝,“上”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如“上古”的“上”,指的都是“远古”。随着人们宗教观念的演变,远古的“帝”被认为灵魂到了天上,就成了天上的帝①李申:《宗教简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页。。所以,无论如何,“上帝”并不等同于基督教的“God”。前者是多神,是祖宗神,而后者是唯一神,是宇宙神;二者之间的性质也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理雅各把“God”植入中国经典的做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我国宗教界翻译《圣经》,也随着这种做法,把“God”回译成“上帝”。这足以在中西方民众中把“上帝”和“God”二者混淆。几百年间,不仅使西方基督徒误以为中国自古就信他们的“God”,也使很多不了解儒家经典的中国人误以为“上帝”是来自西方的《圣经》,而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本土神。由此可见,翻译上的这种中西核心文化概念上的故意混淆,数百年来以讹传讹,其所造成的宗教、社会影响及学术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二、“天”的基督教化
儒教之“天”,自始就有。“天”在《今古文尚书》出现301次。如《尚书·尧典》中,尧问群臣:“有能典朕三礼?”“三礼”就指祭祀天神、地示、人鬼的礼仪。《尚书·甘誓》中夏启征伐有扈氏前告诫臣子说:“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供恭行天之罚。”其中“三正”也指天、地、人之正道。“天之罚”一说,可见天的权威远在君王之上,已经被神化。《尚书·汤誓》中,商汤号召子民推翻夏桀统治,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他同样把天奉为最高神。《诗经》中“天”神共出现过159次,如《十月之交》:“天命不彻”;《板》:“昊天曰明”;《荡》:“天生烝民”。可以看出,古代原始宗教中的天,已经具备了人格神的某些特征。
然而,儒教之“天”与基督教“God”虽然都是神,但二者并不相同。其一,“上帝”是唯一真神;“天”则是众神之主,有一个神组成的体系。在周代,“天”是高于上帝的。《孝经·圣治章第九》:“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皆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效乎?”因为后稷是宗周的始祖,所以周公以后稷配天,在远郊祭祀后稷;文王为周公之父,只能以文王配上帝,在明堂,即近郊祭祀文王。邢昺《孝经·疏》云:“旧说明堂在国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为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远为严。五帝卑于昊天,所以于郊祀昊天,于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文王配明堂,义见于上也。”②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4—47页。在上帝之下,还有主宰一方土地的神及主宰山川河流的神,等等。和犹太教、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亦是典型的一神教:在基督徒心目中,“上帝”是唯一真神。据《圣经》记载,上帝曾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儒教则是多神教,它不只是崇拜天,同时还崇拜山川河流等自然物。不过,儒教的多神崇拜是以“天”为主要崇拜对象的,正如董仲舒所说,“天”是“百神之大君”。其二,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天”则是人类的祖先。按照基督教经典《圣经》的教义,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当初造人时,是用泥土首先造出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后来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后来成为亚当之妻的夏娃。所以,“上帝”与人类之间原不存在任何血缘上的联系。人类中唯后来成为基督教教主的耶稣,是“上帝”通过某种奇特的方式使玛丽亚感受“圣灵”怀孕而生,是“上帝”的独生子。然而,即便如此,“上帝”还是命令约瑟娶已经身怀耶稣的玛丽亚为妻,以便做耶稣名义上的父亲,以此来掩盖其事实上的父子关系的真相。这表明,“上帝”是羞于男女交媾而以之为罪过的,也就是说,“上帝”是以人类的生命为一种罪孽的。相反,儒教之“天”作为人类的祖宗神,则与人类有密切的血缘联系,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天”就是“人类之曾祖父”;同时,“天”还是“群物之祖”。因此,“天”绝不以人类生命为一种罪孽;他不但生育了人类,还为人类的合理生活创造了一切必需的条件:“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①董仲舒:《春秋繁露》。。其三,基督教徒实在的“上帝”是耶稣;儒教徒实在的“天”是圣人。按照基督教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信条,耶稣是“上帝”的化身。与耶稣的身份约略相当,儒教徒“实在的天”则是圣人。和耶稣一样,圣人亦是既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的,唯圣人的神性不像耶稣那样体现在其原本与神(“上帝”)为一体,而是体现在其有“先知先觉”。圣人是奉“天”之命以化天下。圣人之化天下,犹耶稣之以殉难为人类赎罪,唯前者旨在使“天下归仁”而生生不息,后者则旨在使人类得救而入于天国。
理雅各在《中国圣书》寻求“God”的同时,他注意到了“天”的神性。但在翻译的时候,他明显感到了儒教中的“天”与基督教“God”之间的不同,他感受到“天”神在儒教中的权威很高,乃至高于“上帝”。但若把“天”译作一个单独的神,那么这就意味着儒教中还有一个高于“God”的神,而“God”在基督教中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神,是宇宙中的至高神,哪里容得下另一个更高神的存在。于是,他采取了前言中先把“天”和“God”的关系先作说明,而在译文中把“天”另译作“Heaven”的策略。在《诗经》译本和《东方圣书》前言中,他把“天”(Heaven)说成最高神,而“上帝”(God)是“天”的人格化名称:“Heaven被用人称称谓时就叫‘God’。”②Preface to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p.xxv.这样,Heaven实际上在译文中就和God统一起来了。理雅各在《中国圣书·书经》译本中用Heaven和heavenly两词翻译“天”,凡301次,其中用Heaven 翻译“天”295次。例如,《盘庚中》:
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
You do not consult for a distant day, nor think of the calamity that must befall you (from not removing).You greatly encourage one another in what must prove to your sorrow.Now you have the present, but you will not have the future;—what prolongation of life can you look for from above? My measures are forecast to prolong your (lease of) life from Heaven;—do I force you by the terrors of my power? My object is to support and nourish you all.
在理雅各的译文中“Heaven”有与“God”同样的人神合一性。如《诗经》译文反映了Heaven的一些特性:其一神秘性。如《十月之交》:“天命不彻”:The ordinances of Heaven are inexplicable;其二明辨性。如《板》:“昊天曰明”:Great Heaven is intelligent;其三化育性。如《荡》:“天生烝民”:Heaven gave birth to the multitudes of the people;其四权威性:如《大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Heaven surveyed this lower world; And its appointment lighted [on king Wen];其五仁慈性。如《閟宫》:“天锡公纯嘏”:Heaven will give great blessing to our prince;其六惩罚性。如《抑》:“天方艰难,日丧厥国”:Heaven is now inflicting calamities / And is destroying the State;《 桑 柔 》:“天降丧乱”:Heaven is sending down death and disorder;《瞻卬》:“天之降罔”:Heaven is letting down its net.
“Heaven”这样的“天”神在整个《诗经》中共出现159次,其中《国风》中15次,《雅》《颂》中144次,理雅各译文中同样使用了159次“Heaven”或“heavenly”“heavens”(后二者仅有数例)来翻译“天”字。他把“Heaven”的首字母大写,其用意是把“天”神化,追求与“God”的首字母大写同样的效果。虽然在儒家经典中“天”和“帝”二者乃同质异名,很难区分,但“天”和“上帝”并非“God”和“Jesus”那种两位一体的关系。理雅各一方面把“天”和“God”统一,一方面又不把“天”译作“God”,可见其用心良苦。其意在于避免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创造一个高于God的神,而在其中追求基督教中Lord与Jesus之间两位一体的关系;抑或是在显示中国古代宗教的原始性,亦未可知。
三、揭示中国古代宗教的多神等级体系
尽管理雅各在译文中使用了“Heaven”一词,但在他的心目中,“天”神实际上与“上帝”(God)是同一个神,而“上帝”才真正居于万神之主的地位。他对前言中出现的众神做了这样的说明:“中国古人就是这样信仰上帝,也是这样想象上帝的。他们也信仰上帝率领下的诸神。这些神,有的掌管山川河流,有的居住在上。其实,几乎所有的东西身上都有守护神,每一个地方都有神,人们必须随时随地保持善良的心和良好的行为。”①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Vol.IV—Part I, Part II: p.132.他提到天体神、河神、山神、旱魔、地神、战神、路神,等等。在这神的王国中,“帝”是最高“神”,其次是日月星辰神,再次是山川河流神。祖先的灵魂也有无上的权威和力量。这些神都能降福祉,也能降罚于后代。这样,理雅各把中国先民的“神”依照希腊罗马神的体系模式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上尊下卑、各司其职的神的体系。《时迈》的翻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
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理雅各将其译作:
Now is he making a progress through the States,
May Heaven accept him as its Son !
Truly are the honour and succession come from it to the House of Zhou.
To his movements, All respond with tremulous awe.
He has attracted and give n rest to all spiritual Beings,
Even to [the Spirits of] the He , and the highest hills.
理雅各认为这首诗反映了周人宗教中神的等级观念。他在1879年《中国圣书》中对这篇译诗加注说:
“所有的神”实际上就是“天”神之下掌管大自然的“百神”,尤其是指周土中众河神和山神。诗中提及黄河五岳之神,因为他们既然对武王的作为满意,其他河神山神自然也就满意了。(‘All spirits beings’is, literally, ‘the hundred spirits,’ meaning the spirits presiding, under Heaven, over all nature,and especially the spirits of the rivers and hills throughout the kingdom.Those of the Ho and lofty mountains are mentioned, because if their spirits were satisfied with Wu, those of all other mountains and hills, no doubt, were so.)②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p.318.
在此,理雅各所排列的神的等级是清楚的:天神至高,大河大山之神次之,小河小山之神再次之,武王就更在这些自然神之下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理雅各用这首诗来证明“上帝”(God)是众神之主,实际上已经混淆了“天神”Heaven和“上帝”God之间的区别。这反映出,理雅各在基督教和中国古代原始宗教之间求同的心理是如此迫切,以致自己在一神论原则问题上都发生了矛盾。
不仅如此,理雅各还在诗篇中极力寻求耶稣的形象。他以《生民》中“履帝武敏歆”证明作为周人最高神的后稷是上帝的儿子: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The first birth of [our] people,
Was from Jiang Yuan.
How did she give birth to [our] people ?
She had presented a pure offering and sacrificed,
That her childlessness might be taken away.
She then trod on a toe-print made by God ,and was moved,
In the large place where she rested.
She became pregnant; she dwelt retired;
She gave birth to, and nourished [a son],
Who was Hou-ji.
这实际上是他在暗示稷与耶稣之间具有相似性。他巧妙地用后稷传奇的身世和神的地位,与耶稣的传奇身世和地位进行类比,只是没有明言耶稣的名字而已。在这里,译者的基督教情结又一次隐约流露出来。他引《大雅·崧高》一例,说明申甫两个周臣是山神所生: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Grandly lofty are the mountains,
With their large masses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From these mountains was sent down a Spirit,
Who gave birth to [the princes of] Fu and shen.
Fu and Shen,
Are the support of Zhou,
Screens to all the States,
Diffusing [their influence] over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kingdom.
关于甫和申,郑玄注:“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贤知入为周之桢干之臣。”①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07页。对此,现代诗经学似乎也有分歧。如程俊英称甫应指吕侯,申即周宣王舅母申伯②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5—488页。;而周振甫则认为,甫、申分别为甫侯和申伯,两人同为周宣王大臣③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73页。,从郑氏。关于“生甫及申”一句,《毛诗正义》说:“又解四国,而独言申、甫者,岳降神灵和气,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申伯和甫侯是周臣,按照殷商以来的观念,王为天子,尹吉甫作颂,不敢称臣为天之子,因为臣只能是大山之神降和气所生。这又一次印证了理雅各所描绘的神的等级体系。从译文来看,理雅各的笔下出现了不易令人觉察的改动:“从大山派来一个神灵,生下了申和甫。”这里由于用的是被动语态,派神灵者没明确为谁,但可推断出派神者就是上一级的神—上帝。就是用这种方式,理雅各为中国原始宗教中的诸神编织这样一个等级体系:上帝—日月神—星辰神—大地神—黄河五岳神—小河小山神—其他小神—祖先神。其中祖先神也有分别,先君王由最高神上帝所生,已故臣子由山河神所生,等等。而像后稷、文王、武王这样的祖先神虽然为上帝所生,但也要侍奉自然神。从翻译角度看,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也是十分有意义的现象,虽然在表面上看翻译相当忠实,但实际上,译者通过前言、题解、正文、注释等多种途径,在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着十分隐蔽的改写。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四、基督教的崇高性与中国古代宗教的原始性
理雅各后期的中国经典翻译与当时刚刚兴起的比较宗教学有密切关系。1875年,理雅各结识了比较宗教学先驱麦克斯·缪勒,缪氏盛情邀请理雅各担任牛津大学首席汉学教授①Helen E.Legge, op.cit., p.243.。麦克斯·缪勒于1870年建立比较宗教学,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并建立了比较宗教学学科。比较宗教学受当时问世不久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颇深。1859年至1869年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宗教学研究在高扬理性、提倡科学的时潮中,引入进化论以解释宗教。缪勒提倡用“进化的研究法”研究宗教,并标举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的比较研究法。此中的“科学”,意谓不相信先验的、天启的论断,而以归纳方法来考察宗教;其所以是“历史”的,是因为它将人类的信仰行为安置在先后的时序中—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以产生未来的一连串连续、有意义的过程;而“批判”,是指面对资料的一种论证态度;所谓“比较”,是认为这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比较宗教学自此立足于“非宗教”的立场,而且在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中,偏向科学这一边。以进化论立论的比较宗教学观点认为:宗教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一个发展的有机体。进化论的人类学理论主张:人类文化是一个从低级形式发展为高级形式的连续系列—虽然并非直线式的进化。搜集进化过程中的“遗存物”, 能使我们透过研究现代的“原始形态”,于其中知道史前的基本状态。“遗存物”是被进化潮流遗留下来的文化或社会要素—宗教要素是如此。所以如果能在未开化民族中找到某种属于“宗教的”概念,就可以推论这是人类宗教的进化过程中,属于较早期宗教的阶段。
《中国圣书》的翻译与评注表明,理雅各在其后期翻译活动中宗教观有了很大转变,开始实践这种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他通过研究和翻译儒家十经和《道德经》《庄子》等中国经典,在中国先民的宗教信仰中找到了上帝。这使他十分高兴。这是他出于自身的宗教情感所愿意看到的结果。但“God”作为宗教信仰进化最高端的至上神在中国先民的原始信仰中存在,证明了东方宗教的先进性,这是他一生培养起来的基督教情感所无法接受的。在其宗教情感的深处,理雅各对东方宗教的鄙夷态度使他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原始宗教比西方的基督教更为发达,所以他在《中国圣书·诗经》中对诗篇的翻译没做什么改动,意在使它继续成为中国古代宗教的原始形态的佐证。他认定,中国先民宗教的特点是万物有灵论,盲目崇拜,与基督教的一神论相比,尚处于低级的自然神论原始宗教阶段,而基督教则已经发展到了一神论的高级阶段,二者的高下之分不言自明。他在《儒学与基督教》中说,中国先民像古代的亚伯拉罕一样,不完全懂得上帝的本质。《圣经》中的逐步显灵认定,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可能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留下证明,即使这一证明很快被其他坏的影响歪曲。任何文本,包括汉语原文本,都不准确、不纯粹,也不完善。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完全否定这些文本的真实性。中国经典中的“帝”和“上帝”就是“God”,我们的“God”,真正的“God”②James Legge,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London: Trübner & Co., 1877, p.12.。他的这种基督教优越感,在其孙女玛丽·D.理雅各教授那里得到了证明。她说:“我祖父理雅各一直因为好基督教、恶儒家学说而受到责难。但它们一个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此感到气愤。”③Mary Legge, “D.James Legge,” an essay presented on Feb.4, 1951, to the Sino-Scottish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pp.10—11.理雅各对中国宗教原始性的发现曾经受到了缪勒的称赞:
在中国只有一个“God”,最初就是“天”,它的存在证明,自然上升为所谓诸神和与其唯一上帝“天”等同的地位,是不可能的。这是最古老、最强有力的证明。理雅各教授反对中国本土宗教根本上存在的万物有灵论和盲目崇拜,并将其源头直接追溯到我们所知的雅利安人古代宗教信仰起源。这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几乎无法怀疑,无论这些说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项最重大的发现,而奇怪的是,这一发现迄今没有得到多少重视,尽管也没有多少反对的意见①Lauren Psfister, “Some New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James Legge: Part I,”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1990, XII, p.46.。
最后,缪勒根据理雅各的“发现”下结论说:“(中国宗教的起源)肯定是自然的(宗教)。”②Ibid..这说明,理雅各的翻译,使缪勒乃至整个东方宗教研究都受到了影响。
结语
理雅各的翻译视野显然与其传教士身份和长期的神学生涯所养成的职业敏感有关。若说理雅各对《诗经》宗教内容的重视是出于感性的偶然当然不正确。应该说,理雅各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是一种充满理性的目的行为。在他看来,要在中国传教顺利,就必须首先彻底了解和把握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找适当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在《中国圣书》中证明中国古人宗教观念中神的存在,尤其要证明“God”在中国本土宗教中的存在,进而证明中国古人的“上帝”和基督教“God”的同一性。这些事情虽然三百年前的利玛窦等人已经做过,但在英语世界这尚属首次,而且这种证明对理雅各本人的传教工作来说,仍然十分重要。要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圣书》无疑是最好的工具之一,其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古人的信仰状况,而且还呈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的源流。因此,理雅各的《中国圣书》翻译不是公允而准确的宗教探索,他在我国典籍中植入基督教教义,一方面在中西宗教之间穿凿,另一方面故意夸大和篡改我国典籍中的有宗教意味的内容,借以贬低中国古代宗教,抬高基督教的地位,误导西方对中国信仰体系的认识,这有利于达到某种狭隘的宗教目的,却客观上为世界宗教思想史的研究设置了障碍。这说明翻译对于原文思想总是有各种遮蔽,西方建立在翻译文本根据之上的宗教思想史,也往往是不够真实的。
彼得·弗兰克潘与他的丝绸之路研究
彼得·弗兰克潘(Peter Frankopan)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公开演讲。2016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弗兰克潘的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2015)。翻开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你将发现,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关于欧洲或西方,而且关于中国和印度,它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它考察世界的变迁:货物和商品、宗教和信仰、暴力与疾病;它也关注以前被人忽略的那些方面,试图理解各个国家从古至今的起落兴衰,从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时代的意义。(李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