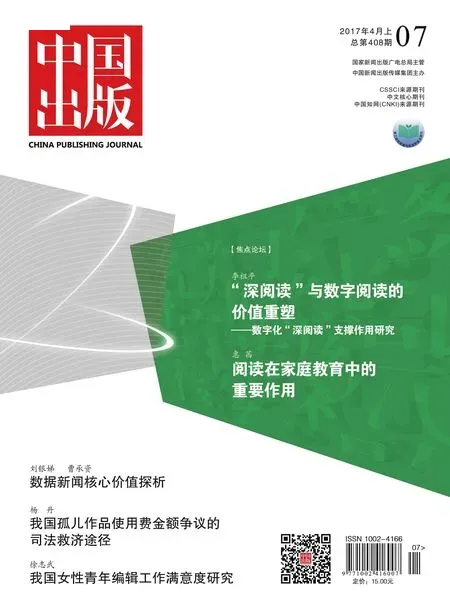新闻出版业版权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文│王 亮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近些年来,网络媒体侵犯传统新闻出版业版权的事件屡见不鲜,新闻出版业也曾试图通过集体合作以维护版权,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早在2005年中国都市报研究会总编辑年会上,就有20多家传统报业发布向网络媒体索要版权补偿的《南京宣言》,要求“坚决维护报纸的新闻知识产权。全国报界应当联合起来,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改变新闻产品被商业网站无偿或廉价使用的现状”。[1]但更多停留在纸面上,在实际操作层面不见下文。而且报业内部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一些报社要求网络媒体支付版权费,但也有媒体当时认为网络媒体的转发能扩大影响力,甚至有一位总编说“恨不得新浪、搜狐天天用我的新闻,唯一的期望就是注明出处”。[2]
2006年新闻出版业再次发起版权保护活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向全国38家新闻出版集团发布《发起全国报业内容联盟的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宣布要“共同制定向网络媒体提供新闻内容的定价规范,提高网络转载的门槛”,保护新闻出版业“自己的知识产权,让新闻内容回归应有的价值”。2005年、2006年报业开始进入寒冬期,它们在索取版权费问题上的态度越发坚定,《倡议书》提出:“我们身处在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每年,办一张综合性日报采编成本数以千万元计算;但当我们把优质新闻信息交给网络媒体时,得到的却只是象征性的区区几万元。付出与回报,何等悬殊!”新闻出版业对过去认为网络媒体的转载能提高影响力的看法进行了反思,“曾经我们还沾沾自喜,把自己最好的内容提供给网络媒体,期冀借助网络增加曝光率,显示自己的影响力。然而,当喧闹褪去,如今已是好好反思这一模式、重新审视内容价值的时候”。[3]但是,这一次集体合作仍然宣告失败,内容联盟的第一次理事会都没能召开。在这两次大规模的集体合作后,新闻出版业还组织了几次版权保护行动,如2014年《广州日报》《新京报》等媒体起诉今日头条侵犯其新闻版权。观察近10多年媒体版权案件,虽然一些案例中被侵权方在版权案件中胜诉,但整体来看,新闻出版业特别是新闻领域尚未建立起严格的版权保护制度。
新闻出版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建立严格的版权保护制度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新闻出版行业在版权保护问题上却陷入困境:尽管绝大多数新闻出版机构意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性,也试图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建立版权保护制度,但为什么整个行业却很难有效实现对版权的保护?既然严格的版权保护制度对行业成员有利,为什么行业成员不能共同努力实现该制度?如果说新闻出版业成员在版权保护问题上的态度不一致导致其无法建立版权保护制度,那么当成员意见一致后就能够建立版权保护制度吗?从集体行动理论出发,新闻出版业集团的成员在版权保护问题上的态度是否一致并不是决定因素,当它们态度不一致时自然无法建立版权保护制度,但即使它们态度一致,新闻出版业集团仍然难以建立版权保护制度。本文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对此进行分析。
一、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此书被誉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人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集团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成员所组成,集团也会追求集团自身的利益。这一点在涉及经济领域时尤为明显,既然个体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集团也会追求集团利益最大化。但是奥尔森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即使在实现集团目标后每个成员的利益都会增加,也不能认为成员会采取行动实现集团目标。奥尔森提出,“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所有人在实现了集团目标后都能获利,由此也不能推出他们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认为个人组成的集团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这一想法远非一个集团中的个人会有理性地增进他们的个人利益这一假设的逻辑推论”。[4]
个体之所以组成集团是因为集团可以增进共同利益,集团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的集合。个体参与集团以便获取集体物品带来的利益,但个体并不愿为集体物品支付任何成本。特别是当集团规模很大、集体成员很多时,每位成员都会有“搭便车”心理,希望由他人支付集体物品成本,自己获取集体物品的利益。正如奥尔森所说,“尽管集团的全体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但它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5]因此,集团成员的态度是否一致,不是影响集体物品供给的主要因素。如果成员在提供集体物品上的态度不一致,就没有必要组成集团。态度一致的成员组成集团以提供集体物品,但成员都想获得集体物品,却不愿支付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这就使它们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中。
影响集体物品供应的因素主要有:集团规模大小、获取第一批集体物品的成本、集体物品为成员带来的收益、是否存在能从集体物品中获得较高份额的个体。集团规模越大、成员越多,越难以提供集体物品。这是因为,一方面,集团规模越大,每个成员能从集体物品中获取的收益就越小。另一方面,集团越大,组织成本、协调成本随之增加,提供集体物品的总成本变大。获取第一批集体物品的成本越大,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就越小。集体物品为成员带来的收益越大,成员组织起来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会增加。如果有成员能获取较高份额的集体物品,即使该成员要支付较高成本,只要它从集体物品中获取的回报大于成本,与所有成员只能获得有限回报的集团相比,前者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更高。
二、版权保护的困境
新闻出版业在版权保护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新闻出版业希望通过集体合作提供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但是,在版权保护问题上,新闻出版集团在集团规模、集团结构、集体物品性质三方面的特点,使其较难提供集体物品。
首先,从集团规模角度看,在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上,新闻出版业是一个成员众多的大集团。小集团中成员数量少,每个成员可以获得集体物品中较大比例的收益。因此,即便由单个成员承担全部成本,小集团也可以在无须协议、组织、协调的情况下提供集体物品。换句话说,小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组织成本、交易成本较低。而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集团的组织成本、交易成本会逐渐上升,集团必须通过正式的协议、合同、协调才能获得集体物品。集团越大,成员数量越多,成员之间签订协议、合同的成本随之增加,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难度越来越大,集团的组织成本、交易成本随着集团规模扩大不断增加。
集团必须通过组织协调采取集体行动才能获得集体物品,无论提供多大数量的集体物品,集团都需要支付一定的初始成本,可以把这种成本看作提供集体物品的固定成本,只要集团通过组织来提供集体物品,就必须支付一定量的初始成本。集团的规模越大,这一初始成本就越高,第一批集体物品的成本也就越高,第一批集体物品的成本必然高于随后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成本。不管集体物品能带来多大收益,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越高,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难度就越大,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就越小。这进一步增加了大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难度。
奥尔森教授认为,有三个因素使得大集团难以提供集体物品:[6]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即使集团能够获得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其数量也远远低于最优水平。第二,集团越大,成员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它们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它们提供集体物品所支付的成本。第三,集团成员越多,组织成本越高,获得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越多。
在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上,新闻出版业是个成员数量众多的大集团,任何一个成员从版权保护中所获得的收益不足以使其有动力提供集体物品。按照国家版权局2014年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文字作品费用标准为每千字80~300元,转载所需支付费用更低。在司法层面,法院要求取证时将每篇侵权稿件单独立案,这进一步增加了版权保护的成本。比如2007年《新京报》起诉浙江在线,认为浙江在线网站使用《新京报》原创作品7706篇,杭州中院要求《新京报》将7706篇作品分拆立案,最终《新京报》由于诉讼成本太高、胜诉后收益太小撤回起诉。
其次,从集团结构角度看,在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上,新闻出版业缺乏能从集体物品中获取较高份额的成员,没有哪个成员能从集体物品中获得高额回报,导致成员缺乏提供集体物品的动力。在小集团中,某个成员能从集体物品中获取较高收益,即使由它独自承担集体物品成本,只要它从集体物品中获取的收益大于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它也会主动提供集体物品,其他成员通过搭便车而获取集体物品。这类似于博弈论中的“大猪小猪博弈”,大猪为获得高额回报而愿意付出劳动,小猪获得较低收益而坐享其成。
但是,在版权保护问题上,新闻出版集团中没有哪个成员能从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中获得高额收益,即便某成员深受侵权危害,但在目前政策法规条件下,它从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很小,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仍然超过从集体物品中获取的收益。除非它对这一集体物品有很强的偏好,愿意为提供集体物品而付出额外成本,否则该成员不会有动力提供集体物品。
最后,从集体物品性质角度看,在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上,新闻出版集团具有排外集团的性质。根据集团所要实现的目标,将集团分为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在相容集团中,成员数量越多,提供的集体物品越多,不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不会影响集体物品供给量。比如集团向政府要求税收优惠、贸易保护时,具有相容集团的特征。排外集团中,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是固定的,每位成员都要参与集体行动,不参与者会从参与者手中攫取集体物品。比如某一市场中的报刊试图集体提价,从提价中得到的回报是相对稳定的,每位成员都要参与这一集体行动,不参与者凭借低价优势从参与者手中攫取集体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排外集团中集体行动的成本更高,提供集体物品的难度更大。因为每位成员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不参与者,以便在对集体物品的分配中得到更大利益。
在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中,新闻出版业是一个排外集团。新闻出版业从版权保护中得到的收益是相对稳定的,实现版权保护需要每位成员的共同努力。新闻出版业集团作为大集团,成员数量很多,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很高,每位成员都可以将自己定位成不参与者,以便在集体物品分配中获得更高收益。而且,不同成员的态度和意图也不尽相同,有些成员重视版权保护,有些成员看中网络媒体转载带来的影响力提升。在成员态度一致时都很难提供集体物品,成员态度不一致时就更难以进行集体合作了。
三、解决版权问题的思路
从集体行动理论出发,可以在三方面着手解决版权保护问题:对个体进行选择性激励、建立元规范、调整新闻出版业市场结构。
首先,当集团没有动力提供版权保护这一集体物品时,不应继续对集团进行激励,而应将激励转移到集团中的成员,通过对能从集体物品中获得较高回报的成员进行激励,使其他成员产生提供集体物品的动力,将整个新闻出版集团动员起来提供集体物品。根据是否主动提供集体物品,可将集团分为三类:特权集团、中间集团、潜在集团。特权集团是指无须组织或协调,集团成员会主动提供集体物品的集团。中间集团指成员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不足以让成员有动力提供集体物品,成员只有通过合作、协调才能提供集体物品。潜在集团指集团成员人数众多,个体成员没有动力提供集体物品,成员也不会协调或组织起来提供集体物品。新闻出版集团在版权保护上是潜在集团,个体成员没有提供集体物品的动力,这时需要对部分成员进行激励,激励对象是能从版权保护中得到较高收益的成员以及对版权保护有强烈偏好的成员。通过对成员进行激励,使其从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收益高于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将集团从潜在集团动员为中间集团,促使更多成员参与集体合作。
其次,需要建立保护合作的元规范。新闻出版业集团在版权保护问题上是排外集团,每位成员都可能将自己定位于不参与合作者,以便在集体物品分配中得到更多份额。如果不能惩罚不合作者,集团将无法提供集体物品。但惩罚不合作者需要支付成本,集体行动中的成员不愿支付惩罚成本。如果成员们不惩罚不参与合作者,会有更多成员成为不合作者,集团就无法采取集体行动提供集体物品。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是惩罚那些宽容不合作者的成员,以此建立共同惩罚不合作者的行为规范,即对不惩罚不合作者的成员予以同样惩罚,这种规范叫“元规范”。[7]建立元规范后,整个集团可以持续保持合作。在元规范之外,观念内化、社会认同、成员身份、法律法规、社会声誉等都可以起到支持元规范运作的功能。拥有元规范的系统中,不惩罚的成本上升,在这种系统中惩罚机制可以正常运作,不合作行为下降,合作可以长久持续。
最后,调整新闻出版业市场结构,将大集团转变为中小集团。越是大集团,成员数量越多,集体合作的组织成本越高,每位成员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份额越低。而小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低,每位成员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份额更高,即使由一位成员承担集体物品的成本,其从集体物品中所获收益也足以抵消成本。因此,通过多种手段适当调整新闻出版业市场结构,将大集团转为中小集团,有助于新闻出版集团更有效地开展版权保护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