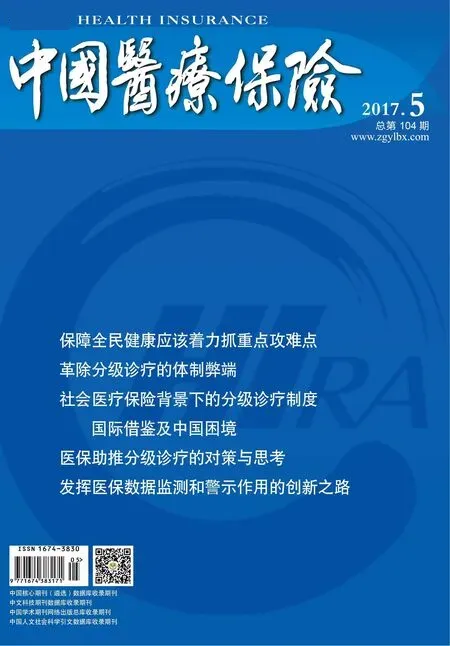社会医疗保险背景下的分级诊疗制度国际借鉴及中国困境
社会医疗保险背景下的分级诊疗制度国际借鉴及中国困境
赵 斌1李 蔚2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 北京 100716;2河北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石家庄 050061)
当前,分级诊疗制度广受关注。我国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方面也进行了诸多尝试,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为了解社会医疗保险背景下的分级诊疗制度的设置规律和内在要求,本文选择最早引入强制“守门人”机制的荷兰、已经引入经济激励“守门人”机制的法国,以及正在尝试引入“守门人”机制的德国作为典型案例,描述其机制设计,归纳机制有效运行的环境和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当前的思路并提出相关建议。
分级诊疗;社会医疗保险;“守门人”机制
近年来,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备受关注。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还将“分级诊疗”定位为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首。但当前,分级诊疗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分级诊疗概念的官方描述最早见于2006年《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号)中“建立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制度”。文献研究发现,当前学术界对于分级诊疗制度尚缺乏明确的界定。现有概念主要分两个思路:一个是从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服务体系,以及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间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角度进行定义;另一个则是从患者就医行为角度,强调患者逐级就诊的结果。欧美文献中,没有直接对应分级诊疗制度的概念,较为类似的概念就是垂直整合和“守门人”机制。其中,“守门人”机制表述为“Gatekeeper”“First contact”“Self-referral ”等,这一概念更多强调初级医疗保健医生(一般为全科医生)作为“守门人”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的核心作用,由其通过引导等方式帮助参保者实现合理就医,同时提高患者医疗服务连续性。可见,“守门人”机制与分级诊疗制度目的基本一致。因此,本文讨论分级诊疗制度的国际经验时,实际讨论的是其“守门人”机制。
传统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并不包含分级诊疗制度。但随着全民医保的实现,医疗费用的高速增长,专科医学服务的滥用等原因,使许多传统社会医疗保险国家开始讨论建立“守门人”机制的可行性,部分国家甚至开始进行尝试。
本文选择最早引入强制“守门人”机制的荷兰、已经引入经济激励“守门人”机制的法国,以及正在尝试引入“守门人”机制的德国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其机制设计,特别是机制有效运行的环境和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当前的思路。
1 社会医疗保险背景下的分级诊疗制度的国际案例
1.1 荷兰:强制的“守门人”机制
荷兰是最早建立强制“守门人”机制的西欧社会医疗保险国家,这源于其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面临的医保基金支付压力。在荷兰,全科医生是整个医疗服务网络的中枢,扮演全科和专科医学服务之间的“守门人”。每位公民必须选择一名全科医生签约。全科医生除注册人数已满或因距离原因无法服务外不得拒绝签约。参保者患病后,除非危急重症和特定专科医学服务,都需全科医生首诊,甚至部分急诊也由全科医生服务站(GP posts)首诊。当然,获取牙医、理疗医师、矫正治疗师和助产士的服务不需转诊,可直接就诊。
当前,荷兰共有接近9000名全科医生,多数为团体执业。全科医生主要提供全科医学服务,较少提供手术等治疗服务,主要手段为咨询和药品,但药品使用水平较低。晚上和周末等法定工作时间外的全科医学服务主要由全科医生服务站提供。这一服务站是全科医生的合作体。发展趋势上,尽管荷兰的全科医生仍扮演核心角色,但许多原本属于全科医生的业务被分散给了其他的初级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此外,执业护士也开始负责照顾许多特定类型慢性病的患者;专科护士也可在医生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开具处方药。
运行效果上,荷兰全科医生首诊病人的96%通过全科服务解决,仅4%患者转诊(Westert,Wammes,2014)。类似英国,荷兰“守门人”机制的最大问题是全科与专科医学服务之间协作困难,难以提供连续性医疗服务(Geelen,Krumeich,Schellevis et al.,2014)。
1.2 法国:经济激励的“守门人”机制
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就开始讨论引入“守门人”机制的可行性。
1998年,法国开始了首次尝试。当年,一个专业医务人员自治组织与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签订协议,试行转诊医生(Referring doctor)计划。全科医生自愿参加,并邀请病人与其自愿签订合同,患者承诺患病时到全科医生处首诊(急诊和部分特定医疗服务等除外)。作为交换,全科医生可获得医保基金额外的人头费支付,2001年为46欧元/人/年。同时,全科医生需遵守约定的服务价格、社会医疗保险付费、保存和管理患者档案、参与公共预防保健计划、遵循临床服务指南、按照社会医疗保险目录开具药品等一系列要求。但是,这一计划被大多数医务人员协会所抵制,患者参加也不积极,最终只有10%的全科医生和1%的患者参加,患者主要是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Dourgnon,Naiditch,2010)。
2004年,法国新的《健康保险法(2004 Health Insurance Act)》中引入了新的“守门人”机制,称为优选医生计划(Preferred Doctor Scheme),并废止了之前的转诊医生计划。新计划中,每位参保人需选择一名医生作为首诊医生,即优选医生(Preferred Doctor)。当然,妇科、产科、眼科、精神科和神经科医生服务可不经转诊,直接就诊。同时,16岁以下的儿童也豁免首诊。新机制的鼓励措施主要针对参保人。如果患者未经其全科医生转诊直接获得专科服务或去另一名全科医生处就诊,社会医疗保险报销待遇将从70%下降到30%。同时,特定医生的服务可额外加收17.8%到19.1%的费用,且医保并不补偿。对医生而言,若患者不注册将无法获得40欧元/人/年的建立和管理医疗档案的费用。同时,法国所有自愿医疗保险都不得报销未经转诊就医产生的额外费用,否则将征收附加税;对遵循基层首诊的患者,自愿医疗保险需要与基本医保配合实现全科和专科医生诊疗费100%报销,政策范围内用药和检查95%报销,同时必须涵盖两种重要的预防服务。
这一计划的运行情况较好。依据随后的评估研究,2007年81%国民签约了优选医生,其中99%为全科医生,2006年70%的一般医疗保险基金(CNAMTS)患者经优选医生转诊(Dourgnon,Naiditch,2010)。
1.3 德国:试点中的经济激励的“守门人”机制
传统上,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并无类似荷兰的强制“守门人”机制,患者可以自由就医;且门诊和住院服务完全分开,提供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不提供除急诊外的任何门诊服务,门诊服务由法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负责提供,住院服务则是联邦和州政府各自的责任。这种门诊和住院服务分割的设置是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德国建有分级诊疗机制的依据。与我国学术界认为这一分割是分级诊疗制度的有效形式不同,德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分割导致了医疗服务连续性的不足,并降低了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绩效。当然,随着最近德国提高医疗服务连续性改革的推进,这一分割有所松动。
当然,德国的自由就医也导致了一定的浪费,特别是滥用专科医学服务的问题。因此,德国一直试图引入“守门人”机制。
当前,德国的“守门人”机制仍为试点方案。1993年,疾病基金就开始以试点方式尝试建立“守门人”机制,主要是奖励参加“守门人”计划的参保者。但是,仅有少数地方进行了改革,且由于一系列法律障碍及地区社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反对试点带来的额外支出,使得改革得以维持的地方更少。2004年,德国再次尝试建立“守门人”机制,疾病基金允许参保人自愿参加名为“家庭医生服务(family physician care model)”的计划。这是一个典型的“守门人”计划。第一个成规模的“家庭医生服务”计划由巴登-符腾堡州的地区疾病基金与本州家庭医生协会及地区社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签订,该州3700名家庭医生和州内所有超过18周岁的参保者必须参加。到2011年春天,这一计划覆盖了100万人。参加这一计划,仅需支付就诊自付费用的50%,且经转诊可减少等待时间并帮助安排专科医生。同时,还可以使用晚间诊疗服务,全科医生服务等待时间更短且免除部分药品的共付费用。但具体效果仍有待考察,到2007年1月,2460万人有机会选择参加“守门人”计划,但只有460万人真正参加。
2 模式总结及其内在的支撑机制
2.1 改革模式总结
2.1.1 “守门人”机制不等同于逐级转诊机制
从前述国家经验看,“守门人”机制强调通过设置全科医生这一“守门人”来实现专科和全科医学服务市场之间的区隔,防止参保人盲目到专科就医带来的资源浪费。同时,全科医生作为全科和专科医学服务的衔接者,提高医疗服务连续性,并节省医疗保险基金。这并非逐级转诊的概念,参保人在全科医学和专科医学服务市场中分别享有完全的自由选择权。
实践中,强调逐级转诊的分级诊疗制度,并不见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中,而仅见于沿用苏联医疗保障模式的国家(主要为中亚国家)和一些北欧国家,其制度基础为医疗保障待遇为国家福利、个人免费享有;医疗机构为政府所属预算单位、没有管理自主权且分属不同层级政府。故而,这些国家的国民就医需要逐级转诊,对就医机构缺乏选择权。
2.1.2 “守门人”机制的典型模式
如前述,“守门人”机制可分为强制和自愿两种类型。
强制“守门人”机制下,参保人须选择一名全科医生作为首诊人,患病时除危急重症等少数情况外,均须到“守门人”处首诊,“守门人”负责转诊。如果参保者不经转诊,则无法获得法定医疗保险制度补偿。
自愿“守门人”机制则通过经济激励(惩罚)方式引导患者首诊。通常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济奖励的引导方式,经过首诊、获得转诊许可的患者,法定医疗保险将提供更高水平的补偿,如土耳其、德国。另一种是经济惩罚方式,对未经转诊的患者降低补偿水平,如法国。自愿“守门人”机制主要应用于社会医疗保险国家中,这些国家一直保留着自由就医的传统,民众对限制就医较为抵触,缺乏引入强制“守门人”机制的时间窗口。
2.2 “守门人”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
2.2.1 恰当的经济激励及其有效传导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
实践中,除福利国家和原苏联医保模式国家依托高度行政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实行逐级转诊外,社会医疗保险国家极少使用强制首诊机制。且中东欧国家实践证明,以行政命令方式塑造的分级诊疗制度效果不佳,转诊率偏高。这源自行政命令机制与医疗服务市场天然的不适应。因此,分级诊疗机制的建立需要遵循市场机制,而非强化管制、通过行政体系内整合医疗机构以及行政命令控制参保者行为的方式来实现。
社会医疗保险国家“守门人”有效运行的关键条件是购买者(医保基金)经济激励能够有效传导给医疗服务提供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牵制、相互协同的关系。这实际隐含如下要求:一是医疗服务购买者必须合理设置经济激励,保障“守门人”机制的有效运行;二是要求医疗服务供给市场能够有效响应购买者的经济激励;三是医疗服务购买者所拥有或代表的医疗保障资源必须足够充足,是医疗服务提供者无法拒绝的市场份额。
2.2.2 医疗服务供给市场需要满足下述特点
第一,全科与专科医学服务之间相互补充、分工协作,而非相互替代的由基层到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分级关系。从欧洲经验看,全科和专科医学服务存在较大差异。全科医学服务更多用于处理常见健康问题,负责疾病早期预防、行为干预、后期医疗照顾、医疗服务整合、健康管理等一系列服务。专科医学服务则主要负责疾病形成后的诊疗,主要处理全科医生无法明确和处理的问题,强调临床干预。即基层医疗机构与二、三级医疗机构间在提供服务上存在差异性,基层机构提供的并非简化的专科医学服务,而是全科医学服务。
第二,“守门人”领域中相互信任且熟识的医患关系。从欧洲经验看,取得签约人信任是“守门人”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这种信任使参保人患病后自发到签约医生处首诊,而非制度强迫下的不得已选择。欧洲国家中,“守门人”和参保人之间邻里关系超过医患关系。这与其宗教传统及各国限定注册医生与参保者之间的物理距离有关。同时,得益于欧洲的医学教育,这些国家“守门人”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值得信任,收入水平较为适宜使其愿意留在基层提供服务。
第三,私营个体执业为主而非公立机构为主的门诊服务市场。这与我国基层医疗机构以高度管制的公立机构为主的状况存在极大不同。实践中,自雇形态的全科医生扮演“守门人”角色更加成功。这是因为购买者的经济激励可更好、更直接地作用到全科医生身上,也不存在通过基层医疗机构管理者中转后的经济激励变形问题,较少存在机构目标和医生目标之间的差异和扭曲。
2.2.3 法定医疗保险支付和结算制度的相应设计
第一,引导全科医疗服务和二、三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形成有限资源的竞争关系。上述国家经验看,通过医保支付制度设计,特别是预算制定环节设计,使全科和二、三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形成有限医疗资源的相互竞争关系非常重要。这种竞争必须为市场机制下的公平竞争,并非行政体系内行政资源的争夺机制。这种竞争可防止全科医学和二、三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输送和互通关系,从而更好地履行“守门”人角色。
第二,保障“守门人”体面和可预期的收入水平,并通过绩效考核改善服务质量。实践中,社会医疗保险国家对“守门人”往往采取按人头付费为主、绩效和按服务项目付费为辅的组合方式。这使全科医生更加注重初级医疗保健服务供给且能更好地扮演“守门人”角色,也能为全科医生提供稳定和可预期的收入。在此基础上,按服务项目付费可改善初级医疗保健领域供给不足的问题;按绩效付费考核全科医生服务绩效,激励全科医生改进并完成相应绩效要求以获得额外的奖金。
第三,参保者是否首诊的待遇差异程度足够大。这要求法定医疗保障制度提供的待遇足够慷慨。同时,不经“守门人”转诊的医疗保障待遇损失足够高,能迫使参保人首诊。这是对参保者最重要的经济激励。从中东欧部分国家的经验看,法定医疗保险制度待遇较低也是“守门人”机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2.2.4 参保者“以脚投票”竞争机制的有效推动
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参保者为核心的“以脚投票”机制在制度运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通过引入“参保者选择权”机制重新调整了“医”“保”“患”三方关系。
一是在经办服务市场中引入“以脚投票”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社会医疗保险国家开始赋予参保人对参保基金的自由选择权,从而形成竞争性经办服务市场,如荷兰(2006)和德国(2007)改革允许疾病基金在有限范围内就保费、待遇和服务等进行竞争。
二是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继续维持参保人对服务提供者的自由选择权。即便引入“守门人”机制,也仅削弱了患者直接接受专科医学服务的权利,并未削弱参保者在全科和专科医疗服务各领域对服务提供者的选择权。对签约的全科医生,参保者有自主选择和阶段性调整的权利;对专科医生和服务机构,在获得转诊许可后,参保者享有完全自由选择权。
3 我国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困境和思考
3.1 我国重建分级诊疗制度的尝试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有严格的分级诊疗体系。改革开放后,这一分级诊疗体系逐步松动和解体。
而我国自1997年起的历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保改革都试图重建分级诊疗制度,但并不顺利。实践中,重建的思路大致有两种:一是以基本医疗保险偿付和结算政策为杠杆,引导参保者和服务者分级就医和诊疗,如阶梯形设置待遇起付线;待遇向低级别医疗机构倾斜;规定不经转诊转院降低保障待遇;低级别机构实行费用包干责任制;门诊统筹按人头付费等。二是重构医疗服务市场,形成分级的医疗服务体系,如医疗机构集团化和医联体化;提升基层机构能力;细分不同等级医院医疗服务包;农村地区重建地域性医疗服务体系;基层转诊绿色通道等。但很不幸,效果有限。
3.2 难以建立有效分级诊疗制度的深层次原因
表面上,我国难以有效重建分级诊疗制度的原因众多,如制度层面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医疗机构运行机制,所有制歧视,行政命令的强制首诊导致民众反弹大等;医保方面则缺乏门诊统筹平台,经济激励效果有限,审计政策限制等;医疗机构方面基层机构能力弱、患者信任不足、全科医生不足等等。但对深层次原因却缺乏分析。
3.2.1 政府和市场机制的错配导致行政管制和市场引导的双失灵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中计划经济传统残留较为浓重。所谓的公立医疗机构市场化是行政单位体制制约下的伪市场化,虽日常运营收入来自收费服务,但其他方面都受行政力量制约,其管理体制核心仍是资源配置权力的行政化,即科尔奈所称“官僚协调机制”。公立医疗机构除业务部门遵循市场机制有效率运行外,整个机构治理仍遵循行政事业单位体制。但市场机制与医院人员收入息息相关,医务人员行为更多遵循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机制。这种市场和政府机制的错配实际导致了公立医疗机构行政垄断下的行政命令管制失灵和市场机制难以顺畅运行的两难情景。公立医疗机构一方面追求运营收入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处于行政资源的配置体系下。
就分级诊疗制度而言,当前错配带来的核心问题是行政配置资源机制中资源向上集中的内生动机和分级诊疗要求资源向下倾斜的政策之间的矛盾。现实中,医疗机构出于收入的考量,有着做大、做强的强烈动机。而公立大型医疗机构拥有市场和行政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大型公立医院由于传承、技术、体量等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行政资源依据机构行政资源禀赋配置,高级别、大型公立医疗机构在人员、设备、科研等资源分配方面占据极大优势。这表现为医改以来,我国大型公立医疗机构的快速膨胀。这也自然产生了优质医务人员向上集中,基层机构人力资源弱化的情况。最终表现为基层机构硬件虽不断改善,但服务能力却不断恶化。同时,私立医院在与公立医院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3.2.2 分级而非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与分级诊疗制度之间的不匹配
如前述,国际上,全科医生、专科医生、医院服务之间有明确的不同定位和分工,各自专长不同,是相互协作、而非分级的关系。
而我国的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仍延续计划经济时期分级的概念,强调医疗机构的层级化,也就有了基层和二三级医疗机构间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机构是小医院、差医院的认知,甚至服务定价、人员薪酬、药品配备等政策体系都因循了这一逻辑。因此,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内,民众对基层机构的信赖度最低。加之基层医疗机构收支两条线改革、过重的公共卫生服务压力、基本药物制度等原因,辖区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熟识度也不断降低。
这样情况下,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基本尊重,民众必然选择高级别医疗机构就医。分级诊疗制度成为了不符合民众主观意愿的强制措施,故而推动缓慢。
3.2.3 医联体内生运行规律与分级诊疗制度目标之间的不匹配
我国许多先行试点地区已采用典型欧美“守门人”机制要求的付费制度设计,改革的重点转移到了医疗服务市场。当前,主要为推动医联体建设的思路,其逻辑是通过医联体建设,实现基层和高级别医疗机构间的垂直整合,从而“以大带小”,强化基层机构能力。现实中,医联体可能难以按照设想逻辑运行。第一,国际上医联体是医疗机构对抗医保议价能力的产物,可能出现借助市场垄断导致医保政策的变形,进而危害民众权益。各国对医疗机构的合并多采取审慎态度;而我国普遍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建立医联体,存在出现区域性垄断的隐忧,同时也弱化了医保的议价能力。第二,当前,我国公立医院做大、做强的自我发展动机强烈,因此医联体中高级别、高技术、高回报的医疗机构必然成为投入的重点,基层医疗机构往往被忽略,成为向高级别机构提供病员和优质医务人员的附属单位。实践中,部分医联体中大规模扩建病床后的高级别医院,确实将所属基层医疗机构作为招揽病员的机构;同时,将基层高年资、有潜力的医务人员上调到医院,将难以管理、技术不佳的医生下放到社区机构的情况非常普遍。
3.3 改革思路的调整
3.3.1 在医疗服务市场中激活基层活力、鼓励私营机构发展是重要的可选思路
如前述,由于我国医疗服务市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大型公立医疗机构在整个制度博弈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并不断借改革自我强化,公立医院改革的成果基本都表现为大型医疗机构的扩张。这与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推动改革、增加投入,以行政禀赋分配资源的机制息息相关。当前,过度扩张的公立医院成为诱导需求、争夺病员的主力军,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因市级公立医院过度扩张导致县级医院病床闲置的情况。
因此,如若继续推动大型公立医院主导的改革,出于维持医院运转的考虑,必然进一步导致就医向大型医疗机构集中,医联体政策更为上述现象提供了便利。未来可能仍将出现政策目标(分级诊疗)和实际结果(就医向上集中)之间的偏离。故而,建议停止继续推动以大型公立医院扩张为特点的改革。
实际上,我国改革经验表明,只有倒逼出来的改革才真正有效。而当前可供利用的是强化基层医疗机构和强化私营机构发展两个政策杠杆。
强化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其逻辑为强化基层能力来吸引患者,从而形成合理就医秩序,并倒逼高级别医疗机构的改革。这一思路并非简单倾斜资源的问题,而需体系化的改革。在资源倾斜的前提下,核心在于激活基层医疗机构活力,当前的收支两条线、工资管制等旧有事业单位管理体系需要改革,甚至必要时可学习欧洲经验,形成私营个体执业为主的格局。与之相配套,监管、自律、信息纰漏、质量控制等机制需进一步强化。同时,基层医疗机构需要逐步全科医学化,强调慢性病管理和预防保健。一个有活力的全科医疗服务市场自然会引导患者就医趋于合理。
强化私营机构发展的实质是希望通过鼓励私营医疗机构发展来激励公立机构改善效率和做法。私营机构对经济激励的敏感性远强于公立机构。通过对私营医疗机构的扶持,可以改变当前公立医疗机构的实质性垄断局面,并引导其探索新的分级诊疗方式。同时,私营医疗机构也更容易通过经济激励的引导形成合理分级的医疗服务体系。当然,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必须适应私营机构的发展。
3.3.2 调整医保内部管理机制
对参保人,强化其“以脚投票”竞争机制的作用。一是在引入全科医生“守门人”机制的情况下,仍需维持参保人对注册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疗服务提供者各自的自由选择权。二是在公立医院改革到位后,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体系改革,逐步赋予参保人对经办机构的自由选择权。此外,还需要拉大转诊与否的待遇差距,通过经济激励方式提高转诊积极性。
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结算制度方面,一是通过付费制度改革,特别是总额预算制度改革,引导基层医疗机构和二三级医疗机构形成资源竞争关系,并适度向基层倾斜,鼓励基层服务的全科医学化。二是基层医疗机构的付费方式组合,需要既保证其收入水平,又提高其服务积极性并改善服务效果。
[1]Schaefer W, Kroneman M, Boerma W, et al. The Netherlands: health system review, health systems in transition[M]. Copenhagen: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16.
[2]Geelen E, Krumeich A, Schellevis FG, et al. General practition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role in cancer follow-up care: a qualitative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J]. Eur J Gen Pract 2014;20:17-24.
[3]Dourgnon P, Naiditch M. The preferred doctor scheme: a political reading of a French experiment of gate-keeping[J]. Health Policy, 2010, 94(2):129.
[4]Chevreul K, Durandzaleski I, Bahrami S B, et al. France: Health system review.[J]. Health Systems in Transition, 2010, 12(6):1-291, xxi-xxii.
[5]Busse R, Blümel M. Germany: Health system review,Health Systems in Transition[M]. Copenhagen: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2014, 16(2):1.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a's Dilemma in Constructing the Tiered Medical Services System
Zhao Bin1, Li Wei2
(1Institute of Social Security,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Beijing, 100716;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bei Economic and Trade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61)
Currently, the tiered medical services system is widely concerned. In china, many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but it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etting rules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s on gate-keeper system in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three typical countries were selected to analysis. One is the Netherlands which was the fi rst to introduce a "gate-keeper" mechanism, another is France which has been introduced economic incentive gate-keeper system, the third is Germany which are try to introduce a gatekeeper system. Hence,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its mechanism design, summarize the setting rules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s on gate-keeper system, and analyze the dilemma in China.
the tiered medical services,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gate-keeper system
F840.684 C913.7
A
1674-3830(2017)5-14-6
10.19546/j.issn.1674-3830.2017.5.004
2017-4-23
赵斌,博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医疗保险室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