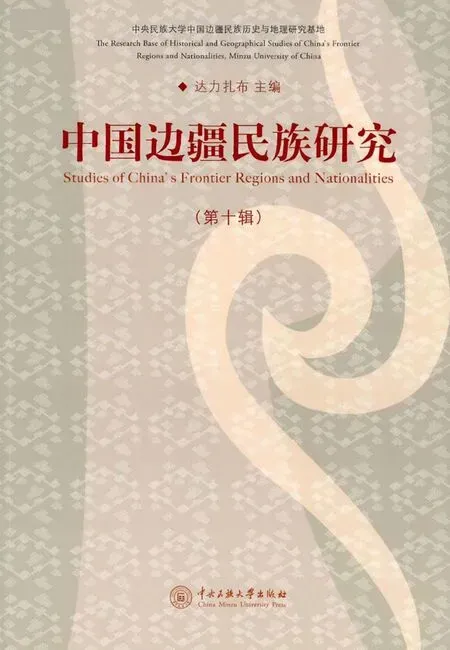探究历史奥妙的车道最好由考据的路口驶入:柯娇燕构建的相关历史命题评议
钟 焓
序言: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看待跨国界学术批评
在本文上篇于2013年正式发表以后,笔者有幸读到了国内学者关于“新清史”评价的一系列最新论著。这些文章虽然切入视角各异,阐释观点也间有异同,但都对读者深入思考“新清史”学术话题起到了开阔眼界与整合思路的启迪作用,充分彰显出目前中国史学界百家争鸣的民主氛围和学人之间质疑辩难的求真精神。尤其像笔者这种非清史-满族史的专业人士,更是从这种针锋相对的坦诚讨论中获益良多,从而意识到自己先前思考的盲点所在。根据上述论著的评价取向,读者大体可以将其归类为对“新清史”成果持基本肯定和批评否定的两派。集中反映前一种观点的文章主要有2013年定宜庄研究员和“新清史”健将欧立德合作刊出的一篇长篇评论、2015年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连载的姚大力教授的相关评论以及随后他回应汪荣祖教授的商榷之作。①定宜庄、[美]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收入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6-146页;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5日;《“新清史”背后之争的民族主义》,《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12日;《回应汪荣祖:略芜取精,可为我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5月31日。此外承认“新清史”学派对于学术研究存在正面性影响的论文还有清史专家高王凌在西文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中文论文,参看氏著:《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58/1-2, 2015.与之相映对照,形成鲜明“对比色”的论著则体现在汪荣祖先生在2014年主编的一部由大陆和港台学者共同捐稿的专题论文集、2016年度《历史研究》(北京)等刊发的数篇专业评析长文及此前汪先生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针对有关批评所作的回复等。②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14年(笔者得读此书要感谢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与任小波博士的指教帮助);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教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徐泓:《“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等。还可参看程秀金:《“新清史”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常建华:《祈福: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以及最近李勤璞在澎湃新闻上以《乾隆帝》为据质疑欧立德的满语水平的评论文章等。显然,像如何评价“新清史”这样重要而敏感的学术议题,国内学者难免会由于各自学术背景的差异与观念立场的不同而存在分歧争论,因此在短期间无法达成一致也在情理之中,这完全符合学术讨论的自身规律。毕竟,不同观点的历史学者之间在思想认识上的碰撞交锋与理性辩难对于学科的发展多有裨益。此点想必参与讨论的双方均有共识,不致因为见解存有出入就对彼方的论点立场心怀芥蒂。
先前笔者在业已发表的上篇中,通过分析该学派出现及兴起的学术背景,继而对于“新清史”的学术理念多持质疑与批评立场。①钟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上),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七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虽然近期浏览了以上结论迥异的各篇新作而个人的基本观点尚无实质性变化,还是更倾向于上述两派中的后者,不过肯定“新清史”贡献的学者基于扎实知识准备之上所做出的认真发问与雄辩驳难也促使笔者从广度与深度上重新检视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以期对原本思虑不够周延的地方能够有所加强。此前因为拙作中有数万字的内容是对一位“新清史”代表人物(尽管她本人似乎对此有所保留)的著述中大量论据的检证性指误,所以很容易引发关于这一做法的说服力究竟如何的争议。而在由此引申出的围绕学术批评的问题上,相应地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表述。第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在从事学术批评时,应该始终坚持那种针砭尺度宜缩不宜增的学术立场,力戒过去那种肆意拔高,动辄上纲的大批判作风。第二种意见则强调在国外通行的学术批评中,素以严苛锋利著称而不讲求任何私人情面,因此有关商榷只要是处在正常的学术范围内,即符合学术批评的一般通则。考虑到目前中国学者对于“新清史”的批评已经在学界造成不小反响,甚至有些言论借网络之力还辗转流入国外,恐怕会引起彼方人士的一定反应,这里似有必要先谈谈个人关于学术批评应持态度的一点粗浅体会。②例如笔者在2015年5月初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接受相关专访时,曾提到了柯娇燕等新清史学者的论文一般不会刊登在《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等西方内亚研究的专业期刊上。柯氏后来在网络上发文(关于其文的中译文,读者可以自行上网搜索阅读)反驳称,她的论文已在《中亚杂志》上发表过而笔者却不知道,以此批评拙文并不属实。然而,截至笔者接受专访时,刊登其文的《中亚杂志》第58卷1-2期尚未刊印发行,故专访中未提此文实属正常,关于这一是非,读者只要阅读同期刊发的牛贯杰的论文即可明辨,因为后一文中最后的注释内还提到了笔者的上述访谈。君子不可以其方而欺之,此之谓也!
首先笔者想与大家一同重温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个涉及中外学者论争的真实事例。一件是五十年代晚期,国内一位在民国年间即饱受尊敬的学界耆宿推出了一部北宋东京文献的校注本,却随即遭到那时还很年轻的日本学者入矢义高的严词批评,其在书评中公开贬斥此著为劣质书。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与之类似的事。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所的几位资深学者合作完成了在当时来说以收录众多敦煌世俗文书录文见重于学界的《敦煌资料》一书,结果该书出版不久,再度引发了其时刚崭露头角的日本敦煌学界新秀池田温在1962年的《东洋学报》上发表的批评性长文。由于那时国内的学者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先生们一般在历行文字交往中多持以文会友,切磋析疑的态度,故在涉及学术批评的言辞表达上尽量为被批评方考虑以使商榷双方最终皆有台阶可下,所以对于这种文势咄咄逼人、不留回旋余地而又出自邻国学界晚辈的西式批评一时感到颇难理喻。不过鉴于这两篇书评确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虽然评语失之过苛却未完全流于意气,所以中国文史学界在冷静反思之后,还是虚心诚恳地接受了这种批评,转而将其作为鞭策自身精进严谨的激励动力。而入矢义高和池田温日后也在中国学人中一直深受尊重,并未因此影响到他们与国内学界的正常交往,尤其是后者现在几乎已经成为日本敦煌学家在国内人缘最好的学者。正因为相关学界从这两件事件中认真汲取了教训,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敦煌学界欲再次联手对大陆某学术著作进行讨伐批判时,国内随即刊布了出自另外一位敦煌学家之手的质量远超前著的相近主题的新书,从而适时有效地化解了一场已处于酝酿之初的学术风波。
与日本学者常常习惯在细节考证上指摘中方的具体失误不同,北美学者则更热衷于在政治立场(近来尤其喜欢从民族主义上着眼)和研究方法论上(多指责大陆学者缺乏应有的理论思维训练)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评判。这或可归结到史实考据尚远未转化为其治学的长处强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很少有幸读到出自北美专家之手的像入矢义高这样自负的技术性批评。发生在近年来让人记忆犹新的一场跨国界学术纷争就是一部分北美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联合发起的针对国内启动的由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等共同承担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当项目启动之初,有些美方人士在尚未看到任何具体成果的前提下即诉诸媒体将这一工程定性为中国官方刻意扶植的带有沙文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形象工程,因此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科学客观性,无端揣测说政府赞助该项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把中国文明的出现时间提早到能与古埃及文明比肩的时代。以上做法实际上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通过将自己的理论根据建立在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上,把原本发生在学者之间的纯学术争论转变为政治上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场“围剿”,因此这与前述日本学者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批评毫无共性可言。而中国学者对于态度如此不够友好的攻讦却显得至为冷静,没有急于在第一时间内予以回击,代之以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稳步扎实地推进工程进度。而当工程取得的研究成果陆续对外公布时,人们却惊奇地看到,研究团队通过组织严密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手段,从实证的角度清除否定了在科技界和史学界曾经流传已久的相关陈说:中国是世界最早观测并记录日食、月食和太阳风暴的国度。上述科研成果的取得显然使那些臆测断代研究属于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工程的诛心之论不攻自破了。在从政治立场上批判断代工程的企图招致失败之后,部分北美学者只好又把抨击的靶标转移到了对于工程最后所发表的“简本”报告上。客观地说,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这类高难度课题来说,最终的周王谱系编年的排列必然极富争议性,分歧的弥合最终应通过平等商榷的办法来理智地加以解决。可是有些北美学者却在这场学术争辩中处处表现出以势压人的武断一面,他们由此发出的偏激言论不在个别,最为失态的莫过于新近辞世的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肆言无忌:“国际上的学者将会把这份报告撕得粉碎。”①关于对美国学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作批评的敏锐观察,参看顾明栋著,张强等译:《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3-252页。巧合的是,倪氏本人同时还是一位清史学者。而中国学界的反映依然是报之以冷静与理性,有关的工程学科带头人在针对这类批评时坦然大度地回应称,“简本”的报告并非最终结论,将来更加精密详赅的研究成果还会在“繁本”中刊布,而国外学者的意见如果确实可取的话,也必将得到认真对待与采纳。以上回答同样表现出一种理智稳健、通情达理、不求争胜于一时的宽宏雅量。
因此,上述案例反映出,国外学者在进行学术批评时确实以严厉无情、宁严勿宽居多,甚至有些批评本身已经超出了学术的尺度。不过当今的中国文史学界在遭遇跨国界的学术批评时,无论对方所持的立场多么偏执不智,多数场合下总能表现出不卑不亢、有容乃大的学人风范。这也清晰折射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史学者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业已趋于成熟与自信。当然就笔者本人而论,相对认可前述日本学者所做的那种与意识形态等末流杂音毫无关联的纯学术化批评而非北美学者习惯采用的后一类做法。这也是拙稿为何不吝篇幅对某些“新清史”著述详加辨证的原因所在。既然中国学者都能够客观平静地对待日本学人的这类严厉批评,那么在行文措辞上远远不及此类评论尖锐的拙文对于“新清史”的辩护者来说,自当不能算是一篇有意“冒犯”的动气之作。事实上,此前也已有欧洲学者发表了对“新清史”某著作的强硬书评,口吻用词全不留情,通篇行文从始至终未对所评之书道出任何肯定之语,似乎也未因此受到相关的反批评。至于该文的具体内容,笔者以后若有机会或会加以介绍。
而像这类与内亚史主题息息相关的犀利评论在国际学界并非罕见个案。我们还可再举一例,当下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在2002年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其成名作《古代中国及其对手》(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国内已有中译本发行)。是书问世以后,一时学界佳评不断,公推其为新世纪以来最好的内亚史著述之一。可是即使像这样一部确有个人不俗见解和杰出贡献的力作,《早期中国》(Early China)上仍然刊登了一篇鱼圣爱(Sophia-Karin Psarras)精心撰写的摧毁性长篇评论,全文的评价基调从首页最后部分的总结评语中可见一斑:“此书在概括使读者深致期盼的考古数据方面和重新评估早期中文基础史料领域皆告失败。书中错误令人忧心,这既是因为其失误出现在了基础性研究层面上,同时也是由于此类谬误充斥贯穿全书。”接下来鱼圣爱分节逐章地检讨狄宇宙在引用考古资料等方面的具体失误。平心而论,狄书不失为一部瑕不掩瑜的上乘著作,只是按照内亚史的学术标准来看依然悬有诸多立论未安之处,其所下结论也还留有争议而已。现在既然“新清史”的学者志在将内亚史的视角引入清史研究且被视作其突出贡献所在,那么我们在评论中对其论据严格把关兼详加商榷似乎从学科规范性上看也无不可,至少不致有违内亚史研究摈弃空论,求真务实的传统学风。
唯拙文虽举证甚多,然大多还是属于基本史实层面。可能在有些并不认同“细节决定成败”原则的“新清史”辩护者看来,这样的商榷即便成立,最多也仅能说明被评者的学术训练略欠完备而已,未必就能动摇其所构建的学术命题的主干根基。换言之,那些史实上的错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原作的中心观点以致使其难以成立还有待明判。即以柯娇燕的观点为例,她所倡导主张的满洲人由最初明清之际的文化共同体,到乾隆朝转变为种族(race),再到清末发展成为民族的“三部曲”式的满洲民族生成模式依然被有的学者认定为深具说服力和启发性的历史叙事,虽然在史实的具体运用上未臻精致与完美。然而对于这一模式,刘小萌研究员已在一篇概述性文章内简要分析指出:“有学者套用美国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声称满族先是文化共同体,后来成为血缘共同体,与满族的历史实际显然凿枘不合。”①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那么柯娇燕首创的“三部曲”模式究竟是能够得到有效证据支撑的科学假说还是作者单凭一己私意憧憬畅想的空中楼阁呢?
在本节中,我们拟依据“论从史出,无征不信”的实证原则以对柯氏的这一民族生成的“三部曲”模式及相关命题进行检讨。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在对有关模式进行解析时,有必要将催生这些宏大命题的学术渊源上溯到其发轫之初。此即柯娇燕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发表的一组环环相扣,彼此关联的论文群。事实上,它们的基本结论完全构成了她在1989年以后出版的《孤军》(Orphan Warrior)和《透镜》(A Translucent Mirror)两书的立论基础,常常被她当作定论化的前期成果而在书中大幅度地直接引用,并且还得到了深度的详尽发挥和拓展延伸。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结论作叙事铺垫的话,《孤军》、《透镜》恐怕双双无以立说成书。因此,如果我们不对她的这些早期论述进行认真细密的省察,实际上就无法对两著所涉命题的适效性做出中肯有力的准确评判。可惜目前笔者读到的相关书评却毫无例外地对于这些早期论文的学术价值均未认真探析,仅仅局限于单就本书的内容开展归纳评议,可谓不寻其源,难求其末;不究其往,难测其来。为了纠正这一认知偏向,我们在起底“新清史”的学术渊源时,自有必要先返溯至20世纪的80年代初。这相比或被称作“新清史”开端的罗有枝和何炳棣论战所发生的90年代中后期,无疑在时间上要早出许多。这些构成了《孤军》(此书最近已有中译本发行)和《透镜》叙事的源头活水的论文是(依发表时间早晚而定):
1.《两个世界中的佟氏:13-17世纪的辽东-奴儿干地区的文化认同》。①P.Crossley, “ The Tong in Two Worlds: Cultural Identities in Liaodong and Nurgan during the 13th-17th centuries”,Ch’ing-Shih Wen-t’i.Vol.4,No.9, 1983, pp21-46.
2.《清朝始祖神话序论》。②P.K.Crossley,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Foundation Myth”, Late Imperial China.Vol.6, No.2,1985, pp13-23.
3.《〈满洲源流考〉与满洲传统之定型化》。③P.K.Crossley, “Manzhou yuanliu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6, No.4, 1987, pp761-790.
4.《乾隆朝对于汉军旗人的出身回溯》。④P.K.Crossley, “The Qianlong Retrospect on the Chinese- Martial (hanjun) Banners”, Late Imperial China.Vol.10,No.1,1989, pp63-107.
在这组论文中,正是其中的首篇之作《两个世界中的佟氏:13-17世纪的辽东-奴儿干地区的文化认同》(以下简称《两个佟氏》)成为奠定作者后来相关专著极力表述的满洲民族“三部曲”模式的第一块重磅基石。该文正标题考察东北的佟氏家族,副标题则是揭示清朝入关以前围绕东北人群的文化认同问题。实际上,按其内容叙述,恰恰副标题概括的才是作者试图论证的中心观点,而佟氏家族在明清之交的际遇则是说明这一论点的最有效个案。该论点强调在明代东北地区,女真人和汉人(尼堪)的人群认同差异在于文化而非种族,女真人的特点是按照部落方式生活,多分布在辽东都司以北的奴儿干都司的地域内,使用女真语;汉人则与之相反,过着定居化的城居生活,主要位于在辽东都司辖区内,通行汉语。正因为双方的差别不在种族,所以被女真人称作尼堪的那些城居人口中实际上包括了众多在起源上和他们同出一脉(均为金元女真人后裔)的近亲,可是仅仅因为后者已经“去部落化”生活在辽东汉城内,又改操汉语,所以在奴儿干的女真人看来,他们已经不再和自己具有一种类似同胞族人般的亲缘关系,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尼堪”(汉人),表现在其文化特征处处与女真传统格格不入。其中最典型的此类案例就是后来在清朝康熙年间活跃一时的佟国维、佟国纲兄弟在明代的佟姓远祖。既然入关之前的女真(满洲)人是根据文化认同来维持其人群内部边界,那么这一时期的他们应当被视作一个文化共同体,相应地处在作者概括总结的民族生成模式“三部曲”的第一阶段。
那么柯氏此文究竟是经过了哪些中间性的论证步骤才最终导出这一结论的?这些中间环节的推导从考证上来说是否严密呢?澄清这些疑点正是本文下面需要检讨解决的问题。首先从推理逻辑上看,柯氏命题的整个推导过程有些类似于形式逻辑中最为常见的三段论推理法,所谓的女真人趋于汉人化近似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而佟氏先祖的个案则属于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大小前提密切啮合方才能够促使作为结论的相关命题矗立稳固。以下先来审查她是如何论证其中的大前提的。柯氏的论文架构为了证明部分女真人的汉人化,采取了以下的论述步骤:一,她认为明朝前期以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的三万卫野人女真先是经历了一次大的分流,一部分女真人迁徙到了辽东,并以抚顺为中心形成定居的规模。二,而在同一期间,尚未内迁的另一部分原属于三万卫野人女真则继续向东转移到奴儿干之地,并维持部落化的形态,形成了继续保持女真文化传统的建州三卫。可以说,正是三万卫野人女真这一迁徙形成了她整个推理链条中的第一张骨牌。那么其史料依据何在呢?她所引用的文献证据系《明实录》卷一八九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徙置三万卫于开元”条的有关记事:
先是,诏指挥佥事刘显等至铁岭立站,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会卫指挥佥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立卫,以粮饷难继,奏请退师,还至开元。野人刘怜哈等集众屯于溪塔之口,邀击官军。刘显等督军奋杀百余人,败之,抚安其余众,遂置卫于开元。
上引史料说得非常明确,明朝原本计划在今依兰县一带的斡朵里设置所谓的三万卫,可是由于粮饷补给难于实现,最后不得不改设于开元。按照明制,这里的三万卫属于卫所军事编制下面的一级单位,其直属人口则由世袭制下的军户成员(包含其家属)组成。对照该史料可知,原计划设置在斡朵里的三万卫是由调拨给侯史家奴的两千步骑士兵组成,其兵员来源实与世居此地的野人女真三万户无关。当然那里如果条件适宜的话,那么这两千人或将按照命令长驻斡朵里并安家定居,这样才能逐渐建立起“抚安”当地土著女真人的常态化卫所驻防体制。①关于明朝卫所制度对于疆土的实际管辖作用,参看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有关三万卫的代表性研究参看鞠德源:《从〈三万卫选簿〉看明朝政府对奴儿干地区的经营》,《文物集刊》1980年第2期;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等。事实上却由于出现了难以克服的补给困难,这两千人马根本就未能在斡朵里完成长期戍守的任务,结果在1388年全部撤回到开元,设立了一个从地理位置上看名实不符的三万卫,故这里的三万卫决非作为当地土著的女真三万户。后者是指元朝合兰府水鞑靼等路下的在今依兰县一带的斡朵里、胡里改、桃温三军民万户府,女真语称作移阑豆漫(“三万”之意)。而明朝和朝鲜方面也沿用三万户一名笼统称之。②贾敬颜:《〈龙飞御天歌〉所记的女真首领》,收入氏著《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需指出的是,元斡朵里等军民万户府的水鞑靼女真是不被看作野人女真的,而入明后随水鞑靼女真一名在明朝和朝鲜的史料中逐渐消失,这些女真人也开始被泛称为野人女真。因此,元明时期所谓“野人”所指各有不同。元代水鞑靼女真和野人女真分布地望的差别参看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1984年。综上所述,《明实录》记载的此次内迁开元的事件仅仅关乎两千明朝卫所官兵而已,这与作为当地土著居民的斡朵里等女真三万户何干?故当时根本没有发生大量野人女真成员跟随明朝官兵一同迁徙来到辽东开元定居的情况。柯氏对《明实录》的解释全凭随心所欲,将由明朝戍边官兵组成的卫所体制下的三万卫与作为该地土著的女真三万户混为一谈,以为前者的内迁即意味着后者的西移入边,结果制造出一桩子虚乌有的野人女真大举迁徙内附的不实史实。①关于《明实录》三万卫所在的开元的位置,学界除了辽东开原城说外,还有将其比定在今吉林市东南方的他说。后者参看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初刊于1956年),收入氏著:《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该文还认为三万卫是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真人三万卫的简称。
作者认为同时(1388)所发生的另一部分女真三万户东移到奴儿干并形成了建州女真部落联盟的论断也系误解。实际上努尔哈赤的远祖,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早在洪武二十一年以前就开始向东迁徙到靠近朝鲜边界的地方,所以永乐三年(1405)《李朝实录》的记事称其人自述“我等顺事朝鲜二十余年矣”。大约在洪武十五年(1382)前后,他已经被明朝封为斡朵怜万户。②贾敬颜:《〈龙飞御天歌〉所记的女真首领》,收入氏著:《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第182页;王钟翰:《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初刊于1990年),收入氏著:《清史续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年,第13页。因此,建州女真集团开始形成的时间明显早于1388年,只是被明朝正式设置为管控从今黑龙江省东南部到吉林省东北部及其东侧的建州卫(具有半羁縻性质)是在后来的永乐初年(1403)。而这些女真人无论是早先的从依兰出发东迁还是后来成为奴儿干都司下的建州卫都与1388年的三万卫回撤开元无关。因此,柯娇燕整个推理环节的大前提完全落空。
下面再看所谓的小前提也即佟氏源流问题。柯氏引用了清初顺治年间佟国器重印的其先人《幽愤录》后附的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佟氏家谱史料:
始祖讳达礼,洪武十六年充小旗迤北征进。二十一年,齎开设铁岭卫榜文,前去高丽张榜,升总旗,节次招安奴儿干野人有功,奉钦依升与试百户,调三万卫右所。二十八年,前去忽剌温地面杀死野人一名,元配王氏。二世祖讳敬,袭授百户(后略)
从中知其家族最早可溯至明初在东北卫所中效力的军官佟达礼。此人生平履历如下:他首先于洪武十六年(1383)明军北征时入伍并担任小旗,随后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改戍铁岭卫,升任总旗,因担任镇抚奴儿干野人女真的百户军职,改戍三万卫右所,并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在忽剌温参与剿灭野人女真。洪武十六年以前明朝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尚局促于辽东一隅,到该年四月时由于原为元朝的海西右丞阿鲁灰差人到辽东请求内附,明朝始着手考虑经略阿鲁灰占据的松花江流域,但对于当时尚在海西以东的野人女真仍无暇顾及。其实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纳哈出归降为止,明朝在东北投入的军事力量多用来对付作为北元残余的该股军阀势力。此后明朝方开始正式经略野人女真,继而于次年发生了在斡朵里设置三万卫未果故回撤开元的事。③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5-6页。因此,直接导致佟达礼于洪武十六年入伍的历史背景系明军当时正着力用军事手段解决北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并非直接用兵于野人女真。
然而柯娇燕对佟达礼履历的分析结果却是,其人明显出自三万卫的女真人,而被明朝方面允许定居在辽东(Tong dali was clearly one of the Jurchen from the Sanwan wei who was permitted by the Ming government to settle in Liaodong)。此处柯氏又一次把明朝官兵组成的三万卫和野人女真三万户混为一谈,再加上她深信1388年发生了野人女真集体迁入辽东这件里程碑似的大事,所以才会设想作为清初佟氏一门的始祖佟达礼当年正是从依兰一带迁徙到辽东的众多野人女真人中的一员。事实上,根据其个人履历,佟达礼早先入伍应是参加明朝清除东北的蒙古残余势力的战事,降至1388年因这些残部已于上年最后投诚方被改派到铁岭卫去镇抚野人女真,此后则在镇压野人女真的反抗中有所作为。因此,早在洪武十六年已入伍服役的佟达礼即使本人确实源出女真,那么他的原籍地理应来自当时明朝早已控制多年的辽东或者正拟着手经略的海西,决非还远未与明朝发生直接关系的野人女真。终上分析,按照其履历所叙,明明是佟达礼先在辽东一带入伍服役,在对蒙古的战事结束后才被改派去管控野人女真,供职于奴儿干等地。而现在柯氏为了附会其说,竟然罔顾事实,宣称他一开始即出自野人女真,1388年后才随着三万卫的内迁入籍辽东,纯属颠倒时空,漏洞百出,与已知史料的记载及有关历史背景完全矛盾,从基本观点到论证细节均无一可取。
柯娇燕精心演绎的所谓佟氏家族史这才刚刚起程,随后她注意到明末后金崛起之际,佟氏名人多出于抚顺,所以她先是极其武断地把该地看作佟氏在辽东的唯一入籍城市,论文中动辄使用抚顺佟氏一语加以概括,而实际上该系佟氏族人开原、辽阳也有支脉分布。①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原著于1944年),收入氏著:《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不过她也意识到,《明实录》的记事只是提到1388年的三万卫内迁开元,并无任何记载揭示抚顺与这次迁徙存在关系。于是,柯氏只好尽情发挥她以想象力治史的本领,浮想联翩地声称这些内迁的野人女真在到了开原、铁岭以后,又陆续转移到像抚顺这样更小,更远的城镇,甚至包括辽东的一些村庄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职业身份不再局限于从军入伍一途,而是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一面,尤以投资商业贸易,牟取丰厚利润著称,善于经商的抚顺佟氏即其中之一。以上演绎不啻创作出原系野人女真的佟氏先人继从斡朵里来到开原、铁岭以后又辗转入居抚顺安家的徙家三部曲,最后又从龙入关,权重一时。可惜正缘于没有史料来支撑,所以她精心编织的这一佟氏入关之前的历史叙事在正文下面始终无法列举出哪怕一则足证其说的参考文献注释,无论是基础性原始文献还是二手性研究成果。②顺治以后,清代佟氏后人的传记谱牒中多称发迹于后金时代的佟养正(真)家族是在其祖达尔哈齐时因从事贸易寓居开原,而后迁来抚顺。惟在达尔哈齐的生活时代上却说法不一,有的称其为佟养正祖父(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七所收其在史馆所作的《佟国纲传》),还有的则上溯到时间更早的15世纪前期,称其始祖达尔汉图墨图,同东旺(康旺)、王肇舟和索胜格等来往近边贸易,先后寓居开原、抚顺(雍正十年镶黄旗汉军世职家谱等),虽然互相抵牾不合,但均在刻意回避早期顺治年间佟氏祖谱中因籍贯出身莫详,无以确定为女真族属的始祖佟达礼。其中后说漏洞尤其明显。查考《东夷考略》,永乐元年奴儿干野人四酋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琐胜哥一同归附明朝,以后朝廷遂设奴儿干都司。是知顺治以降,佟氏后人为了坐实其家族的女真背景,极力把祖先攀附成原为奴儿干本地酋长以后成为都司武官的佟答剌哈,从而试图掩盖洪武年间三万卫军官佟达礼本为其先祖的事实。然而晚期佟氏族人所述的达儿哈齐的身份、经历、居地皆与佟答剌哈的本人情况无以勘合,傅会缝合痕迹历历可见。其实郑天挺早就推定达儿哈齐的始祖事迹出于佟氏后人伪托,所作辨析参看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第23-24页。稍前朱希祖也已指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佟氏源出答剌哈的记载有误,应当修正为佟达礼。参看氏著:《后金国汗姓氏考》,收入《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南京: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44-45页。惟康熙四十年序《佟氏宗谱》仍将佟达礼列为始祖,该宗谱以后在民间一直收藏流传到民国时期,所记佟家人物的谱系关系参看冈本さえ:《清代禁书の研究》,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年,第556页。看来在叙及祖源时,佟氏后裔保存流通的内部族谱与其对外上报宣称的官方性世系并不一致。
柯氏文中另外一处使人相当惊诧的论断是她认定以佟答礼为始祖的抚顺佟氏和努尔哈赤家族存在血缘上的远亲关系,两者的族源均是1388年三万卫女真“大迁徙”之前斡朵里万户府下的某一女真大族,这也无怪乎她会选用“两个佟氏”这样的表述作为其文的正标题。这一论证除了依托一场并不真实存在的三万卫“大迁徙”的民族分流作为历史背景之外,更主要的是她以文献中提到的努尔哈赤起初曾自称佟姓和其远祖猛哥帖木儿冠以童姓为立论基础,遂以相信努尔哈赤家族本为佟姓为出发点,按照早先朱希祖“佟姓同源论”的推理提示,断定这支佟氏和佟达礼族人在血缘上共承一脉,只不过在经历了1388年的那次明代女真历史上分水岭似的大分流之后,一支入明发展为“尼堪”,终以抚顺佟氏闻名;另一支却成为继续保持其部落文化传统的建州女真,直到其后裔建立后金国,改姓从佟氏名称中衍化出来的爱新觉罗氏。
撇开其说赖以奠基的1388年“大迁徙”的虚幻性不谈,柯氏此处所做的全部论证都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首先,无论是汉族或者少数民族,“同姓不同宗”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凡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历史学者很少会采取仅以姓氏定其同源的片面化推理思路,藉以大胆构建人群流动迁徙的历史。朱希祖早年因所见佟氏人物资料较为有限,故仓促结论为“明代辽东著名之佟氏,仅有三派,其远祖必相同也”。①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收入《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第52-53页。其实翻检稍后张鸿翔根据明朝东北卫所选簿所做的非汉人军官姓氏统计,可以清晰地发现明朝东北籍的佟氏武官人数众多,源流家世出身各异,乃至出自不同家支而姓名雷同者也数见不鲜,甚至还有一些佟姓人物的出身被选簿记作与女真相区别的“山后人”。②张鸿翔:《明代各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完成于1936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110页。其中的山后人或指金元以来华北北部因邻近草原而深受北族文化影响,故娴熟弓马,惯于征战的边地汉人,故在明初作为和普通汉人不同的群体屡屡被纳入卫所体制下服役。参看奇文瑛:《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9页,31-34页。因佟达礼在洪武十六年即早早入伍,似乎也不排除有来自山后的可能。凡此种种,皆可证实朱氏当初推测之非。相反,当佟达礼的八世子孙佟卜年因故被捕下狱并面临与建州努酋同出一源的嫌疑指控时,自陈力辟同宗一说之非:“卜年之姓,如姓张姓王之类。辽东二十五卫姓佟者,不下数十家,已非一族”,仅供认“卜年不幸,与佟养性同族”,此皆庶近佟姓之真相。而为柯娇燕所张大的朱希祖的卜年辩解均系遁词一说则未得其实。事实上,明廷后来在议定卜年罪名时,卒以佟养真近族论以流刑,迄未坐实其与努酋同宗的指控,是“明廷上下深知佟氏之世居辽东,确为汉人,不能以诬”。③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第25-26页。柯氏不察,反以为随后其人病死狱中系相关指控证据有力之后果,诚属误解史料记载。
此外在涉及辽东佟氏的问题上,即以主张猛哥帖木儿本为童(佟)氏的三田村泰助而言,他指出该支建州佟氏实际上的正确名称应该是董氏,译自女真人的donggo,这与部分佟氏可能出自的佟家氏(dunggiya)在起源上完全不同。而且,所谓的佟家氏在东北分布范围甚广,按照其原居地至少可以分为四大支系,很难说他们皆出一源。④三田村泰助:《清朝の开国传说とその世系》,收入氏著:《清朝前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65年,第10-17页。其次,现在学界一般认为,猛哥帖木儿一系的真正姓氏就是觉罗氏,而其冠名的童(佟)氏属于冒姓而已,后来在万历四十年代时创制了和一般觉罗氏存在人为区别的爱新觉罗氏。①神田信夫:《爱新觉罗考》(初刊于1990年),收入氏著:《清朝史论考》,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觉罗氏的起源或可上溯到金代女真的交鲁氏。②金启孮:《爱新觉罗姓氏之谜》,收入氏著:《沈水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5-198页。还有学者认为,努氏一系实际来自觉罗氏下的觉尔察支系,参看敦冰河:《清太祖努尔哈赤族属考——兼论觉尔察氏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渊源》,《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而猛哥帖木儿一族的发源地虽然学界存在争议,但不出黑龙江中游和长白山两说。③关于以上两说,分别参见Matsumura Jun(松村润), “On the Founding Leg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Acta Asiatica 53/ 1988, pp19-22; 王钟翰:《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第15-19页。也参看敦冰河:《努尔哈赤祖居地考》,《满族研究》1996年第4期。这在地理上和各支佟氏的世居地也不吻合。至于柯氏将觉罗(Gioro)一名在对音上和金代的夹谷氏(金元时相继改作彼此音近的同氏与仝氏)勘同也系穿凿附会,因两者的发音本不相同。故觉罗一名决非从佟氏中演化而来,彼此的源流判然有别。所谓“两个佟氏”的立论不啻捕风捉影。
还要强调的是,柯氏其文对15世纪建州女真的史实叙述也多有舛误。她认为在1388年女真三万户的大分流中,斡朵里部的阿哈出(李思诚)率众南下图门江流域。后来当1403年建州卫的设立即主要依靠其子释家奴(李显忠)。而在1388年的迁徙中,后来形成了建州女真的斡朵里和桃温分裂成了两大集团,一部分由佟猛哥帖木儿统率向东徙居到浑春,而阿哈出带的另一支则西移婆猪江流域。前者在15世纪早期进一步迁入到朝鲜北境的斡木河流域。当他与其子在1433年被七姓野人所杀后,其同父异母弟凡察带领余众在1436年抵达了婆猪江,经过了一番权力之争后长久地归附于建州李满住及其后人。随后不久,建州卫再度分裂成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的左所和凡察的右所。而佟佳氏即肇源于这些入居婆猪江的佟猛哥帖木儿族人后裔。
她所重构的这段历史叙事需要纠正的错讹极多。首先阿哈出不是斡朵里万户府而是胡里改万户府的首领,他在朝鲜史料《龙飞御天歌》中被称作火儿阿(胡里改)豆漫古论阿哈出。④贾敬颜:《〈龙飞御天歌〉所记的女真首领》,收入氏著:《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第182-183页。因此,认为后来的建州卫只是以斡朵里和桃温两万户府为基础的说法亦误。其次,以阿哈出为指挥使的建州卫在1403年设置时,地望即在今珲春以东的中俄边境一带的故元开元万户府。⑤孟森:《建州卫地址变迁考》(初刊于1932年),收入氏著:《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31页;郭毅生:《明代建州卫新探》,《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建州卫在此地的时间一直延续到1423年。而猛哥帖木儿在洪武十余年时从依兰迁徙到今朝鲜咸镜道阿木河流域之前并未在今浑春一带中途停留过。⑥董万仑:《建州女真定居阿木河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3期。柯氏由于笃信1388年大迁徙之说,因此在猛哥帖木儿迁徙的时间和方位上连续出现了误判。故15世纪初期建州女真的两大集团李氏和童氏分别活动在故元开元万户府和朝鲜咸镜道阿木河流域。稍后在永乐十年(1410)前后又形成了以猛哥帖木儿为首的自立于李氏建州卫以外的建州左卫。⑦孟森:《建州卫地址变迁考》(初刊于1932年),收入氏著:《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第35-37页。由此形成了建州卫与建州左卫两相并立的态势。最后建州卫迁徙入驻婆猪江则是李满住担任首领的1423-1424年,远非其祖阿哈出的时代。在1433年猛哥帖木儿被杀以后,李满住加紧了对其余部的笼络和争取的工作,积极吸引建州左卫前来婆猪江定居,并最终在1440年而非柯氏宣称的1436年迎来了原左卫余部凡察等人的投奔。①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初刊于1935年),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4-527页。在建州左卫迁来婆猪江一带后,其内部又发生了凡察和猛哥帖木儿另一子董山的争印纠纷,最终导致明朝于正统七年(1442)复从左卫中分出右卫专任凡察统领,其辖地即以后努尔哈赤家族发迹的兴京一带。柯娇燕大概对建州卫所制度及其演变皆不了解,误将均从建州左卫分出的左右两卫理解为从建州卫分出的左右所。而佟家氏实非猛哥帖木儿的所谓佟氏,前引三田村泰助文已详辨之。
柯氏在她自视圆满地解决了抚顺佟氏的渊源关系后,迫不及待地将这一认识加以推广。由于抚顺佟氏在明清之际被编入八旗汉军,所以她极为自信地宣布皇太极时期成立的以辽东汉人为主的汉军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和佟氏一样,他们的祖先本是女真,但因后来迁居辽东并经历了文化转型而成为“尼堪”,所以在东北地区,汉人和女真仅具有文化上的差别。其实“辽东之地,自古以来,为夷、汉杂居地区。佟氏最初本为夷族,后来渐受汉化,家族既众,其中自有受汉化深浅之分别。佟卜年一家能由科举出身,必是汉化甚深之支派,佟养性、佟养真等为明边将,当是偏于武勇,受汉化不深之房派”。②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81页。陈寅恪先生的独具只眼相较柯娇燕因刻意求新却在论据上网漏吞舟的观点来说,在立论上更显平实稳健,也更为深刻有力。其一,陈先生明确揭示了辽东自元明以来长期存在的汉人女真人混居融合的背景特征,这一解说完全符合基本历史事实,而没有像柯氏那样极其主观地虚构出一场把大量野人女真裹胁卷入辽东地区的迁移风暴。其二,他同时准确概括出辽东地区民族融合中所出现的以汉化为主流的社会现象,并切实做到整饬之下,又有区分。相比之下,柯氏却自始至终回避正视这种文化交往中的汉化主流,所以在解释女真人变成“尼堪”的原因时,只能套用几个公式化的暧昧术语敷衍了事:定居、城市化、去部落化等,仿佛在辽东以外的东北地区,女真人及其先民自古以来都只过着一种游牧化、部落化、不知城居为何物的原始生活一样。而我们只要稍稍留意有关渤海国和金朝时期,吉林、黑龙江两省和俄国滨海地区的蔚为大观的考古发现,就能发现这种看法是多么无稽。同样当她任意使用“部落化”这样的词语时,似乎并不清楚女真-满洲人的最具民族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以氏族为基础的哈拉-穆昆制(hala mukū n),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部落。当然就更不可能指望其像陈氏那样结合佟氏族人的具体史实深加辨析并总结规律。因此,尽管柯氏的文化共同体理论粗看之下和陈先生平生主张的“种族文化观”在某些提法上似曾相识,但实际上却多呈拼凑证据、架空立说、不得要领、结论苍白。两种史观的学术境界和批判精神高下分明,难以等量齐观。
柯氏本文中重构的佟氏家族历史的最后一站则是入关以后其作为汉军大族所经历的回归满洲,也即“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的上演,以此说明满洲文化共同体所发生的裂变。作者精心选取的历史场景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佟国纲上疏以先祖达尔哈齐原系女真为由,请求将其家由汉军改回满洲,最后得到允准,但仅限于佟国纲、佟国维两家。作者对此事的解读可概括为:一、这一请求的获准实际上是以后乾隆朝弃绝文化标准,改以种族来重新定义满洲做法的前奏,显示入关以后清朝在族性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已经开始寻求全新的人群认同标准。二、佟氏申请改回满洲其实正是所谓“抚顺尼堪”汉军群体希求重获满洲身份的一个缩影。该群体成员大多和佟氏具有相同的家世背景:种族上起源于女真,来到明属辽东以后成为尼堪。虽在康熙一朝只有佟氏兄弟等个别特殊家庭如愿以偿,但到乾隆朝则正式确定了以种族起源作为满洲身份的新认同标准后,他们统统改隶返归满洲旗分。随着乾隆年间新旧标准一举完成了彼此的相互取代,终于导致满洲由文化共同体改造为种族共同体。不妨说她主张的“三部曲”的第二部奏响于康熙,终止于乾隆,几与整个“康乾盛世”相始终。
令人遗憾的是,以上解读皆为误读。清史学界在佟国纲请求改隶满洲一事上已有深入研究并多存共识,最基本的结论是将此事定性为开以后“抬旗”之先例,根本无关满洲认同标准的变化。①王锺翰:《满族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收入氏著:《清史续考》,第62-63页;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5-328页。试析如下:首先,将佟氏此举归入“抬旗”的类型之一始自清人吴振棫的概括,可见清人对此事性质已有明晰认识。②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1,第2页。其次,柯氏相信这次改隶使得佟氏兄弟由汉军旗分进入到满洲镶黄旗下。然而郑天挺先生早就指出,当康熙将此议交户部处理解决时,户部的处置方案是将国纲族人改归满洲,却仍留于汉军旗下。此点显示朝廷实际上采取的是折中处理佟氏的请求,且不取以其先祖血统来界定满洲旗人的做法,因为若照此标准实行,则佟氏其他各支族人势必都将享受抬旗对待。皇帝的恩准也只是考虑到佟氏兄弟当时具有的外戚舅氏身份,故将相关殊遇推于乃父佟图赖一支并不泽及其余族人(因康熙生母即图赖之女)。③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第26-28页。而且郑氏在写作此文时已经看出晚出清朝文献中关于佟图赖一支最终归属的旗分记载颇有含混,改入满洲镶黄旗的说法尚待确证。惜囿于其时史料所见,未及得出确凿结论。辨析至此,我们即知仅以柯氏此文发表的时间而论,其说已落伍于当时清史研究的水准,所谓的认同标准转移之说断难成立。不过,对其观点最致命的证据还是后来侯寿昌先生终于从现存旗务档案中查考出,佟图赖一支的“抬旗”事实上发生在佟国纲上疏之前近二十年的康熙八年(1669),系从原属下五旗的正蓝旗汉军抬入上三旗下的镶黄旗汉军而已。而康熙二十七年上疏的结果只是朝廷允许该支佟氏改称满洲,但在所归旗分上仍然使其附于镶黄旗汉军名下,事实上成为无具体的满洲旗分可以对应隶属的纯粹名义上的“满洲”。换言之,朝廷对之是仅赏其名而拒予其实,以致其后人镶黄旗汉军身份降至清末亦无变更。故有些文献记载中的该支佟氏改隶镶黄旗满洲的说法实属讹传。④侯寿昌:《辽东佟氏族属旗籍考辨》,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7-369页。这一重要发现既完全消除了先前郑先生产生的疑惑,更使得柯娇燕的前述观点彻底丧失了被纳入学术考虑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柯娇燕将抚顺佟氏与所谓的“抚顺尼堪”相联系的解读也属谬误。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抚顺佟氏虽然支脉众多,但在明清之际多被编入外八旗汉军的旗分,遂形成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汉军正身旗人(乌真超哈),不入满洲旗分之列。然而,所谓乾隆期间通过官方修谱被正式接纳的“抚顺尼堪”却恰恰相反,按照此时成书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例》所述:“蒙古、高丽、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等人员,从前入于满洲旗分内历年久远者,注明伊等情由,附于满洲姓氏之后”,可知有资格列入《通谱》的这些有汉人背景的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家族一直都是满洲旗分下的具有一定人身依附性的旗人群体,这与外八旗汉军的身份性质截然不同。因此,以上三类“尼堪”并非与佟氏境遇相似的汉军正身旗人(乌真超哈),其中的“抚顺尼堪”显系后金当初占领抚顺后曾劫掠为奴,编入满洲八旗的那一部分汉人的后裔。同时也缺乏证据显示这些丧失了人身自由的抚顺平民多像佟氏族人那样,原系已经汉化的女真后裔。正因为这些“尼堪”从始至终生活在满洲旗分下,所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编修时才将他们也列入其中,算是正式承认该群体具有一种“准满洲”的身份地位,故当时逐渐实施的“出旗为民”规定也不施用于他们。因此,柯氏设想的乾隆时期“抚顺尼堪”群体最终从汉军各旗改隶满洲旗分的判断又与事实完全相左。这样她所苦心构建的满洲民族生成模式“三部曲”的第二部,正如此前的第一部那样,一旦与基本的历史史实当堂对质,即遁现出空中楼阁的原形,沦为绝无指望成立的谬见。
现在终于可以给柯娇燕新清史工程的首块奠基石“两个佟氏”下一简明结论:她的“三部曲”模式固然设想恢弘,可惜就该文的具体实践来看,委实与实证史学存在着天渊之别。其构建的整个历史叙事最初竟肇始于一场虚妄不实的1388年野人女真分流大迁徙,而在随后的一连串递进推导过程中,几乎每个中间环节都出自作者对史料的严重误读或者一厢情愿的任意臆想,以致每每推理到下一关节时,就会无法避免地滋生出新的错误论据并且前面环节的种种失误照样延续甚至还被衍生放大。不妨说这一看似雄辩诱人的宏大叙事完全是凭借多重错误数据链彼此叠加啮合才得以累积形成,从而“蝴蝶效应”般地蜕生出作者寄予厚望的“三部曲”结论,多年以后再进一步延伸发展为《孤军》和《透镜》的立论基础和再出发点。故前引刘小萌先生对该模式的观察评价是客观、平实而精准的。
柯氏随后发表的《清朝始祖神话序论》(以下简称《始祖神话》)也是一篇对于其后续论著相当重要的前期成果。正如题目本身所揭示的,该文考察的是清朝始祖神话问题。对于探寻清朝前史来说,本课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该文因其引用史料的二手性,难免会在学术性上让专业人士深感意外。显然,既然是分析研究清朝始祖神话,那么研究者自有必要追溯出记载该神话的最早史源。然而柯氏通篇行文中引用的关于这一神话的最基本史料却是迟迟于民国年间才成书的《清史稿》卷一的有关部分,仅仅在个别注释中才略微提及《东华录》和《满洲实录》的对应记载。《清史稿》的清朝始祖神话文本不仅成书时间最晚,而且在具体介绍从始祖布库里雍顺到肇祖孟特穆的传说事迹时,相关内容也失于简略,明显属于一种后出的文本删节类型。对于任何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在有选择余地的条件下,径直选取成书时间最晚(虽然也许是最方便到手)的史料作为自己的立说基础,实乃史学研究之大忌。具体到清史领域,即以其文发表的1985年而论,作者在处理本课题时所采取的以上做法能够反映当时清史专业的研究水准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首先记载清朝始祖神话的传统史料自以《太祖实录》为基础。这一点从20世纪早期,清史研究起步不久后即成为学者之共识。而要正确评估始祖神话所蕴含的史学价值,当然离不开对《太祖实录》成书过程的研究。到20世纪中期,中日学者基本从传统史料学的角度梳理清楚了其成书的经过及现存的版本情况。①代表性论文有:内藤虎次郎:《清朝开国期の史料》(1)-(2),《艺文》卷3,11-12号,1912年;今西春秋:《清三朝实录の纂修》,《史林》第20卷第3号,1935年;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卷七,1938年;《清实录修改问题》,《辅仁学志》卷八,1939年;鸳渊一,户田茂喜:《罗氏所藏の草本日记档に就ぃて——努尔哈赤实录改修过程の一稿本の研究》,《满洲学报》第8-9合期, 1944年;三田村泰助:《清太祖实录の纂修》(初刊于1959年),收入氏著:《清朝前史の研究》,第363-380页;达力扎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收入王钟翰主编:《满学朝鲜学论集》,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5-56页等。其中今西春秋1935年发表的论文大致奠定了清史学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界普遍重视北京故宫博物院1930年代初期排印的成书时间比较早的汉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其次才是更为通行的修成时间晚至乾隆初年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当时孟森即主要以前者为据,专门研究过其中的布库里雍顺始祖神话和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内容。②孟森:《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卷3期,1932年;《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北京大学史学》第1期,1935年。惟孟森相信原藏北京故宫,后被排印出版的武皇帝实录即崇德初纂本,实际上该本属于顺治重修或重缮本。此外乾隆时期的三体合璧《满洲实录》实际上是根据入关前的崇德本重抄,并参照了顺治本才最终成书的,尤其是其中的满文对照部分,对于研究始祖神话颇富征引价值。因此,即以20世纪前中期的清史研究现状而言,考察清朝始祖神话当以顺治本《武皇帝实录》的相关记载为主,兼采对比乾隆时的《满洲实录》和《高皇帝实录》的同类记述。这才可以说符合最基本的史源学要求。相比之下,柯氏以《清史稿》为主的做法就显得在史料选取上太不专业,而这又源于她对学术界关于《太祖实录》成书与版本流变的相应知识了解得过于有限。
其次或者说更为关键的是,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非常珍贵的满文原始史料《天聪九年档》的再发现与利用使得国际清史学界对于该神话的研究步入到全新的境界。③记录完整的《天聪九年》档于1935年发现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来被运往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在1969年将其与1930年代发现的其他满文原档一同以《旧满洲档》的书名刊行。以后日本东洋文库本在1972、1975年连续出版了两册译注本。大陆也已于1987年出版了其汉译本,即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合译:《天聪九年档》,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松村润最先认识到《天聪九年档》五月初六的记事中完整叙述了清始祖布库里雍顺来历的传说,④其汉译本参看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合译:《天聪九年档》,第55-56页。此即刚刚归顺了后金的虎尔喀人穆克西科所述:
吾之父祖世代生活于布库里山下布勒霍里湖。吾之地方未有档册,古时生活情形全赖世代传说流传至今。彼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恩库伦、哲库伦、佛库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是也。布勒霍里湖周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后略)
松村润将其与《武皇帝实录》等中的同一故事作了比较,指出顺治重修《太祖实录》中的开国神话的原型即《天聪九年档》中的该故事,同时也有可能更早的崇德初纂本业已将此故事纳入其中,惜已无法证实。他还根据清代舆图资料推断所谓的布库里山是在黑龙江中游北岸。⑤Matsumura Jun, “The Ancestral Legend of the Manchu Imperial House”, in.Ch’en Chieh-hsien(陈捷先) ed.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East Asian Altaistic Conference, Taipei, Dec.26-31, 1971, pp192-195; 松村润:《清朝の开国说话につぃて》,收入《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2年,第431-442页。稍后他又发表论太祖武皇帝实录编纂的专文,继续重申补充先前的有关看法。①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の编纂につぃて》,收入《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425-428页。松村氏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皇太极以前,努尔哈赤家族可能并不掌握相对完整的布库里雍顺起源神话,因此《天聪九年档》记录的该故事应当是它最早的文本形态,其成了日后实录纂修时编写开国神话的基础。
包括《天聪九年档》在内的《旧满洲档》的刊布和松村润论文的发表,很快引起了美国专治中国古代先秦文学史及满学的汉学家杜润德的注意。他于1979年发表论文,概述翻译了这一新材料,并简要介绍了松村润的研究。该文重点比较了《天聪九年档》和《满洲实录》中布库里雍顺故事的详略差异,在总结该故事母题特征的基础上,从口承故事和书面文学的各自特点对其相关差异进行了解释。文中最后对于皇太极此前不知晓这一故事的论断持保留观点。②Stephen W.Durrant, “Repetition in The Manchu Origin Myth as A Feature of Oral Narrativ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3/ 1979, pp72-83.杜氏大概是最早研究这一新资料的欧美学者。意大利满学家斯达理随后也发表相关札记参加讨论,他基本认可松村润的研究结论,倾向于在天聪九年以前,后金统治集团确实有可能并不知道这一传说,而在穆克西科向皇太极讲述之后,才着手将其整合入自己的国史中。③G.Stary, “Mandschurische Miszellen.Ⅰ: Über die Fälschung des Ursprungs-Mythos des mandschurischen Kaiserhauses”,in.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2, SS76-79.因此,在柯氏论文发表的1985年之前,单以欧美学术界而论,已经出现了用英语和德语详细介绍《天聪九年档》相关传说的专业论文,更不用说时间更早的日文研究了。令人十分不解的是,这些极其重要的研究报告连同已经刊布了十多年的《天聪九年档》本身竟然都没有出现在柯氏此文的正文及注释中。按照常理,即使柯娇燕因语言关系不大熟悉日、德语论文,那么她至少应该对本国学者杜润德的英文成果并不陌生。事实却是她连后者的文章也未提到。④仅仅在该文的注释25中,柯氏才提到他从中国学者孙文良、李治亭合著的《清太宗全传》(1983年出版)中获悉有满文史料称1635年“黑龙江高原”(Heilongjiang highlands)的野人(wild men)部落知晓这一传说。大概由于对其具体内容不知其详,柯氏错误地将这一史料记为根本没有收载此事的“满文老档”(manwenlaodang)。由此可见她对该研究信息掌握之滞后。看来,柯氏对国际满学界进展动向的掌握实在是有些薄弱。难以想象,如此做派会出现在一位平素向来以强调满文资料重要性过于汉文的资深的专业满学家身上。读者或有理由质疑,她对满文资料的真实态度是否带有叶公好龙的色彩?要之,作者在本课题上以《清史稿》为基本史料的做法直接暴露出其在清史尤其是满学修养和训练上的薄弱与欠缺。
以下再来分析其文具体得出的相关结论。柯氏此文最基本的论点是,在明代辽东以北的东北地区,女真(满洲)与蒙古在文化与种族上的混杂现象十分严重,以至有时几乎不能明辨孰为前者,孰为后者。有必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个可以视作变相的“族性(ethnicity)晚生论”的观点一直贯穿到20多年以后她所撰写的断言蒙古民族性极晚才塑造成形的论文中,真可谓道恒不变,一以贯之。而为了“证明”当时东北地区长期具有的这种足以阻碍族性发育的人种-文化混杂性,她特地选取清开国神话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相关基本思路其实早在“两个佟氏”中就已有所表露。该文在未提供明晰证据的前提下(当然确实也无法找到),极为自信地声称位于今依兰一带的元明之际的女真三万户深受兀良哈蒙古的影响,理由是当野人女真迁徙到朝鲜边境时,李朝方面即称这些女真人为兀良哈。①P.Crossley, “ The Tong in Two Worlds: Cultural Identities in Liaodong and Nurgan during the 13th-17th centuries”, p33.看来在处理人群源流问题上,作者这时又从当初判定“两个佟氏”同出一门的“同姓同宗论”原则向“同名同宗论”原则游移,故将朝鲜北部的兀良哈人与兀良哈三卫直接比附。
然而,自20世纪以来,研究明代东北史的学者专家虽然人数众多,但却鲜有将两者直接联系者。相反,他们大多主张朝鲜史料中的兀良哈绝非大兴安岭东-南一侧的由泰宁、朵颜、福余构成的兀良哈三卫。前者是女真人或其亲属,系满-通古斯语族成员;后者在元明之际已是较为典型的蒙古人。欧美明代蒙古史研究权威司律思为了防止西方读者弄混淆,在其关于明初女真人的专著中提到女真系兀良哈人时径直用“假兀良哈”(pseudoUriyangqad)这样的表述,还曾特地写了一则注释以澄清两者的区别。②H.Serruys, Sino-Ĵürčed Relations dиring the Yиng-lo Period,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5, p41, p52n84.其实兀良哈(Uriyangqad)一词并非民族专名,只是通古斯语“山林中人”之意,用来指代生活环境类似彼此却未必有关的各森林部族。③Käthe Uray-Kőhalmi, “Tungusen in Der Geheimen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55/1-3, 2002.因此,如果以同名为由,断定不同记载中的兀良哈之间必定有起源关系,那无疑于宣布所有北亚-东北亚的“山林中人”皆出一源,显然经不起事实检验。何况朝鲜史料中并未像柯氏想象的那样,将兀良哈与冠以佟姓与李姓的建州卫集团随意相混,只是有时笼统地皆以野人称之。实际上关于这些频繁见于李朝史料的兀良哈部,早有学者作过专门研究,将其大体比定为明、清与朝鲜之间的女真瓦尔喀部。④田中克己:《清鲜间の兀良哈(ワルカ)问题》,《史苑》20卷2号,1959。上述瓦尔喀(兀良哈)人在明代属于毛怜卫下的女真集团,分布在从朝鲜北部到今吉林南部的区域内,对明和李朝常保持政治上的两属臣服关系。⑤增井宽也:《明末のワルカ部女直その集团构造につぃて》,《立命馆文学》第562号,1999年。他们与原居依兰一带,后来发展为建州卫的三万户女真在起源和分布上截然不同。因此,柯氏自信可为定论的出发前提一开始又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
那么《始祖神话》在确信女真三万户与兀良哈三卫的相互混合性这一错误前提的基础上又做了哪些进一步的递推呢?她将“三万”(ilantumen)或“三姓”(ilanhala)中的数词‘三’作为问题切入点,极其主观地把它与兀良哈三卫中的‘三’联系起来,认定所谓的三万或三姓实际上指涉的就是兀良哈三卫联盟(Sanwan was for a time the Ming name of Ilantumen; the later Manchu name was Ilanhala.The name seem to refer to the tripartite confederacy, the Uriangqa)。对比前文,柯氏此处的推理又跳跃了一大步,现在她已经确信女真三万户和兀良哈三卫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溶性,而是可以不加限制条件地直接勘同,合二为一了。在取得了这一“考证成果”后,她随即将其作为前提背景来重新诠释布库里雍顺传说。于是,她终于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布,基于开国神话中提到的将布库里雍顺奉为国主的三姓正是兀良哈三卫,所以这一始祖神话实际上反映了满洲统治家族起源于兀良哈人集团的历史史实。故布库里雍顺时期的政体基础是一个由女真人和兀良哈人共同联合组成的政治同盟。同时该神话表明爱新觉罗家族的远祖在元代的真实身份是管控三万户兀良哈人的斡朵里万户长。以上认知堪称她在清朝开国神话问题上“发前人之未发”的最好写照。其实上述惊人结论的出台不过是为她最终主张的“女真蒙古不分论”这一族性晚出命题铺路架桥而已。所以,当她在十几年后出版的《透镜》中引申认为明代海西扈伦女真诸部被建州方面一概看作非女真的蒙古人,就并不出乎读者意料了。①P.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p205.质言之,在柯娇燕眼中的元明东北,蒙古与女真两大人群高度混合,因此根本无法依从“族性”的标准将其从容区分。当时既不存在族别意义上的蒙古人,也不存在族别意义上的女真-满洲人。反映满洲始祖起源于兀良哈三卫的布库里雍顺传说就是证明这一论点的最佳直观例证。此认识当然和她之前在“两个佟氏”中标榜的入关以前的女真-满洲人并非民族团体,仅是文化共同体的主张毫无矛盾,并且两者还可以相互配合与支持。
此外,她关于该传说的一些其他认识也需要我们认真斟酌。她由于并不了解此前学界对《天聪九年档》的研究利用情况,而仅仅以《清史稿》为文献依据,所以不加考辨地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清朝始祖传说在地望上始终是围绕长白山地区展开,所谓的布库里山也是在广义的长白山一带。二,布库里雍顺传说故事是在努尔哈赤时期得以体系化,不仅是源于努氏借此来突出爱新觉罗氏的出身高贵,而且试图让所有归顺其统治的人群都编组为氏族的形式,所以要用布库里雍顺来为其他女真氏族提供一个祖先样板,表明努氏一族对其余女真各氏族的统治从其神话般的远祖那时就开始了,遂导致后来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收的大多数氏族皆将其历史追溯到一个出现在年代无考的相当于布库里雍顺的远祖。关于第一点,松村润指出布库里山的原型应是黑龙江中游北岸的薄科里山,而《天聪九年档》中的这段故事并未提到长白山。因此要说这一始祖起源神话一开始即围绕长白山展开,显然与该史料所记存在矛盾。关于第二点,尽管现在学界在皇太极之前的爱新觉罗家族是否知晓该传说存有争议,但即使其知道若干关于该传说的具体信息,也应当是远未体系化的零散片断。所谓努尔哈赤时代该传说已经被体系化的观点显然无法成立。而作者所分析的努氏利用该传说的政治动机也不具备说服力,把布库里雍顺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的各氏族祖先进行类比尤属误解。这是因为到《通谱》编制的乾隆时期,除了少数大族以外,多数氏族根本就无以提供相当于“史前史”的其氏族最初形成时的祖先事迹,往往仅能上溯至努氏崛起之初的“国初来归”阶段,因此只好相应地把“始归顺之人”立作谱牒中的祖先,从而在时间上完全不能和布库里雍顺相提并论。柯氏因为未能掌握关于该传说的第一手资料,又没有认真阅读了解《通谱》所记氏族祖先的一般情况,仅凭主观想象,故产生了上述不合史实的臆断。
最后柯氏本文在对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下令以满洲代替诸申一事评述时,仅仅简单地说满洲一词此前的用法含义皆不清楚。这又反映出他对当时清史研究动向的相当隔膜。三田村泰助依据《满文老档》中所见的满洲用法,早在1936年就撰文论证满洲实际上是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时起的国号名称,力辩该名称决非天聪九年才初次出现。②三田村泰助:《满珠国成立过程の一考察》(初刊于1936年),收入氏著:《清朝前史の研究》,第467-492页。作者特地在相关附记中就此问题补充了自己的先前看法。类似观点也参看今西春秋:《MANJU国考》,塚本博士颂寿记念会编:《塚本博士颂寿记念仏教史学论集》,京都:1961年,第68-71页。他的观点得到一些日本学者的响应,唯在日本以外一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到1972年,神田信夫通过证实分析满洲一词在比《满文老档》更原始的《旧满洲档》中的万历四十一年记事等的出现情况,再度坚实了三田村氏的旧说。①神田信夫:《满洲国号考》,收入《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第155-166页;后收入氏著:《清朝史论考》,第22-33页,并附有作者的三则补注。自此以后,满洲名称的最初出现时间不始于皇太极的论点大体得到了解决。②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旧满洲档》中的记事足证皇太极始创满洲说之不确,惟对神田信夫满洲国号一直延续到后金时期的论断尚持保留态度。参看薛虹、刘厚生:《〈旧满洲档〉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上述研究成果在柯氏正文及注释中均无体现,显然是她对如此重要的研究资讯了无所知所致。这也再次从一个侧面照见出柯氏对满文史料在清史领域中的应用进展并不真正关心。
相比前两篇论文来说,1987年问世的《〈满洲源流考〉与满洲传统之定型化》(以下简称为《源流考》)则可以看作柯氏“清史工程”在理论探索上的大体完成。这篇论文所揭示的理论命题之多,在当时北美学者的清史成果中,可能算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因此也就更值得我们在此详加研讨。在对其理论命题进行追问之前,拟照例先讨论其文所犯的一般知识性讹误。首先,既然柯氏一文以乾隆年间成书的《满洲源流考》为中心,那么必然涉及对该书相关内容的引用与理解。遗憾的是,其中时常可见因为断句失误等导致的文意理解乖谬。以下试以她对书中的《乾隆皇帝上谕》相关段落的具体理解为例稍加说明。③[清]阿桂等编撰,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满洲源流考》,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前叙”第29页。关于《满洲源流考》编撰的政治背景,参看Niu Guanjie(牛贯杰),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Qing Empire’s Political Influence: Based on the 满洲源流考Manzhou yuanliu kao”,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58/1-2, 2015.
若我朝乃明与国,当闯贼扰乱,明社既移之后,吴三桂迎迓王师入关,为之报仇杀贼,然后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统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中略)要之仍系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哩池。即在长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纪》称唐时靺鞨,有渤海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是金之先即有字矣。而本朝国书,则自太祖时命额尔德尼巴克什等遵制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后因式微散佚,遂尔失传,至我朝复为创造,未可知也。
这段文字的白山黑水系东北地区自古以来的常用地理指代名称长白山和黑龙江,两者在结构上属于并列关系。对此历来没有疑问。可是,柯娇燕在译释“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时却误解为前者从属于后者的“黑龙江地区的长白山”(at Changbaishan in the region of the Amur)。实际上,长白山虽然是图们江、松花江等水系的发源地,但与远在其北的黑龙江地区绝非同一地理单元。这是只要稍微检视地图即可知道的普通常识。而柯氏对此却竟然毫无所知,可见其对于她所研究的东北地理暗昧到何种程度。其误导性质堪比她曾在另外的论著中犯下的混淆巴尔喀什湖与贝加尔湖的错误。附带指出的是,正因为她为长白山相对黑龙江的地理方位茫然无知,又酿成她随后所做的相关诠释彻底错误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将在以后的篇幅中续加辩证。
而在接下来的译释中,她称金史将唐代靺鞨人的情况包容在十篇以上的渤海国王传记中,他们代代以来皆有文字礼仪(The Jin annals for the Moho peoples of the Tang period include more than ten biographies of Bohai kings, who for generations has a literary script and rituals)。此处将“又《金世纪》称唐时靺鞨,有渤海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错断为“又《金世纪》称唐时靺鞨,有渤海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同时误解动词‘传’为名词“传记”。这与原文含义出入之大,一望便知。她随后又解释称,那些有文化的渤海人即金代女真人的祖先。显然,她又把“是金之先即有字矣”中的“是金之先”与后面本应连读的文字错误地断开,并与上句“有文字礼乐”相属。这样渤海人就非常荒诞地被她当成了金代女真的先人,并视之为乾隆心目中的女真起源观。作者之所以这样理解,其实是想借此证明她本文中论述的一大主题:乾隆时期的满洲人竭力塑造一种东北亚统治人群代代相传,从未中断的种族谱系(详后)。可惜她的以上释读却经不起最基本的原文核实。
而柯氏对最后一句的解释则是,乾隆以为,根据当时的常识,不能确定是否清朝已经成功地重构了早已湮灭的当初金代女真人创制的那种文字。照此一来,仿佛乾隆本人连作为国书的“清字”在起源上仿自蒙古文字的知识都不具备,以致不排除它和12世纪出现的金代女真字还有瓜葛。其实乾隆表达的意思是,金代女真人或许已创造了文字,但久已失传,而太祖开国之初命人所创的沿用至今的国书,应当被看作女真后裔在前者湮灭的前提下进行的二度文字创造工作。事实上,在《满洲源流考》卷十七《国俗二 政教附字书》中,史臣即引经据典,将乾隆上谕中的这一见解补充论证为“金初尚用契丹字,至金太祖始制女真字……至蒙古字行,而女真字遂中辍……我太祖高皇帝创制国书,精详简括,虽语言与旧俗不殊,而文字实不相沿袭云。”①[清]阿桂等编撰,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满洲源流考》,“正文”第329页。如果乾隆上谕中确有微疑满文源自女真文之意,作为臣下怎么可能以如此决绝的语气宣布“我太祖高皇帝创制国书……而文字实不相沿袭云”,断然驳正始于皇帝的“御意”猜想呢。此外柯氏对该段文字前面中的“定鼎燕京,统一寰宇,是得天下堂堂正正,孰有我本朝乎”的译释是,本朝实现完成了一切大任,并承载着所有帝国合法性的象征物(the dynasty has accomplished all the tasks and assumed all the symbols of a legitimate empire)。这种十足当代西方学究式的蠡测未免与该段文字中所刻意表达的那种自康熙以来清朝官方不遗余力予以宣扬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政治思想相距太远,毫无相通之处。②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可以断言,她完全不了解这段表述背后的深刻政治含义,更无从触及乾隆在师法其祖,重申此论时的思想动机和历史背景。综上来看,柯氏的汉文文献理解能力明显偏低,相比专业学者应当具有的知识水准尚有相当距离。这一点构成了其在解读原始文献中的突出弱项。
按照《满洲源流考》的编排体例,全书正文二十卷中,居首的七卷均为“部族篇”,凸显出“部族”一门在全书当中处于最为重要的中心地位。那么所谓“部族”的含义应该如何理解呢?柯娇燕给出的定义性解释是复数意义上的“氏族和部落”(clans and tribes),并且更为强调氏族的义项,因此才将正文中的重要一节冠以“《满洲源流考》的起源构思在于氏族”的标题。可是《满洲源流考》中的部族恰恰不是以氏族为主的“氏族和部落”,而是近于民族的人群团体或单位的意思。对此只要稍稍浏览是书凡例对于“部族”的界定即知:
谨拟首立部族一门,凡在古为肃慎,在汉为三韩,在魏晋为挹娄,在元魏为勿吉,在隋唐为靺鞨、新罗、渤海、百济诸国,在金初为完颜部,及明代所设建州诸卫,并为考据异同,订析讹误,博稽史传,参证群书,分目提纲,各加按语,俾源流分合,指掌了然。①[清]阿桂等编撰,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满洲源流考》, “前叙”第31页。
据此可知,此书中所涉及的部族实际上皆是古代相当于民族的实体(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建州卫)或者有关政权的名称(三韩、新罗、渤海、百济),只有其中的“完颜部”似乎带有部落的色彩,但也绝非氏族一语可以概括,因为金代完颜部下面又有宗室完颜、同姓完颜、异姓完颜之分;况且核以本书正文中《部族七 完颜》的具体内容可知,其重在概述辽金女真的整体历史,绝非仅限于完颜一部的部落史。故柯氏将此处的部族解释为“氏族和部落”,实属大谬不然。需要指出的是,柯氏自己曾在注释中提到“氏族”一词的满语对译词是哈拉穆昆(hala mukūn),但她却未去查考《满洲源流考》满文本中“部族”一词的满语对译词语以澄清其义。实际上《满洲源流考》满文本内“部族”的规范性满语对译是aiman mukūn(部-族),绝非与氏族有密切对应关系的哈拉穆昆。②前引凡例中关于“部族”解释的文字的满语对应部分参看承志:《中国にぉける「满族史」研究》,《东洋文化研究》第10号,2008年,第332-333页。其中来自蒙古语“爱马”(aimaq)的中心词aiman即部落、部族等大范围地域性人群团体的含义,非指代范围相对狭仄的血缘性氏族哈拉可比。③E.Hauer, 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 Tokyo- Wiesbaden, 1952, S19.关于柯氏此处所犯错误的意识根源,本文将在下面继续探讨。
柯氏此文第768页还有一处解释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她对牛录(niru)的解释为旗(连队)(Banner〞companies〞)。似乎对牛录与旗(固山或和硕)的各自定义并不清楚,以致发生了概念上本应避免的混淆。事实上,她在2010年出版的一部新书中再次将牛录译释为复数意义上的旗(banners)。④Pamela K.Crossley, The Wobbling Pivot China since 1800: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Wiley-Blackwell 2010, p22.显然,将牛录与旗这两个满族史研究中最基本概念的定义混为一谈不该是专业学者所出的差池。同页还有一处十分刺眼的讹误,即将鳌拜辅政结束的时间莫名奇妙地确定在顺治尚在位的1651年,而且这处错误不像是通常粗心造成的数字上的笔误,因实际结束时间是在1669年。作者在第770页提到了皇太极在1635年对于源自黑龙江地区的三仙女始祖传说的关注,但是又把向其报告提供这一原始传说的虎儿哈人误解成瓦尔喀人,声称这导致皇太极憧憬爱新觉罗氏起源于瓦尔喀人等东北女真部落民。
该文第779页也存在并非一般性疏漏的常识性错误。她将八旗组织中的汉军对应名称释为尼堪,这显然是此前《两个佟氏》中误判尼堪身份的继续延伸。如前所述,八旗汉军的满语名称是乌真超哈,而抚顺尼堪等三类尼堪则是八旗满洲旗分下的具有汉人起源背景的依附性旗人群体,与作为正身旗人的汉军绝不相混。据此可知,柯娇燕对于当初所犯的错误毫无体察。同页还有一处虽非知识性失误,但却涉及作者学风的不能不提的细节。她在文中指出,由于乾隆时期发生了满人和汉人之间文化界限模糊的现象,直接导致乾隆对于满洲性的衰退忧心忡忡。她还在未具出注的情况下特地指出满洲性的满语对应词是manjurarengge。如果这一词汇当时确实存在,这自然对于她的观点颇有助益。然而,早有学者对之表示怀疑,缘于清代的各种辞书并未收录该词。①姚大力、孙静:《“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21页注释3。笔者也认为,所谓的表示“满洲性”的manjurarengge从词语的派生形态上看不像一个当时实际存在的满语词汇,它或许是作者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有力性而生造出来的。②笔者曾就这一问题请教了相关专家,他们一致给出了否定性的意见。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里就不必透露个中详情。不过因为捏造伪证促成己说对于专业学者来说,诚为学术声誉攸关之大事,所以作者此处的表述究竟属于未明示出处所造成的技术性失范抑或另有其他原因,本文不拟对此盖棺定论,只是翘首期盼“新清史”的辩护者能够为她找到该词的确切出处以及有关用例,以免让读者对其学风产生本不必要的误会与怀疑。值得补充的是,在其随后发表的有关论著中,柯氏不断强调乾隆前后“满洲性”意识对于满洲人的群体认同所促生的重要作用,同时她所提供的注释出处即是本文中的上述表述。因此并非笔者挑剔,manjurarengge作为“满洲性”的真实性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柯氏也理应拥有就此疑问彻底证实自己观点的机会,那怕这并不出自她本人的澄清也好。而在该词的可信度坐实之前,尚不宜断然肯定乾隆时的旗人具有所谓“满洲性”的观念。
同文第780页旧话重提,把佟卜年狱事的产生归因于明人视其为努氏同宗。此点前文已辨析过,佟卜年的最终定罪是源于他和佟养真的同族近亲关系,明廷并未认定其具有女真血统。第782页作者声称从乾隆朝开始,随着清朝致力于创造东北亚的政治文化认同,许多以东北地区为主题的著作应运而生。其中她举出的例子有松筠的《百二老人语录》和吴桭臣的相关著作。实际上《百二老人语录》并非以东北作为主题,其涉及中国历朝人物的事迹和言论的典故占了全书的最主要部分,分量权重明显超过该书所记的边疆史地部分,这恰恰反映了18-19世纪之交像松筠这样的上层旗人自觉仰慕学习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现象。本文以后在涉及旗人汉化时,还会具体就此加以阐述。不知柯氏对于此书的满汉文本是否真的寓目,以致做出上述与内容十分不符的判断。吴桭臣则是清前期康熙时代人,其在宁古塔一带流寓客居时正值17世纪下半叶。柯氏竟然把他当作19世纪时的人,疏失如此明显,恐非一时失察所致。
在指出了其文所犯的一般知识性失误以后,下面需要着力检讨的就是作者其文中形形色色的知识性误判最终是如何汇聚积累成宏大叙述主题的。该文叙述的头绪诚然众多,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复杂纷繁的叙事线索中清理分解出三大主题:一,历史叙事的氏族中心主义;二,政治建构的东北亚主体论;三,18世纪以来满洲认同的标准变迁及皇室的相应对策。上述三个主题的交集之处即《满洲源流考》的成书。先来分析其中第一个叙事主题的形成经纬。
作者此文秉持的氏族中心主义直接渊源于前一篇《始祖神话》中的一个结论:努尔哈赤将布库里雍顺神话体系化并作为政治工具,以便造成爱新觉罗家族对女真各氏族的统治源于其始祖的悠远时代。而现在柯氏又进一步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深加发挥。她强调指出,该始祖传说的政治目的在于接续金朝,其与努氏在17世纪初期筹划建立后金国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前后努氏家族的统治对象依然是女真各氏族(虽然其与金代氏族的对应关系已有所断裂),此点影响到1616年后金建国后的基本政体仍属于氏族联合基础上的大女真联盟(the massive Jurchen federation),具有部落国家(tribal state)的特征。从国家的基层社会来看,随着努氏着手推进后金建国,旗制也开始处于形成之中,而所谓的牛录单位(如前所述,柯氏此处对旗和牛录有所混淆)即以氏族为基础建立。以上可以说是柯氏假定的后金建国前后的基本社会背景,显示出她完全是以氏族为中心展开学术思考的。那么她的这一概括与当时的基本史实又有何出入呢?
首先,前文已经对此说前提即清开国传说的体系化源自努尔哈赤时期的误导性做过探析。简言之,该传说的真正体系化当发生在皇太极统治期间。不错,努氏以金作为国号,确实彰显出其欲接续金朝的政治用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将其家族对女真人的统治推远至渺远的古代才能赢得女真各部对其的衷心拥护。何况,即使以皇太极时期定型的该传说而言,作为天女之后的爱新觉罗先人所统治的属民基本只限于女真国的三姓人(ilan halai niyalma),并不包括曾为金朝皇帝所统治的女真各部。因此,该传说的出笼根本无以证明清室远祖在历史上长期统治过所有女真人,所谓通过定型化的该传说来接续金朝正统的立论前提并不成立。这一点是我们评价柯氏此文率先需要认清的。
其次,试以从努氏起兵自立到后金建立的这二三十年的情况来看,氏族组织在其政权内部真的还能保持那么大的影响力吗?作者一方面将旗制的产生归于后金建国时期,诚然失之于晚;①清史学界一般认为,努氏约在1601年对传统牛录制进行体制上的整改,不久或稍晚形成了四旗,而到后金建立前夕的1615年已经完全从制度上形成八旗。另外细谷良夫提出,四旗化时期对应的是统合了建州各部的满洲固伦阶段,而后来的八旗化时期则对应统一了海西各部的女真固伦阶段。参看细谷良夫:《マンジュ·ゲルンと「满洲国」》,收入《シリ-ズ〈世界史へ问ぃ〉》8《历史のなかの地域》,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第124-129页。另一方面又着力指出氏族才是大多数牛录形成的基础以自圆其说。可是,牛录与氏族确有如此紧密的对应关系吗?作为最初行师出猎单位的牛录本来是明代女真社会的临时特定性组织,从起源上看,它是在族寨基础上编设而成的。正如《满洲实录》卷三所记“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族对应的满文词汇并不是表示氏族的哈拉穆昆,而是具有家族、宗族之义的乌克孙(uksun)。②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词典》,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它虽然也属于血缘性社会组织,但其涵盖范围无疑要比氏族小得多。寨是指的噶栅(gasān),基本上属于地缘性社会团体。③旗田巍:《吾都里族の部落构成——史料の绍介を中心として》,《历史学研究》第5卷2号《满洲史研究》特辑,1935年,第83-114页;鸳渊一、户田茂喜:《ジュセンの一考察》,《东洋史研究》卷5第1号,1939年;刘小萌:《明代女真的地缘组织——噶栅》,《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其中旗田氏以吾都里部落为例论述的明代女真社会的部落集团已经不再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观点得到了后继学者的支持。因此,最初具有临时性的牛录在起源上并不依托氏族而成立,只是具有一定的血缘组织性。降至17世纪初,努氏通过改造牛录组织,使其逐渐转变为固定化的耕战社会组织并大大扩展了其成员人数,遂导致新成立的牛录作为地域性社会组织的特征持续增强,而与氏族等血缘组织的差别进一步加大。故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的八旗制度更是基本按照地域原则组建而基本不再借助血缘关系统合民众,这最终促使后金开国以后即能够水到渠成地结束氏族部落等血缘性团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情况。①旗田巍:《清朝八旗の成立过程に关する一考察——とくに牛录の成立につぃて》,《东亚论丛》第2辑,东京:文求堂,1940年,第71-93页;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旗田氏着重论述了新整编的牛录在人数上已经大大超过原先血缘-地缘性社会组织族寨(部落)的平均户数,故一个新成立的牛录往往是在归并了若干族寨的基础上才形成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社会组织关系也被打散重组,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成崭新的八旗制度。陈文石也论证指出,牛录的构成是从氏族社会的废墟基础上建立而成,继而努氏从便于指挥操控的目的出发,对其加以组织制度化的调整统一。参看氏著《满洲八旗牛录的构成》,收入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546-548页。因此氏族组织在后金建立前后的历史期间,其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总体上已呈明显衰退之势,故绝对不可像柯氏那样用氏族基础上的部落联盟来定义1616年成立之初的后金国。②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努氏的建国自立,并非基于部落间的联盟,而是基于对周邻各部的征服,只不过这种通过武力征讨手段实现的强制性统治被人为地披上一层拟氏族色彩的外衣,粉饰性地称作收养(满语作ujihe)而已,努氏本人则被相应地尊为汗父,并取得了所谓天授养育诸固伦英明汗的最高政治头衔。参看蔡美彪:《大清建国前的国号、族名和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简言之,由于她在考察明代女真社会基层组织时,只重视血缘性组织而完全忽略像噶栅这类地域性组织,甚至对于前者也仅仅关注氏族而不及乌克孙这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作用更突出的家族-宗族,同时缺乏从变动的视角来看待牛录的改组与扩大,因此提炼出的结论每与史实凿枘不合,只能服务于其原本即基于误解的既定前提。③中山八郎指出,努氏起兵时女真社会中流行的所谓同族团结与其说是依靠范围较大的氏族,不如说是依靠小范围的家族;而同一氏族内部此时屡见不鲜的贫富分化现象也促使原先依托于同一氏族的共同经济生活渐受破坏,加上政治形势的持续动荡,使得血缘性氏族组织已显得极不稳定。总体上看,当时女真社会的基本背景是氏族基础业已崩溃,但武装冲突之类的特定场合还残存着氏族的色彩。参看氏著:《明末女真と八旗的统制に关する素描》,《历史学研究》第5卷2号《满洲史研究》特辑,1935年,第119-123页。
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柯氏还要将这种虚幻的“氏族中心主义”贯穿到以后的各历史时期中。这清晰无疑地体现在作者在此文序言中所做的概括:氏族及部落联盟传统所赋予的分权政治一直影响作用于清朝入关以后,成为清朝皇帝实现君主集权制与行政官僚化的最主要障碍。在她看来,在后金国成立之后,努尔哈赤固然有着削弱氏族政治影响的动机,但更为现实的需求则是将属下氏族与金代女真的联系转化为其对现在新成立的后金国的政治认同,故特意将那些对自己效忠程度较高的氏族改编为世袭佐领管控下的牛录,并积极提倡以氏族历史为中心的族谱编撰书面化工程,足称后来雍乾时期大规模官方性谱牒编撰的滥觞。这里除了依赖错误的立论前提继续推导之外,所谓努尔哈赤时期启动了族谱编撰工程云云也完全于史无征,纯属作者为了配合自己的观点而有意杜撰出来的虚假论据。
当然清朝入关以后,皇权确实和八旗制度存在着不完全和谐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旗主对属下旗人的控制包括其对于旗下相关职务的任命具有的完全处置权均会直接影响到皇权的乾纲独断。此即雍正时期皇帝主导下的旗务改革所发生的基本历史背景。④细谷良夫:《清朝にぉける八旗制度の推移》,《东洋学报》卷51第1号, 1968年。令人费解的是,柯氏此处避口不提旗制曾经起到的这类对于皇权的限制作用,只是把相关现象归结为入关前就已长期存在的氏族部落传统。产生这种解释上的本末倒置现象的原因除了前述她所依赖的错误前提之外,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她对旗(固山)与牛录的区别迄未厘清,误断牛录即旗;又以为牛录的基础在于氏族,遂导致其深信旗的基础也是由氏族构成,所以入关以后旗主与皇权的矛盾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入关以前氏族长与部落联盟首领关系的延续,因此康熙以来的皇帝出台加强君权的各项措施在她看来仅相当于在新形势下对君主与氏族关系进行再调整的过程。正因为八旗被她移换简化成氏族性牛录体制,所以她才对入关以后皇帝开始亲掌上三旗的重要事实视而不见,转而认定在康雍时期,皇帝加强其权力即通过直接掌握一部分被指定的牛录(designed niru)来实现,降至雍正时期基本清除了根植于氏族传统的所谓集体统治(corporate rule)。综上所论,不妨将柯氏对于后金-清朝的基层权力构造的错误认识用下列关系表示为:旗=牛录>氏族。而贯穿其中的思考主线即“氏族中心主义”。
那么到了随后的乾隆时期,氏族的具体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定性呢?柯娇燕认为虽然氏族的政治作用在这一时期确已大为弱化,但在皇室刻意营造满洲认同的时局背景的激发下,氏族又被激活升华为维护满洲认同和清朝统治最主要的象征符号,具体反映在《满洲源流考》等的成书上。如前所述,她特地将其中一节正文的标题拟为“《满洲源流考》的起源构思在于氏族”,以突出氏族在全书体例中的核心地位。当然,正如前文所析,她其实是把书中的“部族”一门偷换成其个人乐于看作的氏族。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诚不足为训,不过读者难免会询问,柯氏为何会如此固执地抱定“氏族中心主义”先行观念不放,以致把含义非常简易明了的“部族”极尽周折曲解成氏族呢?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其汉文理解能力有限所致吗?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其理论根源上。前面曾经强调过,柯氏所畅想的清史宏大叙事的核心即满洲民族生成的三部曲模式。仅仅在该模式下的第三个阶段也即19世纪中后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才得以破茧而出。按照这一理论,凡在此前的历史阶段,即不允许出现“民族”或者与之类似的人群共同体。可惜事与愿违,《满洲源流考》“部族门”下列出的许多人群共同体,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建州等,从历史学的角度观察,恰恰在组成内涵上较为接近于民族,或者说至少与民族不乏相通之处,而不论人们如何对民族一词进行定义。然而,如此一来,则势必将与柯氏视之为点睛妙笔的满洲民族晚出理论直接发生冲突。因此。为了保护该理论的有效性,她只得将这些“部族”统统用与民族差异巨大的氏族来定义,这样至少不会与她一直以来呵护培育的假设命题自相矛盾。所以,她所主张的《满洲源流考》的氏族化论调不过是为了迁就先行观念而作茧自缚,削足适履的产物。在她看来,“民族化”之前的女真或满洲从社会组织规模上看,仅仅属于氏族结合体或其联盟。
柯氏构建的第二重历史叙事即政治建构的东北亚主体论。她对这一叙事的阐述始于努尔哈赤崛起的阶段,而整个叙事的中心即围绕后金-清朝的政治合法性展开。她首先认为,在努尔哈赤建国阶段,其在政体设计上完全排除了来自其敌对方的儒家化的明朝政府架构,转而向两方面汲取政治资源,一是回归金代女真的政治传统,从氏族效忠的角度赢得后者的归心输诚;二是推进所谓的时代更早的渤海政治传统。同时努氏还借布库里雍顺神话宣传其对东北地区各氏族部落的统治由来已久。因此,后金从立国之初,其政治认同的根源即在东北(the Northeast)而非中国(China),所以在政治体制上也形成了与明朝全然不同的以女真氏族联盟为特征的所谓部落国家,实为东北Vs中国的二元对立论的体现。按照她的这一逻辑,后金-清朝在政治认同上对于中国的排斥性从建政伊始即根深蒂固,牢不可破,这堪称“清朝非中国论”在统治意识形态上的源头。然而,不要说后金时期在体制上深受渤海政治文化影响的观点因缺乏实证而难有任何说服力,即使将其政治设计主要归结于金代女真也显得颇为牵强。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固山—牛录制和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具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点,但这并不能认为前者系对后者的直承沿袭,而应归结为社会结构上的一定相近性。①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の成立过程》,收入氏著:《清朝前史の研究》,第317-319页。努氏后金国时的制度起源固然多与明制无关,但也不能像作者这样为了强证己说而一厢情愿地归之于渤海和金朝。实际上只要稍稍留心学界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即知后金政权在制度创立方面多取法师承蒙古汗国的相关制度。②David M.Farquhar, “Mongolian versus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Early Manchu State ”, Ch’ing- Shih- Wen-ti, 1971,pp11-23; 蔡美彪:《大清建国前的国号、族名和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所受的蒙古文化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柯氏为了加强其相关命题的说服力,还具体举出了一个在她看来可以证据确凿地作为“东北亚主体论”出台定型的例证,此即努氏于1618年与明正式决裂时作为出兵伐明理由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她对此的解析可概括为:“七大恨”的内容直接反映出后金立国的地理与文化上的根源皆在东北而非中国,故努氏起初追求的政治理想是与中国实现带有关系平等性的划疆而治,志在统一东北女真而非入主明属辽东。起初明朝也确曾在1608年与努氏达成平等性的互不侵犯对方疆土的正式边界协定,正式承认了努氏作为辽东以外的整个东北的最高统治者的名分要求,但后来明朝没有遵守不得越界等有关协定内容,以致努尔哈赤深信自己正逐渐处于对方的政治拆台(表现在明朝支持与努氏为敌的其他女真各部)和经济侵蚀(听任纵容其民众越界等)的双重打压之下,从而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努氏转而通过夺取辽东来摆脱新生政权所遇到的政治经济危机,并大力宣扬鼓吹后金与以前的金朝在氏族、语言、传统诸多方面的一致,通过凸显自身对金朝的继承性来提升其政权的合法性,将自己定位为领土广大的金朝的延续(辽东当初确系金朝的固有领土),从而把明朝看作又一个敌对性的南朝。
以上这番看似振振有词的论述实际上又因存在着两点致命缺陷而完全不能成立。首先,柯氏对于用以阐发其说的“七大恨”文本并未标注版本出处,但明显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入关以后编撰的太祖实录中的内容。从史源上看,它属于文字内容修饰改动较多的晚出文本,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后金建立之初努氏发布的“七大恨” 原本的真实情况。孟森在1935年即撰文指出,当时收藏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天聪年间木刻揭牓七大恨文,在内容上当较后出《实录》更为接近努氏在1618年亲撰的原文。③孟森:《清太祖之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北京大学史学》第1期,1935年。后收入文集时增补了对于今西春秋相关商榷的补充性答疑。按今西氏的连续两篇回应文章相继发表在《东洋史研究》卷1的4-5号,1936年。而这通时间较早的天聪年间文本恰恰在文字内容上和后来的《实录》本有着实质性差别。它不像后来的《实录》本那样,处处有意夸饰努氏一族自其祖以来,即与明朝地位对等,相反并不讳言其在历史和现实中均服从明朝的藩属称臣关系,所谓“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以久”,“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畸轻畸重,良可伤心”,“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辽东上司,既已尊若神明;万历皇帝,复如隔于天渊”等;并且表明当时在攻取抚顺后正式书写七大恨的目的只是试图“欲使万历皇帝因事询情,得审冤怀,遂详写七恨”,并由汉商转呈明帝切盼回复。甚至该文本后来增加的皇太极天聪时期的文字从内容上看,也显得较为谦卑委婉(虽然如此低调行文自有其特定的政治用意):“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①与后来崇德年间在政治与军事上日益形成的蚕食鲸吞明朝的有利形势不同,即位不久的皇太极之所以在天聪前期愿意提出相较以后条件尚属宽大的议和请求,主要与后金当时正遭逢严重的经济困难,亟需摆脱内外交困的时局形势有关,故其在致明方的书信中言辞卑恭,暂不谋求与明朝完全对等的与国关系,甚至言称“如和事一成,普天之下,尽为你朝廷所有”,期望明朝能够比照先前俺答封贡的标准,给予后金以相应的政治待遇和一定的经济补偿。参看李光涛:《清人入关前求款之真象——兼论袁崇焕陈新甲之死》,收入氏著《明清档案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393-429页。总体来说,正如前人所指出的,虽然有清一代对建州方面曾长期隶属明朝的事实讳莫如深,但在建号大清之前的天命、天聪之时尚不尽然。②薛虹、刘厚生:《〈旧满洲档〉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
故努尔哈赤当初是在承认建州隶属明朝藩臣的前提下撰写所谓七大恨一文的,而其诉求的政治目标主要还是祈求明朝皇帝能够正视建州方面的要求,以妥善解决多年以来存在于建州女真和明朝辽东官府之间的一些悬而未决的纷争积怨;暂未提出既要在政治名分上和万历帝平起平坐,还要在领土疆域上也和朝廷分庭抗礼的较高要求。③当然努氏所说的七大恨虽然内容多为属实,但也不无渲染夸大之处,例如早先发生的努氏父祖被李成梁误杀之事,明朝辽东方面即出于理亏而及时给予了补偿,而且当时羽翼远未丰满的努氏对于相关善后处理也未持异议。故努氏多年之后重提此事,并置其于七大恨之首实有翻旧帐之嫌。另外自从万历初年以来,包括建州在内的女真各部常常越过边墙俘掠辽民为奴,这给辽东地区的正常社会秩序带来很大破坏,故越境之举更是不得专咎明朝一方。实际上,当时熟悉边务的明人对此也心知肚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中转述七大恨的最后一项,即“我与北关、朝鲜,同为藩臣,他厚我薄”,这里出现的建州身份的自我表述,则与前述天聪文本的相关内容如出一辙。④鸳渊一等认为,王在晋所记的第七款虽然看似和《满文老档》中的相关内容明显不符而显得可疑,但考虑到清朝官方史料一向不提努氏和明朝本来的关系,而这一款内容的中心恰好与视明为天下共主的观点一脉相通,因此可能正是出自最初努氏寄送明朝的七大恨汉文原文,而与之存在差异的满文内容则是后来改作。此解释虽然在细节上与下面卫匡国的说法有所不合,但也可备一说。参看鸳渊一、户田茂喜:《清の太祖の七宗恼恨に就ぃて》,《史学研究》第6卷3号,1935年。稍后前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Martini)也记述说,努氏在攻占了辽东边城开原(按当为抚顺)后,并未继续进军,而是用鞑靼文(疑指满文或蒙古文)写了一封长信,由喇嘛转交明朝以求答复。信中内容即陈述他的兴兵出师实乃蒙受冤屈之后仅仅针对地方长官的复仇之举,只要皇帝能够接受他的申诉请求,即可还地退兵以息事宁人。可惜由于明廷一贯采取的敷衍应付的处置策略,导致局势的不断恶化与升级,最终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⑤卫匡国著,何高济译:《鞑靼战纪》,收入[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中国新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96-197页。然而现存入关以后改定的《太祖实录》中,所谓的“七大恨”的写作时间即由原来的努氏攻占抚顺之后被刻意前移到此次征讨行动开始之前,以表明后金对明军事行动的义无反顾,莫之能御和此前双边政治从属关系的一刀两断,彻底决裂。至于原文中那些努氏承认建州为明之臣属,尊敬仰慕明廷为天朝等违碍内容更是被删改得痕迹全无,通篇文字展现的多是建州统治者自从努氏父祖时代起,就与明朝互为平等敌国的政治诉求。
其次,柯氏文中着重强调的1608年之间明朝与建州之间缔结的双边平等协定及努氏由此取得了和明朝对等地位的观点也是出自对史料的严重误读。从历史背景上看,1608年的努氏还只是征服了海西四部的哈达和辉发而已,另外的乌拉、叶赫两部尚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地位。而松花江流域以北及以东的原野人女真各部更是保存着相当的自主性。试问,在这个局势走向还远远未见最终分晓的时刻,明朝怎么可能立即就承认了努氏对辽东以外的整个东北的统治主权呢?而就具体史料而论,七大恨的这一款在入关以后的《武皇帝实录》中作:
虽有父祖之仇,尚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曰“大明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盟言,大明背之,反令兵出边卫夜黑。此其二也。
而与其对应的更接近于原文的前引天聪牓文则作:
先汗忠于大明,心若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见疑,故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后沿边汉人私出境外,挖参采取。念山泽之利,系我过活,屡屡申禀上司,竟若惘闻,虽有冤屈,无门控诉。不得已遵循碑约,始敢动手伤毁,实欲信盟誓,杜将来,初非有意欺背也。会值新巡抚下马,例应叩贺,遂遣干骨里、方巾纳等行礼,时上司不究出境招衅之非,反执送礼行贺之人,勒要十夷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所谓恼恨者三也。
《实录》中彰显后金与明朝地位平等的“大明与满洲”等表述显然不如天聪牓文更近真相,尤其可疑的是虽然当时建州内部极有可能已经使用满洲这一名号,但在与明朝的政治交往中使用它却显得在时间上有些过早,因为目前见到的早期满文档案史料中努氏一方对外使用满洲的场合不早于1613年,并且均是在和蒙古交往的情况下。而天聪牓文则相对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与努氏共同举行会盟的只是明朝辽东官署的一位下属边将,故双方会商的性质决非明朝中央政府与建州政权之间的对等谈判,仅相当于边将与部族首领之间就特定事宜进行的当面沟通,解决分歧。盟誓的主要成果则限于双方各自严格约束己方民众不得私自越境。这正如唐宋以来朝廷在华南山地常由地方官员与部族首领树立铜柱,举行盟誓定界,以禁彼此无故越界之事一样。所谓明朝由此承认了努氏成为东北唯一君主的说法无论是在此牓文内,还是在晚出的《实录》中均无从体现,纯属她个人空想的产物。再从牓文中透露的誓文后来的生效情况看,即使誓文中已有明确规定,但努氏对于汉人越境行为最初还得向所谓的“上司”即明朝辽东地方官府上报申诉,屡屡未得答复后,才按照誓文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行动,由此招致了辽东方面随之实行的存心报复。此外相关内容还透露出,直至万历后期,每当明朝辽东巡抚新上任时,建州一方均需派人备礼叩贺。故其时明朝与建州双边地位的非平等性由此可见一斑。
柯氏随后又继续论述皇太极统治时期的统治合法性。她认为,皇太极在致袁崇焕的信件中再次引用七大恨重申强调明朝对当初1608年达成的边界协定的违反破坏,以谋求明朝考虑再度和后金进行和议的可行性,从而表现出继续坚持“东北亚本位论”的立国理念。这当然是在误解史实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如前所述,这一所谓的边界协定只不过是建州首领和辽东边将之间的一次特定协商而已,对朝廷中枢而言,不啻辽东边防体制内部事务的调解纠纷,因为盟誓双方的身份一为朝廷正式任命的边将,一为曾经接受龙虎将军封号及相应敕书,并不时前来京城朝贡的羁縻制度下的土著首领。现在柯氏却把它一再误读成两个对等政权之间的国际性划界协定,只能说明残存在她头脑中的成见是多么牢不可破。而当皇太极在1636年前后着手改金为清之际,柯氏又断言后者的政权性质仍旧只是一个联盟(Qing federation)而已,其成立的契机背景则是皇太极在这一时期向东北部落民发动了强度更大的扩张和吞并活动,其结果导致他将自己家族的根源和瓦尔喀等黑龙江流域的部落民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她此处混淆了瓦尔喀人和虎尔哈人。虎尔哈首领穆克什喀将有关传说的上报皇太极只是给了一个满洲上层将开国神话体系化的机会,这与重新改定国名并无直接联系。易金为清明显出于皇太极欲与明朝争夺天下,入主中原而特意采取的意在缓和汉人对其疏远感的重大政治举措,这早已成为流行于国内外清史学界的一项几无争议的共识。不过这样一来,皇太极志在统一天下(中国)的政治观念又必将同柯氏文中强调努氏父子两代皆以“东北亚本位论”为立国之本的观点无法共存,因此她不得不再度削足适履,径直宣称皇太极对东北部落民的持续性扩张征服才构成了其国名更改的政治基础。
柯氏此文对清朝入关以后继续秉持的“东北亚本位论”自然主要集中在《满洲源流考》成书的乾隆时期。对她而言,《满洲源流考》体现了以“七大恨”出台为形成标志的“东北亚本位论”在入关以后的接续发展。让人奇怪的是,她先是对业已体系化的清朝始祖神话中出现了长白山这一历来被东北各族广泛尊崇的圣山作了非常离奇的解释:当时俄国人在滨海地区(maritime region)的势力正处于发展之中,而清朝亟需借助发源于长白山的祖先传说来证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即归自己所有。这一推测完全是建立在错误的空间地理前提下。第一,顺治至康熙前期俄方在中国东北的扩张是指向黑龙江流域中游的内陆腹地,尚未抵达临近日本海的滨海地区。这从其兴建的雅克萨等侵略据点的地望可知。第二,长白山一带与当时正受到俄国入侵威胁的黑龙江中游北岸距离甚远,两地相距几乎上千公里。所谓清朝欲通过塑造祖先起源于长白山的传说来宣布对黑龙江中游一带拥有主权的想法简直荒唐至极。作者产生这一念头的根源来源于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她将“白山黑水”误解为“处在黑龙江流域的长白山”,从而误以为两者必处于同一地理单元内,因此就把传说中清朝始祖起源的长白山和清初一度面临沙俄入侵的黑龙江流域串联起来,最终产生了如此不着边际的乖谬解释。而作者推出这番解说的用意目的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清朝在东北进行的疆土扩张,恰是发生在一种国际竞争的时局背景下,当时的沙皇俄国同样急于用武力手段将这一地区据为己有。起初或许两者机会均等,但满洲人通过将长白山这样重要的东北地理元素糅合进开国神话中,从而在政治合法性的塑造上更显得棋高一筹。想必在她看来,对当时的东北而言,矢志坚持“东北亚本位论”的清朝和从西伯利亚南下不断扩张的沙俄其实都是征服者,故两大列强之间只构成一种竞争对手的均等格局而非中国清史学界阐述并强调的那种抵抗与侵略的关系。
而在具体定位《满洲源流考》的性质时,作者的解析也是随心所欲,毫无根据。作者联系此书在钦定四库全书中的分类位置,指出它和同一时期成书的《满洲八旗氏族通谱》均被有意列入地理类,这就直接彰显出清朝希望以此来加强满洲各氏族在其起源历史上和其东北故土的精神文化上的联系。她进一步认为,《源流考》的章节结构反映出朝廷试图强调满洲的起源及认同皆在于东北的政治动机。因此,满洲的政治认同在地理上应该与中国撇清关系,而《源流考》一书的性质则适宜被看作四库丛书中的主流部分(皆以中国为对象)和满洲-东北文化典籍(集中体现东北亚认同)这一四库支流之间的结合点。首先有必要指出,《源流考》和《通谱》虽然都在史部,但各自所处的门纲子目则完全不同。不错,前者确实被安排在舆地类,可是后者在史部中的位置却是传记类下的“氏族通谱三”,属于所谓的“总录之属”,跟地理之书相隔悬远。因此,二者的具体类别截然不同。上述柯氏之说,无论是否出于对四库目录的无知,其实都是刻意将氏族中心主义这第一重历史叙事和“东北亚本位论”这第二重历史叙事联结交汇,而《源流考》、《通谱》则恰恰充当起贯通二者的连接点。
其次,四库馆臣将《源流考》列入舆地类究竟是否在执行“东北亚本位论”的“御意”,我们不妨来具体观察与它同在一目之下的著作还有哪些?按《源流考》位于史部地理类三“都会郡县之属”,与其同目而列在该书之前的著作依次是《吴兴备志》、《钦定热河志》、《钦定日下旧闻考》,而排列在其后的书目则分别是《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盛京通志》、《畿辅通志》。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将它们同列为一类仅仅是一种结合行政区划与地理方位的权衡考虑,根本不是想借此提醒观者注意“东北亚本位论”,故该目所涉的地理著作范围甚广,既有属于内地的直隶、京师、江南,又有边疆地区的东北与西域,实在看不出将《源流考》附于其下就是为了彰显有别于中国认同的“东北亚本位论”。相反,既然《源流考》所在的这一类目总称为“都会郡县之属”,那就没有把东北与西域分列在中国之外的用意,显然它们与内地一样,在行政区划上均属于“都会郡县”的范畴。综上所论,《源流考》既非柯氏所说的以氏族为核心的著作,更非一部意在强调自外于中国的标榜东北亚认同之作。
还有一点需要提出讨论的,即柯氏行文中对“东北”和“东北亚”(Northeast Asian)的混用问题。虽然她在本文前面的大部分篇幅中以使用前者为主,但到结论性的最后两节中,却转而使用后者作为概括性结语的关键词。这也是我们将其命题称作“东北亚本位论”的原因所在。严格地讲,这两个术语的包含范围存在差别。作为历史性的地理概念时,前者或可指代从山海关到库页岛之间的广袤区域,而后者至少还应该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上朝鲜半岛。那么作者为何会在结论部分中使用地理范围更大的“东北亚”一词呢?原来这和她对《源流考》中相关内容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先是在作为此书编撰方针的乾隆上谕中,皇帝明确提到了他对古代三韩国名的见解(所谓韩等于君主的称号汗),同时认为百济、新罗地在今吉林附近。当然作为对御意的逢迎揣摩,《源流考》的正文中也确实把三韩、百济、新罗一个不缺地都列入“部族”门。柯氏即以此判断乾隆的上述见解系先是针对古朝鲜人(ancient Koreans)而发,同时又相信吉林一地本为朝鲜人的国家新罗和百济的领土(the territory of the Korean States Silla and Paekche )。
然而,她的这一判断实际上和乾隆的本意并不契合。后者之所以要求把三韩、百济、新罗的历史沿革也归并到这部计划编撰的《满洲源流考》中,乃是他深信上述国度的发祥之地并不在地理上的朝鲜半岛,仍然位于传统的白山黑水之地。因此从地域和人群的同一性上考虑,他们的先民其实和满洲的先民深具渊源。确切地说,当乾隆明确指出旧史家误汗为韩时(当然这一点纯属附会),他已经将三韩的起源规划在了比朝鲜半岛位置更靠北的东北内陆区域。如果要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达,那就是乾隆的心目中已经隐约形成了一个以北亚为中心的相当于“汗文化圈”的地理范围,即使三韩政权正式立国于朝鲜半岛,但其先民却肇始于这一文化圈。故从血统起源的角度上看,三韩之民并非“古朝鲜人”;这正如后来的女真-满洲人虽然在金朝和清朝都大批入关定居,但从血统上始终属于东北之民一样。百济、新罗的情况与之类似,按照乾隆的理解,“亦皆其(吉林)附近之地”,同样出自白山黑水之间,后来才扩张到了其南的朝鲜半岛。正是出于对御意的迎合,《源流考》的编撰者不得不在后面的相应正文中极尽附会之能事,论证有的百济词汇可用满语解释,而且三韩、百济和新罗的早期辖境都包含东北的部分地区。①[清]阿桂等编撰,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满洲源流考》,“正文”第35-36页,51-53页。与此形成对比反差的是,乾隆在上谕中一字未提早期与新罗和百济长期对峙的高句丽(后来宋金元时代的王氏高丽和明清时的李朝均和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即缘于他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朝鲜土著,故与发源于东北的三韩等族的谱系源流判然有别。惯于揣摩上意的《源流考》主撰者对此也心照不宣,在相应正文中即不给高句丽及其后继王朝以相近的待遇,所以在与满洲有关联的部族门中自然也就不见它们的踪迹。与此类似的是,宋代史书《三朝北盟会编》中曾有揭示女真人源自高丽的议论,即“(女真)本高丽朱蒙之遗种”,而在今存四库文渊阁本中,此话已被删除得一干二净。②邓广铭、刘浦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因此《源流考》编撰的宗旨实际上是欲将起源地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各部族均纳入其中,即使有些部族后来的活动舞台已经超出了这一区域。综上,从《源流考》对相应政治空间的构建看,以白山黑水为参照坐标的东北与地理范围上还应包括朝鲜半岛的东北亚不容相混。故柯氏之失恰在于以现代人的“东北亚”地理观念去硬套古人的政治空间概念,从而极其冒失地把《源流考》臆断裁判为一件承载“泛东北亚情结”的地域本位主义政治宣传品。
柯氏为了配合其对《源流考》的解说,还继续围绕“东北亚本位论”进行演绎,她注意到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朝廷利用四库修史之际,以先前的辽、金、元三史多有译名讹误为由,对三史中的若干非汉语译名专称等重新厘定一事。她的解读是此举正是清朝标榜其来源于“东北亚本位论”的统治正统性的集中体现,即清廷通过它来彰显其统治并非始自1644年的清军入关或者1616年的建立后金,而是继追溯到东北亚最早有史为证的人群之后(如《源流考》所揭示的各“氏族”),还进而在随后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贯穿到相关的王朝谱系中(辽、金、元)。换言之,清的正统性是直接从辽、金、元三朝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这四个王朝共同构成了以坚持“东北亚本位论”著称因而始终外化于中国的一组政权。
然而她的这一解说又是重重地误解了古人。恰恰是在《源流考》编竣前两年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高宗就杨维桢《正统辨》中排斥辽金,突出宋朝的正统观发表议论,正式承认了这一见解的妥当性,公开批判了那种兴起于顺康时期,并一直流行于当时的满洲必须接续辽金才有正统可言的民族狭隘观念,重新树立起清朝接续中原王朝的正统观。用他本人的话就是:“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中略)然馆臣之删除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他将清朝正统承自辽金的观点判定为“曲为之说”再好不过地表明了皇帝本人对其的批判态度,同时他又在承认宋元正统相继的前提下,却将同样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元朝擢升为与辽金性质不同的“中华之主”。至于本朝就更非“本无所承继”的辽金可比,其正统性也即统治合法性源于“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而从“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的统治标准来衡量,清朝的政权性质显然是如同元朝那样,属于中国大一统王朝。实际上,乾隆否定辽金正统论的理论性思考更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即已定形成熟,只不过在新修辽金元三史和《源流考》相继完成的这短短两三年间又数次深化强调而已。①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很明显,位于四库全书编撰工程这一大背景下的上述修史工作的告一段落并即将刊布为他系统梳理自己的北族王朝正统观,继而将之作为最高官方意志正式告谕训教臣民,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当的契机和场合。从乾隆的上述正统观来看,柯氏将之定位成一位致力于从史学层面孜孜打造“东北亚本位论”的符合己意的君主诚属谬托知己。②乾隆生平热衷导引官方独断历史编撰的个人动机主要在于其执意要扮演历史判官的角色,切实左右操控其中的笔削褒贬。此举实际上是通过追求对以往历史解释的垄断权,以凸显现实中君主权威的不容置疑。参看何冠彪:《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收入氏著《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第146-182页。
此处需要补充的是,乾隆在贬低辽金在正统序列中的地位的同时,另一方面还蓄意破除那种强调华夷界限不可逾越的政治理念。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密切配合。他借前者来塑造强化清朝统治天下的合理性并淡化汉人对于异族政权的抗拒敌视心理,又通过后者来消除汉族社会中挥之难去的反满民族主义潜流。正是这种对华夷对立观念倍加提防的潜意识导致乾隆每以多疑警觉的心态审视相关史书,结果大大夸张了传世辽金元三史在译名问题上出现的错讹程度,终至极其武断地揣度以往的汉人史官时常故意“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即动辄选取不雅丑字作为译名以诋毁贬斥,从而暗含森严夷夏大防之意。作为对此前这类带有种族偏见的修史工作的匡正,他重新代之以“传信示公”的口号,来具体指导新近启动的三史重修工程;表面上是要冠冕堂皇地为早已化为历史陈迹的塞北三朝讨还公道,实际上最根本的动机还是欲借此机会来清算终结传统种族观念在史学领域中的深远影响。③何冠彪:《乾隆朝重修辽、金、元三史剖析》,《蒙古学信息》1997年第1期。以上指导方针落实在重修三史事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正其字,弗易其文”即只需改正音译舛误而无须订补增删史实。④三史之中的辽金二史本属早已摈弃了华夷观念的元季修史的产物,当时的元人史臣多对宋辽金采取一视同仁的对等看待,并无显著的厚此薄彼之分。朱明政权建立之初同样承认了元朝的正统地位,故在此政治背景下仓促成书的《元史》对于胜朝自易多有回护,故三史无需“易其文”即已符合乾隆高悬的政治标准。
虽然三史的正文内容未受明显刊削,但乾隆一朝所修的四库全书中却有相当可观的其他史籍中的违碍文字(既有整句表述,又有单个字词)遭到了史官的刻意删除或替代回避,后者的动机不免有希求“谀圣”取悦旨意的一面,同时也源于唯恐因为处置不当牵连致祸以求自保。①相较于雍正朝忌讳党争,乾隆一朝的忌讳重点则转向为种族问题及明清易代的人物及史事,由此导致禁书激增的现象以及书籍原文中大量敏感词汇及正文的削除或移换。参看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收入氏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第428-430、464-473页。关于数量极其庞大的乾隆禁书内容中涉及夷狄论及明清易代的概括性分析,参看冈本さぇ:《清代禁书の研究》,第79-209页。当然乾隆本人更是躬亲督导,通过批评《契丹国志》中所附的宋人充满华夷观念的议论,以指示对于圣意向来诚惶诚恐,不敢稍违的馆臣在该书的钦定重订四库本中清除删去这一敏感内容。②水盛凉一:《清人のみた契丹》,收入荒川慎太郎等编:《契丹「辽」と10-12世纪の东部ュ-ラシア》,东京:勉诚出版,2013年,第271-272页。综上所述,乾隆一方面将辽金两朝置于宋元之下的偏安政权之列,断然排除清朝与二者之间的继承联系,以利于争取人心,树立正统;另一方面却又处心积虑地试图消除长期以来华夷种族思想对传统史学编撰或明或暗的深远影响,以促使汉族士人在思想深处自觉放弃种族观念,更加柔顺地配合服从清朝在汉地实施的统治。它们可以说是乾隆时期处理正统论及传统史学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理解乾隆一朝官方文化政策的关键。然而柯氏对于至为重要的上述两点恰恰缺乏最起码的了解体会,以致得出了与当时史实全然南辕北辙的认知。
最后作为对柯氏“东北亚本位论”批判的深化和小结,笔者拟进一步论证入关以后清朝皇室的自我地域认同是如何塑造成形的。实际上,与柯氏笃信清朝的地域认同指向东北不同,顺治以后的清朝皇帝的自我地域性定位是强调其帝业起自东方。虽然有些汉人士大夫如赵翼称颂帝气钟聚东北,但自从入关开始,清朝君臣上下转而多以东方或东土等作为本朝发祥地的指代方位。从康熙以来直到乾隆的三代君主更是身体力行,再三论述其帝业的肇基始于广义上的东方而非狭义上的东北之地,以刻意淡化回避其中与北方有关的地理因素。(详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的传统地理方位观常常表现出西北对东南的二元切分论。其中的“西北”表征的方位实际上是并列关系的西方-北方,与它构成对比的“东南”对应的方位同样是呈并列关系的东方-南方。因此,作为古代基本地理方位专名用语的西北和东南常常和今人理解的处于地理坐标横纵轴夹角方向的相关方位并不一样。最著名的即《史记·六国年表·序》中那段广为人知的概括:“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文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此处屡屡成为帝业初起之地的“西北”即不能机械地按照通常的字面含义去理解,因为汉高祖赖以成就帝业的巴蜀汉中只能说是位于广义上的西方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西北。降至中古唐宋胡汉政权并立时期,西北又常常成为代指广义上的北方非汉政权所盘踞的地理方位。如北宋时期曾长期面临辽夏的双边军事压力,这使得当时中原人士的御边言论中出现了一个频繁使用的联称用语:“西北二边”。其实这里的西对应的只是偏处西北一隅的党项西夏政权,而北指代的才是初起于东北的辽河流域,以后统治区域从黄龙府一直向西南延伸到长城一线的燕云十六州的契丹辽政权。降至明初以后,当时的士人在涉及边防一类事务中,曾将鞑靼-瓦剌称为“西北二边”,而在论述内地的水利事业方面,所用的“西北”一名系主要指代京师所在的北直隶,并不时包括山陕、河南、山东(其在行政和监察上的派出机构恰恰覆盖了具有监管女真各部职能的辽东)各省区,以对比江南各省代表的“东南”。①吉泽诚一郎:《「西北」概念の变迁》,收入本庄比佐子等编:《华北の发见》,东京:汲古书院,2014年,第37-40页。因此,从传统方位名称用语的习惯上看,清朝帝业的肇源之地同样应属于西-北而非东-南,故清朝本应以‘北’或者其对应的分野作为帝业兴起的地理所属,就像十六国时期的三燕政权或后来安禄山的昙花一现的“大燕”政权。②明朝后期十分流行的“北虏南倭”之说以及与之相关的将蒙古与女真分别称为“西虏”“东虏”的用语,实际上即明指女真为东北方向之虏。
可是自从入关以后,清朝皇帝却开始有意识地在理论上将帝业肇兴地从 “西北”之‘北’改塑修正为“东南”之‘东’,以淡化消除实际地理所对应的‘北’的因素,其结果相当于肇兴之地的基本方位在坐标系上产生了顺时针方向的九十度位移。以康熙为例,他曾经苦心孤诣地“发明”出一种的寓有政治深意的全新地脉理论,表现在其对臣下数度宣布泰山山脉始于关东长白山。这种将传统的堪舆术与地理格物相混揉的理论的出台正是为了证明将东北与中原联为一体的清朝统治具有地脉上的充分理据,而其对应的政治现实即满洲之龙注定将要入主中原。③姚念慈:《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清史论丛》(2009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165-166页。本来如果从清朝龙兴之地所处的实际方位上看,最有资格成为玄烨附会对象的中原山岳应该是北岳恒山,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他却偏偏选取了东岳泰山作为长白山龙脉抵达的最终目的地。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泰山历来贵为五岳之尊,更重要的就是借此来塑造满洲龙兴之地对应东方而非北方的政治理念。不同于北方容易与塞外或胡人产生无法割舍的联系,作为基本方位的东方在《周易》的预言性卦辞中则有一个专门的对应术语‘震’,以后经过汉代五行术数思想的阐发,最终导致易卦中的相关辞文被有意解读为一个极富政治喻义的预言:《易》卦的“帝出乎震”预示象征着新的圣明天子即将兴起于东方。这一与东方有着对应关联的政治预言作为政治家改朝换代、争取正统的绝好舆论工具,在从魏晋到隋唐以来的整个中古时期都极为流行,数见不鲜。④孙英刚:《“黄旗紫盖”与“帝出乎震”——中古时代术数语境下的政权对立》,收入徐冲主编:《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1-114页。因此与日出方向对应的东方(震)相应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体现帝业肇基的一个深富正统意味的政治术语。所以当康熙的这一附会式的格物成果对外宣布以后,在思想上久已接受了清朝正统观的史学家全祖望即在《皇舆图赋》中引经据典地称颂本朝创业为“帝出乎震,人出乎寅”,显然进士出身,娴熟出典的他在揣摩逢迎上意方面已至心领神会的地步,诚可谓当时君臣上下“一心一德”,清朝正统论深入江南士林的绝好写照。⑤关于全氏是否真正坚持民族气节乃至暗藏反清心理的问题,曾在学界引发争议与讨论。近期的一篇总结性论文参看陈永明:《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说平议》,收入氏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3-276页。
这种将清朝的兴起与东方相关联的政治观念稍后又被雍乾两代君主直袭继承并发扬光大。继起的雍正对清朝肇始于东的强调清晰无遗地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中他和曾静的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在专制皇权的淫威面前,原本就见识阅历尚浅的曾静不仅早已在人身上沦为了听任摆布的阶下囚,而且在精神层面上同样处于被彻底制服的认输状态。此时的他除了摇尾乞怜,哀号求饶之外,就只能指望在受审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配合及揣摩圣意来侥幸逃过“弥天重犯”理应受到的重刑诛戮。而恰恰是在这种极富历史戏剧性的一问一答的场合下,无论是身为原告的皇帝精心亲拟的讯词中,还是竭力配合审问一心只求减轻罪责的曾静的口供里均不时出现清朝帝业起源于东方的论述。作为皇帝来说,他是借此机会要向天下人重申澄清清朝创业的天然正当性,因此每每言‘东’却不及‘北’。不仅如此,甚至在他看来,构成已故吕留良犯禁的一大罪名即他在著书中“不知大一统之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①《大义觉迷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据此凡指名清朝为‘北’或‘燕’之类的从传统方位着眼的称谓用法皆被雍正拔高到“不知大一统之义”的谴责高度以进行最严厉的政治批判。这种看似小题大做的挑剔做法表露出雍正极其不欲汉族士人将本朝与方位用语‘北’相互关联的敏感而多疑的深层统治心态。
因此雍正在对清朝帝业兴起的方位所属的陈述上,一再重复的论调始终不离“盖我朝起自东土,诞膺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来为万国臣民之主”和“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②《大义觉迷录》,第68、84页。后一句表述更是在世人面前,置清初统治者平时乐于宣扬的满蒙一家论于不顾。正是迫于皇帝强势诱供的压力,曾静的呈堂供词和最后所写的总结性悔过书《归仁说》中更是充斥着对清朝兴起于东的称颂,甚至不惜借用宋儒陆九渊的格言来表明其在认罪服辜的前提下已彻底服膺清朝的正统性:“见闻渐广,方知东海龙兴,列祖列圣承承继继,不唯非汉、唐、宋、明所及,直迈三代、成周之盛”;“太宗皇帝龙兴东海,政举教修,仁声仁闻施及薄海内外,并未萌一点取天下之心”;“而近代之精英,尽聚东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者,今日方实信得。东海之圣人,其心理固与尧舜同也”;“恭维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无取天下之心”等。③《大义觉迷录》,第27、36、65、154、156页。上述毫无新意,唯知颂圣的阿谀辞藻,累赘重复到了令人刺目,不忍卒读的地步。耐人寻味的是,当达到了预期效果的审问正式结束之后,雍正特地将这本收入了皇帝审讯词和曾静详细口供的《大义觉迷录》公开刊布并颁行内地各府州县,“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地方当局如有违背不遵则将重谴。皇帝如此大事动作的用意显即希望本朝兴起于东土而非塞外等正统观内容能够清晰而牢固地烙印在每一个汉族士人的脑海中,以致在潜意识中都不敢再对清朝统治的合理性稍存疑议。
降至随后的乾隆时期,清廷又不失时机地利用新修的称颂清朝开国的相关著作,继续阐发张大这一理论。作为《满洲源流考》书序的乾隆上谕中开篇即作“本朝肇兴东土,山川钟毓,与大金正同”,皇帝的这一阐释实际上使得历来被看作起自北边的女真金朝(毕竟他本人在评杨维桢《正统辨》时还曾亲口说过辽金起自北边)也获得了与本朝相一致,同样起源于东土的全新地域化身份。而在该书卷一的御制全韵诗中,则有“天造皇清,发祥大东”的词句,这被认为是他有意以五色配五方,而东方适为青色来解释清朝国号的来历。虽然这一解说因多有穿凿附会而未被现代学者所承认,但却寄托着皇帝欲借此进一步强化东方和清朝的联系,使之牢固到密不可分程度的政治用意。①[清]阿桂等编撰,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满洲源流考》,“正文”第2页。关于清朝国号来历的考辨,参看[日本]松村润著,王桂良译:《大清国号考》,《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G.Stary, “Manchu names and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ir transcription”, in.J.Janhunen etc eds.Writing in the Altaic World(Studia Orientalia 87), Helsinki, 1999, p249.前一篇论文认为“大清”的国号来自《管子》中《心术篇》或《内业篇》中以“大清”“大明”连用的典故,并以“大清崇德”作为“大明崇祯”的对立语。后一篇文章则以蒙古语daicin(“战士”)~满洲语daicing(“士兵”)的用法来解释得名原因。与后说相近的观点也参看鲍明:《大清国号词源词义考释》,收入傅波主编:《从兴京到盛京:努尔哈赤崛起轨迹探源》,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92-205页。
而在另一部完全为歌颂清朝奠基而编撰的《皇清开国方略》的御制诗文中,乾隆又将仙女后裔预示的帝系初起直书为“曼殊帝出震东方”,其中的‘震’字似为一语双关,既可理解成动词化的君临、威慑之意,又暗暗呼应了它自古即有的东方之义的所谓传统隐喻用法。随后所附的诗注曰:“国号满洲,清字本作满珠,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盖曼珠音近满珠也”。②类似的表述也见于上引《满洲源流考》中对满洲名称来历的解说以及关于随后的〈御制全韵诗〉中“号建满洲,开基肇宗”诗句的注释。参看[清]阿桂等编撰,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满洲源流考》,“正文”第2-3页。这里乾隆又再度利用佛教观念中东方的汉地由文殊菩萨(Manjurśiri)负责教化的典故和藏人将汉地君主尊称为文殊化身的传统,愈加深化了从其始祖布库里雍顺以来的清朝帝系和东方之间的关联性,既将清朝皇室与东方的联系上溯到远远早于太祖太宗的始祖传说时代,同时还指出了连远在西土的藏人佛教徒都对这种观念抱有高度认同感,更可照见该观念之遍及华裔。③藏人将汉地君主尊称为文殊菩萨的化身的做法,始自元朝,并由明朝接续。参看David M.Farquhar,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tudies 38/1978, pp5-3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皇清开国方略》的满文本中对上述诗句及原注的解释似比汉文本略详一些,例如“曼殊帝出震东方”对应的满文内容(tede dzang ni baci aname dergi ergi i manjusiri amaba hūwangdi seme dahanjiha)的文意是“后来藏地也来归附,并以‘东方的文殊菩萨大皇帝’相称”。④G.Stary, “Ein ‘Kollektivgedicht’ zur Gründung des mandschurischen Kaiserreiches”, D.Schorkowitz Hrsg.Ethnohistorische Wege und Lehrjahre eines Philosophen: Festschrift für L.Krader zum 75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Peterlang, 1995, S249,S254.台湾学者林士铉的译文是:迄今连藏地都仍跟随着称“东方的曼珠师利大皇帝”,似乎未将动词dahanji-“来归顺”的含义明确译出。参看氏著《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9年,第184页。这样经过从康熙到乾隆连续三代君主在理论上的不懈论证,由爱新觉罗家族创建的清朝帝业与东方这一基本方位的对应关系终于从统治正统性的层面锻造完成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道光年间的魏源在著述中一一列举“西北藩服”的地理范围时,已经只包括内外蒙古、天山南北、卫藏青海,而毫不语及像鱼皮鞑子之类的关外边民所居的东北荒远之地了。以后随着咸同年间西北局势的动荡不定,朝野视线中的“西北”逐渐固定在了陕、甘、新等省区,这基本和今天人们对西北的地理概念相同。唯从清末直至民国时期,以包头、归化为中心的绥远仍然时常被认作是广义“西北”的组成部分。⑤吉泽诚一郎:《「西北」概念の变迁》,第42-50页。而另一方面,同样是在太平天国起义进入高潮的咸同年间,清将李元度在致起义军领袖翼王石达开的劝降书中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辩护即“惟我朝龙兴东土,吴三桂敦请入关定鼎,葬明帝以殊礼,令臣民服丧……得统之正,此其一”。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柯氏大书特书的清朝政治认同始终以东北(或东北亚)为本位,以彻底断绝清朝龙兴故地与中原之地精神联系的认识对古人的误解有多么严重,以致它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自我地域定位竟找不出丝毫相通之处。
除此之外,该文尚存在其他一些需要指正的问题,有的地方反映出作者的文献知识准备相对匮乏,还有一些则反映出作者的研究此时已经带有某种“政治化”的潜在动机。例如她在叙述清廷官方刊刻元史时称,“清朝在1739年重印了北京本后,又于1824年刊印了一个经过大量修订的本子”。实际上继1739年以明北监本为底本的武英殿本《元史》刊刻以后,译名经过“修订”后的新《元史》连同《辽史》、《金史》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印。①此取何冠彪之说,参看氏著《乾隆朝重修辽、金、元三史剖析》注释40。而1824年的道光本不过是在此本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改动而已。然而按照柯氏的叙述,乾隆朝在完成了包括《元史》在内的三史译名修订工作后,居然一直没有正式刊印,以致最后拖到道光年间才终于付梓。花费了如此之大的精力,并由皇帝亲自赐序,才最终弄出来的新本竟然长期不见天日,这岂非极端不合情理的咄咄怪事?显然,这是只要稍做思考就不难发现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却始终没弄明白。她还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刊布于1782年。实际上后者是乾隆五十年(1785)底才修成。柯氏大概将它的成书年份与新修三史的刊刻时间(1782)混为一谈了。作者此前对《元史》更早时期的版本传承的叙述也有不当之处。例如她说《元史》最早的洪武本在1370年完成初稿(drafted in 1370),并称北京本《元史》初刊于1606年。她的这些介绍按照其自注提示,系来自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所附的“出版说明”。核查后者,可知洪武三年(1370)并非《元史》初稿完成的时间,而是此书的定稿和相继刊印的时间,“当年七月书成,十月已‘镂版讫功’”。大概作者的古汉语知识较为贫乏,不明白“镂版讫功”就是刻版业已完成的意思,而将其误解成初稿完结。此外,“出版说明”只是说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明朝的北京国子监重刻包括《元史》在内的二十一史,并未确切指明《元史》是在这段时间的最后一年才刊印的。作者此处似乎又误会了“出版说明”的原意。看来作者不光古汉语阅读能力有限,即使对于文白易懂的现代汉语也时有语义上的理解欠周。
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结论之后,还专门附加了一节标题为地方主义的补记(Postscript: Regionalism),由此她开始初次从清朝的视窗向1911年之后的中国现代史窥望探视。柯氏此节的中心思想反映在其中的开篇之语:“在清时期以前,东北只是一个部分地被归并到中华帝国的地区;而在清的统治下,试图使东北保持文化和经济独立的措施颇为显著,而在清朝结束以后,这一地区迅速呈现出再度脱离中国轨道的发展趋势。”如果说以上概括的前面部分只是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作者此前刻意揭橥的东北非中国论的话,那么最后一句话则已暗示出作者所抱的当代政治理念,即以东北为本位的地方主义实际上对于那种认为该地区从空间上应当由现代中国加以继承的民族国家观念是持排斥态度的。换言之,脱离中国版图对于1911年之后的东北来说是一条貌似合理而且颇具可能性的历史出路。为了证明上述合理性在当时的客观存在,柯氏接下来就论证从19世纪晚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伪满时期,许多坚持东北本位论的学者竭力借助学术活动来宣传鼓动“东北地区主义感情”(northeastern regionalist sentiment),并直接体现在清末东北地方性文献的大批编撰和学者们逐步加强对历史上在东北地区活动的各个民族和政权的学术研究,以揭示这种与以谋求中国的自强统一为诉求的爱国主义背道而驰的“地区主义”在当时的许多知识人士那里确有牢固的民意基础。
柯氏的此类解说怀有高度政治倾向,如果说乡土文献的编撰等于鼓吹宣传自外于中国的“东北地区主义感情”的话,那么中国的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的浩如烟海的乡土文献是否也都在鼓吹一种从文化上消解中华统一体的“地方主义”?答案显然是非常荒谬的。毋庸置疑,对本地区文化的关注、研究与表彰并不意味着因此就要排斥中国的统一性。中国的统一性和地区文化的多元性之间绝不是类似鱼与熊掌的那种二者只能取其一的关系。让人苦笑的是,如前所述,柯氏不惜乱点鸳鸯似地把17世纪出自原籍关内的流人之手的《宁古塔纪略》和主要反映旗人谙熟汉文化及其历史典故的《百二老人语录》都找来随便点卯凑数。
而在20世纪体现“东北地区主义感情”的学术成果中,她除了征引积极卷入伪满复辟活动的罗振玉之流的事例之外,更多地强调了金毓黻(1887-1962)的著述与所谓的“东北地区主义传统”的关联渊源性。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作为爱国史学家的金先生决非惯于误解古人、谬托知己的柯氏所幻想的那样,是一位认同东北甚于中国的“地方主义者”。与之相反,本为汉军旗人的他不甘栖身于日伪的反动统治下,毅然在1936年利用造访日本的机会,辗转脱身秘密前往上海,以后相继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和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大学。长期以来作为在政学两界皆有影响与声望的寓居内地的东北人士,他始终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来贯彻宣扬东三省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爱国主张。①关于金毓黻的学术经历及史学成就的全面评价,参看董明琨:《东北史坛巨擘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对这样一位因坚持爱国,治学有成而广受世人景仰尊重的硕学长者,柯氏竟然把他与向来诓主媚日,人品卑污的汉奸政客罗振玉之辈相提并论,并将其学术成绩看作是“东北地区主义传统”动机下的产物,不仅显得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岂非痴人说梦式的佛头著粪,厚诬时贤?尤其可贵的是,金氏忧国忧时的民族感情还直接影响到他对中国古代王朝正统论的认知阐释。虽然身为原籍东北的汉军旗人,并且尤其熟悉擅长辽金东北历史,他本人却在抗战期间出版的《宋辽金史》中,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旗民畛域和狭隘的地域观念,转以中华本位及民族大义为重,推崇褒奖杨维桢《正统辨》中以宋为正统的观念,主张宜“以《宋史》为正史”,“包辽金之纪载”,既将适足代表中华文化巨浸主流的天水一朝高度尊崇,同时又不摈弃辽金两史于外国之列,诚为公允适中,两得益彰的处理方案。他还在同一时期完成的《中国史学史》中高度评价历史观与《正统辨》相近的明代史家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将之嘉许赞赏为远较并不独尊宋统的元修《宋史》更为高明的《新宋史》。②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如此评价绝非要否定辽金两朝和契丹、女真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当时抗战时期的特定时局背景下,金毓黻倡导的以宋为正统,包举辽金的历史观显然更加有利于教育激励国民,以汉族为凝聚核心,联合各兄弟民族共同抵抗外侮。因此,在对金毓黻先生的人格精神和学术成就的定位上,柯氏歪曲误导的程度有多严重,已经无需作更进一步的论证和辨析。而从她的以上与事实迥然不合的种种曲解中,不难发觉现实性的意识形态因素对其学术研究的显著负面影响。
至于柯氏此文的第三个主题即清朝入关以后满洲认同从文化移向种族的变化显然即此前《两个佟氏》中的论点的继承与发展。作者此处又补充论述称,伴随这一过程中,皇权也经历了变化,即它开始了对帝国境内几大人群的意识锻造,使得皇帝高居于其上,形成了个人化特征十分鲜明的君权意识,从而强调可以追溯至祖先的个人化效忠等。①这里先指出柯氏论述中的一处细节疏漏,她以为乾隆时期的多语种合璧碑铭文献中使用的正式文字,除了人们熟知的汉满蒙回藏五体之外,还有梵语。实际上梵语的流通渠道主要还是局限于陀罗尼经文类宗教内容,没有证据表明它在当时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公文书写中已经取得了和上述五体文字相平等的使用地位。柯氏所述参看“Manzhou yuanliu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p780.按乾隆时期曾创制过一种专门用于转写拼读梵语经咒的满文阿礼噶礼字,应用于《大藏全咒》和满文《大藏经》等宗教作品的刊印中。参看G.Stary, “An Unknow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anchu Writing: The《Indian Letters》(tianzhu zi天竺字)”, Central Asiatic Journal48/2, 2004, pp280-291; 罗文华:《乾隆时期满文阿礼噶礼字》,收入氏著:《龙袍与袈裟》(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622-624页。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我们拟结合柯氏四篇论文中的最后一篇《乾隆朝对于汉军旗人的出身回溯》的具体内容来加以评论。而她的这篇长达四十余页的长文反复论述的主题即以汉军旗人为个案,继续拓展始于《两个佟氏》所倡导的满洲认同变迁论这一命题,并将其与不同时期的君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建构相联系,以全面服务于作者有关民族性及皇权建构等中心思想。那么这篇论文在前述论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那些新说呢?以下我们来对其逐一进行剖析。
柯氏是文论述的出发点还是起步于前面我们曾详细解析过的明代东北的汉人(尼堪)只具文化属性的论点,即尼堪只是意味着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Chinese style)。如前所述,她为了回避使用“汉化”(Sinicization)这一本来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话语(试对比陈寅恪以此来分析佟氏一门各支的不同特征和取向),就只得满足于使用如农耕、定居及城市化等既不科学,又不严密的概念来界定这中所谓的中国化生活方式,而刻意回避东北的许多女真人早在明代之前就对定居务农甚至城居等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并不陌生。而在本文中,她为了给自己的这一极不成熟的观点增加稍许说服力,又迂回引用了元代的例证作为类比。她论述称,正如当初被蒙古人泛称为契丹的元代汉人包括了大量来自中亚和东北亚,但已经定居、务农或城居的人群一样,明代的辽东尼堪与之类似,也包含了许多先人本为女真、朝鲜、突厥、蒙古的非汉人群。事实上,尽管元朝的汉人确实包括了原金国统治下的女真-渤海人等东北民族,但是对于原籍中亚-西亚的大量突厥系人群以及阿拉伯-波斯移民,当时的政府则将之定位成广义的色目人(虽然这一概念有时在使用中并不十分严密),即使他们已经定居在汉地,熟谙汉语,从事农商各类生业,甚至还有的家庭已经改用汉姓了。柯氏引用元朝例证来为其说张目的做法,因其纯属个人想象,故实在是不堪置评。
而从努尔哈赤崛起到后金正式建立前后期间的历史叙述,柯氏更是口口声声地强调当时“在女真、蒙古、汉军之间没有制度化的区分”,“女真语中的尼堪(在所指对象上)具备了当时汉语中的汉人一名所没有的灵活弹性”,“建州女真和他们之中的尼堪确实没有公开的制度化和法律上的差别”,而尼堪作为一个待遇存在差异的群体,只是在一定场合下受到歧视对待,如经济地位更为脆弱,相较女真而言容易受到惩罚,并且不被信任等。以上这番喋喋不休的叙述的目的只在于说明在当时的这种缺乏对不同人群进行有效区分的前提下,女真人自然不可能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自我族属意识,因此距离“民族”的衡量标准尚称遥远。可是,她为此举出的例证是哪些呢?首先,她引用了一句清最高统治者亲口道出的对于汉人“原无二视之理”的原话来为已说张目。可是根据其原注,该语却出自入关之后的顺治口中,故柯氏以之论证约半个世纪前的历史的做法不啻关公战秦琼,徒增史实混乱,殊不足取。
其次,她强调努尔哈赤在1619年发布了著名的命令即将原先归附其的汉人享受与女真同等的待遇。根据其文注释,这一点实本于魏斐德《洪业》中的有关论断。核查魏氏著述,得知其实是在1623年而非1619年的时候,努氏下令将1619年以前主动归附其的汉人同以后加入近来的汉人两相区别,而唯有前者方可享受和女真同等的待遇,所谓“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①Jr F.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44-45;[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32页。因此,受到一视同仁优遇的汉人需要同时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第一点是汉人必须归附于努氏“定都”于费阿拉的时期,具体对应的是从1603年起至1619年4月(阴历)移至界藩城之前的这段时间。②户田茂喜:《清太祖の都城迁移问题》(二),《史学研究》第九卷第二号,1937年。第二点则规定了这些汉人的身份只能是“归顺”的良民,即不包括任何战俘或掳掠得来的人口,也即努氏当时厉行的针对汉地的抗者杀,俘者奴,归顺来降者才编户为民,成为佐领下人的既定政策的实际体现。以努氏攻占不久的抚顺为例,主动剃发归降的李永芳及其所部即能享受这种良民的待遇,李氏本人还因此成为额附,名义上或许可被“视同诸申”,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当时抚顺地区的多数汉人则被降斥为奴,成为没有基本人身权利可言的佐领下的依附人口。因此,同时符合上述硬性条件的汉人在整个汉人群体内必然仅占很有限的比例,多数汉人在后金社会中的地位已下降到与奴仆无异的地步。换言之,当时大多数汉人的社会地位较早已具备正身旗人身份的普通女真人来说,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故柯氏以上论断难掩以偏概全之失。
最后,她随后还以达海这类具有汉人或朝鲜人血统出身的“跨境人群”(transfrontiersmen)在后金国所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来表明汉人受到的歧视并不很严重。这一点或也本于魏斐德著作的提示。③Jr F.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p44;[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第31页。事实上,魏氏将达海本人看作非女真人出身的观点并无任何坚实的文献证据,属于较为典型的推论失误。他的根据是《朝鲜李朝实录》所记1595年河世国造访努氏后的报告,“麾下……文学外郎,则唐人投属虏地,几至三十年,而凡通书,此人专掌云”,认为他的职责适与达海相同,因此可以勘同为一。这个名为外郎的“唐人”,也即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中所载的“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云”。仅从此人在1595年时已经投效女真近三十年的情况来看,便可判断他绝不会是该年才出生的达海。当然歪乃虽属女真化的汉人,但却远未有证据表明他在当时的努氏身边起到了类似后来的达海那样重要的政治作用。①关于歪乃,参看王钟翰:《歪乃小考》,收入《满学朝鲜学论集》,第19-24页。至于达海其人,《八旗通志初集》、《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等明记其出自觉尔察氏,实际上属于爱新觉罗氏的宗亲,故其支子孙皆用紫带,而该支属的女性也参照氏族外婚制原则,不需被选为秀女。②敦冰河:《清太祖努尔哈赤族属考——兼论觉尔察氏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渊源》,《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较早德国学者林可曾译注过《八旗通志》中达海传中的内容,参看Bernd-Michael Linke, Zur Entwicklung des mandjurischen Khanats zum Beamtenstaat,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82, SS112-120.因此,以达海为例说明后金当时对汉人“视同诸申”,予以信任实属谬论。或应指出的是,像达海这样高度熟悉汉文化的人如果确有汉人血统的话,那么倒是可以给柯氏历来主张的其时汉人和女真尚缺乏族属之别,故可以在种族血统上互相渗透,而在文化上却存在明显差异的观点提供一些有限的帮助,但是既然此人确系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女真人,甚至还是皇族的远亲,那就表明当时即使作为血统意义上的纯正女真人,也可以在文化上趋于汉化。同时文化上的汉化也不意味着达海即抛弃了本族认同。因此,达海的真正情况恰好与柯氏的设想结果完全相反,即一个人纵然种族出身完全与汉人无关,而在文化修养上照样能够实现深度汉化。
然而柯氏相信后金之初团结信任汉人,无分彼此的主观假设随即导致她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连环推理,即她认为1619年后金国内成立了与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军队相并列设置的独立性汉军(Chinese-martial),而其成员就是由受到努氏同等信任的汉人组成,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未实现编旗化。她推论的理由不是征引任何已知的史料记载,而是相信既然1618年的攻取抚顺使得努氏获取了大量人力资源,那么这应当就是后者次年声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的历史背景,总之两者之间断非巧合。如前所述,她将此番言论系于1619年纯属对魏斐德原作的误解,实际的时间却是1623年。因此,柯氏的整个推论前提也就自动作废了。再以具体史实而论,李永芳归附后不久就被取消了单独掌辖旧部的权力。终天命时期,除了汉人奴仆早已沦为满洲旗下的依附性人口之外,即使具有良人身份的汉人也逐渐被大量改编入满洲牛录之下,从而陆续成为隶属满洲旗分这一新的社会组织下的旗人成员。像投诚汉人中的头面人物李永芳即被置于满洲镶白旗下,其他几位归附的汉官代表情况也与之类似。此外在天命末年,后金在镇压了辽东汉人的反抗以后,更是强制性地将担任农业生产任务的汉人壮丁大批降为满奴,形成所谓“辽东之民,久经分给将士,谊关主仆”的局面。③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02-103页、160-161页。因此,在这种满汉地位差别迥异的背景下,即使后金一方为了弥补缓解军力的不足,需要强征汉人良民及奴仆一起随军出征,那也与后来形成的与满蒙军事力量相并列的制度化汉军在性质上绝不等同。柯氏产生的以上误解,不可谓不深矣。总体上说,正与柯氏的估计相反,努尔哈赤时代(尤其是天命后期)的后金全力推行的一系列带有整体性的民族歧视政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起到了隔绝满汉两大群体的族际鸿沟的效果。
现在柯氏既然错误地以为1619年以降后金政权下的汉人已经渐渐地开始制度性地军士化,成为后金武装力量的一个正式组成单元,但同时又不像女真(满洲)人那样早已入旗,因此她进一步将汉人的这种处境定性为尼堪政治地位的模糊性(political ambiguity innikanstatus)。至此“模糊性”这个看起来有些令人奇怪的术语被她定义为汉军群体的一大突出特征,并常常见于以后的行文中。这将导致她的失误在理论认知层面同样是越陷越深。接着在史实的叙述方面,她径直认为汉军编旗仅持续了约五年的时间(1637-1642),不察汉军的编旗始自天聪五年(1631)的止列一旗,以后相继经过崇德二年(1637)的编为二旗,随后四年的扩成四旗,最终到七年(1642)才彻底形成了八旗的格局。①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第161-164页。而这种汉人入旗如此时间滞后的认识反过来又加深了她头脑中的固有成见,导致她深信八旗体制中的汉军政治经济地位皆不及满洲蒙古实与此种时间滞后性息息相关,而非实际上在八旗内部早就形成的汉满有别的族际鸿沟。因此,在她的逻辑推演中,汉军在后金内部的社会地位先是受制于政治身份的模糊性,以后又由于入旗时间太晚,造成了入关以后该群体的整体地位始终不能和满蒙旗人相比。这等于说,汉军地位长期以来的相对低下与后金—清初统治者刻意经营的族际歧视或差别的总体统治思路无关,只是当时一系列具体政策的不幸结果或意外产物。通过这种错误演绎,柯氏实质上是再次试图回避明清之际已经出现并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民族”或“族性”问题,以便将它们的产生推后到她认定的相对较晚的时期。
而另一方面,汉军旗分从成立之初的仅仅一旗到最后八旗具备则经历了12年的时间,这自然说明汉军编旗绝不像柯氏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在五年间完成的进度甚速的历史事件,而是和天聪崇德时期的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是密不可分的。总体上说,皇太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父对汉人的仇视政策,既允许少部分汉人脱离旗下奴籍,并试图减轻旗主权贵们对于归附汉官的任意欺凌的政治打压和索求无度的经济盘剥(此举曾直接酿成刘兴祚兄弟重新归明反正)。同时又为有效利用汉人所掌握的先进军事技术,成立了由逐渐脱离满洲旗分的汉军组成的炮队武装,但另一方面仍然担心汉人难治而不减其防范心理,更需要保障八旗满洲显贵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不受影响以免动摇旗制根本,所以即使单独化的汉军编旗工作在政治军事上均已势在必行,皇太极却始终拒绝委任相应的汉人旗主(按不应将此与汉人担任的固山额真这一军职混同),仍旧以过去的满洲旗主贝勒作为新建汉军各旗之主,在现实中继续担当着监控统领汉军的角色职责。因此,这种汉军的单独编旗即使显著加强了后金的军事力量,并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善了部分汉人的地位身份,但是在政治上却注定无法削弱足以制约君主集权的旗主权力。与之相对应,在完成了汉军八旗建制的崇德时期,君权仍然不能有效干预插手各旗的内部事务。不过,作为满洲统治集团中的较为成熟的政治人物,身处于维护八旗旧制和渴望成为明朝皇帝般的专制君主矛盾夹缝中的皇太极对于上列弊端也是敏于察觉的,所以在崇德年间将原满洲旗分下的汉人大批单独编旗时,却始终未把在天聪七年至八年(1633-1634)归附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大集团同样援例设旗编为汉军,而是组建成唯听命于君主本人而非各大旗主贝勒的直属性武装力量,以免颇有军事实力的这些集团编旗后反而会加强原有各和硕贝勒的权力从而助长这种军政分权的势头。②细谷良夫撰,王桂良译:《浅论归附后金的汉人》,《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同氏著,曹力强译:《与后金合作的汉将》,《黑河学刊》1990年第4期。以上应该是我们理解汉军单独编旗的基本历史背景。可是现在柯氏既然把汉军编旗错误地理解为一个纯由君主个人意志决定的在几年内即一蹴而就的事件过程,那么她对相关原因的分析也就大大偏离了当时真正的历史背景,表现在她认为汉军八旗的创建动机和崇德初年的设置文馆以收容摆脱旗下奴仆身份的汉人文士一样,均是出于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并削弱贵族权势的需要。这就与事实的本相大相径庭了。
而在对汉军成立史实的理解上,柯氏声称八旗汉军的满语对应名称乌真超哈早在努尔哈赤的时代就出现了,它的出现既与后金1618年攻取抚顺取得了红衣炮需要有专人维护使用这种重型火器有关,而且攻取抚顺所取得的大批汉地人力资源也为成立单独的汉人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1637年重新析旗为二之前,这支尼堪军队的旗色都是与满洲八旗所选用的四色(黄、白、红、蓝)区别显著的黑色。至于“汉军”一词,她认为是在皇太极时代开始流行,原因是后者一向以12世纪的女真金国为学习对象,从后者那里借鉴吸收了若干专用术语,其中就包括汉军一词,因当时的金国就用它来指代华北与东北多地的各定居化人群(peoples of the settled regions of north China and the Northeast)。采取这一名称有助于在以后的征服战争中减少关内汉人对于满洲方面的敌意因为汉军一名就是汉人之义。
以上推论可以说全不成立。首先后金方面取得仿制的红衣大炮是在比抚顺陷落要晚10多年的天聪五年(1631),并在当年的大凌河战役中初次使用。①侯寿昌:《浅论佟养性》,《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关于后金部队装备红衣大炮的代表性系列研究参看田中宏己:《清初にぉける红夷炮の出现と运用》(一)、(二)、(三)、(四),相继刊于《历史と地理》第78、79、81、82号,1974-1975年。故将乌真超哈的出现与抚顺陷落相联系属于倒填日月似的时间错位。再说当时的后金军队中也没有以黑色作为军旗颜色的部队,直到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归金之后,皇太极不欲使之编入汉军旗,这才给他们的部分配以黑色作为军队旗色的标志,即孔、耿两部各为黑色旗或镶白边的黑色旗,稍后尚部则使用带白圈的黑色旗,以与八旗军队在旗色上明确分开。②《清太宗实录》卷十五,天聪七年八月丁亥条;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甲辰条。参看上引细谷良夫两文。因此认为努氏时代就有了以黑色为旗色的乌真超哈的提法等于犯了双重错误。况且从天聪五年才开始单独编旗成军的汉兵并未被立即赋予乌真超哈(“重军”之意)之名,最初只是被简单地称作旧汉人之兵(fe nikan i cooha)。以后到了天聪八年(1634)才出现了乌真超哈这一直接源自满语音译的专用术语,而入关以后改修过的《顺治实录》的汉文本天聪五年的记事下出现的该术语实际上是后人修改所致,不能作为1631年即已产生这一名称的文献证据。至于清朝创造了意译色彩明显的汉军一词来取代音译化的乌真超哈在汉语中的应用,就更是晚至入关多年之后的顺治十七年(1660)。故汉军一词的出台有利于减轻清朝入关时遭遇的汉人敌视全属时间错置的空想臆测。同时反观柯氏率意提出的认为皇太极出于对金人的拟古模仿而创造出“汉军”一词的论点(当然此观点显然有利于证实她的“东北亚本位论”),只能认为她的论断是多么虚妄不实。
其实她的关于汉军的种种谬说实际上只是想证明纯由汉人组成的军事单元在后金政权下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努尔哈赤进攻辽东之初,以表明尽管他们因未入八旗而带有身份上的某种暧昧性,但似乎仍然受到了统治者一视同仁般的政治对待,以至于当辽东汉人群起反抗女真庄主的事情发生后还把他们中的大批人从女真旧主支配下的劳役阶层(the service classes)超擢整编入后金先前成立的汉人职业化军事团体(the professional military sector)乌真超哈。以后到皇太极时期,该组织又重新集体编旗,并被赋予了“汉军旗人”这一标明其身份地位的专用名称,从此与满蒙八旗成员一起共同成为入关之后的征服者。因此在柯氏笔下,起初努尔哈赤拟使辽东的汉人成为和女真人共同承担劳作的生产者,即双方形成一种在农业生产上合作互补(cohabitation and cooperative working)的关系格局,可是这一计划却由于辽人的激烈反抗而遭到失败,他才重又把他们改组为随时应征的常备兵员,并具有单独配置的与先前八旗不同的旗色。这样在天命晚期残酷镇压境内汉人的合理反抗至于心理畸形,杀人如麻(尤其是针对辽东的生员士人群体)地步的努尔哈赤转而以一副对于女真汉人皆为仁慈宽大,体谅由衷的公正无私面目出现。这真是对历史史实的巨大嘲讽。换言之,辽东汉人的反抗得来的竟然不是残酷血腥的仇杀屠戮,而是在后金国内地位的节节攀升,最后同满蒙旗人一道共同成为关内汉人的征服者。他对辽东汉人的做法真是说得上“以德报怨”!这差不多可以被定性为北美新清史版的“农民起义催生让步政策论”了。归根结底,柯氏始终拒不承认天命后期的后金国内存在着极其尖锐而复杂的民族矛盾,故有意误导歪曲史实以免与她固执其见的民族晚生论发生冲突。
柯氏为了证明这一时期的后金国内的汉人虽然遭到某种歧视,但却并非无法忍受,转而以同时期明朝对待辽东汉人作为对比。她深信明朝当时对辽东的汉人比后金对待他们还要恶劣得多,以致这些辽人一旦投奔了明朝,就在前途上绝无指望可言。那么对应于天命后期的天启年间的情况真是如此吗?柯氏此论实际上是将她先前对佟卜年系狱事件的错误解读竭力扩大化,即她认为此事反映了朝廷对于血缘上有女真成分的辽人群体已经极度不信任故有意迫害之。前文对此已详加驳正,故不拟重复。此处仅补充一点,佟氏下狱实祸起于明朝内部其时已愈发激烈的党争(被朝中政敌攻讦为党附熊廷弼),这也是稍稍熟悉明末史实的学人所共知的。事实上,天启年间明朝内部虽然阉祸煽毒,党争不息,但在辽东的边防问题上,朝廷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最初由熊廷弼筹议,并由继任者孙承宗加以完善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积极恢复方针,尽管熊氏本人的下场结局极其悲惨,而随后的孙承宗和袁崇焕在实践该方针时也不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掣肘。具体而论,先是在熊氏任事的天启初年,辽沈和广宁相继失陷后众多不愿降金的辽东军民均曾得到了来自明朝的援助接济,并被重新安置在关内和胶东登、莱等州。继起的孙承宗则进一步从内迁辽民中招募兵员,强化军事训练,使辽人的军人化程度得以提高并渐次成为明朝稳定辽西局势的主要边防力量。同时明朝也相当重视对于归附后金的辽人军政官员的策反工作,曾经取得过在后金统治下境遇不佳的刘兴祚兄弟举家反正的可观成果。①渡边修:《明末の辽人につぃて》,《东方学》第65辑,1983年。实际上只是在崇祯二年(1629)的袁崇焕因“己巳虏变”下狱以及随后发生的皮岛内讧才导致“以辽人守辽土”这一战略的渐渐失效,而这时后金政权已值明显改变了以往敌视辽东汉人政策的天聪时期。②关于皇太极一改其父的高压方针,转而奉行拉拢争取辽人军事人材做法所取得的成效,除了人所熟知的前三藩主动投效的史实以外,还可参看姜守鹏:《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3期。因此相较于开始大肆迫害屠杀汉人的后金天命晚期,明朝天启年间对待辽人的主动安抚措施无疑才是深得人心的。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以辽人守辽土”战略完全失效的以后阶段,辽人群体中的某些佼佼者仍然不乏在明朝出人头地的情况,像原籍铁岭卫的黄得功即因多立战功而迭经升迁,以后在南明初期一度成为政治上炙手可热的江北四镇之一,直至最终为保护福王而以身殉职。故柯氏论述之严重失实,早已不容自辩。
柯娇燕关于入关以前八旗汉军的史实判断失误还体现在其对汉军组成的理解上。本文此前曾经辨析过,柯氏在最初发表的《两个佟氏》中,误将清朝文献中的抚顺尼堪理解成汉军旗人的名称,而实际上这一群体却是长期附着于满洲旗分之下,从未编入汉军八旗的依附性人口。而现在柯氏的错误又继续向前发展。她将“从龙入关”的汉军旗人区分为两大主要群体,一类是所谓的台尼堪,这其中的一个内部分支即抚顺尼堪。他们的归清时间多是在1618年至1629年。而另一类则是抚西拜唐阿,这是指的在稍后清朝在1643年取得锦州之前(按:锦州陷清的实际时间是1642年)进攻北直隶和山东、山西时期前来投奔的汉人。如前所述,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例》,其中列举的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三大群体同属于长期隶属于满洲旗分之列的依附性汉人群体,他们的身份既非八旗汉军,彼此间也只是相互并列而非包含关系。
这里的不加修辞词的尼堪群体实际上多为清朝内务府下的内三旗包衣汉姓人口,尚不同于一般满洲旗分中的外八旗下的台尼堪等人,而与汉军外八旗下的正身旗人差别就更为显著。①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收入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七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38页。大概柯氏一看到文献中出现尼堪两字,就望文生义地把它们一概理解为汉军。实际上自从乌真超哈和它的意译汉军一名相继被官方使用后,八旗制度下的各类尼堪之名就逐渐缩小到了专指满洲旗分(内三旗和外八旗)下的汉姓依附人口,而与汉军旗人渐无关联了。事实上,柯氏文中所列举的李永芳、佟养性兄弟、石廷柱等,均为典型的汉军正身旗人而非她所想象的台尼堪代表。②可以断言,凡属入关之前甚至在顺治年间成为台尼堪的汉人旗籍均位于满洲旗分内,只有在康熙年间的三藩平息之后,一部分投降余众被安置在东北地区以承担十分艰辛的台丁苦役工作,才被归列为汉军旗籍下的台尼堪。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与前述满洲旗分下的台尼堪相比,甚至还在普通的汉人编户之下。参看刘小萌、定宜庄:《台尼堪考》,《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柯氏对抚西拜唐阿的解说更属谬见。必须强调的是,“抚西”一词绝非她所理解的意为“镇抚征讨(辽东)以西,因此代指北直隶等华北地区”,它指的就是辽东的抚顺地方,这从当初抚顺守将李永芳剃头归降后迎娶了努氏之女而被后金礼遇为“抚西额驸”中可知。故抚西拜唐阿是指当初原籍抚顺,以后在满洲旗分下充当各类杂职差役的被俘汉人之后组成的特殊群体,这与抚顺尼堪的含义和性质比较接近。③关于拜唐阿的原义以及入关以后其所指对象的多元化,参看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词典》,第387页;杜家骥:《清代“拜唐阿”探略》,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25-337页。柯氏随后指出的同样在天聪以降皆为正身旗人的宁完我、范文程等重要汉官均为抚西拜唐阿这类差役杂职的叙述就更属不经。可见对于向来偏好递进推理的她来说,若是先前的错误积久未改,那么即会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滋生出多少新一层次的谬说,以致最终错误累积到了纠不胜纠的地步。
柯氏在对入关前夕汉军的叙述中,还存在一些次级差池。譬如她为了强调辽人地位的特殊性,故又声称许多在1629年之后归降的非辽籍汉人并未被允许接纳入汉军旗人组织中,而是直接隶属于满洲旗分内。实际上即以“己巳之役”后的华北而论,正是在1630-1631年之际,不少在永平府、遵化及京郊归附清朝的明朝降将在随后的编旗过程中皆入汉军旗分,成为与天命年间即已投靠后金的“旧汉人”所不同的“新汉人”。其中有的像马光远旋即得到皇太极的信任重用,几年之后成为与旧汉人石廷柱地位相当的八旗汉军成立之初的固山额真(系军队统帅但实非旗主)。还有的如在永平府归降的孟乔芳虽然最初事迹不显,然在以后顺治初年的入关之役中战功赫赫,官至陕西总督。①渡边修:《「已巳の役」(1629-1630)にぉける清の对汉人统治と汉官》,收入《松村润先生古稀记念清代史论丛》,第150-155页。非常令人奇怪的是,从柯氏此处的前后行文用语来看,她又把马光远这位从华北“新汉人”中涌现出的汉军将领看作是和石廷柱一样的1629年之前即已归降的辽东旧汉人。这种误识大概根植于她相信来自华北的“新汉人”在后金-清朝的政治生活中始终不能望辽人之项背,因为后一群体先是得到了努尔哈赤的优容照顾,后来又被皇太极正式划定为较早入八旗的汉军人群,凡此皆为被后金-清朝倚为国策的“东北亚本位论”依据地域原则对待汉人群体的清晰体现。因此,按照以上逻辑,归附后的马氏既然政治地位与石廷柱相近,那么自也应为辽人出身的旧汉人无疑。
至于皇太极以后的顺康时期,柯氏关于汉军的论述更是让人莫名惊诧。她耸人听闻地叙述说,在入关之后的较短时间内,汉军在整个八旗组织中的人数比例飙升倍增。以1649年为例,各种汉军的总人数在八旗兵力(banner forces)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五,以后到1667年才下降到总兵力的七成。那么她的这一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呢?好在她给出了明确的注释出处,即出自安双成198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所提供的原始统计数字。②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原来雍正即位伊始,出于想摸清八旗人口的内部比例的动机,故嘱托交代一向深受其信任的弟弟允祥负责彻查此事。不久后者即在雍正元年(1723)呈交了一份机密性质的满文奏档,内中清楚地记述了自入关以来的顺治五年(1648)、康熙六十年(1721)和雍正元年(1723)三个年份旗务档案所显示的八旗人口内部比例。这份对于学界了解清前期旗人内部人口比例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始史料由安双成首次绍介翻译,公之于众。
根据安氏论文的主旨,易知上述三年中又以顺治五年(1648,并非柯氏所记的1649)汉人在八旗丁额中的比例最高,业已超过了七成五。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该资料所调查到的八旗人口泛指所有男丁而言,决非仅限于披甲人(banner forces)。故其中的汉人不仅包括了作为正身旗人的汉军,还有大量多处于满洲旗分下的台尼堪和包衣阿哈尼堪,三者之和才得以凑成如此之高的比例。至于汉军旗人占旗人总数的比例如何,鉴于这份统计资料并未提供进一步的详细数据,所以暂无从深究。不过考虑到清初尚称凋敝的国家财力,能够像满蒙八旗成员那样从官府定期领取薪俸,披甲应役的汉军旗人数量必当少于其他两类依附性人口。否则以国家当时的财政基础根本无法支撑数量如此庞大的汉军队伍。更何况,政府财源的主要部分还需赡养历来被视为武力统治基础的满蒙八旗。如果说汉军真的如柯氏所言,已占旗人总兵力的近八成的话,那么势必导致清政府供养汉军的财政支出会大大超出满蒙八旗,即使汉军的人均薪俸数字确实低于后者,而“首崇满洲”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势必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顺治初年汉人旗人中的依附性人口的数量之所以如此惊人,显然又是和入关以来清朝奉行赤裸裸的武力征服政策,导致全军从上到下任意大量俘虏掠夺平民为旗奴的残暴行径分不开。柯氏对此史实漫然无知,竟然臆断相关的统计数据均指披甲人而言,又将与汉军旗人的身份有着本质差异的各类尼堪等依附性旗下人口也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计作正式的汉军成员,因此才得出了上述绝非事实的无稽之谈。①虽然八旗出征时,奴仆常常需要跟随主人一道出生入死,但这被认为是他们原本就有替主子效犬马之劳的天然义务,因此即使赴汤蹈火,丧失生命也得在所不辞,这并不等于他们由此成为披甲旗人中的正式一员。最为准确生动地揭示这层主仆关系的就是《红楼梦》中对贾府老仆焦大昔日曾随宁国公贾演数度出征,并冒死救护主人脱难出险的描写。仅在某些特定情况如布尔尼之乱时期,由于现有兵员极其缺乏,作为平乱将领的图海才不得不临时性地武装动员大批家奴以解军情燃眉之急。
与顺治五年的统计类似,后来的康熙六十年的比例数据也是将汉军和另外两种汉人旗人一同估算,并未单独列举出汉军占旗人男丁总数的比率。而且这时的汉人旗人内部成分的复杂程度更甚于顺治年间,共计有当初“从龙入关”的汉军、台尼堪、抚西拜唐阿以及满洲蒙古旗分下的包衣汉人、“定鼎后投诚”的北京汉人、内务府系统的太监、“带地投充”的汉人等形形色色的各种类型。而这几大类汉人的累积之和则占旗人总丁额的六成九。这一比例在随后的雍正元年中又下降到六成七。因此,允祥奏档中的数据殊不足以提供汉军占旗人总数的精确比例,但能够明晰反映出清前期时旗人总数中与正身旗人相区别的汉人依附性人口的比例之高则要大大高出人们之前的估计。即使如此,仅就有权领取薪俸的披甲旗人而论,从入关定鼎以后直到乾隆时期的“出旗为民”政策实行之前,汉军的数量比例在正身旗人中并不居于明显优势的传统观点无需作大的调整修正。当然柯氏此处失误的知识根源还是在于其对汉军的包含范围从始至终全然混淆不清,复加上她历来笃信汉军等于汉人(尼堪)的错误理论前提,导致她不假思索地把旗人社会中的所有汉人成员,上至正身旗人,下到太监小厮一律视作汉军正式成员,可谓离谱之极。当然这种将其推论葬送得干干净净的知识短板也将她对清代八旗社会内部的复杂多元性的近乎一无所知暴露的清晰无疑。
既然汉军的内部构成及其占旗人总人口的比例均被她完全误会和人为高估,那么这类乖谬如同此前的那些误断一样,继而滋生出更多的后续性连环失误。接下来,她首先将康熙前期反清自立的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之乱定性为部分汉军中的头面人物并包括一部分老资格的家支(including some of the old lineages)公开鼓吹掀起反清活动的政治事件。它于1673年的突然爆发宣告了汉军旗人对于满洲统治者的忠诚表征不再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而在整个17世纪的后半叶中,汉军在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则变得愈加微妙。一方面,随着大量新进成分注入汉军,使得该群体的整体文化面貌暧昧模糊起来,往往因人而异的满化与汉化的双重景象同时皆见其中。而另一方面,汉军群体因其过于庞大的人口数量所导致的对政治经济重要资源的抢占挤兑(从官员的入仕机会到驻防兵丁的薪俸支付)又使得数量相对较少而无以自安的满洲旗人难免对此怨声载道,激愤不平之声甚至上达朝廷(按:如果汉军确实占正身旗人男丁总数的逾七成,那么这种推论自无问题)。这样随着忠诚度的受到猜疑和政治地位的不再稳固如初以及自身文化面貌的多变性,汉军旗人内部逐渐产生了新一轮的裂变即部分汉军家族转而以其祖先原本出自满洲为由申请重新改入满洲。
柯氏对于17世纪后半期汉军政治地位的描述完全与已知史实相矛盾。首先三藩事件的肇乱者并非汉军旗人,更不属于汉军群体中的资深成员。虽然吴氏、耿氏、尚氏确曾被怀疑为在当初归清之时即已入旗成为汉军,但是这一广为流行的旧说目前业已在学界得到纠正。如前所述,较早在天聪年间携家举兵来归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大军事集团均被有心限制贝勒旗主权力的皇太极单独留置在八旗体制之外。上述家族及其部属的这种非旗人的身份一直持续到入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其中孔氏率先战死于南征李定国之役中,致其后人仅存一女孔四贞故该族在政治上早已势微)。仅仅是在三藩平定之后,清朝高层面临如何处置其归降的余部及某些未卷入叛乱的家支的问题时,从加强监视并增大管控力度以免再生祸端的统治动机出发,重新检讨了先前对待他们的优容宽大政策的失计,因此不再容许其继续游离在八旗体制之外,这才强制性地将以上特殊人群改隶入汉军旗人之列。
其中以子孙众多,家支复杂而众多族人并未预乱,故而受到牵连较小以至后裔子孙依旧繁衍昌盛的尚可喜一系而论,降至康熙年间以后,其在北京和辽东的后裔不仅已经接受适应了这种身为汉军旗人的新身份,甚至还在相应的谱牒中将本未入旗的远祖尚可喜也重塑为汉军旗人,并逐渐为清朝官方所默认,遂导致有些晚出于雍乾时期的官修文献如《八旗通志》、《清史列传》等均将尚氏的身份追记为汉军镶蓝旗人。①对尚氏身份及其后裔旗人化问题的探究,以细谷良夫的论著最多。参看氏撰以下论文:《尚可喜一族の动向を传ぇる诸史料——辽宁省海城市尚氏藏『尚氏宗谱』の调查から》,收入《第一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印,1987年,第791-809页;《围绕尚氏家族的诸史料》(王桂良译),收入支运亭主编:《清前历史文化——清前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7页;《清末の汉军旗人——尚氏一族をめぐつて》,收入氏编:《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フィルドと文书を追つだ》,东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第96-122页;《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张永江译),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1-105页等。这实际上是将其后世子孙所在的旗分移置于乃祖头上,而与清初的史实并不契合。与之相反,编撰时间更早的多的顺治九年的满文档案《汉王公各官员世爵名册》和康熙二年的同类型史料《汉军旗内兼任官员世爵名册》中均没有记载三藩及其部属的旗分,这也可以作为当初三藩尚未入旗的佐证。而在叛乱平息以后的强制编旗过程中,作为耿、尚族人的领主对佐领一职的控制力度则被削弱以至相关余部的佐领常常不是世袭佐领。②[日]绵贯哲郎:《关于入关后编立的八旗汉军佐领》,收入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祝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487-490页。同样来自于《清实录》的资料也证实耿尚集团在三藩之乱以前只设佐领但并未编旗,事件平息之后,剩余部属才被改隶于相应的汉军旗下。③王锺翰:《满族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第68-70页。因此早期满汉史料在三藩未入旗上的记载是彼此相合的。不过平西王吴三桂所部的情况稍微有别于耿尚二藩。相近之处在于三藩起事以前,吴藩军中同样也是参照八旗兵制,设置了以佐领为中心的军事组织,即都统、参领、佐领、护军统领、护军参领等官,大体按照了八旗汉军的相关标准,即《平西王吴三桂题本》中所言“第官名及甲马差徭俱与乌金超哈同例”。①神田信夫:《平西王吴三桂の研究》,收入氏著:《清朝史论考》,第200-203页。该文原刊于1952年。不过大概因为三藩之乱平息后,吴氏族人几乎无人得到清廷宽宥,故官方对其部下的处置也与耿尚两藩有所不同。目前难以找到证明其余众被改隶于正身汉军的原始记载,仅能综合时人留下的相关记载,显示这部分人众大部分都被政府发遣东北专事守台苦役,成为虽然身属汉军旗下但其社会地位却大大低于普通旗人的台尼堪这一特殊底层群体。②王锺翰:《满族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第70-71页; 刘小萌、定宜庄:《台尼堪考》。也就是说,吴藩余部虽然得以集体入旗,却并未如耿尚两部那样成为正身旗人故其境遇相对低下凄惨。由此可见,清廷着手处理三藩余部问题时,是在坚持入旗总原则的前提下,对于原属三藩的部下做到了区分对待。
综上所述,三藩之乱的产生与汉军集团并无直接关系。何况在整个事件的初期,有些在三藩辖区内出任督巡要员的汉军旗人,还极力效忠清朝,最后以身殉职。例如因在云南担任巡抚而被吴氏在起兵之初诛杀的朱国治,同样死于吴氏子弟手中的马雄镇和被耿精忠谋害的范承谟。其中马氏和范氏的就义事迹以后得到了朝廷最高形式的褒奖和纪念,并被作为当朝忠臣的榜样反复宣传。③[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第831-840页。魏氏引用当时戏剧家李渔的观察指出,鉴于范氏家族在辽人旗人群体中的特殊影响,因此范承谟的个人动向就显得十分重要,而由于他最终选择了忠于清朝并为此英勇就义,因此自然稳定了其他辽籍汉军大族对于清朝继续保持忠诚取向。柯氏声称这一事件改变了朝廷对于整个汉军群体的态度只是一个建立在误判史实基础上的不能成立的错误假说。她的这一评述在于试图为其以后的论述找到一个合理的史实切入点,意在将此事与汉军地位的动摇失落建立关联,表明入关以后汉军与满洲关系转变的实质所在。事实上,最新的研究表明,三藩事件的爆发因为有些出乎最高统治者的意料,再加上事变初期由于战事蔓延迅速导致的南方各地的清朝官员“从逆”现象的普遍化,导致康熙确实对于朝中任职的汉官群体产生了十分深重的猜忌心理,以致事隔多年之后依然不能释怀。④姚念慈:《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收入氏著《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第28-51页。该文初刊于2008年。不过,他所猜疑的对象尚仍限于旗人群体之外的一般汉官,总体上来说并未减少传统上对于汉军臣工的信任,尤其是某些和他有特殊关系的汉军家族更是在其统治时期以多出股肱重臣而闻名。故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其母系家族有密切关联的“佟半朝”的说法,开始在朝野不胫而走。⑤侯寿昌:《康熙母系考》,《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即以汉军整体而论,在康熙一朝的定期前往热河巡幸的活动中,在一般情况下不见汉人阁臣随侍同往,而汉军出身的臣僚却得享扈从厚遇,不在限制之列。⑥姚念慈:《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盛世心态》,收入氏著《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第419-425页。至于柯氏宣称的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满洲旗人对于汉军优越地位的不满与反击,也属于其一相情愿的奇思异想。正是因为此说于史无征,所以她无法在相应的论断下面明示文献出处以备检证。不仅如此,在柯氏关于17世纪后半期汉军旗人地位微妙化观点的整页论述中,都未出现一条最基本的文献注释以提示原始文献出处或者前人研究的成果,充分彰显出此处所论皆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当然柯娇燕进行的如上论述还是为她以前在《两个佟氏》中强调的佟国纲兄弟请求从汉军改为满洲并得到批准的论点提供解释性的背景平台。可是如前所述,第一,佟氏该支在康熙时期经历的所谓改旗实际上只是汉军内部的一次“抬旗”,即从正蓝旗汉军被抬入镶黄旗汉军;第二,朝廷只是允许该支佟姓族人可以对外自称满洲,但是其隶属旗分却不予改变,仍在镶黄旗汉军内,故在正式名分上始终未具满洲之实。因此,以权倾一时而被民间渲染夸张为“佟半朝”的佟氏一门仍然只是资深的汉军望族而已。这对柯氏津津乐道的汉军地位下滑论不啻强有力的反证甚至绝好的讽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清初汉军名将石廷柱的后人中。本来与佟氏、石氏后人申请抬旗相似的事例在以后的清朝历史中所见多有,不足为怪,此皆缘于八旗体制内部一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待遇差别,个别成员适逢特殊机缘实现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实不称奇,并且这种向上的流动现象出现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十分正常的。对此的解释理应做到因人因事而异。如果按照柯氏逻辑催生出的深文周纳式的过度解释,但凡出现汉军抬旗请求,是否都与这一群体地位中衰以致其成员多不自安的焦虑境况有关呢?而且目前已知的此类案例,还有蒙古八旗中的下五旗成员被直接抬入满洲上三旗的情况,那么这是否又表明了蒙古旗人群体同样也感受到了某种危机呢?①关于对各种抬旗现象的原因分析,参看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325-334页。
柯氏在《两个佟氏》中对于佟国纲改旗事件的解读本来已属严重背离事实,而现在又引申出更多的疏误。那就是她将佟氏的申请改旗诠释为一个政治互动过程的开启,即它反过来导致对于文化因素倍感焦虑的康熙转而认识到祖先血统对于维系满洲认同观念的支柱作用,并发现了所谓家族谱系对于证明满洲身份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关键妙用,可谓“文化不足恃,谱系长流传”。可是,现实中的康熙一朝,清朝对于满洲文化衰退的对策却是继续强化“国语骑射”等所谓的满洲文化要素,并保持满汉分界来扭转颓势,试图以刚性行政手段阻止悄然进行的文化变迁,这反映出满洲统治者仍然是把文化当作保持自身活力的头等大事来抓,虽然其实施效果未必都尽如其意;同时官方也并未启动任何以重新识别满洲人群为目的的修谱工作,于是自知其实证分量明显不足的柯氏只得暗示这对后来雍正一朝的要求旗人普遍提供族谱的政府举措产生了后续性影响。然而这同样是一个充斥着循环论证的伪问题,因为雍正对族谱修撰编制的关心只是服务于其大力推行的以整顿牛录为中心的旗务改革的重要一环,旨在使君主在八旗体制内部能够建立起官僚化的统治秩序,以革除此前存在的旗主与佐领间存在领属关系的封建式分权传统,为此就首先有必要将私人家谱在性质上转化成国家档案,以形成佐领直接面对并听命于君主的新型绝对服从形式。②细谷良夫:《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编撰とその背景——雍正朝佐领改革の一端》,《东方学》第36集,1968年。由此可见,柯氏为了对一个错误的观点自圆其说,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臆造编排出更多的虚幻论点来加强其说,所以错误的链条就会传递延伸得越来越长,终至难于自拔的地步。这突出表现在柯氏文中随后长达数页的对于佟氏改旗一事的基本分析都是没有任何实证价值的臆断,只会导致她的解说距离当时的事实越来越远。
除了佟氏改旗事件以外,柯氏论述康熙时期汉军地位转变的另一基本案例是关于范承谟殉清一事的重新释读。此事本来在魏斐德的著作中有过相当精致的分析,即官方通过对此的旌表刻意要在社会上传递出一种有效信息,相对于三藩这类跳梁小丑而言,清朝统治被赋有的无可挑剔的正义性决定了像范氏这样的忠贞楷模为之甘愿捐躯以舍生取义。范承谟和马镇雄的不屈而死的感人事迹也在经过了政府的巧妙宣传之后,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有助于人们承认天命的转向清朝已经不可逆转,而像范马二人这样的正义之士的涌现则是对此深具说服力的事实证据。然而柯氏此处却刻意求新,以求在迁就其既有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异于前人的解析。她将范承谟与其父范文程的事迹并案处理,试图以父子两代人在相关叙事中的形象为例,折射说明汉军群体所经历的身份变迁与形象改塑。
她先是引用国内学者张玉兴先生的研究结论,承认历来被视作开国文臣之首的汉军旗人范文程其实最初并非是主动投奔后金,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天命年间的被俘奴仆到天聪年间的得力臣僚的转型过程。①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辨》,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编:《清史论丛》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不过更值得重视的倒是随后她对此史实的展开评论。她认为在清朝入关定鼎以后的后征服(post-conquest)时期,范氏在史书中的个人形象经历了与前征服(pre-conquest)时期的重大变化,即在后征服时期的形势下,范氏最初略带屈辱的经历被改塑成自愿投效太祖并深得后者器重的君臣之间愉快合作的关系了。这种君臣之伦对主奴关系的超越取代寄寓着强化臣僚效忠君主观念的政治用意。而这背后的思想变迁则折射出清朝统治者力图将在入关之际实际已处于征服者位置的八旗汉军名臣的形象淡化处理为平常汉人,以表明对于汉人来说只要主动归附,尽忠臣节,就有可能在英主的赏识重用下,成长为一代名臣。而柯氏此处所坚持的前提依然是,像范氏这类典型的辽东汉军旗人,实际上其祖上很可能都有女真血统的嫌疑,与关内的一般汉人存在着种族出身上的实质分别,故清朝的做法只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已,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柯氏的上述辨析看似新颖可取,实际上只是自编自导演绎了一个假命题而已。因为目前已知的有关范文程生平经历及个人形象的任何传记类史料,均是出现在顺治入关以降的“后征服”时期,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一个范氏的个人形象从入关前的“前征服”时代向“后征服”时代逐渐转变的明晰过程。目前以揭示范氏早期被俘经历最为生动详细的记录,已经是康熙年间彭孙贻(1615-1673)的《客余偶闻》。该史料甚至指出范文程还不像当时一般记载那样是在抚顺陷落之际,辗转流入后金军中,而是在此后只身前往关外葬亲投宿农庄时被当作汉人生员即将遇害时(按此点明显反映的是天命晚期后金对待汉人生员所实行的滥捕滥杀背景)侥幸逢赦并被录用。康熙年间关于范氏投诚的记录也均用“始得公”之类的文字表述,表明当时举朝上下实际上并不以范氏最初的俘虏身份为讳,只是到了后来的雍乾时期才一律改为表现其早早预知天命从而主动投效的“来归”等词。①以上对于不同时期史料的列举梳理,参看张玉兴前揭文。最早官方版的范氏个人小传实际上是康熙年间朝廷颁发的满汉合璧的一通诰命,详细叙述了他从天聪八年(1634)直到顺治七年(1650)的六度官职升迁过程,其中追溯他入金的经历是“克抚顺时,得尔育之”。参看W.Fuchs, “Fan Wen-ch’eng 范文程,1597-1666,und sein Diplom (诰命)”, 《史学研究》第10卷3号,1938年。这也符合历史撰著中时间越晚,有关人物在传记中的事迹附丽增饰的越来越多的通例,故亦不足为怪。
柯氏继而又把这种清朝皇帝需要把汉军还原成汉人(即她所概括的使汉军“去征服者化”)以巩固其统治的动机沿用到三藩事件中死难的范承谟和马镇雄二人的身上。可是,从康熙到乾隆时期清朝对于他们的持久赞扬从来都是围绕着超越了种族背景的君臣之伦和清朝统治的正统性而展开进行的;而从中受到教化的民众似乎也是如此理解的,因为18世纪的戏剧作家蒋士铨在以马镇雄家族殉难为背景创作的《桂林霜》中才会将这次家族成员的集体殉难与当初为明朝尽忠而死的马氏祖上相提并论,均视作应该受到同等尊敬的忠贞之士。因此完全说不上清朝需要依据柯氏所臆断的在入关以后渐渐形成的“种族原则”先把现实中的汉军征服者还原成作为被征服者的抽象汉人之后,相关的英烈事迹才会被广大汉人群体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接受。柯氏此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只是为其所作叙述持续增加了败笔而已。不过公道地说,她的这一论述固不足取,但却反映出其已经意识到清朝统治在汉地的巩固需要在思想上赢得大多数汉人的承认与拥护,或者说他们至少不能公开流露出对抗意识,所以才在范马死难的事件上重做文章。这一思考取向本身尚属可取,只是在实践中因作者严重误解史实而推论前提又多不正确,故才导致其立论彻底失效;不过似乎不必据此完全否定这种探索的本身。除了前述强化伦理道德上的君臣观念以及宣扬《大义觉迷录》一类的华夷相对主义以外,清朝统治者采取何种手段在意识形态上说服广大汉人臣民效忠本朝不失为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最近姚念慈先生运用具体史实所剖析论证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一深具历史感的政治命题即能将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推向新的高度。
柯氏此文中的最后部分即如该文标题所论,阐述乾隆时期的汉军问题。如所周知,乾隆时期在八旗制度的历史演进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方面,通过继承雍正时期即已开始的官方组织的系统性修谱与编撰“旗史”性质的通志等工作,君权进一步确立了对于八旗制度的直接统治秩序,从而强化巩固了雍正时期所取得的在旗务问题上,成功实现君主集权的政治成果。另一方面,自入关以来已困扰满洲统治者多时的“八旗生计”问题在这一时期严重到了积重难返,无药可医的地步,直接造成国家财政越来越不堪重负和旗人贫困现象的愈发普遍化,正是在这种现实环境不容回避的严峻形势下,已经近于无计可施地步的乾隆开始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出旗为民”政策,舍车保帅式地把许多京城以外的关内驻防旗人中的汉军强制性地分流出去,使之返归民籍,进而以节省下来的兵员空额和相应薪俸接济改善八旗满洲久已不敷赡养的困难处境。以上可以说是学界在讨论乾隆时期八旗问题时的基本共识。也就是说,当时清朝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造成了以牺牲部分汉军利益为代价的“出旗为民”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然而,柯娇燕对乾隆时期汉军现状的分析再次显得与众不同。当她论述“出旗为民”政策的实行原因时,几乎只字不提上述经济因素,转而继续张大《两个佟氏》所做的如下臆测:这种以种族指标为识别依据的区分满洲的工作始于康熙时的佟氏改旗,而终于乾隆时代的汉军大举出旗为民。而在本文张大此说的论证中,她出人意料地将乾隆时期《贰臣传》的修撰动机与朝廷解决汉军问题第一次联系起来。考虑到以往学界对《贰臣传》的理解均围绕乾隆试图以此来强化臣下对君主及本朝的绝对忠诚无贰这一政治信念来进行,而将其与汉军问题相关联诚属前无古人。①以这种视角来分析《贰臣传》成立背景的论著很多,此处仅举一文以例其余,参看陈永明:《〈贰臣传〉、〈逆臣传〉与乾隆对降清明臣的贬斥》,收入氏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第220-259页。另外关于《贰臣传》编撰过程的文献学考察,参看神田信夫:《清朝の国史列传と贰臣传》,收入《东方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记念东方学论集》,东京:东方学会,1972年,第275-291页。此文收入《清朝史论考》时增加了追记和补注各一则。柯氏具体的论述要点有:
一,被列入《贰臣传》的传主大多为明清之际的汉军旗人,这使得该书具有以汉军为中心的国史列传性质。二,《贰臣传》的编撰中贯穿了“东北亚本位论”,即全书按照褒贬次序所厘定的两编六等中,被置于受到批评较少的汉军贰臣多为辽东出身的台尼堪而且“贰臣”标准总体上对于这一辽人群体施行得相较原籍华北的抚西拜唐阿出身的贰臣宽松。三,考虑到范承谟和马镇雄的光辉形象,朝廷有意对他们的祖辈范文程和马鸣佩网开一面,故后者皆未被列入贰臣行列。四,《贰臣传》的成立标志着以种族为指针将汉军重新认定为汉人的工作在官方舆论中已接近完成。
以上几点颇易驳正而无一能够成立。首先《贰臣传》中的半数以上人物根本就不是汉军旗人,怎能将此书定性成一部汉军人物列传呢?尤其是其中乙编三等的近七十人,大多数人一生都未入旗。甲编三等中汉军人物的所占比例相对要高一些,但也只是仅过半数而已。像甲编上等的九人中,汉军只占四人(刘良臣、孙定辽、郝效忠、马得功);中等的十名中,汉军占到了七至八人(李永芳、孟乔芳、张存仁、刘武元、祖可法、刘芳名、李国英等),算是比例最高的;而下等的三十四人中,汉军又只有十六人。故在事实证据面前,柯氏的前述观点或者说她关于《贰臣传》的立论基础根本就不值一驳。
其次,在贰臣内部定等问题上,也绝非依据的是作者所臆断的“东北亚本位论”。列为等级最高的甲编上等的九人均是在入关之后的战役中为了新朝而死于疆场未得善终之人。清朝将其列为上等显然是一种具有旌表性质的纪念,以表明其过失最低或者功大于过(所谓“其人入本朝而能没王事者,列甲之上”)。而在甲编的中下二等中,明显又是考虑了对于新朝而言所建功勋的大小(所谓“若显有功勋者,列甲之中”),故原籍福建的洪承畴被列为中等而高于出身辽人的祝世昌、祖大寿、鲍承先等(皆为甲之下等)。当然,凡是《贰臣传》出现的汉军旗人的身份皆非台尼堪或抚西拜唐阿这类满洲旗分下的依附人口。而许多像郎廷佐之父郎熙载这样的辽人未入贰臣之列,并不是因为清廷对于辽人的贰臣标准有意放宽,而是因为这些人归降时的身份只是生员或普通平民,迄未正式担任明朝官职。类似地,像范文程归清时的身份也只是生员而已,这和马鸣佩在明朝没有任何任官经历的履历背景是相同的,故他们不属“贰臣”是很正常的,与其子孙成为清朝表彰的烈士无关。可见柯氏对于当时判定贰臣的标准完全无知,故每当遇到自己的理论解释不了的史实时就任意曲解以回护其说,毫无学术严谨性可言。最后,《贰臣传》的编撰与朝廷从舆论上发出汉军即汉人的政治信号也并无关系。柯娇燕在《贰臣传》问题的刻意求新实际上是给学界制造了更多的误会和混乱,毫无贡献可言。
综合前文所论,柯氏的四篇大作讨论的问题固然良多,但仔细检讨下来却不难发现其构建的一系列历史命题最终无一能够成立,均只能看作存在于她自己头脑中的空中楼阁,它们的虚幻性无异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海市蜃楼。然而这些虚无缥缈的伪历史命题却又成为她在1990年以后所推出的专著和其他论文的基本出发点,这些后继成果的价值如何,当然还必须由读者自行判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其基本思路,笔者这里再对其中的要点略作梳理:《两个佟氏》的基本命题是满洲民族/族性形成三部曲论:
1 在明代-入关前仅是文化共同体而族性(ethnicity)特征尚多不具备
2 在入关后的康熙-雍乾时期逐步强调以祖先血统为中心的种族(race)共同体
3 清末完全具备族性(此点后来在《孤军》中得到详尽阐发,但在本文已埋下伏线。)
通篇论文欲烘托的观点实质上是回应(或者说作者是有意在硬套该模式)“民族是到18世纪以降才形成的想象共同体”学说所催生的族性/民族晚生论。作者证明其第一阶段的立论基石是明初1388年东北野人女真大分流,同时还认为三万卫即斡朵里等三万户。这就导致:一部分人如佟氏先祖流入辽东,成为汉人(尼堪)。另一部分人则迁徙奴儿干形成建州集团。第二要点: 以佟氏后人改旗为中心的分析。作者随之证明的第二阶段的事例则是康熙二十七年(1288)佟国纲以先祖非汉人为由申请从汉军旗人改回满洲。按照柯氏的理解,其结果是佟氏的请求完全如愿以偿。而此事意味着满洲人群的边界标志由先前的文化转移到现在的血统(祖先谱系为代表)。同时佟氏代表的是所谓抚顺尼堪的群体,该群体后来在乾隆时期,被彻底接受这一新的关于满洲的认同标准的清朝允许悉数改回满洲。故满洲的认同边界从文化转向种族化的血统起于康熙,终于乾隆。正因为最终形成满洲民族/族性足足需要经历三个漫长的不同阶段,所以相应的族性要素也只能是到了很晚时期(太平天国起义以降的清末民初)才悉数具备的晚生性历史现象。
她的第二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明代东北的女真与蒙古互相高度混杂,彼此之间缺乏族性(ethnicity)之别,以之来加强首篇论文中构建的女真-满洲族性晚生论的命题。为此她的核心证据是清始祖传说中的远祖布库里雍顺统治的三姓正是蒙古兀良哈三卫。基本理由是一,《李朝实录》频频将建州集团称作兀良哈人;二,三姓中的三可以和三卫中的三对应。上述错误推理得出的结论则是努尔哈赤远祖实际上生活在由大量蒙古人构成的政治联盟中。
接下来所发表的关于《满洲源流考》的长文的中心命题则是: “东北亚本位论”即后金-清朝的地缘政治认同始终在于东北亚而非关内的中国(实际上只是内地)。为了论证其主张,柯氏不惜严重歪曲〈满洲源流考〉中的所引原文, 除多处断句错误外,进而臆断乾隆对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抱有认同感的原因是其怀有的东北亚认同。同时她又将《源流考》中的部族(aiman mukūn)偷换成氏族(hala mukūn) ,以避免与族性晚生命题相冲突。而作为论证其观点的另一基石,此文还对入关以前的满洲历史进行了臆想性重构,坚称努尔哈赤初起时的七大恨文告贯穿了“东北亚本位论”的出台,其中心思想是努氏政权以东北亚立国,而与以中国立国的明朝平起平坐,互相独立。这种政治信念还延续到皇太极时代,甚至后者改用大清为国号也不是为了和明朝争夺天下,而是发生在向黑龙江流域的土著女真部落大举扩张的背景形势下。甚至晚到入关以后的清中叶,乾隆帝还把清朝建立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远溯到同样以东北亚立国的辽金两朝。而此文的最后一节对金毓黻个案的考察更是直接显露出作者的非学术化的意识形态倾向。
最后她发表的论汉军旗人的长文的叙事主线是:按时间为经纬,构建了从后金天命一直到乾隆的汉军演变历史,可称为新清史版的汉军旗人史。对入关以前汉军形成史的重构是当后金于天命之初夺取抚顺后就建立了乌真超哈这支汉人军队,但并未编旗,迟至攻占辽东各地后还试图让汉人在田庄中与女真相互协作共同劳动以无分彼此。到天命后期汉人的反抗举动促使努氏将农庄汉人纳入军队中中,即汉人的身份在这时由农转兵,反而促使其地位好转,最终成为了以后入关时的征服者。这一论说简直堪称新清史版的“反抗催生让步政策论”了。而随后的皇太极时期则将汉军编旗,并命名了“汉军”这一专有术语,作者臆断这是拟古先前金制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柯氏对入关前的后金国内局势的分析中,避而不谈天命晚期努氏对于辽东汉人的反抗所采取的屠杀镇压政策(尤其是针对当地生员阶层), 同时也回避后金征服战争和压迫所造成的族际鸿沟,这正是为了与”族性晚生论”中的成因分析抵触冲突,因为在目前西方学界流行的关于族性的理论中,通常都强调族性意识的尖锐化和显性化,恰是根植于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与歧视敌对现象的不断升级。
柯氏在此文中完全不熟悉汉军旗人的概念界定,故臆断凡是旗内汉人皆是汉军,结果她把上至正身旗人下至太监、奴仆等各类旗下依附性人口一概统计为汉军,故作惊人之论,声称入关以后长期汉军比例高居旗人男丁总数的七成五到六成七。她误认为正是如此之高的人口比例,再加上三藩之乱是由汉军扮演着主导角色,共同驱使清朝高层着手解决汉军这一尾大不掉的历史难题。而康熙则从佟氏改旗的申请中受到启迪,转以种族血统代替文化作为新的满洲群体的认同边界。降至清中期时的乾隆,则将康熙确定的这一新的认同边界进一步固定化,为此朝廷通过编撰〈贰臣传〉作为驱逐汉军出旗的舆论动员。柯氏所持的错误理由即该书从性质上看就是一部汉军历史,同时又将与佟氏性质相同的抚顺尼堪(汉军中确有女真起源背景的群体的代表)集体改回满洲,后者获准改旗的理由即在于他们的祖先在血统上是满洲人。此外柯娇燕在第四篇论文中还想方设法地规避汉化问题,如她将入关后满洲旗人经历的文化变迁及其危机,解释成因为汉军数量太过庞大,故在整个旗人群体中起到了稀释满洲文化特征的掺沙子似的效应,以避免谈及入关之后的满洲旗人群体所不得不直面的汉文化包围与影响这一真实的现实环境。
纵观柯氏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她最突出的治学特征是善于提出宏大的带有结构性的历史命题和知识论断,而在美国的新清史学者群中可以说无人能在理论分析和概念提炼方面出其右。所以,尽管柯氏时常回避甚至不屑于使用“新清史”这样的名称来为自己的研究定性,但是在美国学界除了她本人以外,却从来无人能把她排除在新清史的学者群之外。这正是源于柯氏在研究中所推导出的这些宏大命题恰恰成为其他新清史学者汲取理论灵感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来源。如前所述,其中影响最巨者就是她在学术早期阶段所撰写的以上四文内系统构建的两大命题:族性晚生论和东北亚认同中心论。
事实上,这两大命题后来也成为她发表的更多论著的立论出发点。譬如她在《始祖传说》中提出的明代满蒙不分论,此后又在其2006年发表的《创造蒙古人》一文中被推向高峰。用她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是清帝国的创立“制造出”了满洲人和蒙古人等民族集团,而不是这些民族创立了清帝国,也即帝国在先,民族殿后。她提出的第二个命题更是在随后的研究中被拔高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这反映在她在2008年法国的《年鉴》上刊发的论文中竟然将清朝版图内的汉地、蒙古、回部、藏地统统看作“受保护地”,而这些地区所对应的居民也都随之成了“被保护人”,这实际上是只承认东北亚才是清朝的直辖领土,其他的几大区域都是清朝的殖民地,因为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受保护地”和“被保护人”就如同国际法中的“保护国”一样,都是针对殖民地而非直辖领土所言。这正如二战结束以前的大英帝国,其直辖领土或者说本土仅限于英伦三岛和北爱尔兰,而从直布罗陀到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广大地区都是其殖民地或“受保护国”。正是源于这一对清朝的全新定位,她进而强调1911年以后的现代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来继承原属于清帝国的政治遗产,所以现代中国的四大边疆本应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相应国家政权。她的这种政治倾向应该说已经直接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其他诸多的新清史学者。关于美国新清史研究中数见不鲜的这种意识形态化取向,笔者在年初的《中国民族报》上曾有所列举和批评,这里就不用多谈了。
当然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审查,柯氏构建的相关命题多不足取,其论证的失误程度有时是如此惊人,以致已经难于用语言来形容。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堪为致命伤的一点则是她在研究中滥立缺乏有效证据支撑的“建设性假说”(working hypothesis),而在对相关史实的处理上又常常是不由自主地“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傅斯年评拉铁摩尔语),①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收入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73-174页。并且还在研究过程中一再将立论有误或者极不严密的“疑点性假说”视作继续推论的定论化前提,由此导致推理环节如果越多越长,那么其论著中的相关叙述就乖离事实越来越远,这种错误论据的累计叠加终至形成一种类似于自然界的“蝴蝶效应”,故历史史实的本来面目在其文中几乎已经完全不可辨识。像柯氏竟然能够从一场子虚乌有的1388年野人女真大分流入手,经过层层递推,直到最终得出一个像族性晚生论这样的宏大命题就是彰显其学风的最佳例证。对于这样一种将既往历史根据己意随便装饰打扮的取径路线,即使其立说再巧,影响再大,对于笔者而言,也只能用“非我所知”来为之定性。不妨说,柯氏的研究模式给笔者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探究历史奥妙的车道,最好还是由考据的路口驶入。
——以战迹巡拜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