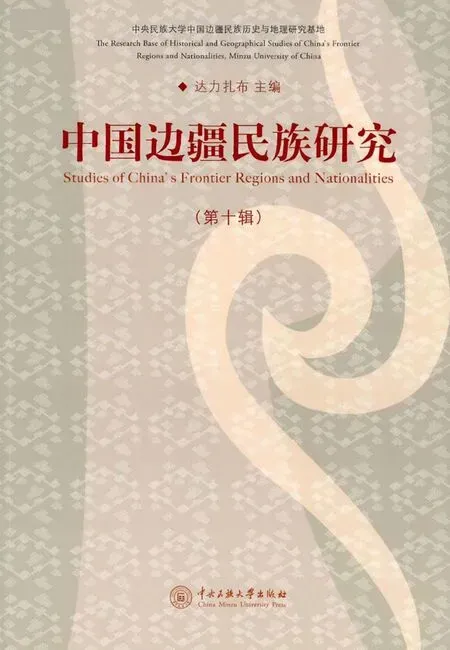清朝的准噶尔情报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鼐家族*
齐 光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等档案史料,再辅以藏文《颇罗鼐传》等文献,阐明18世纪前期西藏王公颇罗鼐家族在清朝收取准噶尔情报的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当时的清朝与准噶尔的形势,以此探讨颇罗鼐在清准双方关系中的作用,并对颇罗鼐的历史地位给予新的评价。
前 言
笔者曾在拙文《拉达克与18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①参见齐光:《拉达克与18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载《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6-214页。中,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朝《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蒙古文书信史料,论述了17世纪80年代青海和硕特领主噶尔丹策旺征服阿里、拉达克后,青海和硕特、西藏地方政府、准噶尔之间怎样通过拉达克进行往来,而于1720(康熙五十九)年清朝进军西藏之后准噶尔又是如何通过拉达克收取西藏及清朝方面情报的史实,以此理清了18世纪前半期的拉达克在准噶尔与清朝之间所发挥的情报渠道作用。但因探讨对象的不同及论文篇幅有限,笔者在上述论文中没有正面详细论述颇罗鼐及其家族在当时的清朝与准噶尔之间进行的“情报战”或其角逐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
颇罗鼐,生于1688年,卒于1747(乾隆十二)年,享年60岁。正如笔者在拙著《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一书中阐明的那样,作为青海和硕特拉藏汗的属下官僚,颇罗鼐长期辅佐拉藏汗治理西藏地方政府,逐渐博得较高的政治地位。1720年清朝进军西藏后,颇罗鼐积极辅佐拉藏汗又一名臣康济鼐,为延续和维护固始汗创立的青海和硕特保护西藏地方政府的体制,除与七世达赖喇嘛属下的噶隆官僚进行权力斗争外,还巧妙地与青海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及清朝的雍正帝保持联系,最终于1727(雍正五)年后通过属下蒙藏的兵力及清朝可汗(皇帝)的权威,确立了自己在西藏的领导地位①参见齐光著:《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9-171页。。在整个雍正朝(1723-1735)后半及乾隆朝(1736-1795)初期,颇罗鼐排挤七世达赖喇嘛及其亲信,不仅独掌西藏地方政府,还令其长子珠尔莫特车布登掌管阿里,让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驻扎达木草原、承袭王爵,以此达到家族世袭以控制整个西藏的目的。但最终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亲信于1750年公开反抗清朝,杀害驻扎拉萨的傅清、拉布敦两大臣而被清朝严厉镇压下去。至此,颇罗鼐及其家族掌管西藏长达20年之久。
以上颇罗鼐及其家族掌控西藏的岁月,也是清朝与准噶尔对抗十分激烈的时代。1730年,围绕罗卜藏丹津的返还及双方边界的定立问题,试图像其皇考康熙帝消灭噶尔丹那般建立丰功伟绩的雍正帝,执意要与准噶尔开战,然在不谙军事的雍正帝本人的远距离遥控指挥及前线清军将领的疏忽大意而又不熟悉对方战术的情况下,1731年清军在和通淖尔地方受到小策凌敦多布率领的准噶尔军队的毁灭性打击,很多清军人员被俘虏到准噶尔营地。其后,虽于1732年在喀尔喀蒙古额驸策凌的奋勇之下,清军于额尔德尼召大败准噶尔军队,但同时清朝也没有了以绝对优势兵力去消灭敌人的信心和实力。为此1734年雍正帝不得不首先向准噶尔派出使团,提出停战议和。经多次遣使谈判,1739年前后清朝与准噶尔达成和平协定。其后,准噶尔又屡屡派遣使团到北京,切磋双方的外交关系,及怎样进藏熬茶,以及如何在边境地区进行贸易等事。但是,基于长期的斗争经验,清朝并不相信准噶尔,常以“准噶尔贼人甚是狡猾”为由,处处提防,事事小心,以警惕准噶尔与西藏恢复传统关系及窃取清朝内部情报。清朝陪护大臣与准噶尔使臣,虽表面和气,然彼此并不说实话,互相隐瞒,难以达成信任。在此情况下,不仅准噶尔无法听到清朝及西藏的真实情报,反过来清朝也对准噶尔的内部动向无从了解。所以,正如笔者在前述拙文中的论述,基于青海和硕特领主噶尔丹策旺签订的条约而与西藏方面关系紧密的,一方面又毗邻准噶尔,彼此往来不断的拉达克汗国的存在,成为重要的情报收取渠道。
那么,在自1727年掌权后至1747年去世为止的20年时间里,颇罗鼐及其家族是怎样通过拉达克收取准噶尔情报,并怎样提供给清朝的呢。于此,笔者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现已影印出版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中的相关满文档案原件,着重阐明颇罗鼐及其家族在开始掌权的雍正后半至乾隆初期④为了日期准确,以下的论述,皆使用清朝皇帝年号。为止的近20年时间里,怎样收取准噶尔情报、怎样将情报传达给清朝可汗(皇帝)、其收取到的情报有哪些、为何要收取情报等问题,以此探讨当时的清朝与准噶尔的内部形势及颇罗鼐的历史地位。
一、有关颇罗鼐及其家族收取准噶尔情报的奏折及驻藏大臣的职责问题
本文所利用的史料,即有关颇罗鼐及其家族通过拉达克收取准噶尔情报后由驻在拉萨的清朝大臣转奏给清朝可汗(皇帝)的奏折,在《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及《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中共有15件。其中最早的,是雍正九年四月十三日的马喇奏折。但从该奏折所记“以前曾报称:准噶尔一宰桑率三百人来叶尔羌驻扎,于酉年返回”①《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册,《驻藏大臣马喇奏报准噶尔派宰桑率三百余人赴叶尔羌等情形》,雍正九年四月十三日,第40页。的内容来看,这种收取情报的事情在雍正九年以前即已存在。
马喇最早于雍正五年七、八月间到达拉萨②据《雍正朝满文奏折》载,马喇从北京出发后,于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七日到达成都,其后四月十八日启程前往拉萨(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2621号,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自成都府启程赴藏日期折,第1464页)。而马喇到达拉萨后上奏的第一件奏折日期是在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是其抵达拉萨后不久即发出的,故判断马喇到达拉萨应在雍正五年七、八月间(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699号,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密奏噶隆等杀害康济鼐之详情折,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第1506-1508页)。,在他尚未到达前的六月十八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卫地出身的噶隆合谋擒杀了原拉藏汗属下康济鼐。其后,隆布鼐等噶隆又领兵前去后藏欲消灭颇罗鼐,以至于颇罗鼐不得不向西逃往阿里。当时,因阿尔布巴等噶隆是达赖喇嘛的直隶属下,康济鼐与颇罗鼐暗中又与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罗卜藏丹津等蒙古首领有书信联系,是故驻在拉萨的马喇等清朝大臣一时偏袒阿尔布巴等噶隆,站在其立场上报告事务③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699号,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密奏噶隆等杀害康济鼐之详情折,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第1506-1508页。及第2703号,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请遣内地绿旗官兵到西藏折,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第1510-1511页。以及第3150号,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领兵入招等事折,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第1634页)。。一方面,颇罗鼐被阿里、萨迦、后藏地方的首领拥戴为“诺颜”,且原驻扎于达木等地的厄鲁特蒙古近四百户投奔于他后,实力大涨,一路破竹,于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领兵进抵拉萨,拘禁了躲进布达拉宫,等待清军救援的阿尔布巴等噶隆,同时还派属下蒙古人楚鲁木塔尔巴至清朝大臣马喇处问好。其后五月二十八日,颇罗鼐又亲自到马喇处,跪请圣安,表示恭顺。见此情形,马喇等立即顺水推舟,承认既成事实,接受了颇罗鼐的恭顺④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725号,散秩大臣副都统达鼐奏报颇罗鼐为康济鼐复仇而起兵折,雍正五年十月初三日,第1520-1521页。及第3157号,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进入布达拉宫折,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第1637-1638页。。可知,清朝并非一开始就支持颇罗鼐反对阿尔布巴等噶隆,而是在颇罗鼐已控制卫藏的情况下,坐收了渔翁之利,《清实录》中的记载是清朝后来的编纂,颠倒史实的部分颇多。最后,雍正帝也于雍正六年十二月承认颇罗鼐管理前后藏的事实⑤参见[清]鄂尔泰等纂:《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以下简称《清世宗实录》)卷76,雍正六年十二月丁亥(十一日)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08年。,同时册封其为贝子⑥参见《清世宗实录》卷76,雍正六年十二月丁酉(二十一日)条。,以此开始了清朝可汗(皇帝)与颇罗鼐及其继承人之间长达22年的“可汗(皇帝)——诺颜(王公)”隶属关系。
承认了颇罗鼐在卫藏的统辖权利之后,基于青海和硕特领主噶尔丹策旺→拉藏汗→康济鼐→颇罗鼐集团与拉达克汗王之间的已有关系,清朝大臣马喇、僧格二人致书拉达克汗王尼玛那木扎勒,要求其向清朝传达准噶尔的情报。两位大臣致给拉达克汗王的书信内容,在《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中,记载如下:
钦差驻藏大臣文书。致拉达克汗尼玛那木扎勒。先前康济鼐尔二人甚亲密交友而行。康济鼐将尔之好事奏闻圣主,故大主子施恩于尔。今康济鼐虽离世,然仁爱之意与康济鼐在世时的一样。请将准噶尔一切情报妥善告知我等。现颇拉台吉已来召地,将仇人俱行捕获,正在等候大主子特遣的审理此事的大臣。尔等乃是好兄弟,故行文知会。作为礼物:完整蟒缎五匹,哈达一束,一并送去①《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为驻藏办事而来之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折(汉译请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3331号,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副都统迈禄等咨拉达克汗及其复文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第1705页)。。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注意马喇与僧格二人的身份“钦差驻藏大臣”的问题。“钦差(Man:hese i takūraha,Mon:ǰarliγ-iyar tomilaγsan)”意思即他们是奉清朝可汗的旨令派遣的,大清帝国最高权威者“可汗——皇帝”的代言人、办事人,而不是清朝国家机构理藩院派出的官员。驻扎蒙古、西藏的清朝大臣,往往都是“钦差”,否则无法被蒙古王公和达赖喇嘛,或者像诸如颇罗鼐这样的相当于蒙古王公的西藏王公所承认和接纳。他们是“可汗(皇帝)”与“诺颜(王公)”之间的联系人和办事人,而非理藩院的官僚,更不是礼部、兵部这些个王朝机构的官员,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因为是“钦差”,所以马喇、僧格二人才能利用康济鼐、颇罗鼐这两位诺颜(王公)的人脉,巧妙地推进与拉达克汗王之间的关系。原拉藏汗属下康济鼐与拉达克汗尼玛那木扎勒之间“甚亲密交友而行”的关系,成为马喇等致信拉达克汗,要求其提供准噶尔情报的前提。而已经掌控西藏的颇罗鼐与尼玛那木扎勒之间的“好兄弟(Man:sain ahūndeo)”关系,则成为马喇等笼络拉达克汗的有力背景。再需明确的是,不可将雍正五年后的颇罗鼐认为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隆,这不符合颇罗鼐的真实身份及其在当时的西藏、拉达克、蒙古与清朝所拥有的地位。虽于雍正九年十一月清朝授予颇罗鼐“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印章②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12,雍正九年十一月丁丑(十八日)条。,但斟酌一下便可知,他是“办理卫藏噶隆事务的人”,而非“噶隆”。很明确,颇罗鼐是“多罗贝勒”,是诺颜、是王公,其存在于西藏地方政府之上。关于颇罗鼐的诺颜(王公)身份,成书于18世纪上半期的《颇罗鼐传(Tib:mi dbang rtogs brjod)》的作者多卡瓦・策仁旺杰(也称“东喀夏仲・才仁旺杰”)③多卡瓦・策仁旺杰——东喀夏仲・才仁旺杰——策凌旺扎勒,长期跟随颇罗鼐转战南北,处理西藏地方政府事务,深知颇罗鼐的身份及其办事方针。其整理档案文件撰写的藏文《颇罗鼐传》,是不可多得的好史料。但对颇罗鼐收取准噶尔情报一事,并没有记载。这可能是因为这种情报收取是非常秘密的,只有颇罗鼐及其家人知晓的缘故。即使清朝大臣的奏折,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上的,只有具奏资格的人才可。因颇罗鼐收取到的情报需由驻在拉萨的清朝大臣具折上报,故清朝可能严令颇罗鼐不可将此事泄露给任何人。也之所以,拉达克或珠尔莫特车布登方面寄过来的情报,往往由颇罗鼐本人亲自转达给清朝大臣。阐述的非常明确,颇罗鼐为“mi dbang”即王公、人主,相当于蒙古的诺颜、领主,清朝的王公。此外,颇罗鼐在当时被认为是青海和硕特领主噶尔丹策旺的转世,这也从另一面支撑了颇罗鼐的诺颜(王公)身份。
上揭史料中“正在等候大主子特遣的审理此事的大臣”,指的是被雍正帝派往拉萨处理阿尔布巴等与颇罗鼐间战争善后事务的吏部尚书查郎阿,其于雍正六年八月初一日抵达拉萨①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3217号,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两路大军顺利抵招折,雍正六年九月初十日,第1664页。。可知,马喇、僧格的以上书信是在颇罗鼐攻取拉萨的五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初一日之间写就的,也就是说颇罗鼐占领拉萨之后,马喇等立即行文拉达克汗,要求其提供准噶尔的情报。可见马喇及后来的查郎阿以及雍正帝并没有怪罪颇罗鼐,反而认可其“战争行为”的背后,存在着清朝试图通过颇罗鼐与拉达克汗的关系来收取准噶尔情报的大谋略。面对这种情形,拉达克汗王回复如下:
告知办事大臣等。在彼处身体安康健朗,遵照上大主子谕旨于土伯特国平安施益而在,将此事与书信、礼品一并仁慈寄来,故我心中感到无尽欣喜。我在此处,仍照前一样处理着于内外地方之间守护的事务。再告知,如尔等所教之言,曾经贝子康济鼐与准噶尔交战时,我亦念及佛法及上大主子、达赖喇嘛之一切事情,与康济鼐同心协力,成就了事情。现在卫、工布的有些妖魔,不顾主子与达赖喇嘛之事及图伯特国的安逸太平,彼等企图任意统治,为此心中嫉妒,暗害贝子康济鼐,大风席卷土伯特国。因不爱戴上大主子及达赖喇嘛,行悖逆之事,故扎萨克台吉整饬兵力,成就了事情。听知此消息,犹如亲眼目睹般的感到欣喜。我乃承受上大主子恩德之人,在此听到后,理应派兵前去才对。只是战事迫近,地方遥远,且要守护疆土,故没能派兵前往。阿里军队出发后,因库克、布朗、鲁托克三地皆属边内,唯恐从其他地方引发战争,故外出野外驻扎防守,果然奏效。对事情真实尽力之处,扎萨克台吉心中明知。我想永远如此尽力。现在上大主子与达赖喇嘛二人,明鉴一切事情,将图伯特之事交一人办理为宜。若多人办理,彼此不睦,易生无理之事。教导如何能和气同心协力谨于战事为好。告知如此思考之处。我在此处,亦不违背上大主子之谕旨,先前曾尽力而行,现在亦尽力而行无两样。明鉴深广,永世教导,明鉴犹如滔滔恒河之水②《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为驻藏办事而来之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折(汉译请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3331号,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副都统迈禄等咨拉达克汗及其复文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第1705页)。。
如此,拉达克汗王尼玛那木扎勒也基于自己与康济鼐、颇罗鼐二人的关系,表示尽力于清朝可汗(皇帝)。当时清朝并没有征服拉达克汗国,也没有使其归顺投附,从关系性质上说,清朝与拉达克汗国之间并不是上下级统属关系,双方不仅没有中华王朝式的朝贡关系,就连蒙古式的可汗与诺颜(Mon:qaγan—noyan)或诺颜与属民(Mon:noyan—albatu)的统属关系也没有。清朝与拉达克之间完全是基于西藏王公康济鼐及其盟友颇罗鼐的个人关系来建立和维系的。而拉达克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也并不是隶属关系,拉达克汗王不是达赖喇嘛的臣子或属民,拉达克汗国也不被西藏地方政府所统治。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684年噶尔丹策旺与拉达克汗签订的条约来维持和发展的。而作为噶尔丹策旺→拉藏汗→康济鼐→颇罗鼐这一统治体系的人物,颇罗鼐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因颇罗鼐称呼清朝可汗(皇帝)为“大主子(Man:amba ejen)”,故拉达克汗王作为颇罗鼐的“好兄弟”,亦如此称呼。一方面,面对清朝大臣,拉达克汗王在书信中以“告知(Man:donjiburengge,原意为使对方听到)”一词来开头,意思即双方没有隶属的上下级关系,只有交往关系。拉达克汗王还明确说出了“驻藏大臣”的真实身份,即“遵照上大主子谕旨于土伯特国平安施益而在”的人。如此,清朝若想与拉达克建立关系来收取准噶尔情报,则西藏王公颇罗鼐最为关键,颇罗鼐与拉达克汗王的“好兄弟”关系实际上决定了清朝与拉达克的关系。至此,清朝通过拉达克收取准噶尔情报的渠道,正式得以开通。这是在清朝承认了颇罗鼐于西藏的政治地位及权利的前提下达成的。
另外,关于马喇及其后在拉萨办事的清朝大臣的出身及职责问题。
马喇,满洲正黄旗人,富察氏。曾三次被派往拉萨办理事务,第一次的职位是正红旗满洲副都统,第二次的职位是正黄旗护军统领,第三次的职位是正红旗满洲副都统①参见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僧格,镶红旗蒙古人,巴林氏,驻在拉萨时期的官职是内阁学士、理藩院侍郎、镶红旗蒙古都统②参见《清代驻藏大臣传略》,第1页,及《清世宗实录》卷92,雍正八年三月甲戌(六日)条以及《清世宗实录》卷123,雍正十年九月己酉(二十五日)条。。青保,驻在拉萨时期的职位是正蓝旗蒙古副都统③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03,雍正九年二月己酉(十六日)条。、左翼前锋统领、正蓝旗蒙古都统④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20,雍正十年六月甲戌(十九日)条。、镶黄旗满洲都统⑤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23,雍正十年九月庚戌(二十六日)条。杭奕禄,满洲镶红旗人,完颜氏,驻在拉萨时期的官职是工部左侍郎⑥参见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7,大臣划一传档正编十四,杭奕禄,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纪山,满洲镶红旗人,驻在拉萨时期的官职是镶红旗满洲副都统⑦参见《清代驻藏大臣传略》,第11-13页,及《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册,熬茶档一,第20号,驻藏大臣纪山奏请遣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折,乾隆六年八月十七日,第173-179页。。索拜,驻在拉萨时期的官职是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兼武备院正卿⑧参见《清代驻藏大臣传略》,第13-18页,及《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册,熬茶档二,第23号,驻藏大臣索拜奏报由颇罗鼐转赏御赐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物品折,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第545-552页。。傅清,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乾隆九年命为驻扎西藏办理事务的副都统,乾隆十四年十月再次被调往西藏办事,乾隆十五年五月抵达拉萨,是年十月十三日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中被害⑨参见《清史列传》卷19,大臣划一传档正编十六,傅清子明仁。。
可见当时作为钦差前去拉萨办理事务的清朝大臣,其官职各有不同。有的是八旗的前锋统领、副都统、都统,有的是理藩院的侍郎,有的是内阁的学士,有的是六部的侍郎,或武备院的正卿,他们并没有统一的官衔、官职。这说明“驻藏大臣”还没有被作为制度安定下来。不过重要的是,不管官衔、官职怎样,驻扎拉萨的清朝大臣在西藏、拉达克人面前,是以清朝可汗(皇帝)的“钦差”代表来存在的,其官职、官衔在其与卫藏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作为“钦差”的身份才是其能够办理事务的最主要条件。自雍正五年始,因达赖喇嘛属下的噶隆与原拉藏汗属下的康济鼐、颇罗鼐两大势力不和,且西藏在清朝与准噶尔的政治、军事、外交上极为重要,故雍正帝派大臣前去拉萨,对藏内的各大势力进行监督,将其动向秘密上奏,或以皇帝钦差的身份对各势力间的关系进行调节,或拉近各大势力与清朝可汗(皇帝)间的关系,以此为其职责。另外,正如笔者阐述的这样,利用颇罗鼐的身份和关系,通过拉达克收取准噶尔的情报以及在后来的准噶尔入藏熬茶当中监视准噶尔人,防止和离间其与卫藏上层的关系,成为当时被派驻拉萨的清朝大臣们的主要任务。当然,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偶尔领兵驻藏,或防御准噶尔,或保障安全,以彰显清朝可汗(皇帝)作为黄教大施主来保护卫藏的权利。
另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及《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中所录的有关本文内容的这15件奏折,雍正九年的有3件、雍正十年的1件、雍正十一年的2件、雍正十二年1件、雍正十三年有2件。乾隆元年、二年、三年各1件,然后是乾隆五年1件、八年1件、十二年1件。在此可以看出,雍正九年的奏折最多。这和当时的清朝正与准噶尔进行战争有直接关系。雍正八年,雍正帝下令与准噶尔开战,不久清军就在巴里坤和阿尔泰两路战场受到准噶尔军队的突袭而处处被动,为此急需得到准噶尔的内部情报。其后雍正十年、十一年,清准之间发生两次大的战役,即和通淖尔战役和额尔德尼召战役,双方各有胜负,战争进入胶着状态。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三年之间,清朝正积极准备与准噶尔媾和,所以不仅收取情报的次数少,且也不积极。乾隆四年前后,清朝与准噶尔达成和平协定,双方关系进入和平时期,因此直至乾隆十二年为止,清朝并没有怎么通过拉达克收取准噶尔的情报。如此,清朝利用颇罗鼐,通过拉达克收取准噶尔情报的事务,与清朝、准噶尔双方的政治、军事关系密切相关。那么,在这种清朝收取准噶尔情报的事务中,西藏王公颇罗鼐是怎样行事、怎样收取准噶尔情报的呢。
二、雍正朝后期的收取准噶尔情报事务与颇罗鼐家族
以下,通过分析清朝驻扎拉萨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内容,阐明颇罗鼐及其家族在清朝的收取准噶尔情报事务中的存在及清朝、准噶尔双方的动向,以及当时的内陆亚洲形势。
史料一:《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册,驻藏大臣马喇奏报准噶尔派宰桑率三百余人赴叶尔羌等情形,雍正九年四月十三日,第40-41页。
奴才马喇等谨密奏。为奏闻事。雍正九年四月初九日贝子颇罗鼐向奴才我告称:我子头等台吉珠尔莫特车布登自阿里地方于三月十八日向我寄出的书信已到来。恳请大臣等转奏大主子,等语。如此呈文。将此,臣我等大致翻译看得:以前曾报称:准噶尔一宰桑率三百人来叶尔羌驻扎,于酉年返回,等语。适才叶尔羌商人来至拉达克告称:今年正月下旬,准噶尔又一宰桑率三百人来至叶尔羌地方。向我下人傲慢妄言:准噶尔兵前去巴里坤攻击了大军,等语。还从我叶尔羌民众收集马驼,等语。再,拉达克之尼玛那木扎勒因年岁已高,欲让其次子拉西那木扎勒继位。对此,其长子德仲那木扎勒抗拒,言称:依拉达克地方旧制,俱由长子继承,若不让我继承,我即从台吉珠尔莫特车布登处请兵与你争斗,等语。是故尼玛那木扎勒才与属下众人商议,让德仲那木扎勒继了位。分给巴克迪等四城,让尼玛那木扎勒、拉西那木扎勒居住,等语。为此谨密奏闻。除此之外,将贝子颇罗鼐所呈蒙古文书信,一并谨奏览。
在《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这件奏折是前往拉萨办事的清朝大臣上奏给雍正帝的有关收取准噶尔情报的最早的一个。文中的头等台吉珠尔莫特车布登,指颇罗鼐长子珠尔莫特车布登,雍正八年以“统阿里诸路兵,防准噶尔贼,保唐古特”为由,雍正帝册封其为扎萨克一等台吉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卷92,扎萨克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列传。。后来,就在上奏这篇奏折稍前的雍正九年二月,雍正帝在册封颇罗鼐为贝勒的同时,册封其子珠尔莫特车布登为辅国公②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03,雍正九年二月庚子(7日)条。。因北京与拉萨相距遥远,是故写这封奏折时的四月十三日,其册封诰命还未到达马喇及颇罗鼐处,所以马喇仍以贝子、头等台吉称呼着对方。当时珠尔莫特车布登在驻防阿里,拉达克方面的情报是通过他传到拉萨的。阿里因是前述青海和硕特领主噶尔丹策旺征服后纳为己有的领地,是故拉藏汗被害之后,先是康济鼐,后是颇罗鼐占为己有,清朝的雍正帝也于准许颇罗鼐管理卫藏时对这一既定事实给予了承认③参见《清世宗实录》卷76,雍正六年十二月丁亥(11日)条。。雍正六年颇罗鼐移住拉萨之后,将其领地阿里交给长子珠尔莫特车布登管理,以显世袭。此次珠尔莫特车布登收取的情报可分两大部分:一是准噶尔派人到叶尔羌收集战略物资马驼,以与清朝交战;另一个是拉达克内部的汗位斗争,其结果尼玛那木扎勒的长子德仲那木扎勒,以颇罗鼐长子珠尔莫特车布登为靠山,顺利登上了汗位。当时德仲那木扎勒与珠尔莫特车布登已结成连襟,珠尔莫特车布登迎娶阿里古格诺颜的长女为妃,德仲那木扎勒则与古格诺颜的小女布里特旺姆结成婚姻④参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3册,驻藏大臣马喇奏颇罗鼐所报自拉达克处闻得准噶尔被重创策凌敦多布被参事折(附咨文议复片5件),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430-438页。。从这层意思上来看,当时的颇罗鼐家族控制的卫藏、阿里,与德仲那木扎勒家族领有的拉达克已结同盟。可能就是因为结成了这种同盟关系,所以颇罗鼐及其家族通过拉达克收取准噶尔情报的事情,得到了稳定的政治保障。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颇罗鼐呈给清朝大臣请求转奏清朝可汗(皇帝)的绝大部分文书,都是用蒙古文写成的。这虽然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语言文字问题,但其中隐含着深刻的政治道理和政治传统。文书中称呼清朝可汗(皇帝)为“大主子(Mon:yeke ejen,Man:amba ejen)”。如前所述,颇罗鼐自身及其政治权力的基盘是原拉藏汗的政治遗产,拉藏汗在位时称呼康熙帝为“大主子”⑤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合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8册,满文第392-393页,蒙古文第394-395页,“翊法恭顺汗拉藏之奏文”,日期不明,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也就是当时的蒙古王公们对清朝可汗(皇帝)的普遍称呼。颇罗鼐称呼雍正帝为“大主子”,意味着他是作为拉藏汗事业的继承者来与清朝可汗(皇帝)联系的,为此理应使用蒙古文。反过来,清朝可汗(皇帝)作为全蒙古的可汗,不仅承认了颇罗鼐在卫藏的政治地位及其作为诺颜(王公)的身份,同时也欢迎他利用蒙古文上奏,因为如此可以更加稳妥地拉近清朝与西藏的关系,这符合清朝的帝国统治理念。这又一次验证了笔者一直强调过来的,当时的清朝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是基于蒙古的政治传统来联系和处理事务的论断。此外,颇罗鼐曾被拉藏授予过“比车齐台吉(Mon:bičigeči tayiǰi,Tib:sbicha’i chi tha’iji)”即“秘书、文书台吉”的封号⑥参见多卡瓦・策仁旺杰著:藏文《颇罗鼐传》,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14页(汉译请见汤池安译:《颇罗鼐传》,第四章初入宦途,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104页)。,可见其蒙古文、蒙古语是非常流利的。不光如此,想必颇罗鼐对蒙古政治的运营理念及其方式也有深刻的了解。
史料二:《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册,驻藏大臣马喇奏报据称土尔扈特与天朝和好噶尔丹策零甚惧及其弟欲率兵征剿噶尔丹策零等事折,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第50-51页。
奴才马喇等谨密奏。为奏闻事。雍正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驻扎阿里的头等台吉珠尔莫特车布登向奴才我送来蒙古文书信,将其大致翻译看得:阿里头等台吉珠尔莫特车布登之文。为向召地大臣报所收情报事。珠尔莫特车布登我本人派至拉达克收取情报之人回来告称:十七人从叶尔羌来至拉达克,向德仲那木扎勒告称:我等来时路上雪甚大,所骑乘的牲畜俱已死去。噶尔丹策零问安尼玛那木扎勒,送来哈达一束,克什米尔绸缎一匹。噶尔丹策零之言:将卫、藏之一切情报寄信给我,等语。并无它言。再,适才从准噶尔叫乌巴锡的人来至叶尔羌,向与其关系甚好之人言道:噶尔丹策零之弟舒努巴图尔驻扎哈萨克地方,率领众多士兵欲要讨伐其兄噶尔丹策零。再,噶尔丹策零听到土尔扈特已倒向大主子后大为惊恐,于哈萨克地方预备了众多士兵,等语。再,以前俱已呈报准噶尔派往巴扎汗的使者纳辛巴巴的情报,近几日内纳辛巴巴即将到达拉达克,俟到达后再报大臣,等语。为此呈文,等语。为此与珠尔莫特车布登送来的原文一并谨密奏闻。
如此,珠尔莫特车布登从拉达克收取情报后即向马喇直接呈来蒙古文书信,报告了准噶尔的情况。其中最为主要的即噶尔丹策零要求拉达克汗王德仲那木扎勒“将卫、藏之一切情报寄信给我”的事情。正如笔者在拙文《拉达克与18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中所论述的那样,不仅清朝通过拉达克在收取准噶尔的情报,准噶尔也在通过拉达克收取卫藏及清朝的情报。而在这一“情报战”中,拉达克采取了“不偏不倚、两不得罪”的策略,不仅向颇罗鼐提供着准噶尔的情报,同时也向准噶尔传送着卫藏的动向。显然,这与拉达克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当时的拉达克,居于西藏和准噶尔之间,国力羸弱,地小人少,为了自保不得不采取平衡战略。清朝虽然国力强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但地方遥远,清军一时无法实现对拉达克的占领或保护,而准噶尔虽没有清朝那般强大,但军力雄厚,傲视中亚,且与拉达克毗邻而居,随时都可以将其吞并。所以拉达克不能选择一边倒的政策,只能在这两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友好交往。此外,颇罗鼐本人经历过康熙五十六年的准噶尔军队的入侵而深知其破坏力,故在通过拉达克汗转给噶尔丹策零的蒙古文书信中,虽在清朝大臣的严密监视下不能帮助其寻找大喇嘛和医生,但也表示出非常委婉的态度,报告了卫藏的社会形势很安定,黄教在隆兴的情况,以此解消了噶尔丹策零对卫藏的担心及随之而来的军事进攻①参见《拉达克与18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第210-211页。。所以说,拉达克汗与颇罗鼐,从各自的安全及利益考虑,都在积极实施“平衡战略”。本文中利用的奏折所反映的颇罗鼐及其家族对清朝可汗(皇帝)所表现出的忠诚及积极合作的态度,都是颇罗鼐为保护卫藏的安全及维持自身地位、权利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并不是颇罗鼐作为清朝的一名官僚,完全从清朝的利益着想去行动的。最后,文中提到了准噶尔派一名叫纳辛巴巴的人物前往巴扎汗处的事情。巴扎汗,亦称“巴沙尔汗”,是印度莫卧儿帝国西北部的一个邦国的君主。这位巴扎汗曾在1683年前后噶尔丹策旺和噶尔丹的联军征服拉达克时协助过噶尔丹策旺①参见〔意〕伯戴克著,扎洛译、彭陟焱校:《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五)——拉达克力量的衰退》,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30卷第6期,第24页。,准噶尔可能是在那时与巴扎汗建立友好关系的。
史料三:《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册,驻藏大臣僧格奏报探获噶尔丹策零派苏尔杂回藏消息后在喀喇乌苏等处添设卡伦防范折,雍正九年七月十三日,第66-69页。
奴才僧格谨密奏。为奏闻事。总理藏事护军统领马喇等咨文内称:为知会事。我处于七月初五日曾密奏:为奏闻事。雍正九年七月初五日多罗贝勒颇罗鼐将拉达克汗德仲那木扎勒寄给他的报告纳辛巴巴及准噶尔情报的书信呈文奴才我,并恳请转奏主子。将此翻译写成折子上奏,不可耽搁,故将颇罗鼐所奏蒙古文书信谨慎包扎后奏览主子。而将书信内容,令颇罗鼐急忙遣人去告知内阁学士僧格。奴才我等亦咨文。为此谨密奏闻。为此护军统领马喇、护军统领麦禄、总兵官包进忠行咨,等语。颇罗鼐所遣之人于七月初八日夜里到达,向我告称:拉达克汗德仲那木扎勒为报告其所收取到的准噶尔情报而送来的书信,将此多罗贝勒颇罗鼐呈文驻扎召地的大臣,以使上奏上曼珠舍利大主子。行文内称: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派往巴扎汗的使者纳辛巴巴,亲自率领三十人于六月初四日来到拉达克,而其货物则由前往巴扎汗处的老路送往叶尔羌。从叶尔羌地方前来迎接纳辛巴巴等的八人,于同月初八日到达拉达克。此八人言称:听说噶尔丹策零照看拉藏汗子苏尔杂特好,今年噶尔丹策零给苏尔杂五千兵丁,要将其送往藏地,即拉藏汗位。是故贝勒颇罗鼐派我将此情告知大臣,等语。是故奴才我立即向领兵驻扎喀喇乌苏地方的诺颜和硕齐,及在达木地方带领蒙古兵驻扎的颇罗鼐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行文:有准噶尔人要来藏地的情报,看守好尔两地之兵营、马匹,加固防守。尔等兵营当值的喀穆尼山口要加设卡伦,不可怠慢。准噶尔人要来,预测仍会越过去年走的哈马尔岭,从那条路寻喀喇乌苏而来的,此路甚是紧要。诺颜和硕齐,从尔之喀喇乌苏蒙古兵内挑选身体强健者十五名,从那条路至喀马尔岭地方为止速派去寻踪,并收取情报,等语。如此将拉达克汗德仲那木扎勒所报准噶尔人来藏之情报一并秘密具文行知。在后藏纳克产设置的三卡伦、腾格里湖设置的三卡伦、喀喇乌苏设置的三卡伦,奴才我给前去巡视此三路九卡伦的千总、把总,调配汉、蒙古兵丁,派出寻踪并收取情报。再,行文驻扎召地的护军统领马喇等,及贝勒颇罗鼐:令速速妥当办理在前藏、后藏预备的马、步唐古特兵丁,立即预备,等语。俟奴才我派出的巡视卡伦、寻踪及收取情报之人收取到准噶尔真实情报回来告知时另奏闻外,为此谨密奏闻。
在这通史料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为何总理西藏事务的马喇向雍正帝上奏颇罗鼐蒙古文书信的原文的同时,还令颇罗鼐遣人向内阁学士僧格报告书信内容呢。况且调动喀喇乌苏、达木等地蒙古兵加强防御的措施,皆由僧格致信诺颜和硕齐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等来展开。想必这是因为,初于雍正六年十月,为了防御准噶尔军队的进攻,清朝在西藏驻留两千兵丁,川陕绿营兵各一千,由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迈禄等总管②参见《清世宗实录》卷72,雍正六年十月己亥(二十二日)条。。其后,雍正八年三月,清朝令其中的一千五百名,由僧格统领转至腾格里淖尔驻防③参见《清世宗实录》卷92,雍正八年三月甲戌(六日)条。。上奏此奏折的雍正九年七月,僧格正在腾格里淖尔地方驻扎。僧格是八旗蒙古出身,会说会写蒙古文及满文,可将颇罗鼐的蒙古文书信或其蒙古语口头报告立刻译成满文上奏给雍正帝,又便于与颇罗鼐属下的蒙古人联系,传达清朝的指令,能够迅速建立防御。腾格里淖尔(Mon:tngri naγur)即今天西藏的纳木错湖,属达木地方,其周围遍布优良草场,自固始汗时代起就是蒙古人游牧、练兵、驻防、中转和修养的重要基地。固始汗、达延汗、达赖汗、拉藏汗的汗帐及噶尔丹策旺诺颜最初的领地都分布在这一带。而颇罗鼐掌权后,也将自己的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派至此地领兵驻扎。清朝于雍正八年即清朝与准噶尔开战的稍前,派僧格领兵驻防腾格里淖尔,除了利用他的蒙古语能力联系当地蒙古人建立防御之外,还有可能就是以此压制颇罗鼐的军队,防止其哗变投靠准噶尔。毕竟当时的清朝与颇罗鼐的关系,还未达到彼此完全信任的程度。
此外文中言道,噶尔丹策零计划将拉藏汗子苏尔杂护送至卫藏继承拉藏汗位,以此恢复青海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秩序。拉藏汗共有三子,长子噶尔丹丹忠、次子苏尔杂、第三子色布腾。噶尔丹丹忠与苏尔杂二人,于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侵攻西藏时被携往准噶尔。自雍正二年青海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抗击清朝的军事行动失败而逃亡准噶尔始,罗卜藏丹津本人及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以及噶尔丹策零,都一直没有放弃恢复青海和硕特在卫藏的统治秩序的远大抱负。为此准噶尔与清朝之间进行的战争与外交,在很多场合也都是围绕罗卜藏丹津及卫藏的蒙古王权问题来展开的①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号,雍正帝谕噶尔丹策零昭地驻汗一事不可行,雍正十二年,第45-53页。。正如笔者在拙著《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中的论述,达赖喇嘛的存在与准噶尔上层的统治正统性紧密相连,卫藏地区则与青海和硕特的王权相连,这些都是准噶尔政权的根本大事,其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蒙古政权与清朝的关系。所以基于准噶尔的这种国家政策进行的对卫藏的情报收取与军事试探,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活动。反过来讲,颇罗鼐和清朝也深知准噶尔的这种情节,故时刻预备,没有放松对准噶尔的情报收取、监视与防御。
史料四:《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册,驻藏大臣青保奏闻准噶尔活动情形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3页。
奴才青保等谨密奏。为奏闻事。雍正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贝勒颇罗鼐向奴才我告称:将拉达克德仲那木扎勒寄给我的探察收取情报的书信,恳请大臣看着转奏给上大主子,等语。奴才我等大致翻译其唐古特文书信看得:拉达克德仲那木扎勒之文,呈送贝勒。为使听闻收取到的情报事。叶尔羌领头商人格勒库鲁奈、图尔班奈俩回人及四个帐篷的人以及与纳辛巴巴同去的人,皆于今年十月十二日来至我拉达克。从他们探问准噶尔情报时告称:纳辛巴巴八月从拉达克出发,于十一月初七日到达准噶尔。令纳辛巴巴穿克什米尔服装,让跟役等穿拉达克服装,将纳辛巴巴化作巴扎汗的使者,把跟役装成拉达克汗的使者,于众人面前会见了噶尔丹策零,等语。此次来的商人,是我为收取准噶尔情报而派的人,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七月十五日为止,一直驻在了准噶尔地方,十六日出发返回来了。据准噶尔人议论:〔准噶尔〕与内兵交战,大破内兵。虏获众多人员、马匹、骡子、银两等,又攻打了喀尔喀。鼠年五月,准噶尔以默尔根台吉哈丹土克、多尔济丹巴、查干三人为首,率七万军队前去与内兵交战,不知其胜败。再,哈萨克掳去了驻扎在准噶尔边境的一千户人众,准噶尔派五百人追赶,只回来七人,其他人没有返回,或被哈萨克所杀,或已归顺,不知也。再,俄罗斯使者六十人来至准噶尔,甚是强悍,使者言称:将从我俄罗斯掳掠的财务、人员返还即完事。若不给,即进攻,等语。再,自喀尔喀叛逃的人前来投附,叫乌巴锡的人领兵前去迎接。〔再,〕大主子将三名准噶尔厄鲁特人作为使者派至准噶尔,为送还拉藏汗子苏尔杂从西藏领过去的人众,噶尔丹策零纳贡归顺,及若想交战不要偷偷来战,约定期日以战等事遣来。对此准噶尔人暗中仇视傲慢言称:若行的话就进攻,不行的话就议和,再顺利的话我就征服阿里、鲁都克,等语。不知是真是假。再,准噶尔担心吐鲁番部众反叛,故将其大部移走,剩下的已归顺内兵。现在准噶尔地方召集喇嘛,正供佛并大加念诵甘珠尔经。〔再,噶尔丹策零〕甚是慈爱苏尔杂,而不仁慈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与苏尔杂的跟役一个等级。另外,准噶尔将叶尔羌方面的汉人携至其本土,以建造城池而驻,等语。为此将收取到的情报具文呈送,训敕永远、仁慈不绝,明鉴,明鉴,等语。为此,奴才我等将拉达克诺颜德仲那木扎勒呈给贝勒颇罗鼐的唐古特文原书信,一并谨密奏闻。
这篇奏折记载了清朝、准噶尔双方酣战状态下颇罗鼐通过拉达克收取到的准噶尔情报内容。首先,噶尔丹策零让纳辛巴巴化装成巴扎汗使者,让其跟役化装成拉达克使者,在众人面前令二人朝见噶尔丹策零。很显然这是准噶尔的一种外交战术,一可以让周边的哈萨克人等认为准噶尔是大国,不至于使他们轻易发兵来攻击。二可让周边邻国觉得准噶尔有可能与巴扎汗及拉达克结盟,而使其不得不分兵把守在南部边境,以分散军事力量。当时的准噶尔正在与清朝进行战争,若其西方边境出现问题,则大为不利,所以使出了这种办法。此外,颇罗鼐收取到的情报中也谈到了和通诺尔战役。如前所述,在此战役中清军被准噶尔军队打得大败,很多兵员都当了俘虏。另外,关于准噶尔人愤恨时所说的要“征服阿里、鲁都克”的言语,这可能是因为此次提供情报的人是拉达克汗王德仲那木扎勒“为收取准噶尔情报而派的人”,所以特意突显了与拉达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阿里、鲁都克(Tib:ruthog,Mon:luduγ,即“日土”)。不过,从准噶尔人将阿里、鲁都克很放在心上的事情来看,准噶尔时刻将西藏纳入其征战范围。如前所述,西藏当时是准噶尔“国家战略”非常重要一环。
史料五:《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册,驻藏大臣青保奏将在额尔德尼召大败准兵之处寄信拉达克汗转告叶尔羌等处回人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第15-19页。
奴才青保等谨奏。为谨遵上谕事。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接准军机大臣等字寄内开:由我处奏称:臣我等阅看青保等之密折内称:自叶尔羌来至拉达克贸易人等,及拉达克德仲那木扎勒派去收取情报之人,于〔雍正〕九年十二月至十年七月十五日之间驻在准噶尔而返回。此间尚未听到我大军于额尔德尼召地方对贼大胜的消息,是故贼人傲慢妄言也。自准噶尔地方派至巴扎汗的使者纳辛巴巴等返回准噶尔后,巴扎汗及拉达克汗丝毫没有向准噶尔派遣使者,且令纳辛巴巴穿克什米尔服装,让跟役穿拉达克服装,化装成巴扎汗和拉达克汗的使者,于众人面前会见噶尔丹策零,看来是特意装模作样行欺骗,其阴谋是以此宣扬巴扎汗这样的大部及拉达克人等皆向其友好而遣使,好让哈萨克等回人听到后分兵把守。再,哈萨克掳掠了准噶尔一千户,准噶尔派五百人追击,只回来七人,及俄罗斯使者来至准噶尔逞强等言,与以前听说的无异。已行文将不久前于额尔德尼召地方大胜〔的消息〕知会颇罗鼐,作为颇罗鼐的意思令其告知德仲那木扎勒,以便转告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回人。于拉达克地方,叶尔羌等地回人往来行商不绝,因此行文青保,令其与贝勒颇罗鼐秘密商议后,从藏地回人或颇罗鼐属下人内选择甚可信赖之人,特遣至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向回人们透彻宣扬:大朝之兵已大败准噶尔人,哈萨克人来掳掠了准噶尔一千户,俄罗斯也有挑起战争的情形。如果你们反抗准噶尔的话,不仅有利于你们自身,大朝也会大加施恩于你们的,等语。告知此次派去之人:俟事成之后务必施以重恩,等语。出发时充分赏赐送行。除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回人外,若再有像哈萨克、巴扎汗等理应告知的回人,颇罗鼐亦可详加考虑后特遣使送礼,〔向他们〕宣传准噶尔人被打败、被掳掠之处。〔再宣告:〕派各自军队前去进攻,或大朝军队进攻时你们派兵来夹击,以此若能攻灭准噶尔,尔等永远得到平安太平,尔等亦可与大朝遣使通商,等语。再,还应明确告知:噶尔丹策零将纳辛巴巴化作巴扎汗的使者,将跟役装成拉达克汗使者的阴谋,特是怀疑尔等,分割尔等之实力,等语。为此,作为颇罗鼐的意思寄给德仲那木扎勒时,将书信编造奏览,俟上阅览后,再行文颇罗鼐,译成当地语言,交给派往德仲那木扎勒之人。此外,派人到何处,令其大致即照此编造送往,等语。如此于雍正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上奏时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与作为颇罗鼐的意思而写的寄给拉达克汗的书信一并送往,俟到达之后,令交与颇罗鼐,译成当地语言送给拉达克汗。再,于理应宣传之处,皆进行宣传,等语。如此到来。奴才我等谨遵,除将给颇罗鼐的行文译成蒙古文交与外,将事情启发劝导详尽说明,与其详细商量了派什么人,派往何处,到达后如何行动才能有利于事等。贝勒颇罗鼐之言:我乃极边甚愚昧之人,唯将收取到的各种情报,为回报大主子之恩而尽力。曾如此通过大臣上奏过。颇罗鼐我理应谨遵大主子所降之旨,派人至各地才对。唯以前拉藏汗之时,曾将二十人作为使者派往巴扎汗。将所派之人扣押,没有通至巴扎汗,且使他们驻在炎热地方,唯有阿旺云丹一人逃出来,其他人皆因不服水土而死。从那以后停止遣使,已二十余年了。再,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驻有准噶尔人,若派我之人,被准噶尔人发觉后反而不利于事。拉达克汗德仲那木扎勒乃是屡屡承接大主子隆恩之人,与叶尔羌、喀什噶尔之回人接壤边界而住,且他们善于谋生。将大主子的教导谕旨作为我的意思,制成唐古特文,派出我信赖之达尔罕宰桑及驻扎阿里管理兵丁的长官额尔克绰克图等,一并携带礼物,派往德仲那木扎勒,再将德仲那木扎勒属下行商善良回人等派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再从那里到阿克苏、库车、布哈拉、撒马尔罕、辟展、哈萨克、布鲁特等地回人及住在准噶尔边境的回人为止送达此情报。将此情报,亦转达给巴扎汗。再,被准噶尔贼人胁迫而去之人,向他们内部渗透情报,以制造混乱。或将内大军败走贼人进兵之机及他们如何粉饰演绎之处,令见机行事。如此向我属下详尽训导,于四月初六日立即令他们出发,等语。奴才我等慎思后,遵从颇罗鼐所言将其使者只派往德仲那木扎勒,派往其他地方反而无益之处,照其所言向达尔罕宰桑、长官额尔克绰克图及跟随他们而去的十五人,计算充分的盘缠,令办理粮食、钱粮的通事杨世禄拿出备用银二百五十两,赏给领头前去之两位使者每人五十两,跟随而去的十五人每人十两银子。贝勒颇罗鼐领着他们叩谢天恩。再,屡屡教导练习派去人等,于四月初六日派出。俟颇罗鼐所派之人返回时,将德仲那木扎勒如何派人将此情报送至各部人等,及各部人等如何遵行之处,明确查问另奏闻。除此之外,将颇罗鼐所奏蒙古文书信一并谨奏览。
这通史料记载了清朝怎样利用颇罗鼐和德仲那木扎勒,向准噶尔国内外的回人透漏清军于额尔德尼召大败准噶尔军队的消息,以此激发回人的反抗来削弱准噶尔的谋略。清朝从拉达克、颇罗鼐处收到准噶尔人令纳辛巴巴等假装成巴扎汗使者的情报后,认为这是准噶尔分散周边哈萨克等国兵力的阴谋,为了使这种阴谋难以得逞,实施了此次的策略。其内容是:清朝首先命颇罗鼐将清军于额尔德尼召大败准噶尔军队的消息,作为颇罗鼐自己的意思转达给拉达克汗王德仲那木扎勒,再由德仲那木扎勒传送给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的回人,以此激发他们的反抗,削弱准噶尔。另外,清朝又令颇罗鼐从藏地回人或藏人、蒙古人中挑选十分信赖之人派至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准噶尔统治下的回人地方,告诉他们清军已大败准噶尔军队,哈萨克也掠夺了边境,俄罗斯也要挑起战端等事,以此鼓动回人反抗准噶尔。再令派人至哈萨克、巴扎汗等地,透漏准噶尔被清军打败的消息,要求他们出兵单方面攻击或与清军一同夹击准噶尔,以期消灭准噶尔。清朝制定完策略之后,写成蒙古文书交给颇罗鼐,令他再译成当地语文寄给拉达克等地的首领。对此,具有丰富经验的颇罗鼐认为,如果派颇罗鼐属下的蒙古或藏人前往叶尔羌等地,万一被驻防的准噶尔人抓住会十分不利,担心一旦属下被抓住,准噶尔有可能会以此为契机派兵进攻卫藏,到时战乱又起,生灵涂炭。为此颇罗鼐建议:自己派信赖之人,携带厚礼去拉达克,请求拉达克汗王组织人员去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布哈拉、撒马尔罕、辟展、哈萨克、布鲁特及巴扎汗等地,向准噶尔境内外的回人宣传清朝的意图。而针对颇罗鼐的这种建议,清朝大臣青保给予同意,好好教导及大加赏赐之后,于四月初六日派出了颇罗鼐属下的达尔罕宰桑(Man:darhan jaisang,Mon:darqan ǰayisang)、长官额尔克绰克图(Man:daruga erke cogtu,Mon:daruγa erke čoγtu)及跟役十五人。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颇罗鼐所派的十分信赖的两位使者,皆为具有蒙古称号或蒙古职务的人。从这件事情可知,颇罗鼐与拉达克之间非常注重蒙古因素,当然这与青海和硕特领主噶尔丹策旺的征服活动及其后拉藏汗时代的关系有关,当时颇罗鼐仍是以拉藏汗体制的继承者来行事的。而清朝也试图利用这层关系,向准噶尔境内外的回人渗透,以期达到反抗、打击以至消灭准噶尔的目的。这是清朝与准噶尔正在酣战状态下进行的一种“内部破坏行为”,当时的清朝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难以通过军事活动来攻灭准噶尔,为此利用颇罗鼐、德仲那木扎勒一线,通过鼓动或联合准噶尔内外的回人来打击准噶尔。那么,其最终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史料六:《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册,驻藏大臣青保奏闻颇罗鼐所得准噶尔信息折,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第362-364页。
奴才青保等谨奏。为密奏闻事。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贝勒颇罗鼐将拉达克德仲那木扎勒为收取到的情报事寄来的书信呈给奴才我。将其大致翻译看得:贝勒明鉴之前呈文。贝勒此前所派的额尔克绰克图、达尔罕宰桑二人到来后,小人我即向叶尔羌派人宣传:于喀尔喀地方准噶尔军队被大主子军队大败而逃回家乡,实力减弱,因此现在叶尔羌、哈萨克、和硕特、土尔扈特人等见机理应报仇才对,日后对双方大有裨益,等语。如此秘密传告时,叶尔羌诺颜喀本宰桑听到后,以收取内部情报之人为由,将其抓捕送至准噶尔。噶尔丹策零询问:尔乃携来拉达克货物,为收取叶尔羌情报而来之人,据实招来,否则处死你,等语。对此言道:我俩是在西哈尔、叶尔羌等地与回人一道经商来的,被人抓来送到此处,丝毫不是为收取情报而来之人。卫、藏、阿里地方的黄教皆已隆兴,众生安逸过活矣。训练藏地马兵,比以前更加谨慎,整饬卡伦哨卡而在。此外我没有他言,要杀便杀,等语。噶尔丹策零将我俩交给一名宰桑看守,两个月没让见人,后来反而发给盘缠遣送回来了。我俩在那边时听说,在俄罗斯方面添设卡伦,又大派使者过去。我俩说去年在喀尔喀地方准噶尔兵大败时,有的说的一致,有的人则议论:自从策妄阿拉布坦去世以来,与众多边境上的人都发生了战争,结果如何,不可预测,等语。为此很是担心。有一日,见到苏尔杂说道:内兵已经接近,如果比这个还近的话,在准噶尔游牧地住不下了,等语。听说今年八月两路进兵了。再,准噶尔一位从喇嘛还俗者言道:此次派出的两路军队,若能,则即刻与内兵战斗,若不能,则偷盗其牲畜,等语。还听说已用兵哈萨克,但不知其胜败。叶尔羌等处众人不喜欢准噶尔人,相互议论:日后大主子兵锋前准噶尔必败,等语。此二人与叶尔羌一名叫哈瓦依伯克的商人一同,于九月中旬回来后,立即将此情报具文呈送,等语。是故将拉达克德仲那木扎勒寄给颇罗鼐的唐古特文书信一并谨密奏闻。
在这通史料中,拉达克汗王德仲那木扎勒通过颇罗鼐,向清朝转达了其“内部破坏”策略的实施结果。虽然拉达克遵照颇罗鼐的意思,向叶尔羌派去了密探,但其在行事当中迅速被管辖叶尔羌的准噶尔人长官喀本宰桑逮捕,以此宣告失败。不过拉达克的密探在准噶尔被关押期间,还是听到了一些有关军队调动及清军即将攻来的言论消息,表明当时的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对准噶尔的压力也非同一般,其内部掀起恐惧与无奈。另外,关于清朝“内部破坏”策略的失败问题,笔者认为其最大的原因还在于颇罗鼐、德仲那木扎勒两人与清朝之间的关系上。如上所述,颇罗鼐担心准噶尔的来袭,并没有遵照雍正帝的旨令派自己属下到叶尔羌等地去进行反抗准噶尔的宣传。同样的道理,拉达克汗王德仲那木扎勒作为与准噶尔毗邻的一个小国,更不会因为清朝去做反抗准噶尔的事情。这不仅关系到拉达克的国家安危,对其经济贸易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毕竟比起清朝,拉达克与准噶尔的地理距离更近,关系更为密切。
史料七:《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册,驻藏大臣马喇奏报准噶尔在叶尔羌城信息折,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22-124页。
奴才马喇等谨奏。为密奏闻事。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贝勒颇罗鼐向奴才我呈来阿里公珠尔莫特车布登寄给的一封书信,将其大致翻译看得:公珠尔莫特车布登呈文贝勒。拉达克德仲那木扎勒给我寄来书信内称:九月十一日,一百人为了贸易从叶尔羌来至我拉达克地方告称:准噶尔厄鲁特人曾不走克什米尔地方。叶尔羌商人阿尔皮拉库沙前去印度巴扎〔汗的〕地方经商。再,从内廷将一名将军作为使者派至准噶尔媾和。作为回馈,准噶尔将吹纳木喀作为使者派去,不知为何事,使者尚未返回。再,土尔扈特与准噶尔交恶,噶尔丹策零之弟舒努巴图尔已去世。还有大策凌敦多布、图萨马玲喇嘛也去世了。守护叶尔羌城的准噶尔厄鲁特比以前增多了,此外没有其他情报,等语。如此寄来。于此,我本想今年前去叩拜达赖喇嘛的,看此情报,因守护叶尔羌城的准噶尔人比前增多了,考虑边境地方甚为重要,故不得去。俟后无事时伺机再去叩拜达赖喇嘛。为此呈文,等语。为此谨密奏闻。
该史料记载了准噶尔与清朝进入媾和阶段的准噶尔的内部形势。史料中的“一名将军”,指雍正十二年八月被派往准噶尔的盛京户部侍郎、北路军营参赞大臣傅鼐①参见《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册,第3号,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更改前往准噶尔大臣等带往物品片,雍正十二年八月初三日,第38页。另据《清史列传》卷15,大臣划一传档正编十二,傅鼐部分载:傅鼐,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出任侍卫。雍正二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寻授兵部右侍郎。雍正三年,调盛京户部侍郎。雍正九年七月,召赴北路军营效力。雍正十二年八月,携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前往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处。十三年三月还。。傅鼐于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从巴里坤军营出发前往准噶尔,十一月初五日到达阿克达斯地方,十日至吉木色地方后,准噶尔宰桑乌巴锡领兵前来,引导傅鼐于十二月初九日到达伊犁河,十三日面见了噶尔丹策零。宰桑乌巴锡在本文所利用的史料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叶尔羌,一次是领兵前去迎接归顺准噶尔的喀尔喀人时,想必其是一位很活跃的宰桑。而准噶尔使者吹纳木喀,与清朝使者傅鼐一同于雍正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自伊犁河出发,前往清朝②参见《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册,第17号,侍郎傅鼐等奏报由噶尔丹策零处返回情形折,雍正十三年二月,第90-93页。。该史料中的奏折是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马喇自拉萨发出的,在准噶尔发生的事件情报到达拉萨已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因其主要还是通过叶尔羌商人来收取的,所以路上花费的时间比较多,不过由此可见拉达克收取的情报还是具有很高的准确性的。
三、乾隆朝初年的收取准噶尔情报事务与颇罗鼐家族
清朝与准噶尔之间自雍正十二年八月进入媾和阶段后,经过近五年的谈判及遣使密商,终于乾隆四年前后签署了和平协定。那么,在这一互相遣使媾和的阶段及达成和平之后,清朝又是怎样收取准噶尔情报的,收取了哪些情报,其中颇罗鼐又是怎样行动的呢。以下论述乾隆初年至颇罗鼐去世为止的时间段的清朝与颇罗鼐的活动。
史料一:《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册,驻藏大臣马喇奏报叶尔羌商人多有赴拉达克地方者应酌情办理卫藏人等与其贸易事宜折,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第192-194页。
奴才马喇等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元年三月初八日贝勒颇罗鼐向奴才我呈来阿里公珠尔莫特车布登寄的一封书信,将其大致翻译看得:公珠尔莫特车布登呈文贝勒。拉达克德仲那木扎勒给我寄来的书信内称:去年十月下旬、十一月初旬,从叶尔羌至拉达克的商人陆陆续续来了很多。据他们言称:管辖军队的诺颜都噶尔的儿子车旺领兵俱已返回游牧地,各地卡伦只驻有少量兵丁。相互议论着要与大主子媾和,不知其真伪也,等语。如此寄来。为此从阿里之噶尔笃克呈送,等语。再,据贝勒颇罗鼐言称:我卫藏人等,每年前去拉达克贸易。现在听说叶尔羌人正在拉达克行商。小人我愚思:因现在准噶尔正在寻求与大主子媾和,是故若我卫藏人等前去拉达克地方贸易,则会遇见叶尔羌商人,下等人口出狂言,以至生事,或泄露情报,亦未可定。故请求大臣等行文阿里公珠尔莫特车布登,我亦行文,若有卫藏人等前去拉达克贸易者,令其检查制止,让他们驻在阿里边境鲁都克城。再寄信给德仲那木扎勒,令其将彼处商人送到这边进行贸易,如此则双方俱可顺利贸易,亦不会泄露丝毫情报,似可至边境无事也,等语。为此奴才我等慎思,贝勒颇罗鼐诚心恭戴圣主之恩,唯思不泄露情报,强固边境,以使不生事端,为此照颇罗鼐之所请,奴才我等除向阿里公珠尔莫特车布登发去训导文书之外,为此谨奏闻。
这次拉达克收取到的准噶尔情报大致为:因要与清朝媾和,所以驻扎叶尔羌的准噶尔诺颜车旺已领兵返回游牧地,各个卡伦只留下少量兵丁。可见准噶尔与清朝的外交关系,时刻在影响着其内部的政策及因这种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形势。更为重要的是,颇罗鼐听到了准噶尔与清朝要媾和的消息后,马上与清朝大臣及珠尔莫特车布登商议,禁止卫藏地方的商人前去拉达克贸易。其理由是,唯恐卫藏人在拉达克地方向叶尔羌商人泄露情报,以致生事。笔者认为这是颇罗鼐为卫藏利益着想而商议的一项事务。当时清朝与准噶尔正在摸索媾和,如果此时卫藏方面出现不祥之事,以此对清准双方的媾和带来负面影响,或带来较大的麻烦,战事重启的话,那么卫藏随时有可能会被准噶尔军队攻击。所以,颇罗鼐以大局为重,期待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媾和,采取了卫藏人禁止前去拉达克贸易的指令。
史料二:《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册,驻藏大臣杭奕禄奏闻准噶尔情形折,乾隆二年十月十七日,第381-384页。
工部左侍郎奴才杭奕禄等谨奏。为奏闻事。乾隆二年十月初五日贝勒颇罗鼐呈文内称:今年闰九月十五日到来的拉达克德仲那木扎勒寄给我的书信内称: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派的使者图尔班、芒力克二人携前去克什米尔贸易的库沙、玛喇额敏二人来至我拉达克地方。噶尔丹策零寄给我的书信内称:向我往来贸易于拉达克地方的人提供情报。再,图伯特地方的人生活安逸与否,黄教隆兴与否,班禅额尔德尼的身体安好否,达赖喇嘛驻在何地,颇拉台吉父子在何地。将此情报,明确寄给我,等语。现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与我拉达克友好而行,此或是欲要打通前往印度巴扎汗道路的阴谋。再,使者图尔班、芒力克等口头言称:现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寻得上大主子之恩而和好,为此内廷将一名大喇嘛、一名诺颜作为使者派到准噶尔。准噶尔亦将吹诺木齐、奥洛依伯克两人作为使者,先后派往内廷。再,将以前准噶尔掠去的吐鲁番人等俱返还。吐鲁番地方仍照前不变,则大主子定会施恩和好。不管怎么说,噶尔丹策零已将额尔德尼摩罗姆宰桑作为使者派往内廷。将吐鲁番地方献给大主子,亦未可料。再,准噶尔进兵哈萨克,掳掠到大批人员和财物。返回时,噶尔丹策零之弟舒努巴图尔会同哈萨克半路截击准噶尔人,打死、抓捕了很多人,将准噶尔掳掠到的人员、财物也都抢走了。后来,趁土尔扈特不备,噶尔丹策零派兵前去杀死土尔扈特一大诺颜,又抓捕一大诺颜回到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仍担心舒努巴图尔不管何时定会发动战争而无时无刻不小心警惕。再,准噶尔噶尔丹策零现与俄罗斯互相和好,派遣使者往来。又听说噶尔丹策零欲要进兵阿里三地,不知能否依照其愿望进兵。这些情报虽难知其真伪,然只将所听闻的寄过去,等语。奴才我等向颇罗鼐言道:不要在意情报之真伪,唯行文尔属下驻扎各地的卡伦长官,严加防守警惕,等语。除如此交代之外,为此谨奏闻。
这通史料所记颇罗鼐通过拉达克汗王收取到的准噶尔情报是:首先,噶尔丹策零派遣图尔班、芒力克两位使者到拉达克汗德仲那木扎勒处,要求其向噶尔丹策零提供情报即卫藏地方的情况:黄教的隆兴、人民生活的安定、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人身安全、达赖喇嘛迁移后所住的地方及颇罗鼐父子的住所情况等。这又一次表明噶尔丹策零对卫藏的重视及对其内部情报的收取。自雍正六年起,清朝将达赖喇嘛迁移至泰宁居住,当时清朝与准噶尔还未开战,其主要还是因为颇罗鼐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不和所致。另外康济鼐和颇罗鼐作为原拉藏汗属下,康济鼐曾与罗卜藏丹津及策妄阿拉布坦有过书信联系,所以起初清朝并不十分信赖颇罗鼐,只是在试探他的忠诚。为此,雍正六年十一月清朝安全起见将达赖喇嘛迁移至里塘居住①参见《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己巳(二十三日)条。。这种迁移,作为结果,着实避免了准噶尔为抢夺达赖喇嘛而对卫藏进行的军事侵攻。此外,噶尔丹策零询问颇罗鼐父子的住所,这可能是为以后的军事做准备,当时颇罗鼐依靠清朝可汗(皇帝)的权威,掌握着卫、藏、阿里全部。准噶尔军队若真要行动,抓住颇罗鼐父子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说,虽然准噶尔与清朝之间在进行媾和谈判,但一方面噶尔丹策零并没有放弃对卫藏的试探。史料中的“内廷将一名大喇嘛、一名诺颜作为使者派到准噶尔。准噶尔亦将吹诺木齐、奥洛依伯克两人作为使者,先后派往内廷”,指雍正十二年八月派往准噶尔的傅鼐使团及准噶尔派至清朝的吹纳木喀、诺辉尼使团。可能人名在从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满语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少些变化。此外,对史料中的“大喇嘛”则无从知晓。“额尔德尼摩罗姆宰桑”可能就是噶尔丹策零第二次所遣的使者达什②参见《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册,第86号,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接待使臣达什等事宜片,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416-420页。,额尔德尼摩罗姆是他的称号,宰桑是他的职务。接着,准噶尔使者又说出了与哈萨克、土尔扈特之间的战事,表明准噶尔与清朝进入媾和阶段后,马上将军事进攻方向转移至了西线。最后,拉达克方面传达了噶尔丹策零有意要进攻阿里的事情,对此清朝大臣杭奕禄指示颇罗鼐不要太在意情报的真伪,一心防守好边境即可。
史料三:《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7册,驻藏大臣傅清奏据报准噶尔噶尔丹策零确已病故部内倾轧人员更替等情折,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第188-192页。
副都统臣傅清谨奏。为奏闻事。今年正月初九日郡王颇罗鼐来至我处,将拉达克乌勒吉图汗车布登那木扎勒收取到的准噶尔情报行文于我,并声称:我已将其译成蒙古文拿来了,请大臣过目,等语。如此呈文后,臣我翻译其文看得:郡王曾交代过收取准噶尔情报事,为此我配给朋素克六名伙伴,将此七人打扮成商人派到叶尔羌地方刺探。时被叶尔羌回人头目唤过去问道:将印度巴扎汗及图伯特卫、藏之情报、形势、概况,如实招来,等语。对于巴扎〔汗〕等的情报,将所知道的一切俱说出了。而对于卫、藏,答道:大主子之恩下太平安逸,黄教隆兴,今由颇罗鼐总理事务,等语。还称:我等乃是闲人,不知过于细微之处,等语。于是以没有说出真相为由加以怀疑,作为嫌疑犯被送至准噶尔驻了六个月。照前一样讯问后,仍照前一样回答了。据我等详细探察得:丑年八月噶尔丹策零去世,此乃真事。得痰核病,卧病十五天而死。去世之前遗嘱:于我的位子上,长子喇嘛扎勒二十岁,正好适合。但是,末子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十五岁,〔他说:〕因我父乃是洪台吉的转世真身,故对卫拉特的朝政与教法实在有益。若使即位,除了我还有谁〔,等语〕。尔奉戴〔准噶尔的朝政与教法〕谨慎尽力,等语。依照此言,〔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即了位。给长子一千户人口,令各自管理。其后,将哈柳宰桑作为使者派至京城,寅年六月返回准噶尔。大主子甚是仁慈,大主子降旨训导:尔之父亲已去世,今朕慈爱、恻然轸念,尔亦谨慎尽力,持显诚心。钦此。照礼赏赐无量寿佛等好礼物,赏赐非常,并使赴图伯特做功德之人于来年照旧遣去。哈柳宰桑奏称:以前那条路较远,故牲畜死的多,奏请从喀喇乌苏前去的道路,等语。对此颁旨:那也可以,钦此。对此甚是喜悦。听说将车布登台吉及其女儿、妻子一起杀死了,将其属民分给了宰桑等。将其叔父郭莽堪布喇嘛,虽是自己死的,但好像是被暗中杀死的。扎什伦布寺阿克巴喇嘛即其位,阿克巴喇嘛的位子上,任命了推萨姆灵的索本罗卜藏丹增。从土尔扈特地方来了一名使者。印度主子巴扎汗的使者也来了六圈人。向拉藏汗子苏尔杂的儿子纳古察,介绍了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兄弟的,不知是哪位的女儿,决定给纳古察做妻子。而对拉藏汗子噶尔丹丹忠之子,则不甚慈爱,如同仁慈罗卜藏丹津及其妻子扎木苏多勒玛二人一样。下人们议论噶尔丹策零去世之前王罗卜藏丹津曾放言:给我一万士兵,即能照前一样攻取青海,等语。互相还议论:现在他们尊重的是巴图尔之子纳钦宰桑、都噶尔之子查干宰桑、巴雅思瑚朗宰桑、小策凌敦多布、固始宰桑等人,等语。另有人称:前来图伯特之卫、藏做功德时曾上奏过主子,然到达图伯特地方后他们却禁止自由活动,看守严密,为此甚感困惑,等语。他们的台吉已经去世,新台吉年岁小,他们中间不太平,互相不合,故为防备阿卜杜拉噶里穆、哈萨克、土尔扈特、喀尔喀等地军队的进攻,添设卡伦、哨卡等事,甚是发愁,等语。以上是朋素克亲口说的。朋素克返回时,将罗卜藏达西等三名厄鲁特、回人、木纳作为使者一并派来,想为噶尔丹策零的事,给拉达克所属的黄教寺庙做功德、熬茶,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询问罗卜藏达西等时,言辞无异,此外丝毫没有诡异、欺骗、掩盖之事。将他们所言一切真实之处呈文。询问罗卜藏达西等:尔又要收取刺探阿里情报吗。对此回称:熬茶之事一完即刻返回,等语。为此臣我将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所收取的准噶尔情报,谨奏闻。
这里的郡王颇罗鼐,其郡王爵位是乾隆帝在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晋升的①参见[清]庆桂等纂:《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卷106,乾隆四年十二月乙酉(十三日)条。,这一方面反映了颇罗鼐为清朝的情报收取所做的努力及在对卫藏的安定与治理上做出的贡献,表明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的信任与巩固。另一方面此时晋升颇罗鼐的爵位,预示着清朝要在即将到来的准噶尔使团进藏熬茶的过程中进一步利用颇罗鼐。一方面,当时的拉达克汗王变成了“乌勒吉图汗车布登那木扎勒”,已不是原先的德仲那木扎勒了。在颇罗鼐的指示下,这位拉达克新汗车布登那木扎勒向准噶尔派去密探,并将收取到的情报寄信给了颇罗鼐。此次情报颇为重要,讲述了噶尔丹策零之死及其前后准噶尔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据上揭史料反应,噶尔丹策零于丑年即乾隆十年得痰核病去世①另据《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册,第294号,谕哈柳照准为噶尔丹策零派人赴藏熬茶之请,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第1459页载:噶尔丹策零享年52岁,突然患病,三天就亡故,等语。。去世之前立下遗嘱:由其末子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即位,同时分给长子喇嘛扎勒即喇嘛达尔扎一千户属民,令他自己管理。噶尔丹策零去世后,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统治集团将哈柳宰桑作为使者派往清朝②据《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册,第276号,伴送准噶尔使臣郎中伯达色等为哈柳谢赏乘轿事呈军机大臣等文,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九日,第1394-1396页载:哈柳等28名准噶尔人,于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日,从哈密出发前往北京,可知哈柳是在噶尔丹策零去世不久后即派出的。。对此,清朝方面不仅热情接待了哈柳,还允准了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提出的入藏熬茶做功德的请求③参见《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册,第294号,谕哈柳照准为噶尔丹策零派人赴藏熬茶之请,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第1457-1460页。。此外,准噶尔的新统治集团还下令杀死车布登台吉及其全家,分赃了他的属民,又暗杀了车布登台吉的叔叔郭莽堪布喇嘛。还特别仁慈拉藏汗子苏尔杂的儿子纳古察,向其指配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兄弟之女为妻。另外,虽然罗卜藏丹津还未放弃重返青海的志向,但准噶尔的新统治集团并不看重他,而是尊重属于准噶尔本土派的纳钦宰桑、查干宰桑、巴雅思瑚朗宰桑、小策凌敦多布、固始宰桑等军事将领。还有,准噶尔人对清朝的监视行为非常不满,称虽已上奏过清朝可汗(皇帝),然到达卫藏之后却禁止他们自由行动、看守严密、非常困惑等。而此次收取到的情报中很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们的台吉已经去世,新台吉年岁小,他们中间不太平,互相不合,故为防备阿卜杜拉噶里穆、哈萨克、土尔扈特、喀尔喀等地军队的进攻,添设卡伦、哨卡等事,甚是发愁”一事。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虽是噶尔丹策零的亲生子,然其岁数尚小,15岁即位,一时很难执掌准噶尔这样的封建游牧国家。只要条件具备,噶尔丹策零长子喇嘛达尔扎及其他各大台吉,皆有登基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可能。且准噶尔长年累月地与清朝、哈萨克、俄罗斯等进行战争,周边皆为仇敌。虽一时能通过外交协定得到片刻的安宁,然绝不可在军事上稍微怠慢。其统治集团内部,各大台吉的调动与赏罚,牵动着利益与名誉,面对周围的强敌能否团结一致,就成为对小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的巨大考验。拉达克汗王所派的商人密探在准噶尔六个月期间所探听到的以上这些消息,大都是从民间议论中收取到的,表明当时的准噶尔社会已充满了对小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统治集团执政的不安和恐惧,不确定性在增强,这也预示着社会不久将进入动荡期。当时,听到噶尔丹策零去世消息的颇罗鼐不知有何感想。不久,两年后的乾隆十二年二月六日晚,颇罗鼐也因病去世了。
结 论
本文通过以上的探讨,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作为青海和硕特蒙古政权的继承者,雍正五年(1727)年颇罗鼐基于属下蒙藏的兵力,打败阿尔布巴等七世达赖喇嘛属下的噶隆,开始掌控西藏地方政府和阿里地区。清朝一开始是支持阿尔布巴等噶隆的,后来在颇罗鼐已完全控制了西藏局势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承认了颇罗鼐的权利和地位。而作为诺颜(王公)的颇罗鼐,在清朝国政体系中,与满洲宗室王公、外藩蒙古王公等同属于王公阶层,一同拥戴可汗(皇帝)的权威,而不受理藩院的差使。当时的“驻藏大臣”,不管其官职、官位如何,在西藏人和蒙古人面前是以可汗(皇帝)的“钦差”即代表的身份来存在和办理事务的。这种帝国构造,是清朝向内陆亚洲腹地成功推进和维持其事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其次,颇罗鼐作为青海和硕特蒙古政权事业的继承者,为保住其在卫藏的政治地位及对阿里的领有,利用清朝可汗(皇帝)的权威对西藏地方政府及阿里实行统治,效力于清朝可汗(皇帝),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积极与拉达克汗王联系,利用拉萨⇔阿里⇔拉达克⇔叶尔羌⇔伊犁这条路线,不断地收取有关准噶尔政治、军事、社会等之动向的情报,并将其利用蒙古文通过驻扎拉萨的大臣转奏给了清朝可汗(皇帝)。
再次,颇罗鼐自身通过武力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之后,清朝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对其地位给予了承认的背后,是利用颇罗鼐与拉达克汗王之间的关系来收取准噶尔情报。对原拉藏汗属下康济鼐、颇罗鼐集团通过拉达克联系准噶尔的事情有所了解的清朝,一开始并不信任颇罗鼐,直到颇罗鼐忠诚效力于清朝的准噶尔情报收取事务的情况下,才逐渐改变了想法。在准噶尔的存在及自身兵力难以展开大规模征讨并长期驻扎以支配西藏的情况下,不改变原有的拉藏汗统治体系,通过与当地首领间的关系来稳妥地推进事务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是当时清朝的主要政策。可以说清朝前期的西藏支配,是在与准噶尔的对抗中逐步建立的。
最后,于准噶尔方面,其上层为了自己的统治正统性及青海和硕特在西藏的王权问题,将西藏置于其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时刻没有忘记进军西藏以恢复固始汗创立的统治秩序的政治抱负。虽然准噶尔碍于清朝的干涉不轻易进军西藏,但时刻密切关注着卫藏的动向。颇罗鼐对此十分了解,故而在紧密联系清朝的同时,也采取了对准噶尔尽量不得罪的平衡策略。
结合笔者在拙文《拉达克与18世纪前半期的清朝、准噶尔在西藏的角逐》中的探讨,在这种清朝与准噶尔的情报角逐中,颇罗鼐和拉达克汗王们并没有向清朝一边倒,而是巧妙地、不偏不倚地平衡自身与清准双方的关系,采取了对哪一方都不得罪的办法。在向清朝提供准噶尔情报的同时,颇罗鼐也通过拉达克向准噶尔秘密报告了卫藏的情况,以期解消噶尔丹策零侵攻卫藏的念头。面对清朝与准噶尔这两大军事强国,夹在中间的颇罗鼐及拉达克汗王,为卫藏和拉达克的安全与利益,巧妙地、秘密地收取以上两大国的内部情报,报告给了对方,以此换取了清朝与准噶尔双方的信任。为此,清朝利用颇罗鼐及拉达克汗王来鼓动准噶尔国内外的回人来反抗准噶尔的行动,迅速以失败告终。但是,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统治阶层内部,各大首领在对周边清朝、俄罗斯、哈萨克如何展开防御的问题上意见不合,同时在清朝的严密监视下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又没能从达赖喇嘛处得到新的封号,故出现了控制不了准噶尔内部局势的征兆。一方面,保有了卫藏,利用颇罗鼐一线掌握着准噶尔内部动向的清朝,严密封锁消息,处处监视准噶尔派往拉萨的熬茶使团,以此在与准噶尔的角逐中把握住了斗争的有利方向。颇罗鼐去世后,卫藏也和准噶尔一样,进入动荡期。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依照颇罗鼐的遗嘱,被乾隆帝册封为郡王。随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先是与自己的兄长珠尔莫特车布登争斗,引起战乱,其后又试图反抗清朝而被驻扎拉萨的清朝大臣处死。在西藏发生的这些事情,不能说与准噶尔没有关系,正如本文所论述的那样,其内部间的情报交流是频繁的。那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前后的清朝与西藏、拉达克、准噶尔之间的情报收取及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关于此,请参见笔者以后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