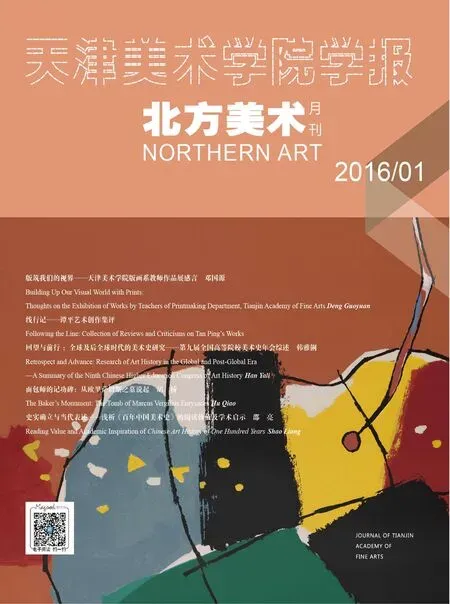迷幻 迷宫 迷梦
——从邓国源的“在花园”说起
云浩 朱大可 邓国源
迷幻 迷宫 迷梦
——从邓国源的“在花园”说起
云浩 朱大可 邓国源
编者按:2016年初,云浩先生、朱大可先生与艺术家邓国源先生一起,展开了一段有关“在花园”主题的对话。在这里,在花园不仅仅是邓国源近年来个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且涉及到诸多哲理与文化认知。我们关注这样的艺术思考,同时亦关注这场艺术交流的形式本身:新浪大V、艺术批评家与今天的当代艺术探索者越来越多地首先通过网络媒介来记录和发表自身的观点和经验,而其造成的文化反响再回馈于传统的报刊媒介,此一趋势已日益成为常态。不同的媒介规律也影响着不同的语言表达,视觉艺术如此,文字的诉说亦然。
Editor’s note: In early 2016, a dialogue with the theme of“In the Garden”was held among Mr Yun Hao, Mr Zhu Dake and the artist Deng Guoyuan.Here,“In the Garden”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opic of Deng Guoyuan’s personal artistic creation in recent years, but also involves much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cognition.We pay attention to such thinking on ar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form of this exchange of ideas about art itself: the trend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new normal that sina big V, art critics and present explorers of contemporary art record and publish their views and experience increasingly through net media then responses to them are refected in traditional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Rules of different media also infuence different modes of language expression.It is true to visual art as well as to textual narrative.

《诺亚花园》作品现场
二〇一六年的开年,我们遭遇“花园”。
这是当代艺术的大家邓国源的作品,他富于哲思地将其系列作品命名为《在花园》。
或者是定数,对于“花园”与构造花园的“玻璃”“镜子”等词汇都做过剖析的朱大可从上海的海上浮现,和天津河运码头的邓国源遥遥相对……
其实,具有深度流浪气质的朱大可和具备深度漕运帮主气质的邓国源互相仰望已久,而中国式的他俩,鉴于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高大,不敢贸然相见,揭开神秘的面纱;而作为匈奴后裔的我携寒冷风暴从草原呼啸掠来,使这两位的伟岸“码头”在广州港口衔接;于是,这艺术的江湖中,两位伟大漂流者的津海相逢就此展开……
——云浩

邓国源、朱大可和云浩在作品现场
1.迷幻:存在与虚无
云浩(以下简称云):我先以我的感觉聊聊,昨天正好下了飞机,也是有点累,也是有点头晕目眩,我昨天还有点晕飞机。我没穿着鞋套,我就先进花园了。我当时感觉瞬间一下子就蒙了,说得稍微转一点和科学一点,我被催眠了。你要说得好听了,就进入另一个世界了。说得心理学一点,可能童年的很多记忆被唤醒了。尤其是您的装置本身有点像我们童年的游戏,我跟朱老师同时想到了万花筒,那个结构是万花筒结构。
邓国源(以下简称邓):等于让你进入了万花筒。
云:对。人在被催眠的时候,说的不是我们现实中被你的理性深度编织以后的语言,实际上你说的语言又简单又明确,但同时是心理深层的东西。我觉得人在那个场景下,心理深层的东西就被调出来了,就如同处在花园中一样,被镜子悬置在空中。剩下的两件作品说明了花园的来处,三件作品又仿佛模糊地指向了一个远处。
在花园中,你是面对那个梦境中的自己。这个作品的伟大之处和邪恶之处皆在此,它是一个梦境或者说是一个幻境。因为上下都是镜子,你可以感觉到你站着的地方不实在。你要靠镜子中的你自己确认自己的存在,而镜子中的自己,首先是不同面的。第二个,你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因为独特的白亮色光来自四面,你整个人是惨白。你发现惨白的自己虽然穿着衣服,但是却是被剥了壳的自己在那儿站着,你是特别惶惑的。实际上我倒觉得在您一方面在给观者制造一个迷梦之前,先给了他一个惶惑。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看法。我不知道朱老师昨天进去以后是什么感受。
朱大可(以下简称朱):我的感受跟你很像。走进“诺亚花园”后站在那儿,感到很晕眩,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晕眩?因为我们看万花筒的时候,是一只眼睛在看。它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是一个筒状结构,而筒的边界是清晰的,跟外面相对稳定的空间产生一个对照。正是在这种参照系里,万花筒的结构可以被识别和分离,你会明确感知到它是一个幻象,所以它不可能引发整体性晕眩。而进入了邓老师的“诺亚花园”,由于它在整个地包围你的身体,所以就等于你掉进这个万花筒里边去了。它跟现实的边界消失了。关键是两种空间的边界消失了。
云:而且你是一个花瓣,你以一个花瓣的身份来反观这个万花筒本身。
朱:对,我也是玻璃的碎片之一,我也是景物之一。景物景物之间互相对应,它又无穷反射,马上就产生了晕眩。
云: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我在里面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多么伟大,反倒觉得自己被置于一种不可名状中。
朱:因为你被镜子复制了。因为它是反射,它会产生无穷的复制,你被增殖了。这个很像是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我忘记小说的名字了。有很多的小石头,一会儿变多,一会儿变少。在这个花园里面,它在无穷尽地自我反射,被变多,不断地增殖……
云:它跟鲍德里亚说的内爆是一个东西吗?
朱:应该有相似之处。
云:鲍德里亚认为这个世界实际上进入了后现代的时候,真实世界被替代……
朱:这是一种拟像式的无限增殖,而且是一种人工的、虚假的图像。邓老师的作品,巧妙利用了这种镜像效应。
云:而且这个花园是以美作为你的第一入射点先进来。进来以后,你被置于一种不可名状的状态之中,不可名状的时候,你产生两个东西,一个是幼年的回忆或者说自我好的那个部分,剩下一个部分是自我对这个世界的各种质疑,与生俱来的质疑,你那些恐惧感以及跟世界对峙时候的不确定性,然后被不可名状支配的你自己又在被无穷多地复制。
朱:我们讲的万花筒,还只是一种儿童玩具,它提供的是简陋而细小的筒形空间,而且它给你看的东西是对称的,但是在镜子花园里面却是非对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对称的状况下,图案具有某种理性的特点,六瓣、八瓣、十二瓣……很像是雪花的结晶方式。总之它是理性的,有规则的,有序的,可操控的。但是在这个花园里,镜子的无穷运动和反射,最终导致一个无序和失控的结局。
云:完全无序的,随机的,而且不可预知的。
朱:是的,不可预测。
云:被当成隐私的那些不可见的角落,你随时可以在最明显的地方看到它。
朱: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同时看到我自己不同的面,除了正面以外,侧面也可以看到,还可以看见反面,这会产生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我好像被剥光了,赤裸裸地站在一个迷幻空间里,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因此它不仅令人晕眩,它还是令人恐惧的。这就是它的双重性。为什么会晕眩?晕眩其实是恐惧的第一层反应。当上下左右所有镜面和光都对着你的时候,你是无处躲藏的,你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呈现出来。这是一个中国人存在的基本隐喻。我们所有人都置身于这样一个迷幻花园,被各种窥视的镜面所照射,这意味着主体性已经被彻底消灭。
邓:刚才你们俩说得特别准确,我这件作品是以一个美好的感觉让人进去的。我前几件的作品,这次展出的是三套:第一套金树、试管,第二套是桌子上那些金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弄这个金是比较直接的,我想用这个金代表人这种贪婪的欲望,一个是贪婪,一个是占有的感觉。我用试管,我一开始从构思的角度,有科学实验的这种形而上的虚假的热情,我想表达这种东西。第一组作品,金色的被砍断的树干其实有一种暴力在里面,直接破坏的暴力。又有一种形而上的意象,让每个人在这种暴力的情况下重新诞生。试管里面的植物是从生到死的过程要展现,让人感觉到生和死,死是生的必然的结果。我把这种隐喻放在里面。桌子那一组,我觉得传统文化的身份,加上这种工业后文明产生的毒瘤,这种文化的感觉一样,也是这种欲望造成的。加上试管,加上有生命力的植物,这样不期而遇地放在一起,在混乱的世界情况下,让人在传统与现代当中看到了一个生与死的必然。那两组作品跟这个花园比起来,就过于直接。
云:太像一个说明文。
邓:也是心理的过程。其实这个,我一开始构想的是真实的美好,好看。在好看当中,会突然感觉到自我消失了,不知道我和对方哪个是更真实的。这个时候出现了对周围、对个人的这种内心的震撼。我没想到更深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对自我镜像的这种反思。这个是很重要的。跟这几组作品比起来,都有传统文化、工业文明、形而上的臆想,也有生与死的过程。在美好和虚假的现实面前,人会想到背后的东西,每个人的脊梁骨都会发凉。
云:这谈到我对邓老师的一个“批判”。我觉得邓老师的早期装置,在设定某些作品过程的时候,仿佛是在“作诗”。他确实在“作”一首诗,“作”的痕迹非常明显,他在制作一首诗,在制造一个诗境。而作为装置艺术,实际上作者设置的前置词越少,有可能折射出来的意义和语义越宽。
“在花园”之所以有趣,也在于这样的多义性。可能一个儿童进去,他就觉得好玩儿,他眩晕,但是觉得快乐。我要说的是,好作品并不一定把一个明确的目的放在出口处:你出来一定要诞生一个这样的想法。应该是每一个人在里面看到的是每个人自我的那个花园,可能越是这样的作品,我反倒觉得它的语义更丰满、更开放,也就更多元。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作品叫作《花园》或者《诺亚花园》。可是他一直强调“在”字要留着,我看过很多人写他的文章,包括邓老师自己写的文章,他一直强调那个“在”。此刻我们强调的是现实感受。如果你不身在这个花园其中,你根本不知道它想说什么。它给你说的所有的语义,甚至语义中最大的一个部分,是靠你自己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具体感受形成的。这是这个作品与这其他人的不同,我看过太多的装置,你会诞生这样、那样的感情,但是你不会在里面引起你生理上的眩晕,引起你心理上的惶惑。而“在”花园就我而言则是眩晕、惶惑,这仿佛是我童年时候的游戏的小心态。这也就是我心象中的“在”。
朱:好,就让我们用这个“在”来做文章,就说这个“在”字。海德格尔会使用“此在”“彼在”和“在所”之类的语词来加以描述。观看这件作品,当你进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脱掉鞋子,或者穿着鞋套,以此保持一种清洁状态。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清洁的乌托邦。乌托邦里的所有镜面都被擦拭得纤尘不染。镜面这种清洁的属性,对于乌托邦而言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高度净化和极其完美的意识形态。
邓:有那种仪式感。
朱:对,通过这种套上鞋套的仪式,进入被高度净化的花园世界,我们叫它诺亚也好,亚当也好,它似乎是用来拯救你的灵魂的。所以叫“诺亚花园”,就像一条用来营救你灵魂的方舟。这是一种被神圣化的崇高“在所”,但当我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产生你所期待的被营救的幸福感,而是先发生晕眩,然后出现恐惧,最后你会发现你自身无处不在,你住进了所有的镜像碎片,是不是?你的“此在”被分解了,变成了无限个“此在”,但它们同时也是无限多的“彼在”。你被其他所有的“在者”观看和窥视。刚才我讲的恐惧感,正是从这个地方迸发出来的,由于你丧失隐私,被剥得干干净净,你就成了一个赤裸的人。但问题是,你融入了那个干净的世界之后,你本来就应当是赤裸的。赤裸是你存在的本性,也是乌托邦花园的本性。在亚当的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被赶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穿上了衣服,这就违反了“赤裸的原则”。所以,在越过恐惧之后,你是否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呢?正是赤裸让你可以成为花园的居民。所以进去被剥掉是很正常的,它完全符合花园的逻辑。这种乐园式的幸福感,可能是恐惧之后的第三种状态。

《诺亚花园》外部
再接下去,我还会产生一种虚无感,因为我被碎片化了,就像云浩讲的,我不知道哪个影像才是真实的存在,它们究竟是“实存”还是“虚在”,另外,“此在”和“彼在”的界限也丧失了,就像庄周的那个“蝴蝶之梦”。最后,你会发现,你的本质已经消失。
云:就在来这里之前,我看到鲍德里亚写的一段话。他说人在北极的时候,所有的风都是南来的。北本身就不存在了,你拿出指北针找不着北。在花园中,你发现围绕着你的都是花园的时候,连花园都自行消失了。如果全世界都是花园,花园这个概念就不在了。当你身在花园的时候,你恰恰是那个目睹花园完全消失的人。
朱:这是一种双重的解构。第一,花园解构了主体,你置身其中的那个主体。同时,因为这主体的被解构,花园也被解构掉了。花园既解构你的存在,也解构了你的在所——存在的场所。我觉得,这种双重解构是这件作品的重要意义。其实我不知道邓老师建造花园的原初意图,从我的私人角度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反讽的花园,先天就具有极大的解构性。它的目标是建造一个乌托邦,然后通过这种镜像的互相反射把它虚拟化,最后把这个“实存”及其“能指”都消解掉。这件作品不仅有它的美学价值,而且还有深刻的现实讽喻性。它给出了一个示范,表明装置艺术是可以如此深入地介入现实,向我们说出人的存在状态的真相。
云:我想这也就是当年邓老师为什么转型,从一个优秀的油画家转向装置艺术,意味着什么?一个优秀的画家往往一张画是上千万的拍卖价,实际成交价也在百八十万。但是您却把这个放弃了,变成一个装置艺术家或者一个实验艺术家。我倒想听听您是怎么想的这个转型。
邓:实际上我并未彻底转型,包括我做的所有的平面作品,你看我做的一系列,《在田野》《在北方》《在花园》。这是一个“在”的感觉,这个“在”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我在这里,还有一个是我想让观众看到我这个东西,能够置身当中。这是我从平面开始做到装置,我并没想放弃哪一个。我觉得哪一个部分如果说得更深,就做这个。或者某一种灵感上来以后,我就做这个,我并没有放弃架上绘画。包括我做的水墨也都是这么一种感觉在里面。但是我为什么用花园这个题材?花园是人们对环境最重要的一个寄托。
云:而且花园这个概念不止一次出现在您的描述中和您对于今后系列作品的构思中。
邓:当时有《在北方》,《在田野》也有,后来就一直叫《在花园》。我觉得花园不是一个简单概念当中的花和草,是对环境和精神的寄托。任何一个东西好看了,他就觉得像花园一样好看。而且花园跟自然有距离,它是超出自然本身的,我觉得这是我考虑的一个东西。
云:最终没有想到正因为叫了《在花园》,从而使花园和“在”两不在了。“在”也不在了,花园也不在了。
(云浩按:可能由于我和朱老师都在一直思考关于这座花园,所以,谈话的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好像两个等着班车的人正好赶上这一班,于是急匆匆地上车……没有一般谈话的轻柔开始;也好,就好比一进入花园就彻头彻尾地迷幻了一样,这个谈话在“花园气质”的影响下抬脚便达顶峰,接下来就是峰回路转了。)
2.迷宫:玻璃、反射、幻象、轮回
朱:无论是平面的架上油画,还是拥有三度空间的装置艺术,它们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无疑是互补的。世界上有两种图像乌托邦,一种是平面的,在人类早期年代,它就以岩画、壁画和器物装饰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云:图像的方式。图的方式。
朱: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空间的觉醒,开始努力把自己从三度空间里剥离出来,建构一种平面的幻象。这在当时是一场思维模式的进化。但今天艺术家反而在努力后退,还原到最古老本原的状态,也就是那个更具本质性的存在空间里去,这个空间不是二维的,而是一个三维和四维的。像这件装置作品,它在花园中间安放了一个旋转的双面镜,构成一个不断变幻的、高度四维的、爱因斯坦式的新时空。而这是邓老师作品的魅力所在。这是当下很多装置艺术家根本无法做到的。
蔡国强的爆破艺术是一种时间艺术,它没有空间。虽然他制造了一个天梯,试图描述“天”与“地”的间距,好像具有某种空间性,但他的梯子还是在时间中呈现的。后一个图像抹除了前一个图像,像水流一样,这种艺术我称之为时间艺术,一个纯粹的线性艺术。
在装置艺术方面,我并不看好艾未未,他的构思主要依赖克隆和模仿,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他的方法是在那些“美术原型”的基础上,以人和物体为材料,进行视觉暴力式的放大。他的三项基本原则是:第一,采用小物体的大数量堆积;第二,这些物体彼此间是完全相同的,是同一物体的大数量重复,比如陶瓷瓜子;第三,追求单个物体的超大体量。这正是以集体主义为基石的法西斯美学的特点,它跟莱妮·瑞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有多少区别呢?他们的语法是完全一致的。你在苏联和朝鲜能找到大量类似的例证。我不喜欢这种东西。
云:朱老师好几次说过,邓国源的装置比艾未未强得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个境界。邓国源的作品比艾未未强多了,别人先不谈。都是装置,都是靠一个构造,想阐述自己的话语。
朱:用法西斯语法来对抗法西斯,这是一种古怪的美学悖论,它不能推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反抗,更不能表达艺术本体的自由精神。我觉得这座镜子花园,已经超越了这些陈旧的帝国语法,回到他个人的反讽式的寓言空间,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变化。
云:和他用镜子这个质素……
朱:有很本质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关系。
邓:镜子会产生空间。
朱:然后旋转的镜子又产生了时间。所以他就把这个时空非常好地组合在一起。
云:本身又是个幻象。
朱:对,又是个幻象。我们不妨先从玻璃开始讲起。我们要分几个话题讲,一个是材料。镜子起源于玻璃,玻璃原来的作用是两个,最早是用来透视的,但它也有一定的反射性。所以玻璃有二元性,其他材料很难做到这点。它的透视性使得它可以透光,令你的视线可以穿越玻璃,看到物体背后的事物及其真相;但同时它又在展开反射,映射了观看者本身及其身后的景色。这两种功能一旦结合起来,玻璃就具有了某种神奇的特点。中世纪教堂率先大面积使用玻璃,因为玻璃的绘画,借助其透光性,把来自神和天使的光线,引入教堂内部空间,同时照亮那些彩色镶拼图案,但当你走近玻璃时,就会发现它的反射性消失了。教堂改造了玻璃的属性。
但在“上海新天地”,情形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玻璃的双重性被解放了。用青砖制造出来的石库门建筑,原本是非常封闭的状态,它的窗户很小,使用高大的门墙,它是根据防卫性语法设计出来的建筑样式,这是近代江南乡村建筑的普遍风格。它之所以出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因为有一个很沉痛的记忆。当年太平天国进攻上海,这些居民大部分是太湖地区的逃难者。他们会拥有充满恐惧的历史记忆,担心被暴力掠夺和伤害,所以用石库门来建造一个盔甲。
但是,上世纪90年代打造的上海商业街区“新天地”,却与此完全不同,它对外宣称精密移植了石库门建筑,就连青苔和尘土都一起搬运了,但其实还是做了重要的改造。不仅内部结构完全打开了,而且青砖的墙体面积明显减小,出现大面积的玻璃。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香港设计师改造了青砖语法,瓦解了防御性语法。但玻璃并不完全通透,它是一种有色玻璃,加上光线反射的作用,游客其实无法清晰地观察内部。但是当内部灯亮起来之后,你又能穿越这些玻璃,进入里面的时尚空间。这是一种妥协的和有限开放的空间。
邓:里外都融到一起……
朱:是的,玻璃能够产生一个空间的跨越和融合。“新天地”表达了青砖和玻璃的双重语法——防守和开放。对“新天地”的打造者而言,它是一种市场行为,它必须表达市场的开放性语法,开放是贸易的前提,也是贸易的目标。所以“新天地”必须改造原来的语法,把“旧天地”变成“新天地”。那么旧天地是什么呢?比如“一大”会址,作为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它原先是非常封闭的,是革命党人进行秘密集会的场所,跟商业和开放的语法完全不同。在整个现代化的都市建构中,玻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云:当玻璃被镀上一层汞……
朱:在变成镜子后,玻璃的通透性就消失了。但我觉得邓老师的特点是使用了单面反射,而且还在花园四周开了窗。
邓:我当时开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植物要呼吸,第二个想给人一种窥视感。我希望人从里面出来以后,在小窗口去窥视,发现他先前找不到的一种韵律。
朱:实景和虚景,透视和反射,这些对立的元素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所以这个镜屋是一个开放性装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镜子完全反射的情况下,它的语法是拒绝性的。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像,但看不到玻璃背后的事物。玻璃实际上在拒斥你,它只反射你,映照你,但拒绝你进入和穿越它,这是镜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我觉得这种镜子语言,在西方可以解释成它对事物隐私的防卫。但在邓老师的作品里,它回到了一个更深刻的古典意义。
我们今天讲到了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所有小说,都是迷宫小说,由网状的小径、走廊、镜子和语词所构成。镜子加剧了迷宫的迷失性,你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出口。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主题是迷宫。这种迷宫也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存在特征。大多数中国人都陷入了巨大的价值迷宫,我们的存在是一种迷失性的存在。当代人的人生,仿佛每走到一个道口,面对很多的道岔,总是失去正确选择的契机,也就是总是选择错误的那条道路。在这期间,还有一大堆虚假的宣传语和广告,冒充生命导向和指南,以欺骗的方式,影响和控制我们的判断,把我们引向歧途。在这样的意义上,花园的空间迷宫,仿佛一个暗喻。
从迷宫的角度来看镜屋,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无穷的反射之中,物体和道路都被虚拟化了。中国园林的本质性特点,就是它的迷宫性。二十年前我在澳大利亚做画展,地点就放在悉尼港的中国花园。这边是完全西式的、风帆式的现代建筑,带有各种白色的金属桅杆和悬索,另一边就是古典的中国花园,我在里面做画展。待了十几天,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经常有老外拿着花园地图找不到北。我跟他讲这样这样走,但过一个小时,见他又转了回来,还是没有走出去。这个细节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实际上中国花园没有那么复杂,中国人对迷宫是有经验的。但西方人没有受过迷宫训练,他们会觉得非常困惑。
云:西方人会生气。
朱:不少游客当时就生气,觉得这是对智商的极大愚弄。那个花园,是广州市园林局的作品,组合了好几个苏州园林的局部。
云:而中国人会着迷于这种别人对他的欺骗中,而且为别人设计的精心而赞叹。
朱:当你走进去以后,中国人会融入迷宫当中,他不觉得这是什么骗局,他会对每一个景点击节叫好。虽然整个存在是迷失的,但是他不会因此而感到焦虑。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特点,跟西方人有很大差异。它塑造了我们的基本信念。

以形而上的方式诞生 III V 试管 植物 铸铜着色 古典桌椅 鸟笼 2011年

(云浩按:作为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快速地经由《花园》找到了诸多和当下现实的接驳点,并以此拓展开去,由此,这一篇文字,绝不仅仅是对邓国源作品和对当代艺术的剖析,而是借着这种阐释,直达中国当代文化深处。)
3.迷梦:轮回、原型、三棵树
云:我写过一篇文章:时间在东方人,尤其是在中国人这里,是个循环系统。我们的纪年方式是六十年一甲子。每一个中国人生下来就知道:我没有远方,我只是圆上的一个点。
朱: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管这个叫“佛教时间”。中国人和印度人很相似,他的时间是自我循环的闭合时间。“诺亚花园”也是如此。从时间上来讲,它在旋转中不断地自我循环,形成自我闭合的四度时空。
云:而且有一点很奇妙,这是我前一段想到的。我怎么想到的呢?是阿城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写他的父亲。我发现他的文章很短,我想你也读过。你读到后面,你会发现前面的很多字词跳出来,他在里面设了很多伏笔。你看到后面,你才知道前面说的是什么。这是类似红楼梦式的语法,那个语法从头到尾在设迷局。你如果不看完全篇,你是不知道它前面说的那句话的完全含义是什么的。我当时欣喜地跳起来了,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忽然发现东方艺术里面的时间性。
朱: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恐惧呢?就是因为它是循环的。我们没有焦虑的原因,是我就待在这里等着,反正总有一天会回到原点。这种闭合制造了存在的安全感。当然,这种安全感也是虚幻的。
云:假如你接受你被轮回的前置词之后,你对时间的焦虑就消失了,你对死亡的恐惧就减弱了。我当时为什么那么高兴?我记得我跟李泽厚先生论到这个艺术的门类的时候,李先生当时说目前还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或者艺术批评家想到中国的艺术是时间性的,至少没有做一个系统的论证。当然我的功底不够,我论证不了。我当时是在写徐冰,不停地找,发现我后面写的东西跟前面写的东西有时候是矛盾的,徐冰作品的意义是多重的。他的作品设了很多埋伏,就像他用垃圾做的凤凰。本身最后是要被放置在一个无比宏大的世博会,但是前置词是用垃圾做的。他埋了很多阴森的或者阴险的伏笔在里面。这个东西在我们今天谈到的邓老师的花园里面,你会发现那个镜像中的自己,当然你看到的是同一个时空,但你浏览的顺序肯定是看完一个地方再看一个地方。等于你是在不同的时间看到同一个自己,实际上这里面偷偷叠加一个时间性进去。
朱: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涉及好几个问题。一个是时间,它是自我循环的,是东方时间或佛教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深受佛教轮回的影响。
云:起承转合。最后要合回去。
朱:对呀,是要合回去,形成一个首尾相衔的圆环。这种圆的原型最初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叫作衔尾蛇,英语叫Ouroboros,表现为一条蛇张嘴咬着自己的尾巴,这种圆形有时也会扭曲成8字形。向东方传播后,成为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和图像学基础。整个东方的艺术基本上是线性艺术,也就是说它是时间的艺术。中国人喜欢把图卷展开来看,看完就卷着收起来。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时间过程吗?书法也是如此。卷轴是中国式时间的工艺象征。
云: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邓老师的绘画是无焦点的。大卫·霍克尼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大卫·霍克尼在尽可能地把他的图像东方化、时间化。他在探索不同的观看条件下,不同的观看时序下,空间的平面排列方式。大卫是冲着达·芬奇去的,冲着焦点透视去的。
朱:原来焦点透视就是强化它的空间性。三度空间在透视的情况下,把空间的主体、前景、后景通过透视的方式组织起来。
云:而且还有一个关键,那个焦点,或者说那个消失的远方,那是逻各斯,它总有一个东西要我去追。但是在中国人这里,这个东西是平的。
朱:因为它被时间解构了。这个事情要谈的话,又涉及一个本源的问题,就是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差异。中国也有它自己的逻各斯——时间的逻各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诺亚花园”把这两种逻各斯做了一个整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两种逻各斯都有它的问题。中国的立场是时间性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自信自己是一个时间民族,它可以在时间里存在数千年之久……
云:永存的。
朱:对,几乎就是永存。而且它还是一个汉字共同体,它可以依赖汉字这种非常具有时间性的文化载体存在下去,直到汉字被消灭为止。中国人把空间奉送给了国家。他会在国家层面上追求领土的伟大性、辽阔性和中央性,但在个体层面上,却不断放弃空间诉求。士大夫阶层尤其如此。这种放弃空间的文化运动,导致了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的精神空间,自明清以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这种缩微化文化推动了江南园林、盆景艺术和微雕艺术的兴盛。你们会发现,这些在空间上经过严重缩微的艺术,是一种病态和畸形的宣言,它旨在告诉世人,我们不需要空间,我们是龟缩和蚁化的一族,我们成功地站立在针尖和麦芒上。这种缩微美学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搞笑的。过去我们曾经嘲笑过这种“南柯一梦”,而后来我们竟然成为这种“蚂蚁叙事”的积极分子。在对待空间的态度上,中国人走向了一条自我萎缩的美学歧途。
云:螺蛳壳里做道场。
朱:尽管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但我们仍然有足够的日常空间,来安放我们的身躯和梦想,可是我们还要去搞微雕,在一粒米上面写唐诗,在一枚枣核上雕出大观园,并很引为自豪。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犹太人这样做,我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民族长期没有自己的生长空间,它是典型的时间民族,但中国并非这样,它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自己的时间事务,但奇怪的是,尽管它拥有自己的时间信念,而个体的精神空间却变得非常狭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六百年以来,中国人的趣味空间就一直在塌陷之中。我所关注的是,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终止这个萎缩的进程。
还有一个来自“诺亚花园”的启发,是你云浩刚才提到的,包括邓老师自己也提到的那组装置作品——《以形而上的方式诞生》,其实它跟花园之间是有逻辑关联的。我一开始就把“诺亚花园”理解为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伊甸园里面其实有两棵树,一棵叫生命树,还有一棵叫知善恶树,又叫智慧树。亚当和夏娃偷吃的,其实是智慧树上的果子,他们没有偷吃生命树的果子。这场背叛导致什么结果呢?他们懂得了善恶,有了伦理观念,也有了爱欲,他们开始做爱,并且有了性的羞耻感,而这些感受都跟知识和智慧有关,从此人开始变聪明了,但是他们没有获得永生的权利,因为他们忘了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对于本雅明这样的犹太思想家而言,从生命树到知识树,这是一个显著的倒退。
在犹太卡巴拉教派的观念里,生命树代表人类的纯洁世界,而知识树则象征着堕落和各种罪恶的开始。生命树朝拜从西亚开始,向全世界蔓延,涉及犹太教、基督教、基督教的神秘教派如诺斯替教、佛教、印度教,等等,它有一个广泛传播和演化的过程。知识树统治的时代很长,它的第一个高潮是希腊罗马时代,第二个高潮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第三个高潮是近现代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在迎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个高潮。你可以把培根的箴言“知识就是力量”,看成是知识树自我宣传的广告语。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棵树的统治下。这是在西方发展出的一条路径。还有一条路径在印度,知识树变成了如意树,树上结满了各种珠宝果实,琳琅满目。印度佛经里有大量关于这类如意树的描写。它跟以前的树的最大不同,就是开始散发出强烈的物质性光辉。这种充满物质性的宝树传到中国后,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摇钱树。
云:我们拜金由来已久。
朱:本来在佛教经典里,那些宝树上挂的东西,仍然是人类精神智慧、精神财富的象征,但中国人却误解了它,把它彻底物化,变成了摇钱树。只要你站在树下使劲摇一摇,铜钱就自己掉下来,你就能不劳而获,成为巨富。大约在东汉时期,在四川、湖北和云南一带,工匠们曾经制造出大量摇钱树,被那些渴望金钱的家庭收藏和摆放,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这就意味着,生命树越向东方行走,越趋于实用化和利益化。最终,今天中国人眼里只有一棵摇钱树,既不是生命树,也不是智慧树。我们就抱着这样的树美妙地活着。所以,邓老师这次展出的作品《以形而上的方式诞生》,出现了用金粉涂饰的那些黄铜树干,正是这种拜金主义现状的写照。它是摇钱树的一种当代表达。
云:换句话说,中国人自古至今对消费主义一点都不陌生。
朱:摇钱树是中国人的重要传统。现在总有人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腐蚀的结果,但摇钱树出现于近两千年之前,古已有之,而且是极富原创性的作品。现下流行的拜金主义,不过是这种历史传统的延续而已。其实这种膜拜本身也是一种迷宫。邓老师如果今后要继续把花园系列做下去的话,建议把树和花园做一个结合,让树回到镜子花园里去,把生命树、智慧树、如意树和摇钱树都做进去,这四棵树就是人类倒退的缩影,一部最简约的人类精神简史。
邓:后来设计这个花园的时候,想在开幕式上,有三个人,一个是cosplay,一个是穿黄梅戏衣服的人,还有一个是保安。我想把这三个人放在里面,各演各的戏剧。当时我想打破时空的界限。
云:没有好,老哥,让作品自己说话,别再做一个作品去解释那个作品。你们看得懂、看不懂,让作品自己说话。
朱:不是说它不能阐释,我觉得阐释可以,但要用原型的思路来进行阐释。我们要回到原型的起点上来。我刚才为什么讲生命树,因为它就是神话的第一原型。花园里面放什么东西?就四棵树,树是人类精神最本质的原型。你只要回到那里就OK了,你就什么都说明白了。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会纠缠于枝叶之间,而是要回到树的主干,回到最本始的原型上去。
云:我非常喜欢他那个青岛作品。
邓:我青岛那个作品也是中间一个大方块,四角上套了四个小方块,露天。在这里面也是采用了中国园林的做法,它是有门的,像迷宫一样。进去以后,自动关上,你就置身于这样一个小空间里。进来以后,可以穿透这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又从大到小。在照片中,我拍的只是那个作品的周围,但是里面没拍。因为冬天没法拍,拍不好。
云:我没具体去,当然我听邓老师一说,实际上那个设计得比这个还复杂。
邓:就像你说的设计一个心理的迷宫。
云:我当时看到那个作品,我当时想的是邓国源玩儿大了,为什么?我在这个事情上,跟你们俩持相反的观点,我认为他现在的作品做得语义过多。我会认为比较牛的搞装置的是用的语法极其简单,用词极其少,由于他用的是源语言,所以他的意义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朱:这就是我讲的回到原型。因为我们在讲的都是神话,你这个乌托邦也是神话。你讲“诺亚花园”,那个诺亚本身就是神话人物,神话就必须要回到原型。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神话呢?全世界有那么多小说、电影、绘画和雕塑,但只有抓住原型,你的作品才会具备力量,因为你说出了事物的本性。
云:其实像蔡国强就抓了火药,就可以用这个无穷地说话。
朱:他那个天梯也是原型,在全球的上古神话里,天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型。天梯叙事试图表明,人和神原来是通过这个梯子来流畅地沟通的,但是后来人类这边出现了问题,所以它被天神切断了,从此人和神就发生分离。巴比伦的通天塔也是天梯的一种转喻。天梯摧毁之后,人和上帝就没有办法沟通,那就需要一个中介,于是就出现了祭司和巫师阶层,他们负责在人和神之间翻译和传递信息。这是蔡国强能干的地方,他抓住了那个神话的基本原型。
云:还有这么一个人也这么牛,徐冰直接用印刷术的语法。
朱:是的,他找到了文字的原型。实际上大艺术家跟小艺术家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原型,用它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这是神话以外的另一类原型——文明(技术)的原型。其实人类史所提供的基本原型是非常有限的。你可以看到,汉字、天梯、花园,这些大制作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推动了原型的再现。我认为,从整个装置艺术的趋势来看,判断艺术家的高低,就是看你能不能发现原型,同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无论东方和西方,它的语法都是共同的。原型是傲慢的,它根本不管你什么东方西方,它是全人类的根语言,是生命树本身。你抓住了原型,不仅能获得表述的深度,而且还能获得人类的语法,打通走向世界的道路,不需要转译和阐释,直击所有观众的灵魂。事情就这么简单。
(本文在发表时略有删节。)
云 浩:学者 艺术批评家
朱大可:学者 艺术批评家
邓国源:天津美术学院院长 教授
Illusion, Maze, and Dream: With Regard to“In the Garden”by Deng Guoyuan
Yun Hao, Zhu Dake and Deng Guo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