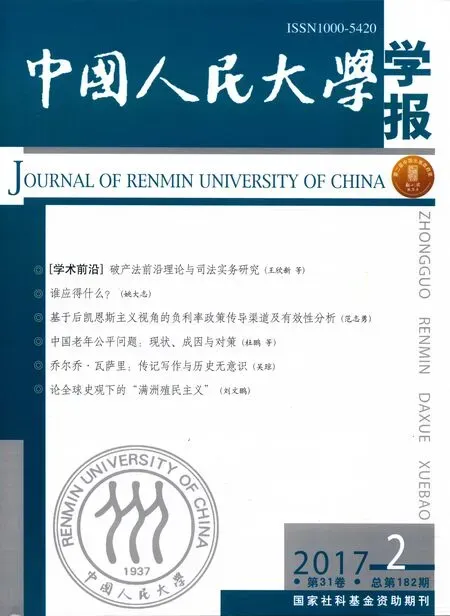仪式、角色表演与乡村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皖东T村妇女“做会”现象的深描
陆益龙
仪式、角色表演与乡村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皖东T村妇女“做会”现象的深描
陆益龙
乡村女性的角色与主体性问题是乡村社会研究和性别关系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性别不平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更多关注女性的不平等问题,并常常把性别关系的各种问题指向社会制度和男权社会的结构。然而,这一范式遮蔽或忽视了诸如女性当家等性别关系的多样现实形态。皖东T村的经验就呈现出了父系从夫居婚姻家庭制度依然维续与妇女普遍当家做主等悖论现象,从实践建构论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可领会到现实生活中乡村女性的行动实践对性别关系价值与文化的建构意义。解析T村妇女“做会”现象的“深层密码”,会发现这一仪式不仅仅是妇女自组织的普通集体活动,而且为乡村女性建构角色和主体性文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和舞台。在仪式过程中,乡村女性主动建构起公共的空间与舞台,并通过集体表演和社会建构实践,建构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隐性权力”和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价值与文化象征体系。
仪式;角色表演;乡村女性;主体性; 建构
民间俗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乡村社会特别是在当下后乡土社会里[1],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她们在社会角色扮演中建构着怎样的性别主体性呢?所谓性别主体性,是指人们对性别分工和不同性别社会地位的主体意识、认同观念、态度和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对皖东T村妇女“做会”仪式活动及其象征意义的解读,揭示乡村女性所建构的主体性及其特征,以及这种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与机制。
一、乡村生活中的女性角色与主体性问题
在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领域里,女性主义与不平等研究范式占有重要位置。女性主义与不平等范式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女性的权益、地位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等。关于女性权益与性别关系问题,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对父权制的批判,认为父权制从制度和结构上决定和型塑了女性权益受损、男女不平等以及紧张的性别关系。在这个制度下,不仅女性是受害者和反抗者,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害。给女性赋权,争取性别平等,会有助于消解性别差异,促进性别关系的沟通与和谐。[2]女性主义社会学也具有“问题”取向的特点,即把现实社会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差异、性别关系视为“有问题的”,进而去加以关注、研究和批判。[3]
对性别关系的不平等现象的解释,有一种结构再生产理论,即认为男女不平等问题是通过一种不平等结构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例如,佟新在针对妇女家庭暴力的个案研究中,认为“‘打老婆’现象得以存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已深入到每个男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中”。“对妇女暴力的各种形式蕴含着性别关系不平等的二重结构”,正是这种男强女弱的二重结构,生产和再生产着性别不平等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不断地“开展女性赋权运动”。[4]
然而,笼统地批判父权制,抽象地用父权制框架去分析和解释妇女问题及性别不平等问题,不仅遮蔽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关系的具象事实,而且对全面地、具体地认识性别关系问题以及建设性地应对这些问题也有局限性。金一虹在《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一书中,选择从具体生活的视角和社会变迁的维度对父权制与性别关系进行了探讨,呈现了父权制在劳动生活、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渗透和具体形态,性别分工和性别差异的组织基础,以及关于性别关系的观念意识,并结合江南乡村的具体经验,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讨论了父权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易性、稳定性和复杂性。[5]父权制是否依然支配着如今的性别关系、父权是否已经式微,无论何种笼统的判断,其实都难以真切地反映性别关系的现实问题,而且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应对助益不大。
随着妇女问题与性别研究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学的视野,乡村女性的生活状况备受关注。对乡村女性的考察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女性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权力关系、生活意义、主体性的建构与实践等方面。对乡村女性的社会学研究,更多的是以经验研究为主,在这个意义上说推进了女性与性别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就是从泛泛的女性主义批判范式转向关注生活与实践的现实主义范式。例如,李银河在对后村妇女的经验研究中,重点考察了乡村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演绎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种角色,分析了乡村女性在上学、就业、婚嫁、抚育后代、家务劳动、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方面与男性的权力差异,并从家庭结构与性别权力关系的角度,总结出乡村社会的男女两性依然存在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正随着社会变迁而逐渐缩小。[6]由此可见,从经验研究角度来揭示性别不平等问题,相对于女性主义的父权制分析框架,让人更容易把握性别关系的现实形态。
李霞在对乡村女性从娘家到婆家生活转换过程的经验研究中,进一步突破了女性主义的父权制框架的束缚,考察和探讨了在父权和夫权占支配地位的乡村社会中为何有那么多女性当家的现实。她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指向一个长期被遮蔽的事实:在一个被界定为父系父权的亲属制度下,女性在家庭生活和亲属关系互动中发挥着核心的影响力”。[7](P226)这一研究借鉴了伍尔芙(M.Wolf)在对台湾妇女与分家现象研究中提出的“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的解释视角[8](P164),认为农村妇女要建立独立的生活空间的愿望是构成大家庭分裂的重要推动力。针对乡村家庭亲属关系网络呈现出的“女性偏重”现象,李霞从“生活家庭”的角度,解释了乡村女性通过隐蔽的或“后台的”情感权力,影响着家庭的亲属关系交往,更多地体现出女主人的情感与目标偏向,即偏重于娘家方而疏离于婆家方。乡村家庭的亲属关系的“女性偏重”现象虽然可能不是普遍的,但至少也是一种社会现实,对这种现实的揭示,表明了乡村性别关系存在着结构与实践的背离。也就是说,尽管女性在社会性别等级结构中处于次级地位,但在家庭和社区生活实践中却有着主导的影响力。
然而,在关于乡村女性社会归属与主体性问题上,杨华根据对湖南水村妇女的经验考察,突出了乡村女性整个人生阶段对父权体系的从属,即女性社会归属感遵从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亡从子”的脉络。乡村女性对生命历程的主体性体验主要是在栖居、立足、安身、立命四个层面,农村妇女对生命终极意义的体验就是为父系家族和村落的“传宗接代”。[9]这一解释显然过于强调乡村女性在父权制体系中的从属性和依附性,而忽视或遮蔽了乡村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一面。虽然在乡村父系家族和从夫居的制度体系中,女性要生活于父权占主导的社会生活空间中,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女性主体性的消失,因为在这个生活空间里,女性也可以演绎“女主角”的角色。
如何衡量乡村女性的地位和主体性的程度呢?有研究提出了自我行为规则的标准,认为西方女权主义通常将妇女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受教育程度、财产权等作为妇女地位的考察指标,这其实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仍难以理解妇女地位、主体性程度的本质意义。从女性行为规则自我界定的角度出发,才是真正把握和理解女性地位与主体性的最高境界。[10]诚然,规则的制定权确实能集中体现出社会系统中的权力与地位关系,但是,社会规则的形成问题实际上属于制度与制度变迁的范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宏观结构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什么层次的规则、什么内容的规则、由谁制定的规则、究竟是男性制定的还是女性制定的、是个人决定的还是集体决定的,这些问题其实都难以给出确定的回答,因为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形成本来就是变动的、建构的过程。
主体性包含行动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行动,自我意识是指个人对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与观念,自我行动则是基于自我意识而做出的行动。在对乡村女性的经验研究中,还有一种是从“女性自我”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解释的,提出“女性自我是情感主体的自我”。乡村女性情感主体的自我在现实经验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女性对相关他人命运的关心和对他人无功利的或弱功利的付出,为社会团结与整合做出自己的贡献。二是乡村女性也会用自己感性的、率性的行为去突破既有的习俗与规则。[11]情感主体自我的观点突出了乡村女性主要依靠感性方式来建构主体性,由此可能忽视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女性,她们在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行动中,其实是富有理性特征的。例如,一项关于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经验研究就提出了妇女理性行动的观念,认为农村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其实是有明确的主观意义的,乡村女性赋予公共参与行动的主观意义所具有的理性色彩, 并不一定是韦伯式的制度和规则理性,亦非那种经过投入产出精密计算的经济理性,而更可能是与社区政治和文化环境相联系、受到当地生产方式制约的生存理性。[12]或者说,就是源自于生存与生活的那种纯朴理性。无论是受哪种理性的支配和驱使,乡村女性的社会行动都是充满理性的,感性的色彩并非她们的主色调。
综合相关性别关系、乡村女性角色和主体性的研究来看,女性主义的视角和父权制的分析框架虽然将不平等和女性权益问题纳入中心范畴之内,显现出人文的、现实的情怀和批判的精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研究范式的价值倾向。或许正是因为带有价值倾向的分析框架,常常会遮蔽一些客观存在的现实,由此可能导致对性别关系现实的不全面认识甚至误解。经验主义的研究策略实现了从批判向现实生活的转向,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加鲜活的性别角色和性别主体性。但是,在经验现实的表象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层意义、什么性质的关系以及何种形成机理,这些都需要通过经验研究的积累,不断丰富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和阐释。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其实就是要通过对一个村落妇女“做会”仪式的深描,来呈现并诠释现实生活中乡村妇女究竟是怎样表演着社会角色、怎样建构其主体性的。
二、妇女自组织的“做会”仪式活动
皖东T村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一个较为富庶的自然村落,村民的生计模式属于农业+兼业模式,目前有70%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或自营小规模工商业。在这里,有一种现象与妇女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那就是每年在农历正月初九或相近的日子,村里的妇女都要自行组织起“做会”的仪式活动。笔者之所以关注和考察T村妇女的“做会”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一现象有着一些特殊之处:一是这一仪式活动是由村内妇女自组织的活动;二是这一活动与民间信仰相连;三是这一现象与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有着某种特殊关系。
T村妇女“做会”通常是在正月初九,选择这个日子有一定的讲究,一是这个时间段妇女基本忙完了自家的“接人”请客礼节。在T村有一种礼俗,就是各家都要选择一天专门邀请给自己家拜年的人来吃饭,当地叫“接人”,实际上就是请客吃饭。二是过了正月十五(当地称正月十五为“小年”),很多人可能就要外出打工了。所以,初九是个相对合适的时间。
T村妇女“做会”仪式活动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敬香拜神,参与仪式活动的妇女要到村内各神庙烧香,并要到会堂给观音神龛上香。二是聚会娱乐,参会妇女在会堂组织打麻将等娱乐活动。三是聚餐狂欢,参会妇女要在酒席上聚餐交流,有些妇女还会在“做会”酒席上拼酒狂欢。
如何看待T村妇女自组织的“做会”仪式活动呢?妇女“做会”现象究竟是村落传统的延续还是传统的复兴,或是传统的新构呢?
对于这个问题,T村一位老年妇女做出这样的解释:
妇女“做会”其实过去村里也有,记得那时妇女在正月要办观音娘娘庙会,后来破“破四旧”不给办,渐渐就没了,这些年好像又兴起来了,四周的村子也都有。(T村妇女Y)
在T村妇女关于 “做会”的主位解释基础上,结合客位观察分析,对“做会”这一仪式活动可以这样去加以理解:第一,“做会”仪式活动并非传统的完全延续,过去的庙会传统已因历史事件而中断且不复存在。第二,新的小传统是随着新时期的社会需要而兴起的。第三,新的小传统的兴起与社会记忆和周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T村妇女组织的“做会”活动,虽与文化传统有某些相似和相关之处,但这种相似与相关可能透露出这一仪式的社会需求和文化基础的共通性,亦即庙会仪式之于T村妇女而言有着相通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新的小传统的出现并不宜简单视为传统的复原和延续。
在一般观念里,乡村社会是相对传统的父权制社会,男人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一些重要事项诸如仪式活动皆由男人组织和操办。那么,T村妇女何以能自组织起“做会”仪式呢?妇女运用什么样的资源、依靠什么样的社会支持自组织起仪式活动呢?
妇女们“做会”主要是拜送子观音,希望能生儿子。计划生育管得紧的时候,刚结婚的媳妇都希望头胎就能生个儿子,这样也就万事大吉了。如果头胎生女孩,就更想要生儿子啦。村里哪家最想要生儿子就希望大家到她们家“做会”。每家都会想生个儿子的,所以每年总有人家要主动办会。(T村中年妇女W)
T村妇女将“做会”活动与生男偏重文化以及生子需求联系起来[13],生育目标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共同愿望,只不过这个目标是由妇女最终来执行的,所以,妇女能自组织起“做会”仪式,实际上依靠的是夫权家庭的支持。
除了村落文化和夫权家庭的支持之外,T村妇女实际上拥有着独立的资源和家庭治理权。T村一位年轻妇女坦言:
我们村没有哪个女人不打麻将的,她们个个腰里都有私房钱,男人们搞不清她们有多少私房钱,反正女人打麻将不需要找男人要,而有的男的还需要老婆批准麻将资金。你看看,我们村哪家不是女人管钱,就是不识字的女人也会管钱的。(T村年轻妇女M)
T村妇女的私房钱就是她们的独立资源,可以相对独立地支配和使用。这一独立资源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结婚时从娘家获得的,二是从家庭收入中公开分得的礼尚往来与娱乐资金,三是从其他非公开收入渠道积蓄的收入。T村妇女能够拥有和使用自己的独立资源,并非倚仗她们在家庭中掌管财权。在T村,家庭财权大多由妇女掌管,妇女当家并不是为了自我利益,更多的是为家庭利益。因为赌钱是T村的一种习俗、一种文化,一般在请客吃饭和礼尚往来的“行礼”场合,主人都要尽量给客人安排牌局赌钱,这样才能显示对客人的尊重和客气,如果没有这种安排就是不合礼。所以,村里人一方面要参与到赌钱之中,同时又要反抗赌钱。妇女掌管家庭财权,一个重要的理由和功用就是妇女要防止丈夫不顾家地胡乱赌博。T村妇女当家现象不仅反映出女性在父权家庭中的独立性,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一定的治理家庭和组织公共活动的能力。
T村妇女的“做会”仪式活动与民间信仰相关,同时也涉及妇女的生育需求。特纳(V.Turner)曾将非洲恩登布人与生育相关的仪式视为“女人的仪式”,这种仪式从象征意义上看,就是结构与反结构的过程,因为在仪式中,“阈限”(liminality)与“交融”(communitas)两种模式的行为代表着从结构经过反结构再回归结构的承接过程。“对于个体和群体来说,社会生活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其中涉及高位与低位、交融与结构、同质与异质、平等与不平等的承接过程。”[14](P97)
然而,就T村妇女自组织的“做会”仪式而言,虽然也能从中领会到个体与家庭、生女与生男、平常与神圣的二元结构,但是“做会”仪式的兴起似乎并非是由结构所决定的,因为这一仪式传统已经中断了很长时间,在没有这一仪式活动的日子里,村民们的社会生活照常运行,农民的生男偏重观念依然延续,拜神的活动则以其他方式进行。由此看来,仪式活动之于社会生活,虽有结构的、象征的意义,但并非结构所必需的,亦非结构所决定的。
一位T村妇女还提到:“后港(T村附近的一个镇)的妇女,在北京还经常‘做会’呢。”这些妇女一般跟随去北京打工的丈夫,在北京居住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在工地上做些活儿,有些人则是纯粹陪伴,同乡妇女经常会一起打麻将,由此相互认识和熟悉起来,逐渐地也根据家乡习俗在暂住地组织起“做会”活动。这一脱离村落情境的仪式活动,意味着仪式的意义和功能的变迁,而对于仪式活动的产生,如果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去理解,那就可能忽略掉现实生活中妇女行动的能动性以及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如果说妇女“做会”是为了满足认同与社会团结的需要,但并不是所有需要都会驱动一种具体的行动实践,那么,仪式活动的发起就不一定是由需要驱动的,而可能是与行动实践密切相关的。正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T村妇女才组织起“做会”仪式。
因此,要对T村妇女“做会”现象有更加全面的理解,还需要增加实践建构的视角。“做会”的仪式过程及其意义与乡村妇女在相应情境中的社会建构实践是分不开的,每个行动者其实都参与到社会建构的实践之中,使得个体的能动性对社会现实的构成显现出相应的意义。与此同时,社会现实的偶然性以及建构的意义也得以呈现出来,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跳出结构—功能框架,从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去把握和理解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意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同样,从仪式实践过程中,也能看到乡村女性建构起何种性别关系以及是如何建构的。
三、仪式、表演与女性角色的建构
从实践建构的视角看,T村妇女的“做会”仪式活动犹如一场社会戏剧,参与仪式过程的妇女在村落文化的舞台上,通过自己的表演行动,演绎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并共同建构起村落共同体的象征意义系统。
社会戏剧的演绎过程,似乎并不受固定剧本结构的限制,表演行为也没有严格意义的导演在指引,每个表演者主要是在随心所欲地即兴表演,这个戏剧就是由这些非正式的即兴表演构成的。在T村妇女的“做会”过程中,虽有一个共同的崇拜对象——观音娘娘神像,但是整个仪式活动远非仅仅是拜神,仪式活动内容的丰富性、变动性及非正式性,反映出社会戏剧的剧本结构的动态性特征。此外,仪式参与者也不是确定的,至于哪些人能参会哪些人不能参会、谁会参加谁不参加,都没有相应的规则,而是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愿望和能动性。这说明仪式戏剧并无固定剧本限定角色结构。“做会”活动虽每年都有堂主或组织者,但承办“做会”活动的堂主在整个仪式活动中对参加者的行动并不会起到“导演”作用,活动的组织者和承办者主要按照大体的程序去完成各项工作,而对仪式行为并无严格要求。所以,“做会”仪式这一社会戏剧更具参与性、实践性的特征,而受结构的制约相对较小,每个参与仪式的妇女用她们的“即兴表演”建构了她们的角色并演绎了这场戏剧。
如果说T村妇女“做会”仪式是由具体情境下一个个表演实践构成的社会戏剧,那么,T村妇女在仪式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是如何演绎着这些社会角色呢?
近些年,T村参加“做会”活动的妇女主要为中青年妇女,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在对2016年T村“做会”会堂的考察中,笔者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在会堂打麻将,于是好奇地问道:“这些不都是年轻的小女孩,怎么也来‘做会’呢?”一位中年妇女回答道:“她们可不是小女孩了,都是我们村的新媳妇,是年轻的女主人了啦。”(T村中年妇女B)
从T村中年妇女B的回答中,可以解读出在“做会”仪式过程中,村里年轻妇女扮演着新媳妇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要参加仪式,实际上是要通过仪式表演行动来建构自己家庭或新家庭的新主人角色。
“做会”仪式为乡村年轻女性的角色转换与角色表演提供了舞台和机会,她们在结婚之后,需要从姑娘转换为媳妇,从父母家庭的一般成员转换为自己生活家庭的女主人,从为父母家庭效力转变为在新家庭当家做主。这个角色转换对于妇女的父母家庭或娘家来说可能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15],而对于年轻妇女而言,其实是她们家庭地位提升的机会和过程。要真正实现角色与地位的转换,就需要通过她们的表演行动,在村落文化中建构起相对应的意义系统。
在仪式过程中,年轻妇女家庭女主人角色的建构机制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同村妇女群体的集体表演与支持机制,二是生活家庭的认可与支持机制。在T村,妇女通过“做会”活动,集体表演着自己在生活家庭或婆家中的主角,并通过集体表演实践建构起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及象征意义系统。妇女当家在T村的普遍存在,是与妇女群体的社会建构实践相一致的。妇女角色与家庭地位的建构过程,包含了对妇女当家价值的建构、象征意义的强化和社会支持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在“做会”仪式活动中都得以完成。一方面,在仪式过程中,参会妇女通过交流、讨论和集体表演,在妇女群体内逐渐形成了一种价值共识和认同;另一方面,仪式由于是与拜神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从而赋予了共同价值的神圣色彩,使得这一价值得到象征的强化,此外,通过集体仪式活动建构起来的价值,表明得到共同的社会支持。
由于年轻妇女参加“做会”仪式代表的是婆家的新生代家庭,而不仅仅是她们个人,所以,年轻妇女在仪式过程中的表演与社会建构实际上得到她们生活家庭的认可与支持,尤其是她们公公婆婆的支持。
在“做会”仪式上,T村妇女实际上还扮演着父系家庭代际传接者的角色。“做会”的仪式功能主要表现为生育崇拜,参加仪式的妇女无论是已生育的还是未生育的,都抱有生男孩的希望,也就是要为父系的、新的家庭“传宗接代”。目前,T村的生育文化和家族观念并非以大家族维续为主,大家族的意义主要是在重要事件上的团结和互助义务,“传宗接代”的观念已缩小至每个核心家庭,即每个从父系大家庭独立出来的新家庭,都面临着生育男孩和“传宗接代”的任务。很显然,这个任务离不开妇女们的努力。所以,参加“做会”的妇女特别是新婚妇女,她们会在仪式上扮演为父系家庭或生活家庭传宗接代的传接人角色。首先,每位在仪式上露面的妇女都代表着一个家庭,象征着家庭的存在或代际更新,并以此来演绎家族和家庭的传承与延续。其次,参加仪式的妇女也在为生活家庭和家族“传宗接代”而作出努力,参会就意味着她们主动接受家庭代际传接者的角色和任务。此外,仪式活动包含了妇女尤其是未生育儿子的妇女追求生男孩的实践,她们在村里大庙中烧香许愿,以及在“做会”会堂的拜神许愿行为,既是一种信仰的实践行动,同时也是在村落文化舞台上演绎着家庭的代际传接与更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仪式的建构力量对乡村家族与家庭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弗里德曼为何关注和研究中国亲属关系与婚姻家庭中的仪式问题。[16]
T村妇女在“做会”仪式中所表演的第三种角色就是“村里人”角色。T村妇女所说的“村里人”,实际上就是村落共同体的成员。年轻的新媳妇一般都会参加“做会”,正如一位新婚媳妇说:
嫁到T村就是T村人了,就要和T村人一样,和她们一起活动,免得人家以后不理你。(T村新婚妇女C)
从T村妇女的表述中可以领会到,“做会”不只有象征意义,而且也在建构着社会文化认同以及村落共同体。参会妇女们不仅为了各自生活家庭的代际传接与更新,而且也在通过仪式实践,为自己建构起“村里人”的角色,同时又在共同建构村落认同。
通过“做会”仪式来表演村落共同体成员角色,在T村还有两种特别的情况:一是本村外嫁妇女的参会,二是外迁妇女的参会。
吴女士曾是T村吴家的姑娘,后嫁到T村附近的城市,目前一家人在T村所在的镇开了一个较大的超市。由于距离较近,她与娘家的联系比较多。近年来,尽管她已步入中年,儿子都已成婚,但她每年仍积极主动参加T村的“做会”仪式。
张女士嫁给了T村王家一男子,曾在T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迁到T村所在的镇上居住生活,经营着农资物品的小店面。目前,她家在T村的房子虽已转让给别人,但T村妇女“做会”时,她基本都回村参加仪式。
两种不同的参会实践,一方面反映了T村“做会”仪式的结构弹性和非正式性,作为一种自组织的仪式活动,对组织结构和会员资格并无刚性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T村“做会”仪式的表演性。所谓表演性,就是用行动来表达某种价值和社会认同。在上面两个个案中,吴女士和张女士参加“做会”仪式,主要的目的并不在于生男追求和集体娱乐,而是要达到共同体的认同意义。她们在仪式活动现场的出现,是把这个场合作为一种舞台,自己在上面表演着T村人的角色,期望其他共同体成员仍将她们认同为T村妇女。
仪式活动是人们建构起来的,仪式活动又建构着各种社会角色。T村妇女自组织起“做会”活动,“做会”为她们提供了表演机会,她们在表演实践中建构着价值和角色。妇女们通过仪式建构起来的价值与社会角色,具有个体性、情境性和动态性,而结构与功能的约束显得弱化。有外嫁妇女和外迁妇女参会的,也有其他人不参加的;在T村普遍存在妇女当家和生男追求现象,而在其他乡村地区可能并不存在,这就表明了结构与功能对社会行动的约束和支配是有限度的,社会建构之于社会现实也有着重要意义。
仪式行为不同于常规行动,是有意识的社会表演行为,按照一定的价值和信念演绎着一定的角色。仪式行为与常规行动的社会影响也不同,仪式通过角色表演将与角色对应的价值和理念建构为共同体的文化象征和共同规范。所以,仪式活动通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建构机制。皖东T村妇女就运用了仪式建构机制构建起了她们性别关系的现实。
四、仪式、隐性权力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关于乡村女性的家庭地位与主体性问题,李霞在华北农村经验中,看到了乡村女性的后台权力。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包括来自于家庭日常操持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权力”和源于情感付出—回报伦理的“后台”权力,女性的“后台”权力主要是女性通过操持家事和经营亲属关系方面所构成的影响力,不具有正式的、仪式性的形式。[17](P233)
然而,在皖东T村的经验中,似乎可以看到乡村女性在仪式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权力。乡村女性这种仪式性权力的获得与信仰和宗教活动有着一定的关联,且一般是在特定的仪式中逐步被认同和强化的。[18]T村妇女在“做会”仪式过程中,不仅仅集体扮演和建构着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也在集体建构着女性在生活家庭中的“隐性权力”。之所以说是“隐性权力”,是指既非来自于父系亲属制度赋予的权力,亦非来自于女性本身力量的权力,而是通过村落社会实践建构起来的文化权力,也就是礼俗文化赋予女性的权力。“做会”仪式就为她们建构在家庭和村落社会的独立地位与文化权力提供了舞台。
在“做会”仪式过程中,与拜神活动同样重要的活动就是打麻将娱乐,T村人称之为“赌钱”。对妇女“赌钱”现象的理解,不宜简单地理解为赌博活动。妇女“赌钱”虽有一些负面意义,但也是妇女在家庭中“隐性权力”的重要建构机制之一。因为妇女在“做会”中一般都要参与“赌钱”,而“赌钱”就要保证身上有钱。那么妇女身上的钱从何而来呢?如果每次参与这种仪式性活动的钱都要从丈夫或丈夫的父母那里讨要,那么妇女可能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参加这类仪式活动。妇女能够“做会”且参与“赌钱”娱乐活动,表明了她们有独立的财权,而且向人们发出她们独立财权的象征符号。
在T村,妇女的“隐性权力”在分家新形态中也得以显现出来。关于分家问题,伍尔芙突出了已婚妇女对独立的要求在分家中的关键影响,其中“分灶”现象就是典型标志。[19](P167)然而,孔迈隆(M.Cohen)则认为,妇女的诉求和妯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复合家庭的分裂中并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分家问题上还是男人具有决定权。[20](P198)那么,从T村的经验看,“分灶”现象并不普遍,更不支持妇女是分家的“替罪羊”的观点,这似乎与费孝通关于中国的家的伸缩性观点较为吻合。[21](P39)一方面,T村的分家实际上从新媳妇进家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所以,“分家”现象在T村是比较普遍的、自然的家庭代际更新,无论是父母与一个已婚子女的家庭,还是有几个兄弟的联合家庭,新一代的结婚就是“成家”,“成家”也就是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家,那也就意味着小家庭已经从大家庭分离出来。这种事实上的分家集中表现为已婚妇女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权,这一权力既可能与父母的经济权相独立,也可能与其他兄弟家庭相独立。另外,由于现在年轻人长期外出营生,相聚时间较短,所以回家后基本上还是在父母家一起吃喝,由此形成“分家不分灶”的现象。
乡村妇女的“隐性权力”显然并不是父权从夫居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乡村社会经济结构所赋予的,既然不是由制度和结构决定的,那么就可能在乡村文化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看到这种权力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T村已婚妇女所拥有的独立权力,实际上也隐蔽在文化、婚姻过程以及娘家所支持的力量之中,目前T村周围已渐渐形成这样的婚俗文化,在说亲、定亲和结婚过程中,娘家与婆家一般会以媒人为“公证方”达成一种默契,也可以说是一种协议,那就是“女儿嫁过去后不承担婆家一分钱的债务”。而且娘家一般也会将在订婚时向男方家索要的彩礼款的大部分,在结婚仪式上以“压箱钱”的嫁妆形式交由女儿支配。这样的协议和习俗文化实际上在经济上将新的小家庭与大家庭分开,无论丈夫是否赞同,无论是否正式,妇女其实都可以在家庭生活中享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
“做会”仪式对乡村妇女“隐性权力”的建构意义还表现在妇女作为家庭代表的身份建构上。妇女“做会”实际上是通过集体实践建构起一些文化象征,其中既包括妇女在生活家庭更替和延续即“传宗接代”中的必要角色,同时也包括妇女具有代表生活家庭的独立身份。既然是家庭的代表,那么就意味着拥有了在交往互动场合代表自己家庭的权力。随着“做会”活动的仪式化和神圣化,这一仪式也就成为一种习俗、一种文化。正是在乡村文化建构过程中,妇女获得了在自己生活家庭以及共同体中的“隐性权力”,因为仪式和习俗给妇女带来了相应的象征资源,同时为这些象征资源和权力发挥作用建构了相应的社会环境。妇女“隐性权力”的建构,实际上并未动摇父权亲属制度和男性的显性权力,其影响更多的是在家庭治理策略上,让妇女享有独立当家的权力。对乡村女性所具有的“隐性权力”的现实,简单用男女平等与不平等理论来解释显得过于简单,需要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来理解乡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多样性形态。
此外,“做会”的狂欢活动成为T村妇女建构她们自我独立的主体性的一种方式。“上席”是“做会”中的一项相对正式的仪式过程,所有参加“做会”的妇女会按照正式酒席规则就座、饮酒和狂欢。通常情况下,那些酒量较大的妇女会被安排到同一桌,她们每年在“做会”会堂上,放开豪饮,斗酒狂欢。一般情况下,总有几位妇女会喝醉,最后由丈夫背回家伺候。所以,斗酒狂欢,喝醉让丈夫伺候已成为T村妇女“做会”的一道“风景线”。那么,一些“做会”的妇女为何要醉酒狂欢呢?她们是怎样看待丈夫及其家人的感受呢?一位常在“做会”酒席上斗酒的妇女给出这样的解释:
一年到头就这么一次,大家在一起高兴,喝多了也没什么,又不是天天喝,就是因为“做会”大家才痛快地喝一次。……喝多了他(丈夫)当然要把我弄回家,“做会”喝醉了很正常,他也不会有什么埋怨的,又不是馋酒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把酒喝多了。(T村妇女J)
从T村妇女对仪式中狂欢行为的主位解释来看,妇女斗酒狂欢并非日常行为,而是与仪式或公共活动密切相关。因此,T村妇女在仪式上的狂欢,似乎不同于崔应令在土家族村落看到的妇女有意识地用自己的 “率性行为”来突破乡村既有规则和习俗[22],她们并不想挑战或替代男性在酒席等正式场合的既有权力和地位,而只是在仪式场合,将独立的自我宣泄出来、表演出来。T村妇女通过仪式狂欢表达出的自我,既呈现出自主独立性的特征,也将自我与家庭统合起来。妇女“做会”既是为了父权家庭,也是为了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家,亦即“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在这里,妇女的主体意识并无“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亡从子”[23]的迹象,她们那种经营好自己的家庭、过好自己的日子的观念更为突出。目前,在T村一带,父母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孩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和习俗,乡村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现象已不存在。尽管父母还要参与和负责女孩的婚事,但女孩对婚嫁对象一般都有自己最终的决定权。已婚妇女将生子视为自己的责任或自己的事,同时也把辅助子女成家当作自己人生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T村妇女是在一系列的文化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建构起她们的女性主体性的,仪式中的狂欢则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项内容,她们通过与仪式相关联的行动,展示并强化那种非从属性而有责任心的主体意识。
在乡村社会,上席、拼酒、狂欢等行为通常是男性在“前台”的事,也就是“男主外”的面子上的事。然而,T村妇女在属于她们的仪式上的醉酒狂欢,并非被动地应酬,亦非压制后的爆发,而是一种主动的演绎,主动地利用公共的、仪式的和正式的平台,呈现着独立又代表家庭的自我。关于乡村女性的权力和主体意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她们在情感方面的优势,认为女性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交往与互动来获得非正式的、“后台”的权力。T村经验则显示出,乡村女性也会利用各种正式场合特别是仪式场合,主动地演绎和建构她们对自我独立和家庭责任的价值与文化象征系统。
“做会”仪式表面上看是村落中妇女的一次集体活动,然而事实上却有着建构文化象征符号的意义,是乡村妇女参与文化建构的实践,而且通过仪式的公共性和神圣性建构起一种地方性文化价值和观念系统。正是在文化建构实践和建构起来的价值系统中,乡村女性逐渐建构起“隐性权力”,由此显示出她们具有自我独立的主体性,而不是被动地从属于父母的家庭和丈夫的家庭。她们在未出嫁前努力为父母家庭做贡献,并在乡村婚姻市场处于女方市场的背景下,建构起了自己婚姻自己做主的价值与习俗。在结婚之后,乡村妇女主动地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并在丈夫家庭的代际更替中积极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更具有伍尔芙所说的“子宫家庭”的特征[24](P167),其意义不仅仅像阎云翔提出的“网络家庭”所具有的功能[25],而且还具有价值与文化象征建构的意义。所以,从T村的经验来看,乡村女性在家庭中的“隐性权力”、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建立,似乎并非是通过反抗、挑战和突破父系亲属制度中的男性权力和规则而达到的,恰恰相反,她们是在家庭生活和家庭经营实践中,通过主体性的努力和文化建构性的策略,将维续父系亲属制度和女性主体性建构巧妙地统合起来。
五、小结和讨论
在皖东T村家庭与性别关系的现实经验中,出现了诸多与乡村女性角色和主体性相关的悖论现象。例如,尽管父系从夫居的婚姻家庭制度依然维续着,但却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女性当家的现象;尽管择偶的家长制依然在乡村盛行,但却出现了女儿做主的现象;尽管生男偏重的生育崇拜还在流行,但却强化了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尽管分家是普遍现象,但却出现了一些家庭“分家不分灶”的现象;尽管乡村女性的权力和影响力在提升,但似乎并未消解父权亲属制度和男性的权力。这些悖论现象可以说是以往性别不平等理论、女权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所遮蔽或忽视的社会事实,因为这些理论常常把所有性别不平等问题统统指向了父权制度和男权社会的结构。如果说性别关系问题都是由男权支配的制度和结构所决定或再生产出来的,那么为何在实践中还会出现多种多样的性别关系的现实形态呢?从实践建构论的视角,不仅可以发现这些悖论现象,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和解释乡村社会中女性角色和主体性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因为乡村女性角色和地位是通过不同的实践行动建构起来的。皖东T村妇女正是通过她们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家庭角色和主体性。她们无论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都用自己的实践行动建构着独立的自我而非被动地从属,与此同时,她们巧妙地将主体性建构与家庭经营策略有机地统一起来。
仪式具有公共性、象征性和神圣性的特征。皖东T村妇女的“做会”仪式是与民间生育信仰相关联的文化活动,为乡村女性的社会建构实践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和舞台。就实践建构的机制而言,一般不外乎两种社会场域,一是日常生活的场域,二是神圣象征的场域。仪式就属于实践建构的神圣象征场域,在这里,人们通过仪式实践建构起具有神圣性、象征意义的价值和规则系统。T村妇女在“做会”仪式过程中,运用角色表演和自我行动建构起她们在家庭中的不同角色、“隐性权力”和独立自主的主体性。当然,这里突出乡村妇女运用仪式实践建构文化象征的机制,并不否认乡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建构作用。在妇女当家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女性所拥有的权力,这种“隐性权力”的获得可能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操持家务以及情感交流实践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究竟是何种家务操持和情感互动策略帮助乡村妇女建构起“隐性权力”,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经验考察。
自行组织仪式活动,并在仪式过程中的角色表演和建构实践,表明乡村女性的活动空间并非局限于家庭之内和“后台”的情感互动,她们可以主动地建构公共的空间与舞台,并通过集体表演和建构实践,在乡村社会与文化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力量并没有依赖于也不从属于父系的亲属集团。相对于男性基于显性力量而形成的权力,乡村女性的“隐性权力”则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行动和家庭经营策略,建构起相应的价值与文化象征体系,她们正是从这种社会与文化环境中获得了力量的支持。
深描是建构论和解释学的一种理论解释,主要用以破解社会行动与文化现象的“深层密码”,解析其深层的象征意义。T村妇女的“做会”现象,表面看就是乡村妇女自己组织的一种集体活动。然而作为一种仪式过程,“做会”则有着深邃的文化建构意义。仪式过程中女性的实践行动,隐含着丰富的文化象征符号意义。妇女通过这些象征符号的建构,向村落共同体成员表达和传播了家庭与性别关系的观念、价值和规则,由此建构起女性的角色期望和社会地位。
对皖东T村家庭生活与性别关系的现实形态,也可以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维度去加以解释,可以把当下乡村女性当家做主和不断增强的主体意识等社会现实,看作是乡土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一种结果,是乡土社会走向后乡土社会的一种外在表现。然而,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视角,还需要跳出结构主义的局限,变迁并不仅仅是因为结构的变迁而产生的,变迁还意味着社会与文化的现实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之所以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是因为社会舞台上的“表演者”的行动具有动态性、偶然性和建构性,许许多多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现实其实是人们在特定场合中用自己的实践共同建构起来的。皖东T村妇女的“做会”活动,其深层意义就在于为乡村女性主体性文化的建构提供了舞台,仪式过程中的角色表演和建构实践构成了鲜活的、动态的家庭运行与性别关系的变迁与现实形态。
个案经验虽不能代表也不能推论乡村女性主体性和性别关系的普遍走势,但可以反映乡村女性地位和性别关系的一种现实情景与一种形成机制,由此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在乡村社会性别关系现实的形成过程中,乡村女性的能动性和文化建构机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 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载《社会科学研究》,2015(1)。
[2] 林丽珊:《女性主义与性别关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
[3] Smith, Dorothy E.TheEverydayasProblematic:AFeministSociology.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7.
[4] 佟新:《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1)。
[5] 金一虹:《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6] 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7][17] 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与后台权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19][24] Wolf, Margery.WomenandtheFamilyinRuralTaiwa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9][23] 杨华:《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10] 王会、杨华:《规则的自我界定:对农村妇女主体性建构的再认识》,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1][22] 崔应令:《乡村女性自我的再认识:一项来自恩施土家族双龙村的研究》,载《社会》,2009(2)。
[12] 杨善华、柳莉:《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3)。
[13] 陆益龙:《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皖东T村的社会人类学考察》,载《人口研究》,2001(2)。
[14] 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5] Zhang, Weiguo.“A Married Out Daughter is Like Spilt Water?”.ModernChina,2009,35(3).
[16] Freedman, Maurice.“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In Freedman (ed.).FamilyandKinshipinChinese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18] Ahern, Emily M.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In M.Wolf, and R.Witke (eds.)WomeninChineseSociety.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20] Cohen, Myron L.HouseUnite,HouseDivid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2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5] 阎云翔:《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载《社会学研究》,1998(6)。
(责任编辑 武京闽)
Ritual,Role Perform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Rural Women’s Subjectivity——Thick Description of “Zuohui” Ritual in T Village of Eastern Anhui
LU Yi-lo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e role and subjectivity of rural women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fields of rural study and gender relation research.In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gender inequality and structuralism, the problem of inequality for women is focused, and often pointing all problem of gender relations to social system and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However, the paradigm neglects the diversity of gender relations, such as women take charge of family.T village experience in eastern Anhui shows paradox phenomenon that the patriarchal family system and women charging family co-exis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we can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rural women’s practice in constructing gender relation value and culture.To explicate the “deep code” of “Zuohui” in T village, we find that the ritual is not only a common collective activity organized by women, but also provides a special opportunity and stage for rural women to construct social roles and subjectivity culture.During the ritual, rural women construct positively a public space and a stage, and through the collective performa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construct the “hidden power” in family for women, and the value and cultural symbol system of women subjectivity.
ritual;role performance;rural women;subjectivity;construction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