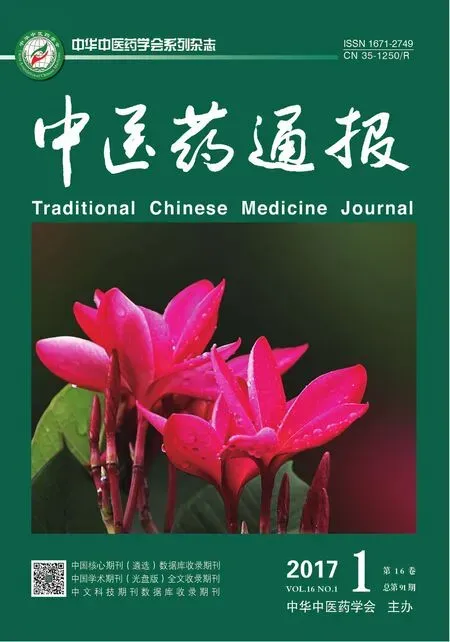张磊从“肝疏泄太过”论治膀胱过度活动症经验※
● 李亚南 许二平 指导:张 磊
张磊从“肝疏泄太过”论治膀胱过度活动症经验※
● 李亚南1许二平2▲指导:张 磊2
张磊教授根据膀胱过度活动症尿急、尿频的病症特点以及“肝主疏泄”“肝主小便”理论,认为本病病机为“肝气疏泄太过、膀胱开阖失度”,可从肝论治,确立了“疏肝抑肝,通利膀胱”的基本治法,并用逍遥散为基础方加减治疗。
膀胱过度活动症 肝疏泄太过 张磊 肝主疏泄 肝主小便
张磊教授为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系国家“十五”攻关“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研究的名老中医之一。张教授学验俱丰,形成了“动、和、平”的学术思想,临床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尤擅内科疑难杂病的诊治。笔者有幸侍诊数载,得窥堂奥,现将其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经验介绍如下,以期共飨。
膀胱过度活动症(Overactive Bladder,OAB)是一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功能障碍性疾病,国际尿控协会将其定义为尿急伴或不伴急迫性尿失禁,通常有尿频和夜尿增多而无泌尿系统感染或其他确切病变者[1]。本病是一种发病率较高且难以根治的泌尿系统疾病[2],现代医学对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且缺乏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3]。本病可归属中医“小便频数”“遗尿”“尿失禁”“小便不禁”“淋证”等范畴,历代医家多数以肾虚湿热为主要治疗依据[4]。张磊教授运用“肝主疏泄”及“肝主小便”理论,认为该病病机多为“肝疏泄太过”,并应用调肝法辨证施治,临床疗效显著。
1 “肝疏泄太过”理论内涵
1.1 肝主疏泄 肝主疏泄理论来源于《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木曰敷和”,又曰“敷和之纪,木德周行,阳舒阴布,五化宣平”。肝木敷布阳和之气,使阳气舒发而阴气布散,以舒调五脏而畅达气机,可谓肝主疏泄理论的最早依据[5]。金元时期,朱丹溪始用“疏泄”描述肝的功能,如《格致余论》言:“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并指出“二者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论述了肝对精液藏泄的重要调节作用。明代很多医家都提及肝的“疏泄”功能,且多强调“泄”[6]。清代陈梦雷明确提出“肝主疏泄,故曰散”,并将“疏泄”作为肝的独立生理功能,而不是与肾或脾进行对举[7]。新中国成立后,“肝主疏泄”作为肝的基本生理机能被写进《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其“肝主疏泄”的内涵也更加丰富,是指肝气具有疏通、畅通全身气机,进而促进精血津液的运行输布、脾胃之气的升降、胆汁的分泌排泄以及情志的舒畅等作用[8],而肝气调节津液的输布代谢是该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1.2 肝失疏泄之疏泄太过 肝失疏泄是指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包括疏泄太过和疏泄不及。如孙广仁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将肝失疏泄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为太过:指肝气亢逆,临床表现为急躁易怒、失眠头痛、面红目赤,甚则吐血、咯血、昏厥等;二为不及:包括肝气虚和肝气郁,前者表现为忧郁胆怯、懈怠乏力、头晕目眩等,后者表现为闷闷不乐、悲忧欲哭、两胁胀痛等。可见,无论是“疏泄太过”还是“疏泄不及”,都只是强调气机紊乱,血气上逆及情志失常所致的病症。如此,则会出现“肝主疏泄”生理机能与“肝失疏泄”病理表现的不对应。所以,“肝失疏泄”还应当包含精液藏泄、津液输布、胆汁分泌排泄和脾胃之气升降等功能异常。因此,“肝疏泄太过”的具体表现包括两大方面。一为病机向“上”的症状:急躁易怒、失眠头痛、面红目赤、昏厥等肝气逆证,咯血、吐血、鼻衄等血气逆证,吐酸、呕吐、呃逆等胆胃气逆证等;二为病机向“下”的症状:遗精、滑精,月经过多、经间期出血,腹痛腹泻、泻后痛止,尿急尿频、急迫性尿失禁等。
张教授认为,肝的疏泄功能既能调畅肺脾肾三脏气机,又能通利三焦,从而维持水液代谢的相对平衡。肝失疏泄则小便排泄异常,如肝疏泄不及可出现小便闭癃,若肝疏泄太过可表现为尿急、尿频甚至尿失禁等。正如《香易塘医话》所云:“肝为五脏之长而属木……约略数之,则有胸腹胀满……小便淋闭,大便或硬或溏而泻。”因此,临床之泌尿系统疾病不仅责之于肾,还当推求于肝。而临证之尿频、尿急甚至尿失禁等症,当考虑是否属“肝疏泄太过”所致。
2 “肝主小便”理论探析
“肾主小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医藏象理论,而“肝主小便”则鲜为人知。因肝与小便关系极其密切[9],古代医家亦有“肝主小便”之说。早在《灵枢·经脉》就有“是肝所生病者,……飧泄狐疝,遗溺闭癃”的经典论述;又《难经·十六难》曰:“假令得肝脉,……其病四肢满,闭淋,溲便难,转筋,有是者肝也。”《灵枢·经脉》曰:“膀胱足太阳之脉……是主筋所生病者”,而肝主筋,前阴为宗筋所聚,故肝与膀胱通过筋而相互联系[10],且肝足厥阴之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前阴亦是厥阴肝经循行所过。此外,肝与水液的输布代谢密切相关。例如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言:“木乃水中之生阳,肝主疏泄水液”“肝气盛而热,故遗溺也”;尤在泾亦云:“肝喜冲逆而主疏泄,水液随之而上下也”;明代医家薛己在评注《明医杂著》时明确提出“肝主小便”。后孙一奎、黄元御、徐忠可等均对此有详细阐述。如孙一奎《赤水玄珠》云:“又肝主小便,使毒邪从小便中出”,王肯堂言:“盖肝主小便,因热甚而自遗也”。清代医家吴达对肝肾二脏与小便关系的描述则更加合理,其在《医学求是》中概括为“肾主二便,其职在肝”。肝肾二脏联系紧密,肾闭藏,肝疏泄,二者协调,则藏泄有度,水气不病[11]。且肝肾同源,肾主水,司二阴,故肝也具有主持小便的功能[12]。
张教授强调不应忽视肝对小便的重要调节功能。肝气畅达,则膀胱开阖有度;肝失疏泄,则膀胱失约而发为淋闭等。此外,小便疾病与五脏皆相关。如肺为水之上源,主治节而通调水道;脾主运化水液,脾失健运则水湿内生而下注膀胱;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神失养则脏腑功能紊乱而小便异常[13]。临证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或有或无,或虚或实,不可拘于一端。
3 从“肝疏泄太过”论治膀胱过度活动症
3.1 病机与辨证依据 基于膀胱过度活动症尿急与尿频的两大特征,确立了膀胱失约的基本病机。针对病症特点,张教授认为:①本病以尿急、尿频、急迫性尿失禁为主,症状核心突出为“急”。而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刚强躁急,故可从肝论治。②西医排除了感染及其它确切病变,中医认为“湿热”邪气等不是主要矛盾。重点是机体生理功能失调,而肝主疏泄,又主枢机[14],若纠其“疏泄”之偏,复其冲和条达之能,则膀胱开阖有度,而“水液随之上下也”。③大多数OAB患者可被某一环境诱因诱发尿急或尿失禁发作,这种条件反射与症状发作的相关性[15],也为“肝疏泄太过”理论提供依据。因此,确立了“肝气疏泄太过、膀胱开阖失度”的病机。
其辨证思路如下:①具有典型“肝疏泄太过”症状者,包括尿急、白天尿频、小便次数十余次至几十次不等、夜尿增多或急迫性尿失禁,伴胸胁胀闷、少腹胀痛、烦躁易怒、喜太息、头晕目弦、口苦咽干、夜寐不宁、舌红苔薄白、脉弦等;②除小便异常外,无明显兼症者;③临床辨为它证而疗效不佳者,如辨证属膀胱湿热、肺脾气虚、脾肾阳虚等,应用相应药物久治无效者。
3.2 遣方用药经验 根据上述病机,以疏调肝气、通利膀胱为基本治法,张教授常以逍遥散为基础方,并重视加减及合方。若大便干,则以《伤寒论》脾约证治之,方用逍遥散去白术加麻子仁丸。原方用白术者,因“治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也”,今大便干,则脾已“实”,故去之;若腹痛大便溏,合痛泻要方以抑木扶土;如伴小腹拘急者,合用芍药甘草汤,即加重原方白芍用量,酸以泻肝而伐其过也;若小腹灼热刺痛,兼下焦瘀热,加琥珀、地龙、牛膝、瞿麦以清热祛瘀通淋;瘀热不甚者,可取五淋散(当归、赤芍、赤茯苓、栀子、甘草)之意,加栀子、赤芍等;若伴口疮、小便赤涩,此为心肝火旺证,合用导赤散清心泻火,并加桑叶、竹茹、丝瓜络以清肝通络;若湿热蕴结,轻者合四妙丸,重者合三仁汤,并加车前草、白茅根、赤小豆以清热利湿;肾阴不足者,用逍遥散合六味地黄丸;肾阳亏虚者,用逍遥散合金匮肾气丸;若两胁胀甚、急躁易怒,合四逆散或柴胡疏肝散,并加郁金、青皮等;伴尿失禁者,加桑螵蛸、金樱子、白果等固精缩尿;若失眠或情志症状严重者,改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等。张教授临床用药灵巧多变,尤擅经方时方合用,并强调医者临证应明了于心,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4 典型病例
李某某,男,23岁,2016年7月18日初诊。主诉:尿急、尿频半年余。现病史:半年前因吃辣椒过多出现尿急、尿频,严重影响学习、睡眠及日常生活,查尿常规、尿细菌培养、泌尿系彩超以及前列腺检查等均未发现异常,西医诊断为膀胱过度活动症,口服托特罗定、奥昔布宁,无明显疗效。刻诊:尿急、尿频,尿意强烈,无尿痛,白天小便次数达20余次,夜尿增多,偶有尿失禁现象,伴头顶刺痛,小腹憋胀,平素性格急躁,学习压力较大,眠差,纳可,大便正常。舌质暗红,苔白腻,脉细。中医诊断:小便频数(肝疏泄太过、夹瘀)。治法:抑肝化瘀,通利膀胱。方以逍遥散合芍药甘草汤加味。药用:柴胡10g,生白芍15g,当归10g,炒白术10g,茯苓10g,薄荷3g(后下),制香附6g,怀牛膝10g,干地龙10g,琥珀3g (另包冲服),生甘草6g。10剂,水煎服,每日1剂。
2016年8月17日二诊:连续服上方30剂,小便次数明显减少,白天5~7次,夜尿2次,仍睡眠质量差,入睡难、多梦,伴头痛,纳可,大便正常,舌质红,苔白腻,脉细。治以调肝安神;方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药用:柴胡10g,黄芩10g,清半夏10g,党参10g,桂枝6g,茯苓10g,大黄2g,郁金10g,胆南星6g,炒神曲10g,生甘草3g。服此方15剂后,睡眠改善,小便基本正常。2个月后随访未复发。
按 患者青年男性,因素性急躁、加之学习紧张,而致肝火偏旺。又因嗜食辛辣,遂成“肝疏泄太过,膀胱失约”之候,症见尿急、尿频、小腹憋胀等。病久则瘀血、痰浊内生,故见头顶刺痛、舌暗红苔白腻等。初诊以逍遥散调肝气;芍药甘草汤缓肝急;加香附增强疏肝之功;加怀牛膝活血利水,补益肝肾;地龙味咸性寒,且入肝、膀胱经,善清肝热而利水道;琥珀活血散瘀,利尿通淋,又能“安五脏、定魂魄”。诸药合用,俾肝之“疏泄”功能正常,则膀胱排泄有度。二诊小便次数已基本正常,仍有失眠头痛,故遵《内经》“间者并行”之旨,方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清肝益气兼以重镇安神;原方铅丹现已不用,加郁金活血止痛、行气解郁,又配伍菖蒲,共奏清心化痰、活血宁神之功;佐以炒神曲顾护胃气。
[1]Abrams P,Cardozo L,Fall M,et al.The standardisation of terminology of lower urinary tract function:report from the Standardisation Sub-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J].Am J Obstet Gynecol,2002,187 (1):116-126.
[2]廖利民,鞠彦合.膀胱过度活动症(OAB)研究进展——来自第 43届国际尿控协会(ICS)年会的报道[J].现代泌尿外科杂志,2014,19(1):15-18.
[3]高红英,吴玉斌.膀胱过度活动症诊治进展[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016,31(5):379-385.
[4]姜安超,赵良运,张春和,等.中医药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研究进展[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6,37(5):64-66.
[5]柴瑞霁.肝主疏泄纵横谈[J].中医药研究杂志,1986,(2):41-43.
[6]赵 迪,任 杰,安海燕.肝主疏泄源流研究[J].西部中医药,2016,29(7):58-60.[7]于 宁,张银柱,车轶文,等.“肝主疏泄”概念的演进[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4,20(1):9-10,22.
[8]孙广仁主编.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17.
[9]毛军民,连建伟.连建伟教授从肝论治小便疾病经验拾贝[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5):280-281.
[10]王 兵.论肝主小便[J].环球中医药,2010,3(6):450-451.
[11]刘清君,卢良威.试论肝主小便[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3,27(3):23.
[12]吴天浪,张培海,常德贵,等.“肝主小便”理论浅析[J].四川中医,2009,27(11):29-30.
[13]闫 雁.从心论治小儿神经性尿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8):1131-1132.
[14]唐军伟,张 杨.肝为枢机理论初探[J].四川中医,2012,30(8):40-41.
[15]杜丽娟,蔡雪跃.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症状发作的环境诱因[J].解放军护理杂志,2015,32(19):52-5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No.12YJAZH171)
▲通讯作者许二平,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方剂配伍规律及临床应用研究。E-mail:xuerping12281119@126.com
1.河南中医药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450008);2.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45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