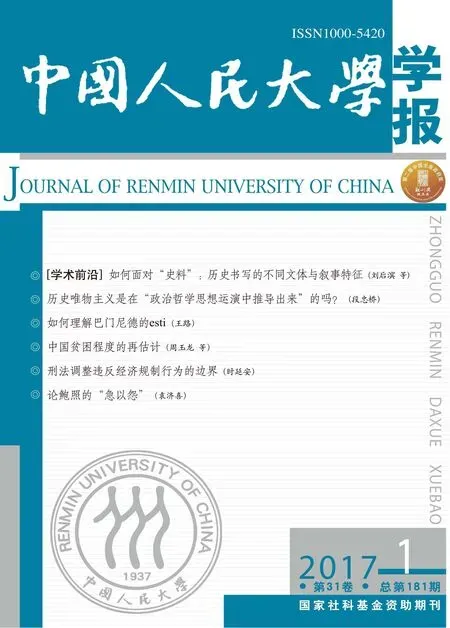论鲍照的“急以怨”
袁济喜
论鲍照的“急以怨”
袁济喜
南朝刘宋时代的诗人鲍照的为文历来被评为“急以怨”,而这种特征往往与道德评价相联系,未能从历史情境与文学特征本身去加以分析。鲍照出身寒微受到压抑,因为急于进取而罹祸。他的诗赋创作具有抗争的悲剧价值,在南朝特定阶段,他的“急以怨”具有重振颓风的积极意义,也是对乡愿社会的反抗。因此,对于他的“急以怨”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评议。
鲍照诗赋;悲剧命运;南朝世态;抗争价值
鲍照是南朝刘宋时代的著名诗人,以个性鲜明、峻切急怨为特点。隋末大儒王通在《中说·事君篇》云:“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1](P79)王通从儒家理念出发,对于南朝的文人一概骂倒,认为鲍照、南朝江淹是古之狷者,其文急以怨。所谓“古之狷者”,即进取不成则怨愤不容的人物,如屈原一类人物。
从南朝开始,人们对鲍照的评价一直低于颜延之、谢灵运。现代学者对于鲍照诗文的研究,大多从作家生平与作品风格入手展开研究,近年来有的学者试图从人生遭际与悲剧角度去探讨,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著。但是系统结合六朝时代的士人命运与人生哲学,再到文学创作层面去探讨的论著依然缺失,本文鉴于此而进行探讨。
一、鲍照诗赋中的“急以怨”
鲍照的“急以怨”,从文体角度来说,人们多从其诗作角度去理解,但是鲍照诗歌的主要成就为乐府诗与拟代体诗作,这类诗作不同于《古诗十九首》与阮籍等人的文人诗,模仿的痕迹较重,对于内心世界的抒发相对来说较为驽钝,如果要全面解读他的“急以怨”,则须更加关注他的赋作,因为正是这些赋作,将鲍照的内心世界与审美个性全面展现出来。正如《文心雕龙·诠赋》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P134)赋是诗的流变,通过体物写志,将作者内心的情志抒写出来。东汉以来的赋作,受到文人诗的影响,侧重文人内心情志的宣泄,较之乐府诗,更能见出文士内心的情志。从这个角度去看鲍照的“急以怨”,无疑会有更大的收获。
鲍照出身较为低微,并非南朝显贵家族。钟嵘评之曰:“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3](P47)。鲍照曾经去谒见临川王刘义庆,有人劝告他位卑不宜干谒王侯,但鲍照大胆奏诗,得到刘义庆的赏识,后来又为临海王参军。其“急以怨”的性格,是他一生不断抗争的彰显,同时也遮蔽了他的智慧,妨害了他客观冷静地观察世道,在频繁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及时引退,终于罹祸而亡。
从审美原理来说,任何崇高及悲剧的诞生,都是主体与客体冲突的产物。这种冲突的范围包括很广,从宇宙人生到命运事件都包括在内。冲突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剧烈的方式,也有无声的遭际。在鲍照的作品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这种悲剧冲突的多样化,以及主体的反应与评价,形成特殊的悲剧美感。鲍照赋作的悲剧感,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
(一)巨大的社会悲剧事件引起的悲剧感
鲍照的代表作为《芜城赋》。芜城指的是广陵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北岸重要都市和军事重镇,历经战乱。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举戈南侵,广陵被焚。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叛变,孝武帝派兵讨平。十年之间,广陵两遭兵祸,繁华都市变成一座荒城。大明三、四年间,刘诞之乱平定后不久,鲍照来到广陵,面对荒芜不堪的城市,感慨万千,写下了《芜城赋》。赋中采用对比的手法写道:“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琁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沈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4](P13)鲁迅曾经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赋中描写的这些生活方式,未尝不是寒门出身的鲍照心仪的人生目标。而鲍照在痛惜繁华凋落、人生无常的同时,也难免陷入深深的痛楚与思考之中: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迳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5](P13-14)
诗人作为审美主体,对于人世间的悲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思索与结论,有的是用虚无的观念来解释,有的是用道德历史主义来批判和凭吊,有的则是痛惋不已。而鲍照则显然不属于上述这几种态度,他采用的是一种间性思维,介于这诸种立场和态度之间。首先,他对于广陵城的今昔命运是痛楚与悲叹的。清代许梿《六朝文絜》卷一评论:“从盛时极力说入,总为‘芜’字张本,如此方有势有力。”[6](P2 )可见,“芜”字千言万语,言不尽意。然而,此赋又不是简单的“芜”字所能概括的,而是在痛悼中蕴含有无尽的沉思。对于这种命运结果与人物遭际,鲍照既认为有其盛极而衰的必然性,同时又由衷地表示同情。最后发出浩叹:“天道如何,吞恨者多!”这八个字意味无穷,喟然深叹,天道如何,意为天道难以情测,令人叹扼,老子尝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7](P22)。意谓天道冷漠无情,有其必然性。这是哲学家语,但是文学家的吟咏却不能无情,因此,对于天道与命运是往往会发出诘问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慨叹:“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8](P2482)。鲍照咏叹“天道如何,吞恨者多”,也是对于天道的诘问与不平。他不甘心接受天道与命运的安排,这正如他对于自己命运多舛始终不平一样,所以吞恨终生,“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则是对于芜城事件的永远不解与郁闷。这也许是此赋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地方。后人对此评论,也往往专注于此。林纡《古文辞类纂选评》卷十评道:“文不敢斥言世祖之夷戮无辜,亦不言竟陵之肇乱,入手言广陵形胜及其繁盛,后乃写其凋敝衰飒之形,俯仰苍茫,满目悲凉之状,溢于纸上,真足以惊心动魄矣!”[9](P486)鲍照此赋表现出来的悲剧性超越其他赋作的独特魅力,也是鲍照“急以怨”的个性在赋作上的彰显。
鲍照此赋中的悲感心态,直接浸润稍后的刘宋时期的文人江淹的《恨赋》。《恨赋》开头即叹:“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10](P161)在平原即目而见的死亡情形,引发了江淹心中的无尽感恨,进而令他想到历史上各种各样的饮恨而亡的人物。文章通过对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这六个历史人物各自不同的恨的描写,来说明人人有恨,恨各不同的普遍现象。不管他们生前身份如何,遭际怎样,最后都是死亡,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11](P162)
这与鲍照《芜城赋》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一是以一座荒芜之城为兴叹,一是以历史人物为咏叹。但悲感主体却是既没有陷入无常之叹,也没有落入简单的道德历史主义的评论,而是从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高度去思考与悲吟。作为六朝的骈赋,这也许是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最具有魅力的地方。
(二)四时之景与感伤情致
六朝时期,对于四时景物的移迁而引起文士的感物兴怀,即景抒情,是一种写作常态,亦是六朝文学的自觉之体现。陆机在《文赋》中提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12](P20);钟嵘《诗品序》提出:“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13](P2)。然而,在感物吟志方面,不同的文人有不同的方式。鲍照赋中的描写与咏叹,是典型的六朝骈赋手法,文辞工丽,抒情婉约,与他的诗作风格有所不同。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评论:“刘宋之世,颜延之、谢灵运,弁冕南朝,体裁明密,并称文章第一。而鲍照雕藻淫艳,异军特起,才秀人微,骖驾其间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沈约继起,更唱声律于齐梁之际。”[14](P158)《游思赋》是鲍照从四时之景的变化来抒发人生感叹的赋体作品。这篇赋首先从眼前所见景色写起:“仰尽兮天经,俯穷兮地络。望波际兮昙昙,眺云间兮灼灼。乃江南之断山,信海上之飞鹤。指烟霞而问乡,窥林屿而访泊。”[15](P1)这是一幅水天一色的景色,于暮色苍茫中,见出作者惆怅之心境。继而写道:
塞风驰兮边草飞,胡沙起兮雁扬翮。虽燕越之异心,在禽鸟而同戚。怅收情而抆泪,遣繁悲而自抑。此日中其几时,彼月满而将蚀。生无患于不老,奚引忧以自逼?物因节以卷舒,道与运而升息。贱卖卜以当垆,隐我耕而子织。诚爱秦王之奇勇,不愿绝筋而称力。已矣哉!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异乎丛棘。[16](P1-2)
作者从眼前的越地,又想到了胡边。“虽燕越之异心,在禽鸟而同戚。怅收情而抆泪,遣繁悲而自抑。”从这些怅然中,作者感受到人生的短促与悲凉。最后归结到隐退,“物因节以卷舒,道与运而升息。贱卖卜以当垆,隐我耕而子织”,这显然是时节的变化与景色的凄婉引发了作者的惆怅之情。在汉魏以来的赋作中,这也是一种经常采用的题材与写法。从悲感来说,主要是作者有感于物色的转换而引起的心绪变化。鲍照的《游思赋》与前人的赋作相比,在景色的绘制与情感的抒发上更加细致些。这篇赋中充满着对命运与环境的不平与愤懑,这是鲍照赋中“急以怨”地咏叹四时之景时自然透露出来的“有我之景”,构成鲍照赋中特有的悲慨意蕴。
鲍照赋作中也充满着内心的矛盾,即对于命运的不满与委顺自然的交织。通过景物在四时运逝来加以咏叹,引发人生与天道、物候的感叹,凸显悲剧命运的无奈。这是汉魏以来诗赋的常见类型,也是鲍照诗赋的重要题材。鲍照在《伤逝赋》中面对秋天的凄惨景观感叹:“日月飘而不留,命倏忽而谁保?譬明隙之在梁,如风露之停草。发迎忧而送华,貌先悴而收藻。共甘苦其几人?曾无得而偕老。拂埃琴而抽思,启陈书而遐讨。自古来而有之,夫何怨乎天道。”[17](P10)这是对于岁月飞逝、人生易老而发出的无奈吟叹。
汉魏以来思想文化的变迁,便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生命哲学与老庄顺应自然的思想观念互相交错。人们对于天道变化与人生境遇的思考进入到整个自然之道的思维之中,不再是简单地从人为努力上去解释与认同,而四时之景的变化以及人生的迁易,生命的消逝,是在整个时空变化的范围内去运动的,因而这种焦虑与彷徨,时时出现在诗赋中,即令是陶渊明这样貌似超脱的人,也难以摆脱这样的焦灼。陶渊明诗既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18](P37),亦云“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19](P36)。可见,六朝人对于天道自然与人生有限的执着与无奈。鲍照的诗文经常表现出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对于命运给自己造成的不公平怨天尤人,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冷静的超脱。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在鲍照的心态与创作中夹缠难解,因而他诗文中的以悲为美,不是简单地用儒家与道家思想就能解释清楚的。这是鲍照诗文中“急以怨”的特点,简单将其归纳为急躁怨恨,忽略其复杂性,难免失之偏颇。
这种复杂的心情,在《观漏赋》中表现得更明晰。此赋通过吟咏漏刻来借题发挥,赋序一开始即感叹人生易逝,描写受不可支配之命运左右的悲剧情景:“客有观于漏者,退而叹曰:夫及远者箭也,而定远非箭之功;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为心,不可凭者弦;因生以观我,不可恃者年。凭其不可恃,故以悲哉!”[20](P4)鲍照此赋充满着哲理,他提出,当下的人生是受主人支配的,而主人又是受冥冥之中的命运支配的,这是最后的推动力,就像箭头的运动是受弓力的支配一样。然而,关于最后推动力的讨论,魏晋以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三国时魏国的王弼《老子注》中“贵无”的本体论,他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受背后的“无”支配的,“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21](P195);而西晋时的郭象则强调事物的变迁是受不可认识、不可求取的玄冥独化之神秘力量所支配与左右的,万生自灭,非有所待;东晋时《列子》一书中有《力命篇》,更是强调“力”受“命”的支配,而“命”则是偶然因素的产物,不可认识,不可左右。而鲍照此赋中对于命运的观点,受到郭象的影响似乎更多一些,他强调命运的偶然性与无从支配的特点。赋中先从漏刻的变化而感叹时光的飞逝,然后再从这一变化引申出天秩即命运的无情,继而哀叹年轮的飞逝。面对这种无情世界,作者唯有在诗酒中得到些许慰藉:
聊弭志以高歌,顺烟雨而沉逸。于是随秋鸿而泛渚,逐春燕而登梁。进赋诗而展念,退陈酒以排伤。物不可以两大,得无得而双昌。薰晚华而后落,槿早秀而前亡。姑屏忧以愉思,乐兹情于寸光。从江河之纡直,委天地之圆方。漏盈兮漏虚,长无绝兮芬芳。[22](P5)
魏晋以来,面对宇宙的大化,人们往往采取自我解脱的方式,特别是在由南入北的文士的晚期之作中,这种心态更是明显。如庾信《伤心赋》赋尾哀叹:“一朝风烛,万古埃尘。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几人。”[23](P63)颜之推《观我生赋》最后悲吟:“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株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24](P4090)这是六朝士人共同的心声,也是人生悲剧观的显现。而鲍照则通过他的“急以怨”独特视角,将这种悲观主义作了演绎,同时也感吟出士人不甘命运摆布的另一面。
(三)咏物赋中的悲感
咏物赋与即景写情、铺写心志的赋作相比,体制较小,寄寓更深。汉魏以来的辞赋文学发展,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从两汉的京都苑猎大赋,衍生出一种咏物寓情,体制细小的赋体,这就是咏物小赋。其中对于禽鸟植物的吟咏,借题发挥,感叹自己的身世遭际。《文选》中所选录的祢衡的《鹦鹉赋》等作品就是代表作,在此之前,还有东汉末年赵壹的《穷鸟赋》、张衡等人的赋作,魏晋以来,这类赋的演变与发展也很明显,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在鲍照与江淹的辞赋中,咏物题材是其中的重要作品。《舞鹤赋》可谓鲍照的代表作之一,此赋借咏叹舞鹤来隐喻自己的人生境遇。赋一开始即写鹤的种种动人的姿态,继而又写出了仙鹤的惆怅与悲凉境遇,它们远离自己的故土,陷于孤苦岑寂之中,“岁峥嵘而愁莫,心惆惕而哀离”[25](P33),这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写法。最后写道:
众变繁姿,参差洊密。烟交雾凝,若无毛质。风去雨还,不可谈悉。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离而云罢,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怅以惊思。当是时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巾拂两停,丸剑双止。虽邯郸其敢伦,岂阳阿之能拟。入卫国而乘轩,出吴都而倾市。守驯养于千龄,结长悲于万里。[26](P33)
此赋通过舞鹤的流落与飘零,写出了那只鹤外表光鲜、内里凄凉,与祢衡之赋异曲同工。内心志向的远大、情感世界的依恋故土与身不由己的境遇间的冲突,构成了此赋的悲剧性。
鲍照咏物赋的另一篇是《园葵赋》。此赋是在人们不常关注的植物中,植入了鲍照的人文情思。他将这一植物写得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尔乃晨露夕阴,霏云四委,沈雷远震,飞雨轻洒,徐未及晞,疾而不靡,柔莩爰秀”[27](P29)。鲍照不愧为辞赋大家,通过他的描写与抒情,我们得以知道园葵的可爱与可人,此物的天性便是随太阳而旋转,而赋家通过对于此物的观察与咏叹,也感悟出人的乐天知命而不忧,荡然任心,以歌以咏,不也是抒发了赋家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吗?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鲍照与陶渊明相似的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人生观与文学理念:“彼圆行而方止,固得之于天性,伊冬箑而夏裘,无双功而并盛。荡然任心,乐道安命。春风夕来,秋日晨映。独酌南轩,拥琴孤听。篇章间作,以歌以咏。鱼深沈而鸟高飞,孰知美色之为正?”[28](P29)鲍照此赋从寻常所见的园葵起兴,通过宛转附物,寄托感慨,最后引出了庄子的相对主义美学观与人生观。
这种擅长从老庄思想中引申出人生明哲保身的意念,我们在鲍照的许多咏物赋中都可以找到踪迹。比如《尺蠖赋》中吟咏:“智哉尺蠖,观机而作,伸非向厚,屈非向薄。”[29](P47)这首赋从尽蠖的善于屈伸的物性起兴,进而感受到人生亦如此,“动静必观于物,消息各随乎时”[30](P47),这样才能随遇而安,动静有常。遗憾的是,鲍照虽然明于此理,但在当时反复无常的政坛变化中,终究没有逃脱命运的摆布,未能免于罹难。《飞蛾赋》则是通过飞蛾趋炎附势最后难逃厄运的形象,揭示出人生的哲理,其旨趣大抵同于《尺蠖赋》。从鲍照上述赋的人生观与悲剧观中,我们可以看到,鲍照的“急以怨”的个性充盈着他那个时代特有的焦虑、愤懑与虚无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充满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冲突,汉魏以来的士人建功立业、寻求超越与人生虚无、明哲保身的心志纠结在一起,造成鲍照人生与文学的悲感与焦虑,与此同时,“急以怨”的个性与风格便浮出水面,形成文本上的特点。而深层的则是老庄与玄学的理念与人生的无望与失意。因此,仅仅用“急以怨”来概括鲍照的个性与文学精神,是非常浮浅的。
当然,鲍照的“急以怨”主体仍然充溢着强烈的冲突之美。悲剧美学的关键是主体与客体的彼此关系,面对客观力量的强大与横暴,主体的应对与抗争是构成悲剧美感的重要因素。汉魏以来,对于天道与人生悲剧,建安时代的文士慷慨悲歌,建功立业,正始文士清峻遥深,追求玄远,太康文士追求身名俱泰,缘情绮靡,东晋士人则嗜好庄玄,归依佛道,他们的心态往往逃于佛道,面对外界的压力,采用自我逃遁的方式来解脱。而鲍照诗文始终荡漾着一股不平之气。在《拜侍郎上疏》中,鲍照自谓:“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众善必达,百行无一。生丁昌运,自比人曹。操乏端概,业谢成迹。徂年空往,琐心靡述。褫辔投簪,于斯终志。束菜负薪,期与相毕。安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罗广收,圆明兼览,雕瓠饰笙,备云和之品;潢汙流藻,充金鼎之实。铩羽暴鳞,复见翻跃;枯杨寒炭,遂起烟华。未识微躬,猥能及此,未知陋生,何以为报?祇奉恩命,忧愧增灼,不胜感荷屏营之情,谨诣阁拜疏以闻。”[31](P60)鲍照在上疏中,对于自己沉处下潦、虚度年华深感愤懑不平,表达了扩时用世、建功立业的心志。在《解褐谢侍郎表》中自谓:“臣照言: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不悟天明广瞩,腾滞援沈,观光幽节,闻道朝年。荣多身限,思非终报。”[32](P55)从这些文章来看,鲍照的个性确实是有些急躁,并非那些城府较深、善于隐藏的人,唯其如此,他的文学作品将其内心情志溢于言表,构成他的文章人性鲜明之特点,他的个性中,优点与缺憾同样明显。
鲍照“急以怨”的性格特征,在五七言诗歌中表现得更为直接。这是因为,诗歌是直抒其事、怊怅缘情的,不像辞赋那样以铺叙为长。鲍照的诗歌以五七言诗为特长,其中乐府诗更是他的特长文体。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指出:“鲍照由于‘身地孤贱’,曾经从事农耕,生活在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处处受人压抑。他在《瓜步山揭文》里曾经叹息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这和左思《咏史》中的‘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的愤慨不平是完全一致的。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使他在创作上选择了一条和谢灵运不同的道路。当谢灵运大力创作富艳精工的山水诗时,鲍照也开始了创作生活,并以‘文甚遒丽’的古乐府逐渐闻名于诗坛。”[33](P311-312 )这一论述,基本概括了鲍照诗歌与谢灵运诗歌的不同特点。鲍照诗歌中的悲剧感,依照内容来分类的话,大约可以分成这样两类:
一是对压抑的社会现实的愤懑。《拟行路难》十八首系鲍照的代表作。这组诗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他在这里对士族门阀的压迫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34](P229)“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35](P231)前一首虽然没有说出他所愁叹的是什么,但是从他的吞声踯躅之中,可深深感到他胸中的一股悲愤不平之气。在后一首里,这种悲愤不平之气一开始就在对案不食、拔剑击柱之中爆发出来,他宁肯弃置罢官,也不愿蹀躞垂翼、受人压抑,这就是他所以愤慨不平的内容。最后两句,更鲜明地表现了诗人孤直耿介的性格和对门阀社会傲岸不屈的态度。
二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拟代抒发心中的不平。《代放歌行》这首诗通过对比的方式,将小人与旷士的品行与遭际加以对比,揭示了贤士不得其遇,而庸人比比皆是的社会现实。除了历史人物之外,鲍照诗中还描写了一些虚拟中的人物悲惨故事,以此影射自己的遭际,《代贫贱苦愁行》咏叹:“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36](P200)鲍照还通过代拟体,写了一些挽歌体《代蒿里行》:“人生良自剧。天道与何人。赍我长恨意。归为狐兔尘。”[37](P140)《代挽歌》:“独处重冥下,忆昔登高台。傲岸平生中,不为物所裁。埏门只复闭,白蚁相将来。生时芳兰体。小虫今为灾。”[38](P142)六朝时代的挽歌,是“以悲为美”的特殊表现文体,意在通过对于死者的哀挽,抒发自己的旷达之情。正如西晋文士陆机在《大暮赋》中所说:“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耶,又何生之足恋?故极言其哀,而终之于达,庶以开夫近俗云。”[39](P197)对于现实的不满与失望,走到极端,便是对于死亡的向往与咏歌,正如《列子》中说的:“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40](P26),但终究也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与超越。陆机有《挽歌诗三首》,其中第三首哀叹:“人往有返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41](P667)陶渊明也有《拟挽歌辞三首》,其中第三首叹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42](P142)。鲍照的《挽歌诗》与他们相比,老庄与玄学的意味少了一些,更多了一些不平与牢骚之气,主体与客体冲突的蕴致更强烈一些。
二、如何评价鲍照的“急以怨”
关于鲍照的“急以怨”,曹道衡先生认为鲍照诗文风格主要来自于《楚辞》与汉赋,有的学者则认为受建安文学影响为主。其实,从全面角度来看,鲍照之所以成为一位从人生到性格都极具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急以怨”文学内格与他的人生直接相关。鲍照之所以成为元嘉三大家,与他的兼收并蓄的文学世界相关,他的文学风骨与描写手法,特别是诗歌,受到建安文士创作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是他的人生悲感,以及对于人生与天道的悲剧意识,则受到“正始之音”的浸润,阮籍、嵇康远大遥深的文学旨趣,给予他很大的润泽,我们从他的诗文中,经常在不平之中感受到那种深沉而无奈的喟然长叹,以及对于世界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西晋陆机、潘岳的文学创作,也直接泽溉鲍照的诗文。
梁代史家萧子显在《南齐书·幸臣传序》中指出:“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43](P972)梁代虞炎《鲍照集序》中指出,鲍照“身既遇难,篇章无遗。流迁人间者,往往见在。储皇博采群言,游好文艺,片辞只韵,罔不收集。照所赋述,虽乏精典,而有超丽,爰命陪趋,备加研访,年代稍远,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傥能半焉。”[44](P5)鲍照生前以才学见称,但因他出身寒微,不甘沦落,个性狷急,因此,命运乖蹇,死后著述零落。鲍照对晋宋之际的文学嬗变之作用,过去的文学史家缺少积极正面的评价。比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45](P675)刘勰对刘宋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很推崇,对于鲍照在南朝刘宋时代之作用不曾提起。钟嵘《诗品》提出:“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46](P2)在钟嵘笔下,刘宋元嘉仍以谢灵运为主,颜延之为辅,鲍照无法与他们匹敌。钟嵘将鲍照的五言诗列为中品,评价曰:“宋参军鲍照,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47](P47)钟嵘认为鲍照兼有众人之美,但是又批评鲍照五言诗“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48](P47),认为鲍照之诗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是负面作用。梁代史学家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批评:“次则发声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49](P908)这些批评都是偏执于外表的皮相之见,未能从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角度去加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东汉晚期至东晋,士人的文学精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便是从慷慨仗气到淡远平和的心境演化。《文心雕龙·时序》提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50](P675)鲁迅先生曾经比较建安文士、正始文士与陶渊明诗文创作风格之不同,指出:
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51](P505)
鲁迅从时代变迁谈到了文章风格的变化,将文章风格的变化置于时代因素中去考察,这比孤立地考察文章风格特征更加深刻。鲁迅指出,从东晋开始,由于世道的多变与世人的心态麻木,于是文章变得平和淡然了,代表人物便是陶渊明,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却丧失了那种慷慨激昂的人生态度与文学风骨,淡泊平和往往掩藏着人生的逃遁与无奈。在这种时候,鲍照以“急以怨”的风格成为与颜、谢并驾齐驱的文学潮流,对于南朝文学精神之传承汉魏风骨,起到了挽救颓风、重振风骨的作用。也可以说,鲍照的文学创作先于刘勰与钟嵘,以“急以怨”的方式打破了东晋以来的平和之美,对于汉末建安文风与正始之音的复兴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刘勰与钟嵘倡导“风骨”与“风力”的文学批评思想,也与鲍照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鲍照的“急以怨”从源头来说,主要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的遭际与创作精神是鲍照及其文学风格的来源。汉代对于屈原的狷介有过争议,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人格与《离骚》作了肯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52](P2482)司马迁从“发愤著书”的亲身感受出发,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在这部不朽之作中,诗人以瑰丽奇特的想象、悲愤沉痛的情感、飞动华美的词藻,抒写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在西汉初年,许多文人与贵族对《离骚》钟爱有加,东汉王逸编纂的《楚辞章句》收录有许多文人与贵族仿效屈原赋而作的骚体赋。到了东汉班固作《离骚序》,针对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关于屈原的评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53](P49-50)班固以其明哲保身的哲学对屈原的高峻人格进行非议,评价他是“狂狷景行之士”,同时也对《离骚》中的艺术特色作了否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54](P49-50 )。迄至东汉后期的王逸,又对班固等人的评价作了否定。他在《楚辞章句序》中根据孔子倡中庸又不废杀身成仁,言时变又反对“乡愿”的思想,提出了他所倡导的“人臣之义”,以批驳班固和光同尘的媚世哲学:“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55](P48 )。王逸认为人臣如果只图顺世以保命,虽然寿比南山,那也是“志士之所耻”,不值得肯定。王逸指出屈原创作《离骚》借用了想象的手法,大量运用比喻,举一反三,引譬连类,使《离骚》的意境瑰丽奇谲,想象纷繁万状,这些观点在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篇》中得到了弘扬,对于正确对待鲍照的“急以怨”不乏启发价值。
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6](P931)孔子的“诗可以怨”,正是这种狂狷精神的彰显。鲍照的狂狷正是在当时被逼出来的,在门阀世族垄断权力,弱者受到欺凌的时代,他不断发出反抗的声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风,但是如同建安骨一样,彰显出不屈的处于社会下层人士的抗争与声音,他的文学价值,以及风格特点也应作如是观。宋齐之交的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有《鲍参军戎行》一首:“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狥义非为利。执羁轻去乡。孟冬郊祀月。杀气起严霜。戎马粟不暖。军士冰为浆。晨上城皋坂。碛砾皆羊肠。寒阴笼白日。大谷晦苍苍。息徒税征驾。倚剑临八荒。鹪鹏不能飞。玄武伏川梁。铩翮由时至。感物聊自伤。坚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57](P128-129)江淹深受鲍照文风的浸润,对于鲍照的遭际深感同情,他自己早年的命运也与鲍照颇为相似。这首诗对于鲍照的命运与慷慨陈词深有体会,对世人理解的“急以怨”作了最好的诠释。唐末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悲慨》一品,其中描写了悲慨的特征:“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58](P35)。鲍照正是这种浩然弥哀的悲剧人物。鲍照诞生于东晋之后的刘宋时代,他的所谓“急以怨”,正是时代的产物,从儒家的中庸之道来看,似乎有些狷急,但是深入分析则不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积极意义。宗白华先生1940年在《学灯》杂志发表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
汉代以来,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支配着中国社会,成为“社会栋梁”,把孔子至大至刚、极高明的中庸之道化成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衷主义、苟安主义,孔子好像预感到这一点,他所以极力赞美狂狷而排斥乡原。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汉代的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原满天下。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其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59](P188-189)
从宗白华先生这一段文化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鲍照“急以怨”性格与诗文风格的历史原因与进取价值。
六朝文化的主体是由皇权与世家大族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构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这诸种关系也彼消此长,门阀世族到了南朝时代,势力有所消退,精神状态更是全面世俗化,失却了两晋时代的锐气,日趋保守与腐化,耽于享乐而不能自拔,在这种时候,鲍照的诗风兴起,与元嘉时代颜谢相比,具有正义感与悲剧观,富有批判意识,传承了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以及太康之英中的精华,形成了刘宋时代的文学高峰。“急以怨”正是这种独特风格的彰显。他的诗文风骨与文学精神,直接影响到齐梁时代的江淹,世称“江鲍体”。虽然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南朝文学精神的平庸化与世俗化,甚至本身也被误解为一种俗流,但其悲剧精神应当得到充分肯定。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这种反抗精神与悲慨诗学的重现。他们虽然对于鲍照的评价不高,但是其文学批评精神却与鲍照的风骨有相同之处。鲍照之文学精神与风格直接影响了刘宋年间的江淹,灌育了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李白的人格与文学精神,可以说,没有鲍照就没有李白。杜甫《春日忆李白》中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60](P52)杜甫所言,可以说是对鲍照的一种终极而公正的评价。因此,对王通评价鲍照的“急以怨”,应当加以全面的分析与认识。
[1] 张沛:《中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2][45][50]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13][46][47][48] 陈廷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5][15][16][17][20][22][25][26][27][28][29][30][31][32][34][35][36][37][38][44] 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许梿评选,黎经浩笺注:《六朝文絜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
[8][52]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
[9] 慕容真:《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0][11][57] 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2] 张少康:《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4] 钱博基:《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8][19][42] 逯钦立:《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21]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23] 许逸民:《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24]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39][41] 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3]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0]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7。
[43][49]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5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3][54][55]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56]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58] 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9]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0] 仇占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 张 静)
On Bao Zhao’s“Ji yi Yuan”
YUAN Ji-xi
(School of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e Liu Song dynasty poet Bao Zhao’s style of writing has been rated as“Ji yi Yuan”. But this literary style is always related to moral evaluation. Few scholars analyzed it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context and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Bao Zhao was isolated and repressed because he was born in poverty in the Liu Song dynasty. As he was full of ambition and dying to change his political situation, he was involved in a political dispute and got killed. Bao Zhao’s poems and proses had the tragic value of resistance. His“Ji yi Yuan” had positive meaning in restoring the prestige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style of writing was also a kind of resistance to Hypocritical society. We should, therefore, analyze and comment on his“Ji yi Yuan”practically and realistically.
Bao Zhao’s poems and proses;tragic destiny;the Southern dynasties;the value of resistanc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朝文学批评形态研究”(15BZW002)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以《登大雷岸与妹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