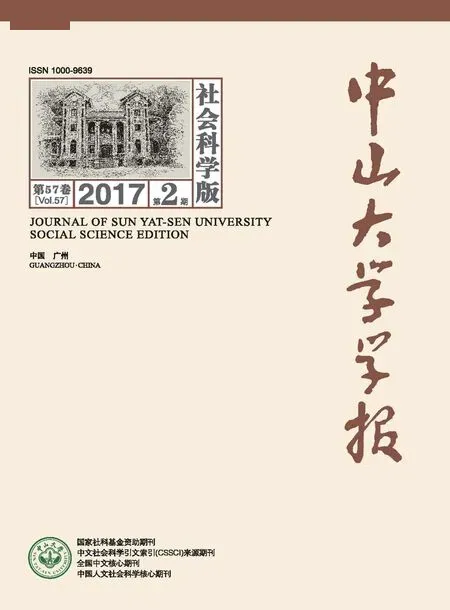“天”与晚宋政治*
——释宋理宗御制《敬天图》
方 诚 峰
“天”与晚宋政治*
——释宋理宗御制《敬天图》
方 诚 峰
宋理宗御制《敬天图》展现了宋代天理观、天人一理说在晚宋政治中的实践方式。《敬天图》的核心是作为道学修养工夫的敬与诚,而非普通的虔敬;该图于嘉熙三年(1239)秋明堂礼前抛出,又是为了以大礼之庆成证明其应天的效用。《敬天图》意味着理宗掌握了整套道学的话语,却抛开了工夫本身,将其中敬、诚这样的核心概念作为政治旗号,展现君主持敬、诚意以与天理合一的姿态,回应了士大夫修实德以应天的呼声,从而也成为理宗的一个保护壳。对《敬天图》的讨论也说明,南宋晚期所谓的“祈天永命”由仪式、实政、修德应天数个相互论证的层次组成。
南宋; 宋理宗; 敬天图; 天人关系; 祈天永命
“应天”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思想基础是天人关系论。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论的质变时代,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事应说”的排斥,即灾异与人事不是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回天意”的关键不在于以某种行为应对某种灾异,而是持续不断的恐惧修省,这可谓一种强化的“天人感应论”。其次,程朱“道学”鼓吹了一种全新的天观与天人关系论,即天不是有意志的、至上人格神的天,而是作为“天理”的天;相应地,“天人一理”“理一分殊”这种全新的天人合一理论成为标准的说辞,所谓“天地人物,万殊一实,其分虽殊,其理则一”*真德秀:《理一箴》,收入《性理大全书》卷7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1页。关于宋代的天人关系论,参见:[日]沟口雄三:《论天理观的形成》,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0—240页;[日]小岛毅:《宋代天谴论的政治理念》,收入《中国的思维世界》,第281—339页;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收入氏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31—280页;韦兵:《星占历法与宋代政治文化》,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60—198页。。
问题在于,天理观、天人一理说在政治上是如何实践的?这一问题应该放到晚宋政治中去考察,因为“晚宋”时期的特征之一即是道学成为正统*段玉明、胡昭曦:《宋理宗“端平——淳祐更化”刍论》,《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62—164页;胡昭曦:《略论晚宋史的分期》,《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106—107页。。而且,在晚宋,尤其是宋理宗赵昀(1224—1264在位)统治时期,一方面边备、楮币、民生、士风等诸多难题引发的焦虑、议论,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君臣对于天、天命的关切又与对上述种种困局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甚至被认为是破解难题的锁钥。因此,考察宋理宗时代的“应天”之举,可以有效地回答新的天观、天人关系论在政治中的实践问题。
本文的切入点是宋理宗御制的《敬天图》。《敬天图》作于嘉熙三年(1239),当时理宗即位已经16年了*王应麟:《玉海》卷56《乾道御制敬天图》,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072页;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卷14《敬天图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1052页。。该图一共12幅:
摘六经之训有关于省躬修行、弭灾兆祥者,亲御翰墨,纂为十有二图,系以圣制序跋,揭诸殿幄,仍命秘馆摹刻坚珉。*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卷14《敬天图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第1052,1052页。
根据理宗自己的说法,就是“取其关于天道之大,而有以启寅畏之衷者,每经表而出之,裒列成编,目之曰《敬天图》”*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行在所录》,《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20页。。即《敬天图》是宋理宗从六经(《易》《书》《诗》《周礼》《春秋》《礼记》)中摘录的被认为是最能说明“天道”的内容,加以抄录、张挂、刻石,作为自警的座右铭。不过,《敬天图》编纂于嘉熙三年何时并不明确,但臣僚云,《敬天图》完成后,“会季秋吉辛,肇禋重屋”云云*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卷14《敬天图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第1052,1052页。,说明正是当年九月明堂礼前夕*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33,嘉熙三年九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36页。。为何要在这一时刻抛出《敬天图》,这是本文要考察的一个重点。
《敬天图》并非理宗的创举,此前宋孝宗于乾道七年(1171)正月亦有御制《敬天图》。孝宗自己说,这是模仿流传已久的《无逸图》,“取《尚书》中所载天事,编为两图,朝夕观览,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图》”*《宋史全文》卷25下,乾道七年正月己亥条,第2109页。。孝宗和理宗的《敬天图》差别很明显:孝宗之图,只是摘自《尚书》,故仅有两图;而理宗之图,则是摘自六经,总为十二图。这不仅是取材范围的扩大,更意味着“敬天”内涵的变化。那么,理宗《敬天图》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这是本文要考察的另一个重点。
总的来说,本文首先考察《敬天图》出台的前因后果,以说明君主(理宗)如何在道学提供的新政治理论下实践。其次,《敬天图》一定程度可被视为当时君臣解决困局的总纲,其内容及其内在矛盾,也展现了南宋晚期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
一、理宗嘉熙三年之前的畏天与敬天
《宋史全文》的整理者注意到,该书的一大价值是详细地记载了宋理宗的“畏天”*汪圣铎:《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宋史全文》附录,第2955—2956页。。在诸多的畏天、敬天之举中,嘉熙三年的《敬天图》有何特殊之处呢?可以先看看此前理宗的一些举措。
如绍定四年(1231)九月丙戌夜,“临安火,延及太庙”*脱脱等:《宋史》卷41《理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5页。。这是前所未有的灾变,朝廷上下受到极大的震动,理宗自称:“累日哭于神御殿,省愆谢罪,伤痛罔极。”*《宋史全文》卷32,绍定四年九月丙戌条,第2668页。火灾后第四、五日,理宗接连下诏出钱、米赈恤百姓,且蠲临安府城内外之征一月;第六日,理宗下诏避殿、素服视朝、减膳、彻乐,且“内外臣僚士庶,咸许直言”*《宋史全文》卷32,绍定四年九月庚寅、辛卯、壬辰条,第2668页。。
如果按照宋代士大夫对“应天以文”与“应天以实”的区分*韦兵:《星占历法与宋代政治文化》,第182—185页。所谓文,就是指礼仪性的修饰,如避殿、减膳、虑囚等;所谓实,则是指实意、实德、实事,即有实际意义的政策调整、政治改革,以及君主的至诚反省。,上述措施多属于“文”,惟求直言略近于实。而在臣僚的应诏上书中,实政、实德才是核心关切,尤其是后者。如李鸣復在上书中认为“今日所以致天变者在君、相”,他批评理宗的“君德”,指其听政之暇即嬉游宴饮,经筵之余则狎近嫔侍,又不问民生国事,毫无恐惧修省之意。李鸣復甚至说:“明诏谓‘朕德不修’,信乎其不修也!”他建议理宗要“正心”,时存戒惧,“立于无过之地,而常励其有为之志”,然后以之正朝廷、百官、万民*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0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00—4001页。。
吴潜(1196—1262)的上疏也对当时的局势、理宗的君德进行了严厉的警告。他说,理宗自即位以来,灾变屡作,“愈变愈异,日迫日危”。这主要是因为今日局势危急,财政困难,吏治腐败,以至“生民熬熬,海内汹汹,天下之势,譬如以漓胶腐纸粘缀破坏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触之则应手堕地而碎耳”。他给理宗的建议是:
臣愿陛下斋戒修省,恐惧对越。菲恶衣食,必使国人信之,毋徒曰减膳而已;疏摈声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曰撤乐而已。阉宦之窃弄威福者勿亲,女宠之根萌祸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为尊严之区,而必敬必戒;以常舞酣歌为乱亡之宅,而不淫不泆。*吴潜:《许国公奏议》卷1《奏论都城火灾乞修省以消变异》(绍定四年),《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52—53页。
吴潜暗示,理宗耽于享乐、溺于声色、阉宦弄权,减膳、彻乐之举只是形式,而非真正的畏天。只有君德达到了“必敬必戒”“不淫不泆”,即“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军万姓知陛下有忧之之心”,然后与大臣改弦易辙、理政励俗,方能回天意、息天灾。先修君德、次理政事,这是吴潜的基本逻辑。
除了李鸣復、吴潜,其余如著作郎吴泳指出,真正的问题是四方之弊;通判镇江府蒋重珎则认为,火灾是因为君主与丞相(史弥远)之间的权柄关系倒置*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09,第4001页。。火灾当月,度支郎官王舆权进对,也说到:“今日灾变可谓极矣,惟有修德可以回天意。”理宗表示首肯*《宋史全文》卷32,绍定四年九月甲寅条,第2669页。。总之,面对绍定四年烧及太庙的大火,理宗的应对与臣僚的期待是有差距的。理宗采取的措施只是行故事,或曰“应天以文”;而一些臣僚则认为,应当修君德、理政事,尤其是前者。
端平元年(1234)正月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天象:
太史奏,元日立春,风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为兵象。*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简称《西山文集》)卷14《乙未正月丙辰经筵奏己见札子》,《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37页。
当时正是端平更化、革新弊政之时,理论上不但不应该有天变,而是应该“昊穹昭格,休应狎至”,但太史之占为何异于此?针对这个问题,真德秀的解释是:“意者应天之实,陛下犹有当尽者乎?”他所谓的“应天之实”,一方面指理宗是否真正践行了“毋不敬,思无邪”六字:“动静起居,真若神眀之在上,然后为敬之实。声色玩好,真若寇雠之必远,然后为无邪之实。”如果无法做到,那就是“虚文而非实也”*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4《乙未正月丙辰经筵奏己见札子》,第38页。按“思无邪,毋不敬”六字,是端平元年以前理宗御书于选德殿东西壁的座右铭。见《宋史全文》卷32,端平元年六月戊辰条,第2688页。。“应天之实”的另一方面,则指正在进行的端平更化于用人、听言、恤民、察吏皆有名无实,其余财用、楮币、边备等事则“皆未闻经理之实”。他建议:“愿诏三省、密院刷具绍定六年十月以后所降御笔,一一稽考,未行者趣施行之,行而未尽者更检举行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4《乙未正月丙辰经筵奏己见札子》,第38页。真德秀主要希望理宗以实际的修德、落实的政事回应天之警戒。
再如端平二年(1235)夏秋也出现了多次异常天象、气候*当年六月,“壬申,太阴入氐”,“庚辰,流星昼陨”,“己丑,荧惑入太微垣”;七月,“丁酉,流星大如太白”,“戊戌,太白经天”,“辛丑,流星昼陨”,“丙午,太白入东井”。以上见《宋史》卷42《理宗二》,第808页。当年八月,还有臣僚提到“积阴多霖”,说明有雨水之灾。见《宋史全文》卷32,端平二年八月乙未条,第2702页。。魏了翁(1178—1237)在端平二年七月就指出:“比日以来,天文示异,何其稠也?”他详述了当年六月、七月的天变及其占(覆军、阴谋、饥、逆、丧、兵等),接着又以应天之文、实区分为基础指出,寄希望于祈祷禬禳乃是浅见。魏了翁说,自己半年来接触的官民,凡“语及亲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来,则忧危之语日闻”,由此他知道“民未可以虚言动也”;既然民未可动,则“天决不可以虚文应也”*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0《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a—2b页。。即因为端平亲政未有实效,则所谓的应天也是有名无实。端平二年十二月,身为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江淮军马的魏了翁陛辞,又指出仅仅祝禳之仪无法息天怒,建议理宗“恐惧修省,以回天怒;恭俭笃实,以图民怨”*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7《陛辞奏定国论别人才回天怒图民怨》,第9a—b页。。
端平三年(1236)夏,以久雨祈晴于天地、宗庙、社稷及宫观、岳渎等处,又有雨血之异*《宋史全文》卷32,端平三年七月甲申、癸巳、乙未条,第2708页。。方大琮(1183—1247)于七月上奏札,他认为灾异的原因是“戾气流行”:妖星、大水、二相不咸、诸阃不协、叛兵等等灾变,“无非戾气之流注激射也”。而要消弭戾气,根本就在于消除理宗胸中“一念之歉”,也就是雪济王之冤、正史弥远之罪,因为这涉及到“理”(即“纲常”)的大问题,故而也就是弥乱之本*方大琮:《铁庵集》卷1《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札》,《全宋文》第321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40页。。同月,方大琮还上札“愿陛下正心以修德,大臣同心以修政”,他指出,理宗有耽乐、奢侈以及信任佞幸、宦官、小人等问题,若不能由这些问题入手,则祷祈仅是虚文,而惟有“改过徙义”“蚤定大本”“侧身修行”,“则弥灾销变之方,祈天永命之实,在陛下一念耳”*方大琮:《铁庵集》卷1《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二札》《八月分第一札》,《全宋文》第321册,第41—43,47页。。
在八月的奏札中,方大琮又对理宗说:“帝王治法,止一涂辙,持心身者乃所以持天下也。”也将矛头指向理宗的“溺宠浮费”问题。关于应天,他指出:“避殿虚文也,犹不即;求言典故也,亦未有闻……不知暗室谨独之地,一堂吁咈之间,其恐惧告戒为何如?”*方大琮:《铁庵集》卷1《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二札》《八月分第一札》,《全宋文》第321册,第41—43,47页。端平三年九月明堂大礼前夕,方大琮又请理宗“益充禁庭露祷之诚……检之身,揆之心”*方大琮:《铁庵集》卷1《九月分缴进札子》,《全宋文》第321册,第51页。。即应天之实的根本是理宗的正心修德。
端平三年九月,理宗行明堂大礼,却遇到了雷雨之异:
庚午,雷。辛未,祀明堂,大赦,雷雨。*《宋史》卷42《理宗二》,第811页。
庚午日是朝飨太庙的日子*《宋史全文》卷32,端平三年九月庚午条,第2708页。按,点校者当于第2708页末己巳条之前加“九月”二字。。即在明堂大礼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雷、雷雨。这对于理宗朝君臣是极大的冲击,故大礼结束后的第二天癸酉日,理宗即以“雷声骤发,上天示谴”令学士院下诏,采取避殿、减膳、彻乐、求言诸措施*《宋史全文》卷32,端平三年九月癸酉条,第2709页。。对此,方大琮先说灾异责在大臣“违天之政”;又补充说此为“王者奢淫乐游之过”,关键在于修省、发政施令*方大琮:《铁庵集》卷1《九月分第一札》,《全宋文》第321册,第51—53页。作者自注此札因改除未上。。
通过以上引述,可知自绍定以至端平,对于种种天变、灾异,理宗的祈祷、避殿、减膳、彻乐、求言、大赦等措置,在当时的一批士大夫眼中皆已成为应天之文,对于应天变、回天意而言是完全不够的。而士大夫眼中的应天之实则主要包括实政、实德两个方面。有些指责非常具体,关于君德,享乐、声色、宦官、佞幸是一再出现的主题。
就政事而言,理宗亲政以后表现出了明显的更革弊政之姿态,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端平更化却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端平二年正月,都省言:“端平改元,务革众弊,次第申明,条目详备。内而官府,外而监司、郡邑,故态未能尽革。”*《宋史全文》卷32,端平二年正月庚子条,第2696页。前引魏了翁端平二年七月言:“所接州县民吏,语及亲政,未有能深信者。”刘克庄在端平二年七月的札子中也说:
臣在田里,见癸巳十月以后所下诏令,虽樵夫野老,莫不欣跃鼓舞,曰:“太平旦夕可致。”及来行都稍久,目击近事,寝异初元……臣闻之道涂,皆谓陛下更化既久,责治未进,稍厌君子,复思小人。*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51《轮对札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44、2548页。
所谓“癸巳十月以后”,即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亲政以后。
又,端平三年秋,时为军器监丞的杜范在轮对时说:
自陛下亲揽大柄,召用正人,天下延颈企踵而望更新之治,且两年于此矣。而纪纲之荡废者未修,政事之苟玩者未饬,风俗之颓靡者未振,气象之凋残者未复。楮轻物贵,国匮民贫,军伍干纪而远迩效尤,边备单虚而中外凛凛。弊端纠结,有不可爬梳之势。坏证捷出,有不可援持之扰。*杜范:《清献集》卷5《军器监丞轮对第一札子》(端平二年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640页。
端平三年,右正言方大琮也说“更化三年,病源故在”*方大琮:《铁庵集》卷5《辞免御笔除右正言申省状》,《全宋文》321册,第78页。。七月,臣僚进对:“更化愿治,三年于兹,而天变见于上,人心摇于下。”理宗的回答是:“比年以来,中外多故,朕未尝一日不忧惧。”*《宋史全文》卷32,端平三年七月乙巳条,第2708页。可见君臣对于更化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异议。
嘉熙(1237—1240)这个年号,就是在端平更化失败的背景下出现的。端平三年十一月,理宗诏议改元,“以示作新之意”,令有司详议;十二月最终下诏改元“嘉熙”*《宋史全文》卷32,端平三年十一月戊辰、十二月甲辰,第2710、2712页。。嘉熙改元诏被误作淳祐(1241—1252)改元诏,保留在《宋会要辑稿》当中:
《春秋》内夏外夷,寔重三正之统;王者改元立号,每因万国之心。朕猥以眇躬,嗣膺大历,践祚十有三载,若涉春冰;临朝一日万机,靡遑旰食。暨更张于鸿化,期开际于多艰。厉精虽勤,计效愈邈。仰而观诸天运,未臻协气之横流;俯而验诸人情,但见浇风之华竞。惟口兴戎而民生匮,藩身以货而吏道衰。疆场骚然,戎狄惊甚。
必欲庶邦之靖,必图百志之安,若非宪法于前猷,何以作兴于群听。重念仁孝两朝之盛,蔼如唐虞成周之和。节用爱人,此嘉祐所以永天命;经文纬武,此淳熙所以恢圣谟。用表新年之名,以达期治之意,其以明年正月朔为(淳祐)[嘉熙]元年。*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4之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59—1960页。
诏书明言“践祚十有三载”[按,理宗于嘉定十七年(1224)登基,至端平三年(1236)恰13年],又言“节用爱人,此嘉祐所以永天命;经文纬武,此淳熙所以恢圣谟。用表新年之名,以达期治之意”,所以此诏肯定是端平三年改元“嘉熙”之诏,而非如《宋会要辑稿》所云淳祐改元诏。
这篇诏书,以法祖宗(仁宗嘉祐、孝宗淳熙)的旗号,表现出了强烈的改弦更张之意。这种作新之意,又是以承认既往的失败为前提的:“暨更张于鸿化,期开际于多艰。厉精虽勤,计效愈邈。”这主要是指“端平更化”及其失败。
因此,当理宗的统治进入嘉熙年间,正值一个相当微妙的时刻。自宋宁宗嘉定(1208—1224)以后,金朝的衰落与灭亡,蒙古的崛兴与征服,宋朝内部的种种危机,使得宋人意识到当时正处于所谓“天命离合之机”*真德秀:《西山文集》卷3《直前奏札》(嘉定六年十月十一日),《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669页。、“天命未定之时”*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3《召除户书内引札子一》,《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22页。。邓小南指出:“祈天永命”口号的流行,正是万般无奈之下冀求有所奋起的反映*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488—494页。。到底应该如何应天?在嘉熙以前,如前所述,理宗所采取的“应天之文”显然无法满足士论。而在“应天之实”上,所谓的“端平更化”虽可谓以实政应天,却同样无果而终。在此情形下,理宗面临的挑战一是如何继续传达更革、调整的姿态,此谓以实政应天;二是如何在“修省”以应天上有所动作?关于第一点,学者已经注意到,理宗亲政以后,其变革贯穿于端平、嘉熙、淳祐年间(1234—1252),历时约20年*段玉明、胡昭曦:《宋理宗“端平——淳祐更化”刍论》,《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第155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理宗所谓的变革,并非“一个”连贯的过程,而是一再重复的主题。刘克庄在淳祐十一年(1251)说,理宗有端平、嘉熙、淳祐、乙巳(淳祐五年,1245)、丁未(淳祐七年)五变*刘克庄著,辛更儒校笺:《刘克庄集校笺》卷52《召对札子》(辛亥五月一日),第2576—2577页。。杜范亦说,理宗有端平、嘉熙、淳祐三改*杜范:《清献集》卷13《相位五事奏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713页。。又,理宗宝祐六年(1258)十二月诏改元开庆,诏书亦表达了更化变通之意:
然察文审己而庶政靡齐,务本重农而群生寡遂,朝纲隳而积玩,吏习狃于怀私,国势仅定而未强,边徼多虞而未靖……欲通变于宜民,乃取新而凝命。若稽成宪,遹广骏声,法艺祖之宏规,混车书之一统;踵仁祖之盛际,致朝野之咸和。爰易嘉名,以兴嗣岁,导迎善气,振起群心。*《宋史全文》卷35,宝祐六年十二月丙子条,第2870页。
诏书先是陈述了庶政、民生、朝纲、吏治、国势的困局,然后也是在法祖宗(太祖开宝、仁宗庆历)的旗号下,表达了祖述变通之意。因此,“更化”成为理宗朝政治中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是因为所谓“更化”(其实主要表现为变更宰执)一再陷于失败,而“应天以实”又要求所谓“实政”,即不断的“更化”。
那么,关于第二点“修省”以应天,理宗又应该如何做呢?理宗的《敬天图》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二、《敬天图》的内容与主旨
如何用《敬天图》这样的经典摘编表示“敬天”呢?不妨看看《敬天图》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完整的敬天十二图今已不可得而见,但从御制《敬天图序》仍可了解其大概*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行在所录》,第3420—3422页。以下所引《敬天图序》皆出此,不再一一注明。亦参见王应麟:《玉海》卷56《嘉熙敬天图》,第1072页。。而要理解其主旨,又必须结合朱子学对相关经典的解释。
《敬天图序》开篇云:
朕观书契以来,人极茂建,圣贤大训,布在方策,其言治国平天下之道,无出于六经,而求之六经之要,一日不可违者,其惟天道乎!大概《易》明其理,《书》正其事,《诗》通其情,《周典》备其礼,《春秋》志其变,《记礼》则杂纪焉者也。人主知天之当敬,视六经格言如金科玉条,罔敢踰越,则逸德鲜矣。
人君之所以要以六经格言为金科玉条,是因为六经言“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六经“治道”中最为根本的内容,则是“天道”。这样的话,“敬天”自然也就是为政的核心内容:
仰惟祖宗丕灵,承帝事,抚有方夏,列圣垂谟,无一息不以敬天为心。国史登载,难以殚举。然未有不本于六经之旨。朕以寡昧,寅奉燕诒,惧弗克钦若眷命,万几之暇,稽式古典,爰以已意,取其关于天道之大而有以启寅畏之衷者,每经表而出之,裒列成编,目之曰《敬天图》。庶几朝夕观览,对越鉴临,以自警省云尔。
即“敬天”的关键是“本于六经之旨”,因此《敬天图》的主旨就成了:六经各自从什么方面阐明了天道,尤其是“关于天道之大而有以启寅畏之衷”者?《敬天图序》对六经一一做了简要的说明。
1.《周易》
关于《周易》,《敬天图序》曰:
《易》六十四卦,大象之义,各有攸属。自出治而言,则谓之后;自定位而言,则谓之上;自创法而言,则谓之先王;自继体而言,则谓之大人;余则总而谓之君子。皆主于人君而言也。卦必有象,象必有义,体而行之,人君能与造化同流者,其以此耳。
《敬天图序》所言重在《大象传》,认为它是专门针对君主的经典(“皆主于人君而言”)。对于人君来说,如果能领会、践行所谓的“大象之义”,就能做到“与造化同流”。
“义”是什么呢?《敬天图序》说:
然他卦大象皆著本卦之名,惟乾独不称乾,而止曰“天行健”,而以“自强不息”归之君子。呜呼!此天德也!人君实以之。君即乾,乾即天也。人君动静语默,政化云为,无一而非乾。以至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皆此物也。而其要则自“闲邪存诚”始。然则求敬天于《易》,岂不尤邃于五经欤!
对于君主来说,最核心的是“乾”卦之义:“君即乾,乾即天也。人君动静语默,政化云为,无一而非乾。”这样的话,所谓的“与造化同流”就是与天合,即“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按照朱熹的解释:“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朱熹:《周易本义·周易文言传第七》,《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就是或生而知之,先天合理;或学而知之,后天知理。总之,目标在于与理合,即与天合。
《敬天图序》指出,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闲邪存诚”。按,此语出自《周易·文言》,程颐在“听箴”中引用了此语,将其作为“复性”的重要修养工夫:“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程颐:《四箴·听箴》,收入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文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89页。
朱熹对“闲邪存诚”的解释是:“‘无斁亦保’之意。”*朱熹:《周易本义·周易文言传第七》,《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147页。“无斁亦保”出自《诗·大雅·思齐》称颂文王之德:“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朱熹解释云:
雝雝,和之至也。肃肃,敬之至也。不显,幽隐之处也。射,与“斁”同,厌也。保,犹守也。言文王在闺门之内则极其和,在宗庙之中则极其敬。虽居幽隐,亦常若有临之者;虽无厌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纯亦不已盖如是。*朱熹:《诗集传》卷16,《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664页。
文王之德不但“纯”,而且“不已”,即不虚假、不间断。下文将会谈到,这就是朱子学中重要的概念——“诚”。“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所谈论的正是这一意思:虽然独处,仍然像有神临视;虽然并无倦怠,仍然坚持修德不懈。
总之,《敬天图序·周易》认为,君主与理合即是与天合,达到此境界的途径在于“诚”。这就说明,所谓“敬天图”之“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虔敬,而是已经被转化为道学体系中的工夫论。下面还会提到这一点。
2.《尚书》
关于《尚书》,《敬天图序》曰:
若昔先王盛时,君臣上下相与儆戒,兢业于敬天一言,最为深切著明,皆聚此《书》。今可考也,曰“天无亲”,曰“天难谌”,曰“天明畏”,曰“天命不易”,凡所以推言天命靡常之理,言言至到,何凛乎其严耶!惟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而能疾敬厥德,则可以祈天永命,无疆惟休矣。不然,则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岂不甚可畏哉。今所纂辑,取于《书》者尤详,噫!肆予曷敢不敬。
《尚书》的作用,在于提供了圣主贤臣“敬天”的实例,特别是其中对天命不常一再强调,故《敬天图》“取于《书》者尤详”。这大概也是之前孝宗《敬天图》独取于《尚书》的原因所在。
强调天命靡常,是为了人君“能疾敬厥德,则可以祈天永命,无疆惟休矣”,即通过“敬德”来达到永续天命的目的。按,这句话的出典是《尚书·召诰》中召公的告诫之辞,敬德、祈天永命在《召诰》中多处出现。朱熹将注释《尚书》的任务交给了蔡沈,故考察蔡氏对于《召诰》的解释,可以更好地理解《敬天图序》的寓意。
召公之辞有云:“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针对这句话,蔡沈的解释是:
商受嗣天位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国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无穷之美,然亦有无穷之忧。于是叹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盖深言不可以弗敬也。
又按,此篇专主敬言,敬则诚实无妄,视听言动一循乎理,好恶用舍不违乎天。与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于此哉!伊尹亦言“皇天无亲,克敬惟亲”。敬则天与我一矣,尚何疏之有。*蔡沈撰,朱熹授旨,严文儒校点:《书集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186页。
这两段中,第一段是文意的疏通,指出了殷周革命是天命不常的实例,必敬乃能保天命;第二段是蔡沈对于整个《召诰》主旨的理解:敬。由“敬”而达到“诚”(即真实无妄),能举动循理、与天合,这样君主才能保有天命。
蔡沈在《书集传序》中说,他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二帝三王之心”,因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因此如果能明了二帝三王之心,那么其道、其治就可得而知了。他又说:“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蔡沈撰,朱熹授旨,严文儒校点:《书集传》卷首《九峰蔡先生书集传序》。所以,无论是“敬”还是“诚”,都是圣人用以使“心”纯明的方法,这就是所谓“严其心之所自出”,也就是敬天。
通过蔡沈的解释,可以理解《敬天图》摘录《尚书》的立意:君主保有天命的根本是与理合,即与天合;而君主合理/合天的根本途径又在于敬、诚,这都是所谓的圣人明心之法。这样的话,《敬天图》中就出现了道学工夫论中另一个核心概念“敬”。
3.《诗经》
关于《诗经》,《敬天图序》曰:
《诗》者动天地,感鬼神,所以通幽微之情,而穷交际之理者至矣。
此言《诗经》“穷交际之理”,即指天人交际而言。《敬天图序》接着说:
方商周盛时,上而卿大夫士,近而侍御臣仆,下而比闾族党,无不知天道而识天象,忧深思远,指事引类,未尝为迫切之词、骇异之语也。方其神祇祖考,燕衎和乐,而隐然戒惧之意寓焉,《我将》之诗是也。方其旱暵为虐,遇灾而惧,而恻然哀矜之情发焉,《云汉》之诗是也。至于“陟降左右”、“缉熙敬止”之类,则又非可以浅近观矣。端居而诵,澡心以思,玩味而紬绎之,其不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乎!
诗为何而作?《敬天图序》认为,商周隆盛之时,上下之人皆能了解天道、识别天象,其思虑深远,因事而发,故有《诗》。如有祭祀、宴乐时的“隐然戒惧之意”,也有因灾异而引发的“恻然哀矜之情”。不过,“陟降左右”“缉熙敬止”两个例子,更说明了《敬天图》通过《诗》要表达的主题何在。
“陟降左右”“缉熙敬止”皆出自《大雅·文王》。关于此诗,朱熹特有针对汉儒的批判:
文王之德,上当天心,下为天下所归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则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继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汉儒惑于谶纬,始有赤雀丹书之说,又谓文王因此遂称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谓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众人之心而已矣。众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于一,而无一毫私意杂于其间,则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为归,则天命将安往哉!*朱熹:《诗集传·诗序辨说》,《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391页。
汉儒认为,赤雀衔丹书乃是周文王受天命之祥瑞,但朱熹批判了这种神学式的天命观——所谓的天乃是理。如果众人之心皆归于一(归于文王),那也就是理之自然,也就是天命所归了。所以说,周文王的天命不是来自祥瑞,而是来自于理。
“陟降左右”上下文为:“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仍然是称赞文王之德的,周之子孙之所以能君有天下,是因为文王之神在天,居上帝之左右*《诗集传》卷16,《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652,653页。。
“缉熙敬止”上下文为:“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朱熹的解释是:
穆穆,深远之意。缉,续。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语辞……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孙子观之,则可见矣。盖商之孙子,其数不止于亿,然以上帝之命,集于文王,而今皆维服于周矣。*《诗集传》卷16,《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652,653页。
按照朱熹的解释,“缉熙敬止”的意思就是不已其敬,不间断的敬。为什么商人失天命而周文王能得天命呢?关键还是在于周文王深远之德,能“不已其敬”。
由此可知,《诗经》虽似因其体裁、题材而显得驳杂,但《敬天图序》指出,其有关天道之大者在于二:一是天即理,天命即天理之自然;二是得天命的关键在于“敬”。这就又与前述《周易》《尚书》保持了一致。
4.《周礼》
关于《周礼》,《敬天图序》曰:
河汾王通尝谓:“如有用我,则执《周礼》以往。”且重发“《周礼》敌天命”之叹。盖其为书大纲小纪、详法略则,粲然靡所不载。玉帛牲器之用,车旗冕服之制,豆笾罍爵之陈,钟鼓匏管之奏,品节度数,必加详焉。至于象纬之考察,眚灾之抑损,亦莫不隶之司存而不敢慢。凡所以接三才之奥,通幽明之理也,圣人于此,岂徒从事于文物典章之饰于外者而已乎?要必有为之本者矣。不然,则《周礼》特一书耳,又安能敌天命而与之并存哉!
《周礼》的主要内容是纲纪、法则,尤其详于那些与“应天”(祭祀、观天、应灾等)有关的设置,《敬天图》采于《周礼》的可能也主要是这些方面的内容,故开篇有“《周典》备其礼”之语。
这些典章制作是有所本的。按王通之言见于《中说》卷8:
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先师,谓孔子也。定礼乐,时极周道而已。)*④ 张沛:《中说校注》卷8《魏相篇》,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8,209页。按,括号中注为阮逸所作。
“子”即王通,其言《周礼》中的具体纲纪法则,乃是王道/周道的体现。而所谓“王道/周道”又是超越历史的:
子曰:“《周礼》其敌于天命乎?”(周公典礼与天命齐其长久,故曰敌也。)④
这些典礼之所以能超越历史而与天命齐长久,就在于《敬天图序》所说的,乃因这些文物典章本于“接三才之奥,通幽明之理”,也就是本于明“理”。
《敬天图序》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符合朱熹的观点。在宋代,已经有不少人怀疑《周礼》的可靠性,但朱熹认为,《周礼》虽然不是周公的亲笔、细节有可疑,但规模、大纲却出自周公*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6,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203—2204、2210页。,他说:
如《周礼》一书,周公所以立下许多条贯,皆是广大心中流出。*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3,第850页。
一部《周礼》却是看得天理烂熟也。*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90,第2291页。
圣人漉得那天理似泥样熟。只看那一部《周礼》,无非是天理,纤悉不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19,第2868页。
《周礼》的内容如何与“敬天”发生联系?不但因为《周礼》载有具体的应天之典礼,更是因为这些具体的典礼乃是王道的体现,是本于“理”的制作,故而具有超越历史、与天命齐长久的性质。
5.《春秋》
关于《春秋》,《敬天图序》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书辰星风电之变,水旱霜雹之灾,螽螟蜮蝝之害,靡不毕备,而于日食之书尤详且密,传者间未免传以列国证应之说,遂使后之星翁历家分诿于所主方域,以启时君之玩心,此则非《春秋》本指也。
《敬天图序》认为,将天变与固定的方域对应起来(分野说),反而会让其他君主有玩天之心。所谓“玩天”,理宗淳祐末所编的类书《群书会元截江网》也有专门的阐述:“谓某事必有某证,某证必应某事,求之而不合焉,则玩心不能不生,此启人主玩天之心。”*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卷3《敬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第39页。按,《群书会元截江网》编纂年代不详,《四库全书总目》以为“首题太学增修,中有淳祐、端平年号,盖理宗时程试策论之本也”。此论甚是,检此书提及的庙号最晚为宁宗,年号最晚为理宗淳祐(1241—1252),卷3所录策问又出自淳祐十年(1250)榜,故推测此书当成于理宗淳祐末。即天变与人事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是难以确定的,正是这种不能落实的事应,可能引发君主的玩天之心。此种“事应说”与《敬天图序》所指责的“分野说”,都是机械的天人感应论。
《敬天图序》接着说:
《春秋》一统之书也,方诸侯专恣,王室既卑,麟笔褒贬,岂独以礼乐征伐关于人事者属之周?而天变之特书屡书,皆系之王,至于书王必曰“天王”,其所望于周者甚深。固曰,诸侯虽无周,而天命未改,承天从事,周之人主不可不任其责也。以周之无政,而圣人犹拳拳焉,南面而治天下者,其可忽诸!
这是针对分野说而言的,天变系用以责周之王室,因为天命仍属周,故周天子仍然要担负起责任。这也是为了说明,对宋而言天命亦未改,应时刻承天从事。
针对事应说,《群书会元截江网》云:
大抵天之于君,父之于子也,父有震怒,为人子者事事当修省,不可以为某事当修省,而某事不必修省。天有谴告,为人君者事事当修饬,不可以为某事当修饬,而某事不必修饬也。今焉汉儒之论,乃以貌作恭。*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卷3《敬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第39页。
此处把天人关系比作父子关系,主要是为了说明:人君不要于某一事上应某一天变,而是应该时时刻刻、无条件地承担责任,修省其身、修饬政事*关于玩天、敬天的区别,参见韦兵:《星占历法与宋代政治文化》,第175—181页。。
因此,《敬天图》关于《春秋》的说明,否认了机械的天人感应说,但并没有消解天人感应本身,而是把天人感应作为推动人君时刻、持续修省的压力、动力。如本文开篇所说,这一点正是宋代天人关系论的特色之一。在“强化”天人感应的同时,《敬天图序》亦确认了宋朝的天命。
6.《礼记》
关于《礼记》,《敬天图序》曰:
《记礼》一经,冠之以“毋不敬”之辞,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者,惟以“敬”之一字而已。或谓《月令》出于吕不韦之手,未免滞而不通。然奉时承天之义,虽细微必谨,言固不可以人废也。
这一段将“敬”作为礼仪的核心精神。《敬天图序》接着说:
至若《中庸》《大学》之书,一则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再则曰“惟命不于常”,援《诗》《书》以明义理之正,而其本则俱切切于谨独之训。诚之不可揜,必戒于不睹不闻;诚之毋自欺,必严于所视所指。二书之旨深矣,可不惧哉!
这一段中,对于《礼记》的《中庸》《大学》章,《敬天图序》特意将“诚”作为核心提了出来。下面对这一段略作解释。
按,“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系《中庸》第二十六章引《诗·周颂》:“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朱熹《中庸章句》指出,《诗经》此章言天道;对于这句诗,他说:“引此以明至诚无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纯则无二无杂,不已则无间断先后。’”所谓“至诚无息”,即“无虚假,自无间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5,25,32,31,17页。。在《诗集传》中,朱熹也说:“言天道无穷,而文王之德纯一不杂,与天无间。以赞文王之德之盛也。”*《诗集传》卷1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723页。总结而言,“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句说明的是:文王之德与天道一致,纯且不已,即无虚假、无间断,也就是所谓的“诚”。
按,“诚之不可揜,必戒于不睹不闻”出自《中庸》第十六章及首章。《中庸》第十六章有“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一语。朱熹此章将“鬼神”解释为“气”(阴阳之气),他对“诚之不可揜”一句的解释是:“诚者,真实无妄之谓。阴阳合散,无非实者。故其发见之不可揜如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5,25,32,31,17页。即气的运行(阴阳合散)及其显现是必然的。这里还必须结合朱熹对《中庸》二十章“诚”的解释,他认为“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5,25,32,31,17页。,云: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5,25,32,31,17页。
“诚”是真实无妄之义,是天理本身的状态。但只有圣人之德是“浑然天理,真实无妄”的,即与天理是一致的;而一般人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所以必须经过一个“诚之”的过程。如真德秀所说:“诚者天道,本乎自然。诚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与人,其本则一。”*真德秀:《西山文集》卷33《思诚箴》(为陈若虚作),《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317页。
如何“诚之”呢?《中庸》首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就是所谓的“存养省察之要”。对于“不睹不闻”,朱熹的解释是:
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5,25,32,31,17页。
因此,所谓的“必戒于不睹不闻”目的在于“存天理之本然”。相比于“慎独”是为了“遏人欲于将萌”,“必戒于不睹不闻”是更为根本的“未发”工夫,属于“体统”“大纲”,也可以作“持敬”解*《朱子语类》卷62,第1499、1502、1503、1505—1506页。。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敬天图序》先选择了这一句。
“诚之毋自欺,必严于所视所指”一句,来自《大学》传之六章,后半句是《大学》引曾子之语。这句话的主旨就在于作为已发工夫的“慎独”,朱熹说:
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7页。
对于曾子之言,他认为:“言虽幽独之中,而其善恶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上文所说的“必戒于不睹不闻”是指自己所不睹不闻,是未发工夫;而这里的“慎独”则是指他人所不知而自己所独知者,属于已发工夫。
因此,《敬天图序》关于《礼记》凸显了如下三点:第一,“敬”是礼仪的核心精神;其次,所谓君主“纯于天道”,即“至诚无息”,也就是与天理一致,亦无间断;第三,“诚之”是包含了已发、未发的修养工夫。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敬天图》所谓的“天”,是作为道学之天理的天;“敬”是作为道学工夫的敬。
综观理宗《敬天图序》对各经的说明可知:首先,《敬天图序》所谓的“敬天”不再是敬畏具有神格意义的上天,而是指与天理合,达到无虚假、无间断(诚)的境地,这才是得天命、保有天命的关键。其次,“敬天”的关键之途在于道学所提供的功夫论,《敬天图序》将敬、诚作为关键词提了出来。而如果考虑到“敬”与“诚”这两个概念在朱子学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敬与诚在朱子学的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钱穆先生有《朱子论敬》、《朱子论诚》二文缕述这两个概念,见钱穆:《朱子新学案》(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99—439、515—535页。关于“敬”,亦参看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7—180页;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2—407页。关于“诚”,亦参见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1996年,第69—72页。两者之中,朱熹对于“敬”尤其看重,认为是“圣门第一义”、“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根据钱穆先生的梳理,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涵义:一曰略如畏字相似;二曰收敛其心不容一物;三曰随事专一,又曰主一之谓敬;四曰随事检点;五曰常惺惺(醒觉)法;六曰整齐严肃。作为修养方法,敬应该是贯穿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所有节目。关于朱子的“诚”,钱穆先生指出,也是一个贯穿内(实然之心,心之诚悫)、外(实有之理,天理之实然)的概念。人之自修,当本诚悫之诚以达于实理之诚;人之为学,必求知于实理之诚以完善诚悫之诚。如此工夫所到,内外二者应是一而非二,即心与理一。,可知《敬天图》的主旨,是它用了道学的话语,重新阐释了君主“敬天”的本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传统的敬天、畏天,被转化为一个道学的内向修养工夫问题。
如此回头审视端平元年(1234)理宗御书于选德殿之柱的座右铭“思无邪,毋不敬”*《宋史全文》卷32,端平元年六月戊辰条,第2688页。,可知其与《敬天图》是一脉相承的——此六字,一指敬,一指诚。《朱子语类》载:
程子曰:“思无邪,诚也。”诚是实,心之所思,皆实也。
林问“思无邪”。曰:“人之践履处可以无过失,若思虑亦至于无邪,则是彻底诚实,安得不谓之诚!”*《朱子语类》卷23,第543、544—545页。
《朱子语类》中类似的话很多,不赘述。因此,端平初的“思无邪,毋不敬”六字座右铭,其实已经在使用道学的术语,将敬、诚二字作为为政之道的核心。
又,宋理宗曾被赐名“贵诚”,但“诚”字在理宗朝是不必避讳的:
礼部尚书魏了翁进读《大学》,因奏:“‘诚’字虽系藩邸旧名,考之故事,未尝偏讳。盖此字纪纲斯世,而科举文字皆避,场屋未免疑惑,乞圣语许免回避,以广陛下谦虚之意。”上曰:“自不必避。”
此事发生在端平二年闰七月*《宋史全文》卷32,端平二年闰七月己巳条,第2701页。。又,端平三年四月,理宗与臣僚有一番对话:
(臣僚)又奏:“人主一心,攻之者众。”
上曰:“常持敬心,则不为外物所移。”*《宋史全文》卷32,端平三年四月己亥条,第2706页。
由此可知,亲政时的理宗对于道学的术语、观念已经非常熟悉,尤其是敬、诚二字已经被提到政治的纲领性地位。因此,宋理宗嘉熙三年明堂礼前抛出御制《敬天图》,是在此基础上的铺陈,可谓水到渠成之事。
总而言之,嘉熙三年御制《敬天图》与此前理宗的一些行为、言论,共同构成了他修德以应天的实践。这些言行以及《敬天图》的共同旨趣,就是在道学的语境中回答什么是修德之实——敬、诚,这就是在追求与天理合,就是敬天,因此也就能保有天命。
三、《敬天图》的反响与困境
理宗《敬天图》出台后,成为当年秋天上舍试策之主题,该题是程公许(1182—?)所拟*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14《试上舍生策题》(己亥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1049页。。在策题开头,程公许以汤、武“所御器物咸有铭”说明《敬天图》的意义:
古先哲王,明睿生知,道德纯备,一动息一颦笑无非天理之流行,而戒谨恐惧,其严若此。岂人心之易于弛,虽圣人亦不可一日而忘其规警耶。
这是一套相当道学化的表述,即《敬天图》意在“规警”,使得人心不弛,与天理合。
当涉及《敬天图》时,《策题》说:
顷又摘六经之有关于天道者,章分句析,亲御翰墨,为敬天十二图……季秋吉日辛卯,九筵穆卜,先期申警,蔬食斋居,言款清宫,冻雨飘洒,祼飨世室,阴凝未舒。逮羽卫导行,玉辂趣驾,云翳一扫,晴景四开,都人骈首以观天仗之森严,天颜之肃穆,而后喜可知也。丙夜禁门启钥,臣工骏奔,上端冕入就次,月星明朗,乐舞和愉,穹示顾歆,克竣熙事。颁贺肆赦,典仪备举,质以前三岁烈风雷雨之变异,思成之庆,宁易致耶?
在这里,程公许特意提到了嘉熙三年九月的明堂大礼*《宋史全文》卷33,嘉熙三年九月己卯、庚辰、辛巳条,第2736页。按,大飨明堂在辛巳日,《策题》云辛卯日,误。,将其与三年前即端平三年的明堂礼进行了对比:三年前是“烈风雷雨之变异”,今年则是“晴景四开”、“月星明朗”,一派祥和的景象。
这种差异的关键就在于《敬天图》的出台,程公许反问:
岂《敬天图》之作,忱念孚格,不专于牺牲玉帛之荐乎?
即这不仅是祭祀的结果,更是因为《敬天图》表达的“忱(诚)念”信至天。程公许在当年冬天所上的《敬天图箴》中也说*程公许于嘉熙三年十一月除著作郎,同月兼直舍人院。见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8《官联二·著作郎》,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86页。:
会季秋吉辛,肇禋重屋……嘉气布濩,欢声翕合。较以岁丙申雷雨之异,兹为庆成无疑矣。呜呼!敬与肆一念之分,而影响之不爽若是,天远人乎哉!*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14《敬天图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1052页。
两次明堂,一次天变,一次庆成,原因就在于“敬与肆一念之分”,即《敬天图》之“敬”产生的效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理宗要在嘉熙三年明堂礼前抛出《敬天图》——因为这是端平三年后的第一次明堂大礼,正可以用庆成来展现《敬天图》的格天之效。
程公许《策题》与《敬天图箴》的上述表述,一方面充斥了鲜明的道学术语,准确地传达了《敬天图》的主旨;另一方面,也充满了明显的天人感应色彩。而且,在《试上舍生策题》中,程公许还提到,天之于君,就像父之于子一样,天变、天怒是天对君(父对子)的训诫、爱护(用“训告保惠”一语,典出《尚书·无逸》)。这和前引《群书会元截江网》的观点一致。这说明,在道学“天理说”成立的同时,天仍然保留了其人格神的特色*田浩(Hoyt Tillman)指出,朱熹的“天”概念仍有人格化、有意志的一面。见《跟随史华慈老师研究宋代思想史:论朱熹和天》,收入许纪霖、朱政惠编:《史华慈与中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158页。,作为一种督促力量而存在。
学者还指出,宋代确立了以气化论为基础的新天人感应理论,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道德反省,促成现实改革*韦兵:《星占历法与宋代政治文化》,第172—175页。。此说甚是。按文天祥在度宗朝经筵讲解《敬天图》摘录于《周易·贲卦》的一段话,然后发挥说:
盖常变虽丽于天,而所以常变则系于时。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时世者也,故天文顺其常,则可以知吾之无失政,一有变焉,咎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镜也,观镜可以察妍媸,观天文可以察善否。*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11《熙明殿进讲〈敬天图·周易贲卦〉》,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265页。
文天祥没有把天比作父,而是认为“天一积气耳,凡日月星辰、风雨霜露,皆气之流行”;所谓“天文”,就是“流行发现处有光彩”;天文的顺逆休咎,则“莫不以人事为主”。以“气”及其运行为媒介,天变就可以作为人君失政、失德的参照物,说明了持续施政、持续修德的必要性。
因此,无论是父子的比喻,还是气之流行的理论,都是为了将天人感应说与天理说统合起来。理解了这一点,就更可以体会程公许在《策题》接近末尾的一段话:
谛观敬天之图,心画谨严,先后如一。退朝燕坐,声色玩好,决莫能为德性之移。而道途窃议,尚有过于责难者。“皇自敬德”,要不必以人言为忤,而益当以高明光大加之意。“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无徇其名而既其实,则怨汝詈汝,其有补于学问者不既多乎?天不远人,随念昭格,圣学就将而不已,圣德日新而又新,易危为安,用祈天永命,岂不同此一机耶?
这里提到“而道途窃议,尚有过于责难者”,说明当时臣僚颇有对理宗德性的批判。而面对这些责难,君主应该做的,一是“皇自敬德”;二是“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典出《扬子法言》),即知而行之。
“皇自敬德”典出《尚书·无逸》周公言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行为:“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这里“皇”作“大”解,孔颖达疏谓:“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骂詈汝。既闻此言,则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17《无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39页。主要是称赞明君“宽弘之若是”。而蔡沈《书集传》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更为强调其修身的层面:“反诸其身,不尤其人……不暇责小人之过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蔡沈:《书集传》卷5《无逸》,第206页。
总结程公许的言论:现实政治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君主之修德口号能否落实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保持天与人事之间的感应是必要的,它能推动君主的持续努力——“皇自敬德”。特别要注意的是,“敬德”与“皇自敬德”,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是再度强调而已。因为敬与诚本身就包含了持续不断之意。这也说明,无论臣僚对于《敬天图》能否落实有多么怀疑,所能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过是复述《敬天图》的逻辑。
这种论调是相当普遍的。如嘉熙三年著作郎李昴英(1201—1257)的奏札*李昴英:《文溪存稿》卷6《嘉熙己亥著作郎奏札》,《宋集珍本丛刊》第85册,第475—476页。,先是说近年以来风、火、雹、旱、蝗、海潮、天变种种灾异,说明上天对人君不再是仁爱而“告戒寓于灾异”,是“仁爱之已极,且转而为震怒矣”,他指出:“敬天之图,未必见于躬行。”那么怎么落实呢?李昴英仍然认为,关键还是在诚、敬:
夫天人之际,本无二致,人君之心,当主一忱,积此忱以消变,推此忱以受言,上下感通,悉本乎是……臣愿陛下充此悔而持之以敬,不容一息之怠荒……陟降常在于左右,戒惧如对于睹闻。以吾之心,合天之心,庶可以转祸而福矣。
“忱”即诚。很显然,李昴英的解决策略并未超出于《敬天图》,也不过是再度强调诚、敬,以达到人心与天合的境地。
再如嘉熙四年(1240)杜范入见,缕述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和李昴英类似,他认为天心自即位初时的仁爱已转为当下之怒,形势极其危急。他说:
陛下敬天有图,旨酒有箴,缉熙有记,文义粲然,环列左右。使持此一念,振起倾颓,以无负列圣付托之重,何难之有?然臣闻之道路,谓警惧之意祗见于外朝亲政之顷,而好乐之私多纵于内廷燕亵之际。名为任贤,而左右近习或得而潜间。政若出于中书,而御笔特降或从而中出。左道之蛊惑,私亲之请托,蒙蔽陛下之聪明,转移陛下之志虑于冥冥之中而不自觉。
在杜范看来,理宗只是摆了修德的姿态,实际举动和《敬天图》的宣示有很大的差距。杜范希望理宗有“大悔悟,大振刷,大转移”,而核心还是在诚、敬:“伏望陛下奋发宸虑,坚秉精诚,以灾谴屡形,天怒未释为大警,而常怀戒惧之心。”*杜范:《清献集》卷9《嘉熙四年被召入见第一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680—681、682—683页。
又淳祐元年(1241),黄应龙在进士对策中先是回答了策问提出的六事,最后的两条建议,一是正朝纲,二是答天心。黄应龙也是先把天视为人格神,他先提及理宗即位以来累年之天变,认为这是“天欲扶持全安”者,然后又说淳祐改元以来“麦秋小稔,雨旸若时”,以为这是“陛下化弦更张之后,君德有加之所致也”。这番天人感应论之后,他说:
敬天有图,不但观览于内殿,而必常省于心中之图;克己书铭,不但警省于翰墨,而必常刻于心中之铭。以不愧屋漏为无忝,以存心养性为匪懈。*《历代名臣奏议》卷63,第873页。
亦是希望落实《敬天图》的主张。
淳祐十一年(1251),孙子秀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应诏上言:“宫庭虽严,传闻易广。敬天有图,而未必能戒狎昵之渐。训廉有铭,而未必能谨迩殖之防。”亦是指责理宗的口号与实践未能合一,他的解决办法是:“臣愿陛下反而求之于心,肃然起,湛然静,事事物物付之公论。”*黄震:《黄氏日抄》卷96《安抚显谟少卿孙公行状》,《黄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79—2480页。这不过是重复了《敬天图》的口号。
此外,淳祐末所编的类书《群书会元截江网》也说:
呜呼!敬天之有十二图,固以敬为主也。“(无)[毋]不敬”之书,更化之初,尝与“思无邪”对掲矣。钦天台之作,迩年以来,尝于内庭规创矣。使圣天子真见夫“毋不敬”之一言所当服膺,则斯图不作可也;真见夫钦天命台之训所当践言,则斯图无有亦可也。敬即钦也,钦即敬也,一敬之外,无复余说。*《群书会元截江网》卷3《敬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第41页。
这里虽然说“斯图无有可也”,其实则是肯定了《敬天图》的核心内容:敬。
由此可知,臣僚对《敬天图》首先是肯定的,因为此图确实抓住了当时语境中君主修德的核心:敬与诚。但同时,现实政治的困境、理宗表现的内外不一,也使他们深感《敬天图》最大的危险是流于口号。在这种情况下,臣僚一方面强调要落实《敬天图》,提出了诸如“皇自敬德”之说,但其实只不过是对《敬天图》所提出原则的重复而已;另一方面,天人感应说以父子关系说或气化流行说的方式继续存在、强化,论证持续改善政治与持续修德的必要性。
结 语
总的来说,本文重在说明《敬天图》的主旨及其出现的时机:这是理宗本人在道学的语境中修德以应天的实践,核心是作为道学修养工夫的敬与诚,而非普通的虔敬;该图于嘉熙三年秋明堂礼前抛出,又是为了以大礼之庆成证明其应天的效用。
结合《敬天图》及其他的畏天、敬天之举,可知晚宋所谓“祈天永命”这一解决困局的总纲包含了几个层次。首先,在南宋晚期,天人感应说并未退出政治话语圈。面对天变,理宗采取的避殿、减膳、彻乐、祈祷、求言、大赦等仪式性的步骤,就是在传统“事应说”的逻辑中行事*宋理宗知道天象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如宝祐六年十月有月食,理宗对大臣说:“夜来太阴食之九分,太史常预言之,以此见星翁历象之学亦无差舛。”不过,臣僚还是说:“愿陛下修政以禳之。”《宋史全文》卷35,第2869页。。以父子关系、气化流行为基础的更为强化的天人感应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南宋《国史》天变记录详于北宋《国史》*《宋史》卷48《天文志总序》,第951页。,而如果以《宋史·本纪》为例,南宋理宗本纪的天变灾异记载要远远多于宁宗本纪,即“天理说”越是巩固的时代,对天变灾异的留意却更多——因为它们是人格化的天警戒、仁爱的体现,也是气化流行的显现即人事的参照,因而是更化、修德不可或缺的助推力量。
其次,自从北宋中期以来,修政、修德才是应天之实的论调已经占据了上风。理宗亲政以后一再表现的“更化”“作新”姿态 ,必须放在实政以应天的角度下去理解。而更重要的是,道学的“天理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天人合一途径:修身以与理合,天或天理内在化于人自身。《敬天图》(以及此前的选德殿柱六字)揭举敬、诚二字,展示了主政者遵从新的天人关系论以“祈天永命”的姿态,这是解决所有困境的总纲。
因此,所谓的“祈天永命”是由仪式、实政、修德应天数个层次组成的,而且它们是相互论证的。作为修养工夫的“敬天”是根本,它也决定了施政的效用,但落实这种工夫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又来自于无时不在的天人感应。
道学首先是一场社会运动,然后才在政治上取得了正统地位。《敬天图》说明,理宗接受道学并不是因为他要践履道学所提出的艰难、无止境的修养工夫,他掌握了整套道学的话语,却抛开了工夫本身,而将其中敬、诚这样的核心概念作为政治旗号,也就回应了士大夫实德以应天的呼声。臣僚虽然高度怀疑口号的落实程度,以强化的天人感应说继续施压,但他们所提的“皇自敬德”云云也只是对同一原则作再度强调、循环论证而已。这说明,尽管是高度形式化的,《敬天图》仍不仅是一种论述,更是一种政治实践,即在“道学”所提供的新政治理论基础上行动,展现君主持敬、诚意以与天理合一的姿态,从而也成为理宗的一个保护壳。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杨海文】
2016—10—28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
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北京 100084)。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