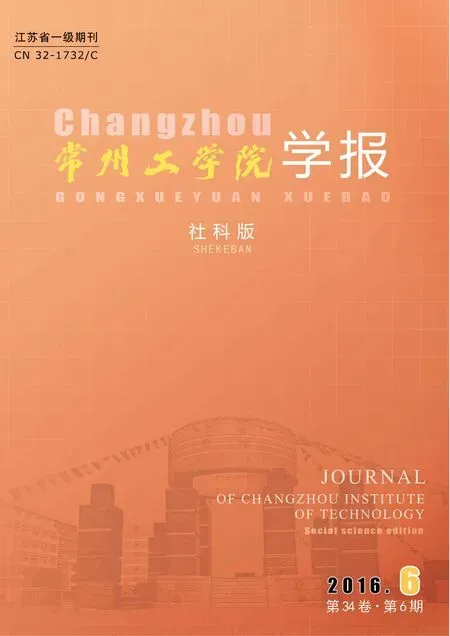看中国传统女性文化沉淀下的集体无意识
——以《生死场》为例
高欢欢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看中国传统女性文化沉淀下的集体无意识
——以《生死场》为例
高欢欢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萧红笔下《生死场》的女性形象如动物般徘徊在“生”与“死”之间,凄凄惨惨,她们活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制下,无意识地恪守着、捍卫着传统女性文化,充当了传统女性文化的牺牲品。文章分析了这些生活底层的女性形象,探讨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性。
《生死场》;传统女性文化;集体无意识
“所谓传统女性文化是一种根植于中国父权封建社会之中,长期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内,并对大多数女性的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产生过重大导向作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传统女性文化一方面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而存在,制约着女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作为社会风俗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束缚着女性的社会行为。”①传统女性文化制约女性思想主要表现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贤妻良母”“天子当头,夫做主”等方面,而其束缚女性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在“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从这些传统女性文化中,我们彷佛看到了万千女性被规范化的命运轨迹,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令人万般无奈,甚至毛骨悚然。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之魂,它的生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原始人用图腾、神话、宗教仪式等等,一方面把与他们现实相关的‘理想’的行为规范变成现实的‘契约’关系,另一方面把想象中的幻境展开为现实的行为方式。这个过程就是文化生成的过程。”②那么,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体制下,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传统女性文化根深蒂固于中国的女性文化发展历史上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正是由于这一传统女性文化的规范化和仪式化,在女性的内心世界中,这种压抑女性的传统文化被她们自身潜移默化地奴役化和内在化了,她们这些“集体人”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并自觉地充当了捍卫传统女性文化的“执法者”。
荣格曾给“集体无意识”下过这样的定义:“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遗传。”③依照“‘集体无意识’是得自遗传,不能为个人所获得”的说法,这些被传统女性文化奴役化了的女性的不自觉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积淀下的集体无意识,她们的命运悲剧揭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性。
一、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底层女性形象
《生死场》常被人们解读为爱国抗日的文本,其实不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认为:“那些目光短浅的文学评论家竟然把《生死场》前一百多页看成了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读者细读《生死场》之后将会发现,这种论调是难以立足的,”“贯穿《生死场》全书中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生死场》中的女性看似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生”在厚重的大地上,实质上,她们活像一个个无魂的僵尸,活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夫权压制之下,犹如“死”了一般。她们的一生就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悲剧是她们的主旋律。
(一)最美丽的女人——月英
“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如此的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是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目光,好比落到棉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漂亮的人儿,在患了瘫病一年后,丈夫不再为她烧香、求神,反而打她、骂她。丈夫用砖头围着她,不让她用被子,不为她清理身体下的污垢,致使“那一些排泄物淹浸了那座小小的骨盘”,“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最可悲的是“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月英的身体将变成小虫们的洞穴!”
在这里,“‘无名主’的传统积习,在《生死场》里更多呈现与物质相关联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尺度的外观,充当着男人向女人施展其男性权威的帮凶”④。在夫权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风气下,月英一没有健康的体魄给予丈夫暴力的肉体反击,二没有经济的独立、觉醒的自我意识来为她呐喊,三没有健全的社会机制为其提供“作为人”“活着”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夫妻间人情的冷漠,不正是作为一个女人所面临的最大创伤吗?而月英至死,都无力甚至也不懂得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做出有意识的呐喊。就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为妻纲”的文化约束沉淀为集体无意识,月英、金枝这些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女性一直在这个魔圈里,难以摆脱!
(二)沦陷的青春少女——金枝
金枝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爱上了年轻的男人——成业。成业和金枝约会了两次,便惹得村里的妇女散布流言,“那个丫头也算完啦!”“我早看她起了邪心,看她摘一个柿子要半天工夫;昨天把柿筐都忘在河沿!”“河沿不是好人去的地方。”这些女人们背地里议论着自己的同类——金枝的“不三不四”“不恪守妇道”“不讲求女儿名节”。同为女人,在自己受过了封建礼教的压迫后又无声息地捍卫着这吃人的伦理道德。金枝嫁给成业后,便生了“小金枝”,“小金枝来到人间才一月,就被爹爹摔死了;婴儿为什么来到这样的人间?使她带了怨悒回去!仅仅是这样短促呀!仅仅是几天的小生命!”金枝这一个眼看着正要绽放却瞬间凋零的少女刹那间一无所有。男人,害死了她,也害死了她的孩子。
金枝凄苦的一生,既忍受着来自男人的“被虐”,也遭受着来自母亲、乡村妇女对她的“自虐”。女性自己却将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历史地内在化了,使之成为了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在《生死场》中,妇女的命运在被虐和自虐的双重迫害中沉浮,女性木然地看着自己的同性在痛苦中死去,她们却连一点反抗的想法都没有。这正是那些乡村女性“自己被吃”的同时也在“吃人”的可怕的真实写照。
(三)夫权下苟活的女人——五姑姑的姐姐
在《生死场》中的第六节《刑罚的日子》中,萧红是如此描写五姑姑的姐姐的生产的:暖和的季节,狗和母猪在忙着生产,女人们也在忙着生产,这样一来,全村都在忙着生产。女性就这么卑贱地生产着,无意识地活着。接着写道:“五姑姑的姐姐就要生产了。她的男人冲进屋里便吼叫,‘快给我的靴子’,‘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来投向那个死尸’,‘女人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在一种父权的、男性中心文化的规定下,‘生育’无形中已经成为对女性生存和意志的一种异己力量,它使女性的生命价值,无论其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只是呈现为一种‘生生死死’的动物性过程。”⑤这些可怜的女人哪怕是在用生命完成她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却还要忍受着男人对她的百般蹂躏。她们的生命被视作动物般低贱,毫无价值可言。
(四)抗争悲苦命运的女人——王婆
许多学者认为《生死场》中的王婆是具有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典型代表,其实不然,在《生死场》第一节《麦场》中,萧红所塑造的王婆只是一个和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有着相似悲惨命运的妇女形象。孩子从草堆上跌在铁犁上意外地身亡了,王婆便向村里的孩子、农妇无休止地述说着自己惨痛的丧子命运,俨然像祥林嫂般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孩子被狼吃掉的模样。《生死场》后面的章节中,王婆全力支持丈夫“反抗地主加租”,当她得知女儿为了“救国”而牺牲后,便又很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事实,并积极地为着这“露脸的死”而拼搏着,因为她的心是装着“祖国”的。
具有“祥林嫂”和“革命女性”双重性格特征的王婆由一个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中国妇人形象渐渐地演变成一个民族意识觉醒的妇人。然而王婆个人意识和爱国意识被唤醒的起因是什么呢?是萧红《生死场》中所描述的大东北?这个大东北在日本人侵略之前,本就是一个女人被男人踩在脚下、女人之间相互诟骂、女人生不如死的灰色世界。王婆向往的并不是那个含有阶级压迫、父权和夫权压迫的“太平盛世”吧?从这个角度看,王婆也不过是中国万千妇女中在生死之间来来回回的一个普通女性罢了。
二、传统女性文化积淀下的女性集体无意识
在封建社会中男性需要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帮助男性实现“齐家”,传统社会在女性身上加上层层枷锁,其核心是“男尊女卑”,并围绕此观念形成了一系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礼数教条。伴随着中国漫长的以夫权形式为主的封建制社会形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逐渐形成。
《生死场》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可以说代表了一部分“集体人”的心理特征,传统的“父权、夫权”文化赋予她们以固定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这极大程度上造成了她们的凄惨命运。程金城认为:“‘集体人’的心理的展示需要相应的集体人的行为方式,从对生理的局限的感知到补充匮乏的心理需要,从外界感觉经验的积累到将它同化为心理事实,再到把这种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所感知的共同心理需要展开为集体的情感和行为模式,是一个从‘集体’的感悟到‘个体’的感悟,再还原为‘集体’参与克服匮乏的过程。”从原型的文化之维看,传统的女性文化成为沟通女性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之间的桥梁,封建体制下的“男尊女卑”等女性文化渐渐被同化为集体女性的心理事实,表现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并将此心理事实展开为集体的情感和行为模式。《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正是不自觉地将禁锢自身意识的传统女性文化展开为集体的行为模式,成为捍卫封建传统女性文化的“帮凶”。
胡风在为《生死场》写的《读后记》中这样说农民的命运:“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了食量,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⑥胡风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地概括了中国农民生存困境的凄凉。《生死场》中所描写的人们生活的画面总的基调是灰色的,这里的百姓整日辛苦劳作,面朝大地,背向蓝天,为了活着而努力地挣扎。地主收取高额的租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青山、赵三”为代表的“镰刀会”向地主刘二爷发出吼声,结果却也在地主刘二爷的点滴“施舍”中受尽折磨,地主到底还是抬高了“地租价”。男人在“自然的暴君”下尚且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更何况命如薄翼的女人们。
《生死场》中以金枝为代表的女性形象不仅遭遇着来自“自然的暴君”的压迫,更让人心痛的是这些女人同样忍受着自己的男人和日本男人这些“两只脚的暴君”的压迫。《刑罚的日子》一章中,萧红写道:“牛或是马在不知觉中栽培自己的痛苦……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五姑姑的姐姐在丈夫的谩骂、咆哮和武力撕扯中用生命产下一个死婴,“她彷佛是在夫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金枝在即将临产之际,丈夫用温存蒙蔽着金枝,这温存使金枝差点命丧黄泉。这些女性如同五月节的动物们一样不停地生产。她们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但这并不能为她们的存在增加价值的砝码,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作为一个“女人”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事情,不值得别人为她骄傲,更不允许她自己来争取这份荣耀。在这里,“生育”成了一件让丈夫憎恨、厌恶的罪孽之举。
除了“生育”威胁着这些女性的命运外,她们也面临着来自丈夫和日本男人的凌辱。金枝在自己的男人亲手摔死自己的女儿后负气离开,在县城里求得生计之时,却遭到了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的玷污。更可悲的是这些女性还遭受到日本男人肆无忌惮的玷污和骚扰。《生死场》中的女人们惨遭中国男人和日本男人的性侵略。中国男人带给这些女人们的是“夫权”下的恪守妇道,不允许她们反抗这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日本男人带给这些女人们的则是“亡国”下的生不如死,反抗的女人只会死在明晃晃的刺刀下。日本男人侵略下的女人尚且知道反抗,因为她们不愿做“亡国奴”,而中国男人侵略下的女人则深受传统女性文化的毒害,她们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安分守己,身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不懂得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和男人享有同等的生命权利,她们苟安而不反抗。
总之,《生死场》中的女性活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之下,忍受着物质缺乏和精神失落的双重折磨,她们终身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凄惨命运可想而知。正是传统女性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得这些女性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之下,不自觉地将女性这一集体的情感愿望演变成集体的行为方式,长期遵守和践行着“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等行为方式,即使生命面临威胁,尊严受到践踏,也不声不响,等待着她们的也只能是无尽的凄凉。
三、女性个人意识自我觉醒的重要性
在文学作品中,原始意象、原型成了继承集体无意识的主要载体。程金城在《原型批评与重释》中论述到:“文艺原型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审美意识和心理情感的积淀。它以一定的‘模式’的方式出现,带着千百年以来人类对美的感悟的精神遗存,似乎具有先天性质和‘本能’的特性。文艺原型是一种心理体验模式,也是一种关于‘美’的心理模式。”⑦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女性文化下精神遗存的产物,并以模式化的形式重复着传统女性的精神状态和文化遗留,她们还处于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的阶段。
那么,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遗留给后人呢?“原始人类为了生存而需要把集体的情感愿望变成集体的行为方式,变成一种具有约定性的行为规范,需要外化为可见的存在,需要以仪式具体地展开,需要作为一种模式传承给后代。正是这种与生存发展相关的需求,把人为地‘创造出’的‘集体人’的心理情感变为了现实中具体人的行为方式(如宗教仪式),这个过程自然生成着文化模式。”⑧由此可知,集体无意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本来面目”,必然要依赖于文化方式才能显现它们的具体功能。例如,谚语作为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民族无意识得以显现给后人的一种文化方式。“如谚语‘妻子如衣服’,意思是说男人可以像换衣服一样更换妻子;汉谚‘富易妻’则常常用来指男人一旦富贵就休弃结发妻子,另娶新妇;‘富人妻,墙上皮,掉了一层再和泥’也同样是此意。”⑨诸如此类的谚语都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男尊女卑思想,在这些文化模式内,传统女性把自身集体的愿望变成了集体的行为方式,这一过程就是对传统女性文化的认可并无意识地适应着这些文化约束。正如J·E·赫丽生在《艺术与仪式》中所论述的:“于是仪式也包括摹仿了;但并非由‘摹仿’而来。它想再创作一种感情,不是再制造一个实体。”⑩所谓的仪式,既承载着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发展着时代所需要的感情。老祖先模模糊糊遗留下来的压制女性自我意识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女性潜意识里共同肯定的东西,它是人类真实情感的表达,是人心实在的体现,对人性具有一种约束作用,因此,仪式很难被人们轻易废除和抛弃。


在《生死场》中,以金枝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如动物般徘徊在“生”与“死”之间,她们在传统女性文化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自身的集体无意识,并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不自觉地捍卫着传统女性文化,为满足丈夫的需求而存在,力求做一个贤妻良母,然而等待她们的却是无尽的悲哀。而当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传统女性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具有解构意义,而这恰恰是构成女性解放的关键因素。
注释:
①薛彦华、张翠芳、张静:《传统女性文化的表现及其在当代的演变》,《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20页。
②⑦⑧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第289页,第224页。
③斯塔夫·荣格,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④刘艳:萧红:《生命边界的孤独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5期,第85页。
⑤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第122页。
⑥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见《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⑨王利:《谚语中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化透视》,《兰州学刊》,2006年第12期,第182页。
⑩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责任编辑:庄亚华
10.3969/j.issn.1673-0887.2016.06.008
2016-04-08
高欢欢(1989— ),女,硕士研究生。
I206.6
A
1673-0887(2016)06-0039-05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