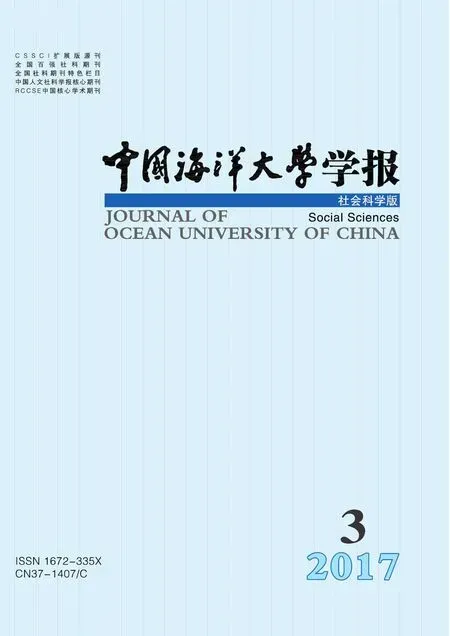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与美俄核信任问题研究
胡豫闽 马英杰
(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防务学院,北京 100091;2.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与美俄核信任问题研究
胡豫闽 马英杰
(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防务学院,北京 100091;2.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国的核军控政策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核军控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适应的是中国所面临的特定安全环境;在涉及对外安全方面,目前首先要考虑到美、俄等核武器国家,通过建立核信任措施,维护全球与地区的战略稳定。分析美俄以及中国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理念与实践,建立中美核信任十分必要。
核军控政策;核冲突;核信任措施;战略稳定
在核军控领域,美苏达成的首个国际法律文书是建立措施,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双方为防止偶发事件导致核对抗而签署的《美苏热线协定》。此后半个世纪,伴随着美、俄战略核关系的演变进程,双方制订了一系列核领域的建立信任措施。从历史上看,这些措施适应了这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在制约核对抗升级与防止核冲突、制订核军备竞赛规则与冻结“镜像效应”的规模、维持国际战略稳定以及缓和欧洲地区紧张局势等方面的需求,在当时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下,体现出了突出重要的战略意义,也为中美建立核信任措施提供了参考。
中美战略核关系是中美国家安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可描述为“竞争与合作”。中美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宗旨有相通之处。中国始终坚持倡导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美国则提出了实现“无核世界”的目标。在防止核扩散、维护核安全、推动核裁军以及促进核能和平利用上,中美有并行不悖的利益,有共同的责任,同时面临共同的挑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美建立核信任措施,加强双方的对话与合作,对于加强两国的相互信任、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
一、美俄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理念与实践
核军备领域的对抗与妥协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显著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双方对核战争性质的理解趋于理性,在防止爆发核冲突等问题上,彼此的认识逐步有所趋同,导致美俄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建立信任措施,这对于改善美俄双边关系和稳定国际与地区安全局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围绕防止核战争这条主线制订相应措施,是美苏缓和与稳定双边关系、促成两国核领域合作的基础
美苏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就意识到彼此之间存在尖锐的地缘战略矛盾并可能爆发冲突,而且就如何处理与核武器相关的问题进行过多轮交锋。双方最初提出的一些倡议更多的是出于维护自身形象并博取国际舆论的考虑,但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这两个核大国逐步认识到相互关系的脆弱性和共同避免核战争的必要性。两国均认识到,避免核战争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这一理念成为促使美苏在核领域采取建立信任措施的原动力和出发点。最初的成果出现在1963年6月。双方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达成了《美苏热线协定》。依据《美苏热线协定》,美苏首脑之间建立了便捷可靠的通信联络机制,以尽量减少因技术障碍造成误解或误判而导致爆发冲突的风险。
此后,美苏在处理双边关系问题时表现出相应程度的克制,试图通过妥协,尽量避免两国关系因某一突发事件而迅速恶化。1970年9月,美国发现苏联试图在古巴的西恩富格斯湾建立核潜艇基地。美国总统尼克松指示,在得到苏联的回复之前,美国政府绝对不能泄露这一消息。通过幕后秘密磋商,苏联最终放弃了在西恩富格斯湾建立核潜艇基地的工程。美方评论称,“通过强硬然而悄悄的外交活动,我们避免了一场本来可能被认为是1970年古巴核潜艇危机的事件”。[1](P333)
与其说,1963年《美苏热线协定》增进了两国间的信任,不如确切地说,该协定提供了必要的渠道,有效地减少了双方针对特定事件的相互猜疑。达成该协定是美苏为解决矛盾与冲突所推动的结果。双方采纳的是旨在应对问题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能确保如期解决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双方更深层次的或者具根本性的矛盾。然而,总体上看,在当时两大集团军事对抗的安全环境下,双方能够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确立防止核战争这一理念并秉持理性的态度,确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认识到两国关系中尚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美苏在上述协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相应“沟通机制”,其中包括1971年达成的《美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措施协定》、1972年达成的《美苏关于防止公海水面和上空意外事件协定》,1973年达成的《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1987年设立的“降低核风险中心”,1989年签署的《防止危险的军事行动协定》和《通告重大战略演习协定》等。
苏联解体后,美俄之间爆发大规模核战争的危险大为降低。然而,作为具有“相互确保摧毁”能力的核大国,双方对于弹道导弹可能对彼此战略预警体系形成的威胁加强了了关注。1998年9月,两国发表了《美俄关于导弹发射信息交换和预警的联合声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完善,目前,美苏达成的核信任措施,已逐步扩展到涵盖双方互动中可能引起误解或误判的诸多领域。
(二)围绕稳定核均势态势及对彼此核力量发展方向的可预测性采取措施,成为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内容
美俄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与双方在核领域相互对抗的历程相伴而行,勾画出了两国战略互动中的突出矛盾与妥协余地。这些建立信任措施降低了美俄因冲突导致核战争的风险,体现了双方在万一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通过克制以避免冲突升级的愿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始阶段,这些措施并没有削弱他们核军备竞赛的势头及各方谋取核军备优势的决心。
事实上,1963年之后的10年正是双方核力量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1969年,苏联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数量达到与美国持平,改变了此前1比4的劣势。然而,苏联并未因此止步,继续以每年200多枚的速度增加部署。自1969年起,苏联的潜射弹道导弹以每年100多枚的速度增加部署。美国则始终在战略轰炸机数量上保持优势。这10年间,苏联核弹头的总量以年均22.5%的速度增长。[2](P27-28)双方在这场螺旋上升的核军备竞赛中,不惜投入巨大资源,表现了突出的意志。由于苏联获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恐怖平衡成为双方面对的事实。然而这种竞争毫无意义,因为,即使美国造出二万枚核弹,也不能抵消苏联二千枚核弹的作用。
美国领导人逐步认识到,鉴于核武器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特点以及美苏核竞争态势的发展,通过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核战争中取胜已是不可取的;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安全感,而是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即使出于维持核威慑的有效性,核力量的发展也应有所节制。[1](P289)
在此期间,苏联在莫斯科周围部署的反导系统曾引起了美国密切关注。虽然该系统效益并不高,但是美国担心,如果苏联进一步部署性能更好的反导系统,将迫使美国要么部署更多的战略进攻性力量,要么相应发展自己的反导系统。这将出现双方发展反导系统的竞赛。面对这一前景,美国开始寻求与苏联谈判限制发展反导系统与战略进攻性武器。美国立场是,若不限制反导系统,即不可能仅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苏联起初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强调反导系统是防御性的,不能剥夺苏联“保卫自身的权利”。但是,随着美国开始部署“哨兵”反导系统,苏联改变了立场。双方开始进行限制反导系统与战略进攻性武器的“一揽子”谈判,导致双方达成了《反导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是美苏在反导问题上由对抗转向寻求共识的阶段。苏联最终接受了美国关于反导系统应与战略进攻性武器系统相联系的立场。该条约使美苏避免了一场反导领域的军备竞赛,更为重要的是,促使双方就限制当时正在进行的战略进攻性武器竞赛形成理性决策,在推动双边核裁军进程的同时,为双方维持战略平衡与稳定奠定了一个基石。
在达成《反导条约》之后,采取进一步措施,将双方核力量均势“具体化”,并维持这一均势的稳定性,符合的美苏的战略利益。不言而喻,美苏这一时期在核领域达成的建立信任措施,是以对维持双方核力量均势的共识为基础。
这一基础共识促使美苏此后达成了一系列限制核军备条约,其中包括1979年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尽管该条约设定的是一个超出双方实际拥有核武器数量的上限,并未影响各自的核力量发展规划,但是,这使彼此对于对方核力量的发展前景有了“合理预期”;与此同时,营造了两国关系缓和的氛围。
1987年达成的《中导条约》虽然仅消除了美苏核力量很小的一部分,但这却是两国首次消除一类核武器,具有重要象征意义。该条约同时设立了包括使用技术手段和现场视察在内的履约核查机制,为双方后续谈判削减核力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91年7月,美苏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将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目削减到6000枚,战略运载工具数量削减到1600件。该条约开启了美苏两国战略进攻性力量向下平衡的进程,成为双方“长期致力于通过军控稳定战略平衡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参见《美国总统就START递交美国参议院的函》.1991年11月25。1993年1月,美俄进一步达成了《第二阶段限制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将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目削减到3000-3500枚,明确将“力求巩固战略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作为目标。
苏联解体后,美国以胜利者自居。2001年,美国为扫除发展反导系统的障碍,公然退出了《反导条约》。美俄核裁军进程虽然没有如人们担心的那样逆转,但是仅仅限制与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使寻求战略平衡与稳定的目标面临更多挑战。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美俄《第二阶段限制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未能生效,核裁军进程陷入了10年停滞不前的局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即做出了调整反导问题立场的姿态,实际上只是策略性地为美俄达成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营造气氛。双方表示,深信条约规定的战略进攻性武器削减和限制的措施和义务,将加强双方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同时承认战略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存在内在联系,而且随着战略核武器的削减,这种关系将更为重要。
美俄当前关系的定位已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虽然双方在核力量上仍维持着“均势”,但是美国在寻求“均势”状态下的力量结构的优势,包括发展反导系统和快速全球打击系统。
(三)展示双方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责任,维护并行不悖的战略利益,成为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补充
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以及维持两国对于其它核武器国家的优势地位上,美苏有并行不悖的利益。冷战时期,在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共同推动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外空条约》期间,美苏通过界定彼此利益、深化共识,达成了一系列妥协,最终形成一致方案,这成为两国增进互信的一个重要进程。
上世纪50年代后期,限制核武器试验爆炸问题分别列入美苏双边、美英苏三边和国际多边军控会谈的议程。1963年,美英苏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取得进展,于8月5日正式签署。该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任何地点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在博取国际社会赞誉的同时,为两国赢得了“维护和平”的名声。先后有124个国家加入了这一条约。[3](P170)
此后,美苏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达成了《限当量条约》与《和平核爆炸条约》,采用各自的国家技术手段包括设在国外的地震台站进行核查。[4](P121)双方采纳了“合作核查措施”,包括向对方通报试验场区的地质情况以及在同一个地点进行的两次核试验的当量,便于对方校准地震监测设备、修订检测数据。根据美国建议,美苏于1988年开展“联合试验”,论证将美国提出的“科特科斯”流体力学系统和苏联类似监测系统用于核试验核查的可行性。此类技术合作以及双方专家之间的交流,营造了一种“关系融洽”的氛围。核军控核查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有关核部件与核弹头的认证与识别上,双方科学家之间的技术交流和试验系统的联合演示与验证,对于增进双方互信,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上世纪60年代,美苏核军备竞赛呈愈演愈烈之势。随着两国空间技术的发展,外空似将成为双方新的竞争领域。当时,苏联在空间技术上具有一定优势,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这一优势却受到国家总体科技水平制约。双方对外层空间的应用、特别是其军事应用的前景,尚未形成明确认知。1967年缔结的《外空条约》禁止将核武器或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入外空。在这一前景难以把握的领域制定有约束性的规则,可以增加彼此行为的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再次展示了双方为维护和平承担的国际责任。
1968年缔结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旨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到更多的国家,有助于巩固这两个核大国在各自阵营中的核垄断地位,与双方的利益并行不悖。缔结该条约客观上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减少核战争的风险,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40多年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促进核裁军、防止核扩散和推动和平利用核能上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成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该条约对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的意义不能仅从美苏建立互信的视角来认识。然而,美苏推动缔结该条约的初衷,体现了双方为维护并行不悖的战略利益所做出的共同努力。
二、中国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理念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宣示了关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愈加重视通过核领域的建立信任措施,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做出贡献,在单边、双边和多边范围采取的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不断取得进展。
(一)中国单方面在核领域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
中国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在屡遭超级大国核讹诈的背景下,中国做出了发展自卫核力量的战略选择。1964年10月,中国进行了首次核爆炸,随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此后,中国又宣布,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冷战时期遭受超级大国核威胁和核讹诈的情况下,还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坚持了自我克制的立场,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二)中国在双边范围采取的建立核信任措施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深入变化和中俄、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与美、俄两个核大国在安全与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出现新进展。中俄、中美在核领域的双边建立信任措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1992年12月,中俄签署《中俄相互关系基础联合声明》,宣布在任何情况下双方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1994年9月,两国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申明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和互不使用武力,特别是遵守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同时,中俄就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联合声明》。同年,中俄签署《防止危险军事活动协定》,以避免意外发射导弹及穿越对方国境等事件。1996年4月,中俄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开通了中俄首脑热线。2009年10月,中俄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
1998年4月,中美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开通了中美首脑热线。1998年6 月,中美首脑宣布,双方决定互不将各自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当年,中美签署了《建立与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中国坚持反对美发展破坏战略稳定的反导系统。与此同时,中美维持了就反导问题的双边对话与磋商。在应对朝核、伊核等地区核扩散问题上,中美保持了积极的合作。2008年2月,中国国防部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中美军事热线由此正式设立。2009 年11月,中美发表《中美联合声明》,重申1998年双方做出的关于不把各自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承诺,此后中美军方高层进行了一系列的互访活动。
(三)中国在多边范围采取的建立核信任措施
中国倡导有关核国家共同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就此做出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承诺。作为对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回应,核武器国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等形式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设立使无核武器国家免受核打击或者核威胁的国际安排,一旦无核武器国家遭受上述打击或者威胁时可获得援助和支持。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信任措施。
中国主张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核裁军进程,通过相互协调立场,不断增进彼此信任。1979年,中国出席联合国裁军审议大会的代表提议,世界各国应平等参与涉及国际安全与裁军问题的讨论,旨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共同推动核裁军进程。中国支持由146个联合国成员代表出席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赞同其主张,即核国家、特别是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别责任;应采取公平和均衡的裁军措施,确保各国安全权利;最终目标是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核裁军。
中国积极参与和促进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中国认为,核国家应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并承担相应义务。1973年,中国签署了《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无核武器条约》第二议定书,并于1974年提交了批准书。1987年,中国签署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第二和第三议定书,并于1988年提交了批准书。上世纪80年代,中国相继加入了《南极条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84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1988年,中国与该机构签订了双方《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自愿将部分民用核设施置于该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
1991年至1993年,中国逐步扩大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的中国核材料进出口情况。1992年,中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忠实履行了条约义务,致力于实现防止核武器扩散、推进核裁军进程、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三项目标。1996年,中国承诺,不向无核武器国家进行核出口,不与其进行人员和技术合作,不对其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帮助;将进口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作为核出口条件。1998年,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2002年,中国完成了该议定书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成为第一个完成该程序的核国家。
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和中亚五国建立无核武器区,同时支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中国尊重蒙古的无核武器地位。中国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1991年,中国加入了《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1996年,中国签署了《非洲无核区条约》第二和第三议定书,并于1997年提交了批准书。
中国是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1996年,中国在核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宣布暂停核试验,随后关闭了在青海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00年5 月,中、法、俄、英、美五国在联合声明中宣布,核武器不瞄准任何国家。中国参加了2009年在伦敦、2011年在巴黎、2012年在华盛顿和201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中、法、俄、英、美五个核武器国家会议,并于2014年在北京主办了第五次五核国会议,与其它四个核武器国家就建立信任措施和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问题保持对话与磋商。
三、探索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上升,中美战略对话趋于机制化。而且,中美对话的范围逐步拓宽,中美战略核关系成为对话的一项重要内容。美俄在核领域的一系列建立信任措施,是美俄战略核关系的重要反映,其中一些理念和措施对当前中美在核军控领域的交流和互动不乏启示和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需要认识到,时代的不同、安全环境的不同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不同,导致了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的实质性差别,决定了中美战略核关系以及中美在核领域的建立信任措施应区别于美苏的实践,超越美苏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理念。
(一)借鉴美俄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思路和理念,探索建立新型中美战略核关系
纵观美俄在冷战时期及之后达成的一系列建立信任措施,是在核领域激烈对抗与冲突的态势下,基于双方对核战争性质认识的理性化及在防止核战争爆发上所具有的共识之上达成的;是双方基于防止核战争的共同战略利益的理性与务实的合作。美俄这种理性与务实的理念和做法对于建立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当前,一方面,由于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不尽相同,在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存在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中美两国作为核国家,双方具有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避免军事危机升级为核危机的需要。两国始终认为核武器只能用于核报复,坚持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人民日报2005年9月2日。中美在核武器和核裁军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识,这是两国建立信任措施的基础。而且,中美两国都有避免误解和冲突,改善并稳定安全关系的愿望,这是双方建立信任的前提。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美在核领域采取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履行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责任。
中国致力于在国际和地区范围促进以“合作安全”为特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建立信任是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与各方建立信任与合作,将其作为新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国应积极地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将之纳入双方共同维护国际与地区安全的努力之内,推进两国的良好合作与互动,共同构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并在这一框架下建立理性务实的新型战略核关系。
(二)参考美俄建立信任措施的经验与做法,寻求建立与完善中美战略稳定与危机管理机制
从美俄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来看,其中一些措施和做法,如建立热线、开展对话、保持交流等,对于双方防止偶发事件导致冲突升级或核对抗,缓和地区紧张形势,维持战略稳定有积极的作用,值得中美两国借鉴。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美国将注意力聚焦到中国核力量上,尤其是以国防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一直是“中国威胁论”的策源地。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根据《国防授权法》,每年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全面跟踪中国军备建设的发展情况,指责中国军费和意图缺乏透明,突出质疑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和中国核力量现代化的意图。*美国国防部:《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2014年6月5日)以及以往历年的相关报告。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就开始了核领域的交流和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活动渐渐深入并形式多样。在非官方层面,双方学术机构交流活跃,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论坛或讲习班。在政府层面,中美两国1997年建立了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定期举行国防部防务磋商及工作会晤,在防扩散、反恐和双边军事安全合作等领域开展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国防白皮书》,2013年。在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多边军控与防扩散磋商机制中,核军控与防止核扩散是重要议题之一。2008年4月,中国军事代表团与美国防部进行了专门的核战略和核政策研讨交流。中美在核材料管理、《全面禁核试条约》相关核查技术应用、核出口控制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然而,上述交流与合作似乎并未减轻美方的焦虑。美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担心中国未来的走向,是在中国国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可以借鉴美苏冷战时期的做法,进一步探索新的有效的交流方式,加强并完善交流、对话机制,以多种形式消除误解、增信释疑,增进双方了解、扩大共识、控制分歧,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中美战略稳定及战略互信,避免核问题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同时,双方需建全军事交流机制,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减少信息传递错误、误解及误判的风险。
(三)认请中美与美俄在建立信任问题上的多方面差异,立足现实推动建立中美信任措施
借鉴美俄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做法,需认清中美建立信任与美俄建立信任之间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由于中美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不同,中美关系在性质上不同于冷战时的美苏关系。冷战期间,美苏意识形态对立,地缘政治利益严重冲突,为争夺世界霸权陷入全面对抗;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迎头相撞,又必须相互妥协。美苏是“冲突与妥协”的关系。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缓和”时期,美苏关系也以苏联的扩张与美国的遏制为特征。与其相反,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导致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双方经济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在国际政治议题方面的共同利益更趋广泛,双方合作的一面不断加强。中美两国虽然存在竞争和分歧,但合作与共赢是主流。中美关系总体上可描述为“竞争与合作”。
其次,中美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战略需求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不同。冷战时期,美苏在核领域大搞军备竞赛,双方在其核力量达到顶峰时期均拥有上万枚核弹头。美苏通过核军备竞赛达到了“恐怖的平衡”,逐步接受了以“相互确保摧毁”理念为基础的战略稳定观。[3]双方的核军控和裁军举措,包括核领域的各种建立信任措施,在这一基础上制订。因此,美苏之间的信任措施是建立在对抗和相互高度不信任基础上的。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从不参与核军备竞赛,也不奉行“相互确保摧毁”的理念,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遏制其它国家的核攻击。美国冷战后致力于削减核武库,寻求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试图将“核武器的用途仅限于慑止核打击。[8]中美当前并不存在核对抗的关系。在当前国际格局和战略环境下,中美对于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需求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大有不同,应更多侧重于减少相互疑虑,增进互信,维护战略稳定,推动核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与合作。
第三,中美两国核力量态势与美俄的核力量态势不同。与美俄之间核力量一直保持着“向上平衡”或“向下平衡”的均势不同,中美核力量的数量和技术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当前拥有完整的“三位一体”核力量结构,且核武器发展技术水平先进。对比之下,中国的核武库小得多,技术水平相对低。中国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战略报复能力的潜在威胁。考虑到中美两国核态势的非对称性,以及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采取过度透明的措施将损害中国的核遏制能力。双方在核领域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应具有非对称性,核力量强大、核态势具进攻性的一方,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不宜超越各自所处的战略环境及安全需求制定目标。中美在核领域的建立信任措施不能照搬美俄的经验,应当结合现实情况运筹规划,应超越美苏建立在对抗和相互之间高度不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理念与实践。
(四)正视中美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的诸多立场分歧,冷静、客观地分析、处置争议
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及建立互信上的立场分歧,是双方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重要阻碍。由于中美之间核力量对比悬殊,战略稳定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成为美对华关系的关注点。2010年,美国国防部出台《核态势审议报告》和《弹道导弹防御审议报告》,提出与中国维持战略稳定,并就此与中国进行对话。[5]但截至目前,美国并未就中美战略稳定的实质内容提出官方认可的意见。近些年来,关于中美战略稳定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学术界。其中形成机制化的对话有“中美战略核关系与战略互信”研讨会和“中美战略对话”。从交流情况看,中美在战略稳定及互信问题上的分歧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美对影响双方战略关系稳定的因素认识不同。中方认为,对于中美而言,战略稳定不应仅局限于核领域,应基于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基于中美整体安全关系的稳定。目前,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军事力量重点部署在亚太地区;大力发展弹道导弹防御和非核战略打击系统,严重削弱中国核威慑力量的效力;坚持对台军售、包括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频繁地对中国沿海进行抵近侦察等,都将不利于中美建立战略稳定与互信。美方则强调,在其它四个核武器国家削减核武库之时,中国在增加核武器的数量,有向与美达成均势的方向推进的可能;中国核力量透明度是五个核武器国家中最低的,缺乏系统的透明使别国怀疑中国隐藏的核力量可能对其构成威胁。这些认识上的差距成为影响建立稳定战略与互信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美对建立信任措施的期待也有很大差距。中方希望,美国应提高在导弹防御计划上的透明度,停止发展可削弱中国核反击能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常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中美应就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达成双边协议,明确宣示将“相互脆弱性”作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基础。美方希望,中国应对其核力量发展的“最终状态”做出说明,包括核武器的类型、部署数量以及核武器现代化的意图;承诺在美俄深入削减核武器之时,不寻求与美达成核武器数量上的均势;就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战略做出说明,包括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件。
在当前形势下,为防止彼此在建立战略稳定及互信方面的立场分歧导致更多的猜疑甚至恐惧,损害政治互信,双方需冷静对待分歧与争议,探索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新思路,更好地推进建立信任进程。
(五)顺应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发展,确立中美未来在核领域的合作重点
冷战后,随着美苏两极对抗结束,爆发核大战的危险渐行渐远,但出现偶发核攻击的风险却在增加。国际军控的重点更多地转向防止核扩散、反核恐怖及维护核安全等。美国强调,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核恐怖主义,即核武器与恐怖主义的结合,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核扩散是当前紧迫的威胁,伊朗和朝鲜发展核能力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冲击。[6]
与核领域的其它问题相比,中美在防止核扩散、应对核恐怖主义上有更多共同观点。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认的核武器国家,对打击核恐怖主义负有独特责任,也有独特能力。双方加强多方面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第一,在官方与非官方层面深入探讨相关问题,增加对威胁的共识;第二,就支持区域内国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1549号决议及其附加议定书进行协调;第三、联手打击核走私和核恐怖分子;第四,就加强对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监管、追踪放射源来源进行合作,交流相关经验;第五,就将高浓铀反应堆转化为低浓铀反应堆进行技术合作,就核恐怖事件风险分析及对恐怖事件后果预测进行联合研究。事实上,中美近些年来已在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上进行了多层面合作,取得了好的效果。
在处理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中国本着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和维护核不扩散国际机制的目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进行了紧密合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稳定与无核化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在美朝1994年“核框架协议”遭废弃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回应相关国家建议,促成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历经重重困难与波折,各方于2005年9月19日达成了关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声明。六方会谈目前处于搁浅状态,但是这一共同声明所体现的原则至今仍是谈判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基础。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中美及时做出了反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2094号决议,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中国在重启六方会谈、促使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上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中美在处理朝核问题上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还是有很多合作的需要。在涉及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中,中美保持了积极合作。
(六)适应军事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适时拓展双方建立信任措施的领域
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战略领域的拓展,中美需要更多地考虑在非核战略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基于军事科技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以及军事强国持续更新的武器发展规划,非核战略武器对核武器的作用以及战略稳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常规快速精确打击系统的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和部署、具特殊功能的空天飞行器的试验、以及网网络安全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引起了双方的关切。
全球快速打击能力的发展,使非核战略武器对核领域的战略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提升常规快速打击精度和突防能力,可对另一方战略核力量形成威胁。由于非核武器系统的使用门槛低,这实际削弱了战略稳定性;对于早期预警能力较弱的一方,非核战略武器来袭可能引发误判,对于其是否载有核弹头或投送目的地产生误解,从而导致冲突甚至核交战;目前,尚没有有效的军备控制机制对远程常规快速打击系统进行限制。
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无助于全球战略稳定,也无助于地区安全。美国声称,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朝鲜或伊朗的导弹。但实际上,这将对中国有限的核反击能力产生威胁。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推进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将严重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中国有理由担忧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未来发展。美国的行为将刺激中国有针对性地发展导弹突防能力。为了避免陷入非对称军备竞赛,美国应该增加其导弹防御计划的透明度,建立相应的信任措施。
外空武器化是中美必须关注的问题。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外空的军事应用日益广泛,成为安全与战略的高地。当前,外空武器化的危险与日俱增。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将对外空资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也影响各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中美应将对外空资产安全的关切纳入讨论范围。
中美广泛采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两国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发展均高度依赖网络空间技术与资产。网络空间有组织的大规模攻击行为,将使受攻击的一方损失严重。网络空间的军事能力对战略核力量的生存与可靠性构成了潜在威胁。在网络空间针对战略核力量指挥控制系统实施攻击,可能严重损害一方的核报复能力。在网络空间采取增信释疑的措施,将是核领域建立信任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从总体上看,中美在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充实、逐步深化的进程;以双方最为关注或者双方认为最迫切的事项为开端,在双方认为较适宜或者更具操作性的范围内拓展;双方达成的每一项具体措施均可视作建立未来两国战略互信大厦的“一块砖石”;通过持续的良性互动,双方可以克服重重险阻,朝营造新型的大国关系和稳定的国际战略环境迈出新步伐。
(七)营造有利于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的战略环境寻求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大国关系
不能指望一个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以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更不可能去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当然,一项建立信任措施的确立与实施,必然对其他领域的良性互动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美俄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两国之间的竞争与对抗的大背景导致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双方业已建立的诸多建立信任的措施,其初始动机往往是解决双方面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是在经历某种危机之后,双方对避免类似危机发生的必要性形成共识基础上采取的,而不是纯粹出于建立信任的目的。比如美苏热线协定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后建立的。与此相伴的双方信任的增强只是在解决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的客观效果,而且这种效果往往还是因时间的推移而可能变化的。比如两国在外空领域的共识并未能防止1983年美国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并导致美苏关系的恶化。
某种信任措施得以建立,特别重要的是,所涉及的双方必须有切实感受到的需求,并且能在此方面寻求到共同的利益,或者双方认为可以交换的利益。否则,如果一方提出另一方难以接受,或者另一方认为无必要,或并不紧迫的方案,并且这一过程又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拖得很长,其结果,很可能不是建立了互信,而是损害了已有的互信。
两国之间建立信任措施必然是一个过程,而且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逐渐积累、不断充实的过程。建立信任措施往往从双方最关注,或双方认为最迫切的事情开始,不能指望一个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以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更不可能去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当然,一项建立信任措施的确立与实施,必然对其他领域的良性互动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每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都值得重视。从解决单一问题到逐渐扩大到整体性的问题,从避免两国在可能的对抗中发生误判,到逐渐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稳定两国关系的措施。这些都体现在美俄两国的互动中。
建立信任措施的过程,其进展的快慢、涉及的范围,一方面与两国关系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双方的认识与理念有关。建立信任措施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双方在处理某种冲突或危机过程中产生的需求,或者是双方预感到可能发生某种冲突或危机,而避免发生冲突或危机,或防止冲突危机升级被认为符合双方的利益的情况下,双方会寻求建立某种信任的措施。因此,建立信任措施往往并非是在双方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发生的。
保持各个层面上的交流与接触有利于理解对方的关切,特别是一些技术专家就某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合作,可以减小合作中面临的一些技术障碍,或者有助于消除将技术问题,如核查问题,作为拒绝采取某种行动的借口;同时,两国关系的明确定位也有利于双方界定各自的国家利益,并以一种坦率的方式来阐释其利益所在,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对方的利益关切,从而在互动过程中更易于形成合作的意愿。
(注:本文依据课题组的讨论撰写,由作者统稿。)
[1] 桂立.美苏关系70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王羊.美苏军备竞赛与控制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3] 刘华秋.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
[4]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军备控制概论[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5]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2010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http://www.defense.gov/bmdr/docs/BMDR_101_MASTER_2_Feb.pdf;2010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http://www.defense.gov/npr/.
[6]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A. 2010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 http://www.defense.gov/npr/.
责任编辑:鞠德峰
The New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the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Russia in Nuclear Issues
Hu Yumin1Ma Yingjie2
(1. College of Defence Studies,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eijing 10009, China;2.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0, China)
China's nuclear arms control polic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 is developed to adapt to specific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e should first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other nuclear weapon countries. We should build effective confidence in nuclear aspects to maintain global and regional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trust building in nuclear issues are good examples for us to learn in building Sino-US confidence.
nuclear arms control policy; nuclear conflict; nuclear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strategic stability
2017-03-27
胡豫闽(1951- ),男,福建上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教授,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军控与裁军问题研究。
D815
A
1672-335X(2017)03-006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