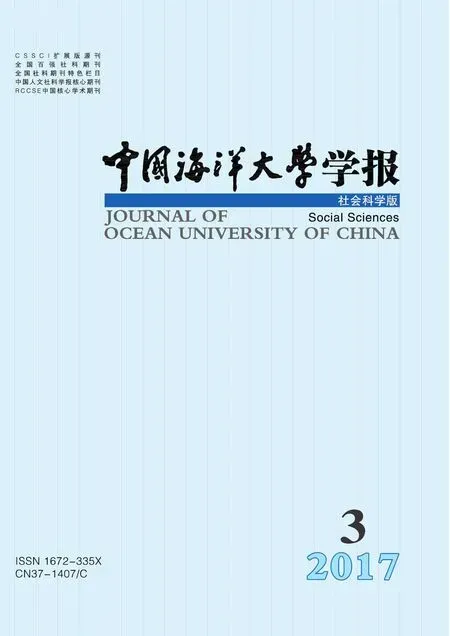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孙晨曦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孙晨曦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事案解明义务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理论,其功能在于弥补负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于证据偏在型诉讼中举证能力或手段之不足,减少证明责任在个案中的具体适用,从而实现当事人在程序上的实质平等。随着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几次修订,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已在司法实践中初现端倪。通过比较法的考察,我国现行立法及相关规定依然处于滞后状态,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此,不妨以域外国家及地区的理论为参照,构建出事案解明义务的中国图景。
事案解明义务;当事人陈述;文书提出义务;事证开示;比较法
在民事诉讼中,基于辩论主义和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基本原理,负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为追求于己有利之法律效果得以实现,必须竭尽所能收集诉讼资料与事实主张,进而提出相关证据方法以证明待证事实。如果该主张最终未能使法院形成确信,造成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则该当事人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与之相对,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并无主动或被动为对方提供协助之义务,更不会被要求对于己不利之事实进行自我揭示。这一规则在传统民事诉讼构造下,似乎并无不当。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型诉讼频发,尤其在医疗纠纷、环境侵权和产品责任等案件中,证据分布不均的情况层出不穷,被害人通常很难充分掌握案件所必要的诉讼资料或证据方法,此时,如果依然恪守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法则,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势必会由于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客观原因从而产生举证困难,最终承担败诉的风险。如此,本该于实体法上所认可的权利却无法于诉讼上得以实现,那些掌握案件事实或证据材料的一方当事人却因为不负担证明责任而能够坐享其成,从中获利。显然,这样的裁判结果有违公平正义,更与民事诉讼的目的相悖。
事案解明义务的提出正是为了弥补此种证据偏在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使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证据的收集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以确保双方当事人对事证资料的平等使用,从而有助于法院发现真实。这一理论在以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已有过广泛而深入研究,无独有偶,为解决证据分布不均及当事人举证困难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事证开示制度,使诉讼中每一方当事人都应向其对方提供和展示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资料,从而简化诉讼程序,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不难发现,在功能设计上二者具有高度的相似之处。而反观我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条文有所涉及,并且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盲点。显然,如此单薄的规定难以应对当下错综复杂的司法状况。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我国的理论现状出发,通过比较法的分析和考察,以期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及立法。
一、我国事案解明义务的现状分析
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也被称为事案解明协力义务,是指当事人对于事实厘清负有对相关有利和不利事实之陈述(说明)义务,以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之义务。[1](P8)可见,事案解明义务并非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当事人陈述义务、文书提出义务、勘验协力义务等等。从广义而言,为保障案件事实的查明,双方当事人均有可能受到事案解明义务的规制。然而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法则,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其有利事实进行积极的主张和举证是应有之义,因此,该理论的研究通常侧重于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是否同样负有事案解明义务。虽然我国对事案解明义务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全面,但就目前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解释而言,仍然可以找到与之相契合的有关规定。
(一)我国事案解明义务的现状
1、当事人陈述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具有两种身份:一是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陈述事实主张以明确诉讼关系;二是作为证据方法接受询问,向法院报告其所经历、体验之事实。两种情形分别属于当事人主张和举证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是诉讼资料,后者是证据资料,在资料提供的意义上,二者截然不同。[2]显然,作为义务性质的当事人陈述应当是针对后者而言,这在学理上也被称为当事人询问。由于当事人询问对于事案解明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各国民事诉讼立法大多都将其作为独立的证据调查手段予以规范。我国规定在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0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捺印该条文从两个层面体现了当事人询问制度:第一,当事人本人出庭接受询问。从表述上看,双方当事人都负有出庭接受询问的义务,换言之,即使是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也必须亲自到庭接受询问。而在《民事诉讼法解释》出台之前,除了离婚案件当事人和特殊身份关系案件中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必须到庭外,其他案件当事人并不负有出庭义务。第二,真实陈述义务。该项规定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集中体现:一方面要求当事人应为具体陈述,不得沉默;另一方面要求当事人所陈述的内容必须为真实。当事人询问的规定使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在案件中承担相应义务,对于事案解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当事人询问在证据方法中所处的地位与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地位所作之陈述并未加以区分,实务中法院利用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资料并以此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例更是少见,使得当事人陈述难以发挥其应有之功能。[3]
2、文书提出义务
文书证据是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通常情况下,文书为举证方当事人所持有并能够主动提交于法院以作证据调查之用。然而当举证方当事人所欲提供之文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范围内,且对方当事人拒绝提供,此时举证方即陷入举证困难,导致法院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因此,为保障双方当事人在利用诉讼资料上的实质平等,以及促进法院发现真实,针对此种情形,受诉法院应当命令执有该文书的当事人提出文书,否则将会承担裁判上的不利益,此即当事人文书提出义务制度。[4]由于书证在我国民事诉讼审判实务中处于中心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书证几乎就是唯一的证据方法,“具有压倒的重要性”,因此文书提出义务被视为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2条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文书提出义务作出了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 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根据该条文,我国文书提出义务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文书提出的主体是不负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其二,文书提出的程序必须先由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方可责令书证持有人提交;其三是违反文书提出义务的后果,即文书持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不可否认,我国确立文书提出义务制度,在弥补当事人诉讼地位不平等、协助法院发现真实、促进审理集中化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该条文过于笼统且缺少相应的配套规定,在具体适用中仍然存在不少弊端,尤其在文书提出条件上未加以合理限制,容易遭致滥用,从而有可能无故增加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负担,损害其合法权益。[5](P157)
3、证明责任倒置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具体而言,原告对权利产生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对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尤其是一些侵权案件中,若依然恪守这一原则,很可能会造成裁判结果的不公正。证明责任倒置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此类案件中负担证明责任方当事人举证困难的难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4条列举了八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形,俗称为“证明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形。*《证据规定》第4条列举的八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形是:方法发明专利侵权、高危作业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建筑物倒塌等致人损害、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缺陷产品致人损害、公共危险行为致人损害、医疗行为致人损害。这一规定突破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局限性,使原本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积极举证以查明案件事实,是对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举证能力不足的一种有效的救济方式。然而,尽管当下我国大多数民事诉讼法教科书都对证明责任倒置进行了专门介绍,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但长期以来该理论也受到不少质疑。有学者提出在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以及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中,加害人所负担的证明事项原本就是依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所得出的结果,应当属于证明责任的正置而非倒置。[6](P181)更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倒置是具体举证责任机制贫困的产物,与特定案件证明困境的解决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不能作为解决现代型诉讼证明困境的方法。[7]
(二)我国事案解明义务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立法现状分析可知,我国目前主要通过当事人陈述、文书提出义务和证明责任倒置等规定来解决当事人举证困难的问题,虽然立法上尚未正式确立事案解明义务,但在形式上已经初具雏形。然而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模式下,事案解明义务的确立及运用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我国事案解明义务的开展缺少相应的理论基础。任何制度与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事案解明义务是自由主义诉讼观向社会诉讼观转变过程中,为修正传统辩论主义之弊端所提出的理论。该理论在产生之初便饱受争议,在坚守传统民事诉讼理论的学者看来,事案解明义务是对作为民事诉讼制度基石的辩论主义和证明责任的颠覆,甚至将从根本上动摇民事诉讼制度的架构。因此,为了使事案解明义务具有正当性基础,学者们开始从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出发,试图寻找出支持其存在的法理依据。受到广泛认可的包括宪法及诉讼法目的、诚实信用原则、实质武器平等原则、诉讼促进义务、真实义务等。而这其中除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明确规定外,其他理论却鲜有提及。此外,由于我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案解明义务的实效性。
其二,忽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法院在诉讼中可以不受双方当事人陈述的约束、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的证据范围之外依职权独立收集证据以及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干预等方面。如果说传统的自由主义诉讼观过于强调个人自由,我国的诉讼模式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事案解明义务要求双方当事人在证据收集和提出方面的相互协作,共同发现作为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尤其强调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在证据上的协力义务。显然,在我国目前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的作用十分有限,难以为事案解明义务的运作提供良好的平台。
其三,我国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如前文所述,事案解明义务是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理论上通常认为事案解明义务包括对于不明事实或证据资料的开示、提出勘验物、容忍对于不动产之调查及对身体之检查及文书提出义务。甚至在诉讼系属前,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亦有其程序前之作用。[8](P152)可见,在民事诉讼理论较为成熟的国家,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已经较为广泛。而我国目前有关的司法解释仅仅对当事人陈述义务和文书提出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范围比较狭窄,不利于该制度功能发挥。
二、比较法视野下的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
从比较法及历史沿革的角度来考察民事诉讼,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诉讼政策。在私法自治的原则下,当事人必须自行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承担因不能提出事证所遭受的不利后果。因此掌握对自己不利证据的当事人当然享有不提出该证据的处分权能。与之相对,第二种诉讼政策认为诉讼结果应当是追求实质公平之实现,而不是取决于证据资料的分布或当事人对其掌握的程度。因此为了追求判决的公正,双方当事人应当将所有与纠纷有关的事证进行开示,以确保当事人在证据资料上的平等利用。就目前的司法现状而言,不论是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之民事诉讼系统,均已先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第一种诉讼政策,并在立法上朝向第二种诉讼政策转变。这种转变在英美法系以“事证开示制度”为典型代表,在大陆法系则表现为“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虽然在具体操作方面这两个概念存在若干歧异,但是在功能价值上二者具有高度之共通性。[9](P187)惟其在类型选择上存在“一般化事案解明义务”与“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的对立,这种对立恰好呈现出两大法系对事案解明所抱持之基本态度。因此,通过两种制度的比较考察,可以为我国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的完善提供他山之石。
(一)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以“当事人对审制度”为其基本原则,双方当事人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辩论程序中通过证据和主张的对决,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供有关纠纷事实的信息,从而使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者进行裁判以解决纠纷。[10](P26)一方面要求当事人只负责自己的主张和证明,而没有义务提出有利于对方的主张及证据;另一方面禁止法官主动介入调查纠纷事实。然而正是在该原则的运作下,引发了所谓“当事人竞赛理论”的强烈批判和质疑。
为了解决传统当事人对审制度在事证收集上的弊端以及响应理论上不断的质疑,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制度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美国于1938年制定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创设了事证开示制度(Discovery),并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0至36条对事证开示的各种方法作了明确规定,具体包括笔录证言、质问书、要求提供文书和物证、要求自认以及身体或精神状态的检查。[11](P178)在这一规则之下,原则上只要与任何当事人的主张或防御有关的事实证,不论其有利与否,当事人均有开始之义务。与美国相似,英国在其民事诉讼规则中同样设计了一系列详细并具有较高操作性的事证开示规则,其中包括第31章第22条的书证的开始和查阅,第32章的证人证言、宣誓证据,以及第34章的笔录证据与证人出庭作证等规定。不同的是,美国民事诉讼事证开示的期间通常始于起诉后而终于开庭审理前,也即所谓庭前开示证据。而英国则通过“诉讼程序中开示义务之继续”的规定将证据开示的期间延伸至诉讼终结时止。[12]
事证开示制度在其设立之初就受到高度的重视,一方面在于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制度价值,强调以庭审以中心,淡化所谓的诉讼技巧,使当事人和裁判者能够从中获益;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该制度所蕴含的诉讼价值,即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首先,事证开示能够使当事人在最大程度上掌握和了解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证据,并对自身和对方的优势及弱点做出初步估计,从而有可能促成双方的和解。其次,通过事证开示能够进一步明确并整理争点,使审理事项具体化,提高庭审效率。最后,事证开示能够有效防止一方当事人在庭审时提出一个令对方完全无从知晓的证据进行“证据突袭”,使双方当事人在武器平等的状态下公平竞技。[13](P355)综上,事证开示制度的建立,显著地改善了当事人对证据资料的掌握所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使当事人处于实质的对等地位。尽管英美法系国家中并不存在事案解明义务的词语表达,但是在内容及功能设计上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事证开示制度的相关规则可以推测出,英美法系国家的事证开示制度试图摆脱以实体法律关系界定诉讼法上开示义务的思考方式,基本上否定当事人隐匿不利事证的自由,在类型上更倾向于一般化的事案解明义务。
(二)大陆法系
与英美法系不同,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以“辩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所谓辩论主义,是指将确定作为裁判基础之事实所必须资料的权能及责任赋予当事人行使及承担的原则。[14](P329)由此,传统辩论主义延伸出一个公认的重要原则:诉讼当事人没有义务提供有利于对方的事实证据。在这一原则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事人对审性格,与英美法系相比,当事人所面临的“证明困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大陆法系国家试图借由“当事人真实义务”和“法官释明”来缓解这一难题,但实践证明不论是通过当事人真实义务抑或是法官释明的行使,都难以改变双方当事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所谓“证据偏在”的状况,也没有对当事人就相关证据的接近或使用所存在的不平等地位作出有效的改正与补救。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意识到传统辩论主义及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如何规制当事人的证据提出责任上,从而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理论概念,诸如证明妨碍、表见证明、摸索证明、事案解明义务等。而其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研究应当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德国学者正是以该理论为研究重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说争论,至今未绝。
事案解明义务的概念源自德国,1939年德国学者冯·希佩尔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与阐明义务》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事案解明义务这一概念,该文对传统辩论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试图提出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全面的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的主张。1966年学者吕德里茨和彼得斯从摸索证明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对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前者认为只有当负担证明责任方做出一定盖然性的陈述时,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才有事案解明义务;而后者则主张应从法律的具体规则中推导出一般化的事案解明义务。直至1976年施蒂尔纳教授发表《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阐明义务》一文,对事案解明义务的性质作出了界定,并对其类型、适用条件及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完善,使得事案解明义务理论走向一个相对完善的状态。[15]此后,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究竟在何种条件下应当承认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即事案解明义务的一般化与例外化的争论。与德国相似,我国台湾地区对事案解明义务的研究同样存在着“一般化”与“例外化”的对立,持“一般化事案解明义务”的学者认为,应当从发现真实、诉讼促进及公平三大价值出发,肯定一方当事人取得相关事证的证明权,以保障双方诉讼上对话沟通之平等地位。[16](P15)而反对者则认为若普遍地承认一般解明义务,将会造成辩论主义和证明责任理论的颠覆与破坏。
尽管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议,但在立法与实务方面,不论是德国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对一般化事案解明义务的确立依然抱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认为将民事诉讼中现存的有关规定通过整体类推的方式进行扩张并承认一般诉讼解明义务的观点不能得到承认。[17](P811)因此可以说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更倾向于例外化的事案解明义务。
三、事案解明义务的基本架构
(一)事案解明义务的法律要件
理论上越倾向于一般化事案解明义务的学者,对其要件的设计越是宽泛;而越坚持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的学者对要件的设计越严格。因此在一般化事案解明义务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之前,有必要对其法律要件进行探讨,即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应负协力事案解明义务。对此,理论上认为事案解明义务的产生需满足以下要件:
第一,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指明解明对象与自己权利主张有关的合理依据。换言之,要求对方履行事案解明义务的当事人,应当首先指出待解明的对象与其权利主张存在何种关系,并提出之所以要求对方当事人解明有关事证的理由。该要件即使是在持“一般化事案解明义务”的学者看来也具有相当之合理性。论者认为应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其认识范围内可期待状况下应对其主张加以具体化,而若缺乏该认识,则应当提出其主张具有可信性之根据。[8]也即,在通常情况下,当应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已首先尽具体化义务时,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才有事案解明义务的发生。
第二,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处于客观上无法证明的状况。此处是指当事人出现证明困难,具体又分为“消极证明困难”与“积极证明困难”两种。前者是指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因证据偏在情形的出现而产生证明困难;后者是指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因为某些特殊理由而无法提出其原本可能取得的证据。对于消极证明困难,由于举证方当事人无法知悉、掌握超出自身认知范围以外的证据,此时对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课以事案解义务,可以调整双方的诉讼地位,有助于实现诉讼上的平等。而在积极证明困难的情形下,当事人并非无法取得、接近有关证据,而是证据的取得或提出将造成更大的损失。例如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中,若当事人以对方应负事案解明义务为由要求其对商业秘密进行揭示,则对事案解明义务人而言无异于将其商业秘密公诸于世,结果很可能使当事人遭受巨大的利益损失。因此,当出现积极证明困难时,可以将其视为事案解明义务例外化的一种情形。
第三,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处于容易解明事实的地位,并且具备进行解明之期待可能性。此处是指同举证方当事人相比,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更容易掌握或接近证据资料,对证据资料的收集和提出不会造成太大困难,也不会因此付出较大成本。这一要件在证据偏在型诉讼中得到普遍认可。例如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由于当事人往往既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又无法掌握相关的医疗档案,原告方通常只能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而难以进一步证明医院存在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反,被告方则处于一种明显优势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被告几乎控制或掌握了全部的证据资料。此时完全可以期待其对有关事证进行开示以解明事实。
(二)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对象
在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对象上,一般化论者认为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范围十分宽泛,并可以导致诉讼上广泛的资讯提出义务。它应当包含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所有的可以考虑的、可以要求的阐明贡献,即对法律上重要的事实以及证据手段存在与否给予答复,在履行方式上,当事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为之。[18](P303)据此,当事人对于事实的说明不仅针对待证事实,也包括相关证据方法在内。具体而言在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包括:(1)对于不明事实或证据方法之开示;(2)勘验物之提出;(3)忍受对于不动产之调查及对身体之检查;(4)文书提出的一般义务。甚至于诉讼前,若举证方当事人因不可归责的原因而缺乏足够的证据资料,也可依据诉讼前之资讯请求权要求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提出文书、及提出勘验物等。[8]
尽管持例外化理论的学者也大致认可上述适用对象,但其在适用范围上提出了质疑,认为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应当受到一定的规制,否则容易矫枉过正。论者认为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对象应当遵循如下规则:其一,资讯义务的提出,有法律特别规定的,应当依照该规定履行;若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则根据有无准用或类推的情形来决定其适用范围 。其二,若当事人因履行事案解明义务而与自身利益产生冲突,裁判者应当依据“比例原则”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三)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法律制裁
欲对违反事案解明义务课以法律上的制裁,必须首先明确当事人在何种情形下造成对该义务的违反。对此,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界定:其一,在事实层面,对于需要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进行解明之事实,若其知悉且拒绝陈述,则视为违反事案解明义务;其二,在证据层面,对于需要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若在其掌控之下且拒绝提供,则属于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综上,当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负有事案解明义务,如果该当事人拒绝陈述其所知悉的案件事实或拒绝提供其所掌控的证据资料,即构成对事案解明义务的违反。
关于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法律后果,理论上存在“单一说”与“分层说”的见解,前者认为对当事人违反事案解明义务应当实施特定的制裁措施;后者则认为应当视当事人违反的程度不同而区别对待。具体而言,持“单一说”的学者认为,当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违反事案解明义务,拒绝做出具体的事实陈述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据时,不能认为其对他造之事实主张进行了有效的争执,此种情形应当直接以他造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基础,进行拟制自认。[19](P556)也即其法律后果为“被主张之事实拟制为真实”。而采“分层说”的学者认为,对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制裁应当视义务违反的程度以及相对人主张之真实盖然性高低而定。当违反义务的程度较大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转换,由使违反义务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若属于轻微义务的违反,则可以纳入证据评价的范围,由法官进行裁量。
四、我国事案解明义务的模式选择与完善
(一)模式选择: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
探讨事案解明义务,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一般化与例外化的争论,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而言,宜选择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即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
首先,从我国的诉讼体制来看,我们应当选择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长期以来,我国被认为是奉行“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职权干预的色彩十分浓厚。在该种诉讼模式下,法院包揽证据调查的事项,将当事人仅仅作为证据的提供者,甚至可以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之外依职权独立收集证据。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一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应当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尽管如此,典型意义上的职权主义模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很难见到,但是从体制整体而言,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模式仍然没有超越职权主义的范畴。法官仍然被要求或被期待在诉讼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并通过释明权的行使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主张和证据资料进行判断,当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主张与案件无关或有误,法院会提醒其作出正确的事实主张;当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资料不够充分,法官督促其进行补充完善。在我国目前的诉讼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像英美法系国家那般广泛地承认当事人的事证开示义务,更不会容忍法官在诉讼中扮演超然中立的消极角色,而借由当事人其及律师来掌控程序。因此,在模式上选择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符合我国当前的诉讼体制。
其次,就我国的立法现状而言,我们也应当选择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如前所述,事案解明义务的设置是为了弥补举证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困难,使不负证明一方当事人发挥一定的作用,从而保障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武器平等。在现代型诉讼频发的今天,事案解明义务的作用尤为明显。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仍有可能产生举证困难的问题。此时完全可以通过现行立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等有关规定进行调整。若广泛地承认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则有可能架空我国司法改革辛苦构建起来的证明责任制度。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的证据偏在型案件中,我国已经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赋予了处于劣势一方当事人相应的救济手段(如证明责任倒置等),若此时忽视现行立法的规定而试图寻求另一种救济途径,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尚未完全转型成功之前,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无疑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最后,我国民事审判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应当选择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我国法院坚持以依法审判为指导原则,这里的“法”指的是实定法。因我国素来有成文法的传统,决定了民事审判中的思维方式必然是以实定成文法为出发点,这种审判思维起源于罗马法,被称为“规范出发型”诉讼,是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主要的审判方式。相反,英美法为判例法,其诉讼的目在于发现事实中应有的法,这种审判思维被称为“事实出发型”诉讼。[20]这两种诉讼思维的差异正好反映出两大法系对待事案解明义务的不同态度。一般化事案解明义务摆脱以实体法律关系界定诉讼法上请求权的思考方式,立足于诉讼法上的观点,直接论证当事人事证开示对于民事诉讼审判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则是以实体法秩序为出发点,只有当实体法律关系赋予一方当事人对他造之情报请求权时,才会使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负担事案解明义务。可见,例外化事案解明义务以成文实体法为基础,与我国民事审判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
(二)我国事案解明义务的完善
为弥补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实现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质武器平等,我国确有必要构建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的理论体系,当然,任何制度的良性开展都离不开其他诸多相关的因素。因此,未来我国事案解明义务的体系构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进一步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转变,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基于辩论主义的要求,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不得作为裁判依据,法官进行证据调查也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的申请为限。而这一要求在我国当前却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法官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并在证据调查方面拥有较大的职权,在这一体制下,事案解明义务开展的效果必定会大打折扣。此外,我国民事诉讼尽管明确规定了辩论原则,但该项原则强调的是当事人所拥有的辩论权,而并没有着眼于当事人辩论与法院裁判的关系,当事人的辩论仅仅作为法官审判的参考依据,没有对法官形成约束。事案解明义务的产生是为了修正辩论主义,但若是缺乏辩论主义这一基本前提,修正便无从谈起。
第二,充实事案解明义务的对象范围。除了目前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的当事人陈述义务和文书提出义务之外,有必要对当事人的勘验协力义务进行补充并将其纳入事案解明义务的范畴。勘验是诉讼中一种常见的证据手段,是指法官基于自己五官直接感知人或物的物理状态,并将其认知结果作为证据资料的证据调查,在内容上包括勘验标的物的提出义务和勘验容忍义务两种。[21]在一些诉讼中,特定事物的勘验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具有关键作用,如果需要勘验的标的物在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下,则该当事人应该提交并容忍法院进行勘验。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规定中,勘验的功能十分单一,仅仅是指勘验人员对不能转移占有或无法由当事人提交到法院的物证和现场进行调查,勘验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证据意义。
第三,建立事案解明义务的制裁措施与保障机制。对于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制裁存在“单一说”和“分层说”的观点,尽管分层制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相对更为公平,但问题在于如何对当事人违反义务的程度进行界定实属不易,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参考标准而交由法官自由裁量则容易造成操作上的混乱。因此,不妨以“单一说”为参考,将被主张之事实拟制为真实作为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制裁措施。此外,为了防止事案解明义务被滥用,有必要赋予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有效的保障机制,一是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权利,当法院认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事案解明义务,该当事人可以通过提出间接反证,使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存在与否无法形成确信,即可推翻被主张事实为真实的拟制。二是赋予当事人程序上的救济权,若当事人受到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制裁,应当允许其通过上诉或申请再审对有关事项进行争议或反驳。
[1] 姜世明.民事证据法实例研习(二)暨判决评释[M].台北: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6.
[2] 段文波.《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关注作为证据的当事人[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3):112.
[3] 占善刚.当事人讯问之比较研究[J].法学评论,2008,(6):61.
[4] 占善刚.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文书提出义务[J].求索,2008,(3):154.
[5]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6] 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 胡学军.证明责任倒置理论批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106.
[8] 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M].台北: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6.
[9] 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展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 (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1] 张卫平.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2] 黄松有.证据开示制度比较研究——兼评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的证据开示[J].政法论坛,2000,(5):106.
[13] 罗玉珍.民事证明制度与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4] (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5] 胡学军.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论坛,2014,(5):104.
[16] 沈冠伶.民事证据法与武器平等原则[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
[17] (德)罗森贝克著,李大雪译.德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18] (德)米夏埃尔·施蒂尔纳著,赵秀举译.德国民事诉讼法文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9] 许士宦.证据搜集与纷争解决[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20] 段文波.一体化与集中化:口头审理方式的现状与未来[J].中国法学,2012,(6):141.
[21] 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分析[J].法学研究,2008,(5):90.
责任编辑:周延云
On the Obligation to Explain Cases of Litigant without Burden of Proof
Sun Chenxi
(Law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China)
Obligation to explain the cases is an important theory of continental civil procedure law,and its function is to make up for the burden of proof of the party in the evidence with partial proof of litigation ability or means of insufficient evidence,reducing the role of burden of proof in specific cases,and therefore achieving the substantive procedural equality of the parties.Several amendments have been made to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in China beforethe applica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explain the case has already taken shape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parative law,China's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are still lagging behind,lackingin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In this regard,with extraterritorial national and regional theory as a reference, we hope to form the case to explain the obligations against Chinese background.
obligation to explain the case;statements by the parties; obligation of propos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disclosure;comparative law
2016-08-06
孙晨曦(1990- ),男,贵州毕节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D915.2
A
1672-335X(2017)03-0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