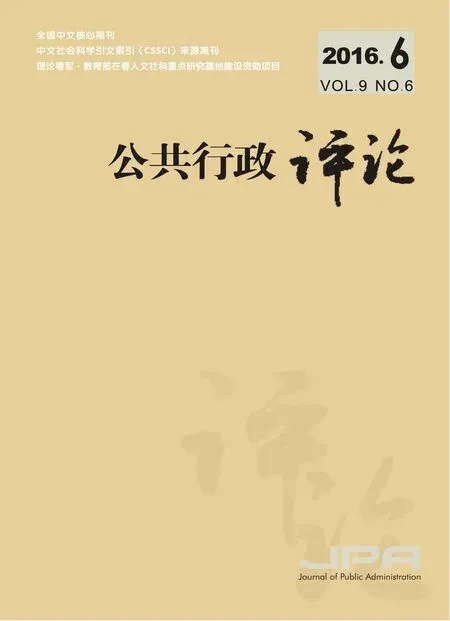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
徐 彪 陆湾湾 刘晓蓉 张 浩
论文
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
徐 彪 陆湾湾 刘晓蓉 张 浩*
论文从公众感知视角,整合了原因属性分析、责任推断等归因过程,构建了公众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感知模型;并通过情境模拟实验,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共危机事件后,(1)相对于政府内部归因,外部归因会弱化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2)在政府内部归因中,相对于将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部门道德缺陷,归因于政府能力不足更有利于弱化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3)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可控性越高,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越强;(4)公众对政府社会责任的感知越强、对政府的认同度越高,则对政府责任的感知越低;(5)受害方共谋关系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6)危机事件越严重,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越强。这些发现当有助于促进公共危机和公众感知的理论研究,并帮助政府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政府责任 公众感知 公共危机 归因 责任推断
一、引 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而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岳经纶、李甜妹,2009)。在公共危机中,若政府通过积极应对,降低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则可以极大地保护甚至提高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反之,则会增加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并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危机事件的责任管理,努力降低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这就要求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即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理是怎样的?
在公共危机中,对危机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判断谁应对危机事件负责,是公众的本能反应之一。由于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责任感知来源于主观的心理认知过程,因此往往与客观的真实原因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政府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对公众感知规律缺乏把握,疏于应对,导致公众错误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过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如在一些公共危机中,政府过度强调客观事实,竭尽全力地证实政府部门没有过失,往往给公众形成推脱责任的印象,认为政府在掩盖和推卸责任,引发怀疑、焦虑、愤怒等心理反应,反而加剧了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危机中公众心理认知远比事实本身来得重要(Pearson & Clair,1998)。因此,想要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必须把重点放在研究公众的心理认知上。
探讨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责任的感知,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研究视角(Tomlinson & Mayer,2009)。政府责任感知作为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不作为”或“作为不当”导致的公众认知结果,其很大程度上受到公众对危机事件归因的影响(Ferrin & Dirks,2003:18-31)。因为归因有助于理解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基于对事件发生原因的判断,最终影响到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如当危机事件被归结为外部、不可控原因时,政府往往不承担责任;而当危机事件被归结为政府内部、可控原因时,公众就会产生“政府应对危机事件负责”的感知(徐彪,2014:27-38)。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由于认知能力局限、信息缺乏、归因偏见等原因,会产生认知偏差,从而对政府责任产生错误的认识或感知。正如徐彪(2014)所指出的,公众极易在危机事件中进行错误归因,盲目地认为政府应对危机事件承担责任,甚至是道德责任。因此,本文从公众感知视角出发,基于归因理论,探索公共危机中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理。期望本文可以促进危机管理、公众认知等相关理论的研究,并对政府更加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文献与研究假设
(一)公共危机后的政府责任感知
公共危机事件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等外部原因或社会矛盾积聚而引发的、危及社会公众的整体生活和共同利益的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影响范围广等特征。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收集信息,通过归因过程,对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最终产生“谁应对危机事件负责”“谁应受到惩罚”的判断。作为危机归因的结果,如公众认为公共危机是因为“政府不作为”或“作为不当”而导致的,则会产生政府责任感知,即政府应为危机承担责任。
(二)公众归因过程
归因是公众一种基本的认知过程,也就是公众利用信息对危机事件原因加以推断的过程(Mayer et al.,1995)。在公共危机中,公众通过探明危机事件的原因来进行责任推断,并更好地认识和应对危机。依据归因理论,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会自然地利用各种信息对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决定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推断(Mayer et al.,1995;徐彪,2013) 。
公共危机发生后,公众有两种归因路线:原因属性分析(Ross,1977)、责任推断(Hamilton,1980)。在原因属性分析中,公众首先利用各种信息对危机事件的原因进行推断(Gillespie & Dietz,2009),危机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因为政府的能力不足,或者道德存在缺陷,也有可能是其他与政府不相关的外部原因引起的;在确定危机事件的原因后,公众会对危机事件发生原因的内外部性、稳定性和可控性进行评估(Weiner,1986)。内外部归因指危机事件原因是来自政府内部还是外部,对内外部性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是否应该为危机事件负责;可控制性是指危机事件的原因是否在政府能力控制范围之内,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危机事件的发生;稳定性是指危机事件的原因是否稳定存在,它影响着公众对在同样条件下危机事件发生概率的预期(徐彪,2013)。
在上述原因属性分析的基础上,公众进行责任推断。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关注的重点不是危机事件的客观原因或结果,而是谁更应该为事件负责并受到惩罚。公众对危机事件原因属性的分析,尤其是内外部归因、可控性归因,对责任的评估具有重要影响。但在责任推断中,除了危机发生的客观原因之外,还会受到道德、认同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其更加看重道德责任(Brewin & Antaki,1987;Martinko,1995)。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晕轮效应,公众在责任推断的过程中会存在爱屋及乌的强烈知觉特点,对政府的某些品质、特性的认识,影响到对其在危机中责任的感知;如公众对政府有负面认知,则倾向于认为政府应该对危机事件负责。
兰格(Donald Lange)和沃什本(Nathan T. Washburn)(Lange & Washburn,2012)整合了这两种归因路线,构建了更加全面的责任感知模型,在模型中包括了危机事件原因属性的分析、认同、受害方的共谋关系等多个因素。考虑到责任感知不仅受到危机事件产生的客观原因的影响,公众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到责任感知;因此,本文在兰格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政府组织的特殊性和政府责任本身的特性,从归因视角提出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模型(见图1)。在政府责任感知形成的过程中,公众进行了原因属性分析和责任推断,前者包括内外部归因、可控性归因、稳定性归因;后者包括公众对政府和受害方的态度、心理认知等变量。

公众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感知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危机事件原因属性与政府责任感知
对于危机事件原因属性的分析,公众遵循这样一个逻辑思路:首先,判断危机事件是不是政府内部原因导致的,然后再判断是政府能力因素还是道德因素造成的(Tafel & Turner,1986)。按照该逻辑,公众首先对危机事件原因的归属进行判断,即判断公共危机是政府内部(如政府组织、官员等)造成的,抑或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如果公众认为是政府外部或环境因素导致了危机事件,这些原因会被认为与政府无关。那么唯一与政府责任感知相关的归因维度是可控性归因,如果危机事件不在政府可控范围之内,则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发生不承担责任。因此,在公众归因过程中,首要的、最重要的是明确危机事件的发生是因为政府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如果公众相信危机事件的原因与政府无关,是政府外部原因导致的,政府不会受到公众的指责,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较小。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公共危机事件的外部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当公众判断公共危机事件是政府自身原因造成时,公众会进一步判断是政府的道德缺失还是能力不足导致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公众通过评估政府是否有能力解决公共危机事件,来判定是否存在能力不足;通过评估政府是否有意愿解决公共危机事件、政府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来判定政府是否存在道德缺失。但无论把危机事件归因到政府能力不足、还是政府道德缺失,都属于内部归因,会导致较高的政府责任感知。但是相对于能力不足归因,道德因素对政府而言更加可控、也更加稳定,其给公众带来政府责任感知越高(徐彪,2013)。因此,一旦公众认定政府违背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而掩盖或放任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就会产生道德危机,公众会更加的愤慨,并导致更加严重的政府责任感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于能力不足归因,道德缺失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的负向影响更大。
在确定了公共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内部或外部原因后,公众会进一步对原因可控性和稳定性进行判断。无论危机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内部、还是外部,当原因对政府而言可控时,政府会被认定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当原因不可控时,政府会被认定应该负较小的责任。稳定性归因决定了危机事件原因是不是不变的,或者是暂时的、多变的,是影响公众未来期望的关键因素。如果原因是稳定的,则公众会预期在类似情境下,同样的危机事件会再次发生;反之,如果原因是临时性的,则公众会预期在类似情境下,不会出现危机事件(Weiner,1986)。因此,对原因稳定性的推断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执政能力的评估、未来可信性的判断;但当危机事件被归因为政府社会管理下的常态时,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将会大大增加(Sitkin & Roth,1993)。
H3:公共危机事件的可控性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正向影响。
H4:公共危机事件的稳定性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正向影响。
(四)责任推断与政府责任感知
在上述原因属性分析的基础上,公众会对危机事件的责任主体(谁为危机事件负责?谁应受到惩罚?)进行推断,在这个过程中,其不仅受到原因属性的影响,更会受到态度、公平等心理因素的影响。由于晕轮效应的存在,对政府和受害方的心理态度和认知,会影响到危机事件道德责任的判断。
1.公共危机事件严重性与政府责任感知
公共危机事件严重性包括事件后果的严重性与事件的影响范围,其是影响公众直观感受政府责任缺失与否的重要因素。心理学研究显示,事件的严重性程度与观察者对事件的责任推断之间有正向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在组织危机事件中得到证实,随着危机严重性的增加,消费者把更多的责任归因于组织(Kim et al.,2006);同样的逻辑,公共危机事件会产生负面后果,如果负面后果越严重、影响范围越大,并且事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处理,此时,公众会认为政府在危机中应承担更大责任,其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越大。这种影响,尤其对低容忍度的群体(面对公共危机时所受到的刺激性和感知风险较高),会认为公共危机更具威胁性,他们会更容易责备政府没能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事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公共危机事件的严重性对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2. 受害方和政府的非共谋关系与政府责任缺失
“共谋”是个体或组织之间,为了谋取某种不正当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结盟的活动。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受害方与政府是否存在共谋行为,也会影响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Lange & Washburn,2012)。公众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受害方是否与政府发生共谋:(1)阻止危机事件发生的能力,指受害方是否已经尽力来避免危机事件发生。如果受害方被认为有能力对危机事件予以控制,但其却没有加以控制,那么其将承受更多的责任,即使受害方在危机事件中受到伤害,但其仍然不值得公众同情。相反,如果事件的受害方没有能力去影响危机事件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方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同情,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越高。因此,受害方阻止危机事件发生的能力越强,其越会被认为与政府存在共谋关系。(2)对危机事件的前瞻性或预见性。如果无法预见事件的不良后果,那么受害方不可能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因此也不构成与政府的共谋。因此,一些对事件控制力较弱、信息掌握不全的组织和个人往往不会被认为与政府有共谋关系,如受害方是权责较低的个人或组织时,政府责任会受到更加严重的质疑。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6:受害方和政府的非共谋关系对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3.认同与政府责任感知
认同是个体与认同目标一致性或归属性的知觉,当个体自我概念中的某些意识与认同目标的某些特性达成一致时,就会产生认同感(Dutton et al.,1994)。它来自于心理学中的个人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Tafel & Turner,1986),包涵价值认同、行为认同、情感认同等一体的认知过程。认同理论对个体和群体的认知和行为做出了新的解释(张莹瑞、佐斌,2006)。当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度较高时,就会较为容易接受政府的行为,并且一定程度上会对政府产生偏好、依赖;在较高的政府认同下,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责任推断就会倾向于弱化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当公众对政府认同度较低时,就会对政府的一切行为产生激烈的排斥,将所有危机事件都归因于政府。从我国近年来社会心态和舆论现象可看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政府行为,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素质,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安、怀疑和指责,人们开始把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医疗药品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都惯性地归因于政府。正如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所描述的,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出台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 办坏事(黄卫平、刘世伟,2015)。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对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当公众认为自身在危机事件中受到伤害时,或者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很有可能遭遇当前受害方的境遇时,公众就会更加同情受害方。尤其在受害方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时,就会激发公众对受害方的保护欲,以及对政府责任缺失的激烈批判。从经验上看来,当社会公众对在公共事件中受害方的认同度较高时,公众更倾向于弱化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消极作用及影响,反过来会强化政府应承担的罪责。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8:公众对受害方的认同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正向影响。
4.政府社会责任与责任感知
政府因为其拥有社会公共管理权而被社会寄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着眼社会宏观层面的期望和要求,政府社会责任就是指其对这些期望和要求作出回应的责任。政府社会责任中责任承担者应当是政府、政府官员、非营利部门以及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其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应当对公众和利益相关者负责。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社会责任会对公众归因的判断产生一种晕轮效应,从而掩盖他们对危机事件进行客观的认识。依据克雷纳(Jill Kleina)和达瓦博(Niraj Dawarb)的研究,当政府具有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时,公众会把公共危机发生归因于政府以外的因素所造成的,政府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行为会降低公众的危险性感知(Klein & Dawar,2014)。
H9:政府社会责任越高,公众对危机事件中政府责任感知越低。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情境实验法分析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理。首先,收集现实中的公共危机情境,通过筛选,选择了5个样本情境;然后,分别根据这5种具体公共危机情境,对问卷进行修订;最后,基于设计的实验情景,展开情景实验,收集问卷数据。
1. 公共危机情境选择
我们从新浪、搜狐、雅虎、腾讯等门户网站的专题报道和热贴评论中,收集具有一定负面影响力的公共危机事件(2010—2013年),经过筛选,从2010—2014年之间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选取了5个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案例:贵州毕节小孩冻死事件、郭美美事件、四川什邡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北京“7·21”特大暴雨事件,并进行摘要性描述,包括危机事件名称、发生背景、发生过程等,做成PPT。在保证公共危机事件有多种归因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选择较少的案例,以减少案例差异对结论带来的影响。
2. 变量测量
研究主要涉及政府责任感知、公众对危机事件归因、危机事件严重程度、政府认同等潜变量。本研究中政府责任感知的测量,主要参考库姆斯(W. Timothy Coombs)(Coombs,1995,1998)的责任感知量表,用“政府应为危机事件承担责任”“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应为危机事件承受惩罚”两个问项进行测量。公众对危机事件原因属性主要测量三个维度:责任点、可控性、稳定性。责任点用“该事件是政府外部原因导致的”来测量,可控性用“政府可以影响(控制)该事件的发生”测量,稳定性用“政府经常会出现该类事件”测量。此外,对于事件内部原因归因,用“该事件是政府能力不足导致的”测量能力不足归因,用“政府并非以社会利益为导向(善意动机),导致了该事件的发生”测量道德缺陷归因。公共危机严重性量表,主要参考黄静等(2010)的研究,在马克斯汉姆三世(James G. Maxham III)和利特迈耶(Richard G. Netemeyer)(Maxham III & Netemeyer,2002:57-71)编制的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修改,形成2个题项,主要从事件严重程度和事件关注度两个方面进行测量,题项包括“该危机事件非常严重”和“该危机事件的关注度非常高”这2个题项。政府社会责任主要参考布朗(Tom J. Brown) 和达钦(Peter A. Dacin)(Brown & Dacin,1997:68-84)的社会责任量表,包括“政府具有承担社会责任意识”“政府能够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等5个测量条目。认同参考梅尔(Fred A. Mael)和蒂特里克(Lois E. Tetrick)(Mael & Tetrick,1992)开发的认同量表,并分别根据研究情景进行了修改,其中政府认同分别从政府组织、政府员工、对社会发展贡献、履行社会职能4个方面衡量,包含4个问项;受害方认同分别从行为、情感、利益诉求等4个方面衡量,包含4个问项。政府与受害方的共谋关系参考兰格和沃什本(Lange & Washburn,2012)的建议,从受影响方对危机事件的可控性、预见性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包含2个问项。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的7点量表进行测量。
3. 实验问卷
基于上述测量量表,针对每种情景都作了适应性修改,形成最终问卷。每个情景下包含 2份问卷,问卷1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前测量问卷,主要包括:政府社会责任、政府认同、受害方认同;问卷 2 是公共危机事件后的测量问卷,主要包括: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危机事件原因的属性维度、事件严重性、受害方的共谋关系等。问卷中各变量的问项进行随机排序,并且在问卷中分别设置了2个反向问题,以甄别出无效问卷。
(三)数据收集
我们选择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本科、专科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占社会公众的主流),可以防止以高学历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可能带来的偏差,同时他们又有较好的知识基础,能够准确地理解模拟情景和问卷中的问项,并且他们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比较贴切的看法。问卷以2种方式随机发放:(1)现场实验:利用样本回高校进修、学习的机会,小规模地展开情景实验,实验分成4个步骤:放映具体政府组织介绍的PPT,留充分时间供被试阅读;让被试填写问卷1;放映对公共危机事件做概要性描述的PPT,留充分时间供被试阅读;让被试填写问卷2。(2)利用历届本科、专科毕业通讯录,随机抽取样本,获取样本的联系电话和Email,通过网络(QQ)发放问卷,并电话或QQ短信告知调研背景,实施过程分为4个步骤:阅读政府组织相关材料(PPT)、填写问卷1、阅读危机事件相关材料(PPT)、填写问卷2。为了保证问卷质量,回收的问卷立刻有专人检查、校对,并与被试沟通。
研究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42份,去除不合格问卷44份,有效问卷299份,有效回收率为74.75%,其中现场发放问卷243份,网络发放问卷56份。研究对象分布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高校、公益组织等多种类型的单位,样本来源的多样性有效减少数据收集时的系统误差,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按照模拟情景来分,“毕节流浪儿童冻死垃圾箱事件”43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42 份,“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71 份,“三鹿奶粉事件”72份,“‘7·21’北京特大暴雨事件”71份。
四、数据分析
(一)变量测量的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均来自于国外的成熟量表,在问卷最终确认前,通过咨询相关专家和学者,通过预试,再次修正了问卷的部分内容,可以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在正式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检测量表的结构效度和信度。结构效度是指问卷是否测到所要测量变量的理论结构,可以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判断实际测量的变量结构与理论变量结构是否一致。我们利用SPSS13.0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对各量表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785,Bartlett检验的卡方值高度显著,说明整个量表都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潜变量的20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处理,以特征值大于或等于1作为因子提取原则,最后提取出6个因子,分别是:政府责任感知、政府社会责任、受害方认同、政府认同、受害方共谋、事件严重性。6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73.107%,各题项在相应的因子上均具有较大负荷,最小因子负荷为0.558,均大于0.5。且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符合测量学的标准,被认为可信度较高。结果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此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用来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表1 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汇总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各变量之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与外部归因显著负相关;与内部归因(道德归因、能力归因)显著正相关;与可控性归因、稳定性归因显著正相关;与事件严重性显著、受害方认同正相关;与政府社会责任、政府认同、受害方合谋显著负相关。这些关系将在后续分析中,通过更加严谨的分析方法做进一步检验。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N =299)
注:*P<0.1,**P<0.05,***P<0.0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政府责任感知的组间差异分析
1.内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为了进一步考察内、外部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影响,我们将样本分组。我们使用问卷中的外部归因题项“该危机事件是由政府组织外部因素导致的”,来判断被试对危机事件的内外部归因。由于问卷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4是量表中值,因此该问题认同度打分高于4,则判定为外部归因;问题认同度打分低于4,则判定为内部归因。最后得出122个内部归因样本,93个外部归因样本;其中外部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2.704,小于内部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3.500,其T检验结果显著(见表3),说明内部归因导致更高的政府责任感知。
此外,针对能力归因和道德归因两个题项,通过被试的认同程度打分,来判断被试是能力/道德归因。考虑4是量表的中值,因此对能力归因题项认同度打分高于4、道德归因题项认同度打分低于4,则判定为能力归因;反之则为道德归因;如果两个问题认同度都高、都低或没有明显倾向(居中)时,则判定为无效。最后得出22个能力归因样本,46个外道德归因样本。其中能力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2.591,小于道德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3.087,但T检验结果不显著(见表3),说明道德归因与能力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没有影响。

表3 内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注:方括号内为P值;*P<0.1,**P<0.05,***P<0.0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 可控性、稳定性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基于危机事件可控性、稳定性归因题项,分别将样本划分高可控组(191个样本)和低可控组(50个样本)、高稳定组(151个样本)和低稳定组(70个样本)。其中高可控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3.174,大于低可控组的政府责任感知2.683,其T检验结果显著(见表4),说明可控性归因导致更高的政府责任感知。此外,高稳定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3.217,小于低稳定归因组的政府责任感知2.526,且T检验结果显著(见表4),说明稳定性归因导致更高的政府责任感知。

表4 内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注:方括号内为P值;*P<0.1,**P<0.05,***P<0.0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 其他变量与政府责任感知

表5 内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
注:*P<0.1,**P<0.05,***P<0.0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我们还依据其他影响责任推断的心理变量,分为高得分组和低得分组,对组间政府责任感知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1)依据事件的严重性感知,把样本划分为高严重性组(257个样本)、低严重性组(16个样本),高严重性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3.051,低严重性组的政府责任感知3.042,T检验结果不显著,说明危机事件严重性不影响政府责任感知。(2)依据政府社会责任感知,把样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责任高感知组(256个样本)、政府社会责任低感知组(24个样本),高社会责任感知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2.937,低社会责任感知组的政府责任感知4.174,T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政府社会责任对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感知存在晕轮效应,政府社会责任越高,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越低。(3)依据政府认同,把样本划分为高政府认同组(230个样本)、低政府认同组(39个样本),高政府认同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2.881,低政府认同组的政府责任感知3.846,T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政府认同对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4)依据对受害方的认同,把样本划分为高受害方认同组(259个样本)、低受害方认同组(30个样本),高受害方认同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3.683,低受害方认同组的政府责任感知2.982,T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受害方认同对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感知有正向影响。(5)依据受害方共谋,把样本划分为高受害方共谋组(102个样本)、低受害方共谋组(148个样本),高受害方共谋组的政府责任感知为2.982,低受害方共谋组的政府责任感知3.683,T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受害方共谋对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感知有负向影响。
(三)回归分析
由于在同一案例情境下,多个自变量(或归因变量)同时存在,因此不能直接把政府责任感知的组间差异,归结为某个归因变量造成的。因此,我们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考察原因的属性维度和责任推断的影响变量对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责任感知的影响。我们构造了5个回归模型,逐步进行了回归分析,模型的因变量是政府责任感知。模型1中自变量包括外部归因、内部归因(道德归因、能力归因);模型2加入可控性归因、稳定性归因作为自变量;模型3加入事件严重性作为自变量;模型4加入政府社会责任、政府认同作为自变量;模型5中加入受害方认同、受害方共谋作为自变量。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中的R2可以看出,多元回归方程拟合效果比较好。另外,我们还对模型进行了共线性诊断,方程各系数的容许度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续上表)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事件严重性0132∗∗0150∗∗∗0113∗∗[0012][0001][0018]政府社会责任-0353∗∗∗-0336∗∗∗[0000][0000]政府认同-0222∗∗∗-0239∗∗∗[0000][0000]受害方认同0034[0457]受害方共谋-0099∗∗[0010]_cons2630∗∗∗2730∗∗∗1996∗∗∗4660∗∗∗5767∗∗∗[0000][0000][0000][0000][0000]R202160231024804190436ΔR20015001701710017F值2714∗∗∗1764∗∗∗1603∗∗∗2609∗∗∗2224∗∗∗
注:方括号内为P值;*P<0.1,**P<0.05,***P<0.0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模型1考察了内、外部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外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显著负相关,内部归因与政府责任感知显著正相关。其中,公共危机事件的政府能力归因和政府道德归因,都会导致政府责任感知的增加。但相比能力归因,道德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的正向影响更大,公众对危机事件的政府道德归因,会引起更强烈的政府责任感知。H1和H2得到支持。所以,相对于内部归因,将危机事件归因于外部原因,更有利于降低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当然,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确实对危机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此时,相对于政府道德归因,将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能力不足,更有利于弱化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模型2在“内外部归因”的基础上加入“可控性归因”和“稳定性归因”两个自变量。由模型2可知,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可控性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H3得到检验。因此,不可控归因成为弱化政府责任感知的重要工具。其次,稳定性归因对政府责任感知没有显著影响,H4没有得到统计支持。这可能是因为,稳定性归因只能影响公众对未来事件再次发生的预期,并不影响其对谁应对危机事件负责的感知。
模型3中加入“事件严重性”变量。由模型3可知,危机事件越严重,政府责任感知越大,H5得到验证。模型4中加入“政府社会责任”和“政府认同”两个变量作为自变量,结果显示,政府社会责任和政府认同越高,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越弱,H7和H9得到统计支持。这说明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存在晕轮效应,公众对政府的初始态度和认知越好,公众越倾向于相信政府在危机中尽责,并更加容易原谅政府不当行为。模型5中加入“受害方认同”和“受害方共谋关系”作为自变量,结果显示,受害方认同对政府责任感知没有显著影响,H8没有得到统计检验。受害方共谋对政府责任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受害方共谋感知越高,政府责任感知越低;当受害方没有能力预见和控制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他们更能得到公众的同情,相对的,对政府不负责任的指责会更严重。H6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研究启示
(一)结论与研究启示
本文基于归因理论,探讨了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责任感知的形成机理,构建了政府责任感知模型。并利用情境模拟实验,定量考察了公共危机发生原因的属性特征、责任推断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相对于内部归因,外部归因会弱化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的感知;(2)在政府内部归因中,相对于将公共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部门道德上的缺陷,将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能力不足,更有利于弱化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3)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可控性越高,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越强;(4)危机事件的稳定性归因不影响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5)危机事件越严重,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越强;(6)“政府社会责任感知”和“政府认同度”越高,公众越倾向于相信政府在危机中尽责,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越低;(7)“受害方认同”不影响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但“受害方共谋”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现实启示:(1)政府要重视引导公众对危机事件原因属性的分析。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应尽量把危机事件产生原因归为政府外部环境因素,则可能弱化政府责任。当然,外部归因要结合危机事件的实际,保证外部归因的可信性;如果违背真实情况,一昧的将危机事件归结为外部原因,公众会认为其有推卸责任之嫌,其不仅不会弱化责任,甚至可能加剧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2)在政府确实负有责任的危机事件中,政府要有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对危机事件进行内部归因;但与公众的沟通中,尽量强调政府某方面能力的不足,不要强调政府的道德、价值取向上存有缺陷;同时,在内部归因的同时,要尽量强调原因的不可控性,这些措施都可以尽可能的弱化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3)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应采取一些正当措施来减少事件后果的严重性和关注度,如用新的热点问题覆盖公共危机事件,让舆论焦点得以转移。(4)政府应重视“晕轮效应”,通过长期的行为过程建立“责任政府”,保证持续的公信力,增强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度;并在日常工作中,谨小慎微,珍视声誉。只有政府公信力高,公众理解和相信政府,才能弱化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感知。(5)此外,当受害方在危机事件中负有责任时,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向公众公开信息,让公众了解受害方对危机事件的控制力和预见性,从而正确地认识到受害方对危机事件也存有责任。
(二)理论贡献与未来研究方向
目前,理论上关于公共危机中政府责任缺失的研究,大多停留现象层面,对政府责任缺失原因进行直观判断和经验总结,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此外,大多数研究是基于政府行为责任的视角,认为政府的一些不当行为导致了其社会责任缺失。忽视了政府责任是公众的主观感知,单一的从政府行为责任视角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偏颇。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文献,本文主要从公众感知视角,整合了公众原因分析、责任推断过程,探讨了危机事件后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理。其对于危机管理、公众认知等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个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感知可能具有倾向性,本研究没有这种个体倾向;未来可以在控制个体倾向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考察。(2)本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政府部门和公共危机事件的描述,而公众对信息的吸收、反应,最终形成责任感知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段,并且是动态更新变化的。因此,未来可以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跟踪观察,从而可以更加贴近现实地考察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过程。(3)本研究仅选择5个实验情境。本研究被试主要为“本科、专科毕业生”,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推广至其他情境和其他群体,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黄静、王新刚、张司飞、周南(2010). 企业家违情与违法行为对品牌形象的影响. 管理世界,5:96-106.
姜晓萍、张亚珠(2015). 城市空气污染防治中的政府责任缺失与履职能力提升. 社会科学研究,1:44-49.
黄卫平、刘世伟(2015). “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战略辨析. 政治学研究,5:3-9.
孙彩虹(2010). 政府责任缺失的理论阐释. 学术论坛,1:40-43.
徐彪(2013). 公共危机事件后的政府信任修复. 中国行政管理,2:31-35.
徐彪(2014). 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和情景实验. 公共管理学报,2:27-38.岳经纶、李甜妹(2009). 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香港模式的启示. 公共行政评论, 6:81-104.张莹瑞、佐斌(2006). 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14:475-480.
Brewin, L. R. & Antaki, C. (1987). An Analysis of Ordinary Explanations in Clinical Attribution Research.JournalofSocialandClinicalPsychology, 5(1):79-98.
Brown, T. J. & Dacin, P. A. (1997). The Company and the Produce Corporate Associations and Consumer Product Response.JournalofMarketing, 61 (1):68-84.
Coombs, W. T. (1995). Choosing the Right Words: The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Appropriate”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ManagementCommunicationQuarterly, 8(4):447-476.
Coombs, W. T.(1998).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Crisis Situations: Better Responses from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JournalofPublicRelationsResearch, 10(3):177-191.
Dutton, J. E., Dukerich, J. M. & Harquail, C, V. (1994). Organizaitonal Images and Member Identification.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 39(2):239-263.
Ferrin, D. L. & Dirks, K. T. (2003). The Use of Rewards to Increase and Decrease Trust: Mediating Processes and Differential Effects.OrganizationScience, 14(1):18-31.
Gillespie, N. & Dietz, G. (2009). Trust Repair after an Organization-Level Failur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34(1):127-145.
Hamilton, V. L. (1980). Intuitive Psychologist or Intuitive Lawyer? Alternative Models of the Attribution Proces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39:767-772.
Kim, P. H., Dirks, K. T., Cooper, C. D. & Ferrin, D. L. (2006). When More Blame is Better than Less:The Implications of Internal vs. External Attributions for the Repair of Trust after a Competence vs Integrity-Based Trust Violation.OrganizationalBehaviorandHumanDecisionProcesses, 99(1):49-65.
Klein, J. & Dawar, N. (2004).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nsumers’ Attributions and Brand Evaluations in a Product-Harm Crisis.InternationalJournalofResearchinMarketing, 21(3):203-217.
Lange, D. & Washburn, N. T. (2012). Understanding Attribu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37(2):300-326.
Mael, F. A. & Tetrick, L. E. (1992). Identifying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Educational&PsychologicalMeasurement, 52(4):813-824.
Martinko, M. J. (1995).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Attribution Theory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Sciences. In Martinko, M. J. Ed.AttributionTheory:AnOrganizationalPerspective. Delray Beach, FL: St. Lucie Press.
Maxham III, J. G. & Netemeyer, R. G. (2002).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omplaining Customers’ Evaluations of Multiple Service Failures and Recovery Efforts.JournalofMarketing, 66(4):57-71.
Mayer, R. C., Davis, J. H. & Schoorman, F. D. (1995).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20(3):709-734.
Pearson, C. M. & Clair, J. A. (1998). Reframing Crisis Management.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23(1):59-76.
Ross, L. (1977).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Advancesin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 10: 174-221.
Sitkin, S. B. & Roth, N. L. (1993). Explaining th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Legalistic “Remedies” for Trust/Distrust.OrganizationScience,4(3):367-392.
Tafel,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orchel, S. & Austin, W. G. Eds.PsychologyofIntergroupRelations. Chicago: Nelson Hall.
Tomlinson, E. C. & Mayer, R. C. (2009). The Role of Causal Attribution Dimensions in Trust Repair.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34(1):85-104.
Weiner, B. (1986).AnAttributionalModelofMotivationandEmo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责任编辑:庄文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473116、7110203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4YJC630198)。
D63
A
1674-2486(2016)06-0144-20
*徐彪,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公共卫生管理与医疗保障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湾湾,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晓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浩,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