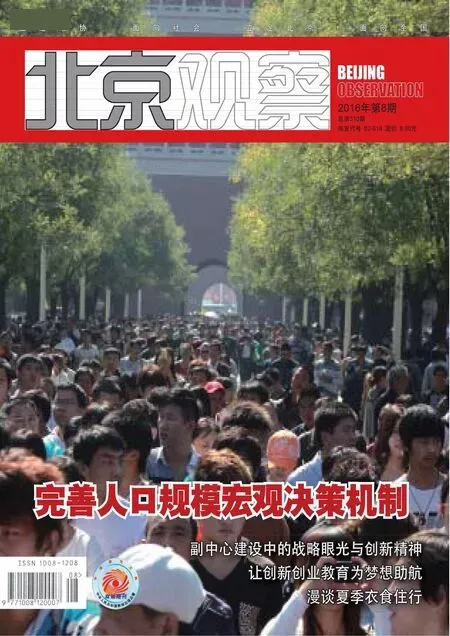楮树
文 蒋伟涛
楮树
文 蒋伟涛
东单公园的楮树是很多的,尤其是北边假山四周,除了南部乱石之中集中了几十棵外,爬到半山腰和山顶,随处可以见到草层中和石头缝里生长的楮树。楮树生命力很强,这些随处可见的小楮树,在岩石缝里成长长大,把根牢牢地扎在岩石缝隙里的泥土中。

东单公园随处可见的楮树
送女儿上学的缘故,早晨经常从东单公园东门穿行到西门,每每走在健身器材北边的小路,一组乱石之中二十余棵笔直挺拔的树,夺人耳目,很是好看。这就是楮树,在我的家乡随处都是。
东单公园的楮树是很多的,尤其是北边假山四周,除了南部乱石之中集中了几十棵外,爬到半山腰和山顶,随处可以见到草层中和石头缝里生长的楮树。楮树生命力很强,这些随处可见的小楮树,在岩石缝里成长长大,把根牢牢地扎在岩石缝隙里的泥土中。
楮树生长得很迅速,每年秋季,公园管理人员都会把楮树砍掉,否则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但是楮树的根部很发达,攀援在岩石缝隙之中,很难除掉,结果是到了来年,像野草一样长得更加迅猛,这样根部越长越大,分不清到底根扎在泥土之中有多深。走在上山的小路上,两边随处可见楮树的幼苗。
楮树的叶子很是奇怪,每一个都不一样,经典的是像京剧花脸一样的半月对称形。还有的是半边构形,另外一边则是全部,很是奇特。据说楮树的叶子与树龄有关,树龄越大,树叶越平滑。好像被什么“咬过”似的一般是树龄小的楮树。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被咬过”的叶子可以防止蝴蝶在其叶上产卵,因为蝴蝶、蛾等会认为叶子已被咬过,不利于其后代取食。这的确是植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好做法。
楮树,又名构树,是落叶乔木,我国北方和南方都有种植。《诗经·小雅·鹤鸣》篇写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g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毛诗品物图考注解说:“,木名,也叫楮树,落叶乔木,叶子卵圆形。树皮可用来织布、造纸。其汁白色,可团丹砂。”但朱熹注云:“,一名楮,恶木也。”这位道学先生一开口就否定了楮树的价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但他总算证明了楮和是一物而异名。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叶子卵圆形的描述却是感觉不太像,北方楮树叶子很像是花脸脸谱,整体上是圆形,但是中间部位有对称的中空。(gǔ)《,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落叶乔木,叶子卵形,叶子和茎上有硬毛,花淡绿色,雌雄异株。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

楮树的果实

楮树花

楮树的叶子
初春,楮树先开花。三四月间,在我的家乡豫东田野之中可以看到雄树开花,是浅绿色,长长的,很像松毛虫,也像长长的桑葚。春天菜不是很多,母亲有时会把楮树花做蒸菜。首先把楮树花洗净,控净水分,撒上适量的干面粉,拌均匀,让楮树花都裹上面粉。然后放到蒸锅蒸,水开后蒸5分钟即可。吃的时候可以蘸蒜泥、盐、生抽、醋和香油调好的汁,闻起来清香,吃起来更是美味。可惜如今很多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一想到农村的春天,就会想起槐花的清香,榆钱儿的可口,荠菜的美味。可不知为何,却很少有人提起楮树花。
古人对植物的研究的确是高超的,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里,对于植物、草药的依赖和研究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楮树是难得的药材,其树叶、枝、茎、果实、皮下黏液等都是一些非常难得的特效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归纳楮树叶的治疗效果,有利小便、去风湿、治肿胀、治白浊、去疝气、治癣疮等。至于说果实,据《本草纲目》列举,它的疗效很广,比如说能治阴痿和水肿,又能益气、充饥、明目,久服不饥、不老、轻身。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中记载:“柠木实赤者服之,老者成少,令人彻视。道士梁须年七十,服之更少壮,到百四十岁,能行及走马。”葛洪的话是否可信,的确耐人寻味。
宋代诗人刘克农有诗云:“楮树婆娑覆小斋,更无日影午窗开。一端能败幽人意,夜夜墙西碍月来。”后村居士嫌楮树枝大叶满,以至于遮蔽日月,很是有趣。楮树虽然不能成材,但可以做成良纸。《天工开物》记载:“凡纸质用楮树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看来楮树的“恶木”名字言过其实。
对于造纸的记载,在网上搜集到资料一则。西双版纳傣族以构树皮为原材料造纸,俗称“构皮纸”,而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长期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傣族创造了一整套优良的土法造纸技术:从山里采回构树皮,刮去表层,晒干;切成片状,放入池水中浸泡数天,同时在池水中加入火灰、石灰等可促进其软化的添加剂;取出清洗干净,去除杂质,放入锅里熬煮四至五个小时;再取出放在石头上用棍棒反复敲打,使其纤维尽量张开;放入纱布里进行清洗,过滤,形成浆块;将纸浆块放入水池中,搅拌均匀,最后用纸模淘器淘出一层薄薄的纸浆,滤去水分,晾干即形成纸张。在纸张取出之前,还要用一个小瓷碗倒扣在纸模淘器里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摩挲,使纸张光滑平整。西双版纳当地居民将这种纸张称为构皮纸或土绵纸。纸模淘器一般为长50厘米,宽40厘米的木框,中部为比较细密的纱网。直至今天,西双版纳仍有部分傣族村寨保持着这一古老的造纸传统和技艺,依然如故地制造着同样的纸张。
楮树的叶子刚长出来是嫩绿色的,后来叶子慢慢长大,光看叶子也分不清楚它们的雌雄。初夏,雌树会结出果实,刚开始树上挂满青青的果子,就像未熟的杏子一样,好看极了。再过些时日,青果子会渐渐变红,最终成为红红的,近看,红色里面是白色,均匀地黏在果核上面,远看是色彩鲜艳的圆球形果实,像一盏盏小红灯笼,点缀着红色果实的树枝依偎在幽绿的树叶上,很是好看。成熟后,会啪地落在地上。我记得小时曾吃过,味道有点酸酸的,酸中带甜,但据说这果实是不能吃的。小时候学《杨梅》那篇课文时,我们会误认为这就是杨梅。
楮树的果实除了吃外,也可以作为孩童的武器。有时候,我们兵分两组,把楮桃子用来当武器,规则无非是看谁对“敌人”的命中率最高,常常弄得青头紫脸的,少不了要挨老爸老妈一顿责骂,但还是乐此不疲。
自从认识了楮树,我发现北京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去年的遵义行一路之上也看到很多山坡都有楮树的身影。尤其是在遵义市内小龙山上的红军烈士陵园,当看完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级军事将领邓萍墓后,正欲转身,突然发现脚下一片红色的浆果,定睛一看这不就是楮树的果实吗?十几棵楮树挺拔地矗立在邓萍墓前的山坡上,仿佛一个个卫士保护着红军墓。
《酉阳杂俎》上说:“构,田废久必生。”确实如此。东单公园、东交民巷、前门街道、北大校园、百望山、昌平虎峪沟、香山等均有许多自然生长的楮树,其中百望山尤多。楮树很易成活,所以东单公园假山上随处可见。它的种子随风飘到哪里,它就在哪里成长起来。有一天从台基厂头条过,在路边墙根下,看到一株楮树幼苗居然在墙根缝隙里探出了脑袋,在风中随风荡漾着,在这大都市里就像害羞的乡下小姑娘,给人一种清新和惊喜。
北京市老干部局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