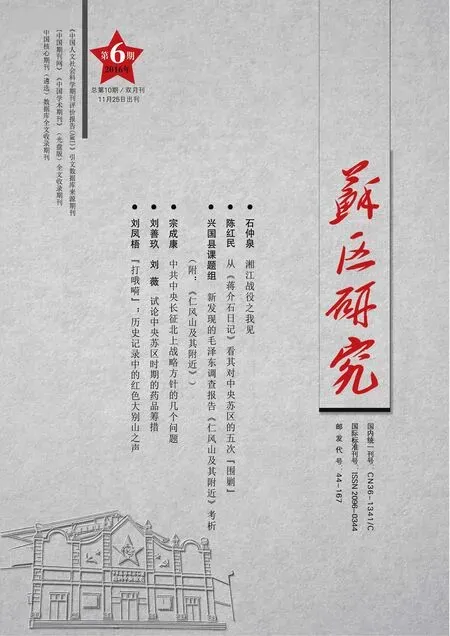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探析
邓美英
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探析
邓美英
劳动妇女是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主要对象之一。她们以母亲、妻子或女儿的身份,在苏维埃制度下展现出劳动之美、革命之光、地域之别和性别之优,创造性开辟一个给予自己获得尊严和成长的生存空间。劳动妇女的政治动员,一定程度上感染和带动了非劳动妇女的进步,虽然她们在性别征用中表现各异。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发出自由与解放之声。由于既有的结构性因素与传统文化的限制,妇女与男性的真正平等还道路漫漫。
中央苏区;政治动员;性别征用;妇女解放
政治动员需要汇集包括性别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社会性别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资源。中央苏区对妇女的政治动员,发生在战争生死存亡的危机和资源匮乏时期,劳动妇女作为母亲、妻子和女人的身份角色资源显示巨大的能量,成为政治动员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劳动妇女在苏维埃社会“性别制度体系内”*王宏维主编:《女性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展现出劳动之美、革命之光、地域之别和性别之优,创造性开辟一个给予自己获得尊严和成长的时空维度。
一、性别优势: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的天然资源
当革命触及苏区妇女,“性别作为革命引擎在第一时间被人们体验为某种生活方式以及身体自由”*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页。。劳动妇女在经济和身体上获得的相对自由,成为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的重要前提。
(一)劳动妇女的生活现状
在中央苏区的赣西南和赣南偏僻山区,妇女大多未缠足。她们同男子一样,是生产劳动的主力,耕田、种植及家务劳动等无所不担。“妇女都是和男人一样的大脚,耕田做工都是和男子一样的负担”。*《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节选)》(1931年10月6日),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闽西的情形与赣南相差无几。“耕种主要依靠于女子。”*《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妇女参加各种劳动需要健康身体作为前提,无论大足还是小足,苏区妇女都赋予自身在劳动中的自然之美。
苏区妇女虽是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主力,但经济上没有过问权,是男子经济的附属品。*《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40页。她们不能与男人同一张桌子吃饭,甚至衣服都不能与男子的用同一根竹竿高挑晾晒。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政治地位,痛苦比谁都大。但是常年的辛苦劳作,造就了妇女健康的身体和吃苦隐忍的坚毅品格。当这样的品格和身体,一旦获得外部条件的支持,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无人能替代。
(二)劳动妇女的主要特色
中央苏区劳动妇女在社会、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在政治动员中充分体现出她们的劳动之美、革命之光、地域之别、性别之优。她们作为一股天然政治力量,在政治动员中与男子们一样并肩革命。
1.劳动技能与潜能的挖掘
健康的身体,是妇女承担繁重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双重任务的前提。由于日常的辛勤劳作,她们对各种农时工作从准备到完成都显得得心应手,熟稔于心。春耕秋收之时,她们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以江西兴国为例,长冈乡16岁至45岁的全部青年壮年733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320人,在乡413人。其中男子只87人,女子竟占326人(1:4)。*《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01页。可见女性成为劳动的主力。城冈区妇女根据“夏耕运动的经验和成绩,有系统的召集妇女干事会主席团会议以及妇女群众大会,提出讨论计划”*《兴国城冈区劳动妇女对秋收工作的准备》,《红色中华》1933年8月1日,第3版。。在“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动员下,女子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顺利完成政府规定任务。劳动妇女能掌握犁耙这样高难度和高强度的生产技能,劳动潜能开发出来,劳动之美特色充分展示出来。对她们而言,健康的身体成为她们获得自身解放的客观前提。
虽然有学者指出,“当年苏区乃至后来解放战争中的妇女解放运动,事实上是为了应付战时乡村大量缺乏男性劳动力而给生产带来的困难,希望女性因此挺身于生产及乡村社会生活舞台的前沿”*吴重庆:《革命的底层动员》,《读书》2001年第1期,第23页。,但这种希望或美好愿望如果不是建立在苏区妇女原本就有的健康身体和一定的劳动技能基础之上,恐怕妇女解放早已成为历史的泡沫。恰恰是劳动技能和劳动潜能的进一步释放,苏区妇女生存能力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才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劳动重新认识自己的经济地位进而在政治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主人,为妇女走入公共领域获得社会认可提供历史前提。
妇女在革命中的身体优势,还体现在其灵巧的双手。中央苏区乃南方稻米之乡,利用稻杆编织草鞋是地方特色。经年累月的磨练,造就劳动妇女一双粗糙却灵巧的手。而劳动妇女在做草鞋布鞋方面明显优于男子。后方送给红军部队的大量布鞋草鞋就是她们的杰作。一篇“从做好草鞋中体现妇女同志对红军拥护的热忱和工作成绩”*《对于做草鞋的意见》,《红色中华》1933年7月8日,第5版。文章,在动员妇女积极做草鞋的数量要求时,也提出了做好草鞋的高质量要求:草鞋不宜短;鞋底不宜厚;鞋脑上的缎子要按到大脚指的初节后一点,要把缎子按长一点,尖上的与腰上的三个缎子交齐在脚背上;鞋踭要勾一点,不要直,穿带子的空要退后一点挖;不要做小脚鞋,根本不适合战士穿!文章批评现实既尖锐,又很有针对性。小脚鞋的出现,或多或少是那些只呆在家里,从不出门劳动的小脚妇女做的。这个带有批评性的意见,将一部分非劳动妇女带入革命视野,引人注意,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行为的进步。善于做草鞋的双手,连同她们富有智慧的大脑和健康的身体,让苏区妇女的性别优势显露。妇女与男子体力上的差距通过灵巧的双手获得弥补。
2.社会性别的身体优势
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很少被人重视。在社会习俗和传统惯例眼中,她们被认为是愚笨的。但对女子的这种社会轻视,却被共产党在苏区革命中巧妙地利用起来,改变着社会偏见和她们自身的认识偏见。
女子身份在战争区域较男子更容易进入战斗状态,比如她们充当秘密交通员和侦探时,不容易被敌人发现。文献详细记载了中共对妇女身份重视的情况:“我们过去的经验女子充当交通是非常之好,因为女子是敌人不注意的,同时侦探敌兵消息,女子亦是适宜。因此,各级政府应督促妇女工作委员会去有计划的去组织妇女群众充当秘密交通员和侦探队。”*《紧急通告 妇字第一号——在阶级决战中妇女应做的工作》(1930年12月1日),《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21页。革命突破原有习俗,当女子的身份进入革命视野,乡村社会固有习俗随之被打破。
当然,这种革命身体的利用也是相互的,首先妇女本身要有非常愿意为革命工作的主观愿望。事实证明,她们有参加革命的勇气和决心。如“自动和帮助红军游击部队运输,到城市去买军需品,当交通带文件,在白色区他们的亲友家里去讲红军的好处”。*《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节选)》(1931年10月6日),《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32页。尤其在党的号召和动员下,革命起来的妇女直接参战,在“永丰全县及龙岗之沙溪上古、龙岗等区,公略之指桂、冠山,宜黄之东黄坡,万泰各边区、赣县之大埠、长洛、茅店等区”,广大妇女“努力的修堡垒,实行坚壁清野,看护伤病员,宣传鼓励慰劳作战的战士,组织妇女的宣传队进行向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进行敌人占领区域的秘密工作!”*《今年“三八”妇女节中江西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1934年2月13日),《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62页。她们发挥自己的身体优势,和男子一样并肩战斗,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女人而偏离苏维埃革命的轨道。
此外,耐心、细致、关爱之情,是多数女性特有的传统性格优势。女性进入看护学校后,可以学习专业技能,为伤员提供女性特有的关爱。她们的身影穿梭在医院,在床头,在伤员身边,展现女性身体的阴柔之美。红军战士在前方打仗流血,急需人员照看。为使女性在学习护理、照看伤员方面应战时之需,赣西南红色总医院决定开办一所女看护学校来照顾和安慰负伤同志,招录“学生名额一百名,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要忠实活泼可靠(稍识文字更好)”*《通告 第 号——选派活泼青年女子入看护学校》(1931年2月1日),《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26页。。
考察史实,妇女剪发,也成为政治动员中的一种独特资源。因为妇女剪发后多余的银器可以低价或无偿送给苏区政府,充当战争经费,支持革命。但农村妇女一般是不愿意剪发的,因为这是性别的象征,是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体象征。所以在苏区各地,动员妇女剪发,把自己的银器售卖或捐给苏维埃国家就成为性别动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剪发动员在中央苏区腹地瑞金等地触及最深。在九堡区,“一天就有三十余个妇女剪发,把插在头上的银针卖给政府”;在官仓区,“钟凤娇同志首先把自己的银器赠送给国家银行,因此影响到徐九秀、王检秀、钟发秀等妇女同志踊跃的把银器送给国家银行”。*《号召劳动妇女把银器售卖或捐给国家》,《红色中华》1934年7月21日,第6版。
二、介入革命: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的多元表达
革命启动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也让女性获得历史出场的机会。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不仅没有遗忘‘女人’,而且主动征用‘女人’,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目标增强感召力。”*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04页。中央苏区地域广大,革命触及深浅不一,妇女动员表现出多样化特点。
(一)妇女动员的地域差异(见表1)
在兴国、赣县、公略、万泰等赣西地区,劳动妇女革命意识成长快,确实被动员起来,“在经济上政治上摧毁了豪绅地主统治,而封建束缚,也相当的打破了”*《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1932年5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2页。。她们对革命身份认同度高,参与革命积极性提高。
相对而言,在赣东(如宁都、石城、广昌)等县,“女子的封建束缚更大,好在十六岁以上的,大部分还是小脚,劳动力弱”*《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73页。。妇女因缠足无法劳动,在生活上要完全依赖男子,加之落后男子的阻止、小孩子对妇女本身的累赘以及地主富农的破坏等因素,妇女明显受到更多的阻止和牵累,这些束缚着她们自由革命的身份发展。这些区域,妇女动员发展较慢,工作不到位。
在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各县妇女代表在扩红与慰劳红军中展开竞赛,自动承认数目。统计对比如下:
兴国、瑞金、博生、胜利等老苏区妇女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在扩红和做草鞋方面优势明显,政治动员的深入带来革命参与的巨大热情;而太雷、赤水等新苏区明显处于落后状况。思想意识落后进一步强化当地妇女的行为落后,根本无法将妇女解放与苏维埃阶级解放汇集在一起。
(二)争当模范:妇女政治动员的激励机制

表1 妇女扩红的地域差异*《各县扩大与慰劳红军的竞赛》,《红色中华》1933年10月6日,第1版。
1934年《红色中华》以瑞金红属名义,号召广大妇女努力成为苏维埃模范公民,条件是:“加入组织;必须劳动;有文化;不断接受教育;主动学习;为战争尽最大的力量服务”*《切实做到模范苏维埃公民的七大条件》,《红色中华》1934年7月26日,第3版。等等。紧迫的战时形势将中央苏区妇女推向一个两难境地:是努力成为一名“模范的苏维埃公民”,还是继续做一个“寄生虫”?明确的行为选择必然区分出妇女的革命态度。从模范苏维埃公民到模范红军家属,劳动妇女无论身在家中,还是走出家门,革命身份意识和行为互为提升。而要让落后妇女从“寄生虫”转变为模范的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公民,必须赋予革命身份的质变。
1.劳动争先的模范
劳动本是人人之责,当然也是妇女应有之义。当劳动从私人空间扩大到公共范围,妇女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延伸并拓展到社会公共领域。在苏区,妇女们善于挤出琐碎的时间,在红军来去的时候烧茶、煮稀饭、唱歌、呼口号来欢送与欢迎,帮助红军找禾草门板、买油盐柴米蔬菜等,更能主动完成上级分配和交代的劳动任务,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数量的布草鞋等。偏远地区黎川县的布草鞋任务远不如革命腹地的瑞金兴国等县的重,但劳动妇女被动员征用后,也会争先恐后努力完成。
政治动员的强大号召力,掀起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热情。有些地方在劳动中甚至出现“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32页。的场景。她们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女人而存在,革命动员让她们重新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和力量。大批男子上前线打仗后,她们成为生产劳动的绝对主力和革命的后方主力。
2.扩红慰劳的模范
妇女在家中是母亲、妻子或女儿,与她们的父亲、丈夫或儿子形成亲缘关系。曾经她们在家中地位卑微,无人认可。现在在扩红和慰劳运动中,家庭身份的角色转变,使她们获得了自己的尊严。尤其在成为苏维埃红军家属后,她们的名字第一次被历史记载。苏区报刊曾集中进行报道和大力宣传。
雩都罗江区前村乡李冬秀同志,“鼓动宣传自己的儿子去当红军”,上杭“才溪区同康乡的少先队大队长王大青同志,旧县新坊乡石隤村邓五妹同志,碧沙村李银秀同志”*《三个模范女性》,《妇女扩大红军的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6月11日,第7版。,都鼓动自己的老公当红军。长汀县大埔区东街乡余玉英,“鼓动自己的丈夫马上归队,并积极领导工农青年扩大红军”*古田会议纪念馆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1933.1-1934.12)》第8辑,2006年内部刊物,第84页。。江西省各地有名有姓的模范妇女还有很多:“夏侯招同志(兴国崇贤区上坪乡)鼓动老公当红军宣传十五个群众当红军,买公债十五元,草鞋廿双;曾四女同志(广昌长生挤区)查出六家地主富农,宣传儿子及侄子当红军,归队四人。”*《江西全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盛况》,《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0日,第2版。在博生等县妇女扩大红军及慰劳品数目也相当可观。这些有名有姓的普通劳动妇女,用她们灵巧的双手和执着的行为改变着乡村社会传统的偏见。
3.努力学习的模范
赣南闽西妇女多不识字。“只有些资产阶级的妇女亦是凤毛麟角写识文字的是百与一之比,但现在有些地<方>有妇女夜校,妇女少数进去读书”。*《赣西南妇女工作报告》(1930年10月),《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5页。劳动妇女识字后,她们很快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能主动接受文化教育,参加半日学校、夜学、俱乐部、识字班或进入列小。特别是年轻红军家属,除了参加生产和赤少队以外,还很积极进行文化工作。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设立专门学校,在马路边树立识字牌,建立乡村俱乐部列宁室,在家里、田间、作坊、工厂和兵营学习,“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55页。,最差的也能看得懂路条,提高参与革命斗争热情。
妇女受教育后,有的主持教育,有的能够带动身边姐妹主动学习,成为教育领域中的主力军。闽西苏区成年妇女学习的积极性尤其高,夜校女学员占70%左右,“仅新泉一区,就办起了18所妇女夜校,学员发展到700余人”*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但是,老年妇女观念落后,封建思想严重,不愿主动接受教育,对识字和学习有很大抵触情绪。
4.“寄生虫”式的妇女
与模范妇女比较起来,那些没能进入革命之列,或是日常行为被认为偏离革命轨道的妇女,可能成为“寄生虫”式妇女。但这些妇女又不在小脚女人之列,而是以其他种种方式表现。如有“帮助家婆压迫童养媳”的;有要“公家的钱买鞋子穿”的;甚至有“连洗澡水都要革委会的委员打给她”*《妇女工作决议》(4月10日),《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218页。。“寄生虫”式妇女在思想上是落后的,在行为上明显缺乏模范妇女的斗志和热情,似乎不在革命之列。
这个群体,常常阻碍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参军参战,那又如何去动员呢?苏区政府从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先从家庭入手,动员她们加入红军家属,在送郎送子当红军、归队、慰劳红军、加入消灭文盲的识字运动中,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接着从妇女身边做起。“送老公上前方;老公已经上了前方的要鼓动老公在红军中更加努力工作;未结婚的结婚后应鼓动丈夫去当红军;组织妇女扩红突击队,分送到各县工作。”*《湘鄂赣省的动员热》,《红色中华》1933年12月8日,第2版。最后,动员妇女参加归队运动。“不让一个跑回家的战士留在后方”*《瑞金全县红军代表大会给全苏区红军家属的通电》,《红色中华》1934年8月8日,第3版。,妇女要作为苏维埃公民,随时履行一个母亲的责任、一个妻子的责任,不贪图一家人团聚、不拖尾巴,就是增强前方战斗力,为保障革命胜利尽自己的力量。
(三)融入集体:妇女斗争的策略选择
妇女解放的阻力是来自他者,还是自身?有学者指出,“女性最大的障碍之一就在于她们普遍倾向于将任何失败和错误都归结为女性本性的一部分,是由她的性别而不是她个人的特质造成的”*[澳]亨利·理查森等著,郭洪涛译:《女人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女性要站出来成为自己,必须首先“把自己看做一个有理性的人”*[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瑛译:《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改变原有的认知,展现自己的主体能力。中央苏区妇女组织的逐步建立,为妇女主体认知解放和身体解放提供外来条件,开辟出道路。
1.到集体斗争中来
没有组织的推动,妇女进入革命有一个艰难的试探过程。起初,她们是不敢独自斗争的。来自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偏见时时阻碍着她们。她们不能与男子在同一个饭桌吃饭,没有自己的财产,更不能选择自己的婚姻。各种束缚让她们处处谨小慎微。从单独斗争到集体斗争,是妇女革命的一个明显特征。“一切群众示威游行等运动,均有女子参加,作战时妇女送饭茶慰问伤兵都极热烈”*《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92页。。中央苏区发布土地分配条例后,妇女获得自己的土地,劳动热情被激发,尤其是年满16岁后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机会同男子一样参与苏维埃政务的决策后,激起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和革命激情。在苏区革命进程中,反阶级压迫和妇女解放汇合在通往自由的大道上。
2.单独走出去
妇女单独斗争在苏区政府实行婚姻自由政策和免费获得学习权利后尤为突出。“瑞金壬田区的妇女与丈夫离了婚,就到区政府去住和吃饭。等找到新丈夫后,由新丈夫到政府来算饭账。”*《壬田区政府成为老公介绍所》,《红色中华》1932年5月25日,第8版。一位普通妇女从争取自己婚姻自由的权利开始,从逃离家庭压迫和丈夫的束缚开始迈出自己单独斗争的脚步。瑞金武阳区武阳乡下角的林生娣,用自己的银器换毛洋准备购买公债票,同乡郭九九叫她不要买。她马上报告乡苏,经妇女指导员召集群众大会,领导全乡妇女对郭九九进行斗争,罚他戴高帽子到市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模范区乡的革命妇女》,《红色中华》1933年10月9日,第3版。
中央苏区《共产儿童读本》第六册一篇课文“模范女同志”*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七)教材,1985年内部刊物,第35页。用两种斗争方式书写妇女斗争的模范。斗争起来的妇女用革命行动感染着即将走进革命的后来者——正在接受教育的妇女和女童。模范妇女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因为她们在革命中积极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模范妇女已经独立自主,因为她们在斗争与行动中学会依靠自身力量,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革命妇女内心强大的过程,正是她们摆脱无名的集体,逐步变成一个个名副其实的“自我”的过程。
3.再到集体中去
从集体中走出,又回到集体,妇女斗争方式“循环往复”的发展,提升着她们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智慧。
随着苏维埃革命在中央苏区各地的深入,妇女动员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这与苏维埃敬重她们密切相关。看轻劳动妇女“这种力量是一个罪过”,“要使每个煮饭的女工都能管理政权”*颖超:《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1933年11月29日),《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24页。。妇女获得的尊敬,是她们在苏区政府鼓励下,从参军参战到担任令人敬重的职位等方方面面展开的。
以江西省苏为例。1933年省苏发出创办干部学校令,决定开办土地、国民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内务劳动、工农检查及裁判6个干部班,规定1/3女性参加。妇女参加干部培训学习后,很快成为当地最有力的战斗员。尤其是各地乡村一级的“女工农妇代表会”,发动妇女参加会议,参与选举,扩红与慰红,讨论用银器买公债等问题,把广大妇女从家务劳动中带入日常政治生活视野,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毛泽东以江西兴国长冈乡女工农妇代表会为例,给予详细记录。*《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12页。女工农妇代表会是基层妇女视域中最直接的组织,集中讨论和解决妇女们碰到的各种问题,关心妇女切身利益,成为基层苏维埃领导妇女政治动员的显性力量。
妇女在家庭中是母亲,是妻子;在苏区社会中是公民,是战士。从家庭妇女到苏维埃公民的角色征用,引导着她们革命力量的生成。在面临第五次反“围剿”艰巨任务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群众一开始有抵触。妇女抵触情绪最大。因为要离开家,各种东西可能都会损失,妇女非常舍不得。如何说服妇女,促进她们的革命自觉?邓颖超指出,使妇女认识“只有苏维埃能解放他们,才能救中国”,“鼓励和发扬他们的伟大力量”*颖超:《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1933年11月29日),,《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25页。。贺子珍亲力亲为,经常一家一家去拜访,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说服年长的老婆婆,带动全家来“坚壁清野”。*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内部发行,第153-154页。妇女的抵触思想一旦获得改变,行动就最坚决,为革命投入也最深,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苏维埃公民,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红军家属”的身份与角色,架起连接小家与大家的桥梁。政府发动红军家属,通过寄一封信到前方的方式鼓励亲人勇敢杀敌。红属代表的信中写到:“家里田地有苏维埃派耕田队帮助耕种,柴水有政府工作人员供给,粮食缺乏的时候政府还募了很多米来给我们吃,各种合作社的油盐,廉价卖给我们”,“希望你们努力的在前方工作,更英勇的与敌人作战,多捉几个白军师长,多缴敌人的枪炮”*《“八一”红属代表大会前瑞金红军家属的活跃》,《红色中华》1934年7月26日,第3版。。政府组织红属亲笔之作,正是征用她们这种政治上的特殊身份,内心情感的释放,有效沟通起前方战士与后方家属、政府组织与群众的情感联系。
三、余论:政治动员背景下的妇女平等
中央苏区妇女的政治动员,通过激发革命意愿,提升参与革命热情,精心照料他人、甘于奉献精神的方式,在生产劳动、参军参战、婚姻自主、文化学习等方面全面展开。因为苏维埃政权制度赋予劳动妇女正当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中央苏区妇女的政治动员,为苏区劳动妇女缓解了来自性别差异的矛盾与冲突。
但是,妇女政治动员的效果,显然需要外力推动和内在自觉的双重作用。妇女主体在认知解放的过程中,仍受到经济限制与文化传统压制,这种局限在苏区社会的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克服。如恩格斯曾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但是,现状不容乐观,苏区劳动妇女“散居在男人中间,由于家务、居住、经济及社会条件等原因,须紧紧依附男人——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王宏维:《论他者与他者的哲学——兼评女性主义对主体与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45页。,要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解放,还很艰难。“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虽然,中央苏区建立的各种妇女组织,如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为劳动妇女获得自由与解放提供外在条件。1931年,永新县苏维埃政府翻印的有关实行妇女解放的革命标语,如“女子工作与男子同等的应有同等工钱”、“妇女产前产后应有两个月休息女工工钱照发”、“反对翁姑压迫媳妇”、“反对老公打老婆”、“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女子要读书识字”、“保护女工”*《赤色区域革命标语(节选)》(1931年3月14日),《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221页。,具体反映了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教育等各方面的迫切要求。理性地思考,这些口号要完全转换为行动仍然艰难,况且很多口号并不现实。例如“离婚结婚绝对自由”不无偏颇,各苏区很快在1931年后均予以废除。
显然,妇女与男子的真正平等依然是理想。因而,有劳动妇女在妇女代表会议中喊出:“一切革命工作,女子都去做,除红军外,后方工作,女子比男子还做得多,为什么女子还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咧?”*《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73页。她们学会了政治表达,提出各种要求和口号。但是,由于妇女身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限制,这些口号的落实依然道路漫漫。
责任编辑:李佳佳
Analysis of the CPC'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o Wome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Deng Meiying
Working women were one of the main objects of the Central Sovie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s a mother, wife and woman, they showed the beauty of labor, the light of revolution,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 and the specialty of gender, and opened up creatively a living space for their dignity and growth within the Soviet power system.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o working women has infected and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non-working women to a certain extent. Although they varied in gender requisition, they sent out the voice of freedom and liberation as a group.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structural factor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al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still had a long way to g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olitical Mobilization; Gender Requisition; Women Liberation
10.16623/j.cnki.36-1341/c.2016.06.008
邓美英,女,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省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江西南昌 330022)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中央苏区时期政治动员的分群分层研究”(JD1433);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动员中的课(教)本研究”(13ZD3L012);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研究”(15DJ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