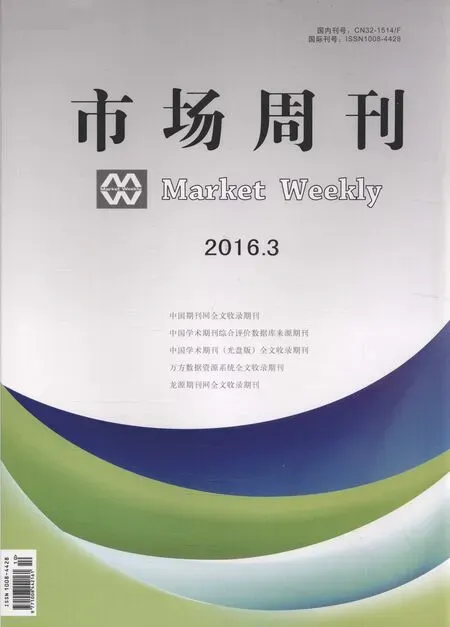合同约定解除之探讨
贺波
合同约定解除之探讨
贺波
民法崇尚意思自治,而合同约定解除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解除合同中的一个具体表现。由于合同约定解除相对于法定解除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不可完全预测性等特征,而合同解除又直接影响到合法生效的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因此,对合同的约定解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约定解除条件的成立与否之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结合中国国情与国内外学术理论前沿,对合同约定解除相关的基本概念,约定解除的条件,约定解除条件认定的基本原则、要素、标准以及特殊情形作了详细的分析,旨在解决实践中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成立与否之认定问题。
合同解除权;约定解除;约定解除条件;异议权;解除权的行使
一、合同约定解除的概述
(一)合同约定解除的概念
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订立双方可以在合同签订的时候约定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事先约定拥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就可以按照约定在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合同。意即,合同解除权在合同签订时具有可期性,当条件成就时,解除权发生效力。
由此可知,合同的约定解除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通过意思表示一致来约定当某种条件成就时,当事人运用享有的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这样设计不仅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来明确合同订立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还可以最大程度实现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期待的利益。
(二)约定解除的法律特征
1.不可归咎于当事人的因素和可归咎于当事人的因素是约定解除的两个原因。从合同订立目的的角度来看,当事人无疑是想实现其最初想要追求的利益。订立合同的作用,就是合同订立双方希望权利义务能够通过合同固定明确下来,以利益为出发点期待能够正确、及时地完成合同所规定的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约束对方当事人,将自己的权益最大化。在合同中就会反映出归咎于合同订立双方的人为因素。不可归咎于当事人的因素虽然也可作为解除合同的“约定”,但因该种情况大都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有关,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2.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合同的约定解除是在合同尚未完全履行完毕之前的行为。如果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合同订立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解除,就不可能再出现合同被约定解除的情形。笔者认为,从时间上看,约定解除可分为合同订立之时的约定和合同订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的约定。
3.约定解除一般表现为拥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单方面解除合同,往往都是约定合同一方当事人在解除条件具备时享有合同解除权,并根据自己的预期和衡量决定是否解除合同。
(三)合同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协议解除之间的区别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当法定的解除权产生的条件成就时,拥有解除权的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制度。
合同的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有以下区别:(1)解除条件的设定主体不同。约定解除是合同当事人基于意思表示一致以合同条款的形式设定合同解除的条件;而法定解除是由法律的明文规定来设定合同解除的条件。(2)是否基于意思表示一致不同。约定解除在合同订立时就通过合同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而法定解除在出现上述情形时,一方告知对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可,无需得到对方同意。其中迟延履行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经过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守约方才拥有解除权。(3)是否以违反合同约定为前提的不同。法定解除的条件主要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而约定解除不一定以违约为条件。
合同的协议解除,意指合同的订立双方在签订合同后,通过协商的方式解除合同,而使合同的效力提前归于消灭的行为。按照《合同法》第9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其实,从字面上来看,很难分清楚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合同解除方式,而且其也确实是合同订立双方通过一致协商得出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往往会分不清这两个概念。但二者在本质上又是两种不同的合同解除方式。
(1)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时间不同。约定解除权解除是在合同订立之前就已经约定好的,属于合同内容,合同中有也仅有规定合同能够解除的条件和合同订立双方中的一人享有的解除权;而协商解除却是在合同已经签订完毕以后双方当事人进行合意达成的,其所包含的意思是在合同成立后根据已经发生的需要解除合同的情况而决定解除合同。(2)是否真正导致合同解除的不同。有约定解除权,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合同要解除,因为合同的解除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够基本具备,合同就不可能被解除;而协商解除则是当事人双方因为想要解除已经生效的合同而通过意思自治的双方合意,所以,其结果是一定会导致合同解除。(3)约定解除权的解除往往是经过约定拥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而提出解除合同;而协商解除是双方解除,这种解除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二、合同的约定解除
(一)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及其甄别
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是指合同订立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约定好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解除合同的情况应当具备的条件,是合同当事人以契约的形式以及以合同内容一部分的表现形式规定的未来可以解除合同的不确定的解除条款。因此合同当事人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首先必须是一个事实,由于条件的不确定性,这个事实是否会发生也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实践中我们在甄别合同解除条件是否具备时,解除条件的具体含义不仅应当从文字意思方面进行解读,更应在综合整份合同的其他条款和衡平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以体系解释的方法予以理解。
(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及其效力
行使合同解除权,必须要以事先约定的解除合同之条件成就为前提,而且,该权利只属于守约一方。所以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及时出现解除合同条件成就的情况也并不必然导致合同解除,因为此时的守约方会进行一个利益衡量,他衡量的结果决定是否终止合同的权利义务。当然,守约方解除合同并不需要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同意。
拥有合同解除权的当事人在行使解除权时应当遵守法律和双方的约定中关于期限的规定,否则将导致解除权的消灭。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期限,拥有解除权的一方经对方催告后合理期限内仍不行使解除权的,也导致该权利消灭。
根据《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的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这一条规定虽然看起来非常确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引来了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很多合同订立人在通知对方要解除合同的时候,自认为已经具备了解除合同的条件,但往往对方当事人却不是这样认为。这就会导致前者的通知并不一定被认可而使合同解除权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其次,就是合同解除权人根本就没有按照程序履行解除合同之义务,而是径直走司法程序,要求解除合同。后者往往会被法院直接驳回。
(三)约定解除条件符合时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
当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合同当事人享有哪些权利?又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呢?
首先,毋庸置疑,约定解除权人(一般是守约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前提是其已确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已经成就,达到了约定的标准,而非自己臆定的标准。当然,解除权人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实体上要求其是根据合同的约定来主张解除合同,程序上要求其主张解除合同时,应当通知对方。
其次,解除权相对人(一般是违约方)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即解除权相对人对解除条件成立与否有异议的,可以就合同解除的效力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进行确认。另外,如果有相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要求在解除合同时必须履行相关手续,如办理批准和登记的,解除权的相对人可以请求解除权人按照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办事。当然,若果相对人的确明显违约并导致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其就有义务配合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并按照约定赔偿守约方的损失。
(四)解除合同除了具备约定解除条件外,还应考虑哪些因素
1.是否有违诚信原则
《合同法》总则第5条、第6条分别规定当事人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也就是说,当事人订立合同至其履行完毕的整过程都应该遵循诚信原则。而解除合同作为合同行为中的民事法律行为,更是应当严格遵守。
2.是否违背订立合同所要达到的目的
如上文所述,双方当事人既然会订立一个合同,就一定有其想要达到的预期的利益,如果合同在未完成前解除,就违背了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初衷。事实上,在实务中,如果合同的提前解除所带来的利益小于继续履行合同的利益的话,当事人一般会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履行合同的各种条件具有多变性,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解除合同所获收益大于继续履行合同所获收益的情况。
3.是否导致当事人的利益明显失衡
合同一旦被解除,除该合同根本未履行外,双方均要尽返还之义务。如果简单的运用解除合同的处理方式,既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本意,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
三、合同约定解除法律制度的完善
笔者通过研究,深刻体会到合同法理论与实务联系的紧密性和重要性。而且我们对合同约定解除制度上、实务上的思索远未终止。
《合同法》第93条第2款合同约定解除的规定,看起来较为明确,然而司法实务中的实际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此规定对合同约定解除的约束若有似无,根本起不到规制合同履行的作用,在实践中表现出任意性的特点,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可以任意约定解除条件。这不仅不利于交易,反而会影响市场秩序。
为了规范合同的约定解除,进一步保障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之策是尽快完善《合同法》对合同约定解除的具体规定,更加明确合同约定解除条件设定的限制。其次,严格规范有关约定解除条款在合同中的内容与格式,制定合理适用的合同解除程序。最后,要加强对交易秩序的管理和监督。
[1]郭明瑞.合同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04):210.
[2]杜晨妍,孙伟良.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J].当代法学,2012,(03).
[3]赵海洋,张洁.论合同约定解除权的行使[J].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报,2011,(01).
[4]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M].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杜晨妍,孙伟良.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J].当代法学,2012,(03).
贺波,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与军事刑法。
D923.6
A
1008-4428(2016)03-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