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真实的鲍勃·迪伦
龚依文
我看见一个新生儿,被野狼团团包围
我看见一条钻石高速公路,空无一人
我看见一根黑色的树枝,滴血不止
我看见一屋子人手持锤子,流血
我看见一条白色阶梯,浸没水中
我看见一万个言说者,舌皆破裂
我看见枪和利剑,握在少年手中
鲍勃·迪伦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民谣、摇滚歌手,并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言人。他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和后来的音乐人。他真正赋予了摇滚乐以灵魂。
毫无疑问,这样的录音带应该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恰恰是我们想了解的:迪伦的头脑在想些什么?他是如何思考的?他究竟要表达什么?“雨的答案”是什么?诸如此类。但是,等一下,他头脑里思考了些什么呢?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方式,去探究难以捉摸的鲍勃。只有这样才行,因为迪伦是一个垮掉派小说家,他像杰克·凯鲁亚克那样写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迪伦杰出的专辑中那丰富多变的幻象,是他内心骚动的表达,也映照着其时正在碎裂的文化。《席卷而归》(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还有《无数金发美女》(Blonde on Blonde)中的那些歌曲,是他内心矛盾和街头冲突的体现,是关于他自己和那个时代的虚幻式自传——20世纪60年代混乱的标志和精神状态。
迪伦正好出现在对抗文化孵化的时刻,他的人生与大众波西米亚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迪伦内心的狂热恰好吻合当时反主流修辞、毒品、政治激进、神秘主义以及被放大了的漂流情结。迪伦的个人故事——不管他喜不喜欢这故事——与20世纪60年代及其影响力交织在了一起。
一个机敏、多变、不可捉摸的灵魂,以他惊人的准确性表现了美国的“第十九次神经衰弱”(滚石乐队歌曲名)。断片式的形象和立体派歌曲取代了民谣歌曲(folk song)中的故事讲述和歌谣(ballad)形象,并且将抗议歌曲的宣传口号转变成一种煽动性的、梦魇般的视像,在其中你难以区分外界的混乱和内心的不安。
不管迪伦逃离风口多远,他都无法摆脱自己与对抗文化间的联系;他与他的时代有着犹如脐带一般的牵连。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的创作困境正好与那时的文化危机对应发生,也并不奇怪了。公众面和私人面的迪伦——其音乐、其时代,以及我们对他的感知——是内在交织的,一种时代精神的产物。
这正是为什么他变换了众多角色出现:风尘仆仆的歌者、街头顽童、“漫游的杰克”(Ramblin Jack Elliott)的儿子、民谣救世主、霓虹灯兰波、旧约先知、亚米西农民、乡村邻家男孩、白面化妆剧演员、帽里藏花的什罗普郡少年、耶稣一般的鲍勃、哈西德派(犹太教)的鲍勃、缠着WWE腰带的晚期猫王、不停巡演的迪伦、杰克·费特、活着的美国国宝……
迪伦是一个有策略的演员,他视自己的生活为一部象征性电影。演唱者通过声音塑造角色,使一首歌听上去可信。而迪伦对各种角色的改换(在2007年的电影《我不在那儿》里有戏剧性展现),是一种赝造真实性的方式——作为哈姆雷特的游吟歌手。迪伦视演艺者为美国的英雄。他的偶像全都是演艺者(还有作家,算是一个分支):盲人威利·麦克泰尔、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20世纪40年代美国乡村音乐的标志性人物、道克·博格斯、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埃尔维斯、詹姆斯·迪恩、卡鲁亚克。他们——加上逃犯、骗子、流浪者,还有诗人——都是迪伦常常乞灵的美国形象。在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国家,演艺者是我们拓荒路上的精神指引。
迪伦脱胎自那些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最混乱不清的、最吵闹的传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摇滚乐破土而出时,它首先被看做一种标新立异的东西。那些早期歌手,包括埃尔维斯,是一群奇妙和怪异的人。这个领域充满传奇角色:放浪的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胖子多米诺(Fats Domino),狂欢节的生动体现;杰瑞·李·刘易斯,他简直是活人打谷机;不断变形的布·迪德里;还有查克·贝里,摇滚战神般的邋遢大叔。而从他们开始回溯,远在现代美国之前,是一个更难以置信的角色阵容:阿帕拉契亚(Appalachia)的“煎锅”乐队、水罐乐队,充满启示的三角洲布鲁斯歌手,比如桑·豪斯(Son House)和斯吉普·詹姆斯(Skip James)。
迪伦像布雷尔兔一样狡猾,但是我的追根问底并不是要把他从假造的荆棘路上赶出去,而是去探寻迪伦的诗歌含义,经由歌曲的闪光来读解他的传记。我一直试着追随迪伦在流沙上的脚印,并且总是像一个手忙脚乱的音乐家一样,努力跟上唱片工作中的迪伦。
当《回忆录》(Chronicles)出版时,关于这本自传的可靠性的责难似乎很可笑。人们抱怨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仍然在杜撰着什么。真令人愤怒!他在戏弄我们!他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摇摆——而我们期待的只是真实的他。说到底,我们在和谁打交道?是善变、可恶、闪烁其词的鲍勃。吞云吐雾和制作镜子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他所虚构的那些东西,是他人格中最深奥、最有趣,也最本真的部分。像堂吉诃德一样,他似乎是从自己假想的神话里走出来的人物。他关于自己的那些杜撰比任何事实描述都更真实。无论他可能有多么狭隘、残酷、麻木和愤世嫉俗,那写下了《荒芜的街》和《乔安娜的影子》(Visions of Johanna)的玄妙的诗人,都不会与一个离婚的凡人,愠怒的、狡黠的被采访者,或者版权的篡夺者是同一个人。他的任性乖张是种顽皮的把戏,是种形式,这形式使其细心掩饰过的人格充满活力,却难寻踪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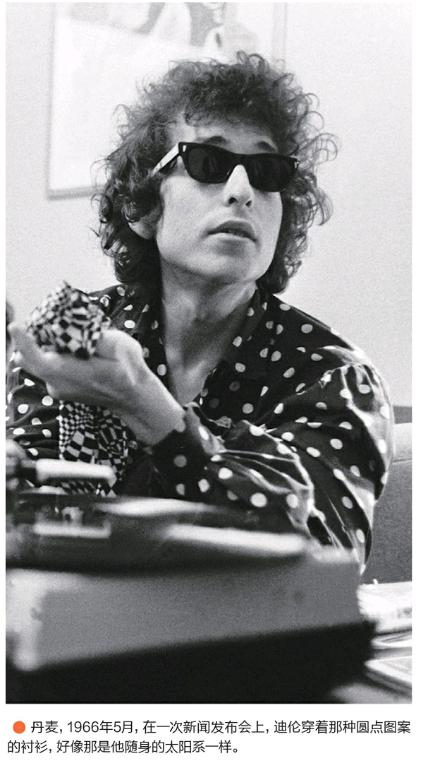
迪伦视美国为一首无尽的、未可完成的歌曲,在我们前行时,这首歌不停地被增加和删减着什么,改变节奏,删掉歌词然后改变顺序后重又修补回去。他是典型的美国人,一个自信的、藉假装来讲真实的人,他的出现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格这种东西。他是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实际上他是各类美国人的一个混合体:演艺人士、恶作剧者和偷盗者。
他的兴趣是把美国的历史碎片重新拼装——它的歌谣、曲调,以及早期的韵文寓言——把它众多的角色和故事的多样性浓缩进一首歌。他对歌曲、书籍和图像的坦率的盗用、窃取,都是他喜鹊一样的本性组成。他符合美国的鲁莽的传统,这种传统试图把密西西比、落基山脉、约翰尼·阿普尔西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还有孤儿安妮,统统塞进一个令人惊异的高大传说中。
我略过一部分时段而放缓另一些——以迪伦的方式暂停时间——那样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画面,同时努力跟上变色龙在石块间移动时的变化。
迪伦的自传和杜撰比任何人的都具有更巧妙的渗透性边界,现实与幻想的混合一直是他巫术一般的杰作。
他是最狡猾、最有意思的自我神话制造者,他精心策划,让我们卷入他那些充满寓意的角色里——他自己的人格是如此之深地寄生于他沿途收集的角色中,以至于他似乎常常不知道“他们”始于何时而“自己”止于何地——这在他的《主题时代·电台时间》里制造了一种怪诞的通灵般的感觉,他在其中成为乔治·琼斯、斯基普·詹姆斯,又或者成为一个冰箱修理工。
尽管迪伦常常迷失于自己的谎言迷宫里,那却使他更具有魅惑力。许许多多疯狂的歌迷拿着手电筒在他隐晦的思维里寻找着线索。
几乎关于迪伦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民间传说中的再造。美国是一部我们一边前行一边构写的小说。像迪伦一样,我们也是天才的虚构者。所以我们需要故事,越神奇越好:我们的歌曲、电影、广告、流行文化——这些都是将我们捆束在一起的虚构的生活。迪伦了不起的洞察力正体现在他看到了美国文化的神话躯壳——并且将其覆于自身之上。
甚至他来到这世界的方式都完全来自一个夸张的故事。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