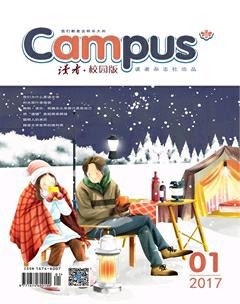鲍勃·迪伦: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
宛洋
鲍勃·迪伦,在每个文艺青年或曾经的文艺青年心中,这个名字,都近乎神明。
这个很少接受采访、私生活成谜、个性坚硬得如一块石头的老爷子,早就成为音乐史上一座活着的丰碑。
他写出过《答案在风中飘》这样脍炙人口的名曲,卖出过上亿张唱片,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最伟大的文化符号”,代表着反叛、激情、解放;他入选过美国摇滚名人堂,获得过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甚至带着他的音乐体面地走入普利策奖的殿堂,推翻了这一主流奖项的保守围墙。
然而,他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依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虽然他的许多歌词足以跻身当代最优秀的诗作,他也正儿八经地写过书,但在大众眼中,他最有分量的身份,依然是歌手。
诺贝尔奖颁奖词给他的评价是:“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
这个评价,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都丝毫不为过。
当鲍勃·迪伦还只是个叫罗伯特·艾伦·齐默曼的男孩时,谁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将是什么样。
1941年,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镇上的一个小老板,家境还算富裕。但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没有办法带着儿子在大自然里快乐玩耍,比起其他的男孩子来,罗伯特的童年异常安静且沉默。
罗伯特上学后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当尖锐的空袭警报声响起时,要立刻躲到书桌底下,因为那时到处流传着苏联人会用炸弹甚至核弹攻击美国的传言。年幼的罗伯特还不太懂得什么是战争,只知道身边的人在不断地营造一种恐怖的氛围,而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这种幻想的受害者。
10岁时,罗伯特无意之中在家里翻到了父亲的一把木吉他,当他用手轻轻拨动琴弦时,吉他发出的声音让他兴奋无比。家里那台硕大的红桃木唱机,更是带给了他一个美妙绝伦的世界。他把家里所有的唱片都听了个遍,并深深爱上了这些旋律。
有一天下午,他一个人待在家中,顺手打开唱机,上面刚好放着一张乡村音乐唱片,他已经不记得那张唱片的名字,只记得那音乐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似的”。音乐的种子在他心里发芽了。
上中学后,罗伯特开始抱起吉他,玩起了摇滚乐。他精心打理自己的发型,爱穿皮夹克、牛仔裤和靴子,那是当时最时髦的穿着。在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后,罗伯特才真正开始人生的蜕变,他发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精神偶像——伍迪·格思里,传奇的“美国民谣之父”。
格思里比罗伯特大29岁,一生命途多舛,总是背着吉他四处流浪,虽穷苦困顿,却写出了上千首让人振奋的歌曲。“他是天才,他的歌曲有惊人的观点,你可以从中知道如何生活。这就是我想唱的歌,我要像他那样唱。”他不断学唱格思里的歌曲,试着推敲他的音乐中的精髓,感觉这些歌正好唱出了自己对生活、对人群的感受。
20岁那年,罗伯特把名字改为鲍勃·迪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从小生长的明尼苏达州。口袋里只有10块钱的他,搭上一趟便车,前往纽约,去拜访他心中的偶像格思里。
从此,他成了迪伦,而迪伦的家在四方,在流浪的音乐中。
纽约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迪伦在格林尼治村的咖啡馆找到了一份驻唱工作。格林尼治村是艺术家的聚集之地,他见到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也认识了不少已经成名的人物。这一切让迪伦感觉如鱼得水。
当他辗转在医院里找到格思里时,格思里已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男人了。他的肌肉已经萎缩,躺在床上,再也拿不起吉他。迪伦只能坐在偶像的对面,拿起吉他弹唱。弹着弹着,格思里的眼睛里有了光亮,他递过来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我还没有死。
格思里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会将民谣发扬光大。他的创作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把他内心感受到的一切都变成了诗歌,变成了旋律,再从嘴巴里流淌出来,震撼人心。
起初,只有少数几个人关注迪伦的才华,他努力了好久,终于吸引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知名制作人约翰·哈蒙德的注意。哈蒙德敏锐地预感到,民谣将会在未来10年大热,于是他签下了迪伦,给了他一纸唱片合约。
1962年,迪伦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鲍勃·迪伦》,专辑中他本人的创作有两首:一首讲述了他眼中的纽约,另一首是《献给伍迪的歌》。有人说它是迪伦对格思里迷恋的终结,但实际上,迪伦更像是在表述自己对于格思里的精神继承的决心,因为在这之后,迪伦也像格思里那样,旗帜鲜明地通过音乐对很多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民权运动、新青年的反传统思潮,还有当时美国人最为关注的事件——越南战争。
在迪伦发行首张专辑的前一年,美国开始介入越战,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迪伦把自己对时事的关注写进了第二张专辑。
1963年,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发行。在《答案在风中飘》一曲中,他用苍茫的嗓音反复吟唱: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作男子汉/一只白鸽要飞过多远的海面,才能在沙滩安眠/一个人需要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喊/一个人能转过头多少回,假装他什么也没看见/这答案,我的朋友啊/答案在风中飘……”这成为反战和民权运动的“圣歌”,被反复传唱。
迪伦并不是最会唱歌的人,他的成功在于他把音乐当成了武器,和这个冰冷的世界搏斗,这为他赢得了无尽的喝彩。“要定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除了我唱的民谣歌词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或者接近它一半的事物了……”多年后,迪伦曾经这样解释民谣对他的意义。
也是从迪伦开始,歌词的寓意变得与音乐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他的歌词比他的音乐更激动人心。多年来一直研究迪伦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维伦兹说:“迪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的歌既温柔又坚韧,既倔强又软弱,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他唱的是人的感受和体会。这就是他被称为‘诗人的原因。”
人们逐渐把迪伦视作偶像,甚至是“时代良心”或“道德的裁判和布道者”等。这些赞美让他有点无所适从,迪伦甚至觉得自己被“绑架”了。在一次颁奖礼上,他醉醺醺地站起来,高声呐喊:“我不分黑白,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
事实上,虽然迪伦曾与马丁·路德·金共同站在民权运动的街头,虽然他与美国文化“旗手”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凯鲁亚克一度过从甚密,但迪伦从来都与主流的社会运动若即若离,他反对外界对他的作品过度解读。曾有记者问迪伦,他那首著名的《暴雨将至》是否在影射“古巴导弹危机”,他没好气地回答:“暴雨就是很大的雨,不是原子弹。”
20世纪60年代是迪伦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对自己怀疑最多的时期,鲜花和掌声把这个敏感的男人淹没了,他第一次感到迷茫,开始“希望寻找回家的路”,找回自己。他开始渐渐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重新拾起他当年迷恋过的摇滚乐,并试图将民谣与摇滚合二为一。
1965年,迪伦发行了专辑《重返61号公路》,其中的歌曲《像一块滚石》成为他向摇滚曲风转型的代表作。在那年7月的一场民谣音乐节中,迪伦登上舞台,使用电吉他演奏这首作品。结果,很快他便被愤怒的观众赶下了台。他被指责为“民谣的叛徒”,遭众人唾骂。
也许迪伦会感激那场被他的歌迷们痛恨的车祸。1966年,他骑着摩托车被重重地摔了出去,脊椎骨断裂。很多人说这是一场阴谋,真相如何,无从得知。而迪伦从此谜一样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他逃回了一个安静的世界,他的解释是:“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随后的若干年里,迪伦一直努力寻找自己,并把注意力从音乐扩展到绘画和诗歌。他拜画家诺曼·鲁宾为师,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从绘画中找到了另外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而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歌唱,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风格。他的歌渐渐褪去了时代的符号,回归到个人的内心世界。
时间如浮光掠影般闪过,迪伦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散发出更强大的影响力,让一代代人痴迷。
从1988年起,迪伦开始了“永不落幕巡演”,平均每年100场;他的《敲击天堂之门》等歌曲被众多大师级音乐人翻唱,包括埃里克·克莱普顿、U2乐队等;关于迪伦的书籍,仅在亚马逊网站上就可以找到五六百种;好莱坞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专门为他拍摄了传记片《无处为家》;美国甚至有了“迪伦学”的专门研究——人们对他的关注可以说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在中国,迪伦的意义也超出了音乐本身。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欧美乐迷开始了解迪伦的音乐,尤其是他诗一般的歌词,使他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
而人们喜欢鲍勃·迪伦,又何止是因为音乐?
他仿佛是自由自在的灵魂,从不为他人改变方向。在人人把他树为偶像的时代,他一再宣称:“我不想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那幅集体图景中。”
当他开始搞摇滚时,原来的民谣歌迷表达了最激烈的反对:迪伦唱民歌时歌迷就欢呼,唱摇滚时就起哄、吐口水,迪伦丝毫不为所动,不惜与歌迷发生激烈冲突。
他傲慢地对待记者,感情、私生活从不向外界透露半分。人们知道的只是,迪伦有过两次婚姻。
63岁时,迪伦写完了自传,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是他对自己最直接的评价:“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现在我的名声已经在我的脸上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我不是一个表演奇迹的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