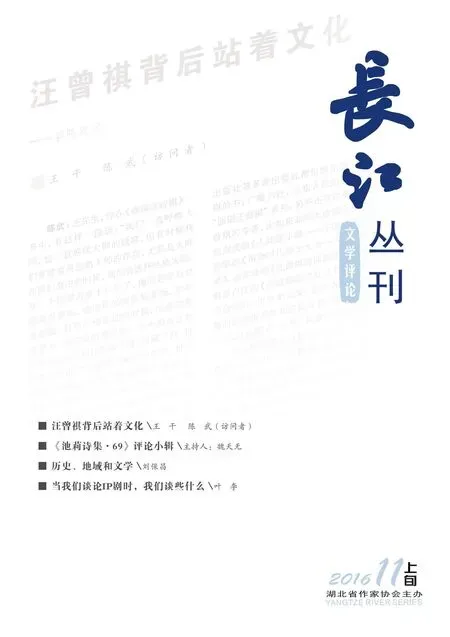IP改编:现实感的理解与诠释
■杨晓帆
IP改编:现实感的理解与诠释
■杨晓帆

杨晓帆,201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要研究方向为80年代文学史研究、当代小说批评等。
韩富虎认定了余罪就是内鬼,一面对他严刑拷打,一面得意地挥了挥手中的小说,让毒枭傅国生念出其中山岗对山峰行刑的片段。这本小说是余华的《现实一种》,这段让文学青年拍手称绝的情节,出自网剧《余罪》。从编剧增加的这一笔,很容易脑洞大开地延伸出时下“IP热”讨论的相关议题: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的二度创作问题、全媒时代纯文学的出路等。当网友以此小细节举证《余罪》颇有“文化感”时,提醒我们放下以为网剧大多情节脑残、全靠颜值和粉丝经济的偏见,去注意它同样追求深度和品位。而当《余罪》持续发酵IP潜力却遭遇一连串问题时,诸如第二季盗版流出,原班人马打造网络电影《站住!别跑!》反应平平,以及原作者常书欣本人和观众都普遍对第二季不满等,又暴露出IP剧生产中存在的命门。除了资金短缺等因素外,从改编角度看,似乎仍然要归于“如何讲好故事”、“我们需要什么故事”的老问题。就像剧中植入《现实一种》的隐喻,即使不只是为了一个噱头,也仅仅在形式模仿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对暴力美学的致敬,还不足以像余华在小说题旨中表达的那样,以有悖常理的方式去呈现令人深省的“现实感”。
有趣的是,原著小说《余罪》首发创世中文网时,类属“都市小说”中的“现实百态”一栏,改编后才被爱奇艺等视频播放平台定位为“罪案剧”和“悬疑剧”。分类标签的不同,当然受制于网络小说与影视剧在媒介属性与用户识别方面的差异,但也透露出IP剧跨媒介生产链条中理解与诠释现实感的可能和局限。
除了经典犯罪刑侦片中那些烧脑情节,《余罪》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像《无间道》那样对人性善恶、道德正义等基本命题重新洗牌,就像剧中被网友津津乐道的大毒枭傅国生的话:“死有余辜、活有余罪”。“卧底”这种独特身份的文化象征意义是在抹除了警匪之间、正邪之间的界限之后,去重新识别和恪守“我是谁”、“我为何而活”。而《余罪》更进一步的是去除了答案中那些崇高、理想的成分,由此才有了张一山饰演的卧底余罪,一个充满了反英雄品格的英雄形象,一个近乎泼皮无赖却又很有是非观的小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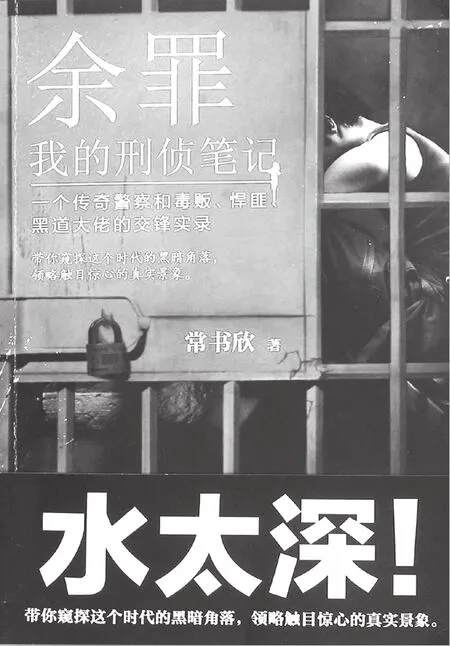
《余罪》
正是这一点契合了观众心目中对当代生活的理解。这种现实感在小说中直接由卧底行动的总指挥许平秋道出:“大部分的警察都是为一份工资和一个职位活着,现在是一个忠诚和荣誉都已经贬值的年代,它的价值远没有利益和欲望带给个人的刺激更大”,“小余,咱们其实是一类人,相同的地方在于我们都现实,不同之处在于,我呢,属于混出来的;你呢,属于才开始混的。”集中诠释这一现实感的情节,当然是余罪如何被选中并成为卧底的一段前史。而电视剧中只占第一季三分之一的这段剧集,原著小说用了第一卷整整55章来叙述。这一卷其实讲的是青年人的出路问题。余罪和狐朋狗友们最大的共性,是他们都来自边远县市、没有靠山、就业困难,上警校纯是为了生计。所以,当鼠标等人卷入余罪的卧底任务时,甚至还憧憬“走私”这么“有前途的职业”,“一点也没有成为警察的自觉”。穿上警服混吃等死,和犯罪一样,都可能被解释为生存所迫。尽管电视剧也成功塑造了一群看上去是人渣却有着极强社会生存能力的警校学生,但类似余罪和解冰之间学渣和优等生的对立,还是被三角恋的情节设计削去了更深层的社会根源。而电视剧中余罪的主角光环,更越来越削弱了他身上世俗功利且不乏凶狠恶毒的一面。如果说卑琐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撕裂,才是小说《余罪》中真正推动情节发展、并使读者对余罪们产生心心相惜之感的精神内核,那么电视剧情发展到第二季,已经完全回到警匪斗法的老套上。学渣们一个个被召唤成余罪最忠肝义胆的后援团,余罪与大胸姐之间感情升级,越来越多因身份暴露命悬一线的戏码,都在偏离小说最初缘起的现实感。
常书欣未见得有写出当代人精神图景的自觉,《余罪》也存在网络小说过分依赖情节紧张与人物个性撑起故事的弊病,但小说里一些繁冗、粗陋的叙述还是堆砌出不少照见时代的细节。比如写余罪的父亲余满堂本是在山西落户的天津知青,做了搪瓷厂工人,下岗后老婆跑了,才成了缺斤短两、偷奸耍滑的小贩;写余罪每年都假装上访坐免费的截访专车回家;写许平秋看似被重用却也要唯唯诺诺地做好一个小处长;写拐卖妇女被解救后反把警察当仇人……是这些看似社会新闻拼贴式的叙述,混杂着作者自己也曾身陷囹圄的生活实感,让《余罪》在刑侦、警匪等类型故事之外,多了一层社会问题剧的外壳。
网剧的长度和制作成本决定了它必须对原著进行大幅压缩,但改编行为本身也是一次阅读与阐释。相较于作品思维,以IP为中心打通影视、小说、游戏、漫画等的产业链模式当然更强调“用户思维”,问题是对用户需求的理解,是否仍存在着思考上的懒惰与商业利益刺激下的盲目。例如当IP剧中奇幻、玄幻、仙侠类题材盛行时,我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90后甚至95后的“网生代”观众偏好沉迷于架空世界。市场一面不断批量生产“霸道总裁”和青春怀旧题材,一面却缺少对支撑这类故事需求的现实感的细致分析,只能不断在表象真实的层面上重复某种情绪与俗套。倒是如《欢乐颂》这类作品,即便褒贬不一,也在社会阶层固化等老话题上挑战着我们的日常经验,有可能打开如何理解现实感的讨论空间。《余罪》的成功和缺憾,或许能启发我们重新审视IP改编中“故事”的意义。“有故事”不仅仅是有情节和人物,或者对成熟类型叙事的发挥。被誉为编剧教父的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说过这样一段看似老套的话,“故事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载着我们去追寻现实的载体,让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去挖掘出混乱人生的真谛。”——即使IP热的市场根基是消费、娱乐,现实感的获得与更新也仍然是故事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