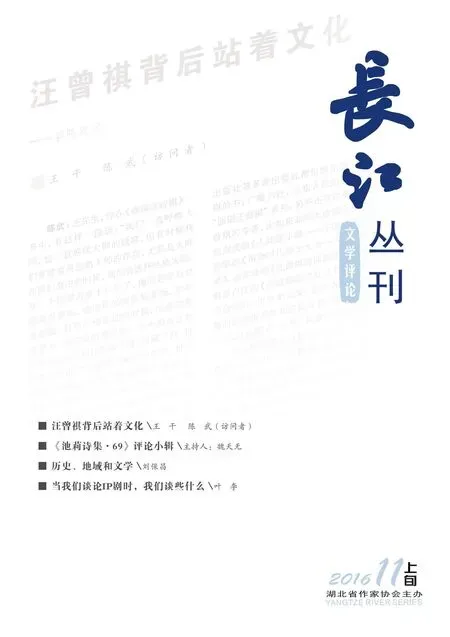《池莉诗集·69》:思考在“世俗”之外
■陈欣然
《池莉诗集·69》:思考在“世俗”之外
■陈欣然
一提起池莉,首先想到的便是她的小说,她笔下热热闹闹的武汉“民间故事”,那些生活在花街楼、吉庆街的一个个“小市民”,他们的欲念、挣扎、顽强与突破。池莉以她对世俗日常与市民生活的关注成为当代小说文坛的“新写实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虽然作品有时也因“世俗”而受到苛责,但一系列基于其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的播出,显示出池莉小说强大的生命力,更是对池莉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能力的肯定。而现在,善于写别人故事的池莉,出了一本关于自己的诗集,在这本诗集里,池莉以诗人的身份,用言语试图探讨那些她没能用故事说尽的课题。
翻开《池莉诗集》,便很自然地被诗中传递的对生活、对人生的敏感心绪吸引。诗人总是擅长将生活中那些珍贵、难以言说且转瞬即逝的情感放大,然后用凝炼的铅字印下,让白纸黑字唤起读者丰富的知觉:在池莉笔下,为第一根白发生出的怜惜如江水般又凉又滑又长;穿针引线时那种刚刚好的窃喜则化为一份宇宙中难得的宁静;亲情的牵连,爱情的热烈,都是池莉关切的对象。池莉以一位女性、一位持家者,一名母亲、一位妻子的身份,用文字捕捉生活。但当读到《欢爱正浓》这首短诗时,作者刚才的那些身份则倏地一一褪去,我仿佛看见一个气急败坏的孩子,为总是得不到老师的表扬而哭泣;又仿佛看见一个痴迷暗恋对象的青年,为自己那份无法开口的情感犹犹豫豫痛苦万分。这才清晰地感受到池莉作为一位诗人,对诗爱得如何深沉:
大约总是这样/爱只能负责“爱”这个字/不能负责爱的能力/也不能负责另外一个词:相爱//是不是所有的世界大战/最深层次的心理原因/都微小得/难以启齿/都像我一样//我与我的诗句之间/试图表达的/浓情蜜意/只能够——/让老师罚我面壁千次回家再抄写万次//爱诗一辈子,但/一辈子写出来的诗句/为数戋戋/其中还有一部分青春期烂诗/永远减不掉可怕的婴儿肥/还有一部分性情乖张/剩下的/那些/又像热恋中的公螳螂/欢爱正浓,已遭腰斩(《欢爱正浓》)

陈欣然,1994年6月生于湖北荆州。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诗的一开始便点明“爱”这个字语义管辖能力的匮乏,于是诗人对诗的爱,既不能说明爱得有质量,也不能说明诗对诗人反过来有着相同的感情。在所爱之物面前,诗人极力放低自己,甚至疑心自己的爱是否像触发战争的私欲一样不可见人。那些写下用来彰显诗而自己却无法满意的文字随之变得拙劣可笑不值一提,“罚我面壁千次回家再抄写万次”的急促节奏,更是将这种失望的情感推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热恋中的公螳螂”这一喻象巧妙得惹人拍手称快,结尾的处理也是颇具匠心,前半句“欢爱正浓”音韵绵长,后半句“已遭腰斩”则斩钉截铁,将之前的情丝切断得不留半点回味余地,只留得读者与诗人一同失声、一同束手无策。整首诗中,诗人对自己诗作的反省是颇为勇敢的,但这种批评越强烈,也就越能显示出其对诗爱得真切,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诗人对诗歌写作、对言与意表达的思考。
在《池莉诗集·69》里还有许多表达诗人对诗、对写诗、对语言态度的作品。《受恩赐者私语》便是这样一首感情酣畅淋漓跌宕起伏的长诗。诗中诗人记录了自己文思泉涌那一刻的狂喜,有如受到了恩赐,被赋予用文字表达一切的力量。于是自封为可以随便支配语言的“女暴君”,可用文字占有一切,让一切都为自己的情感服务,叫嚣着:“我把道路与河流都改变/我把铁路道岔和航线/都指向了我乐意的地方/我把第一缕星光/乃至最后一缕夕阳/都变成了我自己的心思/让海底电缆以及航母上的桅杆/都为我随心所欲的发射/人间消息/我道歉”。如果说这里与前文的道歉都像是在咄咄逼人地变相炫耀着自己的能力的话,那么从下一节单起一句的“我由衷道歉”开始,情感变得温和,语气变得真挚,没了嚣张,只有一种想与语言、想与言说和解的愿景。从《受恩赐者私语》到《欢爱正浓》,我们都能够看出语言与言说一直是池莉作为诗人关注的命题,诗人从反思自己出发,最后落脚于对诗的尊崇。
在诗中所显现出来的第二方面,如前文所提及的,是作为一位女诗人,对女性独到的理解和阐释。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诗人由反思自我延伸到对整个女性生活现状的思考。她诗中的女性是有生活维度的,谈及女性对爱人的依恋,对爱情的执着,感情或细腻羞涩,或热烈饱满;也是有文化维度的,将女性放在整个历史、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去考量:《女子之姿》用跳跃的文字,讲述女性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挣扎的痛苦。在池莉看来,女性在这样的痛苦里孤立无援,而最终“女人/不得不黑暗/顿时/抑或/永远/黑暗”。“没入黑暗”似乎是池莉对女性一种笃定的观点,在《女人自画像》的开头,她也这样写道:“没有黑夜是你可以穿透的/尽管如此明亮又皎洁/当曙色降临/你依然只能退缩/让太阳升华”。如果说前一首作品更侧重于女性内在的束缚,那么后一首则更关注在已有的文化传统中,安置给女性的外在桎梏。且诗中颇为讽刺的处理是,题目虽取名为自画像,但诗人在第四节所清晰描绘的女性形象(也是全诗中唯一细腻描绘的画像),却分明是他人给女性的画像:
你被尊重得好痛/呆在历史的画框里/交叉双手,假装端庄/脸是黄的,唇是紫的/眸子是空洞的,微笑是虚无的/心是从前的或是未来的
诗节开头就是一个被动句,显示出在“历史的画框里”,女性主动权的丧失。在这幅画像里,我们看到的女性毫无生气,是一个被禁锢了的模样。后三句诗不仅用具体的词汇讲述了女性面容的憔悴,其重复的句式也映照出了女性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也无怪乎女性无法寄心于当下,而只能怀念过去,或者悄悄对未来有一份憧憬。
诗的最后一节,诗人引入了一个“小虫子”的意象:
唯有小虫子是你永远的意义/它积极地悄悄地啮噬着/你蓬松的长长的衣裙/从此裙子最开始这样流行:/长了又短,短了又长/时尚因此旷日持久
这不是诗人第一次用“小虫子”这一意象。在《把雨织成雨衣》里,诗人这样写道:“盲目的小虫子/在参天大树弯曲的枝条上/奋力爬行/自以为在高歌猛进/万料不到时空注定弯曲/中国古代‘掩耳盗铃’的成语/我怀疑来源于我/小虫子我也怀疑/是我/曾经是或者一直是”。可见诗人对于“小虫子”这一物象的态度,并不是鄙夷排斥,而是怀有一种悲怆的同情。所以在这首诗中,是女性“永远的意义”的小虫子,似乎暗指着女性心中的被压抑住的情感与欲望,它一点点释放,与长长衣裙所代表的外在桎梏斗争,于是时尚演变为一场战争,长年累月、此消彼长。从这首诗中的“小虫子啮噬长裙”,与《欢爱正浓》中的“公螳螂遭腰斩”,我们可以看出池莉善于赋予意义以生动的形象,又如在《从前有一只姓李的黄鹤》中她将人生比为布匹,将自己比作裁缝;在《春天制造者》里用栽种蔷薇隐喻寻觅爱情。这些巧思都让人印象深刻。
而在诗人对诗、女性之对女性这两个方面的关注之外,池莉将她的反思由自我、女性最终延伸至——人。而这其中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在《成为我》中池莉对于人作为个体的重视:
多少年/多少代/古老的我/竭力摆脱睡意/只为讨回/站立的尊严//母亲/不要踢我/虚弱的腿/我一直都是/你最听话的孩子/而你/什么时候/才是我/懂事的母亲//允许我/成为舞蹈/成为羽毛/成为最简单的沙砾/成为我
整首诗语言朴实、语气诚恳,饱含着对母亲的热爱与深情,也句句透露出想要解放“真我”的渴望。诗中的“我”似乎成为了“大我”与“小我”的集合体。若单从后两节来看,诗人似乎只是将诉求由孩子指向家长:母亲养育了我,但又以养育者之姿牵扯着我。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判决》,受到父亲压制的乔治从桥上一跃而下,口中轻声呼喊:“我的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啊!”深沉的爱与深沉的痛就如此在内心相互纠结撕扯。但加上第一节,整首诗便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世世代代的“小我”化成一个“大我”,向几千年来重集体轻个性的文化发声。
当然,池莉的诗作也不尽是这三类,有的表达一种人生态度,如《不朽如白骨》;有的似乎是记录某一刻的哲思,如《看一切都美的眼睛永远是醉眼》;有的则是单纯的咏物,如《颂雪花飘临那一刻》。诗作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一定的》幽默可爱,《我信仰错误》则深刻尖锐,《清晨远道而来》则营造出一种温暖静谧的氛围。与池莉的小说不同,池莉的诗不再有明显的地方性特色的符号,也很少寻见她小说中琐碎世俗生活的影子,我想这是诗与小说的不同,也是池莉作为一位更加成熟的写作者,在想要表达人类更为普遍的情感时,选择的对于文学传统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同时更是对池莉在小说方面已有的写作形象的突破,让读者看到了在“世俗”之外,池莉的思考。
诗集的后记里,池莉这样写到自己关于诗集出版的期待:“诗集一旦出版,恐惧不治而愈。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过度害怕他人,不再总是更多地感知生存的可憎。”而凡是有着同样期待的人,也许都可以试着读一读这本诗集,在池莉细腻的诗句中,找到自己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