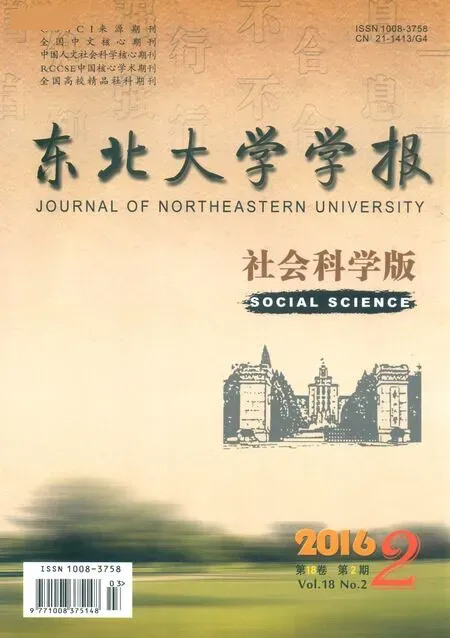从“传统福利”到“积极福利”:我国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体系构建研究
满小欧, 王作宝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从“传统福利”到“积极福利”:我国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体系构建研究
满小欧, 王作宝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社会转型与变迁使传统补缺型儿童救助政策已无法承载当前的困境儿童问题。与传统儿童福利制度相比,家庭支持福利制度既包括来自政府及福利机构提供的福利津贴也包括一系列支持性服务项目,体现了理念上的革新,注重以预防策略为主的积极性政策及专业社工服务的提供。构建我国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即是在肯定“家庭”作为儿童福利制度设计核心要素的同时,从社会投资与能力建设视角出发,为家庭提供包括多层次津贴、专业社工服务及以社区为依托的支持性服务在内的综合福利体系。
困境儿童; 家庭支持; 儿童福利; 积极福利
近年来,“困境儿童”这一包含了更广泛弱势儿童群体的代名词,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迅速夺取了社会的视线,成为备受政府与民众关注的焦点。2012年贵州毕节5名流浪儿童因垃圾箱取暖中毒死亡,2013年南京两名幼儿饿死家中,2015年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每一桩事件的发生都映射了我国儿童保护与救助制度的缺失与盲区的存在。
作为积极回应,民政部已于2013年正式启动了“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探索通过建立津贴制度重点保障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将儿童福利的服务范围由传统的孤残儿童扩展到更广泛的弱势儿童群体。然而,单纯依靠津贴或补贴的制度模式仍有其局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与回应不同困境儿童的需求。因而,笔者从“家庭支持福利”视角对困境儿童救助议题进行探讨,主要鉴于以下原因:第一,社会转型与变迁使困境儿童群体不断涌现,传统补缺型救助政策已无法承载当前的社会问题,儿童福利应逐步转向预防式积极福利;第二,从国际社会来看,家庭政策已成为许多国家高度重视的公共政策议题,家庭支持福利成为保护处境不利儿童的重要制度设计;第三,从我国儿童与家庭事务转折性变化来看,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放开,家庭必将面临新增儿童照料成本、工作与儿童照料平衡、外部经济压力等诸多挑战,亟需家庭福利政策的调整与支持。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家庭本位的儿童福利政策与制度安排,学界也少有从儿童家庭支持福利视角的专门论述,儿童家庭支持福利领域的实践与研究均待进一步拓展。
一、 困境儿童:一个有待澄清的群体
“困境儿童”一词是源自国外的概念。在国外,困境儿童有多种称谓,如:vulnerable children、children in need或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等,是个广义概念,其内涵是指一切因贫困、疾病、意外事件或遭受家庭虐待与忽视而失去家庭依靠,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的儿童[1]。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困境儿童的概念更多是基于理论的一般性阐述,在实践层面往往需要更多的具体界定与区分。
尽管无人否认孤儿应属于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的儿童群体,但从国外儿童福利研究的相关文献表述来看,孤儿(orphan)与困境儿童(vulnerable children)是被明确区分使用的两个概念,同时出现并使用时被称为orphaned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简称OVC。一般意义上,孤儿是指遭受父母双方死亡、失踪或被抛弃的儿童,但也有其他的定义,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将失去父母之一的儿童即界定为孤儿,在此基础上又划分为丧父孤儿、丧母孤儿与双孤孤儿。
相对于孤儿,困境儿童无疑是更加难以界定的概念,因为“困境”一词本身就包含了环境与情况的复杂性。困境儿童的典型特征是尽管他们可能父母双全,但基本的需求与权利却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这些权利与需要包括:安全的环境、父母的照料、充足的食物与营养、免于虐待与忽视等等。由于儿童的非完全行为能力,他们的成长与所在家庭及社区环境密切相关。因而,国外对困境儿童的外延界定通常分为个体、家庭与社区三个层次[2],如表1所示。

表1 国外困境儿童概念体系
在我国,困境儿童的概念呈现了政策操作定义不断完善但学术支持相对滞后的发展状态。尽管困境儿童在2002年开始进入政策研究者们的视野并使用,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角度梳理困境儿童的内涵和外延,但并未达成学术共识,且与国外明显不同的是,国内学者普遍将“孤儿”纳入到了困境儿童的范围。如刘继同认为,中国社会传统存在和政府普遍认可的困境儿童包括孤儿、残疾儿童、弃婴、流浪儿童、贫困儿童、艾滋病孤儿及服刑人员子女[3]。尚晓援则提出了“弱势儿童”这一相近概念,包括“孤儿、残疾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受暴力侵害和虐待儿童及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在此基础上,尚晓媛又从学术层面出发,构建了困境儿童的三级概念体系[4],如表2所示。相比之下,在政策操作层面,困境儿童的外延界定较为明晰具体。2013年,民政部首次提出区别于孤儿与普通儿童,将困境儿童分为自身困境和家庭困境两类,包括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儿童、长期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残疾儿童、贫困家庭患重病和罕见病儿童等。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将孤儿与困境儿童予以区分是出于政府救助传统的考量,并非是类型上的区分,但这一界定无疑与国际惯例更为接近。2014年,民政部在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五类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遭受家庭暴力侵害与遗弃的儿童、缺乏关爱的留守与流动儿童、家庭贫困儿童,以及自身重病重残等特殊困境儿童。

表2 国内困境儿童概念体系
因而,从上述对国内外困境儿童概念界定的梳理情况来看,由于“困境”一词内在含义的复杂性及社会不断变迁赋予的新内涵, 困境儿童并非是明确界定的概念,不同视角下仍存在分歧,而且采用列举的描述方式也必然无法穷尽困境儿童的所有类别。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体系,我们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阐释:第一,父母是否双全不构成判断困境儿童的标准,困境儿童或许父母俱在,但却由于没有能力、主观疏忽或故意等原因无法履行照料与保护儿童的职责;第二,困境儿童的基本需求与权利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这些需求包括家庭关爱、安全、健康、教育、医疗等,资源的缺乏也通常是多重性的;第三,除了个体与家庭因素,社会结构性变迁、社会环境及相关支持性政策的缺位也是导致困境儿童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 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内涵与发展
尽管造成困境儿童的原因复杂多样,但从传统福利模式来看,我们更倾向于以津贴的方式对已经遭受困境的儿童进行“残补式”救助。这一方式在积极改善困境儿童生活境遇的同时,却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家庭对儿童的影响、儿童的心理支持与相关服务,甚至是否可以从源头预防困境儿童产生的策略等等。家庭支持福利(family support welfare)则从某种意义上考虑并弥补了这些不足。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家庭支持福利”这一概念的内涵及范围界定存在差异,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家庭支持福利是以家庭为制度设计核心要素的积极福利策略,强调在维持家庭功能、提升能力建设基础上,充分吸收家庭成员参与并提供相应服务,最终提高家庭对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广义上,它包含了满足家庭成员生存与发展所需的一切相关福利制度与服务安排,但在实践中,家庭支持福利往往是“狭义”的,多针对因拥有残疾家庭成员、未成年子女或就业中断等原因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与传统福利策略相比,家庭支持福利从事后补救的“消极政策”转向预防导向的“积极政策”;福利供给方面,在实施津贴、税收减免等现金救助的基础上,更注重支持性服务等多元福利的提供。
一直以来,即使在西方国家,儿童问题也是以家庭为主的私领域议题,政府在介入家庭内部时十分谨慎;另一方面,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支持福利在发展之初就遭遇了与传统儿童福利拥护者的交锋,“支持家庭的合理性”成为儿童福利提供争论的焦点问题。反对者认为,对于没有能力或无法胜任照料儿童职责的家庭,应该将儿童转移到专门机构或进行替代性家庭照顾,而不是继续对这样的家庭予以支持[5]。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对家庭在保护及促进儿童发展方面不可替代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尤其是80年代以来,受到埃斯平·安德森“社会投资”理论的影响,提高对家庭照顾儿童能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困境家庭儿童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标。其原因在于,从社会投资的视角,对家庭中儿童照顾与教育等系列需求的回应与支持,具有多重正外部性,包括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为社会发展储备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本竞争力,从源头介入提高国家公共资金的利用回报率等[6],这些“效益”都远大于以事后补救为主的传统福利策略。
因而,在新的“投资战略”下,针对困境儿童的家庭支持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受到了政府的充分重视与支持。尽管不同国家由于在福利文化、政府与家庭责任划分及对家庭干预程度上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但从干预手段上看,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政策工具,并采用了普惠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福利策略。
第一,时间政策。以产假、父母假、照护假及弹性工作时间为主要形式,保证儿童在家庭内部获得充足的照顾时间,从而降低儿童处于风险或危险的机会。从20世纪70年代起,除了产假外,欧洲国家开始发展面向父母双亲的亲职假制度,不分性别,都有权利获得额外的假期来照顾孩子,只是不同国家在假期时间及是否带薪方面有所差异。对于有残疾儿童或患病儿童的家庭,还可以享受额外的照护假。
第二,经济支持政策。随着儿童照顾由家庭责任逐渐转变为政府的公共责任,西方国家除了通过直接给付家庭津贴或税收减免的方式为困境儿童家庭提供传统经济支持外,还发展出一种新的、因父母提供幼儿照顾而获得的照顾津贴,尽管这种津贴的给付水平有限,甚至一些国家还需要经过家庭调查,但它的积极作用在于肯定父母照顾价值的同时,为父母在亲职假结束后如何安排幼儿照顾(领取津贴亲自照顾还是使用日托服务)提供了更多的选择[7]。
第三,服务政策。总的来说,西方国家针对困境儿童家庭的服务政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提供儿童公共托育服务尤其是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早期发展计划,将父母尤其是女性照顾者从照料儿童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回归劳动力市场,使家庭获得更好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儿童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如由国家补贴的专业儿童看护服务,支持困难家庭儿童早期教育的托育服务,面向不同家庭、不同年龄段儿童需求的托儿所等。第二类是以社区为依托的家庭干预服务,主要目标是通过向父母传授科学的育儿理念与技巧,以及帮助问题家庭恢复正常儿童抚育功能并获得资源,从源头避免弱势儿童的产生。美国早在1980年颁布的《收养救助与儿童福利法案》中就明确将资金转向了预防性服务与维持家庭的完整,开始实施以社区为依托的“家庭强化计划”等一系列家庭保护与支持服务项目,通过家庭支持干预困境儿童的产生[8]。
三、 积极福利的路径选择:构建我国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体系
1. 我国困境儿童救助:实践与局限
从开启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建设至今,我国已经建立了孤儿生活津贴制度并逐步向其他困境儿童群体扩展,儿童保护工作也从倡议走向实际行动。在对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原则的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将60多万事实无人抚养的“亚孤儿”及其他更广泛的困境儿童群体纳入政府保护网,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面向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保障制度、医疗健康救助制度及保护安置制度。基本生活保障方面,2010年起我国已按照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则,全面建立了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全面覆盖了机构养育及社会散居孤儿,而实践层面上,许多地区更是将事实孤儿、贫困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等纳入基本津贴的保障范围。医疗健康救助方面,在将儿童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体系的基础上,我国于2010年开始探索建立面向困境儿童的医疗救助制度,开展了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儿童社会保护方面,我国逐步加强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未成年人保护试点工作,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联动反应机制,形成“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等。然而,我国儿童福利事业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儿童福利制度设计仍采取“问题取向”的传统福利策略,即注重儿童成为困境儿童后的救助策略(提供生活津贴、教育资助、医疗救助等等),尚未将“积极福利”策略考量在内。而从救助策略向预防策略的重心转移,通过对儿童生存与发展的各个领域(家庭、社区、早期教育、营养健康等)的支持,最大限度预防困境儿童的产生,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积极实践的福利理念。正如肯·布莱克默在论述社会政策(医疗健康方面)效率时提到的问题一样,比思考“治疗是否有效”更有价值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我会去医院”及“预防性服务为什么没有对我起作用”[9]。因而,对于儿童福利制度,我们同样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能够将监测和预防困境儿童的产生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环节,而并不仅仅停留在如何补救。
第二,儿童福利制度设计“重儿童、轻家庭”。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儿童福利对象仅针对困境儿童群体自身,尚未建立家庭本位的儿童福利政策与制度安排,对儿童成长环境影响重大的社区支持也未涉及,这种割裂的福利制度设计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从儿童成长的客观现实来看,任何一个环节的制度缺失都可能不利于儿童摆脱困境和获得健康的成长与发展。相比之下,西方很早便开始关注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设计。美国早在1972年就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家庭支持项目,鼓励残疾儿童与家庭共同生活并从社区获得必要服务,形成了 “州政府出钱,社区提供服务”的制度模式;英国也于1989年正式明确了家庭支持福利的原则,强调父母与儿童权利的平衡、支持父母履行职责、……与家庭成员成为合作伙伴等重要价值观[10],这也是我们需要吸收借鉴的。
第三,儿童福利主体有限,福利供给方式单一。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家庭成为提供儿童福利的重要甚至唯一主体,政府的介入十分有限,社会组织、社区等参与更显不足,儿童社会保护与支持体系也正在探索构建中。此外,从福利给付方式来看,我国目前主要通过补贴或津贴的形式为困境儿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诸如服务等其他福利形式缺乏,无法满足困境儿童的多重需求。
2. 我国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体系构建
从社会福利水平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只是我们迈向更加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的第一步,完成由传统福利向积极福利的转型才是顺应当下全球社会福利变革潮流的积极选择。我们在关注传统的风险事后弥补与再分配的儿童福利机制的同时,更应关注问题儿童的预防及上游干预福利策略,从社会风险防范的视角提供福利与服务。而这一转变,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在福利体系框架设计、政策导向、资金保证的基础上,带动社会组织与专业社工服务的发展,共同构建积极的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因而,作为积极福利制度的模式之一,构建我国的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即是在肯定“家庭”对于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关键作用的同时,从社会投资与能力建设的视角出发,为家庭提供包括津贴、服务及其他支持性福利等多层次服务,恢复与改善家庭功能,以此为困境儿童提供保护与福利,最终从源头预防困境儿童的产生(如图1所示)。

图1 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体系
第一,以“家庭本位”为制度设计核心。家庭是有利于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也是儿童应对社会风险的核心场所。从积极福利的视角来看,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制度设计不仅旨在修补缺陷与事后救助,更重要的是以支持和满足儿童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将家庭作为保护儿童的重要场所进行投资与完善。借鉴西方国家的家庭支持福利政策及考虑与我国当前政策的衔接,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与调整:一方面,逐步建立面向儿童家庭的支持性福利政策,实施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福利策略。如设立普惠式的儿童家庭津贴,政府以专项资金的方式对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予以一定的补贴,注重以预防为主的家庭经济支持,提高家庭满足儿童需要的能力;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亲职福利政策,尤其是育婴假期制度,提高原生家庭对婴儿的照顾能力,以及工作与家庭平衡能力。另一方面,在维护与支持家庭功能前提下,适当加强政府对家庭的介入,必要时剥夺父母的监护权,预防家庭内部伤害儿童事件的发生,同时做好监护权转移变更后的接续工作,如儿童是与原生家庭的融合、短期家庭寄养,还是最终由其他家庭收养等。
第二,以“多层次家庭津贴”为制度基础。我国当前探索建立面向困境儿童的津贴制度与笔者所倡导建立的家庭津贴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理念上,前者是针对困境儿童(重点保障重病、重残及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救助的残补性福利策略,而后者体现的是面向全体儿童群体、以预防性经济支持为主的普惠性福利策略;功能上,前者的给付标准参照孤儿津贴发放,仅满足儿童的最低层次需求,后者则强调通过满足儿童家庭的不同层次需求,达到满足儿童需求的最终目标。因而,从国外儿童家庭支持福利津贴制度经验来看,我国家庭津贴制度的建立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立足于当前困境儿童生活津贴的制度基础,以“分类保障”为原则建立家庭津贴,从“一刀切”逐步过渡到保障不同类型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尤其要加大对特殊困境家庭儿童(父母重病重残、吸毒服刑等)的补助力度;第二步是提高家庭津贴的给付标准与保障范围,从保障基本生活逐步扩展到保障困境儿童获得足够的照料、教育、健康、住房及促进就业等多方面需求;第三步是建立面向所有儿童家庭的普惠式津贴制度,包括税收减免、现金补贴等多种方式,涵盖儿童所需的各个方面,积极保障儿童的健康成长权利。
第三,以“专业社工服务”为制度支撑。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与传统儿童福利模式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注重通过专业社工服务满足家庭除经济外的个别化需求,并协助获取相关社会资源。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向儿童提供专业服务的经济基础及人力资源。民政部也于2014年发布了《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详细规定了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原则、范围和类别、服务流程技巧、督导、服务管理和人员要求等。因而,在未来制度实践中,我们应该注重依托专业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社工服务向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延伸,例如,通过父母亲子技能培训、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指导、心理咨询、就业指导服务等,增强困境儿童家庭的功能。除上述体现治疗功能的社工服务外,还应注重发挥专业社工服务的预防功能,如通过对困境儿童家庭的定期走访、建立档案、风险预估等方式,在困境儿童的识别、危险要素的预防方面发挥作用。
第四,以“社区支持”为制度依托。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及影响家庭环境的要素之一,社区建设也是家庭支持福利体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环节。一方面,注重社区的资源建设,尤其是有利于儿童及其家庭成长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努力构建“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型社区。另一方面,作为福利提供的“最后一公里”,可注重发挥社区的支持性服务功能,如依托社区建立专门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站,在承担汇总儿童福利基本信息、受理儿童津贴申请、定期培训儿童福利督导员等基本职能基础上,为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相应服务。此外,社区还可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社区动员、社区照顾、社区救助等)协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获得其他的社会资源,发挥不同制度的协同作用,丰富困境儿童家庭的社会支持服务体系。
因而,建立家庭本位的困境儿童保护政策与制度安排,意味着摆脱传统含蓄和补缺模式福利的局限,重新认定家庭的价值与政府的权责划分,维护或改善家庭功能,通过为儿童创造良好的家庭、社区环境来保护困境儿童,并从源头预防困境儿童的产生。
[1] Pecora P J. The Child Welfare Challenge: Policy, Practice, and Research[M]. Livingston: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0:234-235.
[2] Skinner D.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Orphaned and Vulnerable Children[J]. AIDS and Behavior, 2006(6):619-626.
[3] 刘继同.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功能变迁与儿童福利政策议题[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7(6):9-13.
[4] 尚晓援,虞婕. 建构“困境儿童”的概念体系[J].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14(6):5-8.
[5] Dagenais C. Impact of Intensive Family Support Programs: A Synthesis of Evaluation Studies[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04,26:249-263.
[6] Hubenthal M, Ifland A M. Risks for Childre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arly Childcare Policy in Germany[J]. Childhood: A Global Journal of Child Research, 2011(1):114-127.
[7] 张亮. 欧美儿童照顾社会政策的发展及借鉴[J]. 当代青年研究, 2014(5):85-92.
[8] 满小欧,李月娥. 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与儿童保护制度——从“自由放任”到“回归家庭”[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2):94-98.
[9] Blackmore K. 社会政策导论[M]. 王宏亮,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23.
[10] 满小欧,李月娥. 西方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模式探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11):117-122.
(责任编辑: 付示威)
From“Traditional Welfare” to “Positive Welfare”: Constructing the Vulnerable Children Family Support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MANXiao-ou,WANGZuo-bao
(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The traditional residual child welfare has failed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 of vulnerable children due to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ison, the family support welfare system includes not only the welfare benefits and support services from government programs and welfare agencies, but also the informal support from communities, families and friends. It reflects the innovative concept, focusing on the positive intervention policies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services. Constructing the vulnerable children family support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means affirming “family” as the core element of system design, while providing the families with multi-level allowanc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community-based supportive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vestment and capability building.
vulnerable child; family support; child welfare; positive welfare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2.010
2015-09-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4YJC84002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130314001)。
满小欧(1983- ),女(满族),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儿童福利、社会救助研究; 王作宝(1985- ),男,山东单县人,东北大学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
C 913.7
A
1008-3758(2016)02-017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