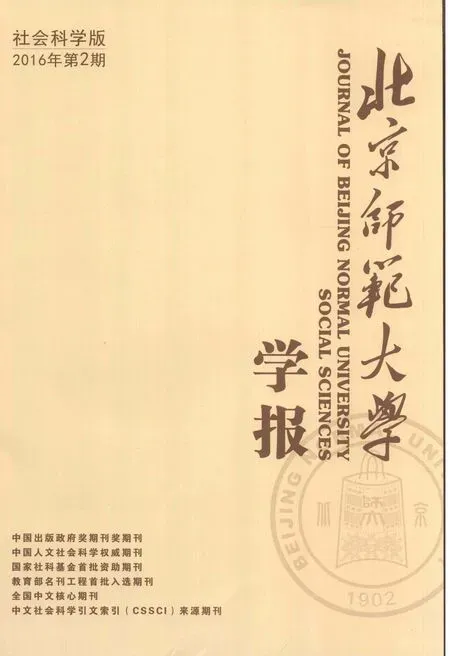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初论
湛中乐,苏 宇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初论
湛中乐,苏宇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教育法学的系统研究兴起,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国内学界对此多有探索,但莫衷一是,相关法理基础研究还不够深入。教育法学的理论研究,应根据教育领域中基本权利义务关系的类型特殊性,以受教育权与国家义务、学术自由与办学自主、人本目标与思想尊严、契约属性与双重义务为理论基础,以教育法律关系与教育行为为理论框架,以特殊优位关系、学校治理行为及专业评价行为为特色,形成相对独立的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教育法学应当成为相对独立的二级法学学科,有自成系统的内容设置,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法学的学科发展和教育法治化事业。
[关键词]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学科建设
近年来,教育法学方面的研究在中国渐成热潮,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吸引了法学界和教育学界的关注。在学术研究渐趋繁荣的背后,是一系列引人深思的根本问题:教育法学能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否存在自身的理论体系?或者仅仅是由其他部门法学的理论“拼装”而成因而不需要自身的一套法理基础和教义学体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法学研究的走向和学科的建设方向,这是每一位教育法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一、教育法学学科基础研究概述
学界对教育法学的密切关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如果自德国学者黑克尔(Hans Heckel)的《学校法学》算起,教育法学的系统研究在国外已经进行了60年左右,涌现出阿维纳里乌斯(Hermann Avenarius)、瓦伦特(William Valente)、布特勒(Des Butler)、麦卡锡(Martha McCarthy)、兼子仁等一系列学者。迄今为止,教育法学还缺乏像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那样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其研究或者处于问题拼接状态,或者借用其他学科的体系(如德国及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法学的研究常借用行政法学的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倒不乏有关建设教育法学学科知识体系的主张。教育法学之系统研究及对学科基础之反思,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30年来,劳凯声、孙霄兵、张维平、谭晓玉、秦惠民、程雁雷、余雅风、周光礼等众多学者对教育法学的立身之本进行了众彩纷呈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也不乏建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的尝试。国内对教育法学学科基础的探讨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①也有学者将中国的教育法学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但更多地是从组织机构及制度动态方面进行划分,本文侧重对学科基础问题的探讨与反思作划分。参见余雅风、劳凯声:《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育研究》,2009年第2期。。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4年前后;第二阶段从1994年首次教育法学术会议到2004年左右;第三阶段从2004年大学章程制定与研究热潮兴起至今。在第一个阶段,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建设热潮,一些学者提出了朴素的学科构建设想。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的研究现状概括为“四多四少”,认为此阶段的研究是“文本中的教育法”②谭晓玉:《教育法学的何谓与何为》,《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6辑(2009)。。此阶段的教育法学研究,尚未深入教育法律关系,缺乏相应的实践素材可供仔细探讨。在第二个阶段,自1994年首次教育法学术研讨会起,学界结合教育法领域的法律实践(尤其是教育行政诉讼实践),开始更为严肃地探讨教育法学自身的学科基础,并且对教育法学有了一些勇气可嘉的反思和主张独立的设想。例如有学者在反思前一阶段研究时提出,教育法学不能是教育法规注释,不应属于行政法的一部分,而应当成为与行政法并列的二级学科,而且“研究对象、任务、体系和基本内容与行政法学的完全不同。”*蒋超:《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研究》,《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秦惠民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宣称“教育法学应有属于自己学科的基本问题”,“如果只是使用行政法学的概念来研究教育法的问题,那是行政法学而不是教育法学”*秦惠民:《中国教育法学的产生发展背景与研究状态》,《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6辑(2009)。。在第三阶段,近几年来,大学章程的制定及大学治理法治化的探讨在国内渐成热潮,学界开始真正深入思考教育法学的逻辑起点及教育法规范体系的特殊性,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开启了“学科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龙洋、孙霄兵:《对我国教育法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思考》,《教育学报》,2011年第6期。。其中,一些著作已经开始尝试构建教育法学自身的学科知识架构,例如张维平、石连海、黄巍、申素平、黄欣、李晓燕、杨颖秀、杨挺、高君智等学者都在这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探索步伐。
尽管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谓精彩纷呈,但却存在两个根本的问题。首先,对于教育法学基础理论及学科知识体系的探索各言其是,较少相互参考,设想大相径庭,缺乏清晰的主线;其次,与前一个相伴随的是,在种种关于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主张中,实际上欠缺深层的法理思考,难以找到一套能够比肩民法上的法律行为(目的意思、效果意思、表示行为、要约、承诺等)、刑法上的犯罪构成(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责任等)、警察法上的危险预防(Gefahrabwehr,引出警察任务、警察作用、警察措施等)之类相对独立的概念基点设想。循此,我们发现存在一个未被追问的根本问题:教育法学在法理上的特殊性是什么?此种特殊性是否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初步展开形态如何?这是我们在探索教育法学学科建设时需要认真考虑的基础问题。
二、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
教育法学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学科?这一问题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如果教育法学只能依靠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德国的教育法学是被作为特别行政法(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加以研究的,从理论体系到学科定位,它都缺乏独立性。教育法学是否存在自身的理论体系,关系到教育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教育法治化建设的蓝图和具体构思。教育法学是法学的一部分,因此,它是否存在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就要判断它在法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框架之下,是否存在自身相对独立的理论基础及法理框架。
(一)教育法学的理论基础
法学是有关公平正义的学问*此说由来已久,影响广泛,其源头已不可考。较著名的经典出处可参见《学说汇纂》:“法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学说汇纂》,第1卷,罗智敏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另见《法学阶梯》:“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法学总论 ——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各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在于根据这些领域的特点,公平正义在此是否呈现出某些特别的、系统的规定性,或公平正义的实现须经由特定的方式进行。当代法学对公平正义的诠释,是通过对权利义务体系进行表述而实现的;因此,一个具体的法学部门如要具备理论体系上相对的独立性,乃至自成一体,在权利义务关系方面就需要有独特的基点和展开方式。教育法学所面对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在基本权利义务关系上具备类型的特殊性,就能够为教育法学的理论基础提供潜在的坚实支撑。
教育法学面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复杂的。教育是国家、学校、教师、学生、家庭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完成的事业,教育的基本法律关系至少需要处理国家、学校、教师(教育者)与学生(受教育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教育法面对的法律关系主体而言,首先是国家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其规范基点建立在受教育权与国家义务之上;其次是国家与具体负责教育事务的学校之间的关系,其规范内涵包括办学自主权问题;复次是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既涉及办学自主权乃至学校的自治与治理问题,也涉及学术自由,涉及师生的正当权益保障问题;再者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涉及学校治理问题,也涉及知识和思想的优越地位问题。这些问题之中隐藏着教育法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而大部分的基础理论问题都显示出它们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突出需求。
1.受教育权与国家义务
教育法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首要基点,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据宪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有推广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般义务。这是教育法学的体系得以展开、教育行政诉讼得以进行的首要基础,也是国家依法治教、对教育事业进行管理的根本依据,更是整个教育法学的逻辑起点*参见龙洋、孙霄兵:《对我国教育法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思考》,《教育学报》,2011年第6期。。这一基点在法理上拥有鲜明的独特性,纵观我国诸多基本权利义务及法律权利义务,并无与受教育的法律地位相当者。宪法明确规定同时作为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惟有受教育与劳动;但在具体法律当中,劳动的义务没有实质性的体现,仍然是宪法上的“光荣职责”;而受教育的义务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下称《教育法》)中得到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下称《义务教育法》)中还得到了具体的规定,是一种有实质内容的基本义务。不仅如此,受教育权还是我国宪法中惟一曾经发挥直接效力的基本权利*2001年的齐玉苓案被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1990年,陈晓琪及其父盗用齐玉苓的姓名获得了济宁商校的录取资格,十年后被齐玉苓发现,齐玉苓到法院起诉陈晓琪等侵犯了她的姓名权和受教育权。最高法院批复:“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山东省高院据此判决齐玉苓胜诉。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这一批复于数年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但判决依旧有效。,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可见,只有受教育权兼有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法理属性;根据耶利内克的主观公法权体系,公民在诸多具体的身份中,惟有受教育者的身份能兼具个人相对于国家除主动地位以外的其余三种地位*德国公法学巨擘耶利内克认为,个人基于国家成员资格被置于为数众多的地位关系之中:个人对国家的服从状态使个人处于义务领域中,此时个人处于被动地位;个人有排除国家、否定统治的领域,是个人的自由领域,在这种领域个人处于消极地位;国家赋予个人利用国家权力和国家制度的法律上之能力,此处个人处于积极地位;个人被赋予为国家而行动的能力时,则处于主动地位。参见〔德〕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9页:当受教育者履行受教育义务时,处于被动地位(passiver Status);当受教育者主张排除行政权力对于行使受教育权的妨碍时,处于消极地位(negativer Status);当受教育者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作为义务、保障其受教育权的实现时,处于积极地位(positiver Status)。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的宪法、法律为教育事业设置了诸多的国家义务和方针条款(Programsatz)*参见陈新民:《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方针条款虽然在德国宪法学中已经式微,它依然存在于许多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受教育者在公法上的地位和权利体系实际上相当丰富,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更遑论建立一整套与“教育——受教育”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法教义学体系。
不仅如此,这一理论基点还隐含着另外一个重要前提:国家义务的履行包含着某种宪法委托*关于宪法委托,国内学界通常受依普生等德国学者影响,认为宪法委托即立法委托,仅限于拘束立法者且明示了立法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宪法委托理论亦有突破性进展,如U.Kuhlmann批判依普生的理论过于斤斤计较条文,未能重视委托的一体性;Wienholtz在宪法委托强度和拘束对象上的扩展;K.Stern的宪法训令也突破了委托的形式准则。这使得宪法委托的解释范围大为扩张。参见上注陈新民书,第11-16页。,其结果就是国家权力的介入。国家依据宪法的要求,制定各种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以教育行政管理权力,也授予公立大学以一定的职权(如学生惩戒权、校园管理权等)。这就使得教育法学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借助公法学的理论,但又不能完全囿于既有的公法学理论体系。在学生与学校关系方面,由于受教育权的特殊性,它在规范上的请求权体系与其他的基本权有别,与公权力之间产生的法律矛盾在内容上也呈现出特殊性(学生可以同时行使积极性和消极性的请求权),但此种特殊性仍然可以为当前的公法理论架构所消化。但就学校与政府和学生的关系而言,受教育权、受教育义务与国家的教育行政管理权力引发了不同的关系,引出了既是权利、又是权力的法律关系内容(典型的如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及下属的各项具体权利),它在教育法中处于相当重要的枢纽位置,但很难为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所消化。这就更需要教育法学打破传统学科门类框架与部门法学方法的限制,以公民受教育权与国家义务为出发点,构筑教育法学自身的理论基础。
2.学术自由与办学自主
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承担的事业不仅仅是教育,还包括科学研究。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宪法的这一条款规定了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自由,学术自由亦为其所涵盖,它是教育法学的又一重要规范基点。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宪法规定的这一基本自由的主体是作为普通公民的个体;在相应的国家方针条款方面,受帮助的对象也只包括从事教育、科技等事业的公民个体;但从另一方面看,宪法并未限定公民必须以个体的方式或集体的方式行使此权利,这就为权利主体的扩展留下了空间。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下称《高等教育法》)进一步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此规定并没有对学术自由的主体作出限制,从字面上看,只要相关活动属于科研、文艺创作或其他文化活动,就应当处于国家依法保障的自由领域内。这就使得大学的整体及其中的机构可以作为学术自由的主体,为这一基本自由与《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办学自主权乃至更进一步的大学自治的联结奠定规范上的基础。
但是,除宪法学在方法论和基础知识上的有限支持(例如“制度性保障”等域外理论*“制度性保障”学说由魏玛时期的学者托马提出,著名宪法学者施米特加以发扬,广泛见诸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法学著作,其主要思想是将某些宪法权利或自由看作一种国家有义务加以保障实现的制度。参见〔德〕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90页。)外,所有其他部门法学提供的法教义学框架,都无法提供这种联结所需要的法教义学结构,也不能梳理大学自治乃至其他类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所面对的规范约束体系。对于包括各种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的教育机构而言,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均难以将建立于基本自由之上的办学自主权乃至大学自治展开为一个规范内涵丰富的法理体系。惟有发展一个自成一体的法教义学体系,才有可能超出于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等既有的概念群而完成这种建构;这套体系应当是为多元的、自治与治理相结合的法律过程准备的,并不在传统部门法学的方法论视野之内,而需要吸收当代关于治理、善治和多元民主过程的有关理论,以完善其内部结构。
3.人本目标与思想尊严
在以上两种基本自由及相应的国家义务以外,教育还有着与一般的民事或行政活动截然不同的属性。一方面,如果将教育单纯看作一种基于合同的服务,即如教育培训机构开展的收费培训服务一样,教育法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用民法学的框架进行处理。但至少在我国,肩负着国家战略、国家义务、行政计划和文化理想的教育活动,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合同法律制度所能处理的范畴,大部分学校教育活动引致的法律纠纷并不是经由合同法途径解决的,甚至大部分学生在学习生涯之中,自公立小学开始至公立大学毕业,都未必接触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的教育服务合同。另一方面,如果将教育看作一种行政行为,教育法的问题即可纯以行政法的框架处理。但是,教育过程中尽管包含部分行政行为,教育本身却决不是任何形式的行政行为,科研就更不能归诸行政行为了。教育和科研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法律问题,固然需要借助部分民法和行政法的理论与制度,但归根到底仍然需要一套相应于它们自身的法理框架和法律制度去解决。
教育的很多法律问题之所以无法用民事、尤其是用合同的方式加以解决,其根本在于教育传授的不仅仅是信息和技能。如果教育仅仅是对特定信息和技能的传授,无论是批量销售还是“度身定做”都不影响它被商品化的潜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不仅传递信息、传授技能,还陶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养育人的灵魂;教育的这些内容是无法被商品化的,甚至很少建立在具体的合意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违约责任等合同法的核心机制几乎完全不适用于教育:品格和灵魂无法复原,也不能估值。同样地,这种教育活动也不应当是行政活动。教育组织与管理可能包含行政行为,但教学与科研本身,归根到底是基于个体知识、能力与思想的事业,尽管存在各种教学团队、科研团队和合作机制,但学者与教师、包括部分学生之个体,是教学与科研活动的真正实施者。至少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教师与从事教育的学者并非任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进一步看,行政的工具色彩太浓重*参见谭海波:《公共行政价值的批判性反思 ——基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其组织管理过程以效率和一致性为基本取向,与纯粹以人本身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在性质上也相去甚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现有的研究框架窄化了教育法学的问题域,与实际的教育法的范围不相匹配”*褚宏启:《教育法学的转折与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因此,对于教育活动,我们必须寻觅一种新的理论定位,以便为其中存在的已发现或未发现的各种法律问题寻求一种体系化展开的可能性。这种定位既要承认教育与科研活动的个体性,又要突出思想和知识的尊严,使得在以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中发生的法律问题能够得到更加深刻而妥当的解决之道。
4.契约属性与双重义务
最后,教育领域也存在与普通民事活动相似的内容,但却又不能简单地以合同法制加以解决。这些内容包括学校与教师之间的人事法律关系,但更具特色的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对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国际上曾有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公法契约理论、私法契约理论、代替父母理论、特权理论、宪法理论、信托理论等多种立场*参见申素平:《高等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2期。;在我国,法律没有直接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定性,但从实践中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程度的契约性,至少可以理解为一种拟制的契约关系:学生支付学费(部分学生由国家代为支付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负有正常开展教学活动和保护在校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这既是法律直接赋予的义务,也是能够从契约性的合意中解释出的义务。如果有可能,应当对合同法的文本及其适用作适当的扩张,或从教育法方面着手完善有关规定。在民办教育形式中,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契约性更为突出,特别是学生入学时学校所作承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的问题,或学校收费项目中有某项服务而实际未提供的问题,除合同法进路外几乎别无选择,但又不能简单地通过合同法的既有理论去解释相关的教育者义务及受教育者权利等问题。
在当前,教育法学在处理公立学校与其师生关系时,经常从《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及下位的行政法规、规章入手,从国家立法直接赋予学校的义务去认识学校的行为,但这对于师生权益的保障远远不够,因为立法中规定的学校义务过于宽泛、抽象,很多法律义务缺乏可直接执行的内容。教育法需要从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中获得另外一种理论资源作为坚实支点。在我国立法未正式承认公法合同的前提下,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阐释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契约性的法律关系的理论,通过契约义务和法定义务的双重义务体系对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作出更加有效的调整。
以上这些关键问题都呼唤一种新的法理框架,惟有在此种法理框架中,才能完整而准确地处理教育法治所面对的种种法律问题,加强对教育行政管理权力的有效约束,促进学校与师生合法权益的保障。
(二)教育法学的法理框架
教育法学是法学的一个子部门,法学所通行的法理框架和基本思维,也应当作为教育法学的法理基础。在当前,尽管以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为核心的法理框架面临诸多批判,但尚未有一种体系化的替代性架构能够有效取代这种法理框架。此种框架仍然可以作为教育法学认识和建构其规范世界的基础。教育法学的法理框架相当丰富而复杂,其主体框架可以由教育法律关系与教育行为组成,其余部分则围绕此二者展开。
1.教育法律关系
教育法律关系类型丰富、形式繁多,从基本的类型上看,教育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法律关系、特殊优位关系、拟制契约关系和契约关系。
(1)行政法律关系
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对学校进行管理、对教师进行奖励和处罚,公立学校依公法授权对师生进行管理和奖惩,都体现了高权属性,其依托的法理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Verwaltungsrechtsverhältnis)*以前的学说曾认为此类关系属于权力关系(Gewaltverhältnis),但无论是“一般权力关系”(allgemeines Gewaltverhältnis)还是特别权力关系(besonderes Gewaltverhältnis)理论在当前的主流行政法学说中均已经衰落。有关一般权力关系的衰落,见Erichsen und Ehlers,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Aufl, 2010, 401;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及衰落,参见湛中乐:《再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7辑(2009)。,这些特定的高权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自“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衰落后,高权性法律关系中不再存在隔阻司法审查的“飞地”,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学校内部高权性法律关系的运行已经完全纳入行政法律关系之中,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在我国大陆地区,教育法中的行政法律关系也正日益如同其他法律关系一样需要接受司法审查,此为教育行政诉讼兴起的基点。
教育法中的行政法律关系,依据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理念,必须有法律授权的基础方得成立。对行政法律关系所引起法律问题的审查,在我国大陆地区即为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在一般情况下适用《行政诉讼法》中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涉及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情形时也适用合理性审查标准。这种关系对于处理教育管理过程中引发的部分奖励和处罚问题、尤其是退学和开除学籍等影响学生重大受教育权益的处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尤为重要。
(2)特殊优位关系
学业评价与学术评价等体现的是知识和专业上的优位,评价者享有专业上的判断余地(Beurteilungsspielraum)*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259页,一般情况下专业评价本身不受司法审查,部分学业评价具有高度属人性,甚至属于“不可替代的决定”*参见伍劲松:《行政判断余地之理论、范围及其规制》,《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这种优位关系与由高权等原因导致的规范性优位关系有别,是一种作用范围有限、作用方式特定化的特殊优位关系,体现着思想和知识的尊严,体现着学术自由的内在价值,也是在教育法中特别发达的法律关系类型和理论构造。对于此种专业判断,法院一般不进行审查;即使进行审查,也仅仅在其明显属于行使行政权力之时介入,而且认为在此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评价结果,而是对价值形塑因素(die wertbildenden Faktoren)的宣告和详细的说明*Zimmermann: Sachverständigenpflichten, DS 2006, S.313.。此种法理认知及法律思维为教育法学把握学业评价与学术评价中的特殊优位关系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
同样地,这种特殊优位关系也体现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运作中。《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等行政立法确认了此种特殊优位关系的存在,例如“学术自由”和“教授治学”的原则即由此种特殊优位关系引申得出。由于此种特殊优位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并存,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在教育法学尤其是高等教育法学当中,就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挑战。只有特殊优位关系和行政或民事法律关系相结合,才能承载大学自治和治理的整套制度安排。
(3)契约关系
学校聘任教师、采购物资、签订科研协议等,体现的是契约关系。契约关系中包含一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同种类的契约,法律关系丰富而复杂。严格而论,教育法中的契约关系包括公法合同和私法合同,但因我国法律还未正式承认公法合同,因此像科研合同等尚无法完全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学校与学生之间还存在一些非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可以有效地解释出学校的保护义务及附随义务,也可以解释出学校要求学生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这种拟制契约关系作为法律所直接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之重要补充,既可以吸纳后者为其中的基本内容,又可以对后者进行体系化和完善化,全面提升师生权益的法律保障。在未来,教育法制和教育法学还须向这些方向努力。
2.教育行为
此处所言的“教育行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个行为(Akt),而是一组作用(Handeln)乃至一系列活动(Handlung)的总称*在行为的层面上,我们首先需要区别各种容易混淆的“行为”概念,然后才能对教育法中涉及的行为作出区分。目前国内法学著作将大量不同的概念都译为“行为”,极易导致误解。在各种“行为”概念中,Handlung为没有特定法律内涵、不一定包含意志因素的客观的行动,本文译为“活动”;Handeln与Handlung意义接近,但带有意志因素,经常包含目的意思,台湾地区习惯译为“作用”,本文也从大陆地区一般行为习惯译“行为”,如“教育行政管理行为”、“学校治理行为”、“专业评价行为”,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是“作用”;Akt较为复杂,一种含义是带有目的意思和效果意思的意思表示,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或行政行为的中心词,与Geschäft相通,本文译为“行为”;另一种与real联结为Realakt(事实行为),表示不包含明确的意志因素但引起客观事物改变、导致权利义务变动的举动,本文也译为“行为”。。它至少包括教育行政行为、学校治理作用、专业评价作用和校内管理行为。
(1)教育行政管理行为
教育行为首先包括教育行政管理行为,主要是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行政机关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决定、命令,大部分教育行政管理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另外也存在一部分行政指导和事实行为。对此,应当运用行政法学的有关理论知识去把握和处理,但要注意结合教育领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些行为已经遍及教育的各个领域,例如2015年制定的《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在教育法领域中的作用,它是我国教育法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2)学校治理行为
学校治理行为包括与治理过程相关的选举、 表决、议事、创设与撤销机构、决定机构的合并与分立、制定校内规章制度等等。这些行为普遍存在于各种学校之中,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尤为活跃,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制中也开始受到重视。2014年施行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就对学校治理行为提出了相当详细的要求。学校治理,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治理,应满足充分代表、专业判断、灵活联合、多元参与的原则*③参见湛中乐、苏宇:《中国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基本原则与关键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它不单纯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高权活动过程。在治理过程中,对于选举、表决、议事等活动,应当视为自成一类的形成性公法行为,没有高权行为的效力特征;校内主要治理机构作出的决定、命令或制定的规章制度,则是典型的高权行为,部分有明确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还属于行政行为。学校治理行为是教育法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行为,因为它在理论上应当是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民主过程和多元参与的合力来进行的;也不同于村委会或居委会的民主自治活动,因为学校的治理强调多元参与而非纯粹的民主表决③,并且学术事务(也包括教学与科研的专业事务)在学校治理中拥有重要的特殊地位,它排除行政权力乃至普遍性民主过程的干预,仅限于相应学术群体,因此学校治理行为的特殊性在此尤为鲜明。
(3)校内管理行为
根据学校治理过程所形成的结果或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学校有关部门对学校内部具体的人事作出决定,则属于校内管理行为;对于公立学校而言,则是一种高权行为。它包括学生的招录、工作人员的任免、晋升、调动以及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奖励、处分等。此类行为在有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行政行为;否则,即应为普通的校内管理行为,相关纠纷须依照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或通过学校内部的治理过程加以解决,对部分符合申诉条件的行为不服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起申诉。
(4)专业评价行为
对于教育法领域而言,最富特色的是此类专业评价行为,即教师或其他专业工作人员以其知识、技能乃至思想为基础,对同行、学生或其他外部机构与人员的学术能力、作品质量、学习成效等作出评价的行为,包括学业评价、成果评价、学术能力评价等。此种行为在法理上属于专业判断,相关判断在其专业范围内享有判断余地,除非存在现行立法规定,或通过自治过程或法律、法规授权制定的既有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特殊的救济途径,一般不受外部审查。专业人士的评价应当不受非专业人士评价的干涉,这应当是教育与科研活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学术自由和教授治学的核心准则,也是学校治理最需要确立的制度基点。
专业评价行为往往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而是与其他行为(通常是行政行为或校内管理行为)结合而成为混合的教育治理或管理行为,例如授予学位、晋升职称、评优评奖、对学术不端的惩罚,等等。对于这些混合的行为,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区分,对其专业评价的部分应当坚持判断余地理论,不能轻易由非专业审查机构推翻专业判断;但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校内管理行为而言,它应当受到有权机构的法律审查;如果在主体、程序和形式等方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校内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它也应当像一般的同类行为被撤销或宣告无效。
专业评价行为目前在我国尚缺乏完善的规则体系和独立的法律调整机制,甚至很多重大评价行为都缺乏说明理由等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这应当是未来我国教育法学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5)民事法律行为和行政私法行为
此外,教育法领域还存在一部分民事法律行为,也包括所谓属于“行政私法”的政府采购等行为,依照一般的民事法律制度及政府采购法制进行。这些行为在制度上和理论上不存在特殊的法理构造,只是需要注意教育领域的特殊性,例如政府采购的标准可能需要向安全性倾斜甚至需要制定特殊的法定标准,但在法理上大体可以直接运用其他部门法学的架构与内容。
由此,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及法理框架已经基本清晰可见,教育法学确实拥有独具特色的理论基础,在主要的法理构成上也有别于其他的部门法学,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尤其是教育法学的相对独立性问题。
三、教育法学的相对独立性
(一)教育法学相对独立性之基础
教育法学是否具备相对独立性?这需要从其研究范围的特殊性、研究方法的专门性、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和理论体系的自主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只有在这些方面都具备鲜明的特色时,它才需要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
1.研究范围的特殊性
教育法学在研究范围上的特殊性非常突出。教育法学的研究范围是教育领域有关教育行政管理、学校治理、招生、教学、科研等一系列活动的法律现象,这一系列活动并不属于单一的规范维度,无法归类于任意既有的研究对象类别,而其中几乎贯穿始终的、在法律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专业评价与学术自由在其他部门法学的研究对象中更缺乏有效的参照物。教育法的研究范围不仅在整体上具有特殊性,在个别具体项目上更是具有其他领域研究范围所无法覆盖的特殊性,例如对于教学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关系、科研与文化活动自由的关系,均有高度的形而上学特征和超越于世俗价值的精神特性,这一点就足以决定教育法学在研究范围上已经超出目前其他类似部门法学的疆域。
2.基本问题的重要性
再者,教育法学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教育法学的众多法律现象中蕴含着若干基本问题,是解决教育法大部分问题所必须回答的,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办学自主权的内容与界限、学校行政权力的来源及界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学术评价之判断余地的范围与保障、教师享有教学自由与科研自由的依据与程度、教师与学生正当权益受侵犯的可诉性、社会力量办学中国家与社会的分工等,除个别问题已经有部门法学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外,大部分的基本问题都十分重要,而且在其他部门法学的理论体系内并不存在现成的答案。这些重要的基本问题对教学、科研的组织和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随着教育普及度的不断提升,它们几乎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一生,因此也更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3.研究方法的专门性
教育法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专门性应有体现。教育法学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仍然借助于法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等;教育法学自身应有的研究方法曾长期被掩盖。即使是前述有关教育法学理论基础和法理框架的分析,主要也是基于其他部门法学及法理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基于教育法学研究范围的特殊性和基本问题的重要性,教育法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应当具备专门性的。
法学的研究方法,从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上看,有历史方法、比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逻辑学方法、伦理学方法、诠释学方法、社会访谈与实证分析等;从法学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看,最为常用也最为基本的是规范实证分析,其余有类观点学(Topik,论题学)、法哲学方法、法律经济分析、价值导向思考(Werteorientiertes Denken)等,但以上常见的法律方法都不能表现法学各个子学科所真正使用的主要方法。在法学的各个子学科中,其教义学体系和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融合的,例如刑法学以犯罪构成理论为教义学体系的核心部分,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即隐藏于犯罪构成理论中,“四要件+社会危害性判断”的犯罪构成体系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气息,而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则是以新康德主义法哲学为其方法论指引的*参见彭文华:《犯罪构成: 从二元论体系到一元论体系——以事实和价值关系论为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6期;邓君韬:《超规范问题及其意义 ——对犯罪认知体系方法论的初步考察》,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368页。教育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也当隐含于教育法学的教义学体系之中,只要教育法学的法教义学体系具备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乃至自主性,其研究方法的专门性也自有根据,所以关键应当是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问题。
4.理论体系的自主性
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其教义学体系)具有自主性,有自己的灵魂所系,不能由“拼装”的其他部门法理论所取代。教育法学的法理框架中固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但就其富于特殊性的部分——特殊优位关系、学校治理行为与专业评价行为看,是任何其他部门法学的现成体系所无法涵盖的。这是因为它们在理论基础上源生于知识的优越地位与思想的特殊尊严,而教育活动的灵魂正居于此处。整个教书育人、繁荣科学的事业之所以崇高,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和思想能够直接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效用和国家利益,更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使命。专业判断与学术评价行为的独立性与学校治理过程的特殊性,也并不完全是因为看得见的功利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外行指导内行”容易导致教育和科研的决策失误和经济损失,更是因为知识与思想不可被肆意折辱的内在尊严。正是这种理论基础的展开,造就了教育法学在理论体系上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如果教育法学不需要考虑知识或思想的优越地位,它和一般的公共服务法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
因此,可以认为,教育法学的核心特殊性在于直面如下问题:对于基于知识或思想的优越地位而作出的行为,应当如何使之受到法规范的最佳约束?法律固然未必可以约束思想、学问,但并非不能约束与思想及学问相关、尤其是凭借思想与学问的名义作出的行为。如果在学术相关事项上采取判断余地绝对化的法理立场,教育法学亦无可资独立之空间,但往往我们并不能完全承认知识与思想名义下的绝对行为自由。对于防止滥用知识与思想的崇高尊严而言至少有两个标准至关重要:首先,我们需要判定相关行为是完全基于知识与思想,而不包含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动机或目的,可称之为“学术相关性审查”;其次,我们需要检视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学术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原则,可称之为“学术原则性审查”。此二种审查均要求独特的规范思维,也包含着特定类型的法律实践与法学方法。例如,在美国,法院区分了公立学校对学生的退学处理,对于“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dismissals for academic causes)不要求类似于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但要求对课程信息的专业意见;而对“基于纪律原因的退学”(dismissals for disciplinary causes)则提出了听证程序的要求*See Board of Curators, Univ. of Missouri v. Horowitz, 435 U.S.78, at 87, 90.。在法院审理案件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判断学校的决定是否出于“纯粹的学业理由”(purely academic reasons),其判断范式仅追问是否存在客观的学术判断依据,需要依托类似于“依事物之本质”(the nature of things)的方法论基础*“事物的本质”(德文Natur der Sache)理论是一种根据事物本质来界定规范类型之适用的学说。“事物的本质”,根据拉伦茨的定义,在当代是指“一种有意义的、且在某种方面已具备规律性的生活关系,也就是社会上一种已经存在之事实及存在之秩序。”Vgl Larenz,Wegweiser zu richterlicher Rechtsschöpfung, in:Festschrift für A.Nikich, 1958, 275 ff; 转引自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这一原则在德国应用尤为广泛,在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也应用甚多。,而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范式截然不同。但是,无论国内或国际学界,都未对这两种教育法学特有的审查方式与思维方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索,也就难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独具特色的教育法学理论体系。一旦基于这一关键问题的理论体系能够获得系统的归纳和建构,从而支撑起前述理论框架,则教育法学的理论自主性也就呼之欲出。惟有如此,教育法学才能彰显其学科特色与独立定位的需要。
(二)教育法学的学科定位
教育法学的学科定位问题集中于一点:教育法学能否成为我国法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二级学科的标准何在。我国目前学科分类的标准主要有五种:一是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二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下称《研究生专业目录》);三是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下称《本科专业目录》);四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代码,即由国家社科基金与社科院系统制定的学科级别分类目录;五是《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参见袁曦临、刘宇、叶继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框架初探》,《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1期。。其中,对于学科建设而言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是《研究生专业目录》和《本科专业目录》,两个目录均没有表明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划分的原则。事实上,在每一个一级学科之下,划分二级学科的原则都不是正式文件明确规定的,大量的二级学科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参考样本可循的,或者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特别设置的。由此,要研究哪一个学科可以成为二级学科,就需要研究二级学科所属一级学科的传统及特性、研究设置二级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根据理论和现实的综合需要而作出判断。
对于法学而言,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二级学科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二级学科,包括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此类学科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由众多学者筑成其法理框架和教义学体系,包含鲜明的理论特色和体系性;另一类是新兴的二级学科,包括经济法学、环境法学、社会法学、体育法学等,此类学科由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形成,其理论体系本可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和系统性,但尚未经过精致的系统化提炼,应用性色彩较强,下属的各部分相互之间也缺乏体系性的整合。判断两类二级学科的标准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对于传统的二级学科,历史本身就提供了一部分清单,其余部分注重的是在学科的逻辑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该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独立性与自足性。对于新兴的二级学科,则在考察其理论体系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之余,还要追问学科的设置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助于系统地解决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在某一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教育法学在法学中的位置目前更加接近于后一类二级学科,因此,对教育法学学科定位的考察就需要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教育法学在理论层面的体系独立性在前文已经得到一定的揭示,但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教育法学能够获得一个正式的平台,教育法学也将提升其体系化的程度,届时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将更加鲜明。在实践层面,教育法学对于当前教育法治化的实践已经呈现出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学校章程的制定与实施、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建设、大学治理事业的推进、师生合法权益的保障、义务教育的落实、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化,等等,都需要教育法学的理论作为指引,需要符合教育自身特性的教育法制度设计。其中,相当大部分内容都无法指望其他部门法学提供充分的支持,而在其余部分,尽管交叉学科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持,但却不足以承载全部的重量。例如,在师生权益保障方面,由于教育行政诉讼和教育民事诉讼的兴起,师生权益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但是,民法和行政法能够提供的救济是非常有限的,它们几乎无法以任何形式触及学术和学业评价的部分,也很难介入校内的治理和管理过程,对于影响教师重大权益的职称评审及影响学生终身的“保研”(免试推荐攻读研究生)、自主招生加分认定等关键事项,更显鞭长莫及;而这些事项本来可以通过专家复审委员会之类直接归属于教育法的救济机制来为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提供法律保障。面对此类问题,传统的学科结构限定了救济机制设计的思维,使得适合于教育活动本身的许多法律制度和救济机制没有形成。中国的教育事业覆盖十亿以上的人口,大量公民需要接受十余年的教育,教育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和争议、涉及侵害正当权益的事情何止千千万万,与教育法治化的需求相比,我们目前的权益保障机制和纠纷解决渠道的建设还远远跟不上。与此相对照的是,“现阶段我国大陆法律体系的部门划分模式有其局限性,传统上教育法被划入行政法部门的现实不应成为教育法学成为二级学科的制度性障碍。”*程雁雷:《诉求与回应:构建教育法学学科的若干思考》,《中国高等教育》,2014年第17期。由此,发展作为二级学科的教育法学,对于中国的教育法治化进程、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良性有序发展,有着十分显著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教育法学作为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可以同时隶属教育学和法学,有利于吸收交叉学科的知识,形成互补,促进专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退一步看,即使不能马上成为一个二级学科,也应当至少成为一个专业方向,可能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发挥作用,为学科建设打下理论、观念甚至制度的基础。二级学科涉及人才的培养和输送,需要制度建设和相关机构的发展到达一定程度或至少展示出相当的潜力,但专业方向就不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也可以考虑将专业方向的建设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方案,但总体上教育法学仍然需要向二级学科的方向努力。
(三)教育法学的内容设置
教育法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如果作为二级学科或专业方向,其下属的各个方向也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教育法学的子领域划分,也存在多种方式,各有长短,可供进一步探讨。
1.以教育形式与阶段划分
从教育形式与阶段出发,教育法学可进一步划分为:(1)高等教育法学;(2)高级中等教育法学;(3)义务教育法学;(4)职业教育法学;(5)继续教育法学;(6)特殊教育法学,等等。这种划分方式能够有效针对每一种教育形式及各个教育阶段的特点,但各个领域之间会存在一些范围上的交叉。从大的范围上看,公立与私立是一重维度,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是一重维度,初等、中等、高等与研究生教育是一重维度,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又是一重维度,各个维度之间无法做到整齐划一的区分,只能采取相互重叠的方式。目前教育法学的研究主要是以此种方式划分子领域,且较多地聚焦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法律问题,应当进一步扩展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2.以教育管理过程划分
从教育管理过程出发,教育法学可以进一步划分为:(1)考选招录法学;(2)教学管理法学;(3)校园管理法学;(4)学业评价法学;(5)学术评价法学;(6)职称评审法学;(7)师生权益救济法学;(8)学校治理法学,等等。此种划分方式将使问题更为集中、更为专业,但可能研究的问题过于细碎,难以独立支撑一个专业方向,并且研究需要跨越教育形式和阶段,在理论的共通性与实践的可行性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
3.以法律关系划分
从法律关系出发,教育法学可以进一步划分为:(1)教育行政法,主要研究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教育行政管理行为;(2)教育合同法,主要研究教育领域的合同与侵权法律关系;(3)教育治理法,主要研究在学校治理尤其是高等学校依章程进行治理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法律关系;(4)学术评价法,主要研究在学术与学业评价过程中涉及的特殊优位关系。这种划分方式的优点在于法律关系清晰、理论性强,教育法学的特色一目了然,但实践中往往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混合法律关系,单纯研究某一个方向的问题,对于处理教育法学的全局性或复合性问题仍有许多不便。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对于教育法学的内部划分和内容设置,可以有更加丰富的思路,以上模式也仅仅是若干参考依据。但是,它展示了教育法学作为一个丰富而复杂的领域,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最好能够在体系化的前提下,在纲举目张的基础上展开不同分支的探索,否则可能有顾此失彼、全盘失调的可能性,这就对教育法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从内容到对象、从形式到方法的体系化要求,需要学界进一步探索。
四、结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之盛,制度为基。教育法学对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教育法治化的积极推进、对于受教育者的权益保障,有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意义。它在理论上既集思广益,又自成一体;它在实践中既适时应务,又别有天地。将教育法学从传统的学科分类中解放出来,建设相对独立的、系统的教育法学,是当前教育学界与法学界的时代使命。
(责任编辑蒋重跃责任校对蒋重跃刘伟)
Theoretical System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Law
ZHAN Zhong-le,SU Yu
(School of Law,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time when systematical researches on education law arose in the Mid-20th century,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law has kept winning concerns of scholars, whose discussions lacked consensus and fundamental reflections on relative jurisprudential problem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ducation law should be grounded on four groups of element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nd the duty of state, the academic freedom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school operation, the humanism and dignity of thought, and the double obligations with contractual duties. The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mainly consists of legal rel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education, with special priorities, school governance and professional judgment as its features. This design could build education law as a discipline subordinate to both legal science and pedagogy and frame characteristic arrangement of curriculum, which will make it better develop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and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education.
Key words:education law; theoretical system;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5-07-20
[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2-0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