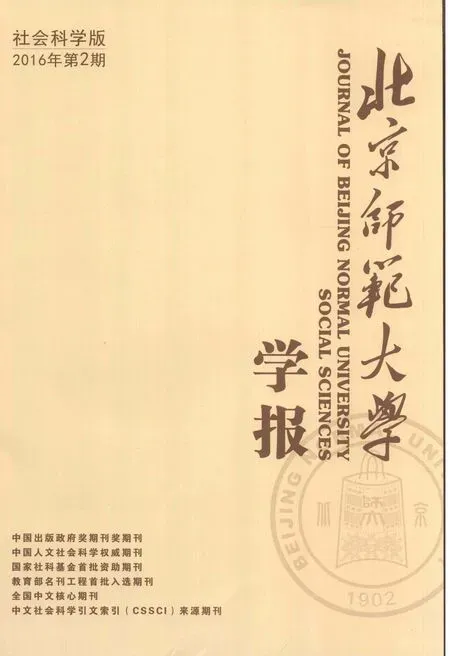对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思考
秦惠民,谷昆鹏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对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思考
秦惠民,谷昆鹏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法治要求健全的法律体系。经过三十余年的教育法制建设,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相对于依法治教的要求,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在与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法律体系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教育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并不具有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教育法律体系缺乏整体设计和系统性,在横向上覆盖周延性较差,在纵向上缺乏配套的支持制度,教育法律的实效性较弱。完善教育法律体系,要求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厘清构建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逻辑——将受教育权的实现与保护作为逻辑起点,将教育权的区分与设定作为现代教育法律体系的规范逻辑,将“独立的法律部门”作为教育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逻辑定位,将立法分类维度作为教育法律体系隐含的逻辑结构。在现实层面上,要把握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有利契机,提升教育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将填补立法空白作为重点,不断优化教育法治实践,积极回应教育法律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教育法律体系的实现,对于实现依法治教、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育法律体系;依法治教;构建逻辑;现实选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依法治国”,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依法治教”要求教育管理与改革实践依循法治思维、采取法治方式,因而必须要有科学、全面、成体系的教育法律法规予以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法律从无到有,已初步形成教育法律体系,但从整体上看,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整体法治推进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和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对于实现依法治教、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概况及发展历程回顾
体系是指某些事物或意识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教育法律体系就是由多种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其内在的秩序和联系组成的系统。我国自1980年颁布第一部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起,三十余年来相继颁布了百余种教育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自成系统的教育法律体系,也可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对规范我国的教育活动、推动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框架之于体系犹如骨架之于人体,把握住框架就可清晰了解一个体系的结构。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的框架为:以《教育法》为基本法律,纵向上分为基本法律、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五个层次,横向上包含《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六个教育法律部门(见表1)。这个法律体系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五个层次、六个部门纵横交错,此外还有百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填充其中,形成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立体式法律网络,结构相对完整、内容基本全面、层次较为清晰、功能相对明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体系是三十余年来中国教育法制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
表1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框架
(二)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发展历程回顾
1.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形成、发展的阶段梳理
到目前为止,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80年为酝酿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通过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修订新的学校工作条例、恢复高考制度,全面恢复、整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破坏的教育秩序,探索和提出新的制度性规范草案,为教育法制的开端奠定了基础。1980-1995为起步阶段。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颁布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第一部有关教育的法律,开启了中国教育法制建设、发展的帷幕,其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的相继颁布,推进了教育法制建设的进程。1995-2000年为教育法制建设的综合化、系统化阶段。这期间颁布了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此后又相继颁布了《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部门法。2000年以后为教育法制建设的发展和体系形成阶段。《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
2.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形成、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推动力与关键节点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程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的提出,既是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背景,也为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注入了强大动力;与此同时,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历程与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历程也是相辅相成的,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中的重要事件或举措,也成为教育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1982年新《宪法》的颁布与实施,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以及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新《宪法》规定了教育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立法依据,规定了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法律规范,为教育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劳凯声:《中国教育改革30年(政策法律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和宪法依据。“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是教育法治发展的重要动力,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首次提出“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要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进行,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就是依据该决定提出的教育改革目标进行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框架”,更是明确了教育法制建设的具体任务。这两个重要文件的颁发,是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二、比较视野中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
英美法系国家的教育法律,法院的判例居重要地位,其成文法往往不追求系统和完善。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较,我国(包括台湾地区)和日本都属于大陆法系或成文法系,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通过与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教育法律体系相比较,可以从差异中分析特点、原因和问题,从而为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教育法律体系的特点
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基本法》是《宪法及增修条文》之下的独立法律部门,《教育基本法》的分类标准同样是“教育活动、教育活动主体、教育行政”。与日本有所不同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法律体系,充分借鉴了英美法系以及国际法中的教育法规范,这表现在司法院大法官解释、法院判例及判决、法理学说、教育习惯、教育基本原理等方面;对国际法中教育法规范的借鉴主要是《国际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关于教育的原则和理念。
日本的《教育基本法》是《日本国宪法》下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基本法》之下按照“教育活动、教育活动主体、教育行政”三个标准进行分类,所有的教育相关法律均归类于三个标准之下,横向上覆盖教育各个方面;同时,每一部教育法律之下均有配套的施行令、施行规则,形成“法律—施行令—施行规则”纵向体系,确保法律效力充分落实。
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教育法律体系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作为教育领域基本法律的《教育法》,均是宪法之下的独立法律部门,体现了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教育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二是教育法律体系完善,逻辑清晰,“教育活动、教育活动主体、教育行政”的分类标准在横向上足以覆盖教育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遵从“自上而下,原则性递减、操作性递增”的规则,保证了法律的实效性;三是教育法律体系注重对国际先进教育法制理念的借鉴。
(二)我国目前教育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通过与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教育法律体系的比较,可看出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具有如下差异:第一,我国教育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并不具有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201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部门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和幼儿园管理条例、教师资格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被列入行政法这一法律部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第二,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缺乏整体设计和系统性。例如,2012年3月28日公布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就是针对近年来“夺命校车”事故频发而应急制定的。但从完善教育法律体系角度需要的一些重要教育法律,诸如学校教育法、考试法、教育投入法等等,虽呼吁和研究论证多年,却难以出台;有些早期制定的教育法律如《学位条例》,虽然已经难以适应和满足我国法治的进步和实践需要,但迟迟不能得到与整体法制建设相协调的系统修订。第三,由于没有如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教育活动、教育活动主体、教育行政”这样明确的立法分类标准,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横向覆盖周延性差,存在大量立法空白,导致教育实践中很多问题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使依法治教难以实现。第四,在纵向上,我国的教育法律缺乏如日本“法律—施行令—施行规则”这样的配套实施规则,导致教育法律难以得到彻底落实。同时在立法技术上由于法律用语空泛,使得教育法律的实效性进一步削减。例如《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师资力量,组织校长、教师的培训和流动,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但在实践中,校长、教师的合理流动缺乏配套的制度规范和保障措施,实施起来还面临诸多困难,导致法律规定仅仅成为一种难以执行的原则宣示。
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发展至今,成果显著,已经建立起基本的教育法律体系。但目前教育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已有的实定法也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解释力较弱,实效性不强,尚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国情,难以满足依法治教的现实要求。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推进教育法制建设十分必要。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厘清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
三、对教育法律体系构建逻辑的思考
(一)受教育权的实现与保护——现代教育法律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教育是实现个人的发展、自由和尊严的前提,受教育权是现代社会中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整个教育法律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所有教育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都应当围绕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核心*秦惠民:《走入教育法制的深处——论教育权的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6页。。从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来看,实体性的受教育权,主要是指各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利,必须实质性地平等享有;形式上的受教育权,则表现为非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享有。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是构建各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二)教育权的区分与设定——现代教育法律体系的规范逻辑
现代社会的法定教育权包括家庭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家庭教育权主要指由法律所确认和维护的父母对其子女在教育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社会教育权则是指法定的社会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所行使的教育权利,它主要指各社会主体依法享有的教育举办权和对教育活动进行参与、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教育权是指国家依法履行教育职能的资格及依法行使的公权力,它包括国家的施教权和对教育的管理权,是国家统治权力的一部分。在这三种教育权中,国家教育权是现代社会教育权的主体。
教育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规范教育权,将多种教育权置于科学、合理的体系和结构之中。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家庭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国家教育权进行区分、规范和设定,明确各种教育权的行使边界,实现教育权的合理归置。例如《义务教育法》主要是对国家、家庭的教育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设定,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则主要规范了社会办学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二是协调三种教育权的关系、促进三种教育权的平衡。在这三种教育权中,国家教育权由于有国家强制力作为支撑,在教育权的制衡中占据主导地位。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就是要通过多部教育法律的协调配合,限制国家教育权力的恣意扩张,引导国家教育权由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使之成为实现公民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平等的基本保障。教育法律体系对教育权的规范限制作用,有利于在家庭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的张力,“既避免了没有制约的国家教育权走向教育国家主义,也防止了绝对的教育自由主义产生的弊病”*温辉:《宪法与教育——国家教育权研究纲要》,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
(三)教育法的地位——教育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逻辑定位
教育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体现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体现着教育这项社会活动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特殊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学者的学术研究*张文显:《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四版,第86页。,还是国家的法制实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教育法都被视为行政法的子部门,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律部门既是一个法学概念,也是组成法律体系的一种客观的基本要素。法律部门虽然是一种学理上的划分,但对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制实践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立法、执法、司法的实践过程(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四版,第81页)。的地位。这种归类方式隐含的逻辑是:教育管理隶属于行政管理,教育法依循行政法的法理逻辑。这是我国传统的教育管理理念在立法领域的反映,不能体现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不符合教育的改革发展趋势。在教育法律实践中,这种立法归类方式所带来的行政法思维逻辑,难免导致教育管理者用行政思维替代教育思维、用行政逻辑替代教育逻辑的思想和行为倾向。
从逻辑角度而言,教育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一部分涉及行政法律关系,但随着学校类型的多样化和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领域内也存在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等其他法律关系或混合型的法律关系。即使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教育行政关系和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也存在差异,教育行政机关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管理学校,而必须要考虑到学校的自主性与专业性。其次,教育法律的调整方法也具有特殊性。行政法选择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维护行政主体的权威、实现对行政相对人的有效管理,而教育管理由于其对象的特殊性,更强调采用协商合作、批评教育、合理引导的方式,要求教育管理者从保护受教育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保护教师的职业权利、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
从现实角度而言,我国的教育法治进程不断推进,教育法律数量不断增多、教育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教育法律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可能性与现实基础已经初步具备。
(四)立法分类维度——教育法律体系隐含的逻辑结构
所谓立法的分类维度,在教育立法中是指制定一部教育法律时首先要考虑该法律所针对的是教育体系中哪一维度或哪一层面的问题。不同的教育法律面向教育体系的不同维度或不同层面(例如《教师法》是立足于“教师”这一“教育主体”的维度,而《高等教育法》是立足于“高等教育”这一“教育阶段”的维度,教育主体与教育阶段显然不是同一维度)。教育立法分类维度,体现着一国教育法律体系隐含的逻辑结构,纵向上使《宪法》、《教育法》与具体的教育法律相衔接,横向上体现着教育法律体系的覆盖范围。教育立法分类维度决定着教育法律体系的逻辑自洽性和结构的科学性。
由于我国现有教育法律体系不是按照严格的立法分类维度建构的,所以已有的教育法律法规缺少体系性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相互衔接。教育法律体系中各法律部门不仅存在着交叉重复,而且存在较多法律空白,一些问题依然无法可依。没有明确的教育立法分类维度,不能不是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之一。如我国现有的六个教育法律部门中,《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是按照教育阶段或教育部门进行区分的,而《教师法》属于教育主体的维度,《学位条例》则属于教育活动过程维度,这些教育法律并不在相同的分类维度上,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覆盖面也就有限,存在内容交叉和法律空白也就在所难免。再如在教育阶段的维度上,就明显地存在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成人教育等相关法律的缺失。
教育立法分类维度的设置应当科学、合理,既要做到系统全面,做到不遗漏、不缺失,也要顾及相互间的统筹协调,做到不重叠、不冲突。如何设置教育法律的分类维度,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教育。首先,教育是一项具有特殊规律性的社会活动,教育法律既是调节教育活动主体间关系的制度与规范,同时还是教育活动过程顺利进行的保障。其次,从系统论的角度,我们还应把教育看作一个系统,教育法律既要协调系统内部各种关系,还要协调教育系统与外部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法律分类维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教育活动”、“教育活动主体”这两个维度,是从教育被看作一项社会活动的角度出发的,“过程”、“主体”基本上概括了教育活动的全部;“教育行政”的维度,则是从教育被看作一个系统的角度出发的,相关法律用以规范教育与政府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分类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教育系统外部不仅仅涉及教育与政府的关系,还涉及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因此仅有教育行政法律规范显然是不全面的。
我国教育立法的分类维度,可以在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教育法律分类方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研究和设计。我国教育法律的分类标准可设计为(见图1):教育活动主体、教育活动过程、教育与政府、教育与社会、家庭,教育与市场、特殊类型。其中,“教育活动主体”、“教育活动过程”是基于教育活动这个维度。“教育活动主体”应当包括学校、教师、学生,关于每一主体应当单独立法;“教育活动过程”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宏观上的教育阶段,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二是微观的教育活动过程,包括招生、培养、考试、学位、就业等具体环节,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应当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教育与政府”、“教育与社会、家庭”是基于教育系统维度,相关法律用以规范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其中“教育与政府”相当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教育行政”这一维度,应当包括关于教育投入、教育质量评估、教育公平的相关法律;“教育与社会、家庭”主要涉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关的法律规范;“教育与市场”主要针对营利性的教育机构;“特殊部分”主要针对我国具体国情,例如由我国多民族的特点所涉及的民族教育问题,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阶层差异所导致的弱势群体教育问题(如农民工子弟的教育)等等,都应制定专门的法律。
四、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现实选择
关于教育法律体系构建逻辑的分析是一种理论探讨,具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现实中的立法活动是一种宏大叙事,不像学者们讨论起来这么简单。因此,就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构建、完善而言,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一)把握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契机
从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形成、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历史契机对于教育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家教育法制发展又面临着三个重要契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对教育法制建设高度重视,为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为教育法制建设从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上进一步推进提出了要求;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对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推进依法治教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提升教育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如前文所述,教育法在我国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行政法之下的一个子部门,这既影响了教育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对教育领域一些法律纠纷的实际解决,还不利于教育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关于教育法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问题,在学界尚存争议。如日本即存在“教育行政法规说”与“教育制度独自法说”。日本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兼子仁就提出特殊法学论的主张,认为教育行政及其他个别行政已分别具有自己的法理论,逐渐成为独立的法及法学,实际上是特殊法学,应将特殊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去而独立*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三)以填补立法空白为重点,促进教育法律体系逻辑结构的完善
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每一部教育法律的制定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例如《学位条例》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律的颁布实施,就是顺应当时建立学位制度的需要而出台的;《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则是适应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对职业教育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进行规范而诞生的。我们应当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认识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已有的教育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与理想的逻辑框架有较大差距,但也要承认这是由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决定的,是我国教育法制发展的现实写照,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不容许我们先设定一个理论框架、明确立法分类维度,逐一制定各项教育法律,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法律体系。
我国当前教育法律体系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横向结构上还存在很多立法空白,在纵向结构上,每一部法律的配套实施制度或下位支持制度尚待完善。因此,结合现实国情,加大立法力度,填补法律空白,努力实现教育领域内重大问题有法可依。不断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是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不断优化教育法治实践,积极回应教育法律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
第一,当前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所缺失的教育法律在紧迫性上存在差异,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在立法过程中,应当注意待出台法律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应当把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人民群众的热切关注作为重要的依据,以确定在不同时间不同法律的重要性排序。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提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需要,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从中可以看出考试法、学校法、终身学习法、学前教育法、家庭教育法是国家教育战略关注的重点,在教育法制建设与发展中具有重要性、优先性。再如2010年、2011年、2012年连续三年的两会提案中,关于学前教育的提案占到教育类提案的80%,从中也看出学前教育立法的社会关注程度和迫切性。
第二,在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避免片面追求法律的高位阶倾向。我国的法律体系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规章等几个层面。并不是所有的教育法律制度都要追求较高的立法层次。就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现实而言,解决教育法律制度的缺失问题从而解决依法治教有法可依以及教育纠纷定纷止争的问题是摆在首位的,不应为追求法律的高位阶而影响实践中紧迫需要的教育法律制度的及时出台。
第三,在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大法律借鉴、法律移植的力度。所谓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国外已有的法律规范,使之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所用。法律移植的范围,一是外国的法律,二是国际法和惯例*张文显:《法理学》,第四版,第164页。。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面临一系列由教育国际化趋势带来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拓展国际视野,需要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理念、法律技术、法律规范。我国台湾地区对英美法系、教育相关国际法的学习即是通过法律移植、借鉴来推动本地区教育法律发展的实例。在法律移植与借鉴过程中,需要将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与其他国家法律以及国际法进行比较,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理性选择和本土化改造。
(责任编辑蒋重跃责任校对蒋重跃刘伟)
Reflection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Law in China
QIN Hui-min,GU Kun-peng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a sound legal system. After 30-years’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institutions of education,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law in China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However, relativ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dministering education by law,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law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and Taiwan education law,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education law is not a independent session in the system of law in China; in fact,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law lacks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ness, and the spreadability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and the supporting systems in vertical dire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ystem per se, we should card the basic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law system clearly: (i) the rea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right to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logical point of departure; (ii) the distinction and the setting of the education powers should be the normative logic; (iii) the status of “independent law session” should be education laws’ logic location; and (iv) the legislative classification dimension should be the implicit logic structur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e sh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law system, promote the status of education law, consider to fill in the legislative blank as the focus, and optimize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by law constantly and response to the real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legal system positively.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 law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by law, and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system of education law; administering education by law; logic of construction; realistic choice
[收稿日期]2015-07-31
[基金项目]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委托课题“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框架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2-0005-08
[主持人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想使教育改革与实践依循法治思维,并采取法治方式,实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需要科学、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予以支撑,更需要教育法学的相关法理基础研究加以引领。本期专栏发表两篇文章:秦惠民、谷昆鹏通过对我国与日本、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缺乏整体设计和系统性,在横向上覆盖周延性较差,在纵向上缺乏配套的支持制度。故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具体构想。湛中乐、苏宇对我国教育法学的相关法理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教育法学应根据教育领域中基本权利义务关系的类型特殊性,以受教育权与国家义务、人本目标与思想尊严、契约属性与双重义务为理论基础,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