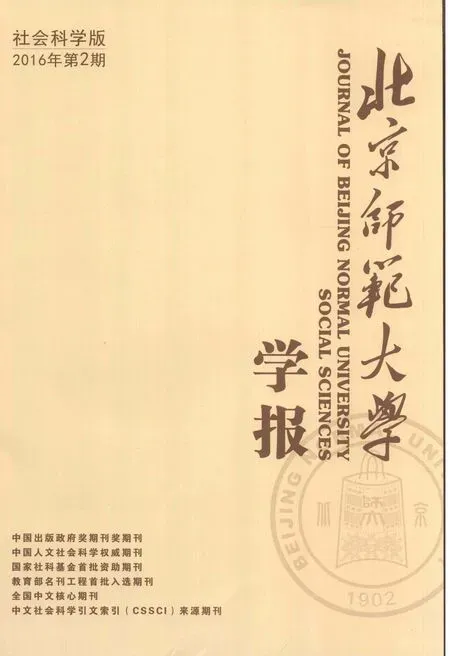文化与创造力:基于4P模型的探析
张文娟,常保瑞,2,钟 年,张春妹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心理系,武汉,430072;2.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桂林,541004)
文化与创造力:基于4P模型的探析
张文娟1,常保瑞1,2,钟年1,张春妹1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心理系,武汉,430072;2.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桂林,541004)
[摘要]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深层心理结构,理解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非常重要。创造力是一个多元构念,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创造力的概念界定各不相同。创造力的4P模型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整合了创造力的不同方面,包括创造性产品和表现(product)、创造性成果产生的过程(process)、创造者的个体特征或人格(person)和创造力产生所需要的环境(places or press from pressures)。以4P模型为框架,本文从四个方面综述了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首先,文化会影响创造性产品的评估标准及表现领域;其次,文化既会影响创造性个体特征或人格的内隐认识,还会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创造性人格。第三,文化对创造力产生的认知途径以及创造力形成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影响。第四,文化对创造性表现的影响会通过时代精神、意识形态、家庭教育等因素建构一种支持或抑制创造性发挥的外部环境。未来研究可以分别从这四个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化与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深入理解影响创造力的跨文化一致性因素与差异性机制。
[关键词]文化;创造性产品;创造性个体;创造性过程;创造性环境
一、问题提出
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Florida(2005)在他的著作《创意阶层的兴起》中反复强调,我们正步入一个创意时代,这不仅仅表现在高科技产业创新产品的异军突起,甚至已经无所不在,渗透到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我们当前正在经历另一个很大的经济转折期——创新转折期。经济发展需要创新来推动。发达国家的经济正转向以信息为基础的知识驱动型经济,而以知识和信息为工具和材料的创新才是最重要的经济驱动力。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多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正是供给侧的四大要素之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必将成为我国改革下一步将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创新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更好地激活和利用人类的创新能力,必须要考虑环境或社会背景对创新的深刻影响。文化作为一个特定人群所共享的符号系统,是影响创造力的诸多环境因素之一。它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不仅可以促进或抑制创造力,影响所属文化下的整体创造性水平,还能够对创造力进行界定和评估,影响创造力产生的过程或途径,甚至会将创造力导向一定的专业领域和社会群体(Sternberg & Lubart, 1996)。
在创造力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化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文化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创造力作为一个多元的构念,不同的研究者所依据的理论视角不同,往往会产生多种多样的诠释。当论及创造力时,可以是在讨论一件前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也可以是在考察一个产生奇思妙想的过程,或是谈论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杰出人才,甚至是一种有助于发挥个体创造潜能的组织氛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为了尽可能全面、客观地综述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我们拟采用Rhodes(1961)和Kozbelt(2010)提出的创造力4P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分别探讨了四大问题:第一,文化对创造性产品的影响;第二,文化对创造性个体的影响;第三,文化对创造性过程的影响;第四,文化对创造性发挥所需要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二、创造力的4P模型
Rhodes(1961)和 Kozbelt等(2010)通过梳理以往的创造力理论和研究,将创造力的概念界定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创造力的 4P模型:创造性产品和表现(product)、创造性成果产生的过程(process)、创造者的个体特征或人格(person)和创造力产生所需要的环境(places or press from pressures)。该理论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整合了如何界定创造力的争议,后期研究者多参照 4P体系对创造性的定义进行归纳。以下是每一个“P”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1)创造性产品(product):这种观点将创造力看作是能够产生某种新颖、独特或者对个人、社会有价值的产品的能力,聚焦于创造者所取得的成果,比如艺术品、发明创作、作品、乐曲等等。这可能是创造力研究中最客观的取向。Sternberg和Lubart(1997)认为,具有创造力潜能的个体,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应当由产品来评判。对创造性产品的主要评价标准为新颖性、实用性和适宜性(Amabile,1983)。
(2)创造性个体(person):这种观点认为创造力更多的是某种人格特质的表现,强调人格在个体创造性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许多创造力的早期研究采用了这种取向,他们通过对照数学家、建筑师、作家以及普通群体的人格特质来确定哪些因素可以作为创造性潜能的指标,比如内在动机、广泛的兴趣、经验开放性以及自主意识(Amabile, 1983)。但另一种研究取向是将人格看作创造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比如Sternberg 和Lubart(1997)的创造力投资理论就将人格看作是影响创造力的六个因素之一。Batey和Furnham(2006)也通过调查和实验研究探索了与创造力有关的人格特质。
(3)创造性过程(process):这种观点认为创造力是由学习、思考、问题解决过程等各种过程所产生的,主张创造是一种心理活动历程,是一种或者多种心理过程的组合。比如,Dreu等(2008)提出创造力的双过程通路模型,认为创造力产品是认知灵活性和认知持久性两种加工策略组合的结果,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
(4)创造性环境(places or press from pressures):这种观点认为创造力离不开环境的作用。创造力产生、表达和发展与个体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体所处环境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创造力的高低。Amabile(2004)归纳出促进创造力发展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由的空间、充足的资源、认同与鼓励、有适当的挑战性和充裕的时间等等;阻碍创造力发展的环境因素包括:过多的限制、不恰当的评价、资源缺乏等等。
文化对创造力的上述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文化会影响创造性产品的评估,不同的文化对新颖性和实用性这两个评估标准的设定并不尽相似。而且文化偏好也会将其所属文化下的群体的创造性表现导向特定的领域。其次,文化既会影响创造性个体特征或人格的内隐认识,还会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创造性人格。第三,在创造性产生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或个人能力也会存在差异,有些文化鼓励发散性思维,有些文化鼓励聚合性思维,这种文化差异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创造力产生的过程或途径。第四,文化既可以被看成是直接影响个体创造性发挥的小环境系统,也可以被看作是影响各个环境系统之间关系的大环境系统。前者通过对创造性的界定与评估、创造性个体特征或人格以及创造性过程起作用影响个体层面的创造性水平,后者通过更为宏观层面的时代精神、意识形态、家庭文化和教育体制等因素对群体层面的创造性水平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下文分别就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
三、文化与创造性产品或表现
一个创造性产品就是那些既独特又适用于发生的环境的产品(Martindale, 1999)。然而,社会文化环境不仅是创造力的促进者,也是创造力的仲裁者(Hempel & Sue-Chan, 2010)。在所属文化背景所看重的领域,能够最优化个体的认知和动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创造性产品,表现为文化对创造性表现领域的影响。Simonton和Ting(2010)用公式C(创造力)= N(新颖性)×U(实用性)来界定创造力,这个乘法公式也是当前学术界在界定创造性产品时所达成的共识之一,即新颖性和实用性是衡量创造性所必须要的指标。然而,新颖性和实用性这两个维度背后的评估标准会因文化和领域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一)文化影响创造性表现的领域
Shane,Venkataraman和MacMillan(1995)收集了来自30个国家、四个不同行业的1228名专业人士的信息来检验个体所属文化与对创新发明的偏好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研究中,创新发明被定义为任何一种对组织而言是新颖的观点。对创新发明的偏好体现在他们会支持新颖的观点,帮助克服那些阻碍新颖观点得以传播和实施的障碍。结果发现,受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个体对创新发明的偏好存在领域差异。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由于在面对不确定的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更高,他们偏好在既定的组织框架之下提出新的想法。权力距离高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较为明确,高权力个体对低权力个体有更多的控制权,因此,创新发明的拥护者会更看重如何赢得重要的权威人物的支持;但在权力距离低的环境中,创新发明的拥护者会致力于建立广泛的、能够看到他们创新价值的大众基础。而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个体会更倾向于将不同部门的员工组织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个创新发明的潜在价值,最后形成统一的想法(Hoftstede, 2001; Lubart, 2010)。与之相似的是,将冒险、独立看得比地位和依赖更为重要的文化中能够看到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看重地位和相互依赖的文化中总体创造性水平更低,个体可能会在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相匹配的领域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比如,在看重和谐和群体凝聚力的文化中会表现出在保持和谐人际关系方面体现出更高水平的创造性,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会发现有更多关于如何获得和维持独立性与个人自由方面的独创性想法(De Dreu, 2010; Williams & McGuire, 2010)。
(二)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文化依存性
新颖性的文化依存性。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认可新颖性是创造力的重要衡量标准,且可以通过同感评估技术来判断一个产品是否新颖。但新颖性通常要根据该想法或产品在创造者所属文化中的常见性来界定(Ward, Patterson, Sifonis, Dodds, & Saunders, 2002)。因此,就同一个创造性产品而言,不同文化给予的新颖性评价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一种文化中不常见的反应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是常见的。以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为例,西方电影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极高,认为其题材很新颖,但中国影评人却认为这是李安导演最普通的作品(Niu & Sternberg, 2002)。因为中国影评人对这类题材的创新模式非常熟悉,认为这部电影没有特别吸引他们的新颖元素;而西方影评人看惯了好莱坞电影中的冒险和科幻题材,对《卧虎藏龙》这类题材反而会感到焕然一新(Hempel & Sue-Chan, 2010; Chiu & Kwan, 2010)。
实用性的文化依存性。对于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个体而言,文化背景会决定他们将什么看作是重要的,机会和挑战分别是什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特定文化的特殊时期内,有些领域很有创造性,而其他领域则相反。比如,在中国历史中,战争对科学技术领域的创造性表现具有积极的效应,但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的创造性却影响不大(Simonton & Ting, 2010)。又如在当今社会发展形势下,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可能会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人在技术创新方面更为开放,但在社会事务方面却很难接受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可能的原因之一也在于社会文化环境对创造性的影响。由于中国文化具有较高的关系互依性,在社会事务领域的创新影响范围更广,那些会威胁或扰乱社会地位的观点要么受到他人的阻碍,要么通过自我审查的方式抑制在萌芽状态中。通过这两种途径,一旦知觉到某些想法不容易被接受,或在所属文化中并无用武之地,个体就会抑制那些观点,最终做出与社会期待更为接近的反应(Hempel & Sue-Chan, 2010)。但是在技术领域的创新通常不会威胁到现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稳定。从而更容易被激发和获得认可和推广。
文化会影响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权重。在评估创造性产品的过程中,新颖性和实用性在不同文化中的权重也会有差异。Morris和Leung(2010)认为,有证据表明中国文化更看重实用性,而西方文化更看重新颖性。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人们会更关心创造有用的产品而不是新颖的产品,期待其他人从实用性而不是新颖性的角度评估他们的工作,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专家可能会更偏向于从实用性而不是新颖性的角度来评估创造性产品,这样的反馈回路会进一步强化重视实用性超过新颖性的规范,形成一种组织内部的文化氛围(Erez & Nouri, 2010; Mok & Morris, 2010),导致实用的观点和产品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被认可和传播。但西方文化崇尚独立和与众不同,鼓励个体在解决问题时提出和他人不一样的观点,因此西方人的新颖性表现要超过亚洲人(Ng, 2001; Niu & Sternberg, 2001; Leung, Au, & Leung, 2004)。
(三)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表现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文化生活或工作的经验能够促进创造力(Leung et al., 2008; Maddux & Galinsky, 2009; Maddux, Leung, Chiu, & Galinsky, 2009)。Maddux和Galinsky(2009)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发现,只有长时间居住在国外而不仅仅是出国旅行才能够促进创造力,并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个体对不同文化的融入程度。对异域文化的适应程度不同,个体创造性表现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适应形式是同化,即接纳当前生活的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放弃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极端的表现就是完全融入异域文化,或完全不能融入异域文化。另一种适应形式就是产生双文化认同感(Bicultural identification),即同时保持对自己本土文化和所生活的异域文化的高度接纳。当两种文化价值观冲突时,便迫使他们发展出一种整合两种文化的、复杂的思维方式(Mok & Morris, 2010)。
以在中国生活的外籍人员为例,随着他们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其创造性表现在一个时期内会增加,逐步到达顶峰之后又会显著下降。因为创造力是新颖性和实用性的乘积。而随着个体对异域文化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他所表现出的新颖性和实用性会存在此消彼长的博弈。从他当前生活的中国文化视角来看,新来的外籍人员带来的观点和解决办法都是新颖的,但实用性不高。这个阶段总体的创造性水平不高。随着他们不断同化到中国文化之中,外籍人员逐步达到创造力的高峰,因为他们仍旧能够引入新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同时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抛弃那些与中国文化不相宜的观点和解决办法。这个阶段,他们的新颖性和实用性都处于中等水平,总体创造力水平达到最高。不过随着他们的进一步融入,尽管实用性水平会上升,但新颖性会下降,总体创造力水平又会呈下降趋势(Hempel & Sue-Chan, 2010)。
而从他们本土文化的视角来看,其创造力水平也呈现出出随时间增长而呈倒U型曲线的发展模式,但是新颖性和实用性之间的动态过程则是相反的。随着在异国他乡生活的时间增长,他们必须要适应异国文化,这需要他们表现出更强的心理灵活性。对本土文化的评估者而言,他们的新颖性会随着其在异国他乡生活的时间增长而逐步提高,但这些想法会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于本土文化,也就是说实用性会随着时间增长而下降。总体创造力水平首先会有一个提高趋势,达到顶峰之后又会表现出边际递减效应,接着就开始下降(Hempel & Sue-Chan, 2010)。
但是对于双文化认同高的个体而言,他们不仅能够避免在顺应异域文化过程中导致总体创造性水平下降的代价,同时还具有提高创造力的优势条件,由于对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都很熟悉,使得他们能够根据情境需要在不同文化范式之间灵活转换(Mok & Morris, 2010)。因此,不论是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还是在异域文化背景下,他们在新颖性、实用性和总体创造力表现上都能够保持很高的水平。更有趣的是,Mok和Morris(2010)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发散性思维任务发现,对于双文化认同高的亚裔美国人而言,启动美国文化能够增加他们在发散性思维任务上的新颖性表现,但对于双文化认同低的亚裔美国人而言,启动美国文化会降低他们的新颖性表现。说明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还取决于个体对不同文化的适应程度。
四、文化与创造性个体或人格
(一)创造性人格特征的文化差异
许多研究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大众对创造性个体的认识。通过对美国、英国、巴西、阿根廷、古巴、中国、朝鲜、新加坡、印度、罗马尼亚等国家被试的研究表明,人们关于创造性个体关键特征的内隐理论具有部分跨文化一致性,比如,都具备特定的认知技能(包括建立联结的能力、提问、想象力、思维灵活性等);都有一些共同的人格特质(例如,独立性、自信、果断)和动机水平(野心、热情)(Kaufman & Sternberg, 2006; Lubart, 2010; Rudowicz, 2003)。然而也发现了一些跨文化的差异。
首先,有些特征在一种文化中被提到而在另外一种文化中根本没有被提及。比如北美对创造性个体的内隐理论提到了“幽默感”、“美感”,但中国人没有提到(Rudowicz,2003)。相反,创造性人才的集体主义特征如“启迪他人”、“对社会的进步做贡献”、“被他人欣赏”被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提到,但北美无人提及。其次,关于创造性特征与诸如智力或智慧等相关概念的区别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存在差异看法。比如,北美被试认为创造力与其他概念具有很好的区分性,而亚洲或非洲的研究表明,这些概念是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鉴别的(Chan & Chan, 1999)。
(二)文化价值观与创造性人格
文化对创造性个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实现的,这个过程又表现为个体对所属文化价值观的接受与内化(Erez & Earley, 1993)。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偏好与要求,然后经过社会化过程传授给个体。Hoftstede认为文化价值对人类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并提出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阳刚气质(masculinity)—阴柔气质(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不确定性接受(uncertainty-acceptance)。这些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与创造性相关的人格特质,且主要集中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三个维度上(Erez & Nouri, 2010; Hoftstede, 2001; Lubart, 2010; Rank, Pace, & Frise, 2004)。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创造性人格。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主要以人们之间的联接强度和凝聚力高低为特征,来自个体主义国家的人们主要关照他们自己,而在集体主义国家中,人们会照顾所属群体大范围内的社会群体成员。已有研究表明,自我决定价值观与创造力正相关,而尊重传统、安全感和服从性与创造力负相关(Dollinger, Burke, & Gump, 2007; Kasof, Chen, Himsel, & Greenberger, 2007)。自我决定观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相对应,尊重传统、安全感和服从性对应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与众不同、自主性、独立性和自发性,这些特质对创新来说都非常重要(Jones & Davis, 2000)。相反,集体主义强调对群体的服从、与他人保持一致和相互依赖,这些因素都会抑制独创性观点的产生以及自我表达(Brewer & Chen, 2007)。但是强调群体一致性和服从性的文化价值观能够促进观点的实用性和适宜性,也就是保证他们的观点被他人所接受,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因此,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方式不同。个体主义文化鼓励观点的新颖性,集体主义文化强调观点的实用性和适宜性。
权力距离与创造性人格。权力距离高表示接受社会等级制度,拥有更多权力的个体能够控制拥有较少权力的个体(Hofstede, 2001)。因此,个体应该服从他的上级,接受他的命令。权力距离低反映的是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在等级社会中,管理者和下属的关系基础是服从和纪律。在权力距离低的社会中,领导风格是授权、鼓励追随者自主决策、承担责任、参与决策,并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Morrison & Milliken, 2003)。
因此,在高权力距离社会中,追随者在社会化过程中没有得到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独特的问题解决办法的训练。他们更倾向于服从现有规则和程序,尊重领导的意见,而不是打破常规。对于偏离常规的恐惧会导致他们更为强调想法的适宜性,以保证其想法被领导接受。相反,在权力距离低的社会中,人们并不怯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没有义务修饰自己的观点,使得它们能够被上级领导所接纳。所以,在权力距离低的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个体可能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新颖性,而在权力距离高的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个体可能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实用性和适宜性(Erez & Nouri, 2010)。
不确定性规避与创造性人格。不确定性规避高反映的是一种严厉的文化。对模糊性容忍度很低的社会,会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来减少不确定性,并且对那些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会采取严厉的制裁。不确定性规避低反映的是一种宽松的文化,社会规范表现为多种选择渠道,能够容忍偏离行为和错误(Gelfand, Nishii, & Raver, 2006)。与严谨的文化相关的核心结果包括秩序感、效率、服从、稳定性和惯性,所有这些因素都支持那些与文化规范相符合的想法。这种对规则和标准化程序的严格遵从会限制即兴发挥和独创性;而与宽松的文化相关的核心结果包括接受多样性、接受不合规行为,并且对改变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些因素能够促进探索和创新。因此,生活在低不确定性规避水平的文化背景中的个体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新颖性;而生活在高不确定规避水平的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则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实用性和适宜性以及更低水平的新颖性(Erez & Nouri, 2010)。
五、文化与创造性过程
创造性过程指有关创造的认知性思维技巧、过程或阶段。从创造性过程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差异就是要考察文化对创造性表现潜在的心理机制的影响。由于现有的创造力测验主要是创造性认知测验,所以从这个角度考察文化与创造力的关系的实验研究较多,尤其是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力的影响,主要关注的是对创造性认知过程的影响。以下将集中从两个创造力过程模型来分析文化的影响。
(一)创造力的双过程通路模型与文化效应
创造力的双过程通路模型(De Dreu,Baas, & Nijstad, 2008; Nijstad, De Dreu, Rietzschel, & Baas, 2010)将创造力分为创造性结果和创造性过程,且创造性结果是认知灵活性和认知持久性两种信息加工策略的产物。认知灵活性有助于发散性思维,它能够打破思维定势(Smith & Blankenship, 1991),运用扁平的联想层级。认知持久性有助于个体在同一个任务上坚持更长时间、产生更多想法,因为创造性想法需要深思熟虑、专注,以及在某些认知类别或视角上进行结构化探索(Nijstad & Stroebe, 2006; Simonton, 1999)。根据创造力的双过程通路模型,任何影响心理激活或工作记忆能力从而影响创造力的特质或状态都是通过影响认知灵活性或认知持久性起作用,且双过程通路至少能够从以下两方面解释创造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De Dreu, 2010)。
第一,文化会影响创造性个体偏好哪一种认知通路。有些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规范鼓励个体从事灵活的、宽松的加工方式,勇于承担风险探索未知,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想法被嘲笑;有些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规范则鼓励个体从事谨慎的、分析式的加工方式,循序渐进,避免过度冒险。西方文化强调个体自由和独立,可能会鼓励个体采用认知灵活性通路;而东方文化强调社会联结和相互依赖,促使个体倾向于认知持久性通路。
第二,双过程通路还能够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总体创造力水平可能并不存在差异,而是达成创造性成果的途径不一样。比如,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能够通过认知持久性达到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通过认知灵活性所能实现的创造力水平。并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创造性表现更偏重于新颖性,而有些人的创造性表现更偏重于实用性。
(二)文化与创造力过程模型
Chiu和Kwan(2010)将创造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提出创造性想法;选择、编辑和推销创造性想法;创造性想法被他人所接受。文化对创造力过程的三个阶段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Chiu & Kwan, 2010)。在提出创造性想法的阶段,文化既有直接的作用也有间接作用。比如,个体所属文化的知识既是个体灵感的重要来源,也为他人评估其想法的新颖性提供了参考标准。其次,所属文化的知识也会为个体提出创造性想法设置障碍,造成个体思维定势与认知盲点。学习外国文化则有助于打破定势,将不同文化下的想法进行创造性整合。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想法产生的影响又表明,文化经验能够间接地影响创造性想法的产生过程。因为个体从多元文化经验中的获益程度还取决于个体的开放程度(Leung & Chiu, 2008)、对其他文化的接纳与适应程度(Maddux, Adam, & Galinksy, 2010)。而在这些心理品质上也存在文化差异,比如,美国人的开放性、成长动机要显著高于中国人,这又会反作用于个体从多元文化经验中的获益程度(Leung & Chiu, 2008; Maddux et al., 2010)。
在选择、编辑和推广阶段,最重要的目标是根据这些想法在市场上成功的概率选择最有可能成功的想法,不断完善和修改提高它的市场价值,提高其在目标受众中的关注度(Chiu & Kwan, 2010)。在这个阶段,知识创造者会根据创造性内隐观的文化一致性评估受众的喜欢程度以及他们的想法的市场价值。对目标群体中流行的文化规范理解越多,越能够促进创造性想法的选择、编辑与推广。文化因素也会影响创造者如何修改他们的想法。比如,Erez和Nouri(2010)就提出一种假设:看重集体主义价值观、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更倾向于就想法的实用性进行详细说明,尤其是有上级或同事压力的工作情境下,或者从事有明确的任务目标的工作时。
在第三个阶段,目标群体的喜好会最终决定这个想法在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当一个创造性想法被接受了,知识创新者可能会开始新一轮的创造性活动。当一个创造性想法被拒绝后,有些知识创新者会终止项目而去开展另一个新的项目,有些知识创新者可能会根据外部反馈修改完善他们的想法。也有一些知识创新者会拒绝外部评价,甚至将他们最初的想法变得更为激进。这些和普通大众相反的创新者的想法一旦最终被接受,最有可能产生革命性的创新。文化的差异就体现在创造性想法被拒绝之后的反应(Chiu & Kwan, 2010)。比如,那些受规避风险动机驱动的个体在面对否定的结果时最有可能选择坚持(Lam & Chiu, 2002)。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具有很强的规避风险的文化中,比如日本,人们更有可能选择坚持、调整,提供渐进性创新,而不是违抗大众意见,提出破坏性变革(Morris & Leung, 2010)。
六、文化与创造性环境
文化作为一种环境因素,既会影响创造性产品、创造性个体和创造性过程,还会影响创造性环境本身。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论,环境是一个鸟巢状的多水平嵌套结构,个体发展发生在多水平环境嵌套影响的复杂关系系统中,包括小环境系统、中环境系统、外环境系统和大环境系统(Bronfenbrenner & Evans, 2000)。文化既可以被看成是直接影响个体创造性发挥的小环境系统,也可以被看作是影响各个环境系统之间关系的大环境系统。前者通过对创造性的界定与评估、创造性个体特征或人格以及创造性过程起作用影响个体层面的创造性水平,后者通过更为宏观层面的时代精神、意识形态、家庭文化和教育体制等因素对群体层面的创造性水平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
时代精神与创造力。Boring(1971)将时代精神定义为“影响思维的舆论”以及“个体所生活的特定文化下的特定时期内可获得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时代精神,有时候时代精神会抑制创造力,有时候会促进创造力。时代精神就好比是人们的思想惯性,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缓慢又坚定。几乎所有创造性突破都产生于既有一些思想自由,又有一些思维惯性,或至少有一些质量监控的地方。以科学研究为例,时代精神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要求原创性的同时,也要确保可靠性,要以确凿的证据和已有知识为基础。如果缺乏这样的基础,一味追求新颖性就属于妄想爱好者,这样的工作尽管独特,但往往没有价值。
Feldman(1994)探索了时代精神在鉴别有才华或天赋异禀的人的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宏观的情境因素如何影响潜能的发展和表达?天才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他们才能的发挥。他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精神中,政治氛围是稳定的还是不安的,战争还是和平,周围是否有不同领域内的行为榜样,哲学、神话、信念系统都是构成这个孩子成长的意识形态氛围。一个杰出的人物出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代精神支持特定形式的才能时,这种才能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发展为现实的成就(Runco, 2014)。
以行为榜样的可获得性为例,根据创造者职业生涯鼎盛期在40岁左右,假定创造者生活在g时代,那么这些创造者在40年以前就一直受到发展的影响。这意味着g-1时代的事件和环境能够影响g时代创造者的数量。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创造性成就产生的特定领域内行为榜样和导师的可获得性。创造性天才都是站在先前时代巨人肩膀之上的。因此历史上的创造性人才都倾向于聚集在某个称为“黄金时代”的特定时期(Simonton et al., 2010)。不论在东方文化还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行为榜样的可获得性与某个时代的创造性成就之间都存在显著正相关(Simonton et al., 2010)。
文化对家庭社会化和学校教育的影响。Ng(2001, 2004)在他的著作《为什么亚洲人的创造性比西方人低》和《释放亚洲学生的创新精神》中特别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他认为,正是文化和社会因素决定了个体的心理结构,个体心理结构又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行为。Ng还进一步阐述了个体的心理结构是由教养理念和实践所决定的,并由此导致了我们所观察到的东方集体主义或儒家文化与西方个体主义或自由文化之间创造性行为的差异(Rudowicz & Ng, 2003)。因为在亚洲文化背景下,社会组织严密,强调集体主义和等级制度,爱面子,过于看重社会秩序与人际和谐。因此,亚洲父母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会强化孩子对群体内成员的依赖性,回避人际冲突。与之相反,西方社会组织较为松散,强调个人主义和人人平等,重视人与人之间自由地交流思想。因此,西方父母对孩子的社会化过程更为强调个人独立性,对人际冲突的看法也很乐观。
此外,Ng(2001)还特别指出儒学的多种特征组合如何通过学校教育抑制学生发散性思维,使得他们难以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儒家文化传统强调教育是获取正确的知识,课本是知识的权威来源,教师是必须要得到尊重的知识库,此外,集体主义价值观还强调群体利益,避免冲突,遵守社会规范,以及基于社会认知和荣耀家族的竞争性学习升级体制。与之相似的是,Kim(2007)也总结了儒学的四个教育原则会抑制创造力:强调机械学习;家庭结构中的服从;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仁爱所要求的自我抑制、情绪控制和谦逊。
创造力跨文化比较的历史测量学视角。历史测量学研究运用传记和史料作为原始材料,通过数学或统计分析来检验具体假设,特别适用于研究创造性发明(Simonton, 2009)。Simonton和他的同事(1984, 1990, 2003)多次从历史角度研究文化与创造性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对一种文化或几种文化长期的观察,对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变量对创造力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Simonton和Ting综合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历史测量学研究,在2010年发表了《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创造力:历史测量学的启示》,检验了哪些因素影响了东西方文化下产生的创造性成果,差别和相似之处分别是什么?结果如表1。
从总体水平来分析,在东西文化下,都表现为行为榜样的可获得性与创造性成就存在正相关,政治不稳定与创造性成就存在负相关。但政局分裂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能够促进创造性成果,而在东方文化下不存在一致性的影响。内乱和意识形态(详见下)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都表现为与创造性成就的正相关,而内乱在中国与创造性成就不存在显著关系,但日本的意识形态与创造性成就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从个体水平的分析结果看来,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早熟、个人作品的产量、多才多艺和寿命都与创造性成就显著正相关,但年龄与创造性成就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关系。而西方的正规教育与创造性成就也呈倒U型关系,即接受中等程度的正规教育最有利于创造发明,中国的正规教育与创造性成就之间显著正相关。西方文化下创造性成就与精神疾病存在正相关,但这种情况在中国较为少见。
表1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创造力历史测量学研究的主要发现(Simonton & Ting, 2010)
注:+正相关;-负相关;0无相关
以意识形态影响创造力的跨文化比较为例,主流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心理”会影响某种文化下的创造力数量和属性。比如,被Sorokin(1937, 1941)称为“感觉智力”的特征(物质主义、实证主义、决定论、个人主义、快乐伦理等等)与科学创造力呈现正相关。然而,被他称为“观念智力”(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自由意志论、集体主义、原则性伦理等等)与人文和宗教领域的创造力呈正相关(Simonton et al., 2010)。不幸的是,Sorokin的数据只是来源于西方历史文明。但在日本文化中存在一些试验性的证据(Simonton, 1992)。例如,儒教对文学创造力有负面的影响,尤其对女性作家。但儒家哲学体系应该属于“观念智力”的范畴,与Sorokin自己的假设相互矛盾。
而儒教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造性成就的影响与日本相似。在汉代,汉武帝提出儒家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尽管还有大家所熟知的道教和从印度引进的佛教存在于私人选择领域。但统治阶层提出所有有志之士都必须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以谋取政治职务。即便在中国人经历暂时的政局分裂时,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依然是高度稳定的。这也能够反向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家的黄金时代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创新活动与文化异质性呈正相关,多样化是群体层面的创造性发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Nemeth & Kwan, 1985, 1987; Simonton, 2004)。
七、总结与展望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深层心理结构,理解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非常重要。文化既会影响创造性的界定和产生过程,也会影响创造力的表现以及所属领域。本文以4P模型为框架,综述了文化影响创造力的不同方式。首先,文化会影响创造性产品的评估标准及表现领域。其次,文化会影响对创造性个体特征或人格的内隐认识,也会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创造性人格。第三,文化还会影响创造力产生的心理过程或形成阶段。第四,文化还会通过时代精神、意识形态、家庭教育等因素影响创造性表现。未来研究可以从这四个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化与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与此同时,在进行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文化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所有文化都蕴含有促进创造力的因素以及抑制创造力的因素,任何根据不同文化下创造性成就的多少进行排序的方法都是不公平的(Runco, 2014)。今后的研究可以多关注造成创造力表现的文化差异的内在机制。比如,能否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东西方文化总体创造力水平是否有本质差异?如果没有,是否如双过程通路模型所假定的那样,只是实现创造性的认知通路存在差异,即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是否更擅长于通过认知持久性做出创造性成就,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被试是否更擅长于通过认知灵活性做出创造性成就。如果有差异,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通过文化交流与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第二,在探讨文化与创造性个体或人格的关系时,要避免研究结论的过度推广,比如,将文化价值观等同于所属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价值观,这种忽略个体差异的思路通常是不合适的。因为文化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代表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所有个体,即便文化中的某个方面代表了某个特定个体的特征,但也不意味着这个人一定会以文化规范所预期的方式做出反应(Runco, 2014)。
第三,文化对创造性过程的影响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认知灵活性和认知持久性在创造性产生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还是有差异的?不同文化在创造力产生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否有显著差异?以往研究比较集中于探讨文化对创造性想法提出以及选择、编辑和推广的影响,关于文化如何影响创造性想法被接纳方面的研究还非常之少。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创造力的历史测量学研究范式在这个研究主题上的运用。
第四,文化对创造性环境的影响可以考虑结合创造力的教育视角或组织视角进行实证研究,从文化影响家庭社会化、学校教育或组织氛围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不同文化所营造的创造性环境方面的差异。就中国文化特色而言,我们尤为重视环境的影响,并尝试通过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激发社会各个层面的创造性潜能,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保障。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营造创造性环境的最终效果是否会因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而有所不同,也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做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Amabile, T.M., & Amabile, T.M.(1983).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45(2), 357-376.
Amabile, T.M., Schatzel, E.A., Moneta, G. B., & Kramer, S.J.(2004). Leader behaviors and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 perceived leader support.LeadershipQuarterly,15(1), 5-32.
Angela K.-Y.Leung, & Chi-Yue Chiu.(2008).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on creative potential.CreativityResearchJournal,20(20), 376-382.
Batey, M., & Furnham, A.(2006). Creativity,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cattered literature.Genetic,Social,andGeneralPsychologyMonographs, 132(4), 355-429.
Brewer, M.B., & Chen, Y.R.(2007). Where(who) are collectives in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PsychologicalReview,114(1), 133-51.
Bronfenbrenner, U., & Evans, G. W.(2000).Developmental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emerging questions, theoretical models, research desig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ReviewofSocialDevelopment, 9(1),115-125.
Chan, D.W., & Chan, L. K.(1999). Implicit theories of creativity: teachers’ perception of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in Hong Kong.CreativityResearchJournal,12(3), 185-195.
Chiu, C.& Kwan, L. Y.(2010). Culture and creativity: a process model.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6(3), 447-461.
Dollinger, S.J., Burke, P.A., & Gump, N.W.(2007). Creativity and values.CreativityResearchJournal,19(2), 91-103.
Dreu, C.K. W.D., Baas, M., & B.A.Nijstad.(2008). Hedonic tone and activation in the mood-creativity link: towards a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Dreu, C.K.(2010). Human creativity: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culture.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 6(3): 437-446.
Erez, M., & Earley, P.C.(1993). Culture, self-identity, and work.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40(3).
Erez, M., & Nouri, R.(2010). Creativity: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social, and work contexts.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 6(3): 351-370
Feldman, H.D.(1994).BeyondUniversalsinCognitiveDevelopment(2nd Ed.). Norwood, NJ: Albex.
Florida, R.(2005).TheRiseoftheCreativeClas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Gelfand, M.J., Nishii, L. H., & Raver, J.L.(2006). O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91(6), 1225-1244.
Hempel, P.S., & Sue-Chan, C.(2010). Culture and the assessment of creativity.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6(3), 415-435.
Hofstede, G.(2001).Culture’sConsequences:Comparing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andOrganizationsacrossN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Kaufman, J.C., & Sternberg, R.J.(2006).TheInternationalHandbookofCreativ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sof, J., Chen, C., Himsel, A., & Greenberger, E.(2007). Values as creativity.CreativityResearchJournal,19(2-3), 105-122.
Kim, K. H.(2007).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sian culture and creativity.JournalofCreativeBehavior, 41(1), 28-53.
Kozbelt, B.A., Beghetto, R.A., & Runco, M.A.(2010). Theories of creativity. In J.C.Kaufman, & R.J.Sternberg(Eds.),TheCambridgeHandbookofCreativity:20-4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m, W.H., & Chiu, C.Y.(2002). The motivational function of regulatory focus in creativity.JournalofCreativeBehavior,36(2), 138-150.
Leung, A.K. Y., Maddux, W.W.,Galinsky, A.D., & Chiu, C.Y.(2008).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enhances creativity: The when and how.AmericanPsychologist, 63(3): 169-181.
Leung, K., Au, A., & Leung, B.W.C.(2004).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East-West comparisons with an emphasis on Chinese societies. In S.Lau, A.N.N.Hui & G. Y.C.Ng(Eds.),Creativity:WhenEastMeetsWest: 113-135.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Lubart, T.(2010).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Creativity. In J.C.Kaufman, & R.J.Sternberg.(Eds.),TheCambridgeHandbookofCreativity:265-27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ddux, W.W., &Galinsky, A.D.(2009). Cultural borders and mental barri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ing abroad and creativity.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96(5), 1047-1061.
Maddux, W.W., Adam, H., &Galinsky, A.D.(2010). When in Rome learn why the romans do what they do: how multicultural learning experiences facilitate creativity.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36(6), 731-41.
Maddux, W.W., Leung, A.K., Chiu, C.Y., &Galinsky, A.D.(2009). Toward a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nk between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and creativity.AmericanPsychologist,64(2), 156-168.
Martindale, C.(1999). Darwinian, Lamarckian, and rational creativity.PsychologicalInquiry,10(4), 340-341.
Mok, A., & Morris, M.W.(2010). An upside to bicultural identity conflict: resisting groupthink in cultural ingroups.Journalof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46(2), 1114-1117.
Morris, M.W., & Kwok, L.(2010). Creativity east and west: perspectives and parallels.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6(3), 313-327.
Morrison, E.W., & Milliken, F.J.(2003). Speaking up, remaining silent: the dynamics of voice and silence in organizations.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40(6), 1353-1358.
Nemeth, C.J., & Kwan, J.L.(1985). Originality of work associations as a function of majority vs. minority influence.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48(3), 277-282.
Nemeth, C.J., & Kwan, J.L.(1987). Minority influence, divergent thinking and detection of correct solutions.JournalofAppliedSocialPsychology,17(9), 788-799.
Ng, A.K.(2001).WhyAsiansareLessCreativethanWesterners? Singapore: Prentice-Hall.
Ng, A.K.(2004).LiberatingtheCreativeSpiritinAsianStudents. Singapore: Prentice-Hall.
Nijstad, B.A., & Stroebe, W.(2006). How the group affects the mind: a cognitive model of idea generation in groups.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Review,10(3), 186-213.
Nijstad, B.A., De Dreu, C.K. W., Rietzschel, E.F., & Baas, M.(2010). The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 creative ideation as a function of flexibility and persistence.EuropeanReviewofSocialPsychology,21(1), 34-77.
Niu, W., & Sternberg, R.(2002).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the east and the west.JournalofCreativeBehavior,36(4), 269-288.
Niu, W., & Sternberg, R.J.(2001). Cultural influences on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its evalua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logy,36(4), 225-241.
Rank, J., Pace, V.L., &Frese, M.(2004). Three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initiative.AppliedPsychology, 53(4), 518-528.
Rhodes, M.(1961). An analysis of creativity.PhiDeltaKappa,42(7), 305-310.
Rudowicz, E.(2003). Creativity and culture: a two way interaction.ScandinavianJournalofEducationalResearch,47(3), 273-290.
Rudowicz, E., & Ng, T.T.S.(2003). On Ng’s why Asians are less creative than westerners.CreativityResearchJournal,15(2), 301-302.
Rudowicz, E., & Yue, X.D.(2000). Concepts of creativit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Chinese.JournalofCreativeBehavior,34(3), 175-192.
Runco, M.A.(2014).CreativityTheoriesandThemes:ResearchDevelopment,andPractice,(2th).CA: Academic Press.
Shane, S.,Venkataraman, S., & Macmillan, I.(1995).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innovation championing strategies.JournalofManagement, 21(5), 931-952.
Simonton, D.K.(1975).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individual creativity: a transhistorical time-series analysi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32(6), 1119-1133.
Simonton, D.K.(1988). Age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what do we know after a century of research?PsychologicalBulletin,104(2), 251-267.
Simonton, D.K.(1992). Gender and genius in Japan: feminine eminence in masculine culture.SexRoles,27(3-4), 101-119.
Simonton, D.K.(1999). The continued evolution of creative Darwinism.PsychologicalInquiry,10(4), 362-367.
Simonton, D.K.(2003).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historical data.AnnualReviewofPsychology,54(1), 617-640.
Simonton, D.K.(2004). Group artistic creativity: creative clusters and cinematic success in feature films.JournalofAppliedSocialPsychology,34(34), 1494-1520.
Simonton, D.K., & Ting, S.S.(2010). Creativity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 lessons of historiometry.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6(3), 329-350.
Smith, S.M., & Blankenship, S.E.(1991). Incub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fixation in problem solving.AmericanJournalofPsychology,104(1), 61-87.
Sorokin, P.A.(1937). Improvement of scholarship in the social.EducationDigest.
Sorokin, P.A.(1941). Tragic dualism, chaotic syncretism, quantitative colossalism, and diminishing creativeness of the contemporary sensate culture.AmericanCatholicSociologicalReview,2(1), 3-22.
Sternberg, R.J., &Lubart, T.I.(1996). Investing in creativity.AmericanPsychologist,51(3), 677-688.
Sternberg, R.J., &Lubart, T.I.(1997). Creativity as investment.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 40(1), 8-21.
Ward, T.B., Patterson, M.J.,Sifonis, C.M., Dodds, R.A., & Saunders, K. N.(2002). The role of graded category structure in imaginative thought.MemoryandCognition,30(2), 199-216.
Williams, L. K., &Mcguire, S.J.(2010). Economic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drivers of growth? Evidence from 63 countries.SmallBusinessEconomics,34(4), 391-412.
(责任编辑侯珂责任校对侯珂孟大虎)
Culture and Creativity: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4P-creativity Model
ZHANG Wen-juan1, CHANG Bao-rui1,2, ZHONG Nian1, ZHANG Chun-mei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2;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review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creativity under the 4P-creativity Model. First of all, culture will affect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creative products and performance. Second, culture can influence both the implicit theori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person; it can also affect the creative personality through socialization process. Third, 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the creativity varies on the different stages or different cognitive process. Finally, culture can promote or inhibit creative performance through creative climate such as Zeitgeist, ideology, or family and school environment. Future studies should provide more and more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four aspects respectively to explain deeply about cross-cul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creativity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Key words:culture; creative products; creative person; creative process; creative places or press
[收稿日期]2015-06-1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当代文化心理学研究”
[通讯作者]常保瑞,E-mail:whdx30042@whu.edu.cn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2-00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