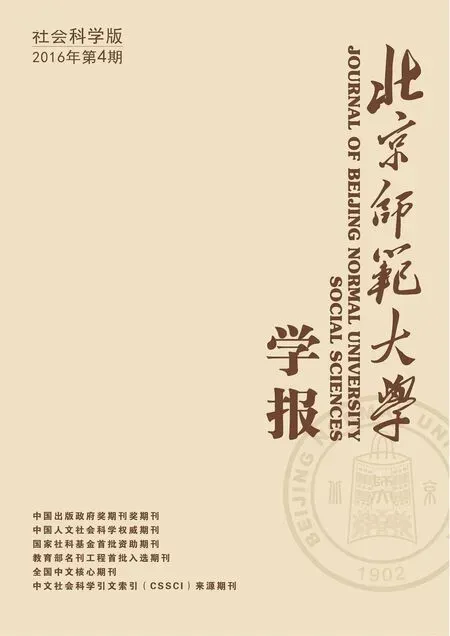麦都思神学思想初探
刘林海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麦都思神学思想初探
刘林海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对于基督教经典中的最高存在者究竟应该用哪个/哪些汉语词加以翻译?这是比较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大问题。19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曾有过长期的争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不同意以马礼逊圣经译本为代表的用汉语的“神”来翻译God的做法,他从比较角度对汉语中的“上帝”和“神”进行分析,并用它们作为Elohim和Ruach的译名。他不但认为“上帝”和“神”在本质上与希腊罗马的theos和Pneuma一致,而且认为中国宗教具有自然神学的特征,与希腊罗马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麦都思关于“上帝”和“神”的观点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当时中西宗教和思想传统相互碰撞、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认识中国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意义。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阐释基督教神学的探索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西方解读中国宗教乃至文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也为中国人认识基督教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关键词]麦都思;神学思想;上帝;神;自然神学;宋明理学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西方传教士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但传播基督教(除非注明,本文的基督教特指新教——作者),而且活跃在文教等领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西方学术界之后,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关系。相关研究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甚至形成了持续的热潮。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传教士的教育文化活动、东西文化交流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方面。相比之下,他们在宗教神学方面的言行,则很少有人关注,尽管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们在神学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则几乎没有专论。
近代来华传教士大都习得汉语。随着对中国语言文化了解的加深,不少人还针对一些宗教问题进行研究,留下了若干神学论著。与一般西方神学家的作品有所不同,来华传教士的神学论著大多结合中国传统的文献材料,对基督教的神学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引起普遍关注并展开持续讨论的是《圣经》汉译中的几个关键术语,也就是Elohim(Theos)、Ruach(Pneuma)的译名问题。译名问题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圣经汉译问题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其基本历史及一般特点也有诸多的研究。除历史线索的梳理外,学术界还从文化传播、翻译学、政治学、殖民理论等角度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解读,从而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虽然传教士的相关论著是这些研究的基本材料,但是,对于这些论著讨论的神学问题本身,似乎没有引起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来华传教士的主要任务是传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过一定的神学教育,了解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客观说来,他们的神学修养未必是一流的,也并无系统的神学著作,无法与专门的神学家相比。从这个角度来看,其论著对西方基督教神学的价值有限,应该不算太过分的评价。不过,如果考虑到产生的具体环境、蕴含的中国文化元素以及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这些论著则有着相当的价值,值得研究。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学术界曾发起过关于中国基督教神学建设问题的讨论,很多学者从哲学、神学、文学等角度发表了高论,但从史学角度的研究较少。此外,这些研究多从20世纪入手,对于19世纪的情况涉及较少。笔者以为,要讨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这个时期也是不能忽视的。虽然传教士并非中国人,这些著作也大多是用外文(主要是英文)写成的,但并不能因此把他们排除在外。一方面,其著述是以中国文化为重要语境的,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的教师和翻译助手)*传教士翻译圣经的一般模式是与中国助手或汉语老师合作,前者将基本意思复述出来,后者协助形成文字,经修改润色定稿。因此,在圣经翻译中,中国人的作用不容忽视。参见:Jost Oliver Zetzsche,The Missionary and the Chinese “Helper”:A Re-appraisal of the Chinese Role in the Case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传教士与华人助理——中文圣经翻译中华人的角色再评价》),《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浸会大学),第3期(2000),5-20页;游斌:《被遗忘的译者:中国士人与中文〈圣经翻译〉》,《道风》27(2007)(《金陵神学志》,2007年第4期)。一些中国学者也对传教士争论的话题发表了看法。参见刘林海:《19世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God/Spirit汉译问题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另一方面,他们用中国文化元素诠释基督教教义,这些认识对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有重要影响。可以说,这些论著是近代以来中国新教神学发生发展的基础,值得研究。
本文拟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为例,对他的神学研究进行初步梳理和分析。希望通过个案研究,窥一斑而见全豹,以期对认识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历程有所帮助。之所以选择他作为研究对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麦都思是近代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著名代表之一,其活动涉及传教、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此外,他勤于著述,有不少著作传世,其神学论著尤其值得关注。与马礼逊相比,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不够。第二,从对他的研究现状来说,现有成果基本在新闻出版、教育、圣经翻译等方面,神学研究则很少*国内学术界关于麦都思在文教及圣经翻译等方面的专论主要有:邹振环:《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美〕韩南、段怀清:《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刘壹立:《麦都思与圣经〈新遗诏书〉译本》,《东岳论丛》,2012年第10期。另有几篇关于麦都思的学位论文,部分关于圣经译名翻译等论著也涉及麦都思,本文不再罗列。。在很大程度上,麦都思研究的现状反映了当下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教士研究的一般特点。
二、麦都思及其主要神学论著
关于麦都思的生平和著述情况,目前学术界依靠的基本资料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857年麦都思去世后伟烈亚力在《六合丛谈》上用中文发表的《麦都思行略》,另一篇是用英文写成的,收录在他于1867年出版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中*〔英〕伟烈亚力:《麦都思行略》,沈国伟编著:《六合丛谈》,第1卷第4号(576-58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Shanghae,1867,pp.25-41.。伟氏的这两篇麦都思传比较简短,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对其活动的叙述,对其早期论著产生的背景有较多介绍,后者则按年代顺序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其论著目录*其中文著作多由他本人创办的墨海书馆出版,其论著见熊月之编《墨海书馆出版书目一览(1844—1860)》,载沈国伟编著:《六合丛谈》,第242-247页。伟烈亚力的传教士传记中有关于他的比较详细的论著目录,尤其是英文著作。据笔者所见,伟氏的目录似不全。。麦都思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一书的第12章至20章,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他在中国的初期活动,是了解其在华活动的一手材料*Walter Henry Medhurst,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containing allusions to the antiquity,extent,population,civilization,literature,and religion of the Chinese,London,1838,pp.306-521.。托马斯·W·M·马绍尔(Thomas William M.Marshall)的《基督教在中国》一书中也对他的活动有所涉及*Thomas William M.Marshall,Christianity in China,A Fragment,Longman,London,1858,pp.68-80.麦都思去世后,慕维廉为他做了专题纪念布道。Rev W.Muirhead,The Parting Charge.A Sermon preache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death of the Rev.W.H.Medhurst,D.D,Shanghae,1857.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也撰文述其行状,以示纪念。W.C.M.,Memoir of the Late Rev.Dr.Medhurst,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and Missionary Chronicle,Sept.,1857 (vol.35),pp.524-529.。
麦都思于1796年4月29日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旅店主家庭,早年受教于伦敦圣保罗公学,14岁时成为一名印刷学徒工。不久,他对宗教及传教产生了兴趣,加入了一个独立派公理会教会。1816年9月,他受聘伦敦差会,前往麻剌甲(马六甲)传教站从事印刷出版工作。在出发前,他到海克尼学院(Hackney College)接受了短期神学教育培训。海克尼学院是由独立派公理会成员乔治·克林森(George Collison)等于1803年创立的非教派神学院,以培养海外传教人员为主要目的。麦都思于1817年2月抵达印度,在此与伊丽莎白· 马丁结婚,并于6月12日抵达马六甲,在差会开办的印刷所给米怜当助手。
麦都思虽然是作为印刷工被派往马六甲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名印书匠。在本职工作之余,他开始学习汉语、马来语等语言和方言,“习华言,效无语,罔间朝夕,欲明究其故”*〔英〕伟烈亚力:《六合丛谈》第1卷第4号(576页)。这里的“无语”是他对“无来由之地”语言的简称。伟烈亚力在麦都思行传中提到麻剌甲“地属无来由”,麦都思“以华无二地之文撰书”,其著作中有一些马来文的。综合判断,“无来由”应是“马来亚”的音译。。其好学深思的精神深受米怜的赞扬*米怜盛赞他孺子可教、虚心好学、热情坚定、进步快,并十分肯定地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是一位非常有用的副主教。William Milne,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s to China,The Anglo-Chinese Press,Malacca,1820,p.195.。麦都思有良好的语言天赋,除汉语和马来语外,还学习了日语等,懂福建方言和一些马来方言。他先后编过《华英字汇》、《日英字汇》、《闽音字汇》,将荷兰文的《虎尾垄语词典》(台湾方言)和汉语的《朝鲜伟国字汇》(明洪舜明著《倭语类解》)译成英文。此外,他还到处散书布道,办报纸,开学校,做慈善,足迹遍布马来半岛、巴达维亚(雅加达)、新加坡、槟榔、巴厘岛、爪哇等地。1819年4月27日,他在马六甲被按立为牧师。1835年7月,他曾访问广州的教会。同年8月,他与美部会传教士士底芬(Edwin Stevens)一起从粤东沿东南沿海游历传教,先后到达山东、靖海*《麦都思行传》中记从粤东“至山东、靖海等处。继至上海,分书传教。道从浙之舟山普陀而抵粤东,继回爪哇岛”。英文的传记中只提到他们到了山东半岛北部的尽头(north side of the Shantung Promontory)几个地方,然后返回上海。此处靖海指当时清政府设置的靖海巡检司,隶属文登。据士蒂芬的游记,他们搭乘美国呼伦(Huron)号双桅船,到了威海、刘公岛、克山湾(keshan bay)、宁海州(Ninghae Chow)等地。Chinese Repository,IV,Nov.,pp.308 ff.、上海等地,经舟山、普陀返回。1836年4月初回到巴达维亚后,随即启程返回英国,经阿姆斯特丹,于8月5日回到伦敦,结束了他第一阶段的传教生涯。回到英国后,他完成了《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一书,于1838年出版。
1838年7月31日,他再次启程,于11月5日回到巴达维亚,继续他在南洋的传教事业。鸦片战争结束后,他于1843年8月抵达香港,参加来华传教士联合举办的圣经翻译会议。同年12月中旬到了上海,全力投入圣经的翻译工作。此后,除偶尔外出外,他常住上海,直到1856年10月9日返回英国。在上海居住期间,他译书著文,办报刻书(墨海书馆),布道传教,活动范围主要在江苏、浙江和安徽。
麦都思好学深思,勤于笔耕,在传教和学习语言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撰写了近百种论著,涉及历史、神学、地理、语言文字等。从神学角度来说,他围绕圣经翻译撰写的一系列论著尤其值得关注。
1822年和1823年,马希曼和拉沙以及马礼逊和米怜翻译的圣经中译本先后问世。这两个译本受到好评,但也不乏批判者,尤其是懂汉语的传教士。随着来华传教士汉语水平的提高及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加深,中译本圣经的不足之处越发明显。就连马礼逊也对自己的译本不满意,一直在设法进行修订。到1830年代中期,虽然传教士们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并没有一致意见,但马礼逊的圣经需要修订已成为共识,并付诸实践,麦都思则是最活跃的一位。他认为,马礼逊的成绩不容否定,但现有的圣经离中国文化太远,无论在句式表达还是术语的选择上,都没有考虑中国的现状和习惯,致使中国人不容易理解和接受,不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为了修订圣经,他曾致信马礼逊。后来,他与郭实腊、马儒翰和裨治文联合修订马礼逊翻译的《新约》。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经过多次修改,该修订本在1835年公开发行*Walter Henry Medhurst,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Bible(Oct.28,1836),London,1836,pp.6-7; ,p.13-14.(注:本文引用的新译本批准争论的信件均收录在耶鲁大学馆藏的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中) 麦都思在返回英国前,已经开始新本的印刷工作。按照他的计划,分别在新加坡、塞兰坡、巴达维亚三个地方开印。但是,这个译本遭到戴尔和伊云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麦都思的翻译已经超出了圣经公会的基本原则,圣经公会不但要否决它,而且应下令收回已流通的印本。。《新约》译毕,他又与郭实腊合作翻译《旧约》。为了继续翻译工作,他在回国游说英国圣经公会采纳其新译本的同时,还带上了华人助手朱德郎,始终没有中断翻译。1836年10月28日,他向英国圣经公会提交专题报告,直陈马礼逊译本的不足,提出“传教士、当地基督徒以及异教徒共同的心声是迫切需要一个新的、习语化的译本”*Walter Henry Medhurst,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Bible,p.6.,力主使用新译本。圣经公会参考了同在南洋传教的戴尔(Samuel Dyer)、伊云士(John Evans)以及已回到英国的基德(Samuel Kidd)的建议,经过讨论,在1836年12月5日正式否决了他的建议,决定继续使用马礼逊译本,收回已经流通的新译本。尽管如此,麦都思仍坚持完成了《旧约》的翻译工作,并在1838年出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华各差会就翻译新版圣经达成一致,成立翻译小组,其成果就是广为人知的委办译本*Patrick Hanan,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Medhurst,Wangtao,and the Delegates’Vers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3:1(Jun.,2003),pp.197-239.此文中译文见:〔美〕韩南、段怀清:《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翻译工作开始不久,代表们就在翻译的风格、关键术语的译名选择等方面产生了分歧,形成分别以麦都思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为代表的两派。双方的分歧在《旧约》的翻译过程中进一步加深。麦都思为代表的一派基本以英国传教士为主,主张将圣经里的“elohim”(theos)译为“上帝”,而将Ruach(Pneuma)译为“神”或“圣神”。以文惠廉为代表的一派基本以美国传教士为主,主张将elohim译为“神”,而将Ruach译为“灵”。两派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自列举理由,以说服对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对方的观点错误,他们都不断加强对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挖掘有利资源,阐述其蕴含的神学意义。译名之争不但引发了在华传教士的广泛关注和参与,而且波及到欧美知识界,成为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神学家译名之争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因对西方和中国文化尤其是一些术语理解不同造成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传教策略的因素,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的分析,无需赘言。本文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产品及对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意义。
随着分歧的出现,麦都思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典籍中与各派提出的译名有关的术语。1847年,他完成了《论中国神学》一文,首次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译名问题的看法。这部著作应该是来华新教传教士撰写的第一部用中国文化与典籍阐述基督教神学问题的专论。1848年,他又完成了《圣经中God一词的恰当汉译方式探析》。1849年,他发表《“神”的真义——以〈佩文韵府〉所收词为例》。1850年,出版《圣经中Ruach、Pneuma 的恰当汉译方式探析》。他还在1852年撰写长文,以回应文惠廉对《以弗所书》翻译的质疑与批判。在这几年的论战中,他还有多种相对短小的文章发表。1851年3月,麦都思等退出翻译委员会。随着各自选择译名、双方《旧约》译本的完成和先后出版,争论逐渐平息。
麦都思重要的神学论著虽然集中出现在1840年代至1850年代初,但绝非仓促成文,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应该说是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长期学习和思考的结晶。他到南洋后不久,就开始学习汉语,阅读中国传统经典。此外,他还从旅居南洋的福建和广东商人那里接触到中国的一些传统习俗,如上帝、妈祖、祖先崇拜等。在他看来,这些均属偶像崇拜性质的迷信。为此,他撰写了《清明扫墓之论》、《普度施食之论》、《妈祖婆生日之论》、《踏火之事论》、《上帝生日之论》等文章。他批判中国人对玄天上帝的崇拜“彻头彻尾都像异端,近于邪术,不合真理,不照圣道”*尚德:《上帝生日之论》,新嘉坡书院。。《神天十条圣诫注解》、《耶稣赎罪之论》、《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神理总论》、《福音调和》等也是他在华第一阶段的论著或译著,从正面介绍宣传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些都为后来的集中论述奠定了基础。在重返中国后,尤其是移居上海后,他还翻译了蔡沈的《尚书集注》(1846),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成果表示赞扬的同时,还从传教士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文化有所缺憾,“那就是缺乏宗教”*W.H.Medhurst translated,Ancient China,The Shoo King,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Illustrated by Later Commentators,Shanghae: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46,viii.。他还用中文出版了许多宗教和神学著作,除了各种圣经翻译、注释外,重要的还有《圣教要理》(1844)、《真理通道》(1846)、《天帝宗旨论》(1848)等。其中《真理通道》是他的布道集汇编,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关于上帝(God)、基督、圣灵(Holy Spirit)的基本知识,并对《神天十条圣诫注释》进行扩充,讨论道德律问题。《天帝宗旨论》则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盛世芻荛》的修订,讨论上帝及其属性*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pp.29-36.。
麦都思对“神”和“上帝”内涵的关注基本伴随着他的圣经翻译工作。从其相关著述可以看出,在关键术语的选择上,麦都思最初基本沿用了马礼逊的译法,总体上用“神”翻译God,也用“神天”和“神主”,并不十分固定,也没有专论。“上帝”一词也出现过。大约在修订马礼逊译本的过程中,麦都思开始对God的翻译进行思考并形成成熟的看法,这可以从他在1836年写给英国圣经公会的备忘录中看出。他在信中明确表示,马礼逊的译法有问题,与中国人的习惯相左,应该用“上帝”翻译God,而用“圣神”翻译Spirit(马礼逊译为圣神风)*Walter Henry Medhurst,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 Foreign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Chinese Bible,pp.10-11.。虽然他和郭实腊主导的新译本没有得到英国圣经公会的认可,但仍然出版流通,从而开创了“上帝”译本的先河。1843年的香港会议上,为了确定译名,还成立了由麦都思和李雅各(James Legge)组成的专题委员会。由于麦都思坚持用“上帝”而李雅各坚决主张用“神”,最终并未达成一致*李雅各最初认为上帝是一个类似宙斯的偶像神,所以坚决反对。1848年他重回中国,加入译名讨论,几个月后态度彻底转变,由“神”派转为“上帝”派。李雅各在介绍自己转变过程时曾说,文惠廉和其他人“是从上帝出发,最终走到了神;我是从神开始,最终走到了上帝”。虽然如此,他的理由还是与麦都思的有所不同,他认为God并非是一个类称,而是相对的(relative)术语。James Legge,An Argument for 上帝(shang te) as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in the Chinese Languages:With Strictures on the Eassy of Bishop Boone in Favour of the Term神(shin),Hongkong,1850.他在同年还有6封写给麦都思的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On the Rendering of the Name God into Chinese Language,Hongkong,1850)。其对儒教与基督教关系的看法见:James Legge,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Shanghai,1877。。在后来的委办本翻译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最终演变为与“神派”的论战,导致麦都思等退出翻译委员会。麦都思虽然认为“上帝”是最合适的译名,但为了缓和矛盾,也曾先后提出用“天帝”和“阿罗诃”的译法,以求与“神派”达成一致。正是在矛盾分歧的过程中,麦都思先后发表了几种神学专论,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
三、上帝与神
整体而言,麦都思的神学论述较多,涉及范围也很广,尤其是其中文论述或译著,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有较为全面的介绍。不过,这些内容均系基础性的神学要义,并非个人独创,本文不再涉及。真正有创造性的是他围绕着 Elohim(Theos)和Ruach(Pneuma)译名争论撰写的英文论著。
麦都思认为,要准确地将圣经译成中文,最理想的是精通圣经原文又有专业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次才是精通汉语又有专业知识的外国人。中文圣经的翻译首先要考虑中国人的语言及阅读习惯。作为翻译主体的传教士,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要找出合适恰当的译名,首先要对相关术语的内涵进行分析。
麦都思认为,根据克纳普(Georg Christian Knapp,1753—1825)、《卡莫特圣经词典》、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世纪爱丁堡著名希伯来学者)、史密斯(Pye Smith,1774—1851)等的解释,《旧约》希伯来文中的Elohim*Elohim源于闪族语eloah,而后者可能又源于el(Il)。一般认为,elohim是eloah的阴性复数形式。不过,Elohim一词既可以作单数(与单数动词和单数形容词连用),也可以表复数(与复数动词和复数形容词连用)。其本义为deity和power,el则是上古利凡特地区宗教里面的创造神和主神,既可以作专名,又可以作类称,在七十士本中用希腊文theos来翻译。Theos可能起源于原始印欧语,本义可能是“跑”或“看”,是希腊人对崇拜对象的统称,在古拉丁文圣经译本中用拉丁文deus来翻译。Deus一词源于印欧语的“天”(sky,梵文deva),也可能是原始印欧语人的主神。英文god一词可能源于原始印欧语,在原始日耳曼语里为gudán,本意为“泼洒”或者“呼唤”,可能指日耳曼人的祭神活动。4世纪乌尔菲拉在将圣经译成哥特语时将它作为theos的译名,做guda或gup,是后世god译名的开端。在基督教语境中,God作为专名,区别于god。(单数为eloah)的词根是阿拉伯语alah,本意为崇拜和敬拜的意思,引申为崇拜对象。这种崇拜不但及于Deity,而且及于其在人间的代表——国王、官吏、法官等。而alah的词根意为“发誓、宣誓”,享有公权的人就职时要发誓公正行使权力。整体而言,该词的特点在于强调权力(power)和权威,在《旧约》里面既被用来指次于Deity的deity,也用来指代有权威和权力的人物如摩西等,尤其是士师们,还用来作为God审判和公义的代名词。因为God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最高的权威,具有无上的权能,是士师中的士师,故也用来指代他。
根据牛津1845年版的《希英字典》、《新约》文献学家布龙菲尔德(Samuel Thomas Bloomfield,1790—1869)、施劳斯纳(Johann Friedrich Schleusner,1759—1831)的《〈新约〉希腊拉丁新字典》等相关内容,麦都思认为,theos在希腊文化语境中既可以用来指代一般的god,也可以用来指Supreme God,还被用来指国王等有权威的人。这些义项和用法见于从荷马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作者作品。在《新约》里面则既用来指代耶和华、基督、逻各斯,也用来指其他各种god,还用来指代受God之命行使权力的官吏等。拉丁文中的deus用法基本与希腊文中的theos相同。此外,这二者共同的特点是与“权威”和“权力”密切相关。它之所以被用来指代最高的神,就是由于神的观念中所蕴含的权威*Walter Henry 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The Mission Press,Shanghae,1850,pp.1-4.。结合elohim,可以看出,权威和权力应该是最主要的特征,对于认识中国神学至关重要。
虽然中国语言和宗教中确实没有能与God完全对应的词和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可以用来翻译的术语。在麦都思看来,这个术语就是“帝”或者“上帝”(supreme ruler)。其一,上帝一词的本义与elohim和theos相似。按照说文的解释,“帝,諦也”,“諦,審也”。“審,篆文宷”。“宷,悉也。知宷諦也”。解释为“審諦如帝。王天下之號”。麦都思认为,“帝”的本意为“审”,与审判有关,强调的是缜密详备、公正无私,是一种权力或权威的体现,用来指信仰的最高对象。“帝”是中国人对天上主宰者的称呼,也是信仰和崇拜的最高对象。他是万物产生与形成的动因、自然的主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帝、上帝与天是同义词。在中国人看来,帝即是天,天即是帝。用天代指耶和华,也是开封犹太人的习惯*Walter Henry 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pp.20-22.。其二,其在汉语文献和中国信仰中的用法与elohim、theos相同。针对有观点认为上帝是一个专称(Proper name),类似于希腊罗马诸神中的宙斯或朱庇特的说法,麦都思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似性,因为在中国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系谱和历史的信息。上帝是名号,帝、上帝被称为天的主人和统治者(主宰),用来指代其最高的治权。天命归于上帝,眷顾出自上帝;对上帝的祭祀和崇拜是最高级别的。除了用上帝表示最高的存在外,他还被用来表示其他低级的无形存在。除了儒家的五帝外,还有道家的各种帝。昊天上帝、玄天上帝、皇天上帝、皇上帝、明昭上帝、天主大帝、天主上帝、诸天上帝等见诸典籍,甚至将释迦牟尼称为“帝释”,民间信仰中则有“关帝”等。在这个意义上,帝或者上帝实际上并非一个专称,而是名号,一个类称。当然,“上帝”往往用来指代独一的deity也就是Deity,尤其是在中国信仰比较纯正的最初阶段。由于他们都表示单独的个体存在,因此又是一个类称,可以作为一个属概念,与其他的修饰词组成专称,如玉皇上帝、玄天上帝等。这种用法是与希腊一样的,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就将造物者作为Deity,文献中也有阿波罗神(ho theos appolon)等用法。其三,“帝”的称号也用于人,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用来指死去或活着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中国的这种做法与希腊罗马是一致的,他们有将英雄人物或者最高统治者神圣化的习惯,罗马的国王、元首的称号里面有theos、deus等。这种习惯在中国起于秦始皇,在罗马则起于恺撒*W.H.Medhurst,Reply to the Few Plain Questions of a Brother Missionary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for July 1848),Canton,1848,pp.10-11;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pp.77-78.。
在阐述上帝的内涵和外延的同时,他对“神”进行了讨论,主张将它作为Ruach和Pneuma的译名。
麦都思认为,根据吉托(John Kitto?1804—1854)和约翰逊等人的定义,Ruach的本义为“风”或“呼吸”,引申为“精神”、支撑身体的活力、“灵魂”(区别于动物的理性的不死的原则)、“幽灵”、“智慧”,也用来指代Deity(指其精神性本性)和Holy Spirit(作为神的一个个人代理)。拉丁文用spiritus(本义也是呼吸)翻译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的这两个术语,是非常贴切的。整体而言,Ruach及其译名具有以下特点:它与物质有别,是非物质、非实体性的、知性存在,其活动限于思想和灵魂范畴,独立于肉体,是灵魂的行为,关注的是纯思想性的*Walter Henry 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Translating Ruach and Pneuma,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criptures, pp.1-3.。
麦都思先后以《康熙字典》、《本义汇参》、《佩文韵府》等所收的与“神”字有关条目为对象,辅之以儒、释、道等文献,分析了“神”的含义。据《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的解释,又根据“神者,申也”、“气之伸者为神,屈者为鬼”等论断和天神、地祇、人鬼等区分,麦都思认为,“神”与Ruach的内涵一致,指的是精神、思想和灵魂,尤其是理性的灵魂或精神,也可以用来指万物的精神,即实存个体的无形部分,与行和物相对。首先,从本义上看,本性(nature)的屈伸是其重要特点,有呼吸的含义。它是天用来引出万物的精神(spirit or anima),而非驱动天的首要力量(primary power),天送出其气(breath)或者精神,以影响或者引导(lead forth)万物。其次,就应用而言,神有抽象和具体两层含义。前者指无形的精神等,指生命活力、人的灵魂、思想和精神、动物的精神以及所有有生气的事物的精神本质,与气、生气相连*Walter Henry 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Translating Ruach and Pneuma,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criptures,p.11.。后者则指人死后脱离躯体而存在的鬼魂、精神、灵魂等,与鬼、妖、灵、精、仙、怪等相连,而与民、鬼、祇等相对。灵虽然与神有相同之处,但双方有区别,“灵”本义为聪明、才智(intelligence)。不过,在抽象意义上,神与灵差距甚大,而在具体含义上,二者相同,可以替换。总体而言,二者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灵”与spirit有较大的差距。最后,神不是崇拜对象,并非独立的存在,并非像“上帝”那样是一个对信仰对象的类称。“神”在一个在上的权力的权威(上帝)指导下,参与引出人和万物的呼吸、养育人、天体的出现和降落、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等,是上帝所以“妙万物者”。虽然它们也受到祭祀的影响,能保护国家和个人,但始终是遵从其上级的意志的,从不是独立、高高在上、毫无约束的终极者。因此,他们并非gods,而是从属性的精神、代理、妖怪和灵魂(manes)*Walter Henry Medhurst,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Chinese, With a View to the Elucidation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Term for Expressing the Deit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The Mission Press,Shanghae,1847,pp.190-191.。他认为,“人神”指的是minds of men,“上帝之神”则是spirit of the Supreme Ruler,“天之神”则是spirit of Heaven,祭祀时接受分享祭品是所祭对象的“神”。他认为,在圣经里面,Pneuma与God相连时,指的其非物质性,如《约翰福音》里面的“主为神”(God is a spirit,4:24)。不仅儒家经典中的用法及意思如此,古典道教和佛教经典中“神”的用法及意思也是如此。虽然后来受到偶像化崇拜的损害,但汉语中“神”始终指的是精神,不具有God的含义。
麦都思认为,综合比对中西以及中国内部各宗教的理解和用法,都可以看出Ruach(Spirit)和“神”的内在一致性。因此,不能用“神”翻译God,为了更好地对应Ruach的内涵,只能用“神”而非“灵”来译。圣经中Holy Spirit是一种真实、知性、个人的主体,他拥有无限的智慧、主权的意志和坚定、权能,他发出命令或禁令,直接向他的人民说话,任何对他的亵渎都是严重的冒犯*Walter Henry 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Translating Ruach and Pneuma,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criptures,pp.57-58.。
四、作为自然神学的中国宗教
应该说,在麦都思的论证下,中国的“上帝”和“神”不但分别具有了新的内涵,而且被系统化了。他按照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从散乱的材料中梳理出一种自觉的体系,形成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内涵的神学认识,削弱甚至消除了基督教的外来性特征。这种认识无论对传教士还是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新颖的。从传教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它可以消除中国人的疑虑或敌意,使基督教义易于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改变传教士的偏见,藉在西方传统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宗教之间建立起的积极内在关联,强化传教的合理性,坚定传教的信心。当然,如果按照基督教关于Elohim和Ruach的教义,麦都思的论述显然还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在Elohim的造物主身份和全能、全知、全善等属性,Ruach的作用,Elohim和Ruach的关系等方面。此外,他也很难在中国的典籍和文化中找到基督这样一个角色,更不用说讨论三位一体和原罪之类的教义了。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如,他在评论《尚书》时说:“有些地方提到了至高者及其对人事的掌控,但又常常将天的庄严权威与物质的天混为一谈,将其荣耀等同于所谓的山川的神(spirit),以及故去的祖先和英雄的灵魂。对伟大上帝及所有人的父的爱从未提到过,与被冒犯的上帝的复合状态,还有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的事实,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W.H.Medhurst translated,Ancient China,The Shoo King,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Illustrated by Later Commentators,viii.。虽然他在论述中也试图强调上帝的造物主身份(《子夏易传》“帝者,造化之主,天帝之宗”之语),并援引两位熟悉或接受基督教的中国人吴天心、郑日昺的文章加以强化*Walter Henry Medhurst,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pp.261-264.,但整体而言,他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能作为反对使用上帝和神作为Elohim和Ruach译名的理由。这些不足是必然的,是由中国宗教的特点决定的。
与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麦都思也认为中国的宗教观念和实践中确实没有与基督教的Elohim完全对等的角色。不过,他并不赞同文惠廉等认为中国人是泛神论和多神论者,因而完全不能理解基督教的Elohim神和基督教的说法。在他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存在一个类似Elohim的最高存在及其信仰,尤其是在古代中国。这个角色就是“中国标准及正统宗教”*Walter Henry Medhurst,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p.1.——儒教的“上帝”,他是精神性的无形存在及最高崇拜对象。麦都思认为,孔子时代的中国虽然也拜精神性的存在,但并不拜偶像。古代的典籍中也确实含有一些关于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内容及其属性,“这表明古代中国人对所谓的自然神学并非完全一无所知。”中国传统神学本源上的固有缺陷加上后来掺杂的迷信,崇拜偶像化了,使得它受到严重毁坏。道教和佛教并非正统,其滥用和迷信并不能伤害上帝的本质,其自然神学的基本真理始终是存在的。这足以证明God在中国是有见证的,中国人是知道God的*Walter Henry Medhurst,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p.2,pp.85-86.。
麦都思认为,虽然中国的自然神学与基督教的启示神学有较大差异,中国历史与西方也有不同,但作为God(上帝)造物的一部分,中国显然不能游离于God的计划和主宰之外。中国的历史和宗教整体上要遵循其设定的一般规律,表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其内在一致性。在这个角度上,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无论在起源、进程和最终结局上都是一致的。天(上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具有普遍性,是所有民族的。所以,中国人的上帝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的神。他相信,中西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轨迹有一致或相似之处,他的《东西史记和合》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而写作的。他认为,中国古典文献中缺乏洪水前的记载,可能与秦始皇焚书有关。文献缺失不能作为中西历史发展不同的证据。圣经叙事中的大致线索,在中国也有所体现。圣经中的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在同期的中国历史中也可以见到,如大洪水、恺撒与秦始皇*爱汉者等编,黄时鑑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癸巳年六月至乙未年五月各期连载之《东西史记和合》部分。。除历史线索和进程的相似外,他还认为中国在最初的时候与西方(犹太教)一样有纯正的一神宗教崇拜,这种崇拜就是中国的上帝。中国的上帝甚至可以说就是西方的耶和华,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后来他虽然不再强调这一点,但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至少与希腊罗马是同一层面的。东西历史和宗教的统一性特点使他非常注意基督教原典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主张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解释或注释基督教经典或教义。他的《三字经》、《论语新纂》等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中国宗教的自然神论色彩使得它与希腊罗马宗教处在同等的地位,这一点非常充分地体现在上帝、神以及theos和pneuma的对比中。对麦都思而言,使徒们的惯例是选择中文译名的重要参考依据。来华传教士对这个原则并无反对意见,但具体认识不同。文惠廉认为,“神”是中国人信仰对象的类称,而“上帝”则是中国人所知的最高神。他不过是一位泛神论中的主神,并不具有创造万物的特性(“万物自生”),并非西方人称之为Elohim的那个存在。上帝与希腊罗马的宙斯和朱庇特相类似,是偶像性的,不能作为Elohim的译名*William Boone,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θεο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Canton,1848; A 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ΘΕΟΣ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Canton,1850,pp.4-5.。如果以上帝作为他的译名,就触犯了十诫,陷入拜偶像的境地。应该仿照使徒的惯例,把作为类概念的“神”作为Elohim的译名,然后加以教导,使中国人树立正确的观念。麦都思则认为,使徒们并没有因为希腊罗马宗教中的多神崇拜、帝王崇拜等而拒绝用theos翻译Elohim。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引导,向信徒们灌输正确的观念,改正他们的错误,恢复纯正的信仰。他指出,既然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扩展,罗马的所有迷信都能被消除,随着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同样的结果也会出现*Walter Henry 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pp.77-78.。这种不同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认识的不同,又体现了他们对基督教以及希腊罗马文化认识的差异。在文惠廉看来,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和宗教是完全异质的,道殊途异。传教士的使命是通过传播正确的宗教,使中国改弦更张,走上正确的道路。麦都思显然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传教士要做的最多是使中国人迷途知返,恢复纯正的信仰。
不过,这种过分中国化的策略却遭到不少传教士的激烈批判和坚决反对。他们认为麦都思美化了中国宗教而歪曲了基督教。这一点从1836年是否批准新译本的争论上就可见一斑。麦都思认为,马礼逊的翻译过于拘泥原文和西方语言表达方式,中国人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接受,反倒容易产生排斥心理。要弥补这个不足,就应该考虑汉语的表达习惯,借用中国人熟悉的习语,以便于理解和接受。为此,他改译了一些术语,如把马礼逊的“吗咥”(magi)改为“贤人”,“公所”(assembly)改为“公堂”,“拉比”(rabbi) 改为“夫子”,“门徒”(disciple)改为“门生”,“先知”(prophet)改为“圣人”,“祭者”(priest)改为“祭司”,“西撒尔”(Cesar)改为“皇帝”,“堂”(temple)改为“殿”,把“祈祷”(recite prayer)改为“念经”,把比喻意义上的“肉血”(flesh and blood)改为“旧人类”等。为了迎合中国表达习惯,将“夫耶稣基利士督之生为如此”(《马太福音》2:18)改为“夫耶稣基督降生之情如左”,把“由圣神风而受孕”改为“感圣神之德,而怀孕也”(《马太福音》2:18),把“我们有亚伯拉罕为吾父者”改为“亚伯拉罕乃我祖宗”(《马太福音》3:11)。在伊云士和戴尔看来,麦都思不是在翻译圣经,而是在意译,严重背离了圣经公会制定的忠于原文的基本原则。表面上看,是随意、不严谨,是擅自增字或删字解经,实际上犯了异端错误,败坏了基督教,有将基督教异教化的危险*伊云士和戴尔的信附在麦都思的信后面。Copy of a Letter from the Rev.Messrs.Evans and Dyer to the Rev.Joseph Jowett (Apr.27,1836),pp.45-48; Copy of a Letter to the Rev.Charles Gutzlaff,&c.&c.,Canton(Apr.25,1836),pp.48-52.。基德更是直言:“其目的在于讨好异教徒”,是为了迎合“异教徒喜欢把神启与他们自己的制度等同”的心理*Samuel Kidd,Remarks on the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p.2,p.5.。
五、麦都思神学思想中宋明理学的影响
作为一位外国人,麦都思对汉语典籍中“上帝”和“神”的理解未必正确,有些甚至显得牵强(如训“帝”为“审判”的例子)。他没有对关键概念做历史的考察,更没有注意到古今的变化。他想当然地把儒家学说视为宗教。虽然也意识到儒教的古今不同,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实际将它等同于朱熹的学说,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有可商榷之处。尽管如此,他的译本和观点还是受到中国基督徒乃至非基督徒的欢迎,后来更是被太平天国采纳。他的“上帝”译名主张也获得了部分西方传教士的认可,与“神派”并行不废。可以说,在基督新教初入中国,国人对基督教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他用中国典籍阐释基督教理论的做法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他的认识不但为中国传统宗教与基督教的初步认同做了大胆的尝试,而且为中国基督徒和儒家知识分子认识基督教乃至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也为后来中国神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途径。
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对中国基督教神学还是中国文化,麦都思对“上帝”和“神”的系统论述都可谓是一种新的建构。他以新的组合方式,拓展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维度和发展空间。表面上看,其认识是外生性的,是西方基督教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只是借助了中国文化元素。实际并非如此。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麦都思的认识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宋明理学为重要根底的。
麦都思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的认识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和正统的,这是其立论的大前提。他认为,道教和佛教并非正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正统的破坏和歪曲,不影响本质。当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儒教也堕落了,与佛道为伍,如都有迷信色彩,同时具有无神论和泛神论的特点等*Walter Henry Medhurst,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Gospel, Paternoster Row,Lodon,pp.218-219.。虽然麦都思在论证中以儒家的经典为主题和正统,但也并不完全排斥道教和佛教经典(文惠廉则比较注重用道家经典和理论反驳他)。只要能支持他的论点的材料,都在他的采用范围,道教和佛教典籍是重要的补充。虽然他在理论上非常清楚儒释道三家的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将它们区分开来,似乎受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不同名号的上帝的列举和认识中看出来。在儒家思想中,他无疑以宋明理学为正统,朱熹(他称之为朱夫子)的相关论断则是他的重要证据和思想源泉(如天即帝,帝即天)。宋明理学中的心物、体用、理气等哲学概念成为他借鉴的重要范畴。如他认为“上帝”是体,而“神”是用。
经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概念的系统化程度加深,在上帝、神等方面也有一些自觉的探讨,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改造和利用奠定了基础。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罗马公教耶稣会传教士就曾尝试过用理学阐释基督教的教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部分传教士也主张用上帝翻译God(Deus),并得到一些中国士人的支持*黄一农:《被忽略的声音——介绍中国天主教徒对“礼仪问题”态度的文献》,《清华学报》(台湾),新25卷第2期(1995年)。。虽然新教传教士明确否定公教的“天主”译名,但就论证所依据的理论角度而言,双方并无质的区别,都深深植根于程朱理学。作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维度,理学是麦都思关于“上帝”和“神”认识的重要起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观点。这也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潜在的知识和思想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麦都思的认识并非开端,而只能算一个结果或升华,即把中国思想中的相关理念和论述系统化,并赋以明确的基督教内涵。元代梁寅有论:“神即帝也。帝者,神之名;神者,帝之灵。帝者,神之体;神者,帝之用也。凡物皆有神也,而物莫大于天,则神亦莫尊于帝。故主宰万物者,帝也,而所以妙万物者,帝之神也”*梁寅:《周易参义》,卷十(四库全书本)。。如果麦都思看到这个论断,虽然未必完全赞同,但没准会发出“英雄所见略同”之类的感慨!
(责任编辑蒋重跃责任校对孟大虎侯珂)
[收稿日期]2015-10-31
[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近代中国新教神学的建立——以圣经译名为中心的考察”。
[中图分类号]B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4-0127-11
On the Theological Thought of Walter Henry Medhurst
LIU Lin-hai
(School of History,BNU,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upreme Being in the Christian Bible is an important thesis for comparative religious history,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It used to be a long controversy among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to China in the 19thcentury as the term or terms of translation is concerned.The British missionary Walter Henry Medhurst disagrees with Robert Morrison,founder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on using the Chinese terms shen as the generic name of Elohim or theos and the sheng shenfeng for Ruach or Pneuma.He renders the Elohim into the shangdi as an appellation and the Ruach into the shen rather than the ling by a detail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hinese texts.He not only argues that the shangdi and shen are terms for theos and pneuma in essence,but also identifies the Chinese religion with the Greek and Roman ones whose characteristic is natural theology.Medhurst’s theological argumen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s and ideas of the shangdi and shen in the works of the Song-Ming New Confucianism.It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and interaction in the field of religion and ideology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at that time,which is significant to understand both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His maneuver to interpret Christian theology with the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theology practice,which provided not only a new pattern for the West to interpret the Chinese religion or culture,but also the theoretic validity for the Chinese to understand or accept Christianity.
Keywords:Walter Henry Medhurst;theological thought;shangdi;shen;natural theology;Song-Ming New Confucianism
——《宋明理学人格美育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