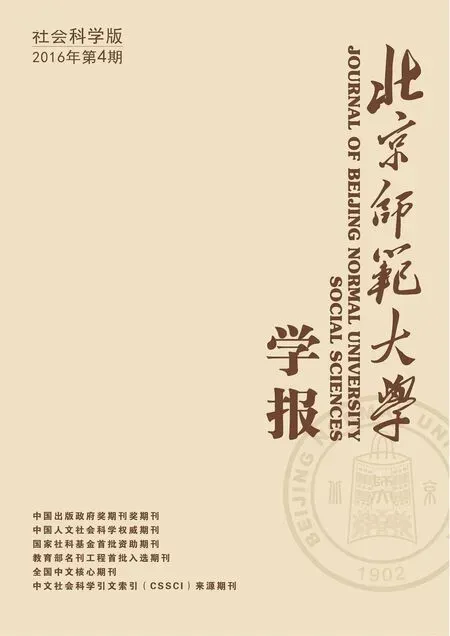论民俗传统的“遗产化”过程
——以土家族“毛古斯”为个案
王杰文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论民俗传统的“遗产化”过程
——以土家族“毛古斯”为个案
王杰文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摘要]“毛古斯”是湘西土家族在传统年节期间表演的一种仪式歌舞,其原始古拙的表演风格与内容近年来吸引了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又为当地政府部门、地方专家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文化保护以及旅游民俗开发提供了话语资源。目前,“毛古斯”正经历着被对象化、僵化地认知与理解的过程,这也是当地民众被疏离于自身传统的过程。作为“文化表演”的传统正在被异化为一种被复兴的、被重新发明的所谓“传统文化”,地方社区的经济模式、社会关系、心理世界也因此而经历重组。湘西土家族“毛古斯”的个案表明,只有给予当地人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与“主导性”以足够的尊重,其文化传统与民俗才能鲜活地、必不可少地存在于当地社区民众的日常实践中。
[关键词]文化表演;身份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化;遗产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民俗学者发现,无论哪一种形式的“遗产”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被不断地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它是由特定社区、群体或者个人从其日常生活实践中“选择”某些内容出来予以特别地推崇与保护,并使之“成为遗产”的过程。这一过程被民俗学家们称作“遗产化(heritagisation)”。“遗产化”的话语与实践在中国湘西土家庭“毛古斯”的展演中也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毛古斯”是湘西土家族地区的一种仪式,兼有说唱、舞蹈甚至戏剧的因素,被戏剧史学家看作是“土家族戏剧的雏形”①彭继宽:《土家族文学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毛古斯”究竟指的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毛古斯”即浑身长毛的古人,是以渔猎作为主要生存手段的原始人群;又有学者依据土家族古代语言的研究成果认为,“毛古斯”是土家族的古语,指的是“毛人的故事”;还有学者指出,湘西各地对“毛古斯”活动的命名略有不同,比如,龙山县坡脚乡一带称为“故事帕帕”或“故事拔铺”,永顺县双凤村称为“毛古斯”,永顺县莲蓬村称为“毛古人”,保靖县仙仁村称为“故事”,古丈县小白村称为“帕帕”等,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所指却基本相同,即都是指关于祖先的故事;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毛古斯”并非土家语的音译,而是根据其活动内容和人物形象而确定的汉语名称,其本来含义是毛人的故事,而“毛人”代表了土家族祖先,所谓“毛古斯”也就是“祖先的故事”。在湘西土家族地区,“毛古斯”总是在“社巴节”②张天如等纂修:《永顺府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中表演。土家语中所谓“社巴”,就是“摆手”。据湘西《永顺府志》载:“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七日,男女齐集,鸣锣击鼓,跳舞唱歌,名曰‘摆手’”。永顺县、龙山县土家语中称“摆手”为“舍把”,古丈县称为“舍把把”,而保靖县的一些地方称为“调年”。现在学界统一称之为“社巴”。“毛古斯”是湘西土家族地区在“社巴节”表演的一种仪式舞蹈。
2008年,湘西永顺县的文艺工作者们经过改编再创作之后,推出民族舞蹈“土家毛古斯——欢庆”*曾维秀:《“毛古斯”走进北京奥运会》,《新湘评论》,2008年第11期,第47-48页。,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表演的26个节目之一。在正式作为奥运会开幕式前文艺表演节目之前,为了使这一节目更具有观赏性,节目的主创人员先后进行了多达13次的艺术加工。
一、作为“民俗”的土家族“毛古斯”
20世纪50年代后期,湘西地方文化工作者首先注意到“毛古斯”,并开始了初步的挖掘收集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的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曾深入湘西从事民族调查,1955年撰写了《湘西土家族访问团调查报告》。另参见潘光旦:《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1959年,中央文化部组织省、州、县民族文艺调查组,对“毛古斯”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和收集,并写出调查报告。1963年,湖南省民委派人访问“毛古斯”的表演者,写出了“马蹄寨毛古斯舞访问记”。“文革”中,“毛古斯”被视为“封资修”,停止活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家族的“毛古斯”表演再次受到重视,恢复了表演活动。
最早从现代学术的角度考察“毛古斯”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持开展“十套集成”的编辑工作,湘西土家族的“毛古斯”受到民族民间舞蹈工作者的关注与记录,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中国舞蹈的活化石”*王炬堡通纂:《土家族简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戏剧史学家们则认为,它是戏剧的早期形态。虽然舞蹈史学家与戏剧史学家都对“毛古斯”的“年代久远”十分感兴趣,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提供有关“毛古斯”表演活动的完整的民族志田野资料;不过,仅从当时保留下来的片断性的材料里,人们仍然可以了解到20世纪80年前后,湘西四县“毛古斯”表演的一般状况,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五个特征:
第一,毛古斯与摆手舞总是相互伴随着被表演的。但是,据当时土家族的老艺人彭继富说,“跳摆手舞时不演‘毛古斯’(一种原始戏剧),亦不唱歌。”*袁丙昌:《湘鄂西采风散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90页。可见,摆手舞、毛古斯又是可以相互区分的;摆手舞是纯粹的舞蹈,而毛古斯已经具备了戏剧的雏形。
第二,“毛古斯”表演中有人物出场,并有相当多的人物对话,如《毛古斯生产》一场中,就有“老毛古斯(土家语称为“拔普卡”)”“小毛古斯(土家语称为“沃必爹”)”和“土王管家”等人物出场;在《毛古斯打猎》中,除了上述正面人物外,还增加了“咕噜子(湘西方言,即骗子的意思)”等反面人物。
第三,“毛古斯”的表演场次因地而异。比如永顺县双凤村的毛古斯表演要持续七个夜晚,每晚安排一场,每场表演一个内容;龙山县贾市一带的毛古斯则是集中在一个晚上表演完所有节目。
第四,“毛古斯”的表演内容十分庞杂。既有反映土家族先民原始生活的内容,也有反映近代生活的内容。比如永顺县双凤村的“毛古斯”,当时保留了“扫堂”“烧山挖土”“打猎”“钓鱼”“学读书”“接新娘”“接老爷”等七个节目,其中既有反映远古社会渔猎生产生活的内容,虽然也有反映封建社会阶级剥削、压迫与不平等的内容,不同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元素被混杂在一起,然而,“群众对这些跨时代的表演,并不计较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只要达到娱乐的目的即可”*彭继宽:《略论土家族原始戏剧“毛古斯”》,《民族论坛》,1987年第2期,第55页。。
第五,“毛古斯”表演同时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与永顺县双凤村的“毛古斯”不同,龙山县报格村等地的“毛古斯”则除了表演“做阳春”“打猎”外,还会表演反映近代生产生活内容的“打铁”“纺棉花”“医病”等节目;龙山县信地村的“毛古斯”则表演“拖木”“起屋”“耕田耕地”“讨帐还帐”等节目,龙山县贾市、内溪一带还要表演“给土王拜年”“讨土”“烧山挖土”“洒小米”“扯草”“打粑粑”“过年”等节目;保靖县恶旦一带则表演“种包谷”“栽秧”“薅草”“捡桐籽”“摘茶籽”*依据张子伟的田野资料可知,晚至1999年,“湘西四县十七乡社巴活动及毛古斯演出活动中,在23个村寨社巴日中,有15个村上演毛古斯,3个村有毛人歌舞表演,另一村虽无毛人,但有毛古斯里的原始歌舞,且有舞动草祖的表演,其余4个村只歌舞祭祖,无毛古斯出现”。参见张子伟:《湘西毛古斯研究》,《文艺研究》,1999年第10期,第45页。等节目。
20世纪80年代,研究“毛古斯”的学者们大致认为:“毛古斯以其古朴、冗杂的形式,为研究土家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资料”*纪成:《毛古斯》,《鄂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第144页。,从中可以初步窥探出土家族历代(从蒙昧时期到近代)社会性质的特征,特别是原始氏族社会的某些痕迹,以及土家族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文化发展的状况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痕迹。
然而,从90年代开始,“毛古斯”表演中有关“土家族不同历史时段的文化元素”的描述渐渐被所谓“土家族先民远古社会生活状貌的多个层面”的描述取代,那些最能证明其“原始性”的特征吸引了学者们更多的关注,而其中有关近代社会的内容被彻底忽略了。学者们在“毛古斯”的表演中发现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证据,找到了一幅幅人类童年时期的生动图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表演者的衣着形象与表演风格。“毛古斯”的表演者皆为男性,他们赤裸着身体,穿着用茅草或者稻草编织的衣服,头上戴着用五条草绳编织的辫子,髀间悬挂着草扎的生殖器模具,模具的顶端缠着红布条,特别醒目;手里握着齐眉的木棒;表演者两膝半屈,臀部下沉,两脚不停地踏着碎步。这些特征被认为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时代,土家族的先人们茹毛饮血生活的反映。第二,表演者说话时会变嗓音,显得怪声怪气;而他们对话的内容则同样反映了原始时期的生活,比如,其中扮演土王管家与老毛古斯的两位表演者之间的对话经常被引述:
土王管家: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老毛古斯:我们是从野兽居住的洞里,从猴子爬过的路上来的。
土王管家:你们昨晚上在哪里睡的?
老毛古斯:在棕树脚下睡的。
土王管家:你们吃的是什么?
老毛古斯:吃的棕树籽籽。哎呀,糙糙的。
土王管家:你们喝的是什么?
老毛古斯:喝的是凉水。
土王管家:你们住的是什么?
老毛古斯:住的是草堆。
土王管家:穿的是什么?
老毛古斯:穿的是棕树叶。
土王管家: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老毛古斯:听说这里好,我到这里来生养儿孙。*在某些地方,比如龙山县苏竹坪,问话者是“热必得”,答话者是“拔普卡”;所问的内容则大体上相类似。
研究者们认为,这些回答勾勒出了原始社会土家族部落的生活情景。此外,当土王管家问到谁是“阿爸”时,众毛古斯争相说自己是“阿爸”,因为争执不下,只能公推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老毛古斯”当“阿爸”。这被视为“古代土家族部落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的情景”。第三,抢婚的遗俗。表演“抢婚”的情景时,毛古斯们都争着与抢来的“新娘”成亲,在喧闹与殴斗之后,最终的胜利者获得婚姻的权力;年幼的表演者们则互相取笑对方为“杂种”,乱报姓氏又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学者们认为,这是土家族人从群婚向对偶婚过渡的遗迹*张子伟:《湖南省永顺县土家族的毛古斯仪式(附录七)》,《民俗曲艺丛书》(台湾),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6年版,第279页。。第四,生殖崇拜。毛古斯的表演中最醒目的道具是所谓“粗鲁棍”,即一种夸张化的阳具模型,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双手紧握粗鲁棍,做出示雄、打露水、撬天、搭肩、挺腹送胯、转臀部、左右拦摆等动作,所有这些动作都充满了生殖崇拜的暗示*李怀荪:《毛古斯与生殖崇拜》,《民族艺术》,1992年第3期,第88-93页。。第五,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砍火畲”一场对土家族祖先“砍”“烧”“挖”的劳动过程和动作作了逼真的再现*曹毅:《土家文化的瑰宝——毛古斯》,《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61页。。第六,原始狩猎。在模拟狩猎生产的表演中,毛古斯先敬“梅山女神”*土家族尊崇的猎神。传说土家猎神是位有胆有力的女猎手,因有虎患,她替民除害,在与老虎搏斗中被老虎抓得片纱未存,羞愤下与虎抱在一起,跳崖身亡。为纪念这位替民除害的女英雄,土家人奉之为猎神。因为她死时是裸体,不便塑像,所以以草码代神像而祭之。,然后表演查找野兽脚迹,放猎犬;一个装扮成野兽的毛人出现,毛古斯将它团团围住猎获,然后敬献给梅山女神,最后杀死猎物并均分。研究者认为,这场戏真实地“再现了原始社会中土家族先民共同劳动的基本方式和平均分配的公社制度”*谭卫宁:《毛古斯:土家族的民俗考古》,《民族论坛》,1993年第2期,第78页。。
然而,如前所述,“毛古斯”表演中“教读书”“接老爷”“打猎贸易”“栽秧”“种苞谷”“洒小米”“扯草”“纺棉花”“起屋”等内容,明显反映的是土家族地区社会历史的演进及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但是,90年代以来,在流行的研究话语中,这部分内容渐渐地被忽略了。当然,也有几位研究者仍然清楚地意识到并坚持了历史发展的观点。比如,张子伟就明确指出:随着文明的进程,“毛古斯”呈现出了世俗化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毛古斯供奉的祖神从女神“三元”,经历了“八部大王”,最后转化为“土王”的过程;第二,毛古斯表演的剧目包括了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内容,这些内容又以不同的方式被呈现出来,有的纯粹是动作表演,有的则在歌舞之外加上大量对白,显然具有戏剧的因子。第三,因为“毛古斯”是仪式性的表演,其表演的模式因崇祀对象、参与人员等因素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毛古斯”表演的世俗化,仪式性权威(梯玛)逐渐被社会性权威(寨主、族长或者村长)所分享甚至取代*张子伟:《湘西毛古斯研究》,《文艺研究》,1999年第10期,第50-54页。。
21世纪初,在有关“毛古斯”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这种仪式表演活动“反映了土家族童年时期生产与生活的原生态,是土家族戏剧艺术的活化石”*陆群:《“毛古斯”戏剧表现形态历史衍变的人类学考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50页。,然后便以想象的方式猜测“毛古斯”发生时期的原始形态,并由此去还原原始人的心理动机。社会进化论主导着整个学术界的话语与思维模式,“毛古斯”被固化为远古的遗存,其中所包含的发展的、创造性的因素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掉了。
二、“毛古斯”的“遗产化”进程
21世纪以来,有关“毛古斯”的话语转向了“保护”与“开发”,而“保护”与“开发”的工作理念又是基于前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即毛古斯是“远古时期生产与生活的活化石”。“活化石”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传承的难题,于是,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面前,一方面,“毛古斯”成为地方文化产业亟待开发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它又是当地文化部门急需抢救与保护的文化遗产;最终,在调和两种需要的努力之下,“毛古斯”正在成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中的内容。
1.作为湘西民俗旅游的“文化资源”
湘西奇异的山水风光、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土家族和苗族浓郁的民族风情有机结合,和谐共生,形成独具特色、相互依存的湘西文化生态链,这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
在湘西著名的旅游景观中,比如张家界、凤凰古城等地,都有被“去语境化”、改编后的、舞台化的“毛古斯”在表演,作为旅游民俗的“毛古斯”已经舞台化、市场化,显然极大地区别于社区文化传统中的“毛古斯”,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相互关联的层面中:
第一,与节日语境相剥离,作为旅游民俗的“毛古斯”已经与传统的节日语境毫无关联,只要有观众,“毛古斯”会随时被上演;第二,与仪式功能相剥离,既然“毛古斯”已经脱离了地方社区的节日语境,伴随其历史发展的仪式功能及其古老的思想自然也就消失了;第三,与地方民众相剥离;那被崇祀的先祖,那主持仪式的“梯玛”(巫师),那组织活动的寨主(族长或者村长),那些虔诚的村民都不复是“毛古斯”表演活动的必要因素,相反,作为旅游民俗,这里有的只是与“毛古斯”传统不相干的机器般高速运转的表演者与对“毛古斯”的形式充满猎奇心理的一拔又一拔亢奋的观众*罗维庆:《共同的舍把日,不同的毛古斯》,2011年第21期,第28页。。第四,与社区生活相剥离,作为旅游民俗的“毛古斯”大有取代地方社区传统“毛古斯”的趋势,村寨里代代相传的“毛古斯”由于其节日性、仪式性、古朴性特征,在现代理性意识与功利主义面前,显得过于陈旧与落后,渐渐走向了没落。第五,与戏剧形态相剥离,作为旅游民俗的“毛古斯”不再可能成本大套地搬演传统“毛古斯”的全部内容,基于现代审美理念的编导工作让“毛古斯”更适合来自远方的观众的心理预期——既是可理解的,又是神秘的。总之,游客的“凝视”改变了客体的呈现方式*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2.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进入21世纪以来,湘西土家族文化的传承、抢救和保护工作倍受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2004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整体列为“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地区。2006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首个地市级的地方性保护法规。在此条例基础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出台了《湘西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湘西土家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自治区政府认识到:
“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无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的威胁。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对民族民间文化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甚至把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看成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任其自生自灭……。一些人打着开发民族民间文化的旗号,却在做着破坏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事,做着愧对祖宗的事,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开发’中变异,变成伪民俗伪文化”。*梁厚能:《把根留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制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纪实》,《中国人大》,2006年第15期,第27页。
现代化的理性意识与商业意识,严重地影响了“毛古斯”的传承,为了尽量避免这些不良因素的干扰,政府部门与专家学者基于“保护”的立场,直接介入“毛古斯”的传承活动,提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然而,问题在于,这些由政府与专家学者们联手发起的“保护”行为,会不会在旅游民俗之外,另外造就某种形式的“伪民俗”呢?
比如,湘西自治州政府部门与地方专家在把“毛古斯”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提出了如下一些详尽周密的保护措施:
为了保护土家族毛古斯舞,湘西自治州民族民间保护中心己制定十年保护计划,此计划由湘西自治州州委分管副书记、州政府副州长负责全面工作,自治州文化局、自治州民族民间保护中心负责具体实施。主要内容包括:
一、全面搜集:组成百人专业队伍,对土家族毛古斯舞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与搜集,尤其是对将要流失的舞种加大力度,系统挖掘。
二、建立土家族毛古斯舞保护机构:从2004年起逐步命名保护区及传承人。
三、建立多个土家族毛古斯舞传习社,培训一批流行区内较高水平的土家族毛古斯舞表演人才。
四、建立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舞研究所(设湘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内),重点研究土家族毛古斯舞的继承与发展。
五、拟在湘西州首府建立一个土家族毛古斯舞展演中心,展示原生态及发展中的土家族毛古斯舞。
六、编篡《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舞大全》一书及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舞系列节目光碟并出版发行。
七、创办一个土家族毛古斯舞道具、服装、乐器制作公司。
八、培养后继人才,在吉首大学、州艺校及中小学增设土家族毛古斯舞教学课程。
九、在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舞流行区各村(寨)组建一个土家族毛古斯舞表演团队。
十、在龙山、永顺推出一台精典土家族毛古斯舞舞台歌舞。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毛古斯”已经被政府部门明确认定为“毛古斯舞”,这一重新定位,显然有悖于之前学者们达成的普遍共识——原始戏剧的雏形——但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标准。当“毛古斯”从仪式性的表演活动变化为“民族舞蹈”时,一系列“削足适履”的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大可质疑的地方至少有如下一些方面:首先,尽管地方政府一直强调要对土家族毛古斯舞进行全面的普查与搜集,但是,其普查与搜集的工作方法却从来没有被提及;其次,命名“毛古斯舞”保护区与传承人的工作引发了许多矛盾。由于“毛古斯”是湘西八县市土家族集体性的传统表演活动,仅仅把某些村寨与个体命名为“保护区与传承人”,客观上制造了不小的矛盾;第三,由于“毛古斯”是一种复杂的表演活动,它涉及到了土家族日常生活与世界观的整体,仅仅把它当作“舞蹈”来传习,是一种明显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第四,政府组建调查队、保护机构、传习社、研究所、展演中心以及相配套的资料与道具生产中心等行为,与其说是“传承”传统,不如说是在“发明”传统。总之,尽管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目的在于保护“毛古斯”的传统行为,实际上却也是一种发明“伪民俗”的行为。
3.“文化生态”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
民俗旅游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于文化遗产及其所属群体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其中负面影响产生的根源恰恰来自于两个术语“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及其所体现的思想意识,既然像“毛古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不涉及到当地民众及其日常生活,那么,以“物化”的方式抢救保护、开发利用的思想,从根本上便带有漠视文化遗产之主体的弊端。然而,这种弊端不仅仅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所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中;也不仅仅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所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布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中,也在所谓的“文化生态”保护工程的工作理念中进一步延续下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国办发〔2012〕14号)中重新强调:“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濒危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抢救性保护,对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生产性保护,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区实施整体性保护。加强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尽管“文化生态”这一术语较之“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这两个术语更强调整体性,但是,无论在政策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文化传统的“主体”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学者、文化公司都不假思索地把民众当作启蒙的对象——他们在经济上是贫困的,在思想上是落后的,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组织上是原始的——因此,地方民众没有被赋予基本的主动性。这种工作理念,从根本上讲,仍然是简单的社会进化论模式的延续。
在这种思想理念与工作模式的指导下,所谓“文化遗产”“文化资源”甚至“文化生态”的保护工作,不过是站在霸权性文化立场上的一种施舍,一种训示。对于地方社区及其民众而言,在文化政治与文化产业的双重挤压之下,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窘境是:一方面,随着旅游开发、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介入,现代文化已经强有力地渗透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了,原有的社区生活秩序与民俗文化传统已经在悄然间改变了(显然,地方民众有权分享现代化文明的成果,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现实的困境——包括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等等——又限制了他们寻找理想生活的渠道。在这种窘境面前,地方社区及其民众正在被迫放弃自身的主动性,正在沦落为自身传统的“奴仆”。
三、民俗的“传统化”及其反思
仪式性、表演性的事件历来都是从事小社区研究的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些在时空层面上被安排、设计好的事件。美国人类学家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称之为“文化表演”*Singer,Milton,When a Great Tradition Modernizes: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Indian Civilzation.New York:Praeger.1972,p.71.,这些被称为“文化表演”的仪式与庆典,被象征人类学家们视为一种特定文化的“元文化的展演(metacultural enactments)”,乃是其社会成员以高度结晶化的形式把自己的文化展演给自己与同伴观看的社会与文化行为。他们所属社会或者群体的核心性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被通过象征性的形式公开展演与评论,具有浓重的“反思性(reflexive)”特征。
湘西传统中的“毛古斯”显然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文化表演”,它是土家族民众自身文化的“元表达”,即人们通过“毛古斯”记忆祖先的历史,展演民族的文化,团结社区的力量,表达自身的愿望,宣泄日常的情绪等等,社区在节日仪式表演的活动中达到“欢腾”的状态。作为社区传统的“毛古斯”显然是土家族民众生命本真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然而,当“毛古斯”被“去语境化”之后——节日不再是其必要的时空语境,神灵不再是其呈现的理想对象,梯玛不再是其主持者,寨主不再是其组织者,社区伙伴不再是其亲密的表演伙伴,表演不再以表演自身为目的——并被“再语境化”之时,“毛古斯”已经从一种神圣的“文化表演”转变为一种世俗的“表演文化”了*黎帅、黄柏权:《遗存与变迁:当下土家族摆手活动功能变迁考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6页。,它与普通的娱乐性表演活动并无二致,不过是借用了某些民族性的符号作为点缀罢了。
在张家界与凤凰古城的文化表演活动中,被加工与改编之后的“毛古斯舞”已经与社区传统中的“毛古斯”绝然不同了,但是,有关“毛古斯”的话语,比如原始、古朴、粗犷、豪迈、放纵、狂野等理念仍然是现代舞蹈艺术从业者们进行再创作的基本前提*张建永、林铁:《民族文化、艺术展演、旅游产业——“魅力湘西”的文化创意理论与实践》,《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4期,第107-110页。,基于这些理念,形形色色被改编的“毛古斯”被呈现在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面前,一种全新的湘西“狂野毛古斯”正在取代“传统毛古斯”,“毛古斯”被重新定义了。
事实上,即使像永顺县双凤村这一土家族文化的典型村落,其“毛古斯”表演也已经变成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毛古斯舞”了。2000年以来,双凤村大力发展村落民俗旅游产业,修建了“土家第一村”寨门和村级水泥公路,偶尔会有旅游团到访,村民们会表演土家族传统的“毛古斯舞”以及其传统节目。“毛古斯”已经成为双凤村民众赖以谋生的重要的“文化资本”,一方面,作为旅游民俗节目,他们通过表演活动向游客收取报酬;另一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他们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财政补助。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两项主要收入还远远不足以维系整个村落民众的日常生活。纵然如此,对于当地民众而言,能否成为国家级、省级、区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毕竟不只是一种荣誉,还附带着经济补助,这无形中引发了村落内部成员之间的竞争与矛盾。无论把“毛古斯”旅游化、“非遗化”给村民们带来了何种实际的收益,一个无可挽回的后果是,神圣的文化传统被世俗化、功利化了。学者们应用话语资源把“毛古斯”对象化为一种过去的文化现象;文化产业公司与政府部门依据学者们创造出来的这种知识,联手把“毛古斯”命名为“(旅游)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而基于现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不仅摧毁了社区文化传统整体性、神秘性、内在性的根脉,而且刺激了地方民众追名逐利的野心与动机。在这个意义上,把“毛古斯”转变为“旅游文化资本”“文化遗产”的过程,乃至于把湘西转变为“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的过程,都是无可避免地把“文化表演”转化为“表演文化”*张远满:《文化传统中的民俗——关于土家族“毛古斯”的田野考察》,《戏剧文学》,2012年第6期,第103-107页。作者也注意到当下“毛古斯”表演少了原始性,而多了表演性,但认为“它也完成了作为民俗文化载体的任务,也娱乐了过节的民众,更重要的是让后人更形象地了解到了毛古斯的表演形式,既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并不仅仅是一块‘化石’摆在那儿供后人参观”。,对传统湘西社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模式进行重组的过程。
当然,既然地方社区的传统经济结构已经断裂,传统的社区组织模式早已崩溃,其劳动人口已经大规模地外迁,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已经深深地渗透进社区群众的日常生活,文化传统已然命悬一线;既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必需兼顾;既然“文化资源”“文化遗产”甚至“文化生态”论都存在某些缺陷,那么,政府、学者以及地方民众都必须重新提出对策,事实上,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了推动文化传统“主体”之“文化自觉”的问题*杨栋、熊曼丽:《民俗旅游业开发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87-88页。,即主张由当地文化的主人保护自己的文化,并在政府的支持与专家学者的帮助下,科学地认识自身文化的历史、艺术与学术价值*覃莉:《论原始戏剧“毛古斯”的保护与传承》,《戏剧文学》,2006年第7期,第40页。
给予当地人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与“主导性”*万义:《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生态学研究——“土家族第一村”双凤村的田野调查报告》,《体育科学》,2011年第9期,第49页。,需要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文化产业实体从根本上改变观念,这在思想上与实践上都将是十分困难的;然而,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是,如前所述,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毛古斯”是土家族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出来“文化表演”,它与该民族独特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传统节庆、民族心理等联系在一起,也受湘西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等制约和影响。问题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毛古斯”的表演形式、组织方式、表演内容以及所表达的内涵等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湘西的传统社区同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和影响。既然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进程,那么,地方社区如何在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秩序被打破之后,积极主动地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组织模式,建立适应现代化社会需求的文化生态修复机制,努力建设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村”,仍然是有待探索的难题。
从“文化表演”转向“表演文化”,显然并不仅仅意味着地方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正在经历重组,还意味着地方民众精神世界正在经历着重构。站在当下民俗学的立场上来说,解放而非凝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存在的“语境”,无论是在理论的层面还是在实践的层面上,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保护;而这一“语境”也最好由产生与保存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来设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意义就在于把保护工作的权利与责任转让给社区自身。如果文化传统与民俗仍然鲜活地、必不可少地存在于地方社区民众的日常实践中,那就是真正地执行了“教科文组织”所倡议的“保护”原则了。这也正是湘西土家族毛古斯的“遗产化”进程带来的启示。
(责任编辑宋媛责任校对宋媛刘伟)
[收稿日期]2016-03-17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4-0059-08
Folklore,Performance and Traditionalization:A case study about Tujia’s “Maogusi”
WANG Jie-wen
(Institute for Art,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Maogusi” is a ritual dance which is performed in the Tujia Nationality in the west of Human Province during the traditional new year,whose antique performance style and content have direct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ome scholars;and in turn,these scholars’ researches have provided a discursive resource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experts who have engaged in protect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ecological culture protection and folklore tourism development.However,when “Maogusi” is objectified and rigidly understood,the local people is also being alienated in their own tradition,the tradition as a “cultural performance” being alienated as a revival and reinvented “traditional culture”,the economic mode,social relations;and the psychological world in the local community also are in a process of restructuring.
Keywords:cultural performance;identity acknowledgemen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est of Human;Tujia Nationality;alienation;tradition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