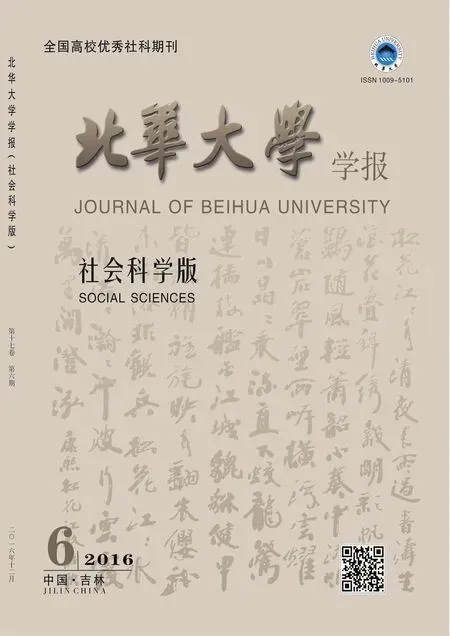“单向度的人”的生存困境
——鲁敏近期生存小说综观
王俊忠
□文学研究
“单向度的人”的生存困境
——鲁敏近期生存小说综观
王俊忠
鲁敏近期的四篇中短篇小说以不同的现代市民生活切片为样本,展现了现代单向度的人无所适从的生存困境。四篇小说的精神内核,均以理想生活或理想生存状态的拷问为出发点。通过鲁敏四篇近作带给我们的文学行旅,我们看到,自觉放逐未来的希望维度,没有历史,也看不到未来的现代人,在现实生活的困境中奔突冲撞,一方面无法逃避内心的质询,一方面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鲁敏;生存小说;生存困境;单向度的人
一、鲁敏:作为写作“试金石”的时代
当下唱衰文学或习惯性地发表“文学风光不再”高见的,多半是所谓的专业批评家们,他们引经据典著书立说,私下激扬文字或公开地高谈阔论,大有天下文学大势尽在其掌握之中的气概。而真正用心艺术创作的作家们,反倒显得相对的安静与坦然。作为“70后”女作家的代表,鲁敏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就有着冷静清醒的认识,“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常听有同行感叹生不逢时、错过高峰,但我却另有乐观之见。现在这样的时代,当可视作最为有效的过滤器与试金石,混文学的、以文学取名声、以文学求利益的,皆可休矣。”[1]
创作力日显丰沛旺盛的鲁敏,是“70后”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近些年的小说创作延续着其江南才女的一贯风格:温婉舒缓的叙事节奏,透出几分直抵主题的凌厉;世俗平淡的百姓故事,掩藏着一种逼人心魄的尖锐。现实生活中,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做选择、做决定、付诸行动。鲁敏小说中的人物,总会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选择、行动中为我们展现一种生存论的图景,总会在此过程中来叩问人的决定、选择以及行动的依据何在,意义何为。这一趋向在她最近的4篇中短篇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平面化的“单向度的人”
从阅读体验来讲,鲁敏近些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变化和跳跃并不是很大,大多取材于一种习常的城市见闻,但作为一名有艺术敏锐度的小说家,鲁敏的功力恰在于:在这种习常的小说题材中,作家并不是流于一种庸俗的市井趣味,而几乎都是围绕现代人两可或两难的生存生活处境来破题,从而开掘出景深丰富的艺术矿脉来。《惹尘埃》(2010)、《缺席者的婚礼》(2011)、《谢伯茂之死》(2012)、《西天寺》(2012),就鲁敏这四篇近作的题材内容而言,既有时尚的年轻人对都市生活体验的新潮追求,也有兢兢业业的国企员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经历的种种不解与困顿的呈现。这些作品,语调舒缓,叙述从容,并不刻意追求一种戏剧化的效果,篇幅和容量不是很大,但匠心独运。鲁敏能以一个独而不特的视角,将主人公无边浩渺的心事,微妙难言的心情,以有形文字细腻地摊于纸上,让那些幽闭晦暗的角落,逐一光亮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鲁敏的中短篇像是一种崭新或曰真正的‘意识流’小说:主人公的心理意识流动,不是夸张的天马行空或任意的飘忽不定,而是有逻辑、有轨迹地心随事动。作家将现代生活中趋于同质的生活经历,艺术并个性化地呈现出来,且能引起读者的会心会意与广泛共鸣,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成功。”[2]现代文明对人心的塑形侵蚀,生成一种怎样才对、如何是好的惶惑与紧张。在此情境中,人的在世感变得像芦苇一样轻浮,既没有历史的厚重沉淀,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在这四篇中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惹尘埃》(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写的是一个有关谎言及现代人该如何对待谎言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肖黎的丈夫两年半前死于一起意外的桥梁垮塌事故,死在了一个肖黎认为他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故事的肇因与展开缘自逝者手机上的一条短信,逝者手机上最后显示有一条名为“午间之马”的不知性别、也不知年龄的人发来的暧昧短信——正是这条短信让肖黎的内心“狂暴像地震与海啸、像所有能想象到的末世灾难,摧毁了她曾有的平和的旧性情”。“午间之马”究竟何许人也?肖黎无从得知,但她判断老公与这个名为“午间之马”的人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然大中午的他为何要出城去往那样一个地方?这种合情合理的怀疑,让肖黎原本以为铁板一块、坚不可摧的婚姻露出了破绽。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鲁敏《惹尘埃》的故事桥段,跟述平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某》的一些情节类似。《某》里的乔丽也是在丈夫死后发现了他原来隐蔽的感情经历,才引发了后续的故事。老公的突然离世并未让主人公肖黎陷入巨大的悲痛不能自拔,而是从此落下了无可救药的“不信任症”,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肖黎偏执地认为孩子唯一需要的教育就是:如何识别谎言,以及如何在谎言的野蛮丛林中过活——这其中自然包含了母爱的天性,也有着一个失去丈夫的单身女性的小心翼翼。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生活的智慧不在于对生活真相的穷追猛打,而在于保持内外平衡、维护身心协调的适可而止。生活本身就不堪穷根究底的再三追问,更何况对丈夫留下的手机,肖黎还时常充电,经常把那条短信翻出来看看,像定期吞服苦药。这就让其内心的裂隙越来越难以弥合,最终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后来肖黎在年迈的徐医生的引介下结识了韦荣。因“不信任症”,专门向老人推销医疗产品的韦荣,一开始自然不可能赢得她的好感和信任,但后来的接触与相处,让肖黎对韦荣刮目相看,并渐生好感。对人以及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生活不能一点都不认真,但又不可太认真。肖黎的问题——用韦荣的话说,是不该当真的当真,该当真的她偏不当真。现实生活中的谎言,就像无处不在的尘埃,本身就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小说的原话,“谎言是全球通用货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认真到将之从生活里彻底清除出去的地步,但“尘埃”太多也不行,“全球通用货币”过多过滥,必然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把谎言当玩笑来看而不用认真,什么时候确实该认真以及认真到何种程度,其实不仅仅是肖黎的问题,也是所有现代人都面临的难题。
《谢伯茂之死》(载《收获》2012年第4期)里的主人公李复,同样面临一个该不该坚持、该不该认真的问题。如果说肖黎面临的是一个比较宏大笼统的生活态度的问题,那么《谢伯茂之死》里的李复遭遇的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真实的工作态度的问题。小说里的“谢伯茂”完全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是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陈亦新虚构出来的那么一个人。作为一个公司白领,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中产阶级,陈亦新家庭和睦,事业有成。表面看来,他成天在网上跟人聊天,和同学朋友在网上见面,但在日常生活中,能说知心话的朋友几乎一个都没有。这也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社会交际的真实写照——表面热闹,内里孤独。与陈亦新形成鲜明对照,他的女儿则有个亲密无间无话不说的朋友“飞鱼”,这让他非常羡慕。陈亦新一时兴起,也虚构了一个他自己的“飞鱼”谢伯茂。他构想出的这个“谢伯茂”跟他同住在一个城市,年龄、性格跟他相当——就是另一个“陈亦新”。为了将自己的这一虚构“创举”弄得像那么回事,陈亦新开始了与“谢伯茂”之间“有去无回”的书信往来。如果说陈亦新的这一行为在开始之初,带有点玩笑之意,只为聊以打发心里的空虚寂寞,那么当他将玩笑慢慢变成一种习惯,接二连三煞有介事地给那个“谢伯茂”写信时,他的玩笑行为多少就有点恶作剧的意味了——那自由而离奇的投递过程他自己很享受,却给老邮差李复带来了巨大麻烦。
李复是一名对本职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老邮差,当年就是因为执着地“救死信”,帮助过很多人,曾被评为省级劳模。在李复行将退休之际,面对一叠“谢伯茂收、本市陈缄”而找不到具体收信人的“死信”,他不甘心也不灰心,跑遍全城去找线索,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背着纸牌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苦苦寻觅。老邮差的执著既有其一贯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因素,也有其行将退休的因素——他不想在退休之际让干了一辈子的工作留有遗憾。后来陈亦新知道了李复背纸牌子寻找“谢伯茂”的故事,去见了李复。陈亦新问李复如此辛苦奔波帮的是谁,李复说那个人他也不认识,但他知道有个人在找这个人,可能比他找的时间还长。听到这话,“那个中年人闭下了眼睛,把什么情绪给闭到里面去似的。”临走时,陈亦新告诉李复:你不要管了,找不到的。悻悻的李复若有所悟,“谢伯茂,对不起。救不活你了。”李复这才把那张白纸板塞到了垃圾桶里转身离去。小说中的“谢伯茂”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缺席者”,这个“缺席者”活在陈亦新的心里,是他精神寄托的一个虚构意象,也活在不明就里的李复的心里,成了他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目标。为了找到这个“缺席者”,李复始终以一种在场的认真精神苦苦寻觅。对陈亦新来说,“谢伯茂之死”意味着陈亦新的“再生”,即这一事件事实上重塑了陈的生活态度;而对即将退休的李复来说,“谢伯茂之死”同样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既是他自己工作生涯的告一段落,也或是一种工作态度或生活精神的暗淡谢幕。
《缺席者的婚礼》(载《上海文学》2011年第7期)同样也是一个关于“缺席者”的故事。《谢伯茂之死》中的“缺席者”有名有姓,《缺席者的婚礼》中的“缺席者”则连姓氏与性别都成问题——小说叙事人“我”实则是一个只有三个月大、还未出世的胎儿,用小说的原话,“我”是“一个该死的不合理的生命”。这样一个特殊叙述者的选择,对鲁敏来说,倒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关于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的去留,以及未婚妈妈跟谁结婚的棘手难题,“我”的姨妈、外婆以及当事人三者间展开了有意思的争论。姨妈明白世故,精于算计,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竭力建议未婚先孕的妹妹暗渡陈仓,争取跟条件优越的Z“把事办了”,酿成“生米煮成熟饭”的事实;而外婆尽管对“那个作孽的小子”气不打一处来,但她还是相信“一开始的搭配最好”,建议女儿跟小杆结婚,从一而终。但在姨妈的反对下,外婆对于时代进步、道德宽松的话题,总有些怯场,况且,她也经常看报纸,知道现在“变天”了,当下的这个时代已不再是她年轻时的那样了。而一声不吭的“妈妈”始终是未置可否,态度不明,在半推半就中去见面相亲,甚至真想过采纳姨妈的建议,跟条件优越的Z走到一起,但终究还是没能鼓起足够的勇气坚持到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妈妈”最后关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既没跟Z结合,也没选择小杆,而是要跟肚里的孩子“我”结婚。
《缺席者的婚礼》的故事结局,显得颇有些出人意料,同时也略带有几分苦涩。姨妈和外婆,无疑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争锋相对:在姨妈眼里,浪漫的恋爱跟现实的婚姻判然有别,婚姻幸福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离不开周到精细的“规划”;而保守传统的外婆,则信奉从一而终,由恋爱到婚姻才是正途,婚姻应该长相厮守,如此,一个女人才会有幸福的归属。相对来说,“我”妈妈的选择,则有点遗世独立的味道,说到底,就是不理“现代”,勿论“传统”,而是一种两可间的折中,这无疑寓意了一种现实的生存困境:既不向世俗低头屈服,又不是完全的理想选择。当然,说到底,这终归是一种小说的艺术化处理方式,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安排——但也恰恰是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才彰显出作为一门艺术门类的小说的妙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不就是表现一种可能性么?或者更直接点说,小说的任务不就是要把生活中的不可能性搬到纸上来么?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敏的小说有了一种人间传奇的色彩。“鲁敏让笔下人物所做的事,都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所‘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些故事仍然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然而,鲁敏让小说中人物所做的,却又是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的。这里的‘不可能’,不是指人的‘能力’,而是指人的‘意愿’。正因为鲁敏让小说中人物做着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这些故事又具有了强烈的传奇性。”[3]鲁敏小说好看又耐读的原因,也或许正在于此。
如果说《缺席者的婚礼》讲的是一个未婚妈妈跟谁结婚的故事,是非典型性的婚事,那么《西天寺》(载《天南》2012年第6期)则说的是一家人上坟的经历,是一件非标准意义的亚丧事。在百姓世俗眼中,西天本是超度的地方,寺庙是了却尘缘的所在。但小说里的西天寺却不然,清明节那天,西天寺人群熙熙攘攘,让本该清净的西天寺,看起来更像是个热闹的集市:人们看上去像是赶集,而不是上坟,像是去交易,而不是去祭祀。《西天寺》讲的是主人公符马一家去西天寺祭奠他爷爷的经历。“符马”谐音“符码”,对作者来说,这显然包含有极强的寓意,即这个“符马”只是一个现代人通用的符号而已,它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小说中符马也确实是一个抽空了内容的躯壳,是没有具体面目的原子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符马是现代都市中一个标准的形象“符码”,而符马的家庭,也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城市家庭中的一个。
在小说中,家庭成员参加祭祀追忆故去亲人的过程,实际上成了一道单薄的远景,或者说根本不构成主人公一家去西天寺的真正目的。推向小说前台的,是充斥着现实生活中多种利益的纠葛与诉求。祭祀完之后家庭聚餐的宴席,也像是一个权力较量的场所,座次安排,谁来买单……浓浓的亲情被稀释了,取而代之的是明面上的斗争或暗中的较劲,但无论是胜还是败,这琐碎的一切,似乎又毫无任何实际意义。符马在祭祀完的返程途中,竟然一时兴起,跟相交已久的网友开房幽会偷情,这看似不可思议,但细想却又合情合理。
符马跟女网友幽会偷情,显然只是为一时的欢愉,从个人品行的角度来说,这并不光彩,甚至可以说有几分龌龊——尤其是刚从清明祭祀的那样一个场合下来。我们要问的,或许不是符马的个人品质有什么问题,而应是他为什么要去寻找这样一种生理刺激?即为什么要在刚刚祭祀完的那会选择那样一个完全背道而驰的生活主题?符马在清明祭祀之后的幽会偷情,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作剧——既是对祭祀过程的无意解构,也是对家庭聚会的无形嘲讽。那么,这其间的反差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说符马的恶作剧行为,究竟是针对祭祀及因祭祀而生发的种种行为颠覆,还是指向一个生活存在论的深度问题?上述种种问题,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唯一能确定的是,对符马来说,性的短暂刺激过后依然是无休止的虚空与无聊。对于多数人而言,日常生活全是些吃喝拉撒睡的应付程序,是破碎的边角料,既没有完整性可言,也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唯独剩下没完没了的不顺与不满,看不到希望和光亮,除了寻找生理的刺激之外,似乎别无他途。鲁敏在《西天寺》中欲向读者表明的是,在纷扰喧嚣的现代社会,西天寺尚且如此,世间又还哪来的安宁净土呢?
无论是《惹尘埃》中的肖黎,《谢伯茂之死》中的陈亦新,还是《缺席者的婚礼》中未婚先孕的妈妈、《西天寺》中的符马,生活中的他们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不满意,但除了被动地疲于应付之外,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对他们来说,过往的历史没有任何色彩,甚至还充满了欺骗和虚伪(肖黎),未来也看不到任何的光亮和希望。他们是一群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可言的“单向度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人就是那种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象更美好的生活,是一种完全平面化的存在。[4]综观鲁敏的近作,“单向度的人”既是小说人物的命运写照,也是现实生活人们生存现状的镜像。
三、现代性的生存困境
“人们无时不在丰富多彩地梦想更美好的、可能的生活。”[5]这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人本身即是超越性的、理想性的、创造性的、批判性的存在。但在众神狂欢的现代社会,“更美好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能否有那样一种“更美好的生活”?鲁敏近些年的小说,从长篇《爱战无赢》《戒指》《博情书》《六人晚餐》,再到《伴宴》《不食》《死迷藏》《字纸》等中短篇小说,作家集中关切探讨的是在光怪陆离、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否仍存可能的问题。美好的生活是否仍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面对家庭社会、同事朋友甚至是爱人不断的追问与期许,重重压力与变化之下,一己之幸福与家庭幸福、社会和谐该如何关联?活着,如何是好?如何更好?这是鲁敏小说一再逼问的现实问题。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一部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其艺术品位与思想深度的形成,固然与作家选择的主题、素材有关。但客观地说,在一个创作环境相对宽松,艺术氛围较为自由的时代,小说主题或素材的选择,并不必然与小说的思想深度或艺术品位呈正相关——写儿女情长并不见得就下里巴人,表现英雄气短未必就一定是阳春白雪。当下小说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不再是题材,主要取决于作家如何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向生活提问,即如何于平凡处见不平凡,发现并提炼出“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有效命题和艺术形式来。
现代人的个体在世感,离不开现代社会的塑造。在哈贝马斯看来,自黑格尔开创现代性的话语以来,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的耳畔。在权利和自由的现代民主政治议题下,政治权利与民主自由不再仅仅局限于公共论域的宏大叙事,此类主题还生发出了个人生活何为的附属衍生题,或者说,在政治权力与民主自由的社会镜照下,个人主体性必然会得到张扬。杜威就认为,生命是在事物之间和事物之中进行的,而有机体只是这些事物的一种。他援引斯宾塞的话说,“一个内在的秩序和一个外在的秩序是两相符合的。它意味着有一个内在的秩序和一个外在的秩序,而且也意味着说:所谓两相符合即指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秩序中的各个成分彼此关联的方式和在另一个秩序中的各个成分彼此关联的方式是一样的。”[6]这里所谓的“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既是指心灵法则与身体法则的内外有别,也是指个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确立的市场权利主体,在经济生活主题之外,必然也会寻求其权利的伸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的某些非理性行为和隐蔽的自私动机,获得了合法性的外衣。现代性主张个体权利的表达,而大行其道的市场经济也并不关心公共道德的约束,这正如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一般的道德观念可以作为一种公共的正义观念的基础。[7]既然现代民主社会中没有观念可以作为一种公共的正义观念的基础,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确立这个时代的道德观呢?
回到鲁敏的小说,如果说《惹尘埃》中肖黎的老公是罪有应得,《缺席者的婚礼》中未婚妈妈是咎由自取,那么对《谢伯茂之死》的陈亦新、《西天寺》中的符马等,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他们是道德败坏还是生活态度不端?想当然地把他们放在道德的天平上去衡量,无疑是回避并遮盖了问题的实质,也不能使我们自己的道德观有所增益。《缺席者的婚礼》中的女主人公跟还未出世的孩子结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而已,事实上是对婚姻本身(未来生活)的否定,是以一种否定历史的方式来拒绝未来,女主人公根本不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西天寺》中的符马,清明祭祀完祖父即去幽会女网友,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抛弃历史(家族血缘联系);《谢伯茂之死》中的陈亦新既看不出其对过往历史的留恋,也看不到对未来的希望,只剩下一个现时语境中的经验意义的自我,这一没有历史感的自我,通过虚构出另一个“自我”来达成对自我肉身的安放与慰藉。
在放逐了生存性的未来维度之后,理想或者说理想的生活,即“更美好的生活”又何以可能呢?理想的坚持与放弃,对任何身怀理想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两难的困境。而置身现代社会,这种两难的生存、生活处境经常不期而至,令人猝不及防,这或许是鲁敏小说要着意深刻探讨的问题。
[1] 鲁敏:鲁敏谈《伴宴》:艺术的自由与桎梏[N].人民日报,2011-05-06(7).
[2] 张翼飞,唐伟.烟火人间,白水生香——鲁敏近期中短篇小说综论[N].文艺争鸣,2013(4):152-154.
[3] 王彬彬.鲁敏小说论[J].文学评论,2009(3):115-119.
[4] 王源.新时期小说与“人”的解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0):90-94.
[5]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M].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
[6] 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07.
[7] 任平,王建明,王俊华.游戏政治观——后现代政治哲学分析[J].江海学刊,2001(5):86-89.
【责任编辑 李开拓】
Survival Dilemma of One Dimensional Man——Review of Recent Works of Lu Min
Wang Junzhong
(CultureandCommunicationCollegeofLimingVocationalUniversity,Quanzhou362000,China)
The recent four novels of Lu Min have unfolded the living dilemmas of modern people,taking different civil lives as example.The spiritual core four works actually originates from the questioning of status of ideal life and living.By reading four works,we can see that the modern people conscientiously give up the hope and see no past or future.They are struggling in the dilemma of reality for they can’t avoid the question of heart or find no satisfactory answers.
Lu Min;Survival novels;Survival dilemma;One dimensional man
I206.7
A
1009-5101(2016)06-0117-05
2016-08-23
黎明职业大学“信息传播与策划”双教能力教学团队项目(LMTD2013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俊忠,黎明职业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新闻学研究。(泉州 36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