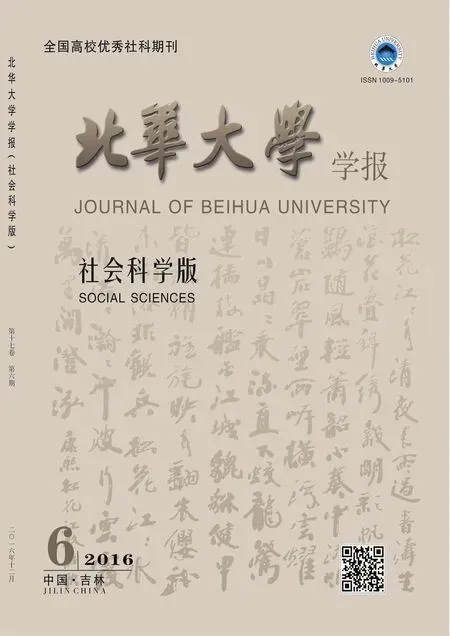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定位与转换建构
席岫峰
□哲学社会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定位与转换建构
席岫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智慧之思的硕果之一,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这门中国人国学中的“国魂学”,有自己的核心主题、研讨论域、价值取向、明理方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传统。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语境下的中国哲学经历了“学着讲”——“照着讲”——“自己讲”的过程,实现了从古代哲学观转向现代哲学观,从“单数”哲学观转向“复数”哲学观,从一般意义的哲学观转向中国特色哲学观的逻辑转换,其终极目标在于重新“认识自己”,真正建构起中国特色的主体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定位;转换建构
一、中国传统哲学:国学中的“国魂学”
在人类诸多的古文明中,唯有古希腊、中国和印度产生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并大致诞生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即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约公元前800—200年)。在这一历史时期,古希腊人超越神话世界观,开始寻找更为合理的自然观和道德原则并使哲学日益职业化,产生了以“求知”“爱智”为取向的古希腊哲学;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产生了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印度则出现了最早的哲学文献《奥义书》和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佛教典籍。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些从宗教和神话母体中“突破”出来的思想形态,是人类文明精神的精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的“轴心”,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众所周知,哲学脱胎于神话和宗教的世界观,但真正意义上的古希腊哲学开始于对自然的思考,力求以自然本身解释自然,它可以说是与神话世界观相决裂的产物。印度哲学则与宗教的联系十分紧密,“它可以说是对宗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精致思辨和系统论证”。[1]而中国哲学则体现出了“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和“道不远人”(《中庸》第13章)的人文理性,对宗教采取敬而远之、不置可否的态度。尽管中国也有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也很大,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的哲学(儒家思想),而不是神学(佛道二教)。在思想表达方式及风格上,古希腊哲学注重“说理”,善用论辩、推理和证明,因而思辨性强;古印度哲学可以说是一种“说教”,它是为宣讲教义服务的;中国古代哲学则是一种“说道”式的开导,所以更多的体现为“名言隽语、比喻例证”。[2]正因如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古代的希腊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并列为早期世界哲学的三大系统。
“哲学”(爱智)作为古希腊的专有名词,首先是个历史范畴,其主要特质在于它的思辨理性。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爱智)这个词汇或概念,中国古代哲学也有别于古希腊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虽然肯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但他又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在西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并且影响深远。直到2001年,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到上海访问时,当华东师大王元化教授问及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时,他的回应是: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3]在当代中国,也有人用这种西方哲学思维来评判中国哲学,并提出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认为哲学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从日本传入的纯粹“舶来品”,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哲学”这门学问,中国哲学是“以西范中”的产物,既无其名也无其实。这种说法不仅与人类思想史的事实不符,而且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相悖,深层地反映出缺少主体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心态。我们不能用西方近现代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和评判中国古代哲学,机械地把古代近代化或现代化。正如宋志明所言,“中国古代哲学属于前近代的哲学理论形态,因而中国古代哲学家不可能像西方近代哲学家那样自觉而清晰地意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不可能依据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来构筑学说体系。”[4]3
尽管“哲学”一词是外来语,但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在中国古以有之是不争的事实,虽说“名殊”“目异”“旨别”,但其理相通,功用是一样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只是哲学的哲学’,只存在着‘带前缀的哲学’,如中国哲学、欧洲哲学、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等等”。[4]3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使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老子《道德经》全书81章,直接谈到“道”的有77章,“道”字出现74次,是老子哲学的一个最高范畴。“道”字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共出现了89次之多,只不过“一以贯之”的是“道不远人”(《中庸》第13章),智慧之思的重心由“天”转到“人”,实现了“信道”“求道”上的思维转换。儒家《易传》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辩,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也就是说,“西方的‘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换言之,在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一层面,中国‘性道之学’与哲学呈现了一致性”。[5]4-5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史中独立发展的主要哲学形态之一,这门学问在中国古代曾称为“道”“道术”“玄学”“道学”“理学”“心学”,它以华夏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阐述了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理念,“是中国人‘爱智慧’的独到方式,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乃是国学中的国魂学”。[4]145所以,在对中国哲学“现代学科”“民族文化”“生命智慧”的综合考量中,仅仅以纯粹的“知性探究”的态度解析“中国哲学”是不够的,它的第一层面是 “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蕴含着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是当代中国人仍然活着的安身立命的民族精神和人生智慧,而不仅仅是“作为学科建制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6]1
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特色及其价值定位
哲学与科学相比较,面对的不仅是自然世界,而且关涉人们的精神世界,同特定的民族主体和思想者个体密切相关。海德格尔讲:“存在”在“此在”间。所谓“哲学”终归是特定的民族主体及其思想家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的深度思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它是开放的话语体系,不存在一门纯抽象的哲学,不存在唯一范式的哲学(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等。近代以来,新儒家梁漱溟的新孔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以及中国现代分析哲学代表金岳霖的新道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学着讲”出来的中国哲学,并没有使中国传统哲学走出困境,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哲学”。牟宗三试图重建的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张立文的“和合学”、张全新的“塑造论哲学”,试图通过“自己讲”和“以中解中”方式建构主体性的中国哲学。而事实上,正如宋志明所言,“‘中话中说’在当下是谁都做不到的事情。”“关键在于‘人话人说’:用现代中国人能懂的语言表述中国哲学的精义”。[4]135也就是说,从中国哲学的具体实际出发,“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中国哲学概念、范畴间的‘哲学逻辑结构’——分析、梳理、诠释中国哲学”。[7]
中国哲学之特色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一直在关注的话题。张岱年曾在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问题)》概括了中国哲学的6条特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不重知论”“重了悟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宋志明则突出强调了中国哲学的“4个特有”:即特有的哲学形态(以解释价值为主题,不以解释世界为主题),特有的思考进路(从“人生”入手,不是从“存在”入手),特有的重行传统(注重人生实践,不太看重理论体系的建构),特有的安顿方式(主要功能是指导人生、安顿价值、成就理想人格,西方人精神生活的价值安顿主要是由神学来承担的)。[4]145-152这些认识应该说大同小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中国哲学的特色是“自我观照”与“他者观照”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应该从“中理西说”——“中理中说”——“中理通说”的探索转型。所谓的“通说”,就是要总结梳理前贤的研究成果,会通中西哲学思想及其表达方式,把我们心之所愿的“自己讲”“讲自己”,让当下的中国人能理解,让西方人也能认同。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其一,思考主题聚焦“天人之际”和“性命之源”。现在通行的说法,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以世界整体及其普遍性为对象。但在中国古代先哲的眼里,世界是以“人”为圆心,“天”“地”“人”一体的世界,而且相互感应交通。也就是说,“人”和“世界”浑然一体,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所以,中国哲学思考探索的核心主题是“人”。无论是孔子讲的“仁”、孟子重的“义”、荀子说的“礼”,其实都是在讲“人应当怎么样”。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人。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至于庄子哲学,反对“人为物役”,追求“人的自由”,而人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即便是继承的道教也是看重人的“长生久视”。中国的禅宗认为,“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六祖坛经·疑问品第三》)指出的是“人性”就是“佛性”。一言以蔽之,讲的都是“人事”。所以,探究“天人之际”“性命之源”,始终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最大主题,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阐述了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西方哲学则主要聚焦在人之外的“世界”上,从而把世界分成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是相分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思考的世界改变了苏格拉底面向“人间”的取向,而是一个对象化的“理念世界”。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又使知识问题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强调的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人”本身。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探求的不论这个世界是精神本体还是物质本体,都是一个对象化的世界。总之,西方哲学追问的指向在于存在的“事实的世界”,从“自然”——“实然”——“本然”(或者说从具体的“多”——抽象的“一”——“理念”或“精神”的“本体”),总在试图“刨根问底”的探求世界的“唯一”或“根本”的“真像”;而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指向意义的价值世界,从“自然”——“应然”(从敬畏天命——顺天应人),主要是回答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人世变迁的道理以及生命的智慧和人生的价值。
其二,研讨论域主要是“人生修养”与“政治伦理”。中国传统哲学的话题主要有:“天命”“天人”“道”“德”“善恶”“和同”“义利”“治乱”“礼法”“名教”“自然”“知行”“心”“性”“气”“理”“阴阳”“五行”“变易”等,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宇宙演化、道德修养、政治伦理、国家治理等。西方哲学的话题主要是:“自然”“本原”“存在”“实体”“主体”“理念”“形而上学”“知识”“真理”“逻各斯”“德性”“认识你自己”等,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世界的本体问题、认识问题等。这种讨论话题的不同,直接反映哲学追问的论域的差异性。总的来说,西方的哲学体系主要涉及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方法论;而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实质性的内容而言,主要涉及的是“人的身心修炼”“国家的长治久安”方面的问题,所以,儒家才会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连在一起,列为人生修养的“八目”,实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冯友兰或张岱年曾套用西方哲学的说法,讲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涉及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致知论),其实,主要是“人生修养”与“政治伦理”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三,价值取向重在“成人成圣”“天人合一”。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句话就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西方哲学以“爱智”为取向,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辨识“真”与“假”,“实”与“真”,突显的是世界“本然”之义,重在“求知”和揭示“真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中国哲学的取向在于“问道”“闻道”“求道”“知道”“明道”,把“止于至善”作为最高目的,体现了“致知”与“求道”的统一。孔子倡导的是:“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把“仁”“义”的价值判断作为衡量是与非的主要标准,强调是“应然”之义,而不是“本然”“实然”本身。正如《大学》开篇所言:“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成人成圣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用儒家《易传·象传上》的话讲,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至于怎么合一?老子讲的法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孟子指的心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而庄子给的心得是:“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
其四,明理方式讲究“顺天应人”“知行合一”。海德格尔曾用“是什么”来概括西方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例如,他们问:这是什么——美?这是什么——知识?这是什么——自然?这是什么——运动?”由这个“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哲学被引导到对存在者的实质、所是、本质乃至于其“第一原理和原因”的探讨。[8]苏格拉底和美诺的对话主要就是为了给美德下定义。西方哲学从自然哲学的视角看世界,把主体与客体分开,选择分析的进路,注重一个“证”字,具体表现为以论辩、证明、推理等的说理为主。这可能由于从事哲学研究在古希腊是一种独立的职业,不像印度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那样属于官宦阶层,促进了古希腊主体思辨精神的发展。中国哲学从人生哲学的视角看宇宙,讲究“顺天应人”“知行合一”之道,选择综合的进路,注重一个“悟”字,主要是通过生活感知、实践体认、内心感悟,把握人世间的“道”或“理”,很少直言不讳、直奔主题,而且多用警句箴言、引证比喻,冯友兰称之为“名言隽语、比喻例证”。中国传统哲学历来强调:“大道至简”,主张“言简意赅”,而不是繁琐的论证,总是力图用简练、形象、生动的表达,说明人生大道的哲理。正如老子所言“道”的至高至极境界时,引用了“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道德经》第四十一章),表述上自然要契合“为学日增,为道日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的要义。
总的来说,源自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主流是自然哲学,而且是一种思辨哲学、认识哲学或科学哲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世界观的学问。至于人生问题,西方人则主要是由神学来解答的。由于用认识论的眼光看待世界,以怀疑事实的存在为哲学思考的起点,“从存在出发,寻求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也可能追寻到超自然的彼岸,追寻到上帝那里。这或许就是古希腊哲学不敌基督教的原因,是哲学沦为神学婢女的原因,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哲学比较发达的原因”。[4]148中国人的人生情结自古以来就非常重。《尚书·皋陶谟》上讲:“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孔氏传》解释说:“哲,智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爱则民归之。”中国传统哲学是从人生论的眼光看世界,以“乐天知命”的态度肯定现实的存在为哲学思考的起点,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是生命的智慧、生活的艺术、治理的谋略,是融为一体的人生观与世界观、道德观与政治观,这种“顺天应人”之道,体现了为学与为人、求知与求道、修身与修心、治学与治国的内在统一性。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尽管相对独立存在,但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儒学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宗教不过是配角而已。
三、近代以来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哲学观转换
在中国的传统学术分类中,的确没有一门被称为“哲学”的学问。作为“爱智”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学人是在16世纪开始接触到的,他们把“哲学”译为“爱知学”。1631年,由耶稣会士傅泛济意译、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开宗明义首论篇章即“爱知学原始”。1874年,日本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将西方的“philosophy”译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之学),后来简称“哲学”。中国学者黄遵宪最早在《日本国志》(1895年刻本)使用“哲学”这一词汇。梁启超等人在其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晚报》上,评介西方哲学及中西思想的文章中多次引用并传播“哲学”这个译名。1901年蔡元培根据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哲学词汇》中关于哲学的定义(基本采用西周所译的哲学术语),撰写《哲学总论》,专文论述了哲学的性质与其他各门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一词在中国日渐通行。实际上,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哲学观,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建构实现了几次重要转型和突破。
(一)从古代哲学观转向现代哲学观
所谓古代哲学,指的是“一切学之学”,即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式的综合之学。这是一种广义哲学观。古代哲学家没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古希腊哲学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凡是能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各种问题,都是他们哲学追问和思考的对象,与科学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类似,也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公元前5世纪,这种朴素的哲学观既出现在古希腊,也出现在中国。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弘道”“穷理”“尽心”“知性”“求是”等,与“爱智”的意思是非常相近的。所谓现代哲学观,是狭义上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指的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在西方,这门学科产生在17世纪,在中国则出现在20世纪初。适应当时中国教育和学术研究以西方学科分类为模式的现代转型,“哲学”在中国应运而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学人参照西方哲学,开始梳理提炼传统学术思想中的哲学史料,如冯友兰所言以“照着讲”方式着手建构中国哲学。1912年京师大学堂(后改称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以“中国哲学史”为主干课程。蔡元培这一时期所写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大纲》等论著,已经区分开了这两种不同的哲学类型,对于现代哲学的学科性质有了明确认识,并大力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
(二)从“单数”(专有)哲学观转向“复数”(类称)哲学观
对学科意义上的狭义“哲学”理解,近代中国以来主要有5种不同的观点:一为“意义说”。即侧重哲学对于人生意义上的理解。如胡适认为,“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9]二为“道理说”。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哲学是说出或写出之道理。”“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10]这种观点把哲学理解为形而上追问的无论东西方都普遍讲的同一个“道理”,包括宇宙论(世界之道理)、人生论(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知识之道理),是“一种单数哲学观”。三为“学问说”。这是张岱年的观点,认为“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11]按照“学问说”,哲学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哲学作为“类称”,只能借助各种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不能以西方哲学标准来裁量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也没必要套用西方哲学。[4]65四为“游戏说”。金岳霖认为,“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成是成功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12]冯友兰晚年也接受了哲学复数观点,认同金岳霖的“游戏说”。五是“实质说”。这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中国虽然没有“哲学”之名,但有“哲学”之实。如杨国荣认为,“历史地看,在实质层面上以智慧的形式把握世界,很早就出现于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并不仅仅为西方哲学所独有。”[5]1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复数哲学观。从“意义说”——“道理说”——“学问说”(“游戏说”或“实质说”),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对“哲学”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体现了“哲学”理解上的中国特色,其目的在于给中国哲学的建构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三)从一般意义的科学哲学观转向中国特色的主体哲学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讲哲学的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哲学遵奉前苏联教科书的提法,被简单化定义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深,出现了教条化倾向,加之受前苏联“两军对垒”模式(即任何一部哲学史都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影响,中国哲学的研究陷于僵化、停滞甚至倒退,甚至还演化出了政治化的以“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为表现形式的斗争哲学。1978年以后,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哲学研究逐渐从“两军对垒”的僵化模式中走出来,恢复了学术自信,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气象。冯友兰重新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契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是其中带有标志性的成果。中国人对哲学的理解又有了新的认识。如冯友兰就不再坚持以往的“道理说”,认为哲学不是西方哲学讲的“自然现象学”,而是“精神现象学”,是对认识的认识。哲学的主题是人,不是物,不应该把哲学归结为解释世界的“物学”,而应视为人类自我反思的“人学”。他指出,“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13]它不是西方那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有关人的行动哲学、实践哲学,并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功用不只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而且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还认为,中国哲学既然是哲学,当然在“人类精神的反思”的范围之内,当然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有共同之处,否则就不能叫作“哲学”;“但就其表现形式说,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则有不同”。[14]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还有冯契的“转知成智”的“智慧说”,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张立文的“和合学”,张世英的“追求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等等,可以说都是试图突破一般意义上的对象化的西方哲学观,努力探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主体哲学观的有益尝试。在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新的语境下,中国哲学这种转型的超越之旅,可以说“始终在途中”,而且任重道远。
四、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转换与建构
19世纪前的中国哲学,一直是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以经典注疏为主,把握领悟及至阐发传统中的“微言大义”。以康有为等人的新今文经学为标志,中国哲学的经学时代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这个话题,经历了从“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或“自己讲”的思考过程,20世纪的“学着讲”和“照着讲”的传统哲学现代化,按照学术界的说法,是“西体中用”“以西范中”或“以苏范中”的产物,几乎就是“西化”的同义语,这种西方哲学思维模式主导下讲出的中国哲学,既没有真正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没有化为中国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心理。21世纪的当代中国,现在许多人都提出要“自己讲”“讲自己”,逻辑上没有问题,愿望也是好的,体现出了中国人主体自觉、文化自信、哲学自新的心声:建构中国特色的主体哲学。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时代转换和发展(或者说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始终“在途中”,这个任务至今没有完成。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哲学传统、讲好中国的什么传统,当然还有如何讲的问题,要用当代中国人能理解、好接受的方式,包括让外国人能够听得懂的思路和语言来讲。
谈“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何谓“传统”?这是传统转换的前提。笔者理解,所谓“传统”其义有三:其一,是指传承下来的和能够传承下来的东西,是“活下来的”,不是“死了的”,它连接着过去,存活于现在,也包蕴着未来,通俗地讲,传统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所以,“传统的”不等于“过去的”。其二,是传承下来的既包括“中国的”本身所固有的原生态的东西,同时也包括曾经是外来的但却被“中国化了的”东西,如中国佛教等。所以,传统的不等于固有的。其三,是传统是动态的,不是僵化的。也就是说,传统也有很强的时代性,总是在不断地“时代化”(现代化)。原有的东西在一定时期被世人理解、认同并积淀成了社会心理,他就成了传统;时异事迁,原有的东西不合时宜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摒弃的东西,让人淡忘了的,也就趋于消亡,“已经失忆的”就不再是传统。当然这个概念很复杂,有些“枯死的”老树,遇到了特定的条件,也会重现生机,“复活”过来的也就成了传统。辨析这个概念,目的在于澄清“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转换”是一种常态的、动态的、开放的事业,不是简单的“以西解中”或“以中解中”的解读方式问题,而是实质上的“与时转换”“创新发展”的问题,是智慧之思的超越,而不是思维形式上的符合。
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转换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从广义上讲,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识形态主导)、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转换(社会意识基础),还有中外哲学特别是中西方哲学的对话交流。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是相互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是主导的政治哲学关注的视域界。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转换,主要是涉及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或价值哲学所关注的视域界,是中国人深层的根柢灵魂。还有,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已经上百年,一些哲学理念也在影响着中国人,特别在知识阶层中,被中国人传播解读的西方哲学已然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所以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对话交流,自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时代转换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子课题。从狭义上讲,主要是历史上存活下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现代转换与创新。“认识自己”是哲学永恒的话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解读,它涉及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如何自我定义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色是什么,中国哲学的独特概念、范畴及逻辑结构是什么,中国哲学的演变路径及走向的逻辑轨迹怎么描述,如何概括中国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现实价值是什么,中国哲学思想具有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如何向外传播讲好中国哲学,等等。只有把这些说清楚,才能逐步建构起来中国哲学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哲学不是第一形态,而是第二形态。但中国人从西周时突破传统的天命观开始,哲学就始终一以贯之地在主导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主导性的东西,更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与西方社会和印度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中国人可以不是宗教的,但他们一定始终是哲学的。所以,中国哲人讲出自己的主体哲学,我们应该有历史的底蕴和文化的自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哲人主体自觉的表达。哲学家只能在他所处的时代语境下讲哲学,这是哲学的大语境。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积淀以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战略,为中国特色的主体哲学的创生,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契机。然而,哲学终归不是所有人能做的事,而是少数哲学家的事业,它需要有强烈的个体自觉,保持内心的宁静、爱智的惊奇、开放的视域、广博的阅历、立命的情怀、日新的觉解,耐得住那分清苦与孤独,唯有如此,方能承担起建构中国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使命。
[1]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
[3] 王元化.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N].中国图书商报,2001-12-13(14).
[4] 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法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 杨国荣.中国哲学十二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6] 郭齐勇.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
[7] 郭庆堂.20世纪中国哲学论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06.
[8]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592-593.
[9]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1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
[11]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
[12] 汪曾祺.蒲桥集(13):金岳霖先生[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430.
[13]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44.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25.
【责任编辑 王 坤】
Value Orie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Xi Xiufeng
(JilinAgricultureUniversity,Changchun130118,China)
Philosophy is not only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but also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life wisdom of human civilization.As one of the thinking of the wisdom of the great China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n the “Axial Age”,it is unique to the Chinese nation’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The Chines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earch in “national spirit” has a core theme,research domain,value orientation,and the way is the unique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In modern times,China philosophy experienced process of “learn to speak” ——“follow it”——“self speaking”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philosophy,realized the turn of modern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philosophy,from the “singular” and “plural” philosophy to philosophy,from the general meaning of philosophy to China characteristics of philosophy logic conversion,its ultimate goal is to “know yourself”,really build up the philosophy of subjec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Value orientation;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B21
A
1009-5101(2016)06-0028-07
2016-09-03
席岫峰,吉林农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长春 13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