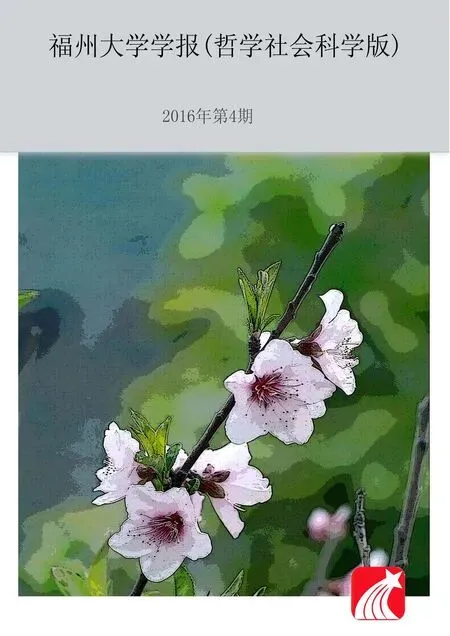《乌托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乌托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自80年前首部汉译全本《乌托邦》问世迄今,中国学界的《乌托邦》研究虽然称得上成绩斐然,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中既有若干史实的模糊与错讹需要厘清,也有个别译文和释义的歧见需要辨析。长期以来,用科学/空想的二元对立模式解释“乌托邦”成了人们的基本认知。这种解读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乌托邦》的认知视野。国内的《乌托邦》研究,亟需对国际相关学界最新成果的吸收和消化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乌托邦》; 乌托邦; 乌托邦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托马斯·莫尔
500年前,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120年前,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首次借用了渊源于莫尔的英文“Utopia”一词,精心构思了一个音译与意译巧妙结合的汉语新词“乌托邦”。80年前,刘麟生翻译的首部汉译全本《乌托邦》问世。莫尔的《乌托邦》及其“乌托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深深地扎根于这片沃土。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乌托邦》也因其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而逐渐被抹上了越来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长期以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语境里,用科学/空想的二元对立模式解释“乌托邦”成了人们的基本认知。这种解读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术界对《乌托邦》的认知视野。在近年的《乌托邦》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年,中国学界在《乌托邦》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辨析。值此《乌托邦》问世500周年之际,特举几例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关于作者托马斯·莫尔的出身与牛津求学
大凡谈到《乌托邦》都或多或少地会提及其作者托马斯·莫尔,但翻阅一下相关的生平介绍,模糊之处甚至多,或则语焉不详,或则错舛讹误。例如,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莫尔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贵族家庭,14岁到牛津大学深造。当时的牛津大学,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播中心,因此莫尔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当时在大学任教的著名人文主义者科利特、格罗辛、林纳克等人的影响,而他们也非常欣赏莫尔的才华。莫尔通过同他们的交流学到很多新知识、新思想,这使得莫尔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就莫尔的出身而论,无论是父亲一支还是母亲一脉,虽然都是伦敦的富有之家,但并没有显赫的家世,似乎都跟那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家庭扯不上关系。莫尔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中也只说自己出身于殷实之家,但并非名门望族。[1]莫尔的祖父威廉·莫尔(?-1467)是一位面包商,祖母约翰娜·乔伊是啤酒酿造师的女儿,外祖父托马斯·格劳恩格尔(Thomas Graunger)是一位蜡烛制造商。[2]莫尔的父亲约翰·莫尔(约1451-1530)是家中长子。1474年,约翰·莫尔同阿格尼斯·格劳恩格尔(Agnes Graunger)结婚,二人共生育六个孩子,托马斯·莫尔排行第二,也是家中长男,生于1478年2月6日。阿格尼斯于1499年病逝,莫尔时年21岁。[3][4]虽然莫尔成长过程中深受父亲的影响确是事实,但国内有著作所谓“莫尔幼年丧母,由父亲带大”[5]之说是没有根据的。约翰·莫尔没有子承父业,而是选择了法律职业。他于1474年进入林肯法学院,从见习律师一直做到高级律师。1503年成为皇室和法院法律顾问团成员,后又从巡回审判法官(1513)、普通上诉法官(1518)一直做到最高法院法官(1520)。约翰常常同伦敦商业区里拥有特权的商会中富有的市民打交道,并同各级官员多有往来。这也是他能够依靠自己的人脉关系把儿子托马斯安排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家里做少年仆从的一个重要原因。约翰曾获爱德华四世赏赐一枚盾形徽章,还曾受封爵士。约翰·莫尔何时受封爵士,尚无确凿证据,但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托马斯·莫尔出生之后的事情。因为莫尔出生之时,约翰27岁,刚刚进入林肯法学院四年,事业飞黄腾达尚需时日。退一步说,像莫尔这样的家庭,即便是获得爵士封号,品级也不高,只能算是属于含义非常宽泛的贵族阶层(aristocracy),而不具有出席上院的特权,即不是真正的上院贵族(peer)。
莫尔求学牛津与其成长为人文主义者的关系也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不能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莫尔在牛津期间就已成长为坚定的人文者了。莫尔入读牛津之时,英国人文主义大潮初起,而牛津大学正是得风气之先的一大思想重镇。新思潮的躁动不可能不对刚刚踏入校门的莫尔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在牛津期间对希腊文化开始有所了解并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或者说,正是在牛津求学期间,莫尔得以初窥古希腊文化的门径。但是,也不能太过夸大在牛津学习这段时间给莫尔带来的影响。此时的牛津大学仍然是经院哲学的中心,主要是供打算在教会任职的人受教育的地方。莫尔在牛津主攻拉丁文和逻辑学,也是为日后走上神学之路做准备的。经院哲学家们把学习希腊语和传播希腊文化视为离经叛道,而人文主义者则把希腊语视为打开古希腊文化宝库大门的金钥匙,他们通过课堂教学、举办讲座等方式向听众展示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世俗人文主义形象。不过,莫尔在读牛津期间,世俗教育不过初露端倪,远非主流。同时,莫尔只是14-16岁时在牛津大学待了不足两年的时间。且不说以一个十四五岁少年的身份去结交牛津知名学者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莫尔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后来与他成为忘年交的格罗辛、林纳克、科利特等著名人文主义学者除格罗辛之外都还没有回到国内,与莫尔不可能有交往,当然更谈不上对他的赏识了。即便是格罗辛,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莫尔在牛津时同他有多少往来。二人彼此熟悉发生在格罗辛成为莫尔所在的教区牧师之后,这已是莫尔离开牛津两年之后的事情了。通过格罗辛,莫尔又先后同陆续来到伦敦的林纳克、科利特、里里等人相识、相知并成为终生的朋友。莫尔之成长为人文主义者,他的学术成就和声望,都是离开牛津之后的事情。
二、关于《乌托邦》一书的出版
《乌托邦》是莫尔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的出版让莫尔声名大振,享誉国内外,这也是国王亨利八世想收他到自己麾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内个别著作说莫尔“出版了《乌托邦》,并因而献出了生命”[6]是不合史实的,何况亨利八世处死莫尔已经是《乌托邦》出版将近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乌托邦》是一部高扬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品,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开创了近代欧洲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先河,预示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乌托邦》不仅是声讨圈地运动的檄文,也是擘画理想社会的长歌,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
国内出版物提到《乌托邦》一书的出版时大都以1516年出版这一比较模糊的说法一笔带过。这一说法对于相关的专业性著作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个别著述稍微明确一点,如汉译本奥西诺夫斯基的《托马斯·莫尔传》说是出版于1516年秋。[7]目前只见到台湾版汉译钱伯斯《托马斯·摩尔》提到了具体日期,说《乌托邦》“是1516年11月1日出版于安特卫普”[8]。这三个时间点比较接近。但细读钱伯斯的著作却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在书中的另一处地方又提到“在《乌托邦》出版之前,莫尔写信给伊拉斯谟……”,而钱氏自注中则标明这封信大约写于1516年12月4日。[9]该信也间接否定了秋天说和十月下旬说。
那么,《乌托邦》一书具体出版日期究竟如何呢?
根据莫尔的好友伊拉斯谟写给胡藤(Ulrich von Hutten)的信提供的信息,莫尔是在1515年5-10月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利用闲暇时间动笔撰写这部作品的。但其间只完成了该书第二部的大部分,回到英国后才又补写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结语。[10]伊拉斯谟是莫尔挚友,1516年8月旅英期间还曾在莫尔家里盘桓半个月。当时莫尔的《乌托邦》尚未脱稿。伊拉斯谟对莫尔的这部作品应该非常清楚,也许还同莫尔进行过深入讨论。伊拉斯谟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乌托邦》的研究者也大都认同此说。国内一些著述称《乌托邦》为莫尔1516年出使荷兰期间写成[11][12][13]是有失准确的,因为莫尔出使法兰德斯的时间是1515年5-10月。
1516年9月3日,莫尔把刚完成的手稿寄给在卢文的伊拉斯谟。此时,伊拉斯谟刚从英国回去不久。莫尔在附信中表示要用“一封致我的朋友彼得·贾尔斯的信”作为序言。[14]9月20日,莫尔在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表达了早点儿既快又好地把书出版的愿望,并希望能得到一些学者并且尤其希望得到一些著名国务活动家的鼎力推荐。[15]10月2日,伊拉斯谟在信中向莫尔保证自己会竭尽全力帮助莫尔实现他的愿望。[16]
11月12日,卢文的人文主义者杰拉德·吉登豪威尔(Gerhard Geldenhauer)兴奋地致信伊拉斯谟说,出版商梯叶里·马丁(Thierry Martens)乐意承印《乌托邦》。[17]11月18日,伊拉斯谟从布鲁塞尔致信贾尔斯,告诉他书稿已到印刷商手中。[18]
12月1日,卡塞尔的约翰·马雷读过莫尔的书稿后致函彼得·贾尔斯,对《乌托邦》大加赞赏,认为该书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看到国家的美好制度的典范。他在信中力促贾尔斯尽快予以出版。[19]12月15日,莫尔在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表达了盼望早点儿拿到《乌托邦》一书的急切心情。[20]1517年1月4日,伦敦的芒特乔伊告诉伊拉斯谟自己已拿到一册,并对他表示感谢。[21]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莫尔的《乌托邦》于1516年9月初正式脱稿,并拜托伊拉斯谟联系出版事宜。其间书稿曾在一些人文主义者同道中传阅。虽然其确切出版日期仍有待考证,但大致可以确定正式出版应该是在12月的中下旬。《伊拉斯谟书信集》主编P. S. 艾伦曾推断《乌托邦》或许是作为新年献礼出版的。[22]如此说成立,《乌托邦》于12月底出版的可能性最大,但目前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因此,耶鲁版《莫尔全集》第四卷和剑桥版《乌托邦》的导论中都只把《乌托邦》的出版时间具体到1516年12月[23][24],至于具体是12月的哪一天,尚有待学界的进一步考证。
三、关于“乌托邦”一词的含义
莫尔撰写《乌托邦》使用的是当时欧洲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但其中的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大都是作者的杜撰。“乌托邦”(Vtopia)这个词本身就是根据古希腊语虚造的。
莫尔何时决定用“乌托邦”取代“乌有乡”作为书名尚待考证,但从目前保留下来的伊拉斯谟、莫尔等人之间的通信推断,这一变化大致应该是在1516年11月上旬前后。前述9月20日莫尔致伊拉斯谟的信中仍然明确使用的是“乌有乡”[26],他在10月31日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对贾尔斯赞赏“乌有乡”表示高兴,这里使用的还是“乌有乡”[27]。但在贾尔斯11月1日致杰罗姆·布斯雷登(Jerome Busleyden)的信中却已出现了“乌托邦岛”(Vtopiam insulam,英译IslandofUtopia)的说法。信中说:“前几天,大名鼎鼎的托马斯·莫尔把他的《乌托邦岛》寄给了我。正如很熟悉他的你所证明的那样,这是当代的一块瑰宝。至今,此岛仅被少数人所知,然而它比起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值得大家去了解。”[28]从目前的资料看,确切的“乌托邦”(Utopia)一词出现在前述卢文的人道主义者杰拉德·吉登豪威尔1516年11月12日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他告诉伊氏“我们的梯叶里乐意承印《乌托邦》”[29]。戴镏龄译《乌托邦》所载附录的一则注释中也曾提到这封信,但说得比较含糊,只说“‘乌托邦’这一标题最初见1516年11月12日致伊拉斯莫斯函中”[30],而没有提是谁给伊拉斯谟的信,容易产生误解。这封信说明这时书名已明确确定为《乌托邦》了。虽然有观点认为这一改变或许是伊拉斯谟的主意[31],因为书是在他的监督下付印的。但即便伊拉斯谟真有此想法,肯定也会征得莫尔的同意,而不可能自作主张。书名的改变应该是莫尔本人的主意。
莫尔之所以另造“乌托邦”一词,多半是因为Nusquamra (乌有乡)一词并不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他的意思。因为莫尔在书中所描述的名为“乌托邦”的岛,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地方,它还是一个象征着作者理想的地方。所以,莫尔在创造这个词时应该就已经埋伏着它的另一个词源,即Eutopia,意为“福地乐土”(happy land,the garden of Eden),即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王国。1518年3月巴塞尔版《乌托邦》序文部分假借乌托邦桂冠诗人之手所写的一首六行短诗中明确使用了Eutopia一词:
当年这里一片蛮荒
乌托邦被称为乌有之乡
而今它已超越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氏的梦想在此已变成人间天堂
人们完全应该改变称呼
乌托邦实乃幸福之邦[32]
考茨基早已指出,从六行诗中可以看出,把Utopia一词翻译成“乌有乡”似与莫尔的本意不符,他认为,译成“未开垦之地”(Unland)一词或许比较接近其原意。[33]这可算是一家之言。不过,西方学者确实比较早地注意到了Utopia一词的双重含意,也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乌托邦的正负两种功能。[34][35]也就是说,现代英语中的Utopia(乌托邦)一词本身应该有两个词源,即Outopia和Eutopia,因而其本身也应该有双重含意,即它既指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有之乡”,也是人们理想中的“福地乐土”“幸福之邦”,而且其侧重点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正因为如此,用“乌有之乡”、“没有的地方”解释“乌托邦”应该是不符合莫尔创造该词的本意的,至少是没有完全、准确地表达莫尔的本意。在莫尔的时代,流行使用双关语,《乌托邦》中很多词都有隐义,“乌托邦”一词也不例外。
四、关于“乌托邦”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汉语翻译
中国人接触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是很晚的事情。
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时,首次借用了渊源于莫尔的英文“Utopia”一词,并精心构思了一个音译与意译巧妙结合的汉语新词“乌托邦”。严译《天演论》第八篇的标题即是“乌托邦”,文中描述了一个众善皆备、富强平等的理想国图案:“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之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36]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严复最初的《天演论》版本,如陕西味经售书处出版的木刻本,译文中“故称之曰乌托邦”一句为“故中国谓之华胥,而西人称之曰乌托邦”。只是后来的版本中删去了“中国谓之华胥,而西人”几个字。这说明严复最初似曾有意用中国的“华胥(国)”来解读“乌托邦”,但后来放弃了这一意图。第二,严复所译的赫胥黎的原文中并无“乌托邦”一词,不仅没有“乌托邦”的标题,而且严译语句原文中用的也不是“乌托邦”,而是“人间天堂”“伊甸园”[37],这说明严复不仅读过莫尔的《乌托邦》一书,而且深谙该词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才在译文中借用了这个词。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原富》时再次使用了“乌托邦”一词:“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国俗,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烦苛,俾民自由而远近若一,此其虚愿殆无异于望吾国之为乌托邦。”[38]大概是此处斯密原文中出现了“乌托邦”(Utopia)一词的缘故[39],严复在这里特意插入了一个解释性的译者注:“乌托邦,说部名。明正德十年(一五一五)英相摩而妥玛所著,以富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此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40]严复在此处不仅明确提到了莫尔的《乌托邦》一书,而且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该词的含义。此后,严复所创“乌托邦”一词被我国学界广为采用。
中国学界最初接触到莫尔的《乌托邦》时,除严复所尝试的“华胥国”之外,还曾有意把“乌托邦”译为“华严界”。如1902年《新小说》之“哲理小说”类下的书目广告一栏出现的“英国德麻摩里著《华严界》”,译者不详。1903年3月13日的《译书汇编》刊载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斯摩尔之华严界观》一文中说:“华严界者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1906年9月5日出版的《民报》第7号上发表的廖仲恺(署名渊实)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一文,在介绍莫尔《乌托邦》一书时也说:“盖在上世宗教与共产主义常相提携……基督教诸教父之著述亦多含此理想之天国者,彼一五一六年德漠师摩(Thomas More)著《华严界》(Utopia)……”在这里,都按照佛教的理想,把“乌托邦”译成了“华严界”。但这一译法最终未被学界认同,绝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严复译“乌托邦”一词。如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兰坪著《社会主义史》提到“穆亚的《乌托邦》”,同年出版的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第二章第一节用的是“摩尔及其《乌托邦》”,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郑学稼译的美国雷岱尔著《社会主义史》一书第4章也是用“摩耳的《乌托邦》”。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麟生译的首部汉译全本名曰《乌讬邦》,只是把“乌托邦”改成了“乌讬邦”。严译“乌托邦”逐渐成了约定俗成的汉字词,其含义也不断扩展,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乌托邦”堪称中国翻译史上音译与意译结合的典范。
但西文中广泛使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一词在进入汉语语境时却发生了转化,最终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早在1907年9月,由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第6号上发表的《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就提到“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所指即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只是把作者误作马克思了。这里就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成了“空想社会主义”。不过,1912年5-7月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1、3、5、6、8期上,连载了施仁荣译的恩格斯《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标题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显然这里又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1920年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其中的“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又翻译成了“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随后的各版本《共产党宣言》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译法。此后陆续出版的《反杜林论》或者《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中,无论是吴黎平、柯柏年还是博古,只要是“乌托邦”一词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几乎都把它翻译成了空想。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译著中使用了“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语,如1930年春明社书店出版的刘下谷翻译日本人土田杏村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一书,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叶启芳翻译的德国毕尔所著《社会斗争通史,第三卷:近代农民斗争及乌托邦社会主义》,1933年南京拔提书店出版的邓季雨、钟维明翻译的德国考茨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之评判》等,但这一语汇在后来的博弈中未能占据主流。“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一直因袭下来,直到今天,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凡提及“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地方无一例外地都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非常熟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的“空想社会主义”概念,而不少人并不知道这里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实是就西文中“乌托邦社会主义”在汉语语境下的语义转换。虽然说“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今天同样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回过头来看,这一转换并不是很成功的。因为它丢掉了“乌托邦”一词最重要的一层含义。
为什么Utopia到中国变成了“乌托邦”而Utopia Socialism却转化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呢?这或许与当时两个概念传入中国的不同途径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关,“乌托邦”主要来自英语语境的Utopia,而“空想社会主义”则与其他众多政治色彩很浓的词语一样大多转道来自日语,而当时很多来自日语词汇的汉语都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日语中的汉字词,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等等,“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最典型的可以以《共产党宣言》中这一词的翻译为例,陈望道翻译《宣言》时是用英文版并借助日文版翻译的,其译文有不少地方都直接借用了日文版中的日语汉字词,陈译本《宣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很大,后来的成(仿吾)徐(冰)本、博古本、成(仿吾)译本、华岗本等都接受了这个概念。但陈瘦石译本则不同,因为陈瘦石的《宣言》直接译自英文文献,同时作为独立学者的陈瘦石翻译时也不受共产党人话语体系的约束,所以他把该词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翻译这一词汇时之所以接受日本的汉字词“空想”,显然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有所贬抑,有明显的扬马(克思主义)抑乌(托邦)之意。这与当时的政治生态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用汉语的“理想”和“空想”来翻译“乌托邦”,都抓住了“乌托邦”一词的一个方面的含义,但又都不够完整、准确,因为它们分别忽略了该词的另一方面的含义。如果一定要在这二者中间选择一个的话,应该说“理想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稍微要好一些,毕竟“理想”中既包含科学的、合理的因素,也会有幻想的、空想的成分,这都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说“空想”里面包含着科学的、合理的成份,听起来多少有些别扭。不过,如果从全面并且传神的角度,“理想社会主义”一词仍然不及“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如果说当初“乌托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时候,在中国人对它的含义比较陌生的情况下,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把它翻译成“空想”抑或“理想”尚可以理解,那么,在“乌托邦”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汉字词的今天,再用“空想”来对应“乌托邦”就显得不太够圆满了。因此,还是回到严译的“乌托邦”,用“乌托邦社会主义”来翻译Utopian Socialism比较好。
五、国内《乌托邦》研究存在的不足
首先,总体上看,中国的《乌托邦》研究和莫尔研究都比较薄弱。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佐证就是,自1935年第一个《乌托邦》汉译本问世至今,我们还没有写出一本全面反映莫尔一生的较为翔实的传记作品。已有的一些简略传记大都是在翻译其著作(其中最多的还是《乌托邦》)时译者前言里,或者其他相关著作中的简要介绍中,其中又以寥寥数百字的简介居多。[41]正是因为对莫尔生平缺乏足够的了解,我们对莫尔的一些知识非常模糊,不仅一些史实叙述不够准确,而且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也往往有失偏颇。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乌托邦》的文本研究,虽然学界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对《乌托邦》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但缺乏系统、全面、前沿的研究成果,至少在大陆,迄今尚未见到一本比较有份量的深入剖析《乌托邦》文本的学术专著。
其次,对国际学界的相关成果吸收明显不足。在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乌托邦》的研究虽然说不上显学,研究成果却也称得上蔚为大观,但国内对这些成果的译介明显滞后,吸收借鉴也很不充分。例如,对于《乌托邦》一书的写作背景、写作过程、出版情况以及莫尔的生平传记、思想解读,国外不断有新成果推出,但国内学界对这些成果却鲜有介绍,译著更不多见,致使一些新成果除少数专业人士外,多数人不熟悉或不知晓,相关认知大多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截止到目前,国内已出版《乌托邦》的各种汉译本十余种,但从这些译本对文本的解读和作者的介绍来看,除个别译本外,大多数仍沿袭旧说,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其实仅就一些译者使用或参考的英文版来看,原版中所涵载的既有研究成果也未被吸纳,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例如前述《乌托邦》的具体出版时间,其实耶鲁版《莫尔全集》第四卷即《乌托邦》卷中就有相关专家比较详细的考证[42],剑桥版《乌托邦》导论[43]中也提到该书于1516年12月出版。但这些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
再次,跨学科交流不够充分。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乌托邦》被抹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部世界名著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和代表性著作,同社会主义之间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乌托邦》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作品,文学、艺术、哲学、历史以及各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乃至科技领域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追本溯源,都会或多或少地关注《乌托邦》这部经典。由于较少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和研究视角的差异,一些学科的研究在某些方面的进展反而超前于社会主义学科领域,但却没有引起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至少没有予以积极的回应。例如,新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分别从哲学、历史、文学、语言等领域对传统的“乌托邦”的汉译及释义等相关问题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理性探讨[44][45][46],其成果是值得社会主义学科领域关注的,无论赞同与否,至少应有所回应,这样才能促进研究的不断深化。
注释:
[1][8][9] R.W.Chambers:《托马斯·摩尔》,梁怀德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3年,第44,133、151注(57),162页。
[2] George M.Logan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ThomasMor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4.
[3] George M.Logan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ThomasMor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family tree of Thomas More.
[4] John Guy,ADaughter’sLove:Thomas&MargaretMore, Fourth Estate, London, 2008. The More family tree.
[5][11] 胡凤飞:《徘徊于理想和现实之间——〈乌托邦〉导读》,见[英]莫尔:《乌托邦》,胡凤飞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6] 张造勋:《译者前言》,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造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7] [苏]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杨家荣、李兴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1页。
[10] P. S. Allen ed.et al.,OpusEpistolarumDes.ErasmiRoterodami,vol.4(1519-1521),Clarendon Press,Reissue,1992,p21.
[12] 山东大学等七院校编写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13] 高 放、黄达强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14][15][16][17][18][20][21][22][25][26][27][29] P. S. Allen ed.et al.,OpusEpistolarumDes.ErasmiRoterodami,vol.2(1514-1517),Clarendon Press,Reissue,1992,p339, p346, p354, p380, p385,p421,p425,p339,p339,p346,p372,p380.
[19][23][28][42]TheCompleteWorksofSt.ThomasMore, vol.4,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65,p26,xxxviii,p20,xxxviii.
[24][43] Thomas More,Utop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9,xi,xi.
[30]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4页注2。
[31] http://stanford.library.usyd.edu.au/entries/thomas-more/
[32] 六行短诗拉丁文原文如下:
Vtopia priscis dicta, ob infrequentiam,
Nunc ciuitatis aemula Platonicae,
Fortasse Uictrix, (nam quod illa literis
Deliniauit, hoc ego una praestiti,
Viris & opibus, optimisque legibus)
Eutopia merito sum uocanda nomine.
耶鲁版《莫尔全集》中这段诗的英译文为:The ancients called me Utopia or Nowhere because of my isolation. At present, however, I am a rival of Plato’s republic, perhaps even a alone have exhibited in men and resources and laws of surpassing excellence. Deservedly ought I to be called by the name of Eutopia or Happy Land.
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版《乌托邦》中的英译文是:
‘No-place’ was once my name, I lay so far;
But now with Plato’s state I can compare
Perhaps outdo her (for what he only drew
In empty words I have made live anew
In men and deeds, as well as splendid laws):
‘The Good Place’ they should call me, with good cause.
[33] [德]卡尔·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关其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7页注2。
[34] Mumford, Lewis.TheStoryofUtopias.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2,p15.
[35] RuthLevitas,TheConceptofUtopia, New York: Philip Allan, 1990,p4.
[36]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
[37] 严复所翻译的那句原文是:Thus the administrator might look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arthly paradise, a true garden of Eden, in which all thing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ward the well-being of the gardeners.(Thomas H. Huxley, 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London, 1911,p19.)商务印书馆1931年再版严译《天演论》时才在所加的编者注中解释说:“乌托邦Utopia,犹言理想国。第十六世纪初年,莫尔(More)氏著书言Utopia为政法尽美之国。实无其地,尽虚拟耳。”([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0页注6。)
[38][40] [英]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6-387,387(注1)页。
[39] 斯密的原文是:To expect, indeed, that the freedom of trade should ever be entirely restored in Great Britain is as absurd as to expect that an Oceana or Utopia should ever be established in it.(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A PENN state electronic classic series publication, 2005,p376.)
[41] 大陆曾出版过三部比较著名的翻译作品,一部是1963年出版的关其侗译的考茨基的《莫尔及其乌托邦》。该书翻译的文字质量非常高,但它主要以思想性见长,对莫尔生平事迹介绍得比较简略,而且该书是考茨基1887年的作品,距今已近130年。另一部是1984年出版的原苏联学者奥西诺夫斯基的《托马斯·莫尔传》,由杨家荣、李兴汉翻译。不过该书虽然汉译名为《莫尔传》,其实是作者1978年出版的一部有关莫尔的学术性思想传记,原书名直译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共产主义、人文主义、改革》,是作者1974年出版的莫尔生平传记的姊妹篇。中国读者在没有生平传记作基础的情况下去阅读这部学术性极强的思想传记,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一部是倪慧良、巫苑之译的《托马斯·莫尔》,原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作者安东尼·肯尼时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肯尼的这部作品文字简约、流畅,一气呵成,通俗易懂,可惜这个译本只印了3500册,市面上很难见得到。此外,台湾也曾译过两部可读性较强的莫尔传记。其中一部便是上述肯尼的那本传记,即王天禔译的《摩尔》,出版于1985年。另一部是梁怀德翻译的著名传记作家雷蒙德·钱伯斯的《托马斯·摩尔》,出版于1993年。钱伯斯是著名的莫尔研究专家,这部传记是他花费25年时间精心打造的一部力作,出版于1935年,是一部世界公认的有关莫尔的经典性传记。把这样一部资料详实、文笔洗炼、观点持中的厚重作品译介给国人,堪称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情。不过,两部译著都在台湾出版,大陆除一些图书馆偶有收藏外,市面上很难见到。这对广大大陆读者来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2014年底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本文作者所撰《莫尔》一书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算得上较新的一部莫尔传记,但限于丛书主旨及篇幅的限制,该书仍然未能全面、翔实地反映莫尔一生的全貌。
[44] 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45] 阎照祥:《小议传统“乌托邦”释义的偏颇》,《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
[46] 周春生:《对莫尔乌托邦政治理念的新认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余 言]
2016-05-18
蒲国良, 男, 河南柘城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D59
A
1002-3321(2016)04-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