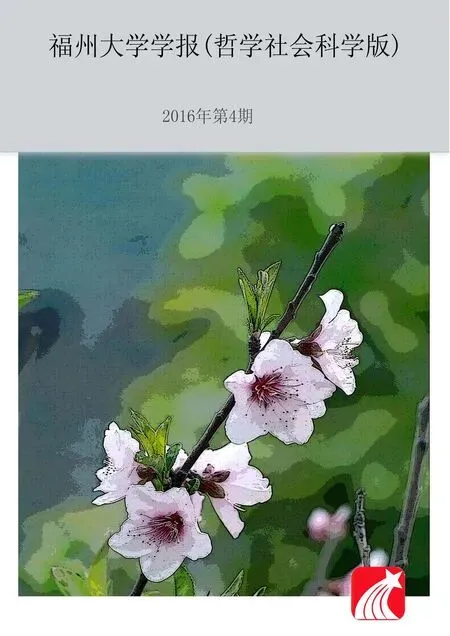论苏轼文对欧阳修的效法与超越
洪本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62)
论苏轼文对欧阳修的效法与超越
洪本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62)
苏轼效法欧公,尊崇韩愈,以文明道,关注现实,为文平易自然。他不仅对欧公心悦诚服,而且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可喜超越,表现在:坚持文道结合而更注重文,展现出神入化的散文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集大成而自铸精品的伟绩;景情事理融为一体的随意挥洒,显创作境界之无与伦比;落笔由欧阳修的“平易”,走向不懈追求的“畅达”。
苏轼文; 欧阳修; 效法; 超越
宋文六大家中,苏氏父子占了三家,辉煌的创作业绩彪炳于文学史册。在三苏父子的发愤与不懈努力之外,欧阳修对苏洵的荐引和对轼、辙兄弟的奖掖,不能不说是三苏成才并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苏氏父子对欧公怀着无限的感激和敬意,而且忠实地沿着欧公开辟的散文发展的康庄大道尽情驰骋。其中,以苏轼的成就最为卓绝,这是因为才华横溢的他不仅对欧公有心悦诚服的效法,而且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可喜超越。
从小就对欧公无比崇敬的苏轼,在登第后所作《上梅直讲书》中写道:“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苏轼又写道:“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可见其从小就对欧公五体投地般佩服。嘉祐二年(1057)礼部试苏轼为欧公所擢拔。后来,在《太息一首送秦少章》中,他回顾当年欧公对自己的赏识和称誉:“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由此可知,当时他受到何等巨大的激励,并得以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上突飞猛进,获得累累硕果。苏轼从对政坛和文坛的观察和自己的成长进步中,深切地感受到欧阳修地位的崇高、指引的正确和成就的伟大。《六一居士集叙》曰:
愈之后三百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这是苏氏对欧阳修一生的概括和总结,对一代宗师全面而公允的评价。他高度肯定欧阳修推崇孔孟之道,在韩愈之后排除万难继续复兴古文的业绩;高度评价欧阳修步入政坛与文坛,为改变萎靡不振的士风和培养众多优秀士人所作的杰出贡献;高度赞扬欧阳修诗文创作堪与古代最著名的大家相媲美的巨大成就。
像欧阳修极为尊崇韩愈一样,苏轼激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1]。韩愈亦如欧阳修而成为苏轼十分敬重的人物。像韩、欧秉持文道结合的观念一样,苏轼同样是以文明道,不作空文。他自然也接受了两位大师的影响,韩欧文的雄奇奔放与委婉从容,他都有所吸收。他效法欧文的平易自然,使之成为后世遵循的主流文风,而不可逆转。他赞同并实践欧阳修发起对骈文的改革,对宋四六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也和欧阳修一样,为宋文体裁多样性的发展,在创作上起了表率作用,他的序跋、书简、笔记等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更为可喜的是,欧阳修鼓励自己的弟子充满个性的自由发展,而苏轼对欧阳修也不是亦步亦趋,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扬己之长,自具特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创作的若干方面,实现了对恩师的超越,主要表现在:
一、坚持文道结合而更注重文,展现出神入化的散文艺术
秉持文道结合的理念,但十分注重文的价值,史无前例地突出散文艺术的重要性,是苏轼与包括他所敬重的欧公在内的同时代作家的有所不同之处。欧阳修的文道观,在他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与乐秀才第一书》《与荆南乐秀才书》《答吴充秀才书》等和曾巩的《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均有较详尽的论述,他主张文道并重,强调道亦重视文,没有偏废,肯定文的艺术价值。当然,他也讲过“道胜者文不难于自至”[2]的话,似有重道轻文之嫌,其实“不难”并非“必然”,倘若综观欧公的文论,不应产生这种误解。当然,毫无疑问,苏轼比起他的恩师来,对文的强调和重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首先,苏轼对道的理解已经突破儒家强调的孔孟学说的范围,往往扩及自然、社会中的万物,表现出对客观规律的积极探究。如《日喻》言水之道:“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也。”显然,“水之道”指的是水的客观规律。《书李伯间山庄图后》曰:“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这里的“有道”,应是掌握物理的意思。无疑,苏轼的道已不等同于传统的儒学观念,亦非政治家的治教政令,更非理学家的心性之说,以致朱熹断定他只是一味为文,到需要的时候,方去讨一“道”来[3]。在韩、柳、欧、苏四家中,苏轼之道内容最是深广,他对道的理解也最为宏通。
其次,苏轼不是高谈只为明道而为文,而是强调“有为而作”。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强调文人士大夫不为空言,“言必中当世之过”,起“疗饥”“伐病”的作用,因此,他深叹“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4]。苏辙亦称赞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5],“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6]。我们看到,他因好言时弊,故元丰不见容,元祐不见信,绍圣更遭无以复加的摧残。前人不是没有主张文应针砭时弊,但像苏轼这样毫不犹疑地将明道定位为杜绝“空文”“有为而作”,亦即在文道结合上,比起欧公的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7],更加旗帜鲜明地赋予“明道”以“必中当世之过”的社会功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再说,应该如何为文呢?苏轼《答谢民师书》曰:“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说》又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可见苏轼坚持并提倡不拘一格、出神入化的散文艺术,赞赏并追求文的独立性及其美学价值,重视散文创作随心所欲的技巧。苏轼还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8]焦竑称赞曰:“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快心也。”[9]苏轼把文学视为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充满“快意”的事业,从发掘散文艺术瑰宝中领略了无限的乐趣。苏轼指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决非一夫所能抑扬”[10],这是对散文客观存在的美学价值的充分肯定。苏轼不遗余力地探讨散文创作的艺术技巧,总结出随物赋形而姿态横生、胸有成竹而意在笔先、身与物化而神与物交等诸多超越时辈的创作经验,和他的大量散文精品一起,成为后人珍藏、学习的宝贵财富。
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集大成而自铸精品的伟绩
苏轼在散文创作上能集前人之大成而加以发展,取得骄人的成绩并不是偶然的。他从小以父为师,勤奋学习,收获甚丰。其父苏洵熟读“《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11],“大究六经、百家之说”[12],对“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醇,迁、固之雄刚”[13],皆深有所悟。苏轼耳濡目染,得益匪浅,故杂取百家,学问广博,对文学性强的著作,尤为喜爱,说:“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14]又说:“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15]苏辙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16]博观约取,融会贯通,自铸宏文,这就是苏轼的创作。故商辂评三苏云:“庄之幻,马之核,陶之逸,白之超,苏氏盖集大成云。”[17]此评苏轼最是当之无愧。
苏轼的“集大成”是在学习继承文学遗产精华的基础上,求变出新,自成一家的。他以书法为例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18]崇尚自然,立主变革创新,而文臻化境的苏轼,决不拘守什么凝固的现成的法度,理所当然地反对一家之学,反对用一种模式来限制和窒息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创作。《答张文潜书》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在《送人序》中,苏轼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他反对千篇一律,不断地呼吁在继承传统精华基础上的创造与革新。
罗大经评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生平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19]学《庄子》《战国策》,是承继传统;“惟意所到”、痛快淋漓的写作,是苏轼创造的结果。茅坤评《留侯论》云:“此文只是一意反复,滚滚议论。然子瞻胸中见解,亦本黄老来也。”[20]“本黄老”,亦是承继传统。归有光释为“寻大头脑,立得意定”。然妙在“遣词发挥,方是气象浑成”,即“以‘忍’字贯说”[21],是苏轼得意之发挥。贾谊、陆贽的文章,亦为苏轼所喜好与效仿。轼有《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称赞陆贽“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又曰:“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对陆贽的见识与文章,可谓倾倒之至。苏轼的奏议,感情充沛,析理明快。他的《上神宗皇帝书》,李淦认为“是步趋贾谊《治安策》”[22];茅坤以为“其指陈利害似贾谊,明切事情似陆贽”[23];沈德潜则指出,该篇“极恺挚,亦极婉曲”,“贾长沙之雄恣,陆宣公之整顿,兼而有之”[24]。当然,才气奔放的苏轼并非一味模仿前人,而自有鲜明的特点,故刘大櫆曰, “宣公止敷陈条达明白,足动人主之听”,此文“虽自宣公奏议来,而笔力雄伟,抒词高朗,宣公不及也”[25]。博闻多识、善取善创的苏轼,并非只学一家,《孟子》的气势磅礴、雄辩有力,《庄子》的汪洋恣肆、诙诡奇妙等特点,在他的文章中都时有所见,故刘熙载云:“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26]
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欧阳修,都是苏轼十分敬重的人物。苏轼的为文自然也接受了两位大师的影响。韩文的雄奇奔放、气盛言宜,欧文的平易流转、从容不迫,苏轼都有所吸收,且融汇于自己的创作中,因而,他的那些行云流水般挥洒自如的作品,兼有韩、欧的长处。昔人以“奇”“粹”之类称韩、欧,而以“博”誉苏轼,当是看出苏文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的特点。可以说,苏轼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集大成而自铸精品的伟绩。
三、景情事理融为一体的随意挥洒,显创作境界之无与伦比
苏轼作品的随意挥洒,表现在他的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莫不得心应手,精彩绝伦;而实现景情事理的自然交融,可谓天衣无缝,真有天工之巧,天成之妙。
苏轼注意观察生活,又有如椽的健笔,故能随物赋形,神态尽出,写景记人,莫不皆然。《放鹤亭记》写景:“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以“大环”形容“四合”之“冈岭”,十分贴切;西面地势平坦,如环之缺口,“适当其缺”,极巧妙而确切地点明“山人之亭”的地理位置。“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以凝练的笔墨,通过景色和气候的变化,勾画出迷人的大自然。山人之鹤,或立或飞,随心所欲,山人隐居的乐趣自在不言之中。
《方山子传》记人:“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岐亭邂逅,始料未及,“矍然”刻划出方山子惊异的表情。得知苏轼贬官黄州的情况后,他的神态耐人寻味:“俯而不答”,是陷入沉思,为友人而不平,无限感慨尽蓄于胸中;“仰而笑”,是看透世事和豪爽不羁的写照。由苏轼的耿直忤世,他再次确认自己由侠入隐为正确的选择。至于“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的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方山子自甘清贫的旷达胸襟。
苏轼的抒情不假雕饰,发自肺腑,《祭欧阳文忠公文》云:“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祭文按欧公“未用”“既用”“释位而去”“请老而归”四个时段,用逐层递进的手法,叙写天下人对欧公的期待和祝福,“孰谓”二句,痛惜欧公骤然仙逝,又连用两句反问表达失去欧公的无限悲痛,抒情可谓淋漓尽致。茅坤评曰:“欧阳文忠公知子瞻最深,而子瞻为此文以祭之,涕入九原矣。”[27]
苏轼的议论亦震撼人心。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发端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盛赞“塞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的威力,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正是浩然正气的体现。在抨击昏君佞臣的同时,颂美韩愈感天动地的诚心。全篇感情充沛,纵横挥洒,充满了雄浑的气势和强烈的感染力,以致洪迈发出“大哉言乎”的感叹,极为佩服地说:“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28]
更值得人们敬佩的是,苏轼在他的诸多佳作里,熔写景、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用笔若天马行空,当行当止,操控自如,落墨即自由挥洒,云卷云舒,仪态万端。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记“苏子与客”泛舟夜游赤壁,风平水静月明,令人陶醉,飘飘欲仙;然而悲凉的箫声引出“客”对曹操和赤壁之战的遐想,并由此生发宇宙永恒、人生短促的喟叹;于是“苏子”就宇宙人生“变”与“不变”的问题展开一番议论,终于使“客”转悲为喜,得以超脱。文章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又由情入理,情理相生。写景展示了可资议论的生动形象,议论又发掘了景物的潜在意蕴,而抒情则成为贯通全篇的脉络。风水月紧扣不离,乐悲喜一波三折,情境理融为一体,使这篇名赋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谢枋得赞此篇“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潇洒神奇,出尘绝俗,如乘云御风,而立乎九霄之上。”[29]李调元指出:“苏东坡前后《赤壁赋》,高出欧阳文忠《秋声赋》之上。”[30]
需要指出的是欧阳修虽然吸收老庄鄙弃荣利、全性保真的观念,但笃信儒学是其思想的主导。而苏轼的思想为三教兼容,释、道二教的濡染对其散文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从东坡文谋篇布局的虚实相生,出入变化,直至用词造句上的驱遣佛典、化用老庄,均可看出。《前赤壁赋》“客亦知水与月乎”一段,紧扣水、月谈变与不变的道理,颇为辩证,清人储欣誉之为“出入仙佛”[31]。段末“而吾与子所共适”之“适”,多种古本作“食”,因佛经有“风为耳之所食,色为目之所食”语,东坡盖用佛典也。[32]当然《秋声赋》中必须善待生命、自我珍重的意识,也可以看出老庄思想对欧阳修的影响。
篇幅短于《前赤壁赋》的《喜雨亭记》亦魅力无穷。在点出“亭以雨名,志喜”的主旨,叙过作亭、降雨、庆喜的情况,并发了一通喜从天降、意义重大的议论之后,又以一段颂雨之歌抒情。作者信笔而书,触处皆春,幽默中见乐民之乐的情怀。楼昉评曰:“蝉蜕污浊之中,蜉蝣尘埃之外。”[33]吴楚材、吴调侯评曰:“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34]
《记承天寺夜游》篇幅极短,也是信笔挥洒而美不胜收: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短短八十多字,先记事,次写景,后发慨,一气呵成,诗情画意交织,生动地展现出身处逆境的作者那惆怅不平的复杂心境。至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谈艺术,忆亡友,述交往,寄哀思,有诗有赋,有笑有哭,叙议抒情,熔于一炉,真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苏轼自评其文云:“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35]晚年作于海南的《书上元夜游》即是例证: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远贬海南是政敌无以复加的迫害,但苏轼坦然面对,随遇而安。“老书生数人”来邀共赏“良月嘉夜”,遂“欣然”同游,足见作者之随和与因缘自适。“步”“入”“历”三动词引出愉悦的上元夜游过程,“民夷”三句再展现当地淳朴的民风和尽兴而归的心境。“放杖而笑”以下是发慨,用“自笑”答幼子苏过之问,抒写自己因耿直不阿被贬至天涯海角之不悔和对小人不择手段的打击的蔑视。又引出韩愈之语意,表达自己的无奈,回应前文“孰为得失”的发问,洒脱中隐含着落寞。这是叙事简明而畅抒胸臆的短篇,亦即“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的杰作,东坡已然臻于无与伦比的创作境界。
无疑,这和苏轼当年的人生处境和精神境界相关。与欧公晚年虽遭诬陷仍身居高位而后退老颍州相比,苏轼已陷缺医无药、食饮不具、至为难堪的窘境。在海南,晚年的东坡有很多“和陶诗”,像陶渊明一样,表现出绝不折腰而以自由洒脱为傲的崇高人格,这种人格光辉也必然投射到他的散文创作领域中来,成为造就“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的崇高艺术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落笔由欧阳修的“平易”,走向不懈追求的“畅达”
欧阳修继承王禹偁“传道明心”之文应“句之易道,义之易晓”之说[36],提出“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主张[37],又在《与王介甫第一书》等文中,强调作文必须“自然”。在文坛领袖身体力行的推动下,平易自然遂成为宋文发展的主流,这是欧阳修对整个古代散文发展做出的极其重要的贡献。
“平易”表达的是平顺、平正、易知、易明之意;“自然”表达的是不做作、不牵强、不怪异、不拘束之意,行文理当如此。苏轼不满“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也反对“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之作[38],完全赞同欧公的理念。可见,就“自然”而言,欧、苏完全一致;在行文用语的“平易”上,苏轼还有更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与王庠书》云:“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答谢民师书》又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这是他对“求物之妙”的要求,也是他对当行当止,舒卷自如,行云流水般创作境界的追求。正因为有如此自觉的追求,故苏轼的笔触已由平易而臻于畅达。他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纯属信笔而书,十分随意,通俗生动,趣味盎然,特别是晚年的作品,看似平淡,实则隽永,毕现炉火纯青的艺术。在书札、杂记、序跋等文体中,苏轼的语言不假雕饰,却分外畅达灵动,个性色彩浓烈,极受读者喜爱。
《记游松风亭》写道: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作者深感自己如“挂钩之鱼”,受尽磨难而无法解脱,就像朝松风亭所在的山上攀登,目标可望而不可即那般。经过“良久”的思索,他顿悟出半山腰亦可休息的道理,如同“兵阵相接”之际,“也不妨熟歇”一样。作者以登山喻仕进,以战场比政坛,阐明了自己置进退荣辱于度外,身处逆境,随遇而安的豁达的人生态度。尺幅短章中,用语通俗、畅达、隽永,包含着鲜活的思想内容、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十分深刻的哲理,有无限的意味,却不假雕饰,明白如话,“恁么”“熟歇”等口语,亦入文中,别有风味。
东坡的题跋、书简、笔记数量远超过欧公,皆以畅达、灵动、通俗、口语化而耐人寻味。《书吴道子画后》是一篇精警动人的画论:“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对于吴道子的画技,既有“如以灯取影”等形象评价,又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等抽象论述,还动用了《庄子》的典故加以称赞,内涵极为丰富,“逆来顺往”“各相乘除”等皆极顺口,通俗晓畅而又活泼生动。
东坡六十岁时在惠州作《答参寥》一书: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得死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远贬南方的政治迫害未能使苏轼屈服消沉,他以无比蔑视的口吻述及苦难,以旷达的态度对待坎坷的人生。行文完全口语化,以“灵隐天竺和尚”的妙喻,“何尝不病”“何必瘴气”的反问和“国医手里,死汉尤多”的谐谑,“更不能细说”“便过一生也得”等拉家常的话语,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宣泄满腹的牢骚,同时抒发自己不向命运低头的气概和万分洒脱的情怀。
笔记文《二红饭》也写得饶有趣味:
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日夜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
此篇写的是贬官黄州时的生活,纯属口述其事,通俗之极,寓苦涩之情于诙谐的描写中。大麦为粗粮,不如粳米精细,故“嚼之啧啧有声”,又有“甘酸浮滑”之味,小儿女开玩笑,说是“嚼虱子”。更妙的是“杂小豆作饭,尤有味”的自我宽慰,及“老妻大笑”称“新样二红饭”之妙语,将苦中作乐的情怀调侃一番。
概而言之,苏轼对欧公不仅有学习与效法,更有超越与创造。笔者对吕祖谦编《皇宋文鉴》和《古文关键》、楼昉编《崇古文诀》、谢枋得编《文章轨范》四书的选文统计中,发现苏轼入选数量已以162篇超过欧阳修的132篇。而在元明清9个选本中,除茅坤与张伯行各自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和陈兆崙的《陈太仆批选八家文钞》外,其他选本(元杜仁杰《欧苏手简》、明唐顺之《文编》、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清徐乾学《古文渊鉴》、爱新觉罗·弘历《唐宋文醇》、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所收苏文数量皆超过欧文。[39]两位大师在古文创作上的传承,真切地显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堪称北宋文坛上引人注目值得称道的佳话。
注释:
[1] 《苏轼文集》卷一七《潮州韩文公庙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509页。
[2][7] 《欧集·居士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书》,四部丛刊本。
[3] 《朱子语类》卷一二六:“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清同治壬申刊本。
[4] 《苏轼文集》卷四九《与王庠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2页。
[5][6][16] 《栾城集·后集》卷三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21,1414,1421页。
[8] 何 薳《春渚纪闻》卷六“文章快意”条,学津讨原本。
[9][17] 见杨慎原选、袁宏道参阅《嘉乐斋选评注三苏文范全集》卷首,扫叶山房1919年再版石印本。
[10] 《苏轼文集》卷五三《答毛泽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71页。
[11] 苏 洵:《嘉祐集》卷一二《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12] 见《欧集·居士集》卷三四《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3] 苏 洵:《嘉祐集》卷一一《上田枢密书》,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9页。
[14] 见许 顗:《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6页。
[15] 《苏轼文集》卷六〇《与侄孙元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42页。
[18] 《苏轼文集》卷六九《评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3页。
[19] 《鹤林玉露》乙编卷三《东坡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页。
[20] 《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一四,皖省聚文堂重校刊本。
[21] 《文章指南》信集,清光绪二年闰五月皖江节署刊本。
[22] 《文章精义》,王水照:《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0页。
[23] 《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三,皖省聚文堂重校刊本。
[24] 《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一八,清光绪壬寅年孟夏宁波汲绠斋石印本。
[25] 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23年。
[26] 《艺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页。
[27] 《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八《祭欧阳文忠公文》评语,皖省聚文堂重校刊本。
[28] 《容斋随笔》卷八《论韩公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7-108页。
[29]《文章轨范》卷七,清同治五年刊本。
[30] 《赋话》卷十,《丛书集成》本。
[31] 《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一四《前赤壁赋》评语,清光绪壬辰湖北官书处重刊本。
[32] 见王水照《苏轼选集》第386页注释(23)“共适”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3] 《崇古文诀》卷二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 《古文观止》,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第489页。
[35] 《苏轼文集·佚文汇编》卷四《与二郎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23页。
[36]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八《答张扶书》,《四部丛刊》本。
[37] 《欧集·居士外集》卷一六《与张秀才第二书》,四部丛刊本。
[38] 《苏轼文集》卷四九《谢欧阳内翰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3页。
[39] 夏汉宁:《从历代古文选本看欧阳修散文的经典化过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6-04-23
洪本健, 男, 福建福州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I206.2
A
1002-3321(2016)04-007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