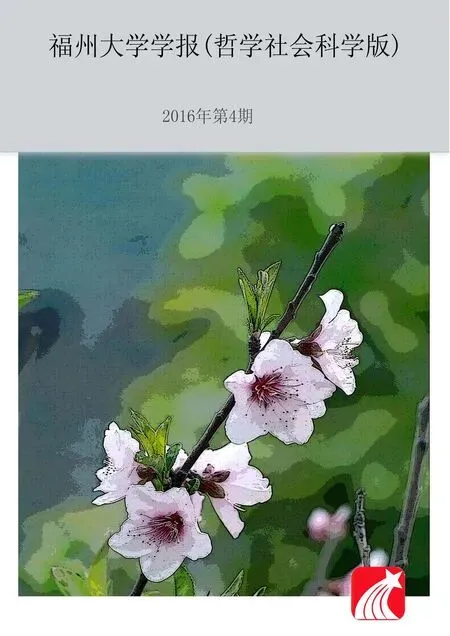顾恺之“传神论”的意涵及承传研究
宫旭红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福建福州 350121)
顾恺之“传神论”的意涵及承传研究
宫旭红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福建福州 350121)
顾恺之的“传神论”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形写神”是统摄其他几个方面的核心。从顾恺之的“传神论”开始,“传神”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审美和品评的标准。从“传神论”的思想铺垫——玄学语境、“传神论”中的形神之辩、“传神论”的承传理路、“传神论”的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展开详细阐述和深刻探讨,可以使我们对“传神论”的意涵和承传有新的认识。
顾恺之; 传神论; 玄学; 绘画审美
顾恺之的画论代表作《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中都有对绘画“传神写照”“悟对通神”的表述,即要表现人物的神情,使观者有“览之若面”的效果。顾恺之在画论中对于如何传神也阐发了相应的技法要求,包括以形写神、点睛、迁想妙得、传神写照、置陈布势等。因此,顾恺之的传神论不仅是一个品评术语,更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形写神”是统摄其他几个方面的核心。“神”成为艺术审美和品评的标准,“神韵”也随之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1]顾恺之“传神”论的美学意蕴在于同人的气质、才性相结合,体现为一种哲理。顾恺之所说的“神”是指一种有审美意味的人的风神,强调人独特的“风姿神貌”。“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2]实则也是魏晋时期兴盛的玄学在绘画中的表现,传达的是魏晋时期人们对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一、“传神论”的思想铺垫——玄学语境
要理解包括“传神论”在内的一系列魏晋审美玄学范畴的内涵,重点就是要把握好魏晋玄学的影响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
魏晋玄学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解说并发展抽象的内容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形神关系的辩论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魏晋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表现在审美情趣上就是用人的内在精神品评人物,考察人物的“情性”,将“神”看作是一种无限自由的境界,超越了有限的“形”。即汤用彤先生所说“学贵玄远……而进探本体存在”[3]。因此,一个人的才情、风貌、韵致等内在精神性变成首要位置,成为最高评价标准和准则,而不再局限于人的外在行为。“汉代相人以筋骨”,到了曹魏时代,品评人物开始重“志质”“聪明”等内在精神内容,并成为人物品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玄学影响引起的人物品藻由德行政治伦理品藻向赞许人的神韵、风姿等的转向,促使当时文人士大夫们追求所谓的“心整形浊”,崇尚清俊放荡的审美趣味、鲜明的精神个性、独特的神气、神韵等内在精神层面的东西。因此,源于玄学关于形神的讨论形成的重神轻形,以神为上的观念,对魏晋六朝书画创作与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顾恺之“传神论”直接来源于玄学关于“有无”“意象”“形神”等几对观念以及相互关系论辩。在这样的情况下,顾恺之发挥自己对绘画的独到见解,在绘画史上首次提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传神论”,推进中国画理论至新的发展阶段。自那时起,中国画致力于追求绝对自由精神境界,“传神”即对画的内在精神气质的表现,成为评判绘画优劣最重要的标准。
魏晋玄学的产生,标志着对理想人格绝对自由的本体探求,汉代的宇宙论至此转向本体论。但是玄学并不是一种书斋里的学问[4],而且反对坐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但同时也不否认群体与社会,而是主张为追求人格的自由独立,打破群体与社会的束缚,仁义道德对个体的要求不再具有绝对影响力。因此,蕴涵在玄学中的新的自我人格美,以“自我超越”为主旨的人格本体论价值体系中,人内在的精神性成为最高的标准,而不是外在行为节操。在玄学的“自我超越”中,将个体的天性、自由、人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个体实现从外部功利世界向自我情性本体的回归。[5]
冯友兰先生用“必有玄心,须有洞见”[6]形容魏晋人的风流潇洒。“玄学”的本质是对人生价值、人格理想的无限追求,进而超越有限的人生,获取无限自由。魏晋玄学以人物品藻、名教与自然、才性之辩为主要内容。随着玄学的广泛影响,绘画艺术出现了崇尚绝对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重在表现人之逍遥的精神,超越世俗之物,探究自然美、人格美之奥秘,创作主体的才性得到激赏。玄学的研究对象是“名”与“道”、“有无”之辨、“言意”之辨“风骨”“神韵”等观念。纯思辩的清谈对象和方式也以“玄言”,即幽深玄远之言为主。魏晋南北朝的玄、儒、道、佛等思想互相渗透、融合,掀起了独特的多元思想发展高潮。个人自我意识增强,思想活跃,人性不断自觉,于是在绘画领域中也产生了新的审美理想。[7]
二、“传神论”中的形神之辩
“以形写神”中“神”的美学意义既指人的本质神韵,也指在特定时空下人的完足精神状态。人的本质神韵是由一个人的知识结构、生活阅历等综合形成的内在精神特征,外化为一个人外在的风貌。顾恺之注重对“神”的表现,如他对《列士图》的评价,“虽美而不尽善也。”顾氏未予肯定的原因是本质神韵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只能评为“尽美而不尽善”。“神”有时表现为特定环境下凝炼的、集中的精神状态,不同于普通的神态。顾氏在《画云台山记》中“弟子中有二人,临下倒身,大怖,流汗失色”是对特定情形下精神状态完足性的描绘,使人觉得栩栩如生,非常传神,给人“览之若面”之感。石涛在《画语录·山川章》中的论述涉及了“形”与“神”辩证统一的精神实质:“此予50年前未脱胎于山川也,亦非其糟粕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8]
形体准确在魏晋时期的绘画审美标准中占有重要位置。顾恺之言“以形写神”,形态正确是传神的基础,“神”通过写形来传达。忽略“形”的探讨,只会限于抽象、玄虚的概念的纠缠。“神”借“形”而表现,“神似”是“形似”的集中表现、提炼和深化。写形是手段,传神是目的,形服务于神。同时,顾氏还关注“形”的美学价值,对《北风诗》一画的评价“美丽之形,尺寸之别”是对“美丽之形”价值的肯定。从谢赫《古画品录》中评顾恺之“格体精微”、顾骏之“精微谨细”等的称赞之词也可看出当时对准确形体的审美要求。而评价宗炳“迹非准的”,所以只能列为第六品。
在人物的“神”到“传神”的过程中,形神相互联系统一。形是基础,是可视的、表象的、具体的;神是绘画的主宰,是隐含的、本质的、抽象的。“形”与“神”虽有具体与抽象之别,却能统一在绘画创作中。“以形写神”也就是哲学上的通过物质表现精神,透过现象表现本质。
《周易·系辞上》对“神”解释为“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是不可见的玄妙和奥秘,却可让你随时感悟到。“神”是一种可以通道的总规律,成“神道”,能使事物生长、并主宰天地、人生和自然,又可以和“妙”“秘”联系起来,形成“神妙”“神秘”。在艺术创作中,“神”被形象化、人化,使艺术的想象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并使传统的哲学思维得到扩展。如在绘画中,以人的形体来表现“神”。对“形神”的理论探讨在汉代进一步深化。《淮南子》中认为“神”是主导的、统制的,而东汉王充是坚持形神统一的一元论主张,属于唯物主义范畴。《世说新语》中《郭景纯诗》关于“神”的描述,体现出魏晋对以上形神观的继承和发展,阮孚用“辄觉神超形越”来形容读了郭璞的诗以后的感受,形象的烘托出诗的独特“神妙”意境,能使人身心超逸。
顾恺之的形神观曾被误读为“重神似而轻形似”,其实不然,他是主张形神兼备的,作画首先应该在“形”上画准,形象的精神与内在生命是通过准确巧妙塑造的外形表现出来的。“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生动阐述了“以形写神”、“悟对通神”的美学概念。[9]顾恺之在这里用一种“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的假设来阐述传神之概念,明显地界定了形神的关系。而“悟对之通神”是对于对象精神和真髓的把握,是物化的“以形写神”之基础。这里也可看出顾恺之对形神任何一者都不偏颇,“形”是传神之“筌”,对形也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如“作人形骨,成而以衣服幔之”,就是“形”是为“神”而造。清人邹一桂也说“未有形不似反得其神者”。写神不可无形,如得鱼不可无筌。“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必须深入对象仔细观察,挖掘精神实质,以获得高度的艺术效果。但正如“筌”之于得鱼仅是一种手段,传神是写形的最高目标,在形似的基础上要传达表现人物的情态神思。否则虽然有“形”,却是无“神”之“形”,“形”只有被赋予了“神”才更生动。可见顾恺之主张“形”“神”既依附统一——形象刻画“形”以烘托服务于生动之“神”,同时二者又有各自独立性的形神观。经过对客观对象深入体察关照后产生妙悟,从而传达出艺术对象的“神”。以“传神”为标准评价绘画优劣的观点,可视为传统文人写意画最早的理论依据。
“以形写神”这一总体性的创作原则,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呢?顾氏首要强调的就是眼睛对“传神”之重要性,即“点睛”。顾恺之强调眼睛是人物内在神韵和独有个性特征的集中体现,眼睛刻画的成功与否决定是否能表现出对象特有的神情气韵,这是“传神”的关键。“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10]这是对“点睛”“传神”的精到讲述。顾恺之之所以在刻画人物时要过很长时间才点睛的原因是,顾氏认为眼睛能传达人物心灵、表现精神特征,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斟酌之后再作。通过这段记载我们也进一步看到当时对于“传神”的重要性和意义的重视。在绘画创作及批评中,对人物的刻画重“神”,正成为更高的境界及要求,并成为后世所传承的评价绘画标准及审美要求。也就是说描绘人物更重要的是传人物之“神”,刻画生动情态,而不仅仅是表现外在形体。“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11]把握住人物最传神的部位眼睛,以充分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是人物“传神”的关键所在。最早明确提出眼睛对于观察内心世界重要性的是孟子。“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重视观察眼睛的主要目的还是强调判断人的伦理道德上的善恶作用,而并非审美意义。顾恺之提出的“点睛”之语是对“以形写神”绘画观点的发挥,也体现对“形”的严格要求,肯定了“形”的美学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先秦两汉尚实美学遗风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顾恺之重视眼睛的传神,但并不局限于眼神。有人从顾恺之“四体妍蚩本无关乎妙处”的理论中得出错误的传神一点论,认为顾恺之把眼睛当作“传神”的唯一部位,其实顾氏并未否定“四体”在“传神”上的作用。有人又偏向另一种平均论的误解,认为“四体”与眼睛在“传神”的作用上同等重要。应持的观点是,必须正视眼睛的关键作用,如魏晋时刘劭《人物志》所说:“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同时要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四体”、眼睛与“传神”的关系。
置阵布势、环境对烘托人物内在精神的作用也是顾恺之强调的内容。绘画要做到“传神”,也需注重刻画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烘托人物的身份、情感。又如“‘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12]。顾恺之敏锐地抓住谢鲲山林志趣的特点,将其置于丘壑中,以景托人,更好的表现了人物的风神,达到了传神的效果。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也体现了顾氏运用环境的布置烘托人物内在精神。他将洛水女神、曹植置于惊鸿、游龙、凌波及云气飘渺的朦胧唯美背景之中,烘托了洛神的飘逸,和曹植对其的爱慕与思恋,画面气氛悱恻缠绵,让人观后有“悦其淑美兮心振荡”的效果。
顾恺之的“传神”与“写照”联系在一起。“照”本是佛学中词,如佛肇《般若无知论》就有“神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智无知,故能玄照于事外”之说,[13]是指主体的不可言语的神妙感知能力,与精神修炼有关,表现出人的心灵、智慧。“是要写出人的神妙的精神、智慧、心灵的活动。‘写照’在本质上也是‘传神’。”[14]顾氏打破了以往绘画技法的教条束缚,“传神写照”便是其创作更加超逸、自由的形象表现,更是他在创作中探求并达到的境界。
三、“传神论”的承传
南齐谢赫发展并丰富顾恺之的“传神”论,著《古画品录》提出“六法”,把“气韵生动”列为首要,“气韵”就有“神”的意味,而“韵”也是从当时人物品藻中引伸入绘画,用于形容人的内在个性与情调、“风姿神貌”。《世说新语》中“韵”就多处提到,如“风韵”“高韵”“天韵”等等。谢赫用“形妙”“象外”的概念作为对“形神”问题的延续探讨。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对顾恺之的绘画没有给予很高评价,却把至高赞誉给予顾的学生陆探微,也是对顾恺之思想的认可和承传。谢赫称赞陆探微之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将其置于第一品第一人。
接下来在中国绘画评论史中登场的宗炳与王微,把“神”引入山水画中,山水也要得其“神”。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论道:“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异。”[15]王微在《叙画》中说:“神明降之,此山水画之情也。”[16]这些主张和理论都发展了“传神”论的思想,并扩大其内涵,使得“神”不再仅用来形容人物,这也是对山水审美的重要贡献。“传神”成为中国传统山水画审美中的重要范畴,对后世影响很大。苏轼“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17],就形象说明花鸟、古松、竹石皆可“传神”。
唐代张怀瓘对顾恺之的“传神”论和谢赫的“六法”作进一步发展,提出“神、骨、肉”的观点,用“骨”和“肉”来表达“形”的意思,并用以评价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18]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开宗明义提出: “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以俗人道也。”[19]张彦远推崇顾恺之,并提出“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的论述,对“形神”观作进一步发展。
五代荆浩对“形神”问题提出新解:“真者气质俱盛。”[20]其中“气”即为“神”,“质”代表“形”,并且发展谢赫的“气韵”说:“气者,心随笔运。”[21]到了宋代,郭若虚又发展荆浩的观点,提出“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22]。至此,所谓“气韵” 仅指画家本人的主观情思,重“神”而轻“形”,文人写意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传神”的涵义也由传对象的“神”转变为传主体的“神”。苏轼“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的主张成为文人画的纲领。“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23],重“神”轻“形”的文人画倾向表露明显。元代是文人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倪云林“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24]。清初石涛“不似似之”说,近现代齐白石“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25],黄宾虹说“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26]。可以看出,从宋代文人写意画开始,强调作画的主观感受,通过对客观物象的加工、变形,从而创造出神似的艺术形象。从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到齐白石、黄宾虹的“似与不似”,“形”和“神”的演变,是绘画艺术本体的自我觉醒,对于后世绘画的创作与批评有重大意义。
四、“传神论”的实现途径——迁想妙得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27]顾恺之“迁想妙得” 这一绘画美学命题解释了在绘画创作中如何把握形象思维的运用。即通过艺术想象,掌握了客观对象的思想、精神后,达到“托形超象”,进而遵循“妙理”, 融创作主体的认知和客观物象形态于一体,物我两忘的艺术构思过程。“迁想”要求创作主体深入探求和观察推测所描绘客观物象的思想和神韵气质,并通过联想和想象,将自己的思想和主体感受“迁移”入客观物象中,身与物化,主客统一。“妙得”则需由创作主体逐步经过提炼而获得。“迁想”中的“迁”是指作者思想对客观物象的“迁移”“移入”“超越”。“迁想”,即在艺术想象中思路的“迁移”“超越”,做到顾恺之所说的“神仪在心”, 完成由认知思维到艺术思维的转换。而“妙得”,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回到更深层次的感性认识,即创作出艺术形象的构思过程。也就是近代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所说“故画家在表达对象时,须先将作者之思想感情移入于对象之中……而臻于妙得……亦即顾氏所谓‘迁想妙得’者是也。”顾恺之“迁想妙得”思想的提出,是对艺术想象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提炼,象征中国绘画创作的进一步成熟和自觉。
顾氏在《画云台山记》设计稿中表现张道陵七试弟子赵升向佛的故事。通过“迁想妙得”准备对画面中的人物作如下精妙布置:“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据碉指桃,回面谓弟子。弟子中有二人,临下倒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应为王长)穆然答问。而超(应为赵)升神爽精诣,俯陌桃树。又别作王、赵趋,一人隐西壁倾岩,余见衣据,一人全见室(应为空)中,使轻妙伶然。”[28]从中,我们可读出顾恺之对道家“神明之居”的向往。
顾恺之在魏晋时就能提出“迁想妙得”理论,得益于当时玄学之风盛行和“人的觉醒”的时代氛围。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核心,重清谈;而“人的觉醒”表现在“人物品藻”对虚静超俗、睿智才情的内在精神风韵的关注,汉朝重功业、品德造诣的思想受到极大忽略。“魏晋风度”,即一种玄澹放达、不拘礼法形迹的人生境界,是文人士大夫们崇尚的最高理念。这些时代文化风潮导致了这个时期美学精神出现重大转折,并影响到当时的艺术实践、艺术批评等各方面。顾恺之的“迁想妙得”等具有极高价值的绘画批评理论应运而生,是中国绘画史上巨大的进步。
注释:
[1] 王来阳:《魏晋南北朝画论与中国审美基础的确立》,《美与时代》2003年第7期。
[2][9] [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杨成寅:《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先秦汉魏南北朝卷),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13,113页。
[3]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4页。
[4][5] 仪平策:《中国审美文化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6]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7] 孙晓波:《绘画艺术的觉醒——试析魏晋南北朝绘画中的审美理想》,《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
[8] 王宏建、袁宝林:《艺术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12][27] [东晋]顾恺之:《画论拾遗》,杨成寅:《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先秦汉魏南北朝卷),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13,113页。
[13] 邓乔彬:《论顾恺之的绘画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24]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 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5] [南朝]宗 炳:《画山水序》,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355页。
[16] [南朝]王 微:《叙画》,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361页。
[17] 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18] [唐]张怀瓘:《画断》,彭莱:《古代画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19]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汤麟:《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隋唐五代卷》,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20][21] [五代]荆浩:《笔法记》,彭莱:《古代画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13,113页。
[22]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邓白校注,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年。
[23] [宋]苏 轼:《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
[24] [元]倪 瓒:《清閟阁全集》,汤麟:《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 元代卷》,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26] 王伯敏:《黄宾虹画语录》,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
[28] [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杨成寅:《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 先秦汉魏南北朝卷》,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责任编辑:余 言]
2016-03-30
宫旭红, 女, 山东昌邑人,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J202
A
1002-3321(2016)04-00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