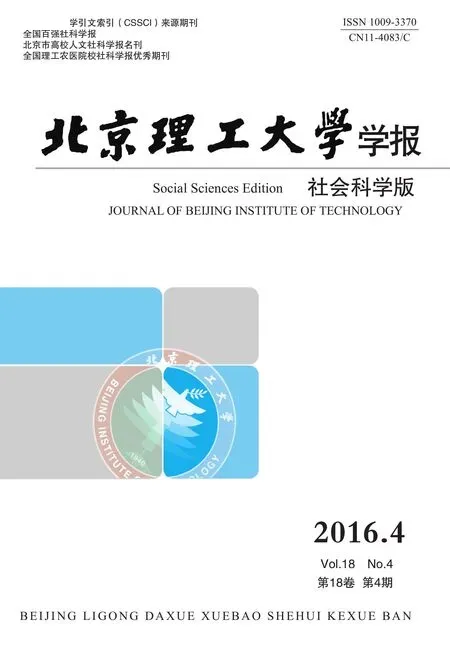论社会治理制度与行政人格
杨艳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论社会治理制度与行政人格
杨艳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制度与人格相互构建,行政人格的生成与社会治理制度密切相关。在传统的权制和法制模式中,由于相应制度中伦理道德的“等级化”和“虚无化”,行政人员分别被塑造成依附人格和工具人格。随着服务型政府从理论走向现实,社会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道德被重新凸显,德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进而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也只有在德制中,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才会得到普遍性的生成和自觉的建构。
行政人格;权制;法制;德制
行政人格作为行政人员之外显的特殊存在,是其人本质不断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无时无刻不受行政人员所处环境的影响,既受其身处的政府组织、治理制度以及行政文化等外部因素的直接塑造,也受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整个社会环境因素的潜移默化影响。从组织角度看,在以官僚制为模型的现代组织中,组织结构的内部紧张和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人格变异[1]。从文化角度看,“所有个体的总和构成了文化”,而“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关于社会现实及其本质的观念成为人们认知和行动的向导,其蕴含的意义和规范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最终沉淀为个体自我的一部分,成为个体人格的“无意识行为”标准[2],因此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人格具有鲜明的文化烙印。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和制度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者,组织中个人行为动机和偏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塑造[3]。无论是从个体人格还是群体人格的角度讲,制度和组织都是行政人格生成和构建的关键因素。关于组织因素,笔者已另文从组织整合机制角度进行了探讨,这里主要讨论制度对于行政人格生成和建构的影响。
一、制度与人格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对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的反思中,“制度”重新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相继出现了各种“制度主义”流派。然而这些共享“制度”名号的流派对“制度”的理解角度和研究侧重点却不尽相同。关于制度的不同理解,表明了“制度普遍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4],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与生活、存在属于同层次的范畴,个体人格始终处于制度之中[5]。制度是现代性演进中的公共性产物,对于社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人员而言,其人格的生成与建构更是时时刻刻脱离不了具有公共性之本质属性的制度的形塑。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之利益、价值、自由等只能在社会总体中得以实现,这一过程中个体与总体关系的体现与处理,就表现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关系,并经由历史的选择逐渐沉淀为制度,凝结为一系列的规则、规范、程序并编织成个人活动的社会空间。换言之,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制度通过对个体类本质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和要素的集合,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对所有人的行为进行激励、指导、规范、约束的总体性空间,而这种普遍性的实现,又具体化为每个人在制度保障和约束下的现实活动。这是一个从个体到总体、又从总体到个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类本质得以展现,人格得以形塑,制度通过人的交往互动成为个体实现类本质的总体环境,也正是在制度环境中,个体类本质才得以真正实现,于是,“个人生活及其所包含的社会纽带深深地交织于抽象体系(systems)之最深层部分”[6]。因此,制度是否能够合理纳入人的类本质实现所需的基本条件和要素,则成为个体人格形塑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现实中,往往是尽管我们意识到人格生成与外在环境有必然联系,但遇到人格完善与形塑时又将其完全寄托在个体(道德自觉和自律)身上,而制度与人格的关系在已有的人格理论背后长期被忽视。
制度与人格是相互构建的。制度之于人格的建构性,积极一面在于作为社会生活的形式系统,制度为人格发展创造必要的空间,其对良善丑恶的褒扬贬抑引导着人格向其倡导的方向发展;消极一面则在于僵化、教条的制度压抑人格的发展,其对某些伦理价值的固执可能与人格的内在发展不协调,例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制度对等级伦理的强调背离了人格独立发展的倾向。诚如罗尔斯(2000)所言,“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7]。人格之于制度的建构性,积极一面在于制度的实际运行离不开人格的支持,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往往存在于人格发展的价值践行中;消极一面则在于分裂的、扭曲的人格将会消解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甚至使得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之于人格的建构性要求制度建设必须以人格的健康发展为其价值导向,而人格之于制度的建构性则要求人格的合理性诉求必须得到制度的保障。
根据制度生成的不同历史条件,张康之(2010)将社会治理制度区分为权制、法制和德制3种历史类型[8]199。制度与人格的相互建构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制度与人格是相互适应的,不存在超越制度建设水平的人格形态,也不存在超前于人格发展形态的制度。在人类的不同历史时期,制度建设的自觉性和合理性也不相同,因此,相应的人格形态也就出现了历史类型的差异。在农业社会时期,制度的生成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自然演进过程,以习俗、习惯存在于人们的共同生活中,缺少理性的自觉建构和利用[9],因而个体人格的自觉性和理性也就不可能吸纳到制度中。相反,共同生活中因人与人相互依赖所产生的权力等级,身份伦理“自然”演化为制度的主要内容,由此在社会中塑造了一种普遍性的依附人格。到了工业社会,在启蒙思想的激发下,制度越来越具有自觉的特征和理性的成分,人的自由和平等成为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独立人格成为社会追求的普遍人格形态。然而,在社会治理领域,理性发生了分化,形式理性与工具理性取代理性成为制度设计的标准,人格越来越被打上“形式化”的烙印,公共领域中的行政人员逐渐被塑造为一种工具人格的个体。
二、权制中的依附人格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产物,存在于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制度具有明显的历史差异性,并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在社会治理领域,不同历史形态的制度塑造了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影响并生产出不同的行政人格。在农业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物质资料尤其是生活资料十分匮乏,“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10],由此确立了分配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这种分配关系包含着对人的“自然差异”的承认,是一种建立在人的差异基础上的分配关系,而这种“自然差异”在阶级社会产生后逐渐被社会等级差异所取代;另一方面,任何分配都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造就出主持分配的权威,分配总是以一定的权威为其保障,这种权威在农业社会中就体现为集权。分配关系在集权的保障下,分配行为自上而下逐级进行,形成了一种垂直的、单线的“关系链”,并逐渐演化为以权力为轴心的单一的线性结构,进而又通过外在的实物、荣誉或称号等形式逐渐物化为一种制度,这就是权制。权制服务于阶级统治的需要,以制度的形式保障权力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而道德和法律则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常常成为权力手中任意役使和变换的工具。
在传统农业社会,尽管权力居于社会治理的中心地位,但道德却一直是统治阶级所标榜和推崇的统治手段。在以维护等级秩序为目标的统治过程中,社会治理体系对等级秩序的维护方式是把社会个体限制于等级结构中的一个个网格中,从而对个体按照地域、种族、家族、社会地位等因素进行分而治之。在严密的等级网络中,个体要么是被等级伦理驯化为安分守己的良民,宿命式地固守于社会强制赋予的等级秩序中,从而失去自身作为人本质的广泛的社会联系的基础,要么是在自由与独立的冲动中奋起抗争,试图打破不公的社会分配关系和等级秩序,而其结局往往是在驱逐、流放、发配、监禁甚至各种酷刑等手段中逐渐消耗掉或直接被消灭掉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这既可能来自于家长权威的惩罚,也可能来自于社会大众之冷漠与不解的训诫,更多的却是来自于国家警察、监狱的强制规训。因此,历史展现给我们的是,权制模式下的德治背后始终伴随着血淋淋的武功暴政,道德只是权治表面的温情面纱和遮羞布,而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往往被历史给予英雄般的记忆。
在任何的社会治理中,法律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传统农业社会中法律工具的存在并未将整个社会导向法治。在中央集权国家产生前的习惯法,“指导着某一等级的成员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如何对待同等级或不同等级的其他成员”,并“适用于狭窄限定的各类人和关系范畴而不是极其普遍的各阶级”[11]。这就是说,习惯法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分配只是对特殊主义的宣示而非对普遍主义的张扬,其实施不过是维持既存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因而法律完全沦为实质性政治利益或伦理道德等意义性内容的承载物。而官僚政治出现后的官僚法,缺乏实质平等,本质上是一种压制型法律,在等级伦理的统摄下,其所追求的效果是要求被统治者出于无知的同意和由畏惧中获得冷漠来支撑的默认,形成一种道德秩序,并且这种深植于心的“道德秩序省却外在惩罚的威胁,并代之以依靠罪过和谦恭这样一些内在情感,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更深层的压制,尽管这种压制更加巧妙”[12]。要言之,权制模式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以权力关系为轴心,法律的具体实施是以垂直性统治权力的绝对的独断的占有为前提的,而等级伦理的秩序需求使法律规范进入了“道德”视野,积极的压制与消极的默认取代了法律的中心地位。
道德的等级化和法律的边缘化,一定程度导致了农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实际上演化成身份伦理与等级权力的制度化,在权力的统筹下,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一体化系统。在这样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存在的只是一种混沌未分、缺乏充分形式理性的权力[13],所谓的行政权力并非现代法治观念中“三权分立”意义上的权力,本质上是君权或皇权的延伸,而君权或皇权的一己之私性自然而然地被官僚体系所继承,行政权力名义上成为社会治理的公共权力,实际上具有强烈的人身专属性。由于政治与行政的混同,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纠缠不清,由于统治与治理的合体,行政权力与公共权力互为表里,它们通常可以相互称谓。在这种混同中,行政权力的独立性丧失掉,表现出等级化程度高、普遍化水平低、特权化现象明显等特征,进而形成一个具有严密等级区分的、先赋身份与权力挂钩、特权与利益同构的金字塔形的权力体系。简言之,权制模式中,行政权力被严格等级化,各种先赋的身份、人格化的权力、地位等级成为标识大小官僚们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不同符号,这些特殊主义要素互相影响,相互为用,共同影响并决定了权力梯度中官僚们的人身依附性,结果是依附人格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三、法制中的工具人格
当历史迈入工业社会后,交换关系取代分配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关系,促动着人对人的人身依赖向对“物”的依赖的革命性转变。交换关系的实质是要求交换主体的自由、自立和平等,遵循自由自愿原则,这些要素构成了独立人格最基本的特性和被广泛认可的价值框架,成为现代人格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和对人格的独立性追求,在理性的主导下被纳入到制度的自觉构建中,这种自觉建构的制度常常是在法律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直接称为法律制度。现代市民社会的真正兴起和政府管理功能的日益凸显孕育并催生了现代法治,社会治理由此走上法治的道路,法律取代权力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社会治理制度被赋予了“法制”的形象。
就整个社会而言,“无论是在宪政或人权层面的宣示,还是部门法中具体制度之设计,人格权制度在其中均担当着轴心性的角色与意义”[14]。法律制度对物的关系进行规定,首先表现为民法中的人格制度建立。尽管罗马法时期的人格确立被赋予完全的财产内涵而成为侵权法的内容,但人类在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中,人格的制度之构建越来越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它既非“仅仅解决人自身之前提问题”,也非全为“解决人与人之平等关系问题,其更进一步之社会功能或法学价值趋向是为了解决在平等身份之后之人与物之关系”[15]。回溯历史,在人格的独立性追求过程中,公法上人格建构的制度化无疑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突出表现在对人作为人的自由、平等一系列根本人权的明确规定和保护上。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宣言》等法律宣言,标志着人格建构的制度化达到巅峰,也预示着现代社会的真正来临。
人格的制度建构在民法与公法上的区分,契合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发展与分离的社会现实,但也是现代理性发生分化的制度性反映,为现代社会中人格发展的片面化埋下了制度的隐患,一方面它为社会领域中独立人格的普遍生成确立了制度框架和保障,另一方面,它将人的自由、平等限定在了不同领域,并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定化。在公共行政领域中,结果是这种人格的法律建构离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生成越来越远。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制度是一种理性的自觉建构,其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但是顶着启蒙光环的“理性”在后来的制度演进中发生了分裂,逐渐演化出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宏观理性与微观理性等相互龃龉的对立物,理性片面化发展的结果在法律上的体现就是表现为纷繁复杂的规则、规范和程序,它以形式化的客观性和统一性、普遍性和稳定性指导个体行为的追求,引导整个社会进入理性化的阶段,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理性在形式化的发展中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在解构一切权威的同时把自己建构为一种新的权威,即形式化的法律制度将其本该包含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给祛除掉,免除社会成员的道德思考和价值判断,强迫社会成员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服从法律制度的规定,从而将自身塑造为一种新的权威,这就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6]的奥秘所在。
以形式理性为本质特征的法律制度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其对公共领域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对行政行为的制度约束,即“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不可否认,在法制模式中,权力仍然是并将一直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是一切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存在的依据,但是与权制模式中的权力相比,法制模式中的权力,其强制性后盾已经远远退后,不再是直接走向前台。在宪政与法治的框架下,行政体系依照形式化的理性要求,被设计成以层级和职位差别为基础的金字塔状的权力结构,越来越精细化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逐渐成为行政人员相互交往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依据和标准,权力运行之命令-服从的强制逻辑不再是直接指向于个体的肉身存在,权威服从不再是基于身份等级的人格认同,也不再是基于等级伦理的消极默认和尊奉,而是对规则的理性跟随。因此,尽管权力本身仍然存在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中,但其形式上的法律外衣及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将权力与人格分离,权力的法律制约对其“任意性的限制”将身份、种族、血缘等特殊因素予以形式上的坚决排除,因而这种权力下的社会治理获得了形式上的公平及效率进而获得社会普遍的认可。
然而,尽管行政人员在对法律制度的依附中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与平等,但这种形式化的制度设计,不鼓励也不允许行政人员进行主动创造,更不允许行政人员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考量,行政人员按照既定的制度规章去办事是最基本的职责要求,“组织伦理”[17]强调的就是对团队、组织和规则的忠诚。这样一来,行政人员所置身于的法律制度,“从整个来说,还远比惯例的制度更少具有伦理准则的性质”[18],而这些“由抽象体系建构起来的常规具有空虚、非道德化的特征,这也是非个人化逐渐吞噬个人之观点的精髓所在。但这并非仅仅是个人生活的弱化以利于非个人地组织起来的系统,它更是个体之人本质发生的真正转变,……个人关系既是现代性之社会现状的一部分,同时也被涵盖进时-空伸延之制度内”[6],即行政人员被锻造成设计精良之“机器”隐喻中的零部件,从权制模式中对人的具体的、随机的依附转变成法制模式中对制度的理性依附,完全成了管理的工具,于是传统的依附人格披上现代性的外衣而以工具人格的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
四、德制中的独立人格
法制模式下的公共行政,由于对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的回避导致了行政人格的工具化,这一现象在20世纪40—50年代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名噪一时的“芬纳-弗雷德里克”之争,名义上是关于如何实现行政责任的道路之争,实际上是对公共行政如何实现伦理道德的不同看法。诚如沃尔多(1954)所言,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又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其对价值和道德的观照不仅有助于减少公共行政实践中的混乱和压力,也有助于发展公共行政事务中的“道德创造力”或“道德建筑风格”[19]。迪莫克则提出公共行政不仅仅是科学,也不仅仅是艺术,它还是一种哲学,应该将行政管理与个人有机结合起来[20]。新公共行政学派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各种踩在新公共管理肩上的“后……”超越行动,实际上是“集中于价值和伦理”的,是“一种基于价值的文化层面的改革”[21]。文化、价值、伦理成为了超越新公共管理或者说“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题,最直接的代表就是公共价值理论的崛起,并大有成为“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22]的趋势。当价值和伦理跃升为当代公共行政领域的核心时,现有制度如何吸收和转化价值和伦理,或者价值伦理如何来塑造和转变现有的制度,就成为行政人格构建乃至整个社会治理变革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官僚体制构筑的公共行政领域中,“由于行政之恶无所不在,公共事务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培养一种对公共机构、权力运用以及普遍文化的批判与反思的态度”,如要防止未来行政之恶的发生,“公共事务除了涉及(但不仅仅立足于)采用复杂的组织与管理技巧来执行公共政策,还必须(并且主要是)带入一种历史意识,能够从国家及其代理人员的角度了解可畏的邪恶潜力,同时还必须带入一种社会角色与身份,在其中不仅仅是要灌注个人与职业的伦理,更重要的是要灌注一种能够识别行政之恶伪装并拒绝与之同谋的社会与政治意识,或者说公共伦理。”然而,传统上的“公共服务伦理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伦理都停留在科学-分析心理上,都停留在解决行政与社会问题的技术-理性方法与职业本身上,它们在面临行政之恶时都无能为力”[23]。出现这种尴尬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伦理建设及其制度安排是基于原子化个人视角出发的,因此,从公共服务伦理的角度而言,作为超越权制和法制的新型社会治理制度的构建,首要之务就是“改变认识社会的视角,即从共同体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以人的共生共在为出发点去形成相应的制度和社会问题解决方案”[24],这种制度绝不能仅仅是工业社会以来逐渐形式理性化的、唯效率至上的制度,而是回归到实质理性的被道德化的、张扬人的价值和德性的制度,张康之(2010)称其为德制[8]199。
生成于后工业社会中的德制是社会治理中伦理关系的结构化和制度化,它“包含着权制和法制全部历史发展中的一切积极成就”[8]199。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3种最基本的关系,即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权制模式中,权力关系占主导地位,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只是权力更好运行的副产品而已,由于权力关系的本质是等级服从和命令统一,因此这一模式下的个体更多的只是被动的服从,依附于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等级结构。法制模式中,统治与管理发生形式上的分离,在权力关系外生成了法律关系,权力在法律规则的约束下运行,而法律关系的本质是独立平等的契约关系,它对权力的制约与调整将人对权力等级的依附转变成人在规则面前的平等和对职业的忠诚。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很好地吸纳伦理关系,或者说伦理关系“始终未获显性化”,权制模式虽然强调道德,但这种道德处处充满着强调亲缘地域、身份先赋的特殊主义取向,本质上是一种与特定身份相适应的等级伦理,而法制模式虽然实现了人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其对道德的武断拒绝,把制度中的人变成了分散的“无意识”“不道德”的原子化个体,如果说法制模式中还有伦理,那就是对规则的热情信仰和绝对服从,而对职业的忠诚也变成了仅仅是承担岗位责任,与道德良心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政府不道德的制度根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中的伦理关系来源于社会的普遍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首先是以充分尊重个体的类本质实现、视其为完整的个体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以服务理念和服务价值的展开为核心的,生成并实现于行政人员的服务行为之中。从个体与组织群体的角度来看,被制度化的伦理关系直接从个人的类本质生成与实现出发,将服务价值的实现以个体为起点,再上升到组织群体,而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直接立足于组织群体,从群体的性质、职能、职责出发,再到个体,这种理论上逻辑自洽的路径常常面临现实的阻塞而出现完整性的断裂,所谓的服务沦为空谈。当德制中的伦理关系被自觉地建构时,通过伦理的融合调整,个体与组织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互动与建构,不再是单向的、封闭的自说自话,从而在个体与组织的同一中实现了服务价值,行政人员自身也获得了社会生命。
现代伦理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开放的、平等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包容、合作互信的一种关系。与法律制度营造的形式平等不同,道德制度造就了实质上的平等,这时的行政人员和行政相对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再是把各自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是作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来看待,进而在主体间的互尊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因此,从个体及个体之间的角度来看,当制度实现了道德化,行政人员对制度的遵守与执行就不再是一种强制性的感受,而是出于内心道德意识的自觉自愿的服从,并将自己的服务行为置于道德的监督和审视之下,这样一种行为就不再是实现目的之手段,而是对行政人员具有了完整的意义。与此同时,行政人员把“道德认知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促使其把他人融入自己的生命活动之中,把他人的事业、他人的要求看作为促使其行动的命令,同时又把自我生存的意义放置在为他人的服务之中”[25]。因此,德制是这样一种制度,即“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26]。德制是能使个体避免陷入孤独境地,抛弃自私特性,进入交互主体性的公共领域的制度。
总言之,德制并非是把制度视为解决道德分裂、伦理虚无的唯一工具,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形式促进和强化道德的自律与他律之间的相互转化与有机整合,并使这一过程成为经常性的、稳定性的过程。在德制中,个体不再是被分隔的碎片化原子,而是拥有人之类本质实现的完整性,个体不再是目的实现所凭借的手段,而是在主体间性的层面成为了目的本身,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信任是一种主体的自觉,不再是外在的强迫;合作与信任是稳定的普遍的,不再是个别的暂时的;合作与信任是客观的,不再是个体选择性的。而在基于信任的合作与服务中,服务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行政人员则拥有了完整的人格意识,获得了独立的行为能力,在道德选择的自主性和责任义务选择的创造性中完成了自身独立人格的塑造[27]。
[1]默顿.官僚制结构和人格[A].彭和平,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94-104.
[2]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三联书店,1988:19,214,231.
[3]MARCH J G,POLSON J P.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78):734-739.
[4]张康之.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德制构想[J].学海,2013(3):148-155.
[5]顾红亮.从制度的视角看人格[J].重庆社会科学,2006(11):31-35.
[6]GIDDENS B A.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20.
[7]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85.
[8]张康之.论伦理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99.
[9]张康之.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思考制度重建问题[J].学术界,2013(4):25-36.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5.
[11]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7.
[12]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5-56.
[13]张康之,张乾友.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J].学海,2011(2):58-68.
[14]王世洲.人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5.
[15]刘云生.道德祛魅与人性张扬:民法人格价值论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167-171.
[16]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1:15.
[17]WILLIAM W.The organization man[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5.
[18]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6.
[19]WALDO D.Administrative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a survey and prospect[J].Political Studies,1954(2):70-86.
[20]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1.
[21]CHRISTENSEN T,LAGREID P.The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to public sector reform[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7,67(6):1059-1066.
[22]何艳玲.“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J].政治学研究,2009(6):62-68.
[23]艾赅博,百里枫.揭开行政之恶[M].白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6,27.
[24]张康之.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20.
[25]杨艳.合作型组织中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塑造[J].中国行政管理,2012(4):68-70.
[26]卢梭.爱弥尔[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5:5.
[27]杨艳.行政责任的实现与行政主体重构[J].探索,2012(2):66-71.
[责任编辑:宋宏]
On Institution of Social Govermance and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YANG Y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Institution and personality is mutually constructed,and the creating of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institu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In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power and law,administrators have been shaped respectively into relied-personality and instrumented-personality because of moral and ethical hierarching and nullifying correspondingly.With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becoming a reality,social governance has been transforming significantly.Morals will be highlighted again and moral institution become inevitable.And so the cre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ha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Only in moral institution can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administrator be created generally and constructed selfconsciously.
administrative personality;power-institution;law-institution;moral institution
D035
A
1009-3370(2016)04-0058-06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6.0408
2016-01-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2CZZ0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YJC630342)
杨艳(1978—),男,副教授,行政管理学博士,E-mail:yangyan8@bi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