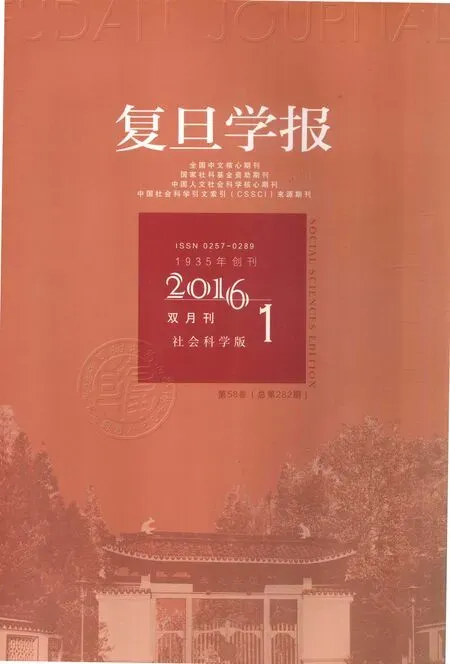争论中的“基因政治学”:理论、方法与范式
葛传红(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政治学研究
争论中的“基因政治学”:理论、方法与范式
葛传红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长期以来,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先验地认为人类是独特的,而社会差别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他们倾向于将文化与天性分开来看,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正是在这种“社会学习路径”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著名论断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中人类本性的部分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然而,随着“基因政治学”的兴起,“先天的思想”的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政治学界所接受,至少它已经成为了政治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并日益冲击着西方政治学的学科视野和学科边界。鉴于此,本文就以这一方兴未艾的“基因政治学”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发生与发展的由来、理论的主要内涵、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范式对政治学这一学科研究的突破性,同时也进一步展望其未来发展的导向与路径。
基因政治学 政治态度 自然实验 研究范式
一、引言
多年来人们观察到一个现象:美国大选时,为什么有人展现“政治狂热”四处拉票,有的人则“政治冷漠”闲坐家中?学者们一直认为是社会环境使然。身边人政治狂热,则自己也会受到感染;周围人政治冷漠,自己也将漠不关心。然而,在2008年,美国加州大学的政治学者詹姆斯·福勒(James H.Fowler)和克里斯托弗·戴维斯(Christopher T.Dawes)的研究报告发现,基因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①James H.Fowler and Christopher T.Dawes,“Two Genes Predict Voter Turnout,”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32008579-594.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特定的基因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political views)。两位学者在洛杉矶选区的调查发现,“同卵双胞胎”(identical twins,共享100%的基因)比“异卵双胞胎”(fraternal twins,共享50%的基因)表现出更高的相似的投票行为,而投票行为中53%的变化可以归因于基因。②Ibid.,pp.579-592.
事实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呼应了“生物政治学”目前的发展趋势。在该研究领域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认为基因跟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酗酒、性倾向甚至学业成绩等都密切相关。不仅如此,遗传学家们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遗传标记”(genetic markers)跟人类的健康、表现与人格相关,包括基因、荷尔蒙水平和神经传递素(neurotransmitter)等都能够影响并塑造人们对政治议题的态度。因此,一些精明的西方政治家企图利用竞选广告来影响这些要素,并最终对政治结果(选举)加以控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政治科学与基因研究却高度隔绝,生物学家与政治学家彼此隔离、互不往来,因此,鲜有真正的“生物—政治”跨学科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随新世纪的到来和选举政治的日益激烈化,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s)研究成为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化”领域的热门研究话题,但渐渐地学者们发现“政治两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现象日渐突出。为了更好地研究这种极端的政治行为,美国政治学者开始探索人类政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根源。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一些政治学者在这一领域展开了学术研究,研究的结果极具震撼力,当然也极具争议性。赞成者认为政治态度乃是天生遗传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而反对者则认为该研究领域误将“后天的政治态度”当成“先天的政治倾向”来建构乃是一种“学术的迷路”。
美国主要的政治学专业学术期刊诸如《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和《政治视点》(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等都刊发了相关的专题或专栏论文,来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和争鸣。其他的著名学术期刊诸如《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The Journal of Politics)等也纷纷刊载论文,加入到学界的大论战之中。
不管怎样,如今“先天的思想”(Innate ideology)的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政治学界所接受,至少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学的新兴研究领域(an emerging field),同时“基因政治学”(Genopolitics)的概念也应运而起,并日益冲击着西方政治学的学科视野和边界。因此,本文就以这一方兴未艾的“基因政治学”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发生与发展的由来、理论的主要内涵、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范式对政治学这一学科研究的突破性,同时也进一步展望其未来发展的导向与路径。
二、“基因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1986年秋,澳大利亚遗传学家尼古拉斯·马丁(Nicholas Martin)的研究小组在发表的论文里指出,“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在社会观点上展现了更高的相似性和共同点,因此,他们认为基因能够影响人类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诸如移民问题、堕胎问题和死刑问题等)。①N.G.Martin,et al,.Transmission f Social Attitudes,Proc.Natl.Acad.Sci.USA8319864364–4368.
尽管马丁的研究对政治科学极具暗示性,但政治学者倾向于忽视这个领域,因为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种族理论让他们记忆犹新,也让他们望而却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基因影响政治观点”的理论简直就是“种族歧视”的当代翻版。
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学术界对于马丁的研究成果保持了尴尬的沉默。
2003年4月,基因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中、美、日、英、法、德六国科学家联合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图完成,发现人类基因组含有2~2.5万个蛋白编码基因。科学界普遍认为,此项研究成果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从此树起了探索人类生命奥秘的新里程碑。
事实上,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读出全部的DNA序列,更重要的是读懂每个基因的功能,它要求人类真正地对生命进行系统的科学解码。然而,“基因图谱”并没有充分的信息来揭示人类生理与生活的秘密,因此,通过观察与实验的方法来“解码人类”(decode)就变得特别重要和具有学术价值。
2005年春天,三位美国政治学者(John R.Alford,Carolyn L.Funk,and John R.Hibbing)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在人类政治行为与基因之间存在着诸多“强相关性”(strong correlations)。②John R.Alford,Carolyn L.Funk,and John R.Hibbing,“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9.22005153-167.一般认为,该文在“遗传政治学”领域是一篇“走进新时代”的作品,但令几位作者失望的是,文章并没有引起预期中的关注。
不过,在经过大约三年的沉寂之后,“基因政治学”研究迎来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两位美国学者(福勒和戴维斯)在《政治学》上发表了他们的成果,认为投票率与政治参与之间具有坚实的基因基础。③James H.Fowler,and Christopher T.Dawes,“Two Genes Predict Voter Turnout,”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32008579-594.也就是从这篇文章之后,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遗传政治学”(The genetics of politics)的热潮,甚至连自然科学的权威期刊《科学》(Science)也专门发表论文来支持这个观点,认为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和生理特征存在着明确的关联。①Douglas R.Oxley et al,.“Political Attitudes Vary with Physiological Traits,”Science 32116672008.
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摆在人们的面前——长期以来“遗传政治学”有着不佳的名声,一般认为它是由达尔文主义和人种改良学复合而来的。因此,对于政治学者们来说,必须给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一个崭新的术语。
于是,在2008年,美国学者福勒将这一领域命名为“基因政治学”(Genopolitics),很快便被美国政治学界所接受。②James H.Fowler,and Darren Schreiber,Biology,Olitics,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Human Nature,Science 32259032008912-914;James H.Fowler,and Christopher T.Dawes,“Two Genes Predict Voter Turnout,”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32008579-594.2010年,彼得K.哈特米(Peter K.Hatemi)等八位学者就联合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撰文肯定了2005年该刊上的研究,认为其指引了此后研究的方向并使该学科得以实现发展和超越。③Peter K.Hatemi,et al,.“Not y Twins Alone:Using Extended Family Design Investigate Genetic Influence Political Belief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32010798-814.
此后,“基因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迅速在传统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上得到传播,有些人甚至还断定说“自由主义者是X”,而“保守主义者是Y”,他们分别按照各自的先天倾向在进行政治活动,从而赋予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以崭新的含义与阐释。④Peter K.Hatemi,and Rose McDermott,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Evolution,Biology,and Poli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三、“基因政治学”的理论与假设
虽然“基因政治学”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形成研究热潮,研究者也遍布世界各地,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研究主题都相对集中,研究方法也几乎大同小异,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总体上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因与意识形态:基因能影响人的政治观念
目前,基因政治学的许多研究都将政治观念的本质和来源作为研究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经典的政治学研究拉开了距离: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均认为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乃是个体与群体及社会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先天遗传因素所决定的。马克思特别在意阶级关系对人们政治意识的塑造,而曼海姆则将政治意识形态放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之中,并认为如果离开了社会背景,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意识形态了。⑤卡尔·曼海姆著,李步楼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3~68页。
然而,新时代的基因政治学者们则愿意另起炉灶,他们甚至还“骇人听闻”地宣称:先天的性状与后天教育在个人的政治发展上都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许多政治意识与行为都不是偶发的,而是植根于人们内在的物质因素,而某些特定的基因差异则将会促使人们持有特定的政治观念。
2005年阿尔弗雷德(John R.Alford)等三位学者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的文章认为,“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和“政治保守主义”(political conservatism)似乎是遗传的。⑥John R.Alford,Carolyn L.Funk,and John R.Hibbing,“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153-167.两年之后,哈特米等五位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对澳大利亚的双胞胎政治态度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⑦P.K.Hetami,S.E.Medland,K.L.Morley,A.C.Heath,and N.G.Martin,“The Genetics of Voting An Australian Twin Study,”Behavior Genetics 2007435-448.2008年,美国学者福勒和戴维斯在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影响人类政治意识形态的两种基因:“MAOA基因”和“5-HTT基因”。两位作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这两种基因不仅会影响人类的政治认知,也将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投票)。⑧James H.Fowler,and Christopher T.Dawes,“Two Genes Predict Voter Turnout,”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08588-589.
2010年,福勒与同事们又发现了一种被称为DRD4的基因,该基因与人们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密切相关。具体的作用机制是:DRD4基因可以控制多巴胺(Dopamine)的受体分子的生成,而那些体内有DRD4基因的变体7R基因的人(即DRD4-7R),他们更倾向于成为自由主义者(在西方的语境下通常为左翼人士)。他们发现,拥有DRD4-7R变体基因的人特别喜欢追求新奇事物和轰动效应,通常不能忍受单调的生活氛围,其原因就在于变体基因DRD4-7R影响了大脑的多巴胺水平:当多巴胺含量较高时,人就开始变得易于冲动、喜欢冒险、过度激动和容易发怒等(思想左倾的标志);而当多巴胺含量相对较低时,人常常表现得比较克制、循规蹈矩、忠诚可靠、勤俭节约和不温不火等(思想右倾的标志)。①J.E.Settle,C.T.Dawes,N.A.Christakis,and J.H.Fowler,“Friendship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Dopamine Gene Variant Political Ideology,”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01189-1198.
(二)基因与政治行为:行为模式可以遗传
在过去,社会决定论者一直不愿承认基因对人的政治行为有影响,甚至还否定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但基因政治学者们则另辟蹊径,数年来他们坚持不懈地对全球数万名双胞胎人口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很明确地指出:与政治有关的行为模式有遗传的可能,也就是说个体间的遗传差异,可能在形成个体间不同的行为模式中发挥了作用。
2008年,福勒等人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研究就指出:基因不仅仅只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与观念,还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尤其是政治参与程度)。通过对洛杉矶双胞胎选民的登记情况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与美国全国性的数据相比,洛杉矶同卵双胞胎在“参与政治”(political participation)以及“不参与政治”的程度上都比异卵双胞胎高出53%。很显然,基因在其中起到了明显的作用。②James H.Fowler,Laura A.Baker,and Christopher T.Dawes,“Genetic ariation in olitical articip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222008233-248.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是“何种基因”在起到这样的作用?在同一年稍后发表的论文里,福勒等人明确指出5-HTT基因对选民的投票行为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具体的作用机制是:5HTT基因可以控制5-羟色胺在人体内的水平,当其水平较高时神经递质活跃度会很高,因此选民就会表现出相当的政治热情去参加投票;反之,则选民表现出相当的政治冷漠而拒绝去投票。③James H.Fowler,and Christopher T.Dawes,“Two Genes Predict Voter Turnout,”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8580-582.
2009年,福勒与其同事戴维斯又发现了影响人类政治行为的另一个基因——DRD2。具体的作用机制是:DRD2基因可以影响到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当其水平较高时选民表现出对党派的强烈感情,因此倾向于去参加投票;反之,则选民表现出对党派的政治冷淡而拒绝去投票。④C.T.Dawes,and J.H.Fowler,“Partisanship,Voting,nd he Dopamine D2Receptor Gene,”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91157-1171.
(三)基因与社会环境:基因会影响人的一生
必须指出的是,基因政治学并不意味着“基因决定论”。很多基因政治学者的研究并不排斥社会环境的因素,相反几位作者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在整个过程中,只有当携带特定变体基因的人与社会环境(通常拥有很多朋友)同时存在并互动时,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才会显现。
事实上,上述观点已成为基因政治学界的共识。与此同时,“基因—环境”(Gene-environment)的新范式也在逐渐构建与形成中。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著名的基因政治学者哈特米便断言说:基因对人们世界观的影响,与环境对人们世界观的影响基本持平。⑤Peter K.Hatemi,and Rose McDermott,“The Genetics f Politics:Discovery,Challenges,Progress,”Trends in Genetics 2810 2012525-533.
不过,在不同的年龄段基因对人的影响力则有所不同。由于受到家庭以及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在9~17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的政治观点保持着很高的相似性;二十几岁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以后,他们的政治主张开始出现差异;在成人之后人们的政治观念则趋于稳定。对此人们很容易认为,在青春期从父母那里“学习”得来的政治观念将影响人的一生,但这种观点近年来受到了基因政治学者们的挑战,他们要问:“难道父母早年的影响真的能跟随子女们一辈子吗?”“难道中间就没有基因的影响吗?”
对于此种疑问,基因政治学者们通过各种研究来试图回答。据哈特米与他的研究团队在2009年发布的研究,他们发现基因能够影响政治观念的代际遗传,并与环境因素一起对人类的政治观点与行为施加着影响:
(1)在青春期的最后阶段(18~20岁),不论是同卵双胞胎还是异卵双胞胎,政治意识有70%相似,显然环境影响的因素比重较大;
(2)在20岁之后,双胞胎们的政治意识相似性开始下降(环境影响下降,基因影响开始稳定凸显),在21~25岁之间,同卵双胞胎的相似比降低到60%,异卵双胞胎的相似比则降低到40%;
(3)在25岁之后,同卵双胞胎的相似比基本稳定在60%以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上升的趋势,在71~75岁之间相似比更达到接近80%的水平;与此同时,异卵双胞胎的相似比则基本稳定在40%左右,即使在71~75岁之间他们的相似比达到最高的水平,但也没能超过45%。
显然,基因在其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①P.K.Hatemi,C.L.Funk,and S.E.Medland,et al,.“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Transmission f Political Attitudes Life Time,”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1320091151-1153.
四、争议“基因政治学”
虽然基因政治学横空诞生了,但与此同时也引来了空前的学术大论战。主要有两位学者对基因政治学提出了挑战,一位是来自杜克大学的伊万·查理(Evan Charney),另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威廉·英格里希(William English)。两位学者联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对基因政治学者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因结构的差异并不能先验地导致特定的政治认知与行为。两位学者批评道:基因型(genotype)与表现型(phenotype)之间并不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而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然而,福勒与其同事的研究则过于简化,简单地进行“自由—保守”(the liberal-conservative)的二分法的研究,结果就将研究变得非此即彼、非黑即白。②E.Charney,and W.English,Candidate Genes nd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6.1(2012):11.两位学者还尖锐地指出,人类已经发现的25000个基因绝不是儿童的玩具(比如乐高玩具),可以任人任意地拼接与组合,因此这种过分简化的研究是荒诞而可笑的。③E.Charney,and W.English,Genopolitics and the Science of Gene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722013382-395.
二是基因政治学者的统计方法非常幼稚(naive)。无论福勒与其同事,还是哈特米的学术团队都使用了定量研究方法,整个研究过程都坚持严格的定量标准,比如数据的来源——调查问卷——也尽量做到样本规模足够大(有时甚至高达上万个)和来源的广泛性(跨国研究),调查结果也都是相当显著的。然而,查理和英格里希这两位学者则使用了讽刺性的话语来批评,将基因政治学者的定量研究斥之为“幼稚”。在他们看来,基因政治学并不是统计学的分支学科(subfield),而基因政治学者却昧于(uninformed)近50年的基因科学发展的根本原理于不顾而贸然进行所谓的“学术发现”——盲目地进行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简单回归分析”(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④E.Charney,and W.English,385-393.
面对着如此激烈的批评和讥笑,作为基因政治学最著名的学者,福勒与戴维斯挺身而出,发表了《为基因政治学申辩》的文章(2013)。⑤J.H.Fowler,C.T.Daw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722013362-374.在文中两位学者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和逻辑将“恶意的讥笑”一一化作云烟。他们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承认MAOA基因可能并不显著,但复盘的结果是5-HTT基因的表现非常强劲。为了回应批评,两位学者又再次复盘了实验过程,而样本容量也由原来的2300个增加到现在的9300个(这样可以使结果变得更加精确),而最后的结果也让他们非常满意,从而再次证明基因政治学并不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其次,不能因为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就不进行学术研究。在查理和英格里希的批评里,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此,进行简单对应式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就是根本错误的。然而,福勒与戴维斯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信正是因为复杂才体现出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发现可能存在的机制便成为了基因政治学的首要任务。
最后,应该搭建生物学和政治学研究的桥梁,而不是人为地加以阻隔。两位学者乐观地指出,“基因政治学的未来无疑是光明的”,而且生物学也应该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⑥Ibid,.pp.362-369.
五、研究方法与范式
事实上,基因政治学的建立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事实依据:其一,是已有的关于双胞胎的研究——比较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的不同;其二,是最近对人类DNA的直接研究——寻找导致不同个体间明显行为差异的特定基因。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上文讲到的定量研究法之外,他们主要依赖的方法是自然实验法,并意图通过大样本的研究来发现可能存在的真实机制。
(一)自然实验法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一直向往着自然科学的学术境界,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可复制、可验证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达到精确和科学,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实验可能是最好的方法。然而,遗憾的是,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是根本无法进行实验的,比如人们无法通过实验来研究革命,也无法通过实验来研究社会动乱,因此,这便成为社会科学永恒的遗憾。
不过,社会科学家们也逐渐发展了一些实验研究的方法,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便是其中一种最方便、最直观的研究方法,并日渐显示出强大的学术研究潜力。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会将自然实验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强大的统计软件的帮助下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①Jared Diamond,and James A.Robinson,Natural Experiments of Hist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事实上,双胞胎研究是“自然实验”中最经典也是历时最久的一种研究。早在20世纪初期,关于双胞胎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在当时,各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关于双胞胎与政治倾向的研究,研究成果大多显示同卵双胞胎在各方面都比异卵双胞胎更为相似。
不仅如此,对于研究的成果和结论,研究者们还在动物(比如猴子、老鼠等)身上做实验来加以检验。因此,人们可以有理由地说:“自然实验研究方法是严密而客观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因政治学者们对双胞胎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有三个特征:
首先,时间跨度比较大。比如在阿尔弗雷德等人的研究中,他们的时间跨度是14年(1980~1994),该项研究共调查了10000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主要问题是调查遗传因素和政治倾向之间的相关性。问卷一共设计了28个问题,主要集中在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上,诸如“死刑问题”、“流产问题”和“裸体露营”等。②Alford,John R,.Carolyn L.Funk,and John R.Hibbing,“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22005153-167.
其次,年龄跨度比较大。比如哈特米2009年发表的研究,对双胞胎研究的年龄跨度高达66岁(涵盖9~75岁之间各个年龄段),几乎涵盖了人的一生,而研究的意义也一目了然:基因真的能够影响人的一生(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attitudes over a life time)。③P.K.Hatemi,C.L.Funk,and S.E.Medland,et al,.“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Transmission Political Attitudes Life Time,”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1320091141-1154.
最后,空间的跨度比较大。在2012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哈特米及其团队的研究不仅时间跨度长达近40年(1970~2010),在空间跨度上也涉及世界三大洲的四个国家(所涉及的双胞胎研究对象来自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和美国)。他们就范围广泛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与倾向进行测验,其中包括个人政治态度、左右思想倾向、社会经济和防务认识以及对于威权政治的态度等。最后的结果揭示,这些问题都与人类的基因状况密切相关。④P.K.Hatemi,et al,.“Genetic Influences n Political Ideologies:Genome-Wide Findings Three Populations,A Mega-Twin Analysis 19Measures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In Behavior Genetics Association 42nd Annual Meeting Abstracts,2012.
(二)研究范式
从学科上来看,基因政治学的研究都是跨学科研究,研究者往往将政治学、心理学、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融合在一起,并希望能够发现隐藏在基因背后的生命奥秘。虽然在此之前也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但可惜的是他们都未能发现基因作用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机制。
按照马里奥·本格(Mario Bunge)的论述,科学研究的终极任务就是发现事物(或系统)的机制(mechanism)。⑤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741997 410-418.而著名的社会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则把机制放在本体论的地位,认为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empirical invariance),即机制(mechanism)。①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3rded(London:Routledge,1998)18-22.
其实,在福勒和戴维斯稍早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的论文中,两位学者就证明了基因是可以对人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施加一定影响的,但这还不是对于机制的分析。②James H.Fowler,Laura A.Baker,and Christopher T.Dawes,Genetic in articip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222008233-248.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只是研究的第一步。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证明基因是可以影响人类的思想与行为,那你就必须找出具体是何种基因,并论证其影响的具体机制,否则还只能是一种猜想而已。
对于两位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学术挑战,但他们并未畏缩,相反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他们成功构建了MAOA基因和5-HTT基因影响人类政治态度和行为的机制:(1)MAOA基因和5-HTT基因可以影响大脑中血红素(serotonin)的水平;(2)血红素能够影响大脑的新陈代谢;(3)血红素与人类的情绪密切相关(诸如恐惧、信任和合群性等)。③James H.Fowler,and Christopher T.Dawes,“Two Genes Predict Voter Turnout,”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08):579-581.客观地讲,这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时刻,它意味着政治学研究范式的一次大飞跃和大突破。
学术界也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only approach)范式构成了学科上的根本性冲击。对此,哈特米兴奋地谈起了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问题。在2012年发表的研究论文里,哈特米指出,一般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主要有两个范式,即社会—心理范式(social-psychological paradigm)和理性—行动范式(rational action paradigm),但现在他则发现了第三个研究范式——基因范式(genetic paradigm)。针对这后一个范式,哈特米明确地宣布:“这乃是我们已知意识形态的终结(It's the end of ideology as we know it)。”④P.K.Hatemi,L.Eaves,R.McDermott,“It's the End f Ideology As We Know It,”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2012)345-369.
然而,“范式”(paradigm)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词汇,它来自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⑤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6~188、158~166页。按照库恩的说法,科学的成长离不开“范式的突破”,换言之,即“科学革命”。
事实上,科学革命总意味着旧传统的破灭和新楷模的建立,同时也使科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⑥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6~188、158~166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基因政治学是政治学研究一个根本范式的转变。它不仅意味着政治学研究的新路径,甚至也意味着整个政治学研究都要面临新的变革。
六、结语
在政治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先验地认为人类是独特的,而社会差别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他们倾向于将文化(culture)与天性(nature)分开来看,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学习路径”(social learning approaches)的影响下,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亚里士多德著名论断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中人类本性的部分。
事实上,这乃是政治学研究中“人类本性的迷失”,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图景。然而,幸运的是,基因政治学的出现正在日渐改变这种状况,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中“人性的回归”了。
尽管基因政治学的真正发展还不到十年,但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当然,也必须明白,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缺失和不足。也许基因政治学研究者还不能立即撼动政治学传统研究的理论“大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研究正为政治学研究实现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全面突破带来新的想象与可能。
[责任编辑 刘 慧]
Genopolitics in Controversy:Theory,Method and Paradigm
GE Chuan-h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For a long time,in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instinctively believe that the human being is unique and social difference is caused by social environment.They tend to consider the culture and nature separately and even put them in the opposite positions.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eeply ingrained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many scholars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ignore one of Aristotle's famous judgments—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However,with the rise of genopolitics,the viewpoint of innate ideology has been largely accepted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At least it has become an emerging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and gets increasing impact on th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boundary.In view of these facts,this paper takes genopolitics as the object of study,analyzes its origin,main connotation,main research methods,research paradigm,and its breakthrough for political science.Finally,the orientation and approach of genopolitics i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is also prospected.
genopolitics;political attitude;natural experiment;paradigm
葛传红,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砖国家’机制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研究”(项目批准号:11CGJ003)和华东政法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强国集团’的道路:关于‘金砖国家’国际战略的比较分析”(项目批准号:11H2K043)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