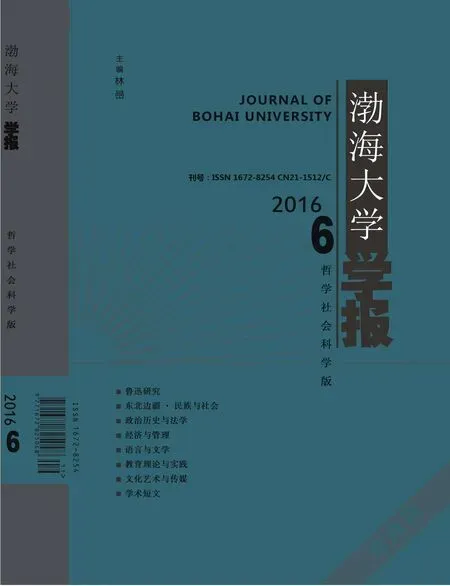读解鲁迅的若干门径和细节
刘恩波
(辽宁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11)
鲁迅研究——纪念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专辑
读解鲁迅的若干门径和细节
刘恩波
(辽宁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11)
研读鲁迅,有各式各样的路数,传记式的,个人印象式的,文化批判和生命哲学式的,等等,共同构成了走进鲁迅精神世界的门径。其中,有意味的细节是读解鲁迅性格的一把钥匙。
读解;印证;回忆
自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后,其生平功业所形成的魅力和影响就一直深深根植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核心腹地,作为精神价值的超级符号指涉,鲁迅经历了被神圣化、人间化、大众化等若干历史阶段的不同读解。偶尔,这三种读解方式会有重叠、相遇和整合。但是,更多的时候,它们分别代表了从相异认知视角、各自人生体验和不同文化关怀立场对先生所作出的理解、剖析、阐发和论辩。以本人的孤陋寡闻,不可能全面评估和权衡这些观点见识,故而以下仅仅是我对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读解鲁迅方式的微观介绍和扫描式分享。不足之处,求教于方家。
一传记式的读解
以传记文学的别具只眼走进鲁迅那斑斓错杂的世界,当为一方面法门。有一年给远在广州的林贤治兄冒昧地写信,请购《人间鲁迅》,他回信,说手头没有存书了。林氏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的大作《人间鲁迅》别具肝胆和情怀。我只是在大学图书馆偶读个别片段,遂起常相与共之意,未能如愿。好在不久就买到了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阅读之余,觉得王氏的看法和领会,同样穿过了鲁迅精神的重重烟雾,给我们还原出了一个本真的鲁迅。正是读王晓明的书,我才终于理解,在和“鬼气”的对抗中,鲁迅有着怎样丰富多姿的生命造型。尤其是他重点写了鲁迅和许广平发生的那段师生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读者是有着相当诱惑力的。我好奇,我探知,心里盘算着这位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是如何谈情说爱的。以往人们圣化鲁迅神话鲁迅,他的形象就是锋芒毕露的思想斗士,就是民族的脊梁,就是那个说过无端地浪费别人的时间的人无异于图财害命的有点刻薄的老夫子。哦,看到王晓明的文字,我不由得会心一笑。原来鲁迅也有他的念兹在兹的人间情怀。“一九二七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但却碰伤了脚……”[1]从这些微小琐事里,不难看出,“为了焕发青春的气息,他的确是尽了全力了。”[1](126)王晓明如此看重细节,意在对一个伟人的精神的光芒,寻求其多层面的表现。尤其难能可贵的还在于,他一方面发现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相恋,等于打开生命的一个缺口,似乎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而另一方面,他又为我们揭示了鲁迅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事,在今天看来太不可思议了。那是与许广平去杭州度蜜月期间,到了晚上,他指定许钦文睡中间那张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如此遮遮掩掩,无非怕人非议,传闲话。也许正是浸润于这种悲哀而无奈的细节深处的点染和捕捉,才有可能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20世纪20、30年代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去感受封建道德礼法的无形窒息和压迫,才能让人切身感受当初鲁迅先生意欲肩起黑暗闸门冲出鬼屋的那种决绝、愤懑和不屈的斗志之所由来的理由和实况。
平心而论,王晓明的书写有些时候未免过于用力,常常将自己的思想也燃烧进传主的个人情感世界所提供的材料里,无以自拔。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想象着鲁迅的绝望,挣扎和救赎,多有戏剧化的笔法,但是由于作者是在吃透了鲁迅的丰富的精神遗产之后而引发的写作激情,故而这种激情本身,就带着强烈的辐射力和个人经验熔铸的魅力,反倒越发吸引我们参与进去。
王晓明的读解鲁迅,显示了文学史传在剥离历史迷雾,映衬传主内心灵魂本色的努力之中所呈现的精彩和深邃,应该说《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主要不是客观认知视域下的鲁迅研究,而是主体体验型的艺术生命的再造。
传记类的关于鲁迅的研究,还有多种文字传播,可供参考。像孙郁寻找“五四”一代人的坐标而将鲁迅和胡适、鲁迅和周作人进行的文化价值意义的对比性梳理,其中多有对传主性格和命运轨迹方面的深层次开掘,就是读解鲁迅精神的另一种尝试、融汇和创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二、个人印象式的读解
这种读解方式,主要是来源于鲁迅同时代人的追忆和回忆录性质的文字。在我看来,个人印象的聚焦、定格和回放,会把那个时代的鲁迅的特征、举止、做派甚至精气神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地镌刻在历史的册页中。同时代人回忆咀嚼鲁迅,或褒或贬,或为尊者讳,或不计较个人恩怨秉笔直书,都会形成不同凡响的生命参与意识和直接经验传递的感觉印证式的复原效应。
此类文字中,最珍贵的当属亲人、朋友、同侪乃至论敌的书写和点评。以我微薄之见,觉得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等篇章,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林语堂的《鲁迅之死》等作品均构成了对鲁迅精神面貌全方位的逼近和写真。
回忆和见证鲁迅,许广平当为首选者。尽管她的《鲁迅回忆录》写于1959年,有“献礼”和“遵命”之嫌,但是,作为鲁迅夫人和历史当事人的叙述,许广平的回忆,依然是研读鲁迅的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在许广平的笔下,鲁迅是生动的,鲜活的,个性的,有许多活着的风趣和积习。我尤爱读她关于“鲁迅的讲演和讲课”一节,里面把鲁迅的外貌写成“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的瘾君子”,但是一到了讲台上,“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地舒畅。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2]
实事求是地说,《鲁迅回忆录》充满了人文掌故式的追忆、回眸和打捞,诸如对鲁迅的交往、鲁迅的斗争、鲁迅的脾气和性格等等,都做出了既有历史可靠性的见证;然而,书中也有不少违心的应景之论,迫于形势的越位见解,像对胡风和冯雪峰的抵触和曲解,完全写成了划清界限的不实之词。其实,这不仅仅是许广平的局限,从中更能折射出历史潮流和时代倾向对写作者本人的先入为主的抑制和盘剥。
于是,许广平就那样身不由己地徘徊在亲人鲁迅和战士鲁迅之间,进行着个体的解说,又带上了社会惯性的枷锁。她在主观立场上,要把鲁迅写得更加完美高大,像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而另一方面,因为深深理解鲁迅的精神和命运身世,那种其来有自的渊源又让她不能不设法记录下鲁迅的一些天真有趣可爱之举。某些段落,竟然又让我们栩栩如生地看到了《两地书》中那个亲切熟悉的鲁迅。
萧红大概算得上鲁迅的亲炙弟子,是忘年交。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许多文字祭奠这位可敬的长者,其实也是她精神上的父亲。在萧红笔下,鲁迅走路轻捷(“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笑声明朗(“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而且懂得女人着装的颜色搭配,喜欢吃北方饭,记忆力非常之强,经常陪着客人聊天一直到深夜,“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女性作家是长于关注细节的,善于用质感的捕捉和描绘,来打量笔下人物的神态举动,揣摩他的心思和意气。萧红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如果说,许广平用粗线条的笔法勾勒了鲁迅的生平概貌,萧红则是以工笔与白描相间的手段,为我们传神地抓握了鲁迅多姿多彩的瞬间速写。如果说,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是领着我们走进了先生的前院,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却是踱入了他的后花园。那里有更多的生命常态和人间烟火气息。那些迎来送往,居家过日子的小细节,为萧红娓娓道来,大概称得上鲁迅写真的最富有人间情怀的微缩版本。
至于许寿裳追忆鲁迅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同样是现当代鲁迅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许寿裳与鲁迅有长达35年的交谊,自留学日本起,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人说,这等感情“不异骨肉”。故而,他对鲁迅的记录、理解和剖析,常常会给我们不小的启迪。譬如,书中谈到鲁迅对佛经的喜欢,鲁迅向佛,但不是崇拜和信仰,“他对于佛经只当作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联想到曾有日本友人称鲁迅为隐居在都市里的佛神的说法,我觉得许寿裳特重鲁迅的佛学知见,还是属于知人会心的别样读解的。只是他的书限于鲁迅生平介绍,而离生命哲学本身的探讨似乎还隔了一层。
与许寿裳和鲁迅终身相契不同,林语堂和鲁迅是半路知己,半路论敌。因为林氏后来一意孤行地推崇闲适的小品文创作和标举费厄泼赖精神,鲁迅专门写文唱对台戏,闹得两人不欢而散分道扬镳。尽管如此,鲁迅生前身后,真正看透了先生为人为文实质的人,其实并不多。这里面就有林语堂。实在地讲,林语堂写于鲁迅去世隔年回想的文章《鲁迅之死》,是研读鲁迅的大手笔,虽说此文不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物换星移之际,它分明印证着一位同代人对先生生平功业和个性的鞭辟入里的精到剖析与确认。
远离上海远离故国,隔着千山万水,林语堂在纽约读鲁,似乎是隔岸观火,却更加洞察幽微,许多说法,甚至撕开了鲁迅研究迷障上的豁口,从而超越了派系纷争形成的时代局限和认知困扰。
是的,局外人才能看到局内的迷惑与盲从。就如林氏文字中的一语破的,“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不正是这80年来鲁迅研究和接受史上所一目了然的景观抑或症结所在?
为鲁迅涂脂抹粉,表面上看抬高了乃至神话了鲁迅,但实际上是隔离和人为地设置羁绊,让鲁迅远离时代的哀痛人性的盲点和个性的有缺憾的大美之所在。而如林语堂那样以披肝沥胆之沉痛笔触,揭橥鲁迅活生生的气脉精魂,切肤痛痒,远远比放大聚焦的夸饰和炫耀,更能还原鲁迅的真正所在。
林语堂说鲁迅“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在林氏笔下,“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之鲁迅,“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之人,是鲁迅精神的还魂和写真。他说,鲁迅者,亦有一副大心肠,随着“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天地间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生命,及到灵感忽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地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这大概是80年来写鲁迅之死的最佳文字了。同一营垒里,只见到膜拜推许直到“厚诬”的写法,敌对阵营里便是丑化漫画化式的抹杀,而林氏的手段,则是透视,是激赏,是争辩,是镌刻和拓印,唯有真懂鲁迅者,才有醉意叹息,才有混沌迷离,才有爱恨交织的陷入……
三、文化批判和生命哲学式的读解
研读鲁迅视角不一,方法迥异,盖因他的精神内核、创作风格、思想底蕴和心理成熟度,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绝无仅有,故而,采取文化批判和生命哲学式的分析、考察与辩识,当能从宏观一点的立场和视点走进鲁迅灵魂深处的堂奥,窥其风骨,探其源流,明其品性。
李长之所著《鲁迅批判》大概称得上此类研究的发轫之作。一个25岁清华大学在读生写的尝试性论著,却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也是唯一经过鲁迅本人披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它的起点之高,用意之深,阐发之悠远,堪为异类奇葩。
本着爱越深,故苛求也切的态度和立场,李长之在研读鲁迅的领地甫一发声,就能超拔世俗习见而振聋发聩,实在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已经站在20世纪人类思想潮流的前沿。他一反常态,没有采用正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而是用精神分析的手段从鲁迅的情感症结上着眼,去触摸鲁迅精神深处的暗礁。李长之认为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灵魂的深处“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尽管这“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李长之眼里的鲁迅不是个完人圣人,他的缺陷却恰恰成全了他的人格上的健朗,他的神经质相反造就了他作品的敏锐,穿透力和颠覆意识。李长之看到了人的性格和他赖以生长的环境的互相塑造和制约关系,这在鲁迅身上表现为病态的社会、家境的颓靡带给他不能自拔的原生态的仇视和自我怀疑。他不仅自我怀疑而且怀疑一切,从而有一种对毁灭的透入骨髓的大欢喜。在《野草》里,他的心是荒凉的,跃动的,充盈着希望和虚妄,在《故事新编》中,他的笔是带着复仇者的快意的,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他却刻意倡导“人得要生活”的类似进化论的单纯的生物学的信条……概而言之,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显示了批判者的眼光、胸襟和气度,他既不膜拜权威,也不摆放自己,而是捧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心,把生命的热力与理智的清醒营造成寄托和审视他者和自身灵魂本相的讲台和祭坛。
李长之是有才气的,是多情的,是敏感而丰富的,他探讨谈论鲁迅的口吻是一个青年人的不世故、不妥协、不屈从的,故而也是高傲、省察、幽邃的,在许多地方,都毕露了他本人思想上的锋芒和性格上的棱角。这其实恰恰和他所谈论的鲁迅是有着若干契合的贴近的。譬如,他说鲁迅“不会世故”,并且举证,“他和这个战,他和那个战,结果这里迫害,那里迫害。他不知道有多少次,纠合了一些他以为有希望的青年,预备往前进,然而骗他的有,堕落的有,甚而反来攻击他的也有,结果还是剩下他自己。他哪里有世故呢?他实在太不世故了。”[3]
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和视角审视剖析鲁迅的爱与恨,悲和喜,残缺与钝拙,理智及其非理性等性格、命运乃至潜意识心理上的表征,构成了李长之《鲁迅批判》的独特光芒和内蕴。当同时代的人或者偏于个人恩怨和情感,或者倾向于党派流派的成见,无法对鲁迅形成整体性的比较中立和客观的个案研究,那么《鲁迅批判》的出现,就成为鲁迅阅读史上筚路蓝缕的拓荒之作。
或许某种程度上李长之对鲁迅情感病态的某些解剖过于严苛,但是,应该说那是最早的对于鲁迅内心之中潜隐的黑暗世界的洞察和深度认知。诚如后来杰出的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夏济安指出的,鲁迅对他幼年时世界的描写标志着对一种“黑暗之力”的迷恋(参阅夏济安《黑暗的闸门》)。再以后异军突起的李欧梵以探索鲁迅内心意识发展的《铁屋中的呐喊》,将海外的鲁迅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无论夏济安还是李欧梵,他们对鲁迅的内心的“鬼气”(即某种“阴暗面”抑或“颓废面”)的研读和解剖,似乎可以看作是李长之文化批判的某种延续、对位、呼应和拓展。
如果说,当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对于鲁迅的正面形象的过度阐释之后,反之,再来领略关于他的负面倾向的读解和梳理,反倒觉得那更像鲁迅本人。对生命弱点、癖好、潜意识的深入骨髓的写照和解剖,不也正是走进鲁迅理解鲁迅的必经之地吗?
要知道,在艺术接受上,正负能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意识和潜意识是互相打架的。本我和超我的角逐从来不曾消停。而这恰恰是艺术自身的活力所在。
我以为相比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收录在本书附录里的文章《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可能对鲁迅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与挖掘,会显得更为出神入化。
李欧梵的话题是从参观鲁迅故居时,对先生卧室里摆放的三张以女人为主题的木刻产生了不解。有两幅描绘的是裸体的女人,而其中一幅还有点《天方夜谭》式的传奇色彩。而这与鲁迅晚年的革命和激进毫不相干。如何理解这种一目了然的错位和落差呢?在此引发了李欧梵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他辨证地认识到“鲁迅一生中在公和私、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存在了相当程度的差异和矛盾,如果说他在为公、为社会的这条路线上逐渐从启蒙式的呐喊走向左翼文学和革命运动的话,他在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个人的艺术爱好上,似乎并不那么积极,那么入世,甚至有时还带有悲观和颓废的色彩。”[4]
这是很准的为鲁迅把脉,确实鲁迅艺术观念里容纳了许许多多的杂质,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表现主义,从革命到唯美到颓废的风格,他采取的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立场。根据李欧梵的研究,在鲁迅作品中尤其是《故事新编》和《野草》里,其实荟萃了不少反传统的呈现爱欲、超现实的梦境和主观变形的东西,这是鲁迅的超级写作,跨越了生死界碑,打破了道德礼教的禁忌,“很容易看得出现代艺术意义的表现”。按照李欧梵的看法,“艺术是和庸俗的外在生活针锋相对的”,那么“出自一种对本国传统文化反抗以后所要摸索的现代感”,鲁迅的某些旨趣和爱好“在基本精神上有些地方是和西方现代艺术相通的。”
李欧梵举了《过客》的例子,以为这部散文诗式的剧,会令人想起贝克特的《等待果陀》(通译为《等待戈多》)。鲁迅《过客》的主人公一直茫无目的地在旷野里走,据说前面有个声音叫他走,这跟《等待戈多》中流浪汉的无所适从的傻等,又有何差别?都是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做、徒劳的生和徒劳的死,这当然是现代意识,类似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的意识,鲁迅居然比萨特、加缪还有贝克特整整早了二三十年。
正是基于此,在对生命极限和宿命般的反抗的领悟中,鲁迅的创作显露了哲学的意味。对此,李泽厚以“提倡启蒙,超越启蒙”来划定鲁迅前后的思想行踪。其具体论述见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的若干部分文字。在李泽厚笔下,鲁迅曾经将人性的孤独和悲凉展现出丰富芜杂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并且结合某种刻骨铭心的荒诞感,从而获取了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
李泽厚从鲁迅的《野草》中找到了心灵无所归依的证词,死亡意识的无处不在,人生搏斗的茫然感,绝望里隐藏的虚妄和依恋,向炼狱突进的欢喜,那就是鲁迅式的体验和认知。应该说李泽厚对此所做的剖析是有力量的并且深具人文内涵和底蕴,他说,“鲁迅对世界的荒诞、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敏锐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浮泛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浮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可惜加缪晚生,否则加缪将西绪弗斯徒劳无益却必须不停歇的劳动(向山上推石头,石头刚推到山顶就滚下来,又重新开始向上推)比作人生,大概是会得到鲁迅欣赏的吧?”[5]
从生命哲学视点出发,李泽厚对鲁迅的捕捉和勾勒,站在东西方思想互相碰撞、洗礼与交接之处,显示了将传统倾向和现代潮流、生命本体和命运意识、家国情怀与漂泊无根的精神漫游交织渗透整合在一起的新的读解可能。
四众声喧哗:永远无法穷尽的鲁迅
不必讳言,鲁迅是一个永远的谜。就像王乾坤在他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增订版)的“自序”中说的,反观中国几千年的精神资源,无论如何,鲁迅是一篇独异的故事,一个不曾有过的结构。
80年来,鲁迅作为巨大的文化遗产,其魅力历经时代变迁而不减。这是一个被高估的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分凸显了他的革命性),也是一个被遮蔽的人(人们往往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连同对他的阅读很长时期都显示了公共话语的同一性均质性)。然而,他又命中注定是我们无法忘却的人,一个永远无法穷尽其价值和意义的大师。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鲁迅终于走下了神坛,不再被文化消费时代刻意邀宠,人们似乎有意识地疏远了鲁迅。但是,鲁迅的流风余韵依旧伴随着思想和思绪的每一次潮汐律动。从若干年前葛涛编选的《网络鲁迅》到陈丹青最近一些年来数次的“笑谈大先生”,乃至在此之前出现的王朔对鲁迅的非议和批评,鲁迅的形象越来越远离公众化而成为个人的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师长、朋友抑或被质疑反感的文化巨无霸的存在个案。
鲁迅就这样离开了历史,走进了生活。离开了刻板的教科书,走进了沙龙、网络或者会议室。鲁迅被抬举着,赞许着,诋毁着,误会着,也越来越被“价值削平”,被“解构”。以至于在许许多多的场合和谈论中,“谁是鲁迅”日趋成为一个问题。也许,追问“谁是鲁迅”恰恰证明了一个文化开明时代的到来,人们不再大一统,按照一个固定的砝码和尺寸来称量和丈量鲁迅。
浏览互联网上关于鲁迅印象的各式各样的记录和表达,我们会由衷感到鲁迅又变得精彩和年轻了。先生的精魂不死,先生的文字依旧涌动着蓬勃的感召力与特殊的吸引力。只要沉下心来读一读《网络鲁迅》,聆听这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众声喧哗,那么我们对“谁是鲁迅”当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和理解。
这是来自民间草根阶层的朴实的看法、体味和印证的集结与融汇,以其火辣辣的热忱,甚至轻率无知的孟浪,以其发自内心情绪的释放和流淌,从而颠覆了正统的正版的鲁迅形象。在那里,放谈无忌,没有固定路数,逃离专家视野,拒绝历史理性价值的板上钉钉,人们说得痛快,我行我素之中,多少有点像话语的狂欢节的意思。
当然,如果剔除其中的一些杂质和过激因素,网上的议论还是能为解读和研究鲁迅提供一扇聚焦的窗口,这些漫不经心随心随意中传递的信息,依然会成为后人走进鲁迅声音和身影的门槛与路径,是的,起码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参照。
[1]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26.
[2]许广平.鲁迅回忆录[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32.
[3]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145.
[4]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香港:三联书店,1991: 222.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 2008:119-120.
(责任编辑 陈方方)
Details and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 LU Xun,the Writer
LIU En-bo
(Institute of Art,Liaoning Province Department of Culture,Shenyang 110011,China)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understand LU Xun,and those ways constitute approaches to enter into the spiritual world of LU Xun,the famous Chinese writer.For example,we may understand him through his biography,personal impression,cultural criticism,life philosophy,etc.In particular,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him is the interesting details about him.
understanding;proof;recall
I210.97
A
1672-8254(2016)06-0001-06
2016-07-10
刘恩波(1968—),男,辽宁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一级作家,辽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家,辽宁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辽宁电影家协会理事,辽宁戏剧家协会理事,辽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从事文学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