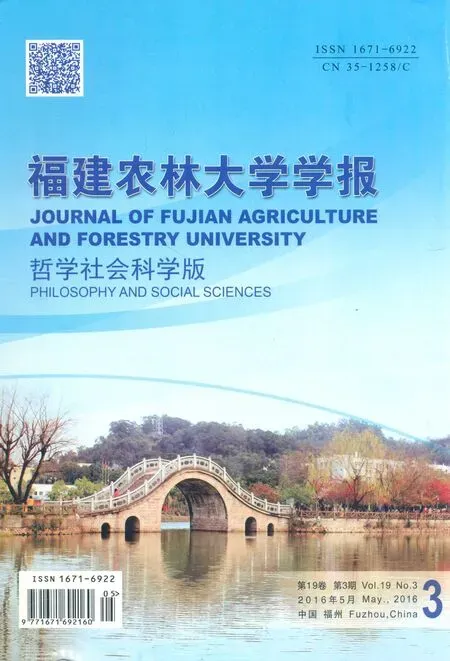农业现代化的反思与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
张孝德, 张文明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北京 100089)
农业现代化的反思与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
张孝德, 张文明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北京 100089)
[摘要]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的“存”与“亡”成为学术界和有关部门争论的焦点。部分学者基于农业现代化与传统小农之间生产方式差异性的判断而形成小农经济消亡论。然而,执此类观点者忽视了农业现代化强势之下所引发的农业功能错位、农业经营主体不明、农业大规模经营失灵等问题,忽视了世界农业经济“小规模”经营回归趋势,由此形成对小农经济的认识误区。中国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需要得到进一步认识:因自给自足及低劳动力成本而形成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生产性),因蕴含农业生态性而促成多元化农业发展(生态性),因体现生命价值与人性而成为农民生计底线(生活性),因维持着乡土社会稳定而成为乡村文化载体(文化性)。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所在是正确把握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困境及化解路径的前提,也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小农经济;生命力;农业现代化
[DOI]10.13322/j.cnki.fjsk.2016.03.001
传统小农经济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小农经济的利弊讨论形成小农经济存亡之争。在厘清何种方式的农业现代化适合中国,以及回答了为了谁的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有助于走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一、农业现代化与小农经济存亡论争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有着很长的历史,对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业革命促成社会化大生产,引发亚当·斯密、西蒙斯第、罗雪尔、马克思等人对小农经济命运的讨论,而考茨基、列宁、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并在苏联(俄国)经济政策制定中付诸实践[1]。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展开系统研究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他在《农民经济组织》中充分肯定了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和稳定性[2]。与此相反,在刘易斯二元结构论述中小农经济则属于落后的产业,势必被现代部门所取代[3]。舒尔茨关于理性小农的假设,强调农业和重新审视小农问题,并主张用市场机制来改造传统农业[4]。
在现代化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要慎重考虑大规模经营,认为适度规模的小农家庭农场应当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5]。国内学者关于小农经济的论争愈演愈烈,大体形成3种观点:(1)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逐步放开农村生产要素,缩小城乡差距,以此快速推进中国现代化[6]。其实质是进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市场竞争加快城乡要素流动,其潜在的结果是小农经济被非农经济所取代。(2)从对马克思经典论述的理解中强调小农经济生命力的短暂性及最终衰亡论[7]。但有学者认为这类观点误解了马克思有关小农经济的论述,不符合小农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小农生产方式仍旧存在合理性[8]。(3)基于中外农业经济竞争力的对比,得出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是大规模化取代小农而富有竞争力的观点[9]。但有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无法遵循西方经典理论预设的模式,小农农作将成为中国多元农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0]。
各界对于小农经济命运的论争,实质是对小农经济生产经营方式与农业现代化适应性的讨论。激进者认为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格格不入,小农经济势必被农业现代化所消灭。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没有认识到农业生产发展或者说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11],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生命力。
二、农业现代化的反思
(一)功能错位调整
农业现代化是保证农民就业和收入的重要手段,为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服务,但农业现代化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发展目标,也并非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单一化体现。在农民分化、兼业化的小农经济时代,并不是所有或者说大部分农民都通过农业生产来致富。农业生产是农民收入的基本保障,也是农民就业的基本补充。中国还有2亿多农户6亿农民,其中农民工数量超过3亿人,“80后”新生代农民工超过2.5亿[12],而农民工回流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一种特殊现象。没有正确认识到小农经济对6亿农民所起到的保障作用而一味地“去小农化”,可能会导致农民工无法回流及原有小农失去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农业现代化作为推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种粮积极性的手段,并非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单一化体现,两者不能简单地互为因果。农业现代化只是手段,不是目标。
(二)经营主体不明
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理解有所偏颇,认为应以大规模化为方向,忽视小农,甚至主张取代小农。实际上,无论什么时候,农业现代化都是小农经济向前发展的手段,农业经营主体始终要以小农为基础,要在小农经营基础上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归根结底是全体小农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其实质是在稳定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实现适度联合,以抵抗大市场风险,而并非是通过大资本下乡挤占小农生产空间。农业现代化应该是小农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化。
(三)大规模化失灵
农业现代化起初的基本内涵是规模化和产业化,而最初“以土地规模经营”为主要内涵的农业现代化却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化而产生的[13]。曾有不少学者倡导中国农业现代化走美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即大规模、超大规模农业生产。近代以来,西方农业生产方式是按照工业经济生产方式而建立起来的。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质是将工业化模式导入农业领域,以此获得成功。追求单位生产效率最优、创造最大资本收益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在美国行得通,但难以普遍适用于“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的中国式小农经济[14]。大规模农业下单一植物抗病虫害能力下降,于是就得使用农药,其结果是食物品质下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大规模农业丧失了农业本身满足人类生存的功能,导致资本收益和社会收益分离。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小农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
(四)世界农业“回归”趋势
因资源丰富而得以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大农场模式,因农业劳动力外迁且兼业化的中产市民较早经营而实现农业资本化的欧洲中小农场模式,以及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维持着小农经济的东亚模式等,作为世界范围内有代表性的农业形态,近年来不同程度地追求一种具有健康、安全、环保、本地化、可视的生产过程等特点的小规模农业。这种新业态的农业生产方式被称为“团结经济”“社区支持农业”等,名称虽不同但其核心理念是相似的,其共同特征是趋向于小规模。越是发达的国家(地区),这类小规模农业受关注度越高,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遭遇了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频发问题,人们越来越关心从土壤中获得的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参与生产过程所获得的喜悦。大规模农业所隐藏的食品质量备受质疑,减少甚至是杜绝化肥、农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只能依靠小而美的小规模农业。
三、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再认识
古往今来,小农经济在中国并没有断根,始终支撑着国人的基本生存。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的巨变催生国人对国家经济基础进行思考,有人试图改造小农经济形态,但应该看到的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小农经济之顽强有突出表现,越是艰难越是顽强[1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率先在农业领域拉开序幕,基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城市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美国大农场生产看齐的声音渐渐变大,主张改变传统小农经营规模与经营方式的观点日益成为主流。所幸的是,时至今日,小农经济并没有被“去小农化”,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政策仍强调以“农户经营为基础”,至今近90%的耕地和80%的粮食产量仍由农户家庭承包经营[15]。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避免出现一些阶段性的认识误区。
(一)生产性: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世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目前,中国粮食实现“十二连增”,其背后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发挥机制作用。农户按照当地的需求进行农业生产,其劳动力成本较低,使得粮食生产更有保障。与工业化农业相比,资本追求单位生产效率最高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国家粮食生产、食品安全风险加大。大规模农业生产要求较高的生产成本,要求承担的自然和市场风险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小农一旦失去土地及传统生产要素,对资本形成高度依附性,农业生产便失去自主性,原有的低劳动成本的优势将丧失,兼业形态的小农将彻底成为回不去的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获得部分自给自足的生活资料的局面将被打破,藏粮于民的优势势必演化为被工商资本所左右的劣势。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依旧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生态性:多元化农业的前提
大自然赋予农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属性,从土地、光、热、水等资源中获得食物,使得人类生命得以延续。农业生产依附于大自然,也将生物、环境连接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并处在一定的稳定结构中才生产出农产品。农业的生态性是人们从事农业多功能性开发的前提,也是一个从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能量输入、传递和转化的过程。生产使得劳动者获得生活资料,也获得了劳动的权利和劳动的喜悦。小农经济的存在是维持农业生态性的保障,它使多元化农业发展有了可能。大规模单一化农业忽视中国资源禀赋特点,工业化农业使得资源环境约束达到极限,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泛滥使用给农业生态环境造成致命破坏。单一化种植破坏土壤生物多样性,追求生产效率最高、利润最大化等无限制的对农业的汲取,忽视了农业生产的生命周期,势必造成重大隐患。小农生产方式满足小农自身的生产生活需求,适合农业生态自身的土壤、肥料、耕作方式和生命周期。保护农业生态性,是进行农业多样化选择、多元化开发的前提。
(三)生活性:农民生计的底线
小农经济不仅包含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农民的生活方式。小农是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农民家庭不使用雇用劳动力,只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生产,其组织经济活动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式的,而是对所拥有的资产进行适当分配以维持家庭消费和生产的平衡为目的[3]。工业化农业追求投入产出比最优,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整体平衡。小农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一方面维持着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另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适用性。小农经济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体现劳动者生命价值与人性特点,从而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起着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诚然,小农经济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因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其体现的社会意义不一样,但始终维持着农民生计底线。
(四)文化性:乡村文化的载体
中华传统文化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内容,广袤的土地上孕育着各民族在区域农耕环境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乡村是人类文明发祥地,农耕社会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发展的命脉所在。工业化农业依靠技术优势改变农业多样化形态为单一性,颠覆农耕文明。单极化技术推动的西方工业文明面临着四大失衡危机:人与自然失衡导致能源环境危机,文化与科技失衡导致世界去文化危机,物质与精神失衡导致人类精神缺失危机,城市与乡村失衡导致文化传承断根危机。大量小农的存在,充实了村庄,为实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供给、村庄管理提供了载体,这便是“中坚农”对村庄的社会意义[16]。载体的体现除了器具物质层面外,更为重要的是农耕文明下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小农经济小规模的熟人社会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内在约束,形成异于西方的低成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小农经济作为乡村文化的载体,无形内化于小农生产生活全过程,这是“去小农化”的大规模农业现代化所无法比拟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之顽强,实质上是小农经济之下的乡村文化起着支撑作用,并不断地形成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继承与发展中影响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乡村蕴含着引领未来文化发展新潮流的新元素、新动力,是生态文明时代新文化的发育温床。
四、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困境突破的路径
(一)鼓励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小农经济随着时代发展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体现。但“分有余而统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小农经济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难题。小规模经营且分散的特点使得单个农户无法与大市场衔接,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交易费用成本高,农户与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劣势,但这并不表明传统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不匹配。随着中国农业经济不断改革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已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由改革初期相对同质性的家庭经营农户占主导的格局向现阶段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转变。农业经营主体类型比较与路径选择在中国当下的学术界基本形成4种意见流派:(1)主张中国农业走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其典型模式是发展大面积连片经营的机械化农场模式;(2)无论是在旧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新的市场竞争体制下,分散、弱小的农村户营经济都必然被集中;(3)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形成农业龙头企业以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国际竞争;(4)从农业生产的性质或是中国独特的国情认识上,中国都应选择家庭经营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以合作社为媒介的纵向一体化。
(二)构建“小农”适度合作组织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大规模、大机械化农场经营模式势必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大规模农场不适合中国,也不应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选择。认为小农经济势必“去小农化”的观点忽视了小农经济的生命力,缺乏对小农经济发展历史和客观现实的正确分析。鼓励资本下乡、促成农业资本化的观点则片面强调市场,忽视小农经济在生产之外的其他功能及其对国家、农民的重要性。基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分析,选择以农户经营为基础构建适度合作组织才是化解“小农”“大市场”矛盾的可行路径。“小农”适度合作组织将“小农”组织起来,解决小农经济规模太小而无法与市场对接及无法单独解决基本生产条件的问题。在这方面,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值得借鉴,但因其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现实情况也有差异,借鉴时要加以辨别,要克服其高度专业化分工,以及对农协提供的服务高度依赖等弊端。某种程度上,当下形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趋势是对分工过于专业化,以及组织服务单一性的一种反思。相反地,中国涌现出的农民自发型、政府主导型及科研院所主推型综合农协模式值得比较分析、总结、推广,区域综合性农民合作的可能性值得试点。
(三)发展基于小农经济的立体乡村产业
西方农业现代化相对单一,其农业文明成分很少,远不及中国小农经济所蕴藏着的多样化的文明形态。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该是小农基础上的现代化,而且是自主创新的现代化,基于小农经济的立体乡村产业的发展是迈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伐。基于自然资本的小农经济蕴含着立体化的乡村产业,包括生态有机农业、乡村旅游业、乡村手工业、乡村农副产品加工业、乡村新能源产业、乡村养老服务业、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以及乡村总部经济(借助古村落等乡村诗意情景形成独特的企业总部办公环境)。其中,有机农业、乡村旅游、乡村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发展乡村经济的新潮流,也是城乡互动的重要元素体现。乡村新能源产业、乡村养老服务业,以及乡村总部经济尚未被主流所关注,但其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基于小农经济的立体乡村产业,是对中国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的调整,也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四)切实转变农业现代化服务对象
农业现代化必须是惠及小农的现代化,特别是要实现全面小康水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现代化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农户。中共中央已经明确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因实现农业现代化而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必须切实惠及农户。坚决遏制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由进行“跑马圈地”、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因农业生产规模、生产方式、承担风险能力、利益导向等差异性,小农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国家农业现代化提供的服务需求截然不同,且全国范围内仍旧以小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力量,农业现代化在全国范围内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可取,忽视各地小农具体情况势必造成恶劣影响,加大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难度。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转变农业现代化服务对象,惠及更多的小农。发挥小农经济的独特优势,完善小农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小农共享现代化带来的增值收益。这对于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缩小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有重要意义。
(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不断完善,组织载体多层次、服务内容多元化、服务机制多形式的格局基本形成,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服务内容与农民的需求差距大、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然突出存在[17]。完善以服务农户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当前,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要紧扣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围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产品效益开展多类型、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针对各地土地细碎化程度、农户兼业化程度的不同,开展精准服务。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尤其是乡、村两级的农技、水利、畜牧和农机服务,加大本地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力度。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完善贫困地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养力度。
五、结束语
农业现代化是小农基础上的现代化,原封不动地继承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去小农化”的农业现代化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反思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认识误区有助于走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现代化是发展小农经济的手段,而非最终目标。农业现代化的功能定位不是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而应是小农经济所承载的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稳定,农业现代化归根结底是全体小农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并非是通过大资本下乡挤占小农生产空间。大规模农场道路不适合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选择,世界农业经济有小规模化回归趋势,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反思应放在中国小农经济历史与现实的长周期中进行。
与此同时,小农经济所呈现的顽强生命力需要得到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经济体制为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廉价原料和大量劳动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起到了蓄水池和稳定器的重要作用[18]。小规模经营依旧是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方式,小农经济发挥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农民生计,以及成为农民精神家园的重要作用,其所承载的乡村文化是农耕文明的重要体现,小农经济生命力远远大于农业生产环节。农业现代化是小农经济时代发展的又一阶段,但农业现代化不能忽视小农。当前,小农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小规模与大市场之间的困境,构建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是化解这一难题的有益探索,同时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乡村产业,走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余永和.小农命运的论争与小农经济的再认识[J].农村经济,2013(9):12-15.
[2]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于东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5-25.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70-124.
[4]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6-44.
[5]黄宗智,高原,彭玉生,等.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J].开放时代,2012(3):10-30.
[6]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11.
[7]张新光.现代小农制历史地位的百年论战及现实意义[J].郑州大学学报,2008(2):67-73.
[8]丁长发.百年小农经济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与张新光商榷[J].农业经济问题,2010(1):92-106.
[9]钱津.中国农业必须走现代化之路[J].贵州社会科学,2010(1):85-93.
[10]潘璐.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2):34-48.
[11]贺雪峰,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6(2):45-65.
[12]贺雪峰.农业现代化首先应是小农的现代化[EB/OL].(2015-05-06)[2016-03-17]. http://www.zgxcfx.com/Article/85662.html.
[13]温铁军,张俊娜,杜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与方向问题[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3):105-110.
[14]贺雪峰.简论中国式小农经济[J].学术前沿,2011(23):30-32.
[15]董志凯.当代中国环境变化与小农经济形态、作用变异[J].古今农业,2013(3):24-31.
[16]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J].社会科学,2011(3):70-79.
[17]关锐捷.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探[J].农业经济问题,2012(4):4-10.
[18]周娟.韩国农业危机及其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5(3):93-100.
(责任编辑: 庄艺真)
Reflec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vitality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in China
ZHANG Xiao-de, ZHANG Wen-ming
(DepartmentofEconomics,ChineseAcademyofGovernance,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rvival or death of 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a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debate. Based on difference of production mode betwee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some scholars hold that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will disappear. However, this view neglect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the function dislocation, the unknown main body and the failure of agricultural large-scale management, ignores the trend of the world agricultural economy management regression, resulting misunderstanding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Tenacious vitality of 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in China needs to be further understood. Because of self-sufficiency and low labor cost it guanantees a national food security; because of containing various ecological systems it forms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s. because of reflecting life value and human nature it becomes farmers livelihood, and holding the local social stability it is the rural cultural carrier.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not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Understanding correctly the vitality i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in China is the premise of resolving its difficulti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form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vitality;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收稿日期]2016-03-17
[基金项目]国家行政学院2015年度重大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张孝德(195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政府经济管理、乡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22(2016)03-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