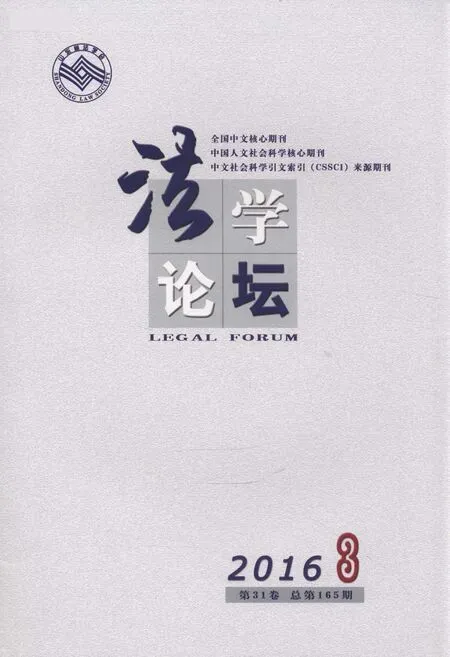论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谢登科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论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谢登科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在技术侦查中,传统权利系谱并不具备足够张力为个人隐私权提供有效保护。国家在追诉犯罪中采取技术侦查必然会侵犯、限制个人隐私权,个人需予以一定程度的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在技术侦查中可以不受限制或者制约。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在本质上属于隐私权的公法保护,它强调个人隐私权免受国家权力的不正当侵害,其运作是要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正当程序控制。技术侦查需要受到法定主义、比例原则和司法审查等方面的限制。我国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关键词:隐私权;技术侦查;司法审查;程序性制裁
一、问题与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悄然来临,国家利用“千里眼”(现代闭路系统足不出户即可监视民众一举一动)、“顺风耳”(通过窃听设备或录音摄像机监控民众谈话)、“隐身术”(依靠微型化技术或后门程序等隐匿行踪)、“追踪剂”(借由定位追踪装置实时精准锁定目标位置)、“蜘蛛网”(建立民众隐私信息联网数据库以供交叉检索)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监控和干涉个人隐私的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传统权利谱系中的财产权、人身权并不具有足够理论张力为个人隐私提供有效保护。依附于隐私利益之下的侵害行为,比如监视监听、定位追踪等等,并非传统权利所能调整和规范。因此,隐私权作为一种新兴权利逐渐兴起。不过,国内学者对隐私权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多集中于民法、侵权责任法、宪法等语境。实际上,据美国某调查结果显示:政府才是个人隐私权的主要侵犯者,而这其中又以因刑事侦查而实施的侵犯行为占绝大多数。*参见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隐私权的私法运作主要实现对私人行为的控制和规范以保护隐私权免受来自个人的不当侵害。而刑事诉讼法中隐私权的保护在本质上属于隐私权的公法保护,它强调个人隐私免受国家权力不正当侵害,其运作是要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随着国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监控和干涉个人隐私的能力不断增强,亦需不断强化刑事诉讼中对隐私权的程序性保障。隐私权作为一种新兴权利已被法律界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但由于隐私权概念的抽象性、客体的不确定性、侵害方式的多样性等问题,其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这在刑事诉讼中亦不例外。因此,研究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离不开对隐私权基本理论的探讨。
隐私权在我国经历了由“利益→法益→权利”的发展历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将隐私列为“人格权益”。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2条正式规定“隐私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技术侦查,为侦查机关开展监视监听、定位追踪、控制下交付等技术侦查措施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技术侦查是当代国家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刑事侦查中历来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而技术侦查则是国家权力与个人隐私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在技术侦查中如何实现隐私权保护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并非中国特色的本土问题,而是信息社会、风险社会下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域外在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所借鉴。因此,本文拟以隐私权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探讨我国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二、嬗变与平衡: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之证成
“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蕴含着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否存在独立的隐私权,或者隐私权是否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通过传统权利能否有效保护隐藏于人身、财产、住宅之后的隐私利益。这涉及隐私权独立性问题,历来是隐私权“否定论”和“肯定论”者争议激烈的领域。“否定论”者通常认为隐私权概念不清晰、边界不明确,缺乏权利内核,从而主张将隐私利益纳入财产权、身体权、知识产权等范畴予以保护。“肯定论”者则认为传统权利系谱无法为隐私利益提供有效保护,隐私权有其独立存在的空间。技术侦查中的隐私利益是通过传统权利保护,还是通过隐私权保护?这必然涉及对隐私权独立性问题的探讨。第二,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性和特殊性。为何要强调在技术侦查中对隐私权的保护,这主要涉及隐私权侵害行为形态变化的问题。上述两个问题并非截然分离而是相辅相成:隐私权的独立性在技术性侦查中得以彰显;而在技术侦查中强调隐私权保护,也离不开对隐私权这一新兴权利的本质探析和理论定位。
(一)权利嬗变:隐私权独立性证成
如何处理与旧有权利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新兴权利发展壮大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隐私权亦不例外。正如姚建宗教授所言:“新兴权利与旧有权利关系极其复杂。一方面任何新兴权利都主要由旧有权利所催生,也可能是旧有非法律权利所催生,旧有法律权利和非法律权利是任何新兴权利的母体和孕育土壤;另一方面新兴权利得到法律确认之后,在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都可能出现不和谐、不协调状态,即旧有法律权利和新兴权利可能冲突。”*姚建宗等:《新兴权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1页。传统权利注重于对生命、身体、住宅和财产等物质性利益的保障。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活中只有部分痛苦和愉悦是源于物质世界,精神、感情及心智需要得到法律承认。法律权利范围逐渐扩大,这其中就包括隐私利益的权利化。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生活日渐紧张复杂,适时远离世事纷扰,保持独处免受干扰,是隐私权诞生的重要根基。个人保持独处、免受干扰的隐私权,不仅包括免受其他公民、新闻报刊、影视传媒等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免受国家对个人隐私利益的不法侵害。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享有搜查、勘验、检查等强制性侦查权,如果缺乏程序性保障措施,很容易因滥用权力而侵犯个人隐私利益。在传统侦查手段中,隐私利益可依附于住宅权、财产权、身体权等传统权利而获得保护。而在技术侦查中,传统权利则无法为个人隐私提供足够保护,隐私权独立性得以彰显。下面将结合两个典型案例予以详细阐述:
案例一:“夫妻看黄碟事件”*余江梅:《河南“夫妻看黄碟事件”始末》,载《法律与生活》2003年第11期。。2002年8月18日晚11时许,某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李某夫妇在家中播放黄碟。于是,3名民警前往调查,在未着警服、未出示证件的情况下强行进入张某家中。期间,民警与张某夫妇发生冲突,两名民警受伤。后民警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将李某带回派出所,并将从现场搜到的光碟、影碟机等作为证据扣押。两个月后,张某以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后李某向派出所缴纳2万元罚款而获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李某向检察院提出控诉,认为自己在家庭财产受到威胁、迫于无奈情况下才动手,属正当防卫,民警既未着警装,也未出示证件,以执行公务为由侵入民宅,属非法行为。后3名民警中,一人被判处滥用职权罪,两人被给予纪律处分。
案例二:热像仪对隐私权的侵犯(Kyllo v. United States)*533 U.S. 27 (2001). 详见[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一卷·刑事侦查)》,吴宏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3页。。警察怀疑凯丽欧家中种植大麻。种大麻需用大灯照射以增加室内热量,为确认该事实,警察用热像仪对凯丽欧家进行扫描。结果显示,凯丽欧家车库屋顶和墙壁散发的热量明显偏高,警察用热像仪分析图和电费单申请到搜查令对凯丽欧家进行搜查,发现凯丽欧家果然种植大麻,凯丽欧被逮捕起诉。但对于使用热像仪是否合法、是否涉嫌非法搜查引起争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认定该行为构成非法搜查,侵犯个人隐私。
通过比较上述两个案件,我们会发现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在保护隐私利益方面的不足,隐私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独立空间。
首先,从权利客体范围来看,部分隐私利益会依附于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客体而存在,因此,部分隐私利益是可经由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而获得保护。比如案例一,本案起因源于夫妻在家中观看“黄碟”,但只要不公开或者聚众播放“黄碟”且未影响到他人生活,其在本质上仍属个人私生活范畴,属个人隐私利益。在前信息化时代,受制于技术条件因素,国家侦查犯罪的手段相对较为有限,个人住宅之内的隐私利益完全可经由房屋所有权而获得保护。法彦曰:“每个人的房屋就是他的城堡”。个人房屋所有权可以抵御他人非法侵入,这其中就包括国家公权力的非法侵入。此时,法律对于个人利益的保护侧重于人身、财产等物质利益,个人隐私缺乏独立根基,只能依附于其他权利。前信息化时代侵害隐私利益的手段相对有限,对财产、住宅等进行保护,其所承载的私人信息便无法对外披露,隐私利益保障亦可同时完成。
但是,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信息社会,个人的合理隐私期待已突破了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的客体范围,有相当比例的隐私利益无法经由传统权利而获得保护。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案例三中的经典论断:“隐私权保护的是人而不是场所。”这说明个人隐私已突破了住宅、财产等特定物质载体或者场所的界限。隐私权之父布兰代斯也曾说过:“隐私权完全可以独立于思想、情绪以及感情的载体,可以独立存在于任何有形实体之外。”*[美]路易斯·D.布兰代斯等:《隐私权》,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相当部分个人隐私在信息社会逐渐失去其客观、有形的庇护体,这使得隐私利益的独立性日益凸显,也催生了人们对隐私权的客观需求。当然,隐私权的独立性并不排斥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对隐私利益的保护,而独立的隐私权却能为传统权利所无暇顾及的个人隐私利益提供更加有效的保护。
其次,从权利效力内容来看,与隐私权一样,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都要求排除他人非法干涉。但是,由于隐私权和住宅权、财产权等旧有权利的客体不同,其排他性效力的范围也存在差别。住宅权、财产权等旧有权利的排他效力,主要体现为排除他人妨碍其对特定财产或者物品予以有效支配的权利。而隐私权则主要表现为保持独处、私密状态的排他性效力。不过,由于部分隐私利益会依附于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客体而存在,这也决定了部分隐私利益可以经由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的排他效力而获得保护。比如案例一中,夫妻在申诉时主要从住宅免受非法侵入的角度来主张权利救济。由于夫妻对其房屋享有排他性的所有权,所有权的排他性决定了任何人未经其同意或者取得搜查证而予以搜查,则搜查行为是违法的。所有权的排他性保护了房屋自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也保护了隐藏于房屋之内个人私生活和隐私信息不受干扰的状态。
但是,在信息时代,新形态的干预手段借助于先进科学技术,使得侦查措施基本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对于个人隐私的非法侵害已不局限于物理性侵害形态。监视监听、定位追踪等技术侦查措施的大量适用,非物理性、非接触性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形态大量出现。个人有形财产即便没有受到物理性侵犯,其承载的个人信息或者隐私利益仍可能被外界所获得。比如案例二中,通过热像仪对房屋进行检测,并不存在与犯罪嫌疑人房屋的“物理性接触”,也并不影响所有权人对其房屋的排他性支配权。但是,这种技术性侦查行为已经侵害到个人私生活和隐私信息不受干扰的状态,而这恰恰是隐私权最为核心和本质的部分。侵害个人隐私使人遭受的精神痛苦与困扰,较之于纯粹的身体或者财产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缺乏隐私权而仅仅依赖住宅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无法为技术侦查中个人隐私提供有效保护。因此,在侦查措施基本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隐私权的独立性亦日益彰显。
有学者将侦查中侵扰当事人隐私行为分为“严重侵扰隐私行为”和“轻微侵扰隐私行为”两类,并认为前者包括搜查人身和住宅、扣押等传统侦查行为,而后者则主要包括技术侦查措施。*参见毕惜茜:《侦查中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该观点注意到了传统侦查与技术侦查对隐私权侵犯的差异。传统侦查行为侵犯隐私权时,往往同时侵犯住宅权、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权利,因为传统侦查措施需要通过物理接触才能窥测隐藏于住宅、人身、财产之后的信息。而技术侦查则多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无需直接接触与住宅、财产、人身等有形物体即可窥测到个人隐私。但是,该观点将搜查、扣押等传统侦查行为视为“严重侵扰隐私行为”,而将技术侦查视为“轻微侵扰隐私行为”,显然忽视了隐私权的本质特征及其独立性。部分隐私利益虽然会依附于住宅、财产、人身等传统权利客体,但这并不否认隐私权自身的独立性。隐私权的本质是保持个人独处和私密信息的权利,技术性侦查与传统侦查在侵犯隐私权上不存在区别,区别仅在于是否附带性地侵犯住宅、财产、人身等传统权利。侵害个人隐私使人遭受的精神痛苦与困扰,较之于纯粹的身体或者财产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技术侦查措施的非物理性、非接触性、非公开性,其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深度和广度要远高于传统侦查措施。因此,不能仅仅因为传统侦查措施在侵犯隐私权过程中,附带性地侵犯住宅、财产、人身等传统权利,就认为其侵扰隐私权的严重程度高于技术侦查措施。
(二)利益平衡: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性与特殊性
刑事诉讼中历来存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种价值的冲突与平衡。犯罪分子利用现代科技实施犯罪的能力不断提高,犯罪手段和形态日新月异。这就要求国家提升运用现代科技打击犯罪的能力,但这也必然伴随国家干预个人隐私权能力的提升。国家在追诉犯罪中可以采取技术性侦查措施,必然会对公民个人隐私权构成侵害和限制。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是个人隐私权的边界之一,个人需要容忍国家适用技术侦查中对其隐私权的侵犯,这是在实现社会秩序必然付出的成本。一般而言,国家不得干涉、侵害个人隐私权,但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而进行的必要干预则属例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用不择手段、不问是非、不计成本的方法来查明案件事实。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虽允许侵犯隐私权,但亦应给予隐私权以正当程序保护,需要受到法定主义和比例原则的控制。由于隐私权在现代权利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亦存在其特殊性。
首先,在适用范围上,隐私权在现代权利体系中的重要性决定了技术侦查仅适用于严重犯罪。隐私权作为一项精神性人格权,自诞生之日就在权利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它意味着在法律上人的身体与精神被平等对待。若法律缺乏对精神的重视,灵魂将在法律中面临不如身体重要的尴尬,甚至会让个人丧失其主体性。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隐私权价值在于个人自由和尊严,体现了个人自主,不受他人操纵及支配。某人若被任意监视、窃听或者干涉,将无法对个人事务保有最终决定权,势必听命于他人,丧失其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上)》,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措施应遵循比例原则,技术侦查亦不例外。由于隐私权在现代权利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侵犯隐私权属于对个人利益重大侵犯。比例原则决定了技术侦查在适用范围上,仅限于严重侵害社会利益的重大犯罪,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毒品犯罪、重大贪污贿赂犯罪,对于轻微犯罪则不能适用技术侦查。
其次,在适用顺序上,隐私权在现代权利体系中的重要性决定了技术侦查适用的末位性。如果能够通过其他侦查措施查明案件事实,则不能适用技术侦查。只有在通过其他侦查措施无法查明或者查明事实成本极高的情况下,才可适用技术侦查。技术侦查适用的末尾性源于比例原则和隐私权的重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侦查机关可以“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采取技术侦查。参与立法者的观点认为:“‘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只要办理案件就可以采取技术侦查,采取技术侦查一定是在使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法实现侦查目的。”*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该观点也体现了技术侦查适用的末位性。由于隐私权涉及人的基本尊严和生活安定,滥用技术侦查会极大地侵扰人们保持独处、不受干扰的生活状态。因此,技术侦查在适用上具有末位性。
再次,在权利救济上,需运用程序性制裁来强化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障和救济。程序性制裁是指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收集的证据、开展的诉讼行为或者作出的裁判丧失法律效力,来发挥惩罚程序违法者的作用。*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176页。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中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也是最能体现对权利人程序性救济的措施,因此,它只适用于程序性违法严重侵犯个人权益的场合。对于违法适用技术侦查侵犯个人隐私权所收集的证据,应适用程序性制裁否定其证据能力。这一方面源于隐私权在现代权利体系中的重要性,完全足以匹配程序法中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也源于隐私权自身特性。隐私权主要内容是维护个人生活安宁、个人私密信息免于公开、个人生活自主决定等等,其本质在于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等精神世界的关注,这决定了隐私权难以事前保护。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言:“对于隐私权保护注重事后救济。”*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载《法学家》2012年第1期。而在程序法领域对隐私权的事后救济主要体现为程序性制裁。只有通过宣告违法技术侦查所收集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才能真正威慑技术侦查中不当侵犯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
三、差异与暗合: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比较法分析
(一)英美法系国家在技术侦查中对隐私权的保护:以美国为例
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65年在Griswold v. Connecticut案中首次明确隐私权系宪法权利后,隐私权就成为宪法中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领域之一,它涉及新闻自由、个人信息、避孕用具使用、同性恋自由等诸多极具争议的问题。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强调刑事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则是在1967年作出的卡兹案(Katz v. United States)这一标志性判例中。
案例三:卡兹案(Katz v. United States)*389 U.S. 347 (1967). 关于该判例中文版内容详见孟军:《艰难的正义:影响美国的15个刑事司法大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204页。。查理斯·卡兹(Charles Katz)在公用电话亭通过付费电话赌博。他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警员已在该电话亭安装电子监听器,记录下其谈话内容,对卡兹的监听并未取得搜查令。在审判中,控方出示该电话录音作为证据。卡兹争辩未取得搜查令在公用电话亭安装监听装置属于非法搜查,申请排除该证据。控方认为证据取得合法,原因在于:侦查人员未进入电话亭,不存在搜查;公用电话亭是玻璃制作,从外面即可看清其举动,该电话亭不属于“宪法保护领域”,故无证监听合法。初审法院采信了该证据,作出有罪判决。卡兹不服,向美国联邦上诉巡回法庭提出上诉。巡回法庭维持原判。卡兹仍不服,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在调卷复审时认为,卡兹在公用电话亭存在“合理隐私期待”,无证监听违法,故裁决撤销原判。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个人享有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搜查通常需要进入住宅或者财产,这就不可避免牵涉个人隐私。但是,第四修正案对住宅、财产等传统权利都明确加以规定,对隐私权则未予规定。在卡兹案之前,对搜查合法性的分析都是以“财产权/侵害”为中心,将是否存在对财产权的物理性侵入作为非法搜查的判断标准。若不存在对宪法保护领域的物理性侵入,则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侵害,也就不适用宪法第四修正案。比如,1928年的奥姆斯泰德案(Olmstead v. United States)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财产权/侵害”分析法适用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典型判例。*[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一卷·刑事侦查)》,吴宏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8页。在该案中,联邦警员未取得搜查令对奥姆斯泰德住宅电话、办公电话搭线监听。但是,法院认为该监听行为不受宪法第四修正案调整,主要理由是谈话是无形的,不属于“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范围,不受宪法保护;住宅和办公室虽受第四修正案保护,但宪法只保护其不受到物理性侵害,眼睛和耳朵不能实施“搜查”,同样也不会造成侵害;搭线监听虽然能够造成损害,但安装搭线装置的电话线并不属于奥姆斯泰德的财产。这是将搜查合法性依附于财产权的典型案例,此时并未确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而卡兹案则赋予隐私权支配性地位,将“合理隐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作为考察搜查的主要标准,此后,影响搜查合法性的核心已不是财产权而是隐私权。正如代表最高法院撰写卡兹案判决的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们的正当隐私权,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人而不是场所。一个人即使在家,但他有意将自己的行为或者文件暴露给公众,那么这些财产和信息也不是第四修正案保护的对象。相反,一个人即使身处公共场所,但他不想将自己的物品或信息暴露给公众,那么,他的这种隐私权仍然可能受到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孟军:《艰难的正义:影响美国的15个刑事司法大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192页。按照“合理隐私期待”标准来分析,则搜查并不局限于住宅、办公室、建筑物或者其他封闭地方,它可能发生于任何有隐私合理期待的地方。如果存在合理隐私期待,即使是在公共场所或者不存在直接的物理性接触,警察无证搜查行为仍然可能违法,他所收集的证据就可能不被法庭所采纳。关于“合理隐私期待”需要从两个层面予以理解:在主观层面个人须表现出真实的隐私期待;在客观层面该隐私期待须被社会公众认为是合理的。*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3页。之所以实现“财产权/侵害”到“隐私权/侵害”为中心的转变,主要在于科技发展扩大了人们的视觉、听觉范围,信息社会的到来凸显了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性和独立性。而美国刑事司法充分运用其判例法所具有的灵活性优势,通过判例解释宪法、确立法律原则,为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提供了依据。
(二)大陆法系国家在技术侦查中对隐私权的保护:以德国为例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在立法中并没有隐私权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法不重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在德国判例学说上,主张将隐私权作为一般人格权的重要内容,通过一般人格权来为个人生活领域提供法律保护。*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上)》,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在德国判例学说中,认为隐私权属于宪法基本权利的范畴。监听、邮件检查和电话监控是侦查中常用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秘密进行,被监视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通讯正处于监控,因而可能会泄露某些秘密信息。《德国基本法》第10条第1款:“信件、邮件以及电子通讯的秘密性不受侵犯。”国家在刑事侦查时亦适用该禁止性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依据司法令状对信件、邮件以及电子通讯进行监控。但是,监控须受到法定主义、令状主义和比例原则的限制。法定主义要求监控须存在法定理由,主要是为了查明特定的重大犯罪案件事实。根据比例原则,如果犯罪轻微,则监控构成对隐私权的不当侵犯。只有对犯罪嫌疑人已经实施严重犯罪存在理由充分的怀疑时,且无法采取其他侦查手段或者其他侦查手段已被证明无效时,才可进行监听。在监听过程中可以进行录音。监听损害了通讯的秘密性,也损害了公民不得违背其意愿情况下将其言词予以记录的权利。立法通过实体性和程序性保护措施,来保护个人免受不当窃听的侵害。只有在特定的严重犯罪侦查中才允许进行电话监听。这些犯罪包括叛国罪、侵害国家利益罪、恐怖组织犯罪、杀人、绑架、抢劫、敲诈、纵火、严重盗窃和收受盗赃、严重毒品犯罪以及违反保护外贸特定条款的犯罪。这些犯罪的未遂、预备行为也包括在内。如果对上述所列之犯罪存在有事实根据的怀疑,且通过其他手段无法或者很难侦查,则可以申请窃听。在监听令中,应当指明监控种类、范围、持续期限。监听最长期限为3个月,但每次可以延长3个月,且没有绝对上限。德国程序法总体上对其通讯提供了较为有效的保护,但是,在实践中运用犯罪嫌疑人言词对其定罪的诱惑如此强烈,以至于超出了对隐私权的关注。*[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7页。
关于违法监听所收集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德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禁止使用此种类型的证据。但是,德国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禁止使用因违法监听所收集的有罪证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警察未取得监听令,径行监听犯罪嫌疑人电话、收集到有罪证据。依据该案客观情形,若警察事前申请监听令,法官应能批准。但由于警察未取得监听令,违法在先,法院禁止将该证据作为有罪判决的基础。在另一案例中,前期电话监听合法,但被监听人通话后未将电话挂好,以至于住宅内的谈话全部被监听,警察因此收集到其他有罪的证据。德国最高法院以后来的监听违法侵犯个人隐私权,禁止在诉讼中使用因此而收集的证据。*林钰雄:《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302页。因此,德国亦通过判例形式确立了违法监听侵犯个人隐私权的程序性制裁制度,通过证据使用禁止强化了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三)差异与暗合:两大法系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规律
通过前面介绍美、德两国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性。鉴于控制犯罪、维护秩序的公共利益,两国均容忍技术侦查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但对于隐私权的侵犯均要求受到正当程序的规制。由于在司法传统、诉讼构造、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两国在技术侦查中对隐私权保护的程度存在差异,美国的“合理隐私期待”标准为个人隐私免受不当搜查提供了更为有效的保护。总体而言,两国在技术侦查中的隐私保护方面存在着如下共同规律:
第一,两国均采取判例形式来推进技术侦查中隐私权的程序保护,有效契合了新兴权利的生成与发展路径。对于新兴权利的生成,姚建宗教授总结为立法确认、司法创设和权利推定三种路径。*姚建宗等:《新兴权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1页。由于法律的安定性与滞后性,立法确认新兴权利并不总能有效适应科学技术、经济水平、社会观念的发展,并不总能及时回应人们新的利益诉求。由于隐私权客体的不确定性、边界的模糊性以及信息社会下个人隐私利益需求的不断扩大,这就需要隐私权的生成、发展保持适当的灵活性。而隐私权的司法创制无疑契合了上述社会需求。通过司法判例来推动隐私权保护,可以最大限度缓解信息社会下个人隐私利益扩张与法律安定性之间的矛盾。
第二,事先司法审查保障技术侦查侵犯隐私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美国,卡兹案确立了“隐私权/侵害”为中心的宪法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只要在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场合进行搜查,就须取得法院令状。通过超然而中立的法官进行事前司法审查,来保障技术侦查侵犯隐私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法官在按照“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决定是否颁发司法令时,可保护个人隐私权免受不当搜查。在德国,窃听、邮件检查和电话监控等技术侦查措施属法官保留的基本范畴,只有取得法官授权才能实施。由法官对国家侦查行为对个人生活产生的侵扰进行事实判断,审查个人对该事项是否存在隐私的合理期待,侦查是否具有法定事由和证据。司法审查的事先介入限制了国家肆意启动技术侦查对隐私权的不当侵害。
第三,事后程序性制裁强化隐私权正当程序保障的制度刚性。在美国,对于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违法搜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德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排除非法搜查所得证据,但在实践中,法院可以根据侵犯隐私权的严重程度和惩罚犯罪的公共利益予以权衡。*[美]弗洛伊德·菲尼等:《一个案例 两种制度:美德刑事司法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15页。若缺乏对违法技术侦查侵犯个人隐私权的程序性制裁,将违法技术侦查收集的证据作为司法裁判依据,将会极大减损对个人隐私权程序性保障的法律效力,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因此,为强化隐私权保障的制度刚性,现代法治发达国家均存在对违法技术侦查侵害个人隐私权的程序性制裁。
四、现状与对策:我国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一)我国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分析
我国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技术侦查,这有利于技术侦查的规范化、法治化,也有利于实现犯罪控制与隐私权保障的平衡。为实现在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定了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将其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而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则不能适用技术侦查。这契合了隐私权在现代权利体系中的地位,符合对技术侦查的比例性要求。总体来看,我国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偏重实体性保护,而忽视程序性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技术侦查启动依赖于行政审批而缺乏司法审查。缺乏中立、超然的司法审查,会导致审批仅注重案件办理的便利性,而忽视隐私权保障的有效性。《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才可采取技术侦查。但立法并未明确“批准程序”是法院的司法审查,还是侦查机关的内部行政审批。实践中,技术侦查都是由侦查机关经内部行政审批来决定。在普通案件中,公安机关在技术侦查中承担申请、审查、决定、执行等多项职权。在自侦案件中,检察院适用技术侦查除内部行政审批外,往往还需根据调查对象的行政级别报请不同级别的政法委批准。*详见闵春雷等:《东北三省检察机关新刑诉法实施调研报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行政化审批方式有利于打击犯罪的社会需求,却不利于个人隐私权保护。缺乏中立及超然者的审查,侦查机关会基于自身便利性考量来决定是否适用技术侦查。
案例四:检察院对法官的监听。在某刑事案件审理中,检察院提出的公诉意见始终未得到法院支持。检察院怀疑承办法官收受贿赂、枉法裁判。于是检察院在经过内部审批之后,对承办该案件的合议庭法官和书记员进行监听。通过监听证实了检察院的怀疑,在技术侦查收集到相应证据后,检察院对该案法官和书记员予以起诉,后该法官被定罪。
该案若仅从实体角度来看,检察院对法官进行监听并无任何问题。但从程序角度出发,则有违公正。技术侦查中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巨大风险,在适用前应进行严格审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事实要件、比例原则和必要性要求。在本案中,检察院仅因其公诉意见没有得到支持,在怀疑法官收受贿赂的情况下,便启动技术侦查,客观上不无打击报复之嫌。对法官进行监听侵犯了其自主决定权,这种自主决定权一方面源于法官独立审理案件的职责要求,另一方面则源于法官保持独处的隐私权。当然,隐私权可因公共利益而有所减损,但这种减损须受到正当程序保护。若检察院可随意监听法官,那么,必然会让法官丧失独立自主性。若技术侦查的适用缺乏正当程序规制,任何人都有随时处于被监控忧虑的可能。个人隐私随时处于他人监控之下,个人将无法主导自己的生活,个人自由将受到极大减损。而具体到检察院对法官之下的监控亦是如此,若因法官作出与检察院指控内容不同的判决,而让其个人生活或者隐私随时处于监控,恐难有法官能在检察官指控面前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
其次,技术侦查适用范围模糊,无法满足人们对隐私保护的合理预期。技术侦查适用应受比例原则规制,《刑事诉讼法》第148条将技术侦查仅适用于重大犯罪契合了隐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但何谓“重大”,存在标准模糊、主观性强的问题。这里的“重大”是已查明系重大犯罪,还是仅为侦查人员怀疑有重大犯罪?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分歧。适用范围的模糊性,既不利于对技术侦查的事前审查批准,也不利于遭受不法侵害的事后救济。技术侦查中适用范围的模糊性和审批程序的行政化,为侦查机关随意启动技术侦查、侵犯个人隐私留有了巨大空间。
案例五:毒品犯罪中的技术侦查*本案例具体内容详见厦门市胡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刑初字市629号判决书。。公安机关在张某贩卖毒品中适用技术侦查,后现场缴获海洛因不足5克。在案件审理中,辩护方提出本案不属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不应适用技术侦查,申请将通过技术侦查所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适用技术侦查合法,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
在本案中,控辩双方对技术侦查的合法性存在分歧,主要原因是立法对技术侦查适用范围规定较为模糊。由于适用范围的模糊性,法院也无法轻易判断技术侦查是否违法、是否应予以程序性制裁。适用范围和标准的模糊性为侦查人员启动技术侦查留有巨大裁量空间,敞开了技术侦查随意窥探个人隐私之门。
再次,缺乏违法适用技术性侦查侵犯隐私权的程序性制裁,不能有效遏制侵犯隐私权的违法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通过技术侦查收集的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并未明确违法技术侦查侵犯个人隐私权所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应当予以排除。“针对公权力的程序性制裁,不是对侦查机关一般意义上的谴责,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法律制裁。”*高咏:《程序性辩护的困境——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为切入点》,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缺乏程序性制裁,侵犯个人隐私、违法收集的证据被法官所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就等于在审判中承认了违法技术侦查的合法性,弱化了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制度刚性,不利于威慑侦查机关在适用技术侦查中的违法行为,也不利于个人隐私权的正当程序保障。
(二)我国技术侦查中隐私权保障的对策思考
随着我国法治化、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国民既希望国家能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提升打击犯罪的能力,创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秩序,也希望个人隐私能得到国家的承认和尊重。正当程序是协调、平衡实现犯罪控制和隐私权保障的有效途径。但是,按照正当程序标准,我国技术侦查在保护个人隐私权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应建立技术侦查启动的司法审查制度,发挥隐私权的权力控制功能。我国技术侦查启动依赖于行政科层式审批,而缺乏中立、超然的事前司法审查。这导致审批中仅注重侦查机关案件办理的便利性,而忽视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有效性。我国正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主张将涉及当事人实体权益以及重大程序争议问题均交由法院予以司法审查。*参见闵春雷:《以审判为中心:内涵解读及实现路径》,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而技术侦查是涉及当事人隐私权的重大强制措施,其实施亦应由中立而超然的司法机关签发令状。虽然,公安机关、检察院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专门机关承担着客观公正职责,但是,其作为国家追诉者的角色会影响在决定适用技术侦查时的中立性和超然性,从而导致隐私权程序性保护的法律规定在自我行政科层式审批中落空。因此,技术侦查启动宜交由中立而超然的法院来审查决定,而不应交由侦查机关和检察院予以行政审批。技术侦查启动中的司法审查,可实现技术侦查申请权与决定权、决定权与执行权的有效分离和制约,发挥法院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技术侦查的司法监督,让立法对技术侦查中隐私权的程序性保障措施得以有效落实。
第二,应细化技术侦查的适用标准,强化隐私权保护的合理预期。可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予以细化和明确,消除适用范围的模糊性和适用标准的地区差异性,增强对隐私权程序性保护和救济的合理预期。当然,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细化技术侦查适用标准,亦不能突破比例性原则的限制。
第三,应明确违法技术侦查的程序性制裁,提升隐私权保护的制度刚性。正如前文所述,隐私权在现代权利体系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完全足以匹配程序法中最严厉的制裁措施。隐私权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对其保护主要依赖于事后救济,其在程序层面的救济主要体现为程序性制裁。若缺乏程序性制裁的保障,个人隐私权将在违法技术侦查面前沦为一纸空文。从域外技术侦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各国普遍确立了违法技术侦查侵犯个人隐私权的程序性制裁,对违法技术侦查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否定其证据能力。我国亦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明确违法适用技术侦查所收集的证据应予以排除。
[责任编辑:刘加良]
收稿日期:2016-02-2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法学会重点专项课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CLS2015C07)、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纪检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2014LZY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登科(1980-),男,湖北随州人,法学博士,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3-0032-09
Subject: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Rights in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uthor & unit:XIE Dengke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The pedigree of traditional rights does not have enough ten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The power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would infringe personal privacy to prosecute crimes. Individuals have obligation to tolerate the reasonable infringement during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However, it's not mean that the power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or controlle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right in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needs to control the power through due procedure.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needs to be subject to legal doctrin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judicial review. In China, there is still large room for improv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rights in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Key words:the right of privacy;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judicial review; procedural punishment
【特别策划·专题二、新兴(型)权利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