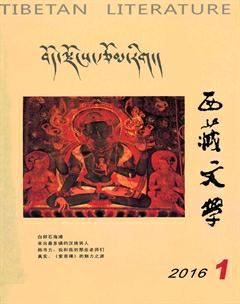消失的背影与沉重的探求
宋可可 徐琴
摘要:“出走”是尹向东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主题,其塑造的一系列“出走”的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意义深刻,各具特色。本文旨在通过对尹向东小说中“出走”这一主题的分析来挖掘“出走”背后,作者想要表达的关于生活、命运、时代的思考。
关键词:尹向东;“出走”;形象
尹向东作为康巴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与其他康巴小说有明显的不同。他的作品宗教底蕴淡泊,更多的是通过刻画甘孜地区普通而真实的人物和生活来表现属于底层人物的生命况味,虽然不直接着眼于时代和信仰等宏大主题,但却蕴含着让人顿悟的力量。他长期生活在康巴县城。对那里中下层百姓的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这成为他创作的源泉。写实是他作品绝对的底色,他的思想扎根于平凡的市民生活,描写的大多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县城顺民生活,普通高中学历,平凡工作履历,造就了一种平民视野与小人物心态,同时非贵族的血统使他内心涌动着倔强的下层藏族汉子的血性。”
城市生活与原始的农牧生活交织在他的作品当中,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双系统结构,这两种截然不同。又无处不在互相侵蚀的生命经验既是康巴地区的现实情况,也是作品中人物命运的终极指向,都市文明和藏族传统文明像是两个交织的圆环,身处其中的个人无不面临着出走或回归的选择,这是形成尹向东小说中“出走”主题的现实原因。
“出走”是一种行为方式,其原因有很多,既有因为逃避而出走的,也有因为追求理想而出走,还有因为生活所迫而出走。“出走”其实是人物在面对问题时的一种非常态的行为,主人公的命运随着“出走”这一行为有了巨大转折,同时“出走”担负着作品的戏剧冲突,以及主题的深化,承载着作者的思想表达。其小说刻画了很多“出走”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各有各的目的和结局,小说的现实意义在出走的主题中得以放大。
一、出走——向着渴望追寻
康巴高原地区广袤隔绝,交通不便,艰苦的自然条件中,人更愿意选择停滞安稳的生活。而不是漂泊不定,因为任何变动都意味着面临残酷的自然考验。“出走”不仅面临着生命的威胁,还面临着不同文化的距离与时代发展的断裂。所以“出走”对于个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隐秘岁月》中年仅14岁的女孩仁青志玛的“出走”是一场决绝地对人生价值和信仰的捍卫。仁青志玛家附近一座寺庙中自己经常跪拜的一尊檀香木观音像就要被毁掉了,她趁夜里偷偷把佛像带走,和佛像一起躲在远处的山洞里,至此她开始了持续一生的保护佛像的旅途。她靠乞讨和别人供奉的糌粑牛肉和酥油为生,打河水解渴,冬去春来,日复一日,自然的残酷考验着她,孤独寂寞折磨着她。她长大、生子、被抛弃,直到自己衰老。她看透自然人生,参悟宗教的意义,最后终于使佛像重新回到寺庙,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本身的宗教色彩加上主人公超脱凡人的人格和经历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着眼于现实的尹向东笔下很少有如此光辉的女性形象,她的光辉在于她的“出走”从而超越了自身的不幸,正如许多宗教故事中的受难者一样,她“出走“的出发点是纯洁高尚的,她主动选择了受难。家庭是温暖的,亲人是爱她的,她在最美的年华里却走向孤独。她不仅仅在拯救佛像。更是拯救自己以及很多在特殊时代中信仰崩塌的人的心灵。
《蓝色天空的琐碎记忆》中的伍金刀登是母亲仁青志玛和藏族男人生下的孩子,后来男人抛弃他们。而伍金刀登一直幻想自己有一个汉族父亲回来把他带走,十七岁那年伍金刀登忽然不辞而别。他无法忍受渴望带来的煎熬,他要去寻找父亲。虽然自己也明白是不会实现的,但“出走”给他的渴望一个承载的时空,使他至少觉得自己是在寻找父亲的路上,只要还在走着,就也许能找到父亲。这次没有结果的出走改变了他的命运,伍金刀登成了闻名的强盗。
失去父亲的孩子和被抛弃的女人是尹向东小说中常见的人物,这体现出他对悲剧人生的关照和悲悯情怀。女人和孩子这样本就弱势的两类群体在失去了成年男性的保护后将会更加悲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幼年的伍金刀登会如此渴望拥有一个汉族父亲,“他想他的汉人阿达一定会打猎,一定有一匹好马,也一定有一群健壮的耗牛”。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汉族父亲会带他走,而父亲和那个将要带他去的地方使他哪怕成为强盗也要“出走”,他骨子里就有对于“出走”的渴望。他必须“出走”,不然会被渴望吞噬,像小时候一样成为一个果子或是傻子。他渴望一个强有力的保障,然而这个强大的汉族父亲只是自己的想象。幻想破灭后,他只能通过武力让自己变得强大,暴力成了他“出走”之后的生存方式。
无论是仁青志玛还是伍金刀登,他们都是艰苦的高原之上不屈的强者,他们有自己的不幸,但是强大的精神支柱使他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宗教在青藏高原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尹向东所刻画的正是这样一群有着渴望和信念,并执着追寻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渴望体现着人的强大,这种强大是雪域大地赋予人的顽强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给予藏民族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勇气。
二、出走——人生的悲歌
并不是所有的“出走”都有生命史诗的意义,“出走”的前方也未必是光明的彼岸。尹向东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群出走的人:他们受命运所逼,环境所迫,被动或是主动选择“出走”。这种“出走”是灰色命运中更加灰色的部分,饱含血泪和苦难。他们似乎被命运抛弃,被悲剧眷顾,他们放逐自己,剥离原本的社会定位,隐身成为流浪者。作者深刻地刻画出这一类人的心路历程,透露出深深的同情以及对人性和社会的反思。
《蓝色的想象》是以一个男孩“我”为视角,写了“我”的姐姐陈丫的成长经历。陈丫作为女性,在家中得不到重视,在父亲的多次的打骂之后她开始仇视父亲,甚至以自己的堕落来报复父亲和家庭,堕落的途径就是“出走”,“出走”于父亲和家庭,更“出走”于自己原本光明的人生轨迹。她没考上大学,闲散在家,结识混混黑幺弟,黑幺弟为了给陈丫买项链而杀人,最后被枪毙,陈丫离家出走。她匆匆忙忙找了一家纺织厂工作,嫁了一个并不如意的丈夫,丈夫发财后抛弃了她,陈丫最终进入夜总会当陪舞小姐。纵观陈丫的经历可以看出,父亲的打骂、家庭的困难、自己所受的委屈使她的心灵受到伤害,但是没有人关心她的心灵。一个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有的爱和教育她都没有。反而是对父亲,甚至整个家庭的恨充满了她的心灵。
她本来可以成为学习优异的大学生,但是她在心灵的痛苦和扭曲之后选择放逐自己,最后她离开家庭成为无依无靠的流浪者。她完成了心灵、家庭和命运的三次“出走”,这三次“出走”也蕴含着陈丫艰辛的心理抗争过程。她明白自己出走的结果,因为是她自己有意识甚至自虐般地亲手毁灭了自己。然而流浪的痛苦并不比来自父亲的痛苦好受。她用这种放逐和流浪报复父亲,可是就连这种报复和放逐的主动权她也没有掌握很久。离开家庭是她第二次放逐,是一次彻底的流浪,这之后她面对生活的压迫,男性的抛弃和玩弄,物质世界的奸污。她也许会后悔当时所作出的出走这一选择,但是她也明白人生没有回头路,她只能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无力扭转,于是她说出了:“到了40岁就能忍受一切”。从陈丫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娜拉式的出走,鲁迅说过:“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陈丫是有勇气的,她没有选择回那个家,但又是弱小的,面对外界的豺狼虎豹她无力反抗,“出走”的结果成了忍受一切,卑微地生存。这篇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它勾画出一幅女性成长的辛酸史,这是很多女性和家庭的写照,它让人们看到“出走”的女性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也让人反思在成长教育和社会中应该赋予女性如何的关照和权利。
《蓝色天空的琐碎记忆》中的瞎子流浪汉是作者塑造的另一个充满现实意义的悲剧形象。他原本是一个自愿到高原投身建设的修路工人,在一次事故中被炸瞎双眼,之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念,他没有选择回到内地,而是悄无声息地离开,成了悲惨的流浪汉。他的“出走”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他的追求和个人价值都随着事故一去不复返,他以一种逃避世人的方式逃避命运的折磨,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保持人性中的最后一点尊严。
瞎子在流浪中萌发出对电灯的强烈渴望,电灯象征着光明和温暖。瞎子一旦回到牧场过安静的生活就会烦躁和痛苦,他就不得不面对没有希望的生活和未来,面对“瞎”这件事实。所以他必须“出走”,去忘记痛苦,追求代表着光明和温暖的灯泡,“出走”使他解脱并有所寄托和追求。后来他“不再讲电灯,他开始讲他水里的感受,他说在水里他舒服极了,在水里他能够想象太阳那炽烈的光。一上岸不久,他又开始要求进人水里,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他心中对光明的渴望将他痛苦地煎熬,他的“出走”自始至终都是痛苦的,最后他只能走进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和痛苦。
瞎子这个人物形象充满悲剧色彩。他的“出走”是对未来的抛弃,对无法接受的现实的逃离,他对电灯的向往说明心中对于光踢和温暖的渴望并没有熄灭,反而是极其强烈的,这个人物带有一定超现实的虚幻色彩,他“出走”的方向是无目的的远方。远方指向的是死亡,透露出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对道路的隐喻和对苦难的怜悯。
三、出走——时代的迷惘
康巴地区身处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原始的藏族宗教和文化世代流传,偏远地区的游牧文明烙印在每一代康巴儿女身上。然而这里又是茶马古道的中枢,属于多元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地带,特别是康定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对繁荣,多种潮流的冲击下使得康巴人不得不面对异己的现实及精神冲击。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之后,现代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一步步向原始的康巴藏区传播,面对充满激情新鲜的物质文明,一些传统的康巴人出现了精神危机,一部分人选择退回到封闭的生活中。而一部分人选择“出走”,他们更多的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一点点被动地走进陌生的时代。
《给幺指打个结》写到电视信号接收器像是“一只只向天空乞讨的碗”。这鲜明地表现出传统康巴人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他们的生活虽然已经离不开日新月异的技术、科技,但是自然与神灵所占据的精神世界仍然无法接受科学的挑战。但是主人公嘎玛骨子里是好奇的。“在岭卡溪,嘎玛是接受新事物最快的人,全村第一个电视接收器就是他架上屋顶的,第一台摩托车也是他从城里骑回来的”。此时他对新世界是有积极态度的。他看电视广告。给朋友买手机,却因为误会而以为被骗了,甚至导致朋友的隔阂,这使他的正义感和自尊受到了伤害,他对新事物开始产生质疑。这时他的右腹总是疼痛,认为是买的假饮料造成的,于是原本充满新奇的外部世界在他心里“收缩成了一个硬块”。他对高原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敌意,而随着受骗的打击,他心中的善良也陷落。他的心灵开始“出走”,他用诈骗、碰瓷、恐吓的方式骗异地人的钱,他却认为:“外面的人太坏了,该让他们尝尝滋味”。后来他决定去成都找卖手机的人。这次“出走”他怀着使命感,甚至报复的决心,他背负巨大的时代和道德的重担,从高原走出去,似乎是要去打一场仗。
他的“出走”可以看做是两种文明、地域、道德体系的一场对决,他的内心通过出走这一行为发生了扭曲,他不仅没有找到自己所认可的公正,反而抛弃了自己原有的道德良知。后来他才知道真相,手机是因为自己不懂汉语而误解了广告的意思,腹部的疼痛是患了肝包囊虫。如此一来。他之前所做的错事成了彻底的恶。那才是真正的欺骗。嘎玛的内心由此产生强烈的忏悔,他竟然决定放弃手术。要把这些虫养在身体里,以此作为救赎。这又可以看做是一次回归,而此时的回归并不是简单地退回到原有的世界,他经历过“出走”之后的醒悟,明白无论是新的经济时代还是旧的精神家园,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交织着螺旋上升,只要保持自我,坚持真善美,就能使新旧两个时代共同进步,这也是一代甚至几代康巴人所面临的正确选择。
在时代的交锋中,道德的缺失、人性的扭曲、罪恶的滋生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藏区在传统的宗教社会被现代价值观日益侵蚀的时候,两种立场似乎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对真善美的态度成了现代人的一种迷惘。就像嘎玛,他面对欺骗选择以恶报恶,反而让自己站在了恶的队伍里,然而他的内心是善良的,善和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这也就使嘎玛同其他迷惘的现代人一样,有了救赎的可能。对于现代人的未来,作者给予了最美好的想象,他用误解这一戏剧冲突展现善的回归,恶的救赎,作者显然相信现代人的未来是光明的,充满真善美的,恶与欺骗只是暂时的假象,善终将会回到纯洁的内心中。
如嘎玛一样的许多人只是时代中的小人物,顺应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虽然“出走”会造成不适与创伤,然而他们却选择了新的时代对自我的考验,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传统康巴人的“出走”,尹向东正是通过刻画这一些走向时代的人来表现一代人的心灵的迷惘和重生。
尹向东用平实而质朴的笔触在其作品中塑造出一系列“出走”的人物形象,显现出他强烈的精神探求和对底层人生命运的思考。在很多经典文艺作品中都有“出走”的人物,无论是因为绝望出走,还是向着希望出走,“出走”这一行为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出走”背后暗含的是时代的浪潮和命运的沉浮。对尹向东小说中“出走”的人物形象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悲剧命运的关注;对于藏族历史和传统的思考;对于小说所反映的现实问题的忧虑。而尹向东的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出走”,他带着温热的故土、挚爱的民族、生存的记忆而“出走”,去开辟更广阔的康巴文学的土壤。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