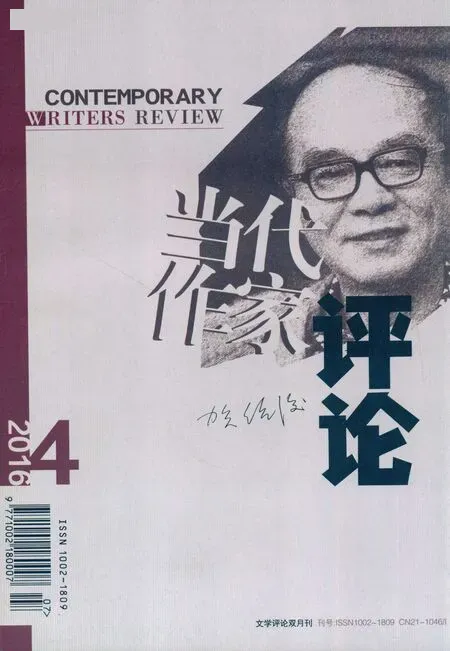昔“校园诗人”今如何?
----关于徐芳近年诗与散文的解读
郝 雨
昔“校园诗人”今如何?
----关于徐芳近年诗与散文的解读
郝 雨
“校园诗人”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现象。一大批充满浪漫诗情的年轻人,那些在刚刚恢复高考而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的群体,以诗歌形式表达着那一代人的激情和思考。至今,已近40年过去。当年的这一代诗人们,如今大多情况又如何呢?徐芳应该是最为典型的一位。徐芳作为一位女性诗人,从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走过来,从80年代红极一时的校园诗人走来,至今一直在写,到为人妻,为人母,到作为社会职责的承担者。在30多年里一直在坚持写,我就觉得这种坚持让我非常感动。其实,30年的时光足可以把任何纯真烂漫的东西磨掉,足可以把任何诗情画意的东西磨掉。而徐芳硬是坚持下来。无论是物质的诱惑还是现实的压力,都没让这么一个年龄意义上青春渐渐逝去(而非诗人意义上的青春)的弱女子放弃她的坚持。至于她坚持的是什么?彭瑞高的评论,我觉得抓得真的太准确了,其中有一句对徐芳诗的概括是:“善良而无奈。”*引自彭瑞高在徐芳诗歌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我觉得尤其是“善良”这个词对徐芳来说实在是说到了骨子里。“善良”——这本身就是她性格当中一种最本质的构成,而她的诗归根结底正是一种善的表达。
我想,这就抓住了徐芳最独特之处,最非同寻常之处。因为古往今来,诗人往往都不是善的化身,往往是批判,是哀怨,是愤怒,所谓“愤怒出诗人”。你看无论是男性诗人也好,还是女性诗人也好,大都是愤怒型的,或者是哀怨型的。但是从徐芳的诗里边你只能读到善良,没有批判。上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对获奖者穆勒的评价是“用诗和散文来批判社会的一个作家”。我当时就说,按照这样的标准,徐芳永远也获不了诺贝尔奖了,因为她根本不会批判,根本不会愤怒。在她的诗中,那每一个字都能让人感受到的就是一种善和纯真,而也正是这样的“善良”的基本内涵和精魂,使得徐芳的诗能够青春常在,也使得徐芳这样一位女性校园型诗人青春常在。
一、“诗神”与“纯诗的境界”
我曾经在我的诗评中反复引用我自己“原创”的一段“名言”:“其实,所谓爱文学的人,说穿了,是原就有许多不同的爱法的。譬如,有的是纯粹将其看得过于神圣而膜拜,譬如,也有的只是为了在其中寻求一种游戏的快乐。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是带着各自十分明显的功利目的,如有将其作为进身之阶的(古代的以文取士,现今的写了几篇作品就去混个一官半职等),也有将其用作赚钱盈利的(以这样的手段养家糊口甚至有些高级写手以此发家致富的不在少数),还有纯粹用它来附庸风雅的(有些官员写点诗词,出本书什么的,甚至在别人的书上挂个名字之类)。总之,不管怎么说,那位伟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文学的爱也是如此。”
这里一开始就在为徐芳而作的这篇小文中搬出这么胡言乱语的一段,并不是因为这话和徐芳的写作有多么密切的联系,而是又想着自以为是地再次“原创”一段类似的“名言”:所谓诗人,往往都是一些不同常人的人。而这些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又常常是因为这些人的心中大都藏有一个“魔”——一个“心魔”,或者起码是一个“诗魔”。之所以称之为“魔”,主要是因为在这些人的写诗动机和欲望当中,大都掺杂着某种现实的目的,无论是现实主义的也好,浪漫主义的也好;无论是“政治”的也好,“人生”的也好,以及“力比多”的也好……总之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可称之为“魔”的非诗的东西驱动着。这和本人的上一段“名言”中所说的最后一类人的爱文学的动机是相近似的。而在我眼中,徐芳却不是这样的诗人。读徐芳的诗,你可以从中感受其内心的一片澄澈,更能从中感受其内心的一片宁静。如果说她作为诗人也同样在心中有点什么,那也应该说她心中有的只是一个“神”,而绝不是“魔”。看得出徐芳的写诗完全不是为了什么很现实的目的,她真的是那种为写诗而写诗,即她自己所说的“纯诗的境界”。但是,徐芳的“纯诗的境界”又完全不是像前文所列举到的那种单纯“为寻求游戏的快乐”,她的诗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性灵之作、性情之诗。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徐芳诗集封面的那幅照片实在拍得太差了,一点都没拍出徐芳本人那种纯情的精神。
承认徐芳的诗是真正的“纯诗”,首先是因为在她的诗中你读不出任何现代人常有的那种牢骚、怨气、不满、压抑,甚至批判,以及那些带有明显思想教育性的语言内涵。包括她写给儿子的30多首诗,也都不是为了像《三字经》《千家诗》之类经典那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她只是以纯美的意境、纯诗的意象,和自己最亲近的儿子进行一种情感深处的沟通。徐芳的诗全都像她曾经出版的那本诗集的第一首的标题那样,都是“风在说话”。“风”当然是最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风”的说话当然也是最无拘无束的一种表达,“风”也不会说那些充满伟大思想的“话”;而徐芳当然也不想借风而传达自己的什么“话”,她就是要让风随心所欲地自己“说话”,并在风的说话中体悟那些富有诗意的内涵:“沙沙的声音呼唤我进入/它在前面的旷野中/逐渐喧响/从路到路/到路的消失……”可以看出,徐芳的诗真的是没有目的,更没有杂质的,尤其是不带有那些很“现实”的目的和功利,即她心中没有一个“心魔”。而她之所以数十年对诗歌的写作“不抛弃、不放弃!”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三个字:我喜欢!这样的三个字独立地看上去有些“小资”,有些“文青”,甚至有些上海小女人的“嗲气”,但是,她又的确体现了徐芳诗歌写作上的单纯,同时也隐含着徐芳内心深处的那种执著;而且,尤其是从我所熟悉的诗人徐芳那里说出来,我相信!
二、“纯诗”与“宁静”的风格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飘逸”、“流动”二品。而一般评诗也常以“空灵”、“洒脱”论之。徐芳的诗与这几种常见的诗歌品性都沾边,但又无法简单地用这几个现成的术语和形容词来概括和套用于徐芳的诗。其实我对徐芳的诗最突出的阅读感觉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就是“飘忽”。所谓“飘忽”,也并不是像那种很词典化的解释,即踪迹不定,隐约不清,甚至没地方着落。而是一种缥缈灵动,空阔悠远。总之是那种不大能说得很清楚的阅读感觉,当然如果能说得很清楚也就不能叫做飘忽了。而且,这种感觉又只能是一种感觉,甚至完全不能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用语应用于诗评。但是,在此我又只能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因为确实没有别的语词能够比这个“飘忽”更能表达我对徐芳诗的阅读感觉了。最典型的是她的那首《睡莲》:
一朵睡莲就是
一个梦!
仿佛来自月的中心
湖的深处
由月光、星光和水光聚合而成
飘忽的、恬然的
一种既明又暗的感觉
欲迎还拒、隐隐约约
像一种希望,也像回忆
哦上帝,我对它知道的
是如此之多
又是如此之少——
……
全诗的感觉,的确都是“飘忽的、恬然的”。当然,笔者在本文中并非要对徐芳诗作评,而是要评其散文。但是由于诗才是徐芳创作的主业,她也一直是以诗人名世,所以她的散文归根到底还是属于诗人散文。那么,评其散文,也就不能忽略其诗人的原始身份。而且我们的评论也应该和必须看清楚其散文与诗的关联和区别。
实事求是地说,关于对其诗的飘忽的感觉,我曾经一直担心自己是否感觉准确,而就在读了徐芳最近出版的一部散文集之后,我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感觉。理由是,书中有一篇散文就叫《诗:我的心灵花园》,其中是这样记叙她的走向诗坛的过程的:“我其实不知道我为什么写诗。不知怎么,我就写诗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7岁还是8岁,或者更早,像送走一艘纸帆船、一架纸飞机,飘飘荡荡的那种感觉,叫人难以相信。但是,这是真实的说法,你不得不信,我自己也是。要从头说起,却真是无从说起。”女诗人在从女孩子走向诗人的路途上,是否都有这样的过程呢?总之她就这么飘飘荡荡地写起诗来。所以,这种飘忽感就贯穿于其所有诗作。
“纯诗”、“宁静”的基本风格和诗学追求,注定了徐芳的诗在意象的选用和组构上大都是那些纤小、柔弱、安静的对象,比如水滴、落叶、烛光、花朵,等等。徐芳诗中基本上看不到特别恢宏、庞大的意象。而即使是比较庞大的物象,在徐芳的诗中也往往被处理得柔美和纤巧。比如:《飞跃夏季……那条公园的小径》,比如:《楼上的春天》,比如:《夜与黎明的守望》,比如《森林的问题,我的问题》等等。徐芳的聪明首先就在于她非常清楚自己作为诗人的斤两。她至今都一直认为“自己成不了大诗人,没那条件”。所以,她从来不把自己无限夸大成能够用诗歌干预社会甚至拯救世界的具有伟大历史使命感责任感的天降大任的诗人。因此她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诗学观:“不无感伤地告别瓦雷里的哲学家般的睿智、艾略特上帝般完美的虔诚、卡夫卡深入血脉的深刻忧郁、埃利蒂斯魔鬼般瑰丽奇谲的想象以及金斯堡歇斯底里般的桀骜不驯……”这里显然表达的是诗人对于诗的方向性、原则性的选择。当然也显示了诗人对于自己的诗学价值的定位。她把那些世界文学史上的各种类型的顶尖级的代表性作家和诗人,全都宣布与之“告别”,那么,这一连串的告别之后还剩下什么?剩下的当然只有“纯诗”。
三、散文中飘忽的坚实
但是,近年来徐芳却大量地写起散文,近几年已出版的散文集有《都市邂逅》《她说:您好!》,还有诗文合集《岁月如歌》。就诗与散文这两种文体而言,散文在本质上是要实的,也就是不能飘忽。由飘忽而落实,这也许与徐芳入世已深,对生活的认识更加实在有关。在这本新近出版的《月光无痕》一书的序里,徐芳认为:文体意义上的“散文”可以信马由缰、自由驰骋,艺术的指向与可能性都可以落实于纸与笔的摩擦或手指与键盘的接触中。就这样,诗人在散文中运用轻盈灵动、饱含哲思的文字,把记忆深处的片光零羽轻描细绘。这些记忆中的划痕、欢笑、痛和沧桑,真切明澈地铺陈出了她对时代的心灵印迹,并透视着现代都市的发展与变迁。虽然,她的许多散文的文字依然灵动飘忽,但其内容已经都是实存的记录。所以,我将其称为“飘忽的坚实”。
毕竟,徐芳的笔下有了许多童年真实的故事,也有了许多成年后深切的感悟。《藏钱》中小姑的秘密,《两个外婆》中隔壁家慈祥老太的关爱、《一年又一年》中对被“没收”的压岁钱的追忆、《阿妮头》中的姐妹情深……这些故事都是实在的。然而,徐芳骨子里还是诗人,她把这些纪实性的文章仍然是当作诗来写的,她说:“我写的一切有缘的邂逅,无缘的挥手,片刻的永驻与永远的流逝,不管技术上是如何应用:在语调或者情调上,表里之间如何转接,如何在控制中表现张力与韵味,如何在口语和不能完全口语之间,以及语言的新与旧之间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把握……也许,说多了反显得笨拙,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词,那就是对生活的珍重,珍重在我用以造型的材料与情感上,也珍重在我所用的心机上。”所以,在《地铁漫游》中,徐芳将地铁看成一个碎片模式,一大群人下车了,又分散了,走远,消失,再不相逢,每一个出口都像是时光隧道。还有《金色的高架路》《搬家故事》……透过这些城市生活五光十色的表面,徐芳深入到置身于其中的城市人的内心世界,咏唱、感叹,用她诗人的灵气诠释传达其特殊的人生领悟。
其实,真正能体现徐芳诗人本性的是她对自己那段“下海”经历的记述。《一个春天和几个诗人的往事》可以说是徐芳散文中最富趣味性的一篇,是你能够一边读一边不时发出会心微笑的一篇。曾经,徐芳居然和她的很多诗友们宣告:“只谈生意不谈艺术。”诗人们居然情绪激昂地辞职、练摊,以为从此也能成为商人赚大钱;她自己也满心欢喜地看货、运货,卖营养液、卖工艺木挂件,甚至在这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极有趣的故事。但最终,诗人还是诗人,诗人成为不了商人。“我要的货和我要见的人一样,都埋伏在黑暗之中”、“眼前这条路是条幻想的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社会无疑是物质的,但是,却又一点都离不开精神。当无数人都在不遗余力,费尽心机追逐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时候,精神的坚守就极为可贵。如果这个社会完全被物质充满,没有了精神的空间,那才是真正可怕和可悲的。谁能读得懂徐芳的这份坚守呢?谁又能真正读得懂徐芳的这一片诗心呢?
徐芳说:“我把写诗当成了一场逃亡。有很多人是向外逃,而我不然,固然是那种对青春的践约,似乎更是一种慌张之后的飞蛾扑火,只怕更表明了,我与现实生活的脱离程度已如此严重。”而她对“逃”的解释是:“欲以诗歌葆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内心世界,在其中种花种草,也以这样的手段与方法,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来明了与进入他人精神的世界。”虽然我们说 徐芳的诗歌风格是飘忽的,但她对诗歌的信念却是极为坚实的:“越是超越的人生,就越是诗化的人生。”在这篇《诗:我的心灵花园》中,我更加真实地读懂了徐芳,更加认识了徐芳作为诗人的生存状态。在这个严重物质化的现实中,徐芳似乎依然像十八岁刚刚写诗的那样,依然是飘飘荡荡的,或者依然是飘忽的。
而从徐芳在这部散文集“序”中的一些自我表达中,她信奉的是苏珊·桑塔格对诗人散文的观念:“请求记忆说话或哭泣”。她认为这里包含的是对记忆的虔诚,是对“散”的姿态的眷顾和挚爱。所以,她一方面努力打开记忆,让曾经的真实作为散文之骨肉;另一方面,她又坚持“循着诗的某种路径,去经营散文”,像普鲁斯特,像乔伊斯一样,沉浸在“无意的记忆”之中,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散”中。所以,诗依然是其散文的灵魂。尽管她的散文在尽量靠近现实,或者在文笔上尽量进入现实,她甚至精心总结了自己散文纪实抒情的“五大技法”,而其整体的艺术风格,艺术韵味,还是显得那么飘忽。而这种飘忽归根结底是因为她不愿意把自己的灵魂依附在任何现实的物质之上,她宁愿一直自由自在地飘。她宁愿把全部生命献给诗歌。这正是她最坚实的人生信念和艺术追求。尽管诗确实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她却真心相信:“它能够超越于现实。”这就是徐芳的全部现实,这就是徐芳在诗与散文中的飘忽的坚实。
(责任编辑 李桂玲)
郝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