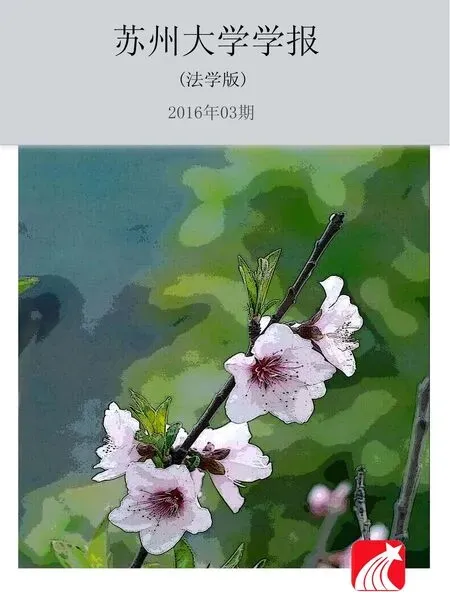龙泉司法变迁及其对当代中国基层刑事司法的借鉴
张 健
龙泉司法变迁及其对当代中国基层刑事司法的借鉴
张健*
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变迁也深刻地影响了基层法院的刑事司法运作。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样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至今三个阶段刑事司法场域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期考察近代以来基层刑事司法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对基层刑事司法治理模式的历史梳理,为现代意义上刑事司法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提供了经验。
基层刑事司法;治理;国家与社会;犯罪
在现代国家,基层社会的治理绩效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村落乡镇与县来透视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与变迁,这一直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在人类学家那里,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研究亲切地称为“小地方、大论题”。将基层刑事司法放置于革命与社会变迁的“大历史”中去考察,或许可以发现刑事诉讼在基层社会的日常运作逻辑与过程。从这些源于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而展开的琐细而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能够探寻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上的特点,以为现代刑事司法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以浙江省龙泉市的司法档案作为考察样本,尝试运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龙泉县百年基层刑事司法变迁史展开讨论。①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浙闽赣边境,是隶属于浙江丽水市的县级市,自古以青瓷、宝剑闻名。文章研究的缘起是晚清民国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大量司法档案的发现对于当代刑事司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②2007年,浙江大学地方文书研究团队无意中在龙泉市发现一大批晚清民国司法档案,引发了海内外史学界与法学界的强烈关注。龙泉司法档案时间自咸丰八年(1858)始,至1949年止,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为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学界普遍认为,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中国司法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龙泉司法档案历史跨度较长,司法档案包括晚清、民国、建国后三个阶段。③文章使用的司法档案包括了三部分。首先,晚清部分,由于晚清部分的司法档案已经整理完毕,于2012年8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所以文章所使用的晚清档案案例来自《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晚清时期);其次,民国部分,由于档案存放无序并有残缺,目前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正在整理过程中,文章所用档案是原始档案,卷宗名称依照原档案卷宗袋上的标签名;再次,建国后至今,建国后至今的司法档案则存放于龙泉市法院。基层刑事司法运作的变迁过程显然带有浓重的时代印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基层刑事司法的历史更迭。①在具体对象上,本文选择“涉林犯罪”这一在龙泉司法实践中颇具典型意义的犯罪形态做为考察对象。本文使用的“涉林犯罪”案件,一般是指有关林业生产的刑事案件。龙泉县属于多山地形,向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谓,林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已经整理的晚清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关于林业纠纷的案件就占据了一半以上。以某一特定犯罪类型为研究对象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准确把握刑事诉讼与社会、经济、历史等因素之间的关联度,更利于对刑事司法的变迁做细致深入分析。
一、晚清及民国时期:刑事和解与国家治理的简约化
在传统中国,皇权止于州县。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领袖、族长、保甲长以及诸如行会组织是国家与地方政治衔接的桥梁,他们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管理,乡村社会因此呈现出“绅治”的特征。国家政权对民间纠纷的介入有限。②在民国时期,费孝通等学者已经注意到传统乡村社会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提出了“上下分治”、“皇权无为”、“绅权缓冲”、“长老统治”等颇具解释力的概念。此后马若孟、黄宗智、杜赞奇等西方学者借助日本满铁调查资料对华北乡村所作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印证和深化了这些看法,并描述了进入20世纪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移、乡村社会自主性逐渐被打破的历史进程。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州县官员作为基层“法官”,只被授权就民事案件和处刑不过笞杖或枷号的轻微刑事案件做出判断。这类案件被称为“自理词讼”(即在州县官全权审判之下的词讼)。③关于“州县自理案件”的界定,滋贺秀三教授说:“没有必要处徒以上刑罚的案件,全部都委任给州县一级进行处理。只要当事者不上诉,上级机关与这类案件就不生关系。这类案件称州县自理的案件。”夫马进教授说:“州县自理案件是指在州县一级终审的案件,即无须报送府以上进行审理,在州县一级,作为刑罚可处笞、杖,或者完全不处刑罚而仅以训谕结案。参见[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第395页。清代大多数州县官员主张应准予两造和息,轻微的犯罪案件上调解的达成,有州县调处,有两造亲友调处,有地方绅耄调处者,亦有由两造双方自行和解者。④那思陆:《中国审判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比如,在龙泉司法档案中,记载了咸丰元年李联芳控韩林秀强霸阻砍一案,当事人李联芳的状词就这样写道:⑤《李联芳控韩林秀强霸阻砍案》,吴铮强、杜正贞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晚清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为控韩林秀等强霸阻砍,挽迈图诈事……生于本春雇工登山砍伐为货,讵地恶韩林秀、坛秀不思业经父手杜卖,专恃强横莫敌……胆拥山内,恃强凶宿,抢击砍伐……生旋即回家报明,遂投庄保朱芝裕、朱芝邦理谕莫何……为此抄粘各据,伏乞廉明父师迅赐拘究以儆凶宿……。”
咸丰元年(1851年),李联芳控韩林秀强霸阻砍案是目前龙泉司法档案记载最早的案件。在这起案件的呈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李联芳在向州县官员呈诉之前,就曾将案件投报于庄保朱芝裕、朱芝邦等人,请他们出面理谕调解未果以后,原告李联芳才将案件呈控于县衙。并且,此案也是经过当事人反复呈词以后才得以受理。这都显示出帝制时期基层刑事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民间调解方式进行,这一利用准官员和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地方治理的方式被黄宗智先生称作是国家的“简约治理”或“简约主义”。⑥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但是,当龙泉“无为而治”的“绅治”模式发展到近代,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清末民初时期,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为中国司法的近现代化改革提供了理论准备。⑦叶麒麟:《现代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载《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5期。如何加强国家权力对乡村地方的控制与实现国家权力下沉,这成为了时代思考的主题。⑧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具体到刑事司法中,突出体现的就是国家追诉原则的引进,国家追诉原则强调国家对犯罪的垄断与刑罚权的统一行使。⑨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对检察制度与国家追诉主义的必要性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明确提出了检察官代表国家利益,不得随意舍弃起诉权。他在《刑事诉讼律草案》之后的奏折中开始强调检察人员的“国家属性”,即“检察提起公诉。犯罪行为与私法上不法行为有别:不法行为不过害及私人利益,而犯罪无不害国家之公安,公诉即实行刑罚权以维持国家之公安者也,非如私诉之仅为私人所设,故提起公诉之权,应专属于代表国家之检察官。”参见陈瑞华:《二十世纪中国之刑事诉讼法学》,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又见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1907年,《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庭试办章程》第106条规定:“凡经检察官起诉案件审判厅不得无故拒却,被害者亦不得自为和解”。因此,“刑事和解”这一传统的司法实践被认为原始落后而遭排斥与禁止。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刑事诉讼法》和1935年《刑事诉讼法》再次明确了国家追诉原则。检察官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决定对犯罪的追诉,刑事案件纠纷解决成为了政治国家集中控制的领地。精英化、专业化和程序化的新型司法程序从国家法层面上得以确立。
然而,尽管立法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将刑事和解排除在国家的正式制度之外,但是,由于传统的巨大惯性,并不能否定它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角色。正如档案所显示的,在民国基层刑事案件纠纷的处理过程中调解仍旧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司法官在案件开始后一般会讯问当事人是否经过了调处,之后,司法官要么自己主动调处要么是指令保甲、宗族、家族亲友等民间力量介入调处。这里,以1940年蒋国祥诉潘根林窃盗竹木一案为例予以说明。①《蒋国祥诉潘根林窃盗案》,卷宗号:M003-01-07096,《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
检察官点呼蒋国唐入庭
问:你是保长?
答:第四保长。
问:蒋国祥、潘根林都归你管吗?
答:是我保里的人。
问:潘根林把蒋国祥竹砍了你晓得否?
答:喊我到山上去看过。
问:你把他们谙②调解、调处的意思。过否?
答:未谙过。
问:为啥不把他们谙过呢?
答:潘根林不曾谙,他说竹是在老竹之下。
问:现在潘根林说是嫩竹出在他田上,所以砍了的,以后不会去砍了。蒋国祥说,要把竹田画到什么地方,那是经界问题,你保甲长是要说说的。
答:是的。
……
上述对话是蒋国祥诉潘根林窃盗竹木一案侦查笔录中的一个片段。从中看到,在原被告双方关于盗窃赔偿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检察官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并且在此过程中,检察官巧妙地利用“保甲长”这一民间力量介入调解,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促成了和解的达成。在本案中,检察官几次使用“同胞兄弟”等“关键词”,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化,劝谕当事人自觉、忍让、和息。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检察官并未摆脱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的在司法中遵循和维护纲常原则,调解依旧多依据“亲情”、“人情”和道德伦理。③俞荣根、魏顺光:《中国传统“调处”的非诉讼经验》,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这可以说是帝制时代教谕式调解的余绪。最终该案在保甲长与检察官的调解下,双方具结和解结案。
既然当时的国家立法层面并不承认刑事和解,那么民国时期的司法官员又是如何对作为“潜规则”存在以及刑事和解必要性进行司法说理的呢?这主要依靠民国1928年和1935年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其中,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1条规定了不起诉的十种类型。对于告诉乃论之罪,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了“告诉乃论之罪,告诉人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撤回其告诉”,所以,对于告诉乃论之罪的当事人和解撤诉申请,检察官一般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17条;对于非告诉乃论之罪,检察官适用的法律依据是1935年《刑法》的第57条和第61条①1935年《刑法》第57条规定:科刑时应审酌一切情状,尤应注意左列事项为科刑轻重之标准:一、犯罪之动机。二、犯罪之目的。三、犯罪时所受之刺激。四、犯罪之手段。五、犯人之生活状况。六、犯人之品行。七、犯人之智识程度。八、犯人与被害人平日之关系。九、犯罪所生之危险或损害。十、犯罪后之态度。前项情形,应附记于不起诉处分书内。第61条规定:犯左列各罪之一,情节轻微,显可悯恕,认为依第59条规定减轻其刑仍嫌过重者,得免除其刑:一、犯最重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专科罚金之罪。但第132条第1项、第143条、第145条、第186条、第270第3项及第276条第1项之罪,不在此限。二、犯第320条之窃盗罪。三、犯第335条之侵占罪。四、犯第339条之诈欺罪。五、犯第349条第2项之赃物罪。。上述条款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自由裁量权。而窃盗罪在民国时期属于非告诉乃论之罪,检察官可以根据1935年《刑法》的第57条和第61条规定做出自由裁量,司法说理并不困难。还是以蒋国祥诉潘根林窃盗竹木一案为例予以说明。
浙江省龙泉地方法院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书
查被告人蒋国祥诉潘根林窃盗竹木一案正侦查间,复据告诉人当庭请求撤回告诉到院,查核案情,被告虽不无《刑法》第220条第1款之嫌,但其所犯者属于同法第61条列举各款之罪名。依《刑事诉讼法》第232条规定,参酌《刑法》第57条一切情状以不起诉较为适当,爰依《刑事诉讼法》第234条予以不起诉之处分如右。②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4规定:检察官依前三条规定或因其他理由为不起诉之处分者,应制作处分书叙述不起诉之理由。不起诉处分书,应将正本送达于告诉人及被告。前项送达自书记官接受处分书原本之日起不得逾五天。
蒋国祥诉潘根林窃盗竹木一案的和解发生在检察官起诉阶段。这反映了龙泉司法档案刑事和解的基本特征,即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主要是检察官在发挥作用。对于严重的刑事案件因为危及社会稳定,系争利益重大,司法机关根本不会调解。这主要集中在政治性犯罪和杀人案件,检察官会毫不犹豫地提起诉讼,进而法院做出判决。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检察官在案件开始后一般会讯问当事人是否经过了调解,之后,检察官要么自己主动调解,要么指令保甲、宗族、家族亲友等民间力量介入调解。在已经研究的300份司法档案刑事案件中,有124起案件通过和解的形式结案,最后通过法院审判结案的案件只有80件,比例还不到三成。这样,大部分刑事案件在没有进入审判程序之前就以检察官不起诉的形式结案了。此时的检察机关承担了重要的案件分流作用。③参见胡铭、张健:《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9)的考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在传统社会起作用的各类调解主体,于民国时期的刑事纠纷解决中仍发挥重要的作用。宗族、家族亲友、保甲长、乡公所④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乡镇自治施行法》第32条的规定:乡公所或者镇公所设立调解委员会,办理以下事项:(一)民事调解事项;(二)依法得撤回告诉之刑事调解事项。等民间力量介入刑事案件的现象普遍存在。这表明,尽管民国时期新式刑事立法已经确立了国家追诉原则,国家正式的刑事司法系统已经初步实现了专业化与程序化,也尽管随着国家政权组织的触角深入到乡村基层社会(比如清末民初的近代警察力量的建设,⑤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龙泉县由地方集款筹建巡警局。1929年5月,县警察所改为县公安局。并在县政府内设警佐室,由警佐兼警察所长,协助县长佐理警事……1948年,县警察局扩充为183人,警察按照性质可以分为行政、刑事、保安和卫生四种……民国警察的任务主要是禁赌、禁烟毒、禁嫖妓、反盗窃,执行《违警罚规》并负责逮捕、押解人贩等警务。参见林世荣:《龙泉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474、475页。国民政府期间的保甲重建等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国家惩罚治理犯罪的专业力量强大,民间社会力量在犯罪治理的场景中有所消退)。但是,传统中国依赖准官员和民间力量解决纠纷的简约治理方法,仍然被国民政府所沿用,旧的草根阶层的简约治理仍然有相当部分被保留了下来。
总之,晚清民国时期刑事案件纠纷解决系统存在三个重要部分:首先是国家的正式司法系统,其次是通过民间宗族调解解决争端的民间体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领域”。①张健:《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第三领域”》,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犯罪治理并不只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尽管在清末民国,国家权力试图下沉到基层,控制乡村,然而这种努力并未成功。乡村社会的宗族组织、士绅阶层等社会力量在整合社会、维护民间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势力既分享着国家权威治理乡村,同时,又对抗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他们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国家的治理成本因此大大降低。
二、建国初期:国家全能主义与司法政治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6月5日,龙泉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此后,龙泉县人民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陆续成立。如果说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更多依靠自然生成要素的话,那么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人为发动运动与革命的形式来进行社会治理、改造的特征就显得极为明显。新政权成立伊始就面临严峻的政治斗争、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碎片化的社会、贫乏的经济以及国际社会的孤立等一系列难题。如何在积贫积弱的环境下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如何巩固政权,使国家权力下沉到基层社会,这成为了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的考虑的重点。在新政权成立后较短的时间内,国家通过各类运动对社会进行了全面干预和控制,也因此获取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形成了整体性国家体制。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以废除六法全书、1953年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法律革命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等运动的开展成为了国家权力下沉的重要方式。经济改造、政治改造、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改造同社会的重组,新生活建设齐头并进,它将职能的触角伸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里以建国初“大跃进”时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为样本展开。
1958年5月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跃进”运动不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司法工作必须适应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势》的指示,“要求各法院研究司法工作应该如何的保卫人民公社的建立……使我们的思想紧紧跟上形势的发展。对于各地在试办人民公社中已经发现的敌人破坏活动和人民内部的纠纷案件,尽狠狠地打击敌人……”③[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下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由于刑事案件基本上属于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的突出反映”,所以,对待犯罪必须严厉打击,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专政机关,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它们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是用来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④简讯:《司法工作必须适应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的指示》,载《人民司法》1958年第14期。从1958年开始,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发展,龙泉县司法系统开始公、检、法三机关“合并办公,一致对敌”,组成公安政法部开展联合办案。这时候的砍伐林木犯罪已经以“破坏生产”、“破坏合作化”、“反革命”等罪名形式出现。
(一)刑事司法中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庭、宗族、村、行会等解决纠纷的功能被弱化或被废除,然而,人民法院的技术治理能力又未能完全发展起来,在此背景下,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群众路线,并通过“身体在场”的方式来确保基层社会秩序。⑤郑智航:《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法院的司法路线——以国家权力下沉为切入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国家治理力量下沉到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刑事司法过程中群众路线的落实。“人民法院对敌人实行专政,惩治犯罪,必然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完成它的任务。真正成为敌人害怕,群众欢迎的人民司法机关。”①王云生:《审判工作怎样贯彻群众路线》,载《政法研究》1959年第6期。群众路线构成了建国初期刑事司法审判的基本特征。
一起普通的犯罪案件的开启往往是群众、人民公社的检举与要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主要证据来源也是群众诉苦过程中的言说和举证。对被告人的科刑依据也往往视当地多数群众的意见来定。群众参与刑事司法的基本的流程分为了四个阶段:首先,搜集材料和逮捕阶段:普遍采用群众或者人民公社检举的方式,通过大大小小的座谈会、诉苦会等方式调查搜集材料,再结合个别访问,寻找人证、物证等。第二,开庭审理阶段,往往根据案件特点和客观条件决定采用何种方式的群众辩论形式。实践中有大型辩论会、小型辩论会、分别辩论、共同协商和家庭会等几种方式。群众控诉时采取“一人说理,大家帮腔”的方法。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宣传教育和政策掌握。目的是广大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达到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学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争大辩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龙泉县法院在1959年审理的一起破坏山林案件最终以反革命定性。②《林世加反革命案》,卷宗号:(1959)龙法刑字第00121号,浙江省龙泉市法院藏。以下是这起案件审判过程的记录片段。
主席宣布斗争坏分子林世加。
到场职工揭发坏分子林世加罪恶事实:
刘志文:林世加一贯不老实,破坏制度……
季月荣:……
刘水根:……屡教不改,一贯对抗改造,没有从本质上改造自己。一贯批评党的政策与社会主义建设……
刘志坚:一贯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领导不满,破坏生产运动,生活腐化堕落,迫使妇女跳楼。领导安排他上山劳动,但是他破坏生产,上山破坏森林……
钟志清:无理取闹,称赞劳教爽,生产时磨洋工。
江金泉:……
许志清、吴月亮、陈吉等人检举。
大会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坚决不允许盗窃活动
如果准予盗窃活动,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完全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是想摧毁社会主义的人。
对叶传义偷窃行为是有历史性的,一贯盗窃,现列举一下……
从林世加破坏山林案的审判过程来看,案件的审判流程呈现出典型的“广场化”色彩,具有高度的仪式化与渲染性。该案并不是一起孤立个案,而被看作是阻碍社会主义改造与破坏合作化生产的反革命典型案件。此案的审理承担着激发阶级情感和打击破坏生产的双重使命,而刑事审判的“广场化”效应则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大众的规训和治理。因为如果仅仅是由法官一人审判,这就削弱了群众的斗争力量,收效不大。法官在审判中起到的作用是引导群众诉苦说理。如果被告人出现狡赖强辩时,法官应当立即指出,然后由群众自动举证对质,加以穷追痛驳,以便群众进一步认识其罪恶本质,从而“使反革命分子在人民的巨掌中战栗失色,深感无处藏匿,而日益暴露于人民面前,把反革命这样一种罪恶的东西连根拔掉”。③罗瑞卿:《对敌要狠,对内要和》,载《政法研究》1958年第4期。
大跃进时期的公审公判与土地改革时期、镇压反革命时期的控诉大会和诉苦大会相似。①郭于华等人经过研究发现,土改中的诉苦对于建构农民的国家观念具有特殊的中介意义,详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526页。类似研究又见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用孔飞力先生的“普通民众对权力的幻觉”来分析恰如其分,“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围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②[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85页。在狂暴的群体运动里,这种幻想中的权力似乎存在。它可以是对反革命的杀戮和批斗,可以是任因仇人冠以罪名后的残忍与疯狂报复。这种权力为冤冤相报提供了广阔自由的舞台。总之,人民公社时期的刑事司法群众路线的大鸣大放大辩论,通过群众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和教育运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司法机关的专业化审判职能。无论是正规的国家司法机关还是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民兵连、党支部甚至学校与家庭都是惩罚组织,惩罚弥散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对整个农村的掌控。刑事司法群众运动带来的显著效应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而“阶级异己分子”的任意指定,导致了国家主义在此一时期的空前膨胀。
(二)管制与劳动教养的大量适用
除了正式的国家司法系统以外,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社会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路径就是劳动教养与管制制度的建立。劳动教养与管制制度在“大跃进”时期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并且在实践中出现了县、人民公社与生产队办劳教制度的现象。③《浙江劳教史》编纂委员会:《浙江劳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1956年8月国家司法部专门就“管制生产”与“管制”两者的区别作了解释:“管制”必须经法院判决,是一种刑事处分;“管制生产”属于监督生产的性质,是行政上的一种改造的措施和办法,所以,也就不需要经过法院判决,只需乡人民委员会决定就行。④李若建:《风起于青萍之末:“大跃进”时期的劳动教养与管制初探》,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然而,如表1显示的,尽管在法律规定上,劳动教养与管制属于不同层次的处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两者在基层被严重混淆。

表1 建国初期的社会管制样态与分类
管制与劳动教养的出现与适用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垄断进入新阶段。如果说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正式的国家机关来运作,在全国基层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县、人民公社与生产队办劳教制度的出现由县、社、队,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⑤高华:《革命时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下面的案件是李启坤破坏生产罪的提请管制意见书。①《李启坤破坏生产罪》,卷宗号:(1959)龙八刑字第00041号,浙江省龙泉市法院藏。这起案件来自吴吉奶的检举:“被检举人李启坤,破坏山林,他的山林1957年入社后,他就以建房屋为由大量砍伐树木五十多株,他不用,把树放在公社腐烂,他拿来砍成柴当柴烧。每天都要砍树一棵,带回家……”。
浙江省龙泉县公安局提请管制意见书
公民李启坤,男性,现年36岁,富农身份,职业种田,现住本县梅岭公社古岑坑管理区,因破坏山林,私自砍伐了杉木300余株,造成严重的后果,及又破坏食堂,又破坏积肥等一案,业经本局侦查结束,证据确凿,已构成犯罪,予以管制。为此特附送呈请管制意见表一卷,请予审查判决。
需要注意的是,建国初期的管制类案件一般由公安机关来提起诉讼。尽管基层的检察机关在1955以后才迟迟得以建立,但是,设立检察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确立诉讼上的权力分立原则,进而实现“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制约的方法,保障形式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②林钰雄:《检察官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建国初期的检察院建立之目的与职能与上述恰恰相反。正如论者所言,“检察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任务就是通过办案,打击敌人,保护人民,预防犯罪。他所控拆的被告人,基本上都是人民的敌人……”③张辉:《这不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评曲夫略谈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诉讼地位》,载《政法研究》1958年第4期。尽管如此,为了简化程序,建国初期的刑事诉讼强调打破清规戒律、破除“死抠条文”、“关门办案”的司法作风,出现了公检法联合办案,“互相支援、通力合作、一致对敌”。④谭政文:《吸取经验教训推进检察工作大跃进》,载《政法研究》1958年第3期。三个机关由公安机关统帅,实际上法院与检察院已经成为附庸,刚刚成立不久的检察院成为了可有可无的机关。
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再次表征了刑事诉讼作为政治运动工具性的存在,而已经建立起来的相对合理的诉讼程序因为无法配合政治运动的开展也一再压缩简化。政治运动的时限性、与对敌斗争的紧迫性必然要求司法机关能够及时、快速地进行办案。由于大跃进发生在人民公社化时期,所以,不难看出,这时期的刑事司法是作为国家权力掌控基层社会的一种工具。同此一时期的其他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说明了人民公社试图全面掌控农村社会的企图。而“公检法联合办案”、“三员办案”破坏了刑事诉讼规律,导致冤假错案发生,所以在“大跃进”以后不久,公检法联合办案就被取消。
纵观建国初期的刑事案件审判流程我们看到,运动与革命构成了建国初期的刑事司法模式的主色调。刑事司法中的国家主义达到了顶峰,处理犯罪与解决刑事冲突的权力都由国家垄断,社会只是充当依附性的角色,尽管群众在运动中广泛参与,但被动的意味浓厚。其特征表现为:第一,国家垄断了解决刑事纠纷的所有权力,民间社会被完全排斥在外。其二,党的路线政策与国家刑事立法被认为是刑事裁决的唯一标准。一切民间规则被排除在外。第三,在控制犯罪的手段上,强调重刑化,认为遏制犯罪必须使用重刑。第四,国家垄断了刑罚的执行权。这不仅加大了国家执行刑罚的成本,而且也很难使犯罪人复归社会。
尽管建国初期的刑事司法产生了诸多弊端,但是采取革命与运动式的刑事司法模式之所以必要,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初期国家治理资源的有限。群众性的政治动员成为了国家治理犯罪的替代性、弥补性的手段。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革命与运动式的刑事司法本身面临深刻的危机,它难以迈入常规性、制度化的途径。运动治理的基本特征决定其在本质上与理性的制度化相背离,其自身也难以维持常规化运作。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因而也呼唤着新的刑事司法模式的来临。⑤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三、新时期龙泉的司法探索:修复性司法与社区矫正
文革结束以后,国家正规的司法系统迅速恢复和重建。1978年12月开始,龙泉县检察院、公安局与法院得以陆续恢复、不断健全,司法人员大幅增编。短短三十多年,伴随着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国家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推进与1978年、1996年、2012年历次《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修改,龙泉基层刑事司法系统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国家正规性的刑事司法机关开始以法律化和职业化的面目出现。
(一)龙泉对生态环境案件进行修复性司法的探索
在经历了三十年激进的革命政治试验以后,国家认识到其权力有限的现实,开始有限退出龙泉乡村。以社会重建与成长为核心的社会转型推动了刑事司法中国家与社会治理方式的演进,刑事司法理念的国家本位主义一定程度被消解。伴随着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从乡村中的撤退,乡村自治性力量开始有所恢复。基层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同时,过去数十年间一直被国家政权作为压制、打击、禁止和消灭对象的家族、行会、宗族等“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民间协会等民间组织开始在民间调解中出现,民间自发调解力量开始复兴。在这个极具变革的时代,龙泉也处于改革的巨大转型之中,地缘的、人员的因素受到市场经济和人口大范围流动的强烈冲击。面对复杂的犯罪形势,龙泉地区也做出了探索。
在国家立法对刑事和解制度“正名”之前,龙泉法院就曾对刑事和解做出试验。由于龙泉“九山半水半分田”,森林覆盖率达到71%,为了保护森林资源,龙泉法院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成了森林审判厅。森林审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龙泉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部分。尽管森林审判是法院民事审判的一部分,但是在轻微的涉林刑事案件中,依旧使用和解结案。这就是龙泉法院探索的“生态修复性司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龙泉法院在森林审判中实行了“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基本做法。这一时期就地调解的案件达到了95%以上。①周功富:《龙泉法院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涉林犯罪的特点决定了恢复生态、恢复植被应作为司法裁判首要关注的问题。龙泉法院提出了“惩罚犯罪是手段,生态恢复是目的”的理念,实行打击、预防与恢复并重,探索出“生态修复性司法”模式。从实践来看,生态修复性司法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委托调解模式。在侦查起诉阶段,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②对于生态修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实践中并没有以法定刑轻重为唯一标准,而是侧重考虑加害人的主观恶性,评估再犯可能性,一般情况下均应允许和解,但有下列情形的不允许和解:一是屡次毁林,主观恶性大;二是曾因毁林受过刑事处罚五年内再次毁林的;三是涉林职务犯罪。涉林职务犯罪侵害的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损害的是公共利益,不宜适用和解。检察院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参与调解的前提下,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居委会进行调解等组织在一定的期限、范围内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检察机关主要承担告知和确认工作。如果当事人承诺履行植树造林等生态恢复义务,检察院往往设立考察期间,不予起诉处理,考察期间终结以后,检察院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自身悔过与义务履行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第二,司法机关居中调解模式。司法人员居中协调,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让加害人与受害林农之间达成谅解,签订由被告人补植树苗或撒播林种,达到相应面积和成活率要求,并履行相应管护义务的协议。协议履行情况由检察院、法院联合乡镇林业站进行验收,作为被告人量刑悔罪情节来认定。加害方在认罪悔过的前提下,经与被害方自行协商,就恢复植被、经济赔偿达成书面协议。
如果在公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悔罪态度不真实,或者生态恢复经林业、环保等相关部门审核鉴定不通过,则撤销暂缓起诉决定,进入正常的公诉程序。而在审判阶段,如果被告人具有前述情形,或经社会调查评估认定不宜适用修复性司法,则恢复正常的诉讼程序。而在刑法执行阶段,可在提交相关生态恢复完成鉴定报告后,按减刑假释程序处理。在下面表2中,我们将生态修复性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进行比较可以得知以下区别。

表2
然而,上述的森林案件审判,只是国家立法规定修改之前的“法外”试验状态与地方探索。尽管这种试验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开展,亦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与反对。但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专章的形式对公诉案件刑事和解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刑事和解在基层由法律外的试验正式走向了制度化。2013年2月1日,丽水市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上级机关的有关规定,就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制定《办理刑事和解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龙泉市按照《丽水市办理刑事和解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国家立法进一步细化,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的案件,积极引导、促成当事人和解。调研发现,龙泉司法机关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盗窃罪等罪名上。其中,交通肇事案件和轻伤害案件共占刑事和解的82%,这大大拓宽了此前龙泉地区涉林犯罪“生态修复性司法”的范围。
与传统执法方式比较,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有利于修复被犯罪损害的社会关系,也有利于加害人回归社会、回归社区。而村委会、居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常设机构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影响颇深。它们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依托现有的民间社会资源,“修复性司法”引入“第三方力量”,邀请居委会、村委会的代表、双方当事人的亲属、朋友、单位配合调解或列席参加,这就为国家、社区、个人之间良性互动提供了平台。社会力量参与刑事司法实践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兼顾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它改变了传统刑事司法中坚持国家主义与集体主义至上,坚持国家单向度追诉机制下忽略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陷,反映出国家独占司法权开始向社会作出让渡。
(二)社区矫正
除了生态环境案件的修复性司法之外,龙泉还在犯罪案件中适用社区矫正制度。2003年,社区矫正制度开始在浙江省展开试点工作。国家正式力量在社区矫正中发挥组织与指导的作用,而矫正的运作主体则更多来自社会,他们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他们与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亲密接触”——帮谈教育、提供咨询、组织学习和参加公益劳动等。在这一过程中,社区矫正往往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的补救。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行为人在社区矫正期间采取力所能及的恢复植被、山林再建等行动对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补救,以维持环境安全和恢复生态平衡。这里以2013年刘长永盗伐林木罪为例予以说明。①《刘长永盗伐林木罪》,卷宗号:(2013)丽龙初字第00076号,浙江省龙泉市法院藏。
被告人刘永长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上缴国库(缓刑考验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刘永长必须在本判决生效以后十日内到龙泉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报到。依法接受社区矫正,在矫正期间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矫正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学习,完成公益劳动,做一个有益社会的公民。
上述文字是龙泉法院刘长永盗伐林木罪判决书中的一个片段。在刑事判决书中明确要求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告人必须接受社区矫正法律义务,这一做法的依据是2012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第13条。它在判决书主文之后,对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分子明确提出,回到社区以后,必须严格接受社区矫正,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完成植树、护林等公益劳动等义务。同时,还提醒犯罪分子要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它使犯罪人充分意识到接受社区矫正是法定义务,从而也增强了社区矫正的实效和法律效果。
社区矫正意味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力践行。社区矫正以社区志愿者力量为主体,整合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共同完成犯罪人的改造任务。在实践中,人们也越来越理性地看待刑事司法资源的使用,因为监禁刑使国家承担的成本过高,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使得刑罚执行的资源投入不断增长,因而包括缓刑、社区矫正等开始进入基层人民法院的视野。
总之,生态修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的出现表明:基层社会的刑事司法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国家仍然是解决刑事纠纷的主体,但除此之外,民间力量、社会组织也分享一定的刑事案件的解决权。也就是说,重罪案件是国家打击犯罪的“重中之重”,而对于轻罪则可以诉诸“民间和解主义”的方式解决。它是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治理犯罪的开放空间。②李林:《我国风险社会刑法观与风险治理》,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又见卢建平、莫晓宇:《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这不仅有效缓解了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压力,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的有效互动。第二,关注基层社会关系的修复。新时期的基层刑事司法注重社区参与,它有效恢复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社区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这与传统的国家正义刑法观有巨大差异。③John Braithwaite & Heahher Strang,Introduction:Restorative Justice and Civi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4.第三,在行刑方面,国家当然是行刑权的重要主体,但是,民间社会似乎可以分享一部分轻微刑事案件的执行权。这不仅减少了国家执行刑罚的成本,更利于犯罪人复归社会。总之,这种转换完成了在价值理念上由“国家场域的管治与惩罚”向“社会场域中的多元与善治”转变,基层刑事司法越来越显示出“多元化协商治理合作”的趋势。④周建达:《转型期我国犯罪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力维控型”到“压力疏导型”》,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
四、从龙泉刑事司法的历史变迁反思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一)国家治理模式主导了基层刑事司法的变革
晚清以后,基层社会总体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作为后发型的国家,在转型的同时,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于是,现代化转型与基层社会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晚清开启的乡村改革,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建设,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步探索的乡村自治,这些都反映了国家试图将基层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在其中,国家主义作为一条红线或隐或现地主导了上世纪基层社会的变革,也对基层刑事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龙泉地区近现代百年来的司法制度改革,自始至终都应该被纳入到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来考虑,这个角度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基层法律变迁的基本逻辑与规律,理解司法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理解法律变革的前景。
从浙江省龙泉市刑事司法的近现代变迁历程来看,刑事司法中的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呈现出国家力量不断扩张,国家对基层的控制不断强化至完全统合、再到国家有限地退出基层社会从而形成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限主导的变化过程。相应地,基层刑事司法中的民间力量也呈现为膨胀—萎缩—复苏—壮大的发展阶段。究其原因,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总体性危机决定了国家首先需要争取解放与独立,而非抽象的制度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构建了革命教化体制,强调以革命的姿态来应对犯罪,依循运动与压制型治理的逻辑,制度建设并没有成为主流。发展到今天,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的逐步彰显,刑事诉讼中原来由国家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格局发生变化,国家治理越来越基于社会与市场自身发展的逻辑与需要,因此可以说,以社会重建与成长为核心的社会转型推动了刑事司法中国家与社会治理方式的演进。
(二)民国时期司法变革的借鉴价值
考察龙泉司法档案,我们发现,尽管国家政权试图强力进入基层,但民国时期基层的自治性力量并未由此而断裂,刑事司法中的社会力量仍旧较为发达。通过考察龙泉司法档案中相当高比例的刑事和解,我们可以洞见龙泉民间组织力量在刑事司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即在刑事司法场域中,国家“抓大放小”)的互动模式。它在肯定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对保甲、宗族、乡绅、行会等非官方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予以认可。他们填补了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国家的治理成本因此大大降低。就当下而言,民国时期刑事和解有以下借鉴价值:
1.扩张刑事和解的范围,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民国时期刑事和解的范围极为广泛,涵盖除政治犯罪、杀人罪外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当前,应探索轻罪案件以经济惩罚替代和减轻刑事制裁,这有利于受害人获得经济补偿,化解社会矛盾。2.检察机关司法角色的调适。民国时期刑事和解主要集中在检察官起诉阶段,此一阶段和解案件大约占到八成。然而今天龙泉统计表明,以公安机关为主体办理的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案件为主体占52%,审判机关比例占21%,基层群众组织为主体的占26%,检察机关为主体的只占1%。所以,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及时调整角色,转变过去一味强调打击与刑事制裁的定位,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和谐。3.完善委托调解、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在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中,大量的案件往往是由民间来完成,如果将官批民调这一“第三领域”并入其中的话,这个比重大约六成左右。现在的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也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社会的犯罪应对能力,“其中绝对的主流,仍是中立的社区组织来承担”。①张健:《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应当看到,当前刑事司法场域中的民间力量介入有限,国家与民间的互动有限。当前不仅要规范公权力的运作,更要激活民间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刑事诉讼,拓宽民间力量的参与渠道和空间。
(二)国家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与基层刑事司法变革路径展望
当前龙泉的刑事司法转换完成了在价值理念上由“国家场域的管治与惩罚”向“社会场域中的多元与善治”转变,越来越显示出多元化协商治理合作的趋势。但同时必须看到,基层社会发展与市民社会的差距仍旧有相当距离。同时,刑事司法的协商治理模式意味着犯罪治理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协作关系。然而目前国家依旧没有摆脱“自上至下”的单向度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治理中,国家一家独大的格局并未改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自主性力量在挫折中迟迟难以发育。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无从谈起,更遑论协商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与合作。
因此,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变势在必行,必须树立国家权力有限、能力有限和资源有限的理念,实现刑事司法理念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使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通过国家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刑事司法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模式来取代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基层社会中的刑事司法来说,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向社会简政放权,积极回应公民的利益诉求和民主诉求,通过与公民社会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来提高基层刑事司法的治理绩效。在不改变国家主导的情况下,注重多元主体之间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和社会资本的培育。它也代表了中国刑事司法的多元化、民主化趋势。
A Study on Judicial Changes in Longquan County and Its References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Zhang Jian
County i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state’s goverance philosophy and the changes in governance methods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local criminal justice. The paper chooses the Longquan historical judicial chang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criminal justice field during the periods of latent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New period of the PRC,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objective is to investigate thedevelopment rule of the local criminal justice. The historical discussion of the local criminal justice could provide experience for criminal justice and state governance ina modern sense.
Criminal Justice in civil Community;Governance;State and Society;Crime
D924
A
2095-7076(2016)03-0051-13
*江苏大学法学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基层刑事诉讼实证研究(1912—2016)”(项目编号:16CFX011)、中国法学会2015年度法学研究项目“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法律制度实证研究”(项目编号:CLS(2015)Y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