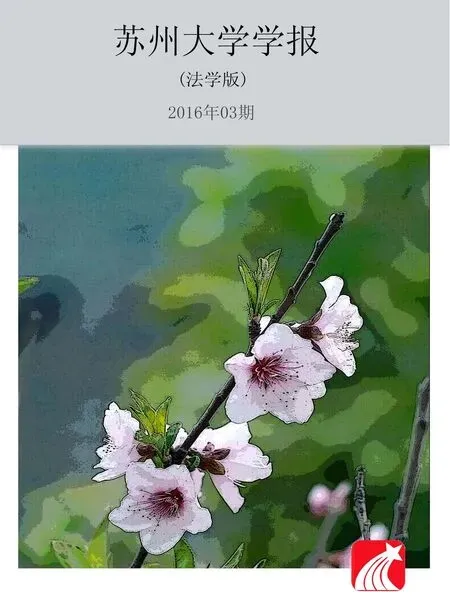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判决—“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判决主文*
申 晨译
● 经典判例
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判决—“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判决主文*
申晨**译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各州是否应当为同性伴侣办理结婚登记,并承认在外州合法缔结的同性婚姻的效力。在历史上婚姻被定义为两个异性的结合,但婚姻制度的发展史是一个兼具变与不变的过程。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四项原则和传统表明宪法对婚姻的基本保护应当适用于同性婚姻:实现个人自治、婚姻结合的重要性、对儿童和家庭的保障、婚姻对社会秩序的基石作用。同性情侣的婚姻权也可以从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中推出。本案的结论无需留待更多的立法、司法和民间讨论的实践积累后得出。一州拒绝承认在另一州缔结的合法同性婚姻没有法律依据。撤销原判,同性婚姻合法性应予承认。
同性婚姻;基本自由;正当程序;平等保护
肯尼迪大法官执笔本院意见。
宪法保障受其管辖的一切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包含了每个人在法律领域定义和表达自己身份的权利。对本案中的上诉人而言,他们实现这种自由的方式,是与其同性伴侣缔结婚姻,并使这种婚姻受到与异性婚姻同等的法律对待。
Ⅰ
本案来自于密歇根、肯塔基、俄亥俄和田纳西州,在这些州,婚姻被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参见Mich. Const.,Art. I,§25;Ky. Const.§233A;Ohio Rev. Code Ann.§3101.01(Lexis 2008);Tenn. Const.,Art. XI,§18]。本案的上诉人是14对同性情侣以及两位同性伴侣离世的男士,本案的被上诉人是执行本案所涉法律的州政府官员。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拒绝赋予其结婚的权利,或拒绝承认其在外州缔结的合法婚姻的效力,这一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上诉人在其各自州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地方法院均支持了上诉人的请求(案件判决参见下述附录A)。被上诉人向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将上述案件合并审理后,推翻了原审判决[DeBoer v. Snyder,772 F. 3d 388(2014)]。上诉法院认为,依据宪法,各州并没有为同性婚姻办理登记或承认外州缔结的同性婚姻的义务。
据此,上诉人要求本院提审。本院在复审案件后,将该案的争议归结为两点[574 U. S. ___ (2015)]。第一,密歇根和肯塔基州案件的争议点在于,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各州是否应当为同性婚姻办理登记;第二,俄亥俄、田纳西和肯塔基州案件的争议点在于,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各州是否应当承认在外州缔结的合法同性婚姻的效力。
Ⅱ
在进入对本案法律原则和先例依据的讨论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本案涉及议题的发展历史。
A
从古至今,婚姻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始终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是何种身份,男女间相伴终生的结合,都是人们获得高尚和尊严的源泉。对于信仰宗教的人而言,婚姻是神圣的;对于在世俗生活中寻求生命意义的人而言,婚姻充实了他们的人生。婚姻使两个人获得永远无法在独处中得到的生活体验,因为婚姻的结合是凌驾于两个个体之上的存在。婚姻源自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其满足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求和希冀。
正是由于婚姻对人类的生存如此重要,婚姻制度也就理所当然地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长期存在。早在远古,婚姻就有使陌生人成为亲属、从而维系家庭和社会的功能。孔子曰:“礼,其政之本也。”①参见2 Li Chi:Book of Rites 266,C. Chai和W. Chai主编,J. Legge译,1967年版。其教诲至今回响。在大陆的另一端,西塞罗写道:“社会的纽带首先在婚姻,其次在亲子,而后在家庭。”②参见De Officiis 57,W. Miller译,1913年版。穿越不同的时代、文化与信仰,从宗教、哲学到艺术、文学,无数的文献和作品讴歌着婚姻的美好。当然有必要指出,这些对婚姻的赞美,是建立在将婚姻理解为异性结合的基础之上。
历史是本案的讨论源头,而被上诉人认为,历史也足以终结本案的讨论。他们认为,将婚姻的定义和法律属性扩展到同性结合的范畴,是对长期存在的婚姻制度的贬损。在被上诉人看来,婚姻的本质就是由一男一女、基于性别差异形成的结合,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点都为全世界真诚和理性的人们所信奉着。
上诉人也承认上述历史,但他们并不认为讨论应当就此完结。如果上诉人的请求旨在贬损和推翻对婚姻的既有认知和制度现状,则本案也许将另当别论,但实际上,这并非上诉人的意图,也与他们的论点不符。相反,上诉人的诉求暗含着对婚姻重要性的高度认可,这甚至是其全部论点的核心。上诉人并非想要破坏婚姻制度,而是想寻求婚姻的庇护,因为他们对婚姻所带来的权利和责任是如此地敬仰和渴求,而他们的天性又决定了,只有婚姻才能使他们真正得到这种灵魂深处的结合。
回顾本案中的三起案情,我们就可以理解上诉人为何如此急切。詹姆斯·奥伯格费尔(JamesObergefell),俄亥俄州案件中的原告,在20年前与约翰·亚瑟(John Arthur)相遇,他们彼此坠入爱河,持久而忠诚地生活在一起。2011年,亚瑟被诊断为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即ALS。这种使人衰弱的疾病是渐进的,且目前无法医治。两年前,奥伯格费尔和亚瑟决定彼此承诺终身,在亚瑟离世前结为夫妇。为了完成这个约定,他们专程从俄亥俄州赶到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的马里兰州。由于亚瑟行动困难,他们是在停靠在巴尔地摩的一架医用运输飞机上完成了期待已久的婚礼。三个月后,亚瑟过世,俄亥俄州法律却不允许将奥伯格费尔列为亚瑟死亡证明上的配偶。由于州法的强制干涉,在死别之后,他们只能以陌生人的关系相称,而奥伯格费尔也将“在余生中饱受折磨”。因此,他提起诉讼,要求在亚瑟的死亡证明中,将自己列为亚瑟的配偶。
艾普罗·德波尔(April DeBoer)和简·劳思(Jayne Rowse)是密歇根州案件中的共同原告,她们在2007年举行了确立彼此为终生伴侣的仪式。她们都是护士,德波尔在妇产科工作,劳思在急救科工作。2009年,德波尔和劳思先后领养了两个男婴,其中后一个男婴是被亲生母亲抛弃的早产儿,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护理。第二年,又有一个身体有特殊缺陷的女婴加入了他们的家庭。然而,密歇根州法律规定,只有异性夫妇和独身者可以领养儿童,因此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只能选择这对情侣中的一人来作为他们的至亲。而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学校和医院也只能将他们作为单亲家庭的子女对待。因此,德波尔和劳思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悲剧,即她们中的一人将无法对孩子享有法律上的亲属权。因此,这对情侣请求消除因无法结婚而给其家庭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
预备役三级军士长伊基·德科(Ijpe DeKoe)和他的伴侣托马斯·考斯特拉(Thomas Kostura)是田纳西州案件中的共同原告。2011年,德科受命前往阿富汗。临行前,他和考斯特拉在纽约举行了婚礼。一周后,德科开始了其长达近一年的海外任务。回国后,德科获得了在田纳西为预备役部队工作的职位,两人也定居在了田纳西。然而在田纳西州,他们的合法婚姻是不被承认的,他们的婚姻效力,取决于他们身处哪个州境内。德科,这位为捍卫宪法赋予的自由而为国奉献的军官,却要为自己的婚姻效力问题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
本案中还涉及其他一些上诉人的经历,他们的故事表明,他们的诉求绝不是要玷污婚姻制度,他们只是想借助婚姻的纽带,过上正常的生活,或是守护与其伴侣的珍贵记忆。
B
婚姻制度的核心内容虽然亘古未变,但其存在绝非独立于法律和社会的发展之外。婚姻制度的发展史是一个兼具变与不变的过程。即使将婚姻定义为异性间的结合,其内涵也是随时代而不断发展的。
例如,曾几何时,婚姻一度是由家长基于政治、宗教和经济因素的考量而一手包办的。但到建国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婚姻是由一男一女自愿缔结的契约。①参见N. Cott,Public Vows:A History of Marriage and the Nation,2000年版,第9-17页;S. Coontz,Marriage,A History,2005年版,第15-16页。随着妇女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婚姻制度也持续发展。在被奉行了几百年的“已婚妇女法”(Coverture)准则下,国家在法律上是将已婚夫妇视为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个体。②参见1 W.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430,1765年版。但此后,妇女逐渐获得了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社会也意识到妇女享有平等的人格尊严,因此“已婚妇女法”遭到了废除。③参见Brief for Historians of Marriage et al. as Amici Curiae,第16-19页。在过去几个世纪,包括以上变革在内的婚姻制度的种种发展,并不仅仅是对婚姻制度的肤浅改造,毋宁说,它们已经深刻改变了婚姻的内在结构,突破了许多在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成见。④参见N. Cott,Public Vows;S. Coontz,Marriage;H. Hartog,Man & Wife in America:A History,2000年版。
新的社会认知的引入,非但没有削弱婚姻制度,反而增强了它的生命力。事实上,对婚姻内涵理解的改变,恰恰反映了在一国之内,对自由新的认知已经在当代社会中深入人心,而这种改变,往往发端于细小的诉求与抗争,并最终被纳入政治议题和司法程序中来讨论。
这一过程在我国同性恋者权利发展的实践中也得到体现。直至20世纪中叶,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同性恋都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甚至被视为刑事犯罪。因此,在公众眼中,同性恋群体是没有尊严的,同性恋者不敢道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即使在二战后,同性恋者的健全人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但其维护尊严的正当主张,仍被视为是有违法律和社会习俗的。在许多州,同性性行为仍被视为犯罪。同性恋者不得被政府雇佣,不得参军,不受移民法保护,他们被警察管控,在社会交往中权利处处受限。①参见Brief for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as Amicus Curiae,第5-28页。
此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同性恋还被视为一种疾病。1952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首次出版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其中同性恋被列为一种心理疾病,并被一直保留到1973年。②参见Position Statement on Homosexuality and Civil Rights,1973,in 131 Am. J. Psychiatry 497,1974年版。直到近年来,包括精神病医师在内的许多人才意识到,性取向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种自然现象,且不能被后天更改。③参见Brief for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t al. as Amici Curiae,第7-17页。
在20世纪末,随着文化和政策层面的实质性改观,同性情侣终于获得了更加开放和宽松的生活环境,并开始组建家庭。这种改变引发了上至政府下至民众的广泛讨论,并使公众对同性恋者的态度逐渐趋向宽容。由此,不久以后,关于同性恋者权利的案件被诉至法院,并被作为正式的法律问题予以讨论。
在“鲍尔斯诉哈威克”案[Bowers v. Hardwick,478 U. S. 186(1986)],本院首次对同性恋者的法律待遇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该案中,本院判决佐治亚州将同性性行为视为犯罪的法律并不违宪。10年后,在“罗莫诉埃文斯”案[Romer v. Evans,517 U. S. 620(1996)],本院宣告了科罗拉多州一项宪法修正案无效,该修正案旨在阻止州内的一切职能机构,将同性恋者作为不被歧视的受保护群体对待。在其后的2003年,本院又推翻了鲍尔斯案的判决结果,并认为,以法律形式将同性性行为定性为犯罪,“这诋毁了同性恋者的人格。”[Lawrence v. Texas,539 U. S. 558,575.]
在这一背景下,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关注。1993年,夏威夷最高法院认为,夏威夷州法律将婚姻限定为异性结合,这是一种对公民基于性别差异的区别对待,因此应当受到夏威夷州宪法的严格监督[Baehr v. Lewin,74 Haw. 530,852 P. 2d 44]。尽管这一判决并未明确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其引发了其他一些州的警惕,这些州纷纷重申本州法律内的婚姻仍仅限于异性结合。由此在1996年,国会通过了《保卫婚姻法案》(DOMA,110 Stat. 2419),申明在一切联邦法律中,婚姻仅指“一男一女以夫妻形式在法律上形成的结合。”(1 U. S. C.§7.)
这一广受争议的议题在另一些州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2003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判定州宪法保障同性情侣结婚的权利[参见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440 Mass. 309,798 N. E. 2d 941 (2003)]。此后,又有一些州通过司法裁决或立法,保障了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具体参见附录B)。两年前,在“联邦政府诉温莎”案[United States v. Windsor,570 U. S. ___(2013)],本院废除了DOMA法案的部分内容,以明确对于已经在各州合法登记缔结的同性婚姻,联邦政府不应认定其为无效。并且本院认为,DOMA法案对于那些“想要在孩子、家人、朋友和邻居面前,展现其对伴侣的忠实承诺”的同性情侣,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伤害(前引,判决意见单行本,第14页)。
近年来,联邦上诉法院受理了大量关于同性婚姻的案件。法官们本着恪尽职守、严格中立的司法态度,严肃而公正地作出了他们的评论,并撰写了大量判决意见,综合考虑了有关本议题的方方面面。这些案例对于本案法律依据的形成和解释,颇有助益。除了本案和Citizens for Equal Protection v. Bruning案[455 F. 3d 859,864-868(CA8 2006)],在其他案件中,联邦上诉法院都认为禁止同性情侣结婚是违宪的。一些地方法院也为同性婚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观点,其中大部分也认为同性恋者有权缔结婚姻。此外,不少州最高法院通过对本州宪法的解释,推动了本议题的讨论(以上这些各州和联邦司法机关的观点,可参见后述附录A)。
在经过多年的诉讼、立法、投票和辩论后,我们可以说,在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上,美国社会发生了分裂。①参见Office of the Atty. Gen. of Maryland,The State of Marriage Equality in America,State-by-State Supp.,2015年版。
Ⅲ
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未经正当程序,”各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该条款所保护的基本权利涵盖了权利法案中列举的绝大多数权利[参见Duncan v. Louisiana,391 U. S. 145,147-149(1968)]。并且,这些自由包括了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信仰所做的私密选择,是个人实现其尊严和自治的关键所在[参见Eisenstadt v. Baird,405 U. S. 438,453(1972);Griswold v. Connecticut,381 U. S. 479,484-486(1965)]。
对基本权利的认定和保护,是司法机关对宪法进行解释时所要承担的艰巨责任之一。这种责任,“不屈从于任何准则。”[Poe v. Ullman,367 U. S. 497,542(1961),哈兰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并且,法院还应对潜在的基本权利予以理性地认定,以使国家对这些权利给予必要的尊重(同上)。在这一过程中,法官遵循的思路应当与其对其他宪法条款的分析路径一致,即从大的原则上入手,而非拘泥于小节。历史和传统仅仅作为引导和约束涉案议题的参考,而不是绝对依据(参见上述“Lawrence案”,第572页)。这种路径尊重和借鉴历史,但并不单纯以过去的结论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不公正的一个特质,在于其虽然时时存在,但我们却常不自知。起草和通过《权利法案》以及第十四修正案的人们,未曾预想到自由发展的所有维度,所以他们赋予后来人一项特权,以使我们能够基于对自由的新理解,来保障所有人的正当权利。当新的社会认知揭示了某项既有的法律限制与宪法的核心精神相冲突时,我们应当保护的是自由。
有鉴于此,本院一贯主张,婚姻权受宪法的保护。在“拉文诉弗吉尼亚州”[Loving v. Virginia,388 U. S. 1,12(1967)]案中,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令被判决无效,并且法官们无异议地指出,婚姻权是“一个以合法手段追求幸福的自由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个人权利之一。”在“扎布洛茨基诉雷海尔”[Zablocki v. Redhail,434 U. S. 374,384(1978)]案中,本院重申了关于婚姻权的上述观点,判定法律不得以拖欠抚养费为由,限制一个人结婚的权利。在“特纳诉萨福利”[Turner v. Safley,482 U. S. 78,95(1987)]案中,本院以同样的依据,判定正在服刑的囚犯,其结婚的权利不受监狱管理规范的限制。在其他案件中,本院也三令五申,强调了婚姻权是受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基本权利[参见M. L. B. v. S. L. J.,519 U. S. 102,116(1996);Cleveland Bd. of Ed. v. LaFleur,414 U. S. 632,639-640(1974);上述“Griswold案”,第486页;Skinner v. Oklahoma ex rel. Williamson,316 U. S. 535,541(1942);Meyer v. Nebraska,262 U. S. 390,399(1923)]。
当然,上述案件都是在异性婚姻的语境下讨论婚姻权。本院也与其他组织机构一样,受到特定时空下既有认知的局限。例如在1972年的“贝克诉尼尔森”[Baker v. Nelson,409 U. S. 810]案中,这种局限性表现得至为明显,本院对该案只给出了一句话的判决结论,即认为:是否将同性婚姻排除在婚姻定义之外,不构成一个联邦层面的法律问题。
当然,对本案具有参考意义的判例不止于此。本院的一些判决的立场表明,宪法原则的保障范围是可以被扩张的。在以下案件中,法官从历史因素、传统因素,以及宪法所保障的人们对亲密关系所享有的自由等角度,定义了婚姻权的属性(参见上述“Lawrence案”,539 U. S.,第574页;上述“Turner案”,第95页;上述“Zablocki案”,第384页;上述“Loving案”,第12页;上述“Griswold案”,第486页)。而法院在评估这些判例的理由和效力是否适用于同性婚姻时,也应当尊重婚姻权长期受到保护的基本理由(参见上述“Eisenstadt案”,第453-454页;上述“Poe案”,第542-553页,哈兰大法官德反对意见。)
上述分析指向的结论是,同性恋者应当享有婚姻权。以下四项原则和传统,表明宪法对婚姻的基本保护,应当适用于同性婚姻。
第一项理由是,个人对婚姻的选择权,是实现个人自治的本质要求。婚姻与自由之间存在永恒的联系,这一点,正是“Loving案”中本院根据正当程序条款判决反异族通婚法无效的原因(参见388 U. S.,第12页;另参见上述“Zablocki案”,第384页,其重申了“Loving案”中“婚姻权是所有人最为重要的基本权利”的观点)。宪法保障人们关于避孕、处理家庭关系、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自由选择,而关于婚姻的选择与上述选择一样,都属于个人最为私密的决定之一(参见上述“Lawrence”案,第574页)。事实上,本院已经注意到,“如果我们保障了与家庭生活相关的各种私人权利,却不保障作为上述权利基础的、即组成家庭关系的权利”,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上述“Zablocki案”,第386页)。
对婚姻的选择关乎一个人的命运。正如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所指出的,因为“婚姻饱含了我们对安定的渴望,它是我们的庇护所,是人类天性的表达,婚姻如此神圣,关乎婚姻的选择,是我们人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Goodridge,440 Mass.,第322页,798 N. E. 2d,第955页]。
婚姻的本质,是在长久的结合中,夫妻二人共同实现自身的自由,例如表达的自由,性的自由,以及精神的自由。婚姻的这种本质,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无关性取向(参见Windsor,570 U. S.,判决意见单卷本,第22-23页)。两个性别相同的人相互结合,自主地作出结婚这一重大决择,这是人格尊严的体现:是否选择与另一种族的人结婚是一个人的自由,国家不得干涉(参见上述“Loving案”,第12页。)
第二项理由是,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因为结婚所带来的两人的结合关系,其重要性是其他任何个人关系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也是“格列斯伍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的核心判决理由,该案认为,宪法保障已婚夫妇采取避孕措施的权利(381 U. S.,at 485),并认为婚姻权是一项“比《权利法案》还要古老的”权利。“Griswold案”是这样描述婚姻的:
“婚姻是这样一种结合,无论日子过得是好是坏,夫妻二人总愿亲密无间,长相厮守,直至永恒。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社会事务;它关乎人生幸福,无涉政治信仰;它只在意彼此的忠诚,并不索取名利。婚姻,以及我们选择婚姻的决定,都是出于高贵的目的”(前引,第486页)。
在特纳案中,本院再一次确认了这种亲密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判决囚犯不得被剥夺结婚的权利,因为对囚犯而言,他们的婚姻关系同样属于婚姻这一基本权利的保护范畴(参见482 U. S.,第95-96页)。婚姻权使得那些“愿意对彼此承诺终身”的情侣们显得更为神圣(前引Windsor,判决意见单卷本,第14页)。由于婚姻的存在,我们不必害怕孤身一人,起身呼喊却得不到回应。它让人们因彼此的陪伴而获得希望,并使我们确信,只要夫妻二人都还健在,自己就永远不会被世界抛弃。
如劳伦斯案的结论,同性情侣与异性情侣在性行为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劳伦斯案废除了将同性性行为视为犯罪的法令,并指出“当我们钟情于与特定对象的性爱,那么性本身只是维持这一长期个人关系的因素之一。”(539 U. S.,第567页)。尽管劳伦斯案确认了同性性行为不受刑事法律追究,但同性恋者的自由不应仅限于此。确认合法是一项进步,但其并不保证完全的自由。
保护婚姻权的第三项理由是,婚姻是儿童和家庭的屏障,其对于与儿童相关的生育、抚养和教育权利意义重大[参见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268 U. S. 510(1925);“Meyer案”,262 U. S.,第399页]。本院认为,上述这些权利应当是一体的:“结婚、建立家庭和抚养子女的权利是自由的一项内容,受到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Zablocki案”,434 U. S.,第384页,引自上述“Meyer案”,第399页)。而在一些州法中,婚姻对儿童和家庭的保护也是实质性的。并且,婚姻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其对父母关系的确认和法律架构,使孩子们能够“认识到他们的家庭是完整和亲密的,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幸福和谐的”(前引Windsor,判决意见单卷本,第23页)。婚姻同时也为子女利益的维护提供长久稳定的保障。①参见Brief for Scholar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Children as Amici Curiae,第22-27页。
毋庸置疑,许多同性情侣正在尽职尽责地抚养他们的子女,尽管其中一些人与他们的孩子并无血缘关系。如今,成千上万的儿童生活在同性情侣的家庭中。②参见Brief for Gary J. Gates as Amicus Curiae,第4页。大多数州都允许同性恋者收养子女,其中很多是以同性父母的方式进行收养(同前引,第5页)。这可以视为法律本身对同性恋者可以建立充满慈爱和保障的家庭的有力承认。
将同性恋者排除在婚姻之外,与婚姻权的核心前提是相违背的。没有婚姻提供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孩子们将会因为知道自己的家庭是不完整的,而感到耻辱。并且,由未婚父母抚养的孩子,也将承受许多实质的利益损失。考虑到孩子们虽然没有过错,却要承担更加艰辛和不确定的家庭生活,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的婚姻法的确对同性伴侣的子女造成了侮辱和伤害(参见前引Windsor,判决意见单卷本,第23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婚姻权对没有孩子的同性情侣就不重要。在任何州,生殖的能力、意愿或承诺都不是婚姻的必要条件。过往的判例表明,法律保护夫妻不生育的权利,因此法院和政府也从来不以生育能力和承诺来定义婚姻权。宪法保障婚姻权的多个方面,生育和抚养子女只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项理由是,本院的既有判决和本国的传统表明,婚姻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石。托克维尔在两百年前周游美国时就曾写道: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重视婚姻这一纽带……当一个美国人从公共生活的繁杂中脱身,回到家庭的怀抱中,他总能找到秩序和平静……然后,他又会将这种秩序和平静,带回到他的公共事务中。”③参见1 Democ-racy in America 309,H. Reeve译,1990年再版。
在Maynard v. Hill[125 U. S. 190,211(1888)]案中,法院援引了托克维尔的思想,解释道:“婚姻是家庭和社会的基础,没有婚姻,就没有文明和进步。”“婚姻长期以来都是一项伟大的公共制度,它赋予了我们市民生活的各种特征”(同前引,第213页)。这一观点已经被反复强调,即使婚姻制度在长期发展中已经发生了实质改变,家长同意、性别不平等、种族相同等已不再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基本前提(参见N. Cott,Public Vows)。婚姻仍然是构建我们社会的基本单元的重要因素。
因此,正如夫妻双方要宣誓彼此扶持那样,社会也应当保证支持这些夫妻,给予他们形式上的认可和实质上的帮助,以呵护和培养这种结合。事实上,随着各州对已婚人士的权益进行各种安排,婚姻已经成为许多法定权利、利益和责任的形成基础。配偶地位在以下规则中具有重要影响:税法;继承和财产权;法定继承规则;证据法上的配偶特权;医疗探视权;医疗决策权;收养权;遗属权益;出生和死亡的证明;职业伦理规则;竞选资金限制;工人补偿福利金;医疗保险;以及儿童监护、抚养和探望规则等。④参见Brief for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第6-9页;Brief for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s Amicus Curiae,第8-29页。超过一千条的联邦法律也是以有效的婚姻状态作为规范形成的依据(参见Windsor,570 U. S.,判决意见单卷本,第15-16页)。国家将婚姻制度放在了众多法律和社会秩序构建的核心地位,这进一步促成了婚姻权基本特征的形成。
在上述层面上,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并无不同。然而,同性夫妻却被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这使他们无法沐浴婚姻的光辉,不能享有国家赋予婚姻的种种利益。由此对他们造成的精神伤害,更甚于他们的实质负担:同性伴侣被迫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结合关系中,这种状态是很多异性伴侣所不能忍受的;而由于国家赋予了婚姻极为神圣的意义,使其无比珍贵,因此将同性恋者排除在婚姻之外,似乎是在表达同性恋者是低人一等的,他们的尊严是不受重视的。国家将同性恋者排斥在了一项社会核心制度之外,贬损着他们的人格。而且不要忘了,同性夫妇同样热切向往着婚姻的卓越荣光,渴望践行婚姻最高尚的意义。
将婚姻限定在异性范围,可能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自然和正当的,但这一规则在实现婚姻权这一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已经昭然若揭。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将同性恋者排除在婚姻之外,将会使他们承受侮辱和伤害,而这恰恰是为我们的基本宪章所禁止的。
被上诉人辩称,本案的正确解决思路并不在于此。被上诉人援引了以对基本权利的“谨慎描述”著称的Washington v. Glucksberg案[521 U. S. 702,721(1997)],他们认为,上诉人所要求行使的并非婚姻权这种基本权利,而是一种新型的、并不存在的“同性婚姻权”(Brief for Respondent in No. 14-556,第8页)。格拉斯伯格案的确坚持认为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应当是以特定的历史实践为依托,且以最为谨慎的方式来定义。但这种路径也许适合于该案涉及的权利(医生协助自杀的问题),却与本案中讨论的与婚姻和性相关的基本权利并不相干。拉文案不是主张“跨种族婚姻权”;特纳案不是主张“囚犯婚姻权”;扎布洛茨基案不是主张“未付清抚养费的父亲的婚姻权”。相反,这些案件涉及的都是一种综合意义上的婚姻权,探讨的是我们是否有正当的理由,来排除部分人群的结婚的权利(参见“Glucksberg案”,521 U. S.,第752-773页,绍特大法官的并存意见;同前引,第789-792页,布雷耶大法官的并存意见)。
上述原理在本案中同样适用。一项权利不是按某个主张权利者的具体情况来定义的,否则既有的实践就只能作为这一个人享有权利的正当理由,并且一旦权利被否认,其他人也将无法主张这种权利。本院在关于婚姻权以及同性恋者权利的案件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上述“Loving案”,388 U. S.,第12页;“Lawrence案”,539 U. S.,第566-567页)。
从历史和传统上看,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但权利不仅仅来源于历史,根据时代特征,对于那些宪法所必须保护的紧迫的自由,随着人们对其定义理解的加深,权利也得到了发展。很多人抵制同性婚姻,是基于那些被他们视为圭臬的宗教和哲学理由,我们尊重他们以及他们的信仰。但当这种真诚的个人信仰转变为法律和公共政策时,就会使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受到侵犯,人格遭遇贬损。同性夫妇依据宪法,要求法律对其婚姻予以承认,如果否认这项权利,那就意味着他们的选择是不被人尊重的,他们的人格是不受重视的。
同性情侣的婚姻权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自由的范畴,并且也可以从该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中推出。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虽然各自构成独立的法律原则,但其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正当程序原则中所蕴含的权利和平等保护原则所保障的权利,虽然基于不同的法理,也并非总是共存,但在特定情形下,它们之间能够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特定案件中,单一条款更适于准确和全面地捕捉一项权利的本质,而两项条款的合力更有利于对权利进行定位和定性[参见M. L. B.,519 U. S.,第120-121页;前引,第128-129页,肯尼迪大法官的并同意见;Bearden v. Georgia,461 U. S. 660,665(1983)]。对上述两项原则的共同阐释,将更有利于我们理解这里所涉及的自由的本质。
本院涉及婚姻权的其他几项判决,就反映了上述机制。在拉文案中,本院判决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令无效,是基于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的共同运用。首先,基于法律对跨种族夫妇的平等保护,该法令应属无效。判决书写道:“毫无疑问,仅仅基于种族不同而限制结婚自由,这显然违背了平等保护条款的基本内容”(388 U. S.,第12页)。由此,判决书进一步指出这项法令对正当保护原则的侵犯:“根据种族区分这项毫无根据的理由否认一项基本自由,如此直接地破坏作为第十四修正案核心内容的平等原则,这无疑是在未经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对公民自由的剥夺”(同前引)。对禁止跨种族婚姻给人们带来的伤害的理解的加深,也使得将婚姻权视为一项基本权利的理由更加清晰和充分。
在扎布洛茨基案中,两项条款的合力作用进一步展现。如前文所述,该案中的涉诉法律规定未付清抚养费的父亲未经批准不得结婚,而本院援引了平等保护条款,作为判决该法律无效的依据。在判决中,法官指出该法律涉及一项“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权利,这构成了平等保护原则适用的依据(434 U. S.,第383页)。扎布洛茨基案的判决书以大量篇幅讨论了婚姻权的本质,而正是婚姻权的存在,使得涉诉法律明显违背了平等保护原则。在该案中,平等保护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给予了彼此有力的支持。
事实上,在对平等保护条款的解读中,法官已经认识到,新的社会认知能够揭示那些在我们社会的基础制度中、长期被我们所忽视的不公。不久以前,在70、80年代的婚姻法领域,这一现象就曾发生。直至20世纪中叶,尽管“已婚妇女法”逐渐没落,婚姻中的性别歧视仍广泛存在。①参见App. to Brief for Appellant in Reed v. Reed,O. T. 1971,No. 70-4,第69-88页。该案可视为关于1971年法律是如何不公平地对待婚姻中的女方的一项有例证。这种性别歧视,拒绝承认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尊严。例如,在1971年,某州法仍规定:“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服从于丈夫;妻子的法律权利包含于丈夫的权利之中,除非法律承认其独立地位,否则其利益不受法律的独立保护”[Ga. Code Ann.§53-501(1935)]。而根据新的社会认知,本院援引平等保护原则,废除了婚姻法中涉及性别歧视的法律[参见Kirchberg v. Feenstra,450 U. S. 455(1981);Wengler v. Druggists Mut. Ins. Co.,446 U. S. 142(1980);Califano v. Westcott,443 U. S. 76(1979);Orr v. Orr,440 U. S. 268(1979);Califano v. Goldfarb,430 U. S. 199(1977),多数意见;Weinberger v. Wiesenfeld,420 U. S. 636(1975);Frontiero v. Richardson,411 U. S. 677(1973)]。与拉文案和扎布洛茨基案一样,这些判例表明平等保护条款能够发掘和纠正婚姻制度中的不公,维护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和平等价值。
还有一些案件也反映了上述两个原则间的联系。在M.L.B.v.S.L.J.中,法官援引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原则,判决一项要求贫困母亲付费以终止其亲权的法令无效(参见519 U. S.,第119-124页)。在Eisenstadt v. Baird中,法官援引上述两项原则,判决一项仅针对未婚人士的禁止派发避孕用品的法令无效(参见405 U. S.,第446-454页)。在Skinner v. Oklahoma ex rel. Williamson案中,法官根据这两项原则,判决一项允许对惯犯进行绝育的法令无效(参见316 U. S.,第538-543页)。
在劳伦斯案中,法官承认了这两项宪法原则在同性恋者法律待遇问题上的内在联系(参见539 U. S.,第575页)。虽然该案是以正当程序条款来组织判决理由,但法官也承认了州法将同性性行为视为犯罪,是对平等保护原则的违反,并试图对其进行纠正(同前引)。因此,劳伦斯案同样是援引了上述两项条款来定义和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并指出各州“无权通过将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定性为犯罪,来蔑视他们的存在,或控制他们的命运”(同上引,第578页)。
这一机制对同性婚姻问题同样适用。很明显,本案中的涉案法律限制了同性情侣的某种自由,并且必须承认,其也违反了平等保护的准则。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实施的婚姻法规具有实质上的不平等:同性夫妇被排除在异性夫妇享有的利益之外,且被禁止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由此,考虑到社会对同性恋者结合的长期排斥,这种对其婚姻权的否认,无疑会对同性恋者造成严重而持续的伤害。这种对同性恋者权利的剥夺,是对他们极大的不敬和侮辱。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一样,不应允许这样地对婚姻基本权利的损害(参见上述“Zablocki案”,第383-388页:“Skinner案”,316 U. S.,第541页)。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婚姻权是一项反映自由本质的基本权利,并且,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同性情侣不得被剥夺该项权利和自由。本院判决,同性情侣得行使其结婚的权利,该项自由不得被干涉。“贝克诉尼尔森”案的判决结果应予废除,本案涉诉的各州法律中,涉及拒绝将异性婚姻法律条款适用于同性婚姻的,应属无效。
Ⅳ
在本案的讨论中,自始就存在一种观点,即认为本案的结论应当慎重推进——留待更多的立法、司法和民间讨论的实践积累后得出。被上诉人诉称,对于如何定义婚姻这样一个基本社会问题,目前的民主讨论是不够充分的。在本案提交于本院前,上诉法院的多数意见也颇有说服力地指出,各州政府宜等待更多的公众讨论和政治举措后,确定是否承认同性婚姻(参见DeBoer,772 F. 3d,第409页)。
然而,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审慎程度,其实早已超出了上述观点的要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公民投票、立法争论、民众运动,有无数的研究、论文、专著和作品,有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大量的诉讼案件(参见后述附录A)。在相关诉讼中,争议双方围绕同性婚姻问题发表了充分的法律意见,这又促进了整个社会对于同性婚姻的讨论,并在过去几十年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超过100位“法律之友”——其中许多来自于政府、军队、企业、工会、宗教组织、执法机构、民间组织、专业组织和大学等美国社会生活的关键部门——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书面的实质性意见。这些均使得对同性婚姻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得这一问题足以被提升为一个宪法问题来解决。
当然,从宪法角度考虑,只要不存在对基本权利的侵犯,以民主程序对法律做出改变仍是更为恰当的途径。不久以前,在Schuette v. BAMN[572 U. S. ___(2014)]案中,本院的多数意见还刚刚重申了民主原则的重要性,指出“保障公民的言论权,这样他们才能学习和讨论,进而通过民主程序,共同缔造时代的发展轨迹”(同前引,判决意见单卷本,第15-16页)。事实上,往往正是通过民主,自由才得以被保存和维护。但正如舒特案判决书所言,“宪法所保护的自由,其至为重要的一点即在于,个人的权利不受政府权力的非法侵害。”(同前引,判决意见单卷本,第15页)。因此,当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虽然民主决策是主流价值,“宪法仍要求法院在必要时站出来纠偏。”(同前引,判决意见单卷本,第17页)。这一点在保障个人权利时是绝对适用的,即使涉及到最为重要和敏感的议题也是如此。
根据我们的宪法机制,个人主张基本权利时,无需等待立法措施的跟进。对于受到侵害的人们,法院随时为其敞开大门,以帮助他们维护那份由我们的基本宪章赋予的权利。甚至即使不受公众的认可和立法的确认,个人在受到侵害时,仍得主张其宪法权利受到保护。正如有观点指出:“宪法将特定的议题从变幻莫测的政治讨论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多数人和官方的控制之外,并以形成法律原则的方式,将其交由法院来掌控”[West Virginia Bd. of Ed. v. Barnette,319 U. S. 624,638(1943)]。这也是为什么“基本权利不由投票来决定,不取决于选举的结果”(同上引)。因此,即使在民主程序上有所缺失,也不妨碍我们对同性婚姻的承认。本院所面临的,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即宪法是否应当保护同性恋者结婚的权利。
这不是本院第一次在试图确认和保护一项基本权利时,被要求谨言慎思了。在鲍尔斯案中,微弱的多数意见支持了一项将同性性行为定性为犯罪的法令(参见478 U. S.,第186页,第190-195页)。这一判决,可以视为是法官谨慎克己、尊重民主程序的例证,而彼时,同性恋者权利的问题也才刚刚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鲍尔斯案的实际效果,却是导致各州纷纷采取行动否认同性恋者的基本权利,进而对同性恋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该案的异议意见表明,在判决作出时,鲍尔斯案合议庭对于作出正确判决所需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清楚的(参见前引,第199页,布拉克姆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布伦纳、马歇尔和史蒂文斯大法官附议;前引,第214页,史蒂文斯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布伦纳南德、马歇尔大法官附议)。因此,劳伦斯案判决书指出,鲍尔斯案判决“在当时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539 U. S.,第578页)。尽管鲍尔斯案最终被劳伦斯案推翻,但在此过程中仍有许多人受到伤害,并且这种伤痛在鲍尔斯案被推翻后,仍将长期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毕竟,尊严受到的伤害,并不能被轻易地一笔勾销。
对同性婚姻的不利判决,将带来同样的效果——并且,如鲍尔斯案一样,是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违反。上诉人的事迹表明,他们的诉愿是如此急切。詹姆斯·奥伯格费尔害怕俄亥俄州政府会永远地勾销其与约翰·亚瑟间婚姻的存在;艾普罗·德波尔和简·劳思忧心密歇根州政府会继续剥夺她们以母亲的身份保护子女、让他们健康成长的权利,因为对她们和孩子来说,童年时光是如此的短暂;伊基·德科和托马斯·考斯特拉想知道,田纳西州政府是否会承认他们在纽约州缔结的婚姻,以维护一个为国终生奉献者的基本尊严。这些案情使本院深感有责任正视他们的诉求,回应他们的关切。
诚然,面对上诉法院意见的极大分歧——这种分歧足以导致对联邦法律解读的不可调和的分裂——本院对同性恋者是否可以行使结婚权利的考虑慎之又慎。如果本院认定涉诉的法律合宪,那么就是在告诉世人,这些法律与我们社会的基本准则相符。如果本院缓步前行,采用个案推进的方式,逐步实现同性夫妇的各项公共福利,那么同性恋者仍将被排除在许多与婚姻相关的权利和责任之外。
被上诉人还主张,允许同性婚姻将对婚姻制度造成损害,因为这将导致异性婚姻的减少。被上诉人声称,这种担忧是切实存在的,因为允许同性结婚,意味着婚姻制度与生殖繁衍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错觉之上,即认为异性婚姻的缔结都是基于繁衍后代的考虑。是否结婚以及是否抚养子女,是一项综合了诸多个人因素、爱情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决定;并且,我们也不太可能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同性恋者可以结婚,异性恋者就会选择不结婚[参见Kitchen v. Herbert案,755 F. 3d 1193,1223(CA10 2014),“认为国家承认同性恋爱和同性性行为,就会使大量异性恋者转变其性取向,这完全是没有逻辑的”]。被上诉人没有给出同性婚姻会造成其所描述的危害结果的依据。事实上,与其以这种理由排斥同性婚姻,我们不如从本案的案情来考虑:这些案件仅仅涉及两个成年人的自愿选择,他们的婚姻对自身和任何第三人都没有害处。
最后必须强调,宗教和信奉宗教的人们,可以继续主张他们所尊奉的高尚神圣的教义,控诉同性婚姻不得被宽恕。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组织和教民的合法权利,以使他们能够传授那些对其生命和信仰极其重要的信条,满足他们以宗教维系家庭持久稳定的愿望。这一点,对那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同样适用。同理,那些认为同性婚姻合理正当的人,无论是基于宗教信条还是世俗信仰,也可以与反对他们观点的人进行开放的、探讨性的辩论。但是就宪法而言,其不会允许政府将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在法律上进行区别对待。
Ⅴ
本案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宪法是否要求各州承认在外州缔结的同性婚姻的效力。根据奥伯格费尔与亚瑟,以及德科与考斯特拉的情形来看,如果拒绝承认这种效力,也会给同性情侣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在某个州缔结的婚姻,却在另一个州被拒绝承认,这无疑是在家庭法领域内“最令人困惑和烦恼的问题”[Williams v. North Carolina,317 U. S. 287,299(1942)]。当前各州的规定,无疑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例如,如果一对夫妇跨过州界去邻省探望亲友,在此期间发生意外住院,他们就可能在行使相关配偶权利时面临很大的麻烦。考虑到已经有很多州允许同性婚姻——且已经有大量的同性婚姻缔结——对同性婚姻效力的拒绝承认,将会造成持续而严重的问题。
正如被上诉方律师所承认的那样,如果宪法强制要求各州为同性婚姻办理登记,那么拒绝承认外州缔结的同性婚姻的正当性也就不存在了(参见Tr. of Oral Arg. on Question 2,第44页)。本院认为,同性夫妇在任何州都可以行使其婚姻权。因此,本院也当然并确实地认为,一州拒绝承认在另一州缔结的合法同性婚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
任何人与人的结合都无法与婚姻相提并论,因为婚姻蕴含了人类至为高尚的信念:爱、忠诚、奉献、牺牲以及家庭。婚姻的缔结,意味着个体合二为一,成为超越自我的存在。本案上诉人的事迹表明,婚姻所包含的爱情甚至可以超越死亡。认为同性恋者不尊重婚姻,这是对他们的误解。他们是如此地尊崇和渴望婚姻,希冀沐浴于婚姻之光。他们不想被世人指责,孤独终老,受斥于文明社会最悠久的制度之外。他们寻求法律眼中的平等和尊严,而宪法,赋予他们这一权利。
撤销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
特此判决。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Obergefell v. Hodges Opinion of the Court
Shen Chen(Translator)
The focus of this case is wheth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requires a State to license a marriage between tw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or to recognize a marriage between tw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when their marriage was lawfully licensed and performed out-of-State. In history,marriage is defined as a union between two persons of the opposite sex,but the history of marriage is one of both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s Due Process Clause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liberties. Four principles and traditions demonstrate that same-sex couples have the equal fundamental right of marriage:the individual autonomy,the importance of marriage to the committed individuals,the safeguar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the effect of marriage to the Nation’s social order. The right of same-sex couples to marry is also derived from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s guarantee of equal protection. The conclusion do not need to wait for further legislation,litigation,and debate. There is no lawful basis for a State to refuse to recognize a lawful same-sex marriage performed in another State.
Same-sex Marriage;Fundamental Liberty;Due Process;Equal Protection
D923.9
A
2095-7076(2016)03-0148-12
*本案案名简写为Obergefell v. Hodges,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5年6月26作出终审判决。本案以5∶4的票数比例判决上诉人胜诉。肯尼迪(Kennedy)大法官执笔判决主文,金斯伯格(Ginsburg)、布雷耶(Breyer)、索托马约尔(Sotomayor)、卡根(Kagan)大法官附议。四位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均发表了异议意见。其中,罗伯茨(Roberts)大法官认为司法应克制其对立法的干预;斯卡利亚(Scalia)大法官认为本判决将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托马斯(Thomas)大法官认为判决主文对自由含义的理解有误;阿利托(Alito)大法官认为婚姻制度是州法事务。应当认为,四位大法官的异议意见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限于刊载篇幅,此处笔者仅提供了判决主文的译文。考虑到中文的表述习惯,译文将原判决书正文中引用的著作性文献改为脚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家庭法。
(责任编辑:黄文煌)
——基于对国内某大型形式婚姻网站征婚广告的内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