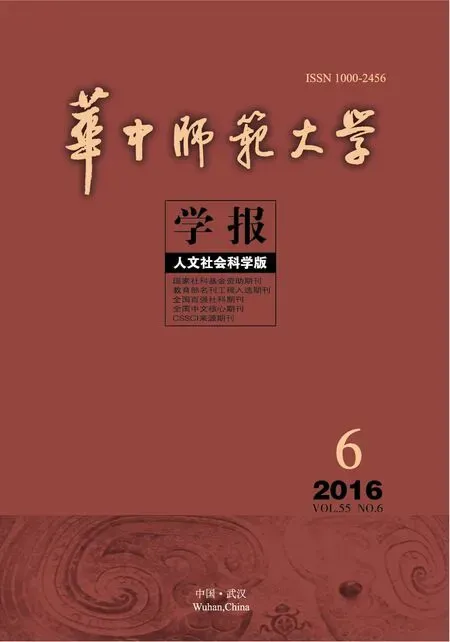陈荣捷与《道德经》英译
刘玲娣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陈荣捷与《道德经》英译
刘玲娣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道德经》英译历史悠久,作品丰富。作为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坚人物,陈荣捷对《道德经》的英译密切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华裔学者逐步加入到英译《道德经》的队伍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主导《道德经》英译的局面。陈荣捷不仅对它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介,还亲自将《道德经》和王弼《老子注》翻译成英语,为海外高校和学术界提供了可靠的经典读本。陈荣捷的译介工作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西方《道德经》英译中的神秘化和宗教化倾向,凸显了《道德经》的哲学意蕴。
陈荣捷; 《道德经》; 王弼; 《老子注》英译
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研究在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已故美籍华裔哲学家陈荣捷(1901-1994)的学术贡献,高度评价他对中国哲学世界化所做的卓越贡献①。作为北美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者和世界范围内新儒学和朱子学研究的权威②,陈荣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比如他在夏威夷大学筹划组建了北美首个中国哲学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凡事亲力亲为;持续多年组织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出版有影响的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多渠道促进东西方哲学的交流;长期在美国的一些大学讲授较为冷僻的中国哲学课程;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哲学的论著、书评;翻译了一批中国哲学经典文献等等。在陈荣捷的学术贡献中,汉籍经典的英译是一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基础性工作,因为正是这些高质量的译本为西方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研究者以及普通读者提供了可靠的阅读文本,为他们开启中国哲学的神秘大门提供了钥匙。同时,陈荣捷还通过对同类翻译作品毫不留情的批判性审视和深入评介,促进了中国典籍英译质量的逐步提高。这些贡献,都可以与他的朱子学研究交相辉映。已有的相关研究多是从整体上粗略介绍陈荣捷的学术成就,或者是从英语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其具体的翻译技巧。尽管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对于我们深入认识陈荣捷作为一个海外中国哲学家的学术贡献仍然是不够的。本文尝试将陈荣捷置于北美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背景之中,一方面总结他对《道德经》英译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探讨他本人如何通过评价《道德经》英译作品和亲自翻译《道德经》来达到他的学术目标。
一、重译《道德经》,为美国的哲学研究提供可靠的中国哲学读本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最早西传的文本之一,自1788年第一个拉丁译本诞生以来,二百多年来,新的西文译本层出不穷,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语言③。米切尔·拉法各(Michael LaFargue)和朱丽安·帕斯(Julian Pas)在《论〈道德经〉翻译》一文中,以“一瓶精致而神秘的陈年葡萄酒”来比喻《道德经》对西方人的巨大吸引力,并将西方不断出现的新译本比做是“新瓶装旧酒”。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地传达了18世纪以来中国道家文化在西方展示的魅力。据两位学者统计,截至1998年(此文刊出的时间),大约有二百五十种西文译本,其中大部分是英语、德语和法语,尤以英语居多④。
据陈荣捷自述,在他1963年重译《道德经》之前,西方已有超过四十种英译本⑤,其中有几种销售较好影响也较大的译本,比较典型的有1868年由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翻译并在伦敦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道德经》英译本、1891年由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1898年由美国哲学家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翻译的第一本中英对照本《道德经》,以及1934年由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除了这些完整的译本外,还有一些严肃的以摘要翻译和简介的方式呈现的节译本,如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此书在第一部分“分封时期”(The Feudal Period,B.C. 600-200,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一章中,介绍了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及其著作,其中就有对《道德经》的节译和概述。该书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如1933、1958、1973年等)多次再版,影响很大。在英译本之外,以法文和德文等其他欧洲语言翻译的译本也不断出现,比较著名的有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842年的法文译本、传教士卫礼贤(Richaid Wilhelm)1911年的德文译本等。他们在欧洲也有不少读者。
在《论〈道德经〉翻译》一文中,米切尔·拉法各和朱丽安·帕斯以1930年代至1990年代在西方最流行的和影响最大的十七种英译本为例,回顾了《道德经》的西译问题。这篇文章没有提及1930年以前的译本。可能在他们看来,亚瑟·韦利之前的各种译本都属于传教士知识系统,与现代学术背景下的译本不可相提并论,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又以1960年代为界,把20世纪的《道德经》英译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包括陈荣捷译本在内的八种译本被认为具有代表性。正如他们理解的那样,《道德经》翻译的差异应该主要归因于译者的翻译技巧和他们自身具备的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背景知识,以及在面对所有译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时寻求的解决方法的不同。这些差异又可以归为三类:关心文本本身的问题(即译者选择何种汉语文本作为翻译底本的问题);理解汉语文本意义的问题;将汉语翻译成英语的问题⑥。这些问题的确是汉英互译时面对的普遍问题。
《道德经》的英译始于清末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这是我们熟知的。19世纪初,当第一个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到中国时,传教士的一切文化工作都是围绕传教工作展开的。马礼逊本人在积极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为了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也附带进行了中国经典的英译工作。但是直至马礼逊于1834年去世,中国文化中的道家和道教都没有像儒家那样引起传教士的重视。这一局面在马礼逊去世后理雅各接替他任英华书院校长一职后才开始有所改变。理雅各在1875年承担了牛津大学教授马克思·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主编的《东方圣书》(TheSacredBooksoftheEast)中的中国圣书系列的翻译,除了完整翻译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外,他还翻译了《道德经》、《庄子文集》、《太上感应篇》等道家经典,这项工作无疑具有开创性。然而遗憾的是,虽然理雅各出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而形成的文化教养,在翻译中充分尊重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被看作是“开创了西方汉学新时代”的人物,但他的翻译仍带有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烙印。正如他的侄子在回忆时所说,理雅各一头扎进中国经典,是因为他“相信并且坚信,在他经过日夜苦读之后,从它的经典当中反映出这个民族的老祖先是知道上帝的”⑦。这一宗教先见贯穿在他的中国典籍英译中,《道德经》也不例外。
在上列影响较大的西文译本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由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英译的《道德经》。它的问世极大地改变了旧有的主要由传教士主导《道德经》翻译的局面,被公认为是西方《道德经》英译的转折点。该译本的全称是《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TheWayanditsPower:AStudyoftheTaoTeChinganditsPlaceinChineseThought)。副标题名称显示出亚瑟·韦利试图通过翻译工作展示《道德经》自身与它所产生的文化母体之间关系的意图。换句话说,亚瑟·韦利要努力矫正过去《道德经》英译中的基督教化色彩,还《道德经》本色。
发生在《道德经》英译中的这些变化,体现了20世纪西方对东方这个“他者”认识的历史性反思,总体上是一种鼓舞人心的趋势。但是,上述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有影响力的英译本都出自西方人之手,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者自身文化背景和中英两种语言隔阂的影响,即便是公认优秀的亚瑟·韦利译本也存在这些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翻译技巧和学术研究的不断自我更新,有些译本越来越显得有些“过时”。陈荣捷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3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亚瑟·韦利译本自出版后,销量可观,几乎每隔五六年就要重印一次,以致“人人引用,几以其解释为不可移易之标准”。该译本中的很多观点,比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反映的是我国30年前的研究状况,本不足为怪,而西方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仍以此为权威,就不免落后⑧。上述两点构成了以汉语为母语的海内外华人学者重译《道德经》的重要学术背景。
亚瑟·韦利译本问世后不久的1936年,四川大学教师胡子霖(Hu TseLing)有感于中国人在传统经典翻译中的无所作为,便翻译了《道德经》。该译本以译注的方式逐章翻译和注解《老子》八十一章,题名“老子译注”,由成都加拿大教会出版社出版。这可能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英文《道德经》⑨。胡子霖在前言中陈述他翻译的理由时,就指出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译本是一个大缺憾。他回忆自己在香港大学上学时,有位叫辛普森的外籍教授和他有一次印象深刻的对话。教授提醒胡子霖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播的主体意识,因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相比,就好比“幼孩与成年人”的关系。他还提醒胡子霖,一般的西方学者缺乏理解中文书籍的能力,希望中国学生将“阐释你们的文明给西方世界”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次谈话成为胡子霖英译《道德经》的直接动机。当时处于二战前夕,胡子霖还认为《老子》是反对战争的,《老子》的教诲,能给世界人民带来和平希望。在《老子译注》的扉页,有“老子教导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和如何使世界和平”的字样⑩。由于资料有限,该译本的发行和销售情况不得而知。

随着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的艰难兴起,20世纪60年代,新一轮的经典翻译出现了。1963年,美国和英国先后出版了由陈荣捷翻译的《道德经》和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华裔学者刘殿爵翻译的《道德经》。众所周知,在陈荣捷的所有译作中,影响最大的是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用英文翻译和写作的ASourceBookinChinesePhilosophy(一般译为“《中国哲学资料书》”或“《中国哲学文献选编》”),《道德经》是该书四十三章中的一章,题名为“老子的自然之道”(The Natural Way of Lao Tzu)。这本书中的《道德经》译文在同年发行了单行本,题名为“《老子之道: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TheWayofLaoTzu,ATranslationandStudyofTao-te-Ching)。《中国哲学资料书》出版后广受好评,直到在陈荣捷去世的1994年,仍被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认为是这一领域里无法超越的标准著作(a standard work still not superseded in this field)。

幸运的是,作为20世纪北美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陈荣捷密切关注着华裔学者的一举一动。上文提到的所有华裔学者翻译的《道德经》甫一出版,他即及时撰写书评发表在海外权威杂志上。下面将根据他的相关论述,结合他的哲学论著以及他翻译的《道德经》等经典文本,分析陈荣捷对《道德经》英译的基本看法,以及陈荣捷译本的特点。
二、对华裔学者《道德经》英译本的评论

第一,有关翻译底本的选择
底本选择涉及翻译策略。传统经典都有一个长期的流传过程,而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文本问题自然对译者造成选择的困难。面对不同的源本,任何一个译者都必须根据其翻译目标做出最合理的选择。《老子》流传至今,留下了多种版本和大量争议,近代学者也曾集中讨论过《老子》其人其书,研究成果丰硕。过去西方译者翻译《道德经》时,选择的底本多是通行本即王弼本。比如亚瑟·韦利就是以王弼本作为底本,同时参照一些其他重要注本,加上他自己的少量考证和诠释,共同构成《道德经》英译本。

如前所述,初大告译本主要是为外国读者提供通俗易懂的英文译本,他不像大多数译者那样选择通行的王弼本作为底本,而是以民国著名学者陈柱出版于1928年的《老子集训》为底本。初大告认为王弼本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舛误甚多,不经辨别无以为用,而陈柱的《老子集训》是当时国内《老子》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值得采用。据陈柱自述,《老子集训》“于考异、训诂、说理三者,既力求其备,复力求其简,所以便吾之讲授,与学者之揅诵而已”,观点公正,无个人喜好之偏见(陈柱做《老子集训》的初衷是为他的学生提供可靠的教科书)。陈柱的主要创新是,他根据自己对历代《老子》注释的全面考察和对近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充分吸收,重新排定了《老子》章句,名《新定老子章句》,附于书后。作为英语语言学家而非历史文献学家的初大告选择陈柱本为底本不失为事半功倍的明智之举。



第二,有争议的词语或句子应该如何翻译
《老子》文本深奥、歧义甚多,是众所周知的。历代注释者和近现代学者在《老子》的文本校勘上用足功夫,才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了形成大致共识。但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见仁见智的观点存在。帛书《老子》出土后,国际学术界再次掀起研究《老子》的热潮,这也给《老子》的翻译带来了更多挑战。






陈荣捷之所以如此计较,大概是认为初大告、吴经熊、刘殿爵、林保罗等都是华裔学者,熟悉汉语,且精通英语,和西方学者相比,更具翻译汉语经典的优势,却犯了如此多的误导西方读者的错误。也许正是因为对林保罗翻译的王弼《老子注》不满意,两年后的1979年,陈荣捷和鲁姆堡(Arrienne Rump)合作,重新翻译了《老子注》(Wang Pi’s Commentary on Lao Tzu),作为东亚与比较哲学丛书之一,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荣捷对林保罗译本的批评,主要着眼于其学术性。所以他说,“总之,译本需要更多的工作以使其成为研究性的著作”。但是他也肯定林译本使《老子》和王弼注“以简单的、清晰的和焕然一新的英语”出现在读者面前,不仅促进了阅读者对《老子》的研究兴趣,也将指导对王弼“哲学方向”的兴趣探讨,所以它的价值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也与陈荣捷推崇王弼思想的哲学性是一致的。


三、翻译核心词汇的策略
现代语言学理论有“核心词汇”一说。本文所说的《道德经》的“核心词汇”,是指《道德经》文本中一些能体现其基本思想并反复出现的词汇,比如“道”、“德”、“无”、“自然”、“玄”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它们是人们熟知的术语,对这些词语的正确理解和翻译是《道德经》英译的基础。


安乐哲提出的这些问题,存在所有中国经典的翻译过程中,而以《道德经》翻译问题最为严重。亚瑟·韦利之前的传教士正是通过“剥离”和“移植”手段,使《道德经》代表的道家哲学——一种不同的哲学传统被改造为西方人熟悉的基督教的东西。应该说,这是中外文化传播初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翻译策略。
陈荣捷翻译的《道德经》,在核心词汇的翻译上,就是要摆脱上述混淆中西哲学本质的倾向。他翻译的《道德经》,至少在核心词汇的处理上,下列两个方面是值得赞赏的。
首先,他列出了主要概念表。作为《中国哲学资料书》一部分内容的“老子的自然之道”由三块内容组成,依次是按照王弼《老子注》八十一章的顺序翻译的正文(translation),然后是编者英文评述(comment)和译注(notes)。英文评述和译注并非每章都有,而是根据需要安排。另外,还有大量脚注穿插其中,随时就文字、意义、注释等予以说明,也即他对其他译者要求的为何选择如此翻译的“证据”。在正文前的介绍(introduction)中,他罗列了《老子》的主要概念(main concepts)及这些概念在《老子》中的参考章节,我们可以视其为《老子》一书的核心词汇。这些概念包括“有与无”、“欲”、“阴柔和水”、“政治”、“仁与义”、“知”、“名”、“自然”、“不争”、“一”、“相对性、善与恶、矛盾”、“反复”、“素朴”、“道”、“虚静”、“德”、“柔弱”、“无为”共十八个(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十八个(组)“主要概念”并非严格的来自《老子》文本的原始概念,而是译者的归纳。比如“政治”(goverment)并没有在《老子》文本中出现,而是指《老子》八十一章中共有对应的十三章主要是谈“政治”(goverment)的。将关键词汇和相关参考章节进行标识,能使西方读者在阅读具有一定文化隔阂的道家文献时避免漫无边际,能迅速抓住《老子》一书的核心思想。
其次,陈荣捷翻译核心词汇时尽量结合上下文的语境进行灵活翻译,并在对应的英文后面用汉语拼音进行标识,它起到了安乐哲所说的“提示性符号”的作用。下面以陈荣捷对“仁”和“玄”这两个核心词汇的处理为例来说明。

陈荣捷则将第五章的“天地不仁”译为“Heaven and Earth are not humane”,“不仁”译为了not humane,并在译文后用括号注明“仁”的威妥玛拼音“jen”,以视特殊。Humane有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能体谅人的、人道的、人心的等内涵,not humane则大致可以表达天地都是为无心无为的这一道家意涵。
第九章的“绝仁弃义”之“仁”,则翻译成humane的名词形式humanity,保持了“仁”这一概念的内涵连贯性。陈荣捷还对“道”、“德”、“玄”、“无为”、“虚”、“中”、“气”、“玄德”、“自然”等核心词汇也采取了同样的拼音标注的方法。与上述布莱克利和刘殿爵的翻译相比,陈荣捷的翻译更加接近道家哲学的原义。



四、通过翻译凸显《道德经》的哲学品质
陈荣捷在《中国哲学资料书》的台湾版(1992年)自序中回忆,此书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他和夏威夷大学的同事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共同致力于东西文化的沟通,而这一工作又源自西方人对东方思想的长期误读和缺乏全面了解。所以,陈荣捷试图通过他的中国哲学经典翻译和朱子学研究,改变这一状况。
首先是去基督教化和神秘主义。
如前所言,西方人对《道德经》的误读首先表现为将其基督教化。正如茱莉亚·哈迪(Julia M. Hardy)在她回顾西方《道德经》诠释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西方早期的《道德经》诠释无不具有浓厚的基督教化特征。她以雷慕沙(J.P.Abel-Remusat)、儒莲(Stanislas Julien),理雅各(James Legge)三个西方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道德经》诠释作品为例来说明问题。1820年,雷慕沙在他关于《道德经》的著作中声称,犹太字母中表示上帝“耶和华”的内容与《道德经》第十四章中表示“道”的三个特征(笔者注:希、夷、微)的描述相一致。他认为《道德经》的“道”好比西方的“逻各斯”(Logos),也传达了三重意义,即“超越性存在”(Supreme Being)、“根源”或“理性”(reason)、“世界”(world)。雷慕沙还把“道”描写为第一因(the first cause)和创造者(creator)。雷慕沙的这一解释可以被看作是将《道德经》直接比附基督教的最明目张胆的表现。







其次,是陈荣捷在多种《老子》注释中特别重视王弼的《老子注》。

概而言之,陈荣捷对王弼《老子注》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的《老子》英译本大量参考了王弼注;二是密切关注学术界有关王弼注的英文译本及其研究,并及时进行有价值的评论;三是在继英译《老子》之后,又亲自将王弼的《老子注》翻译成英文。
受冯友兰的影响,陈荣捷将魏晋玄学称为“新道家”,以别于魏晋之前的道家。在《中国哲学资料书》中,他专辟一章《新道家》,所选文献共六篇,除何晏的《道论》、《无名论》和郭象的《庄子注》节文三篇外,还摘录了王弼的三篇论著,即《周易略例》、《周易注》和《老子注》的部分文字。其中王弼《老子注》的相关文字涵盖了《老子》共十章的内容,他认为这些文字最能体现王弼哲学的本体论色彩。陈荣捷对这些有代表性的文字进行了慎重的翻译、注释和评论。


五、结语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后的北美,如果没有以陈荣捷和狄百瑞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哲学典籍的系统英译和深入阐释,任何中国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都难以真正展开。事实上,无论怎样盛赞陈荣捷的中国经典翻译的学术贡献都不为过。本文以陈荣捷有关《道德经》英译的相关工作为例进行的个案研究,也再次证明了这一事实。
注释
①对陈荣捷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崔玉英的《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陈荣捷的个人学术历程,书后附有 “陈荣捷先生著述详录”可供参考。
②陈荣捷去世后,由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撰写的讣告中称陈荣捷是“中国哲学和宗教研究的卓越权威”(the eminent authority o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和“美国亚洲研究发展史上的早期领袖”(An early lea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studies in America)。可参见Wm., Theodore De Bary.“Obituary: Wing-Tsit Chan (1901-1994).”TheJournalofAsianStudies53, no. 4 (Nov., 1994): 1354-1356.
③有关《道德经》西文译本的详细统计,尚无定论。郑天星在稍早于米切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 )和朱丽安·帕斯(Julian Pas)发表的《〈老子〉在欧洲》(《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1989年,荷兰尼梅根大学的克努特·沃尔夫(Knut Walf)教授在德国埃森出版的一本名为West liche Taoimsus Bibliographie的工具书中,对《老子》西文译本总数的具体统计如下:从1816年到1988年的172年间共有252种译本问世,涉及17种欧洲文字。其中,英语译本有83种,德语64种,法语33 种。米切尔·拉法格和朱丽安·帕斯在这篇文章中统计的“大约有250种”的数据估计也是来自这本书。相关统计还可参见陈才智的《老子研究在西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官方网站中国文学网,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1797;辛红娟、高圣兵的《追寻老子的踪迹:〈道德经〉英译译本的历时描述》,《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④⑥LaFargue, Michael, and Julian Pas.“On Translating of Tao-te-ching,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In Kohn, Livia, and Michael LaFargue, eds.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277, 278.

⑦Legge, Helen Edith.JamesLegge:MissionaryandScholar.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chap., IV.
⑧陈荣捷:《美国研究中国哲学之趋势》,此文是1963年11月7日陈荣捷在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的演讲稿,后收入陈荣捷著《王阳明与禅》一书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10页。
⑨参见吴心海:《胡子霖:中国老子英译第一人》,《出版史料》2012年第1期。
⑩参见康君:《胡子霖交游一例》,《译林》2011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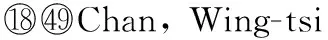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梅莉
Wing-tsit Cha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TaoTe-Ching
Liu Lingd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TaoTeChinghas a long history so that a wealth of translated works has been produced. As a core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Wing-tsit Chan always payed close attention to each and every move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TaoTeChing. Since 1930s some Chinese-American scholars gradually join the team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TaoTeChing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has changed the old situation that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Wing-tsit Chan not only gave int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comment on these translated texts, but also translated the classic text ofTaoTeChingand the comments of Wangbi into English personally. Chan’s outstanding jobs has provided reliable reading texts for readers of overseas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a. In addition,What Wing-tsit Chan done has changed the tendency of mystification and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TaoTeChingto some extent and then highlightedTaoTeChing’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Wing-tsit Chan;TaoTeChing; English translation
2016-04-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老学史”(14DZB00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英美老学史”(13YJA77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