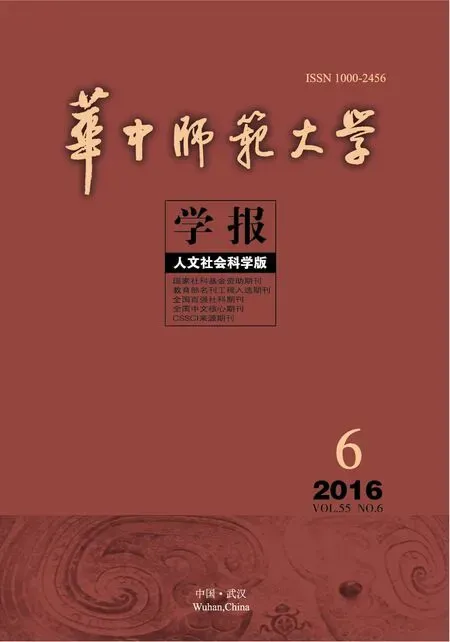实践理性与启蒙精神的复归
——以爱尔兰根学派的研究纲要及其方法论为例
莫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 100026)
实践理性与启蒙精神的复归
——以爱尔兰根学派的研究纲要及其方法论为例
莫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 100026)
实践理性与启蒙的关系问题是切入当代德国哲学史的重要线索之一。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界实践哲学复兴,其目的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继续讨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尤其是讨论实践理性在一种方法论的建构中让启蒙精神复归。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爱尔兰根学派参与到这一讨论中。爱尔兰根学派的研究纲要及其方法论可分解为三个问题:逻辑学与诠释学之间的关系,启蒙与理性的关系,爱尔兰根学派的建构主义哲学对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看法。一种新启蒙的契机是一种启蒙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综合,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尝试与努力。有系统的、可教可学的逻辑学与诠释学的融合提供一种效用,它能弥补早先各种启蒙样态的不足。启蒙表达了人类批判历史、批判现实的情怀,因此它又是一种思想生活。我们在这样一种思想化的现实生活中既可以追溯并分析历史的遗产,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这是启蒙真正长远的、伟大的意义。
实践理性; 启蒙; 建构主义哲学
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个重大问题,康德的回答怀有凝重的历史感: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启蒙就是要使人类能够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人类缺乏理性,而在于人类有没有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所以康德提出的启蒙运动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个口号的真正力量在于,启蒙实际上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
在20世纪德语学界内,里德尔(M.Riedel)所编辑的《实践哲学的复兴》出版是实践哲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一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讨论,其目的在于重新唤起学界对实践哲学所涉及问题和任务的兴趣,并力图通过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协作,在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继续讨论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疑难,尤其是讨论实践理性在一种方法论的建构中让启蒙精神的复归。其中,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爱尔兰根学派(Erlanger Schule)参与到这一讨论中。如何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如何回答实践理性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进行思想储备重新思考上述两个问题,这成为切入当代德国哲学史的重要线索之一。作为爱尔兰根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洛伦琛(P.Lorenzen)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建构主义理论,其重要的代表性文献就是《方法论的思考》、《逻辑学与诠释学》、《启蒙与理性》等文献。何谓一种爱尔兰根学派意义上的方法论建构:哲学研究具有一种对确定性的寻求的传统,“人类知识建立于诸多确定的不能定义的基本概念之上,任何其它的概念都依凭于这些基本概念而被定义。有关基本概念的确定的不可证明的基本命题是公理,任何其它的命题都依凭于这些基本命题而被证明。”①任何一种研究都需要依凭一种科学的方法建构,一种类似于公理的方法,它们用命题性的公理去建构人类的知识。这一理念被笛卡尔以降的西方近代哲学所认可,如果存在一种命题性的公理——无论是发现它,还是构造出它——那么这些公理的自明性可以作为一切学科知识体系建立的基础,并且构建出各种确定性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方法论的问题被分解为三个问题:逻辑学与诠释学之间的关系;启蒙与理性的关系;爱尔兰根学派对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看法。
与之相对应,讨论实践理性在一种方法论的建构中让启蒙精神的复归,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意义上的工作。(1)在保持对原则性问题的广泛而自由地讨论的前提下,获得一种单一向度的一致性,这就需要逻辑学与诠释学相结合的工作。对思考方式与解释方式进行学理上的探究,并不能直接解决实际的问题,但要获得一种自由而有原则的一致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可能性,可以进行一种理论上的实验。(2)一种新启蒙的契机是一种启蒙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综合,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尝试与努力。有系统的、可教可学的逻辑学与诠释学的融合提供一种效用,它能弥补早先各种启蒙样态的不足。同时,这种思维的训练不应是对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模仿。(3)启蒙表达了人类批判历史、批判现实的情怀,因此它又是一种思想生活。我们在这样一种思想化的现实生活中既可以追溯并分析历史的遗产,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这是启蒙真正长远的、伟大的意义。
一、方法论上的逻辑建构与人的自我理解
在人的实际生活处境中,我们的听、说、读、写都与我们的思维方式相关,并且,如何进行正确的思考、以及如何对一个话题进行恰切的解读与交流,这两者都指向两门学问:逻辑学和诠释学。洛伦琛在《逻辑学与诠释学》(1968)一文中,把一种科学的方法建构作了相关的分解,建构行为是在对话中完成的,而一种对话能够最终实现,需要几个要素:人的逻辑思维方式、人的语言构成及理解能力、人的行为能力等。洛伦琛以一种非常有趣,且具有强烈现世关怀的角度切入了这个问题。
在洛伦琛看来,西方人采用多数人的意见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来达成统一与执行,是一种“多元意见”下的多元主义。同时,西方人对其社会系统运行中的“多元意见”模式过度推崇和迷信,而没有对一种前提性的假设作进一步的澄清,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仍然可能是一种意见的混乱的表现。于是,洛伦琛提出了一种论证的假设:相对于“强迫性的单一意见”与“自由的多元意见”,是否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即一种“自由的单一意见”。②这第三种可能性,在保持对原则性问题的广泛而自由的讨论的前提下,获得一种单一向度的一致性,这就需要逻辑学与诠释学想结合的工作。对思考方式与解释方式进行学理上的探究,并不能直接解决实际的问题,但要获得一种自由而有原则的一致性,就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可能性,还可以进行一种理论上的实验。
从逻辑学的角度对语言行为进行分解:“提供一种意见”意味着在自然语言中表述了一个命题,它存在于一种公共语境中,无论是以母语,还是其它语种的方式。洛伦琛沿用了自然语言的一种基本区分方式,即自然语言可以被区分为实践与理论两个部分,两者存在一种渐进演化的过程,后者是对前者的精确化。自然语言的实践部分作为日常语言而存在,它为我们日常行为中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工具;自然语言的理论部分表现为哲学、神学语言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语言。
洛伦琛提出的主张是:“实际的论断精确化为理论化命题,这是一种在方法论上可教的方式。”通过一些可分解的步骤能进行言传身教。其操作的模式如下:从实践生活中的日常论断出发,我们首先提炼出最基本的命题形式,例如“这是什么”或者“这不是什么”。在专名和谓词项构成的基本命题中,谓词项是为了试图抹平谓词一词的含混性。谓词项(Prädikator)是指代所有谓词表达方式的整体概念,它不依赖于谓词的数量,以及不依赖于谓词是单独的还是集合的。问题的要点在于:述谓——在语言行为中,一个谓词项被运用于一个对象上——是如何实现的?③在洛伦琛看来,整个谓词项集合可以分为不同层级的谓词项,而我们首先使用的是在最基本的命题中的、具有范例性质的谓词项。在这种范导性中,我们能区分和命名在世界中的不同对象,类似于儿童对周围世界认知的过程。语言行为的整体被洛伦琛进行了还原:一种对周围世界进行理论化表述的语言行为过程,它从最基本的命题开始,也从最基本的谓词项开始。同时,四种基本的步骤能形成一种理论化的命题,即术语、逻辑算式、定义、标记。④
在语言行为中,谓词项的使用能包含众多的范导性的例证,从而提供出谓词项的使用规则,该规则定义出谓词项直接的关系,并提供出最基本的命题。如果一个谓词项的使用符合规则有效性,那么它就能被称为一个术语,并且,这种对术语的使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建立在术语使用规则下的一种术语规定,在该规范下提供的命题是普遍性命题,而不是经验性的归纳命题。术语规范为谓词项的使用提供各种建议与模式,但作为语言使用者,人们则需要明白:在自然语言中,存在着各式各样依托于传统与习俗的术语规范,当我们用谓词项表述一个对象的时候,术语规范所提供的使用建议天然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语言行为中;同时,我们则需要甄别,该谓词项的使用是否是恰当的。洛伦琛认为,依托于术语的语言行为的运作是一种概念化的思考,它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系统;同时,当我们从众多术语的形态结构中总结出术语的各种属性,它就能提供出特定的规则系统,使我们在语言行为中使用一般的概念进行表达,而不是关注语言学分析中的术语。对语言行为的分析转换为对一种概念化思考方式的分析,同时,概念化的思考模式就囊括了术语学。⑤
在概念化的思考与表达中,我们能不断推演出各种新的概念表达,并形成新的命题,这种新可能性的实现可以用逻辑算式来表达,在日常对话中,逻辑算式连接命题并提供出命题内容最抽象的表达式。逻辑算式通过把日常的命题抽象为符号化的表达,并用逻辑符号连接。这使对话双方能够清晰地讨论命题的各个部分,并最终达成共识。我们在日常交流中,能找到一些基本的逻辑算式,例如:“和”(and)、“或者”(or)、“如果……那么”(if/then)、“非”(not)。就基本的条件句而言,我们设置正反双方进行逻辑推衍操作,当正方提出条件句“if A, then B”的模式时,反方对条件句中的A进行论辩,那么正方必须对条件句中的B进行辩护。例如:对于所有的X而言,如果X是a,那么X是b或者X是c(For all X, if X is a, then X is b or X is c.)。当反方从“X”出发,选择任意一个X的变量,正方需要论辩“if X is a, then X is b or X is c”。当反方质疑“X is a”时,正方则需要进一步论辩,以上就构筑一条对话的序列。通过对前件的数量进行穷尽的抽象,借助于全称量词,术语规范的使用被全称命题清晰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即整个的逻辑序列变成:“对于所有的X而言,如果A1、A2……那么B”。这构成一种在对话中的“逻辑上的真”:即某一命题在日常对话中依据其命题形式而得到正反双方独立地辩护和支持,依照此序列,通过借助逻辑算式,该命题进一步构造并检验了其他的命题。⑥通过确立一个个含有新谓词项的命题,我们在遵从逻辑算式规则中形成定义。需要指出的是,该定义同样来源于我们日常习俗与传统中的基本术语,并且,因为一个定义行为所处的语言环境的不一,所以每一个定义不一定以普遍性命题的形式存在,而往往只是在特定环境、特定传统中的经验性命题。由此,定义行为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演绎的结果。
由以上三个步骤,对话双方之间能最终相互识别、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这依靠理论对话构成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标记。我们需要对语词所蕴含的基本标记进行识别与认出,否则,在双方共处的语境中,对话双方可能辨识不出对方所谈论的对象。对于人与人之间能够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洛伦琛预设并承认了一种“共识域”:对方双方都应具备能达成共识的知识条件。这种条件包括对相应的传统、习俗与文化等等的认知,还包括交往中的个体应具备的理解能力、语言能力等等。
理论命题的语言分析不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进行,即遵循严密科学的思路,去分析一种奠基于传统习俗之上的术语规定,或者普遍的经验命题;同时,也不能采用一种先天综合判断的思路进行形而上学的建构。对于人文科学而言,理论的语言用法将面对另外一个复杂问题,即一个人何以可能说——特别是以书面表达的形式进行表述——我们以何种方式进行一种理论化的思考?这是一种诠释学的工作,对传统文献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吸收是诠释学的特殊使命,传统文献对我们而言,存在两种情况:第一,作者的语言用法对我们而言是未知的。第二,作者向我们谈论的是他自己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对传统文献的内容进行传承与发展必须以恰当的思考方法为引导。一种批判性的继承可以有以下几个步骤: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统;批判性阅读的文本以自己的概念系统为出发点,并随之变化;根据变化的情形,文本的解读与自身的概念系统都随之调整;如有需要,继续以上三个步骤的循环。⑦在洛伦琛看来,自身概念系统在与传统文本的交互作用中能不断获得更新,这不是一种诠释学的循环,而是一种螺旋。无论人们如何努力,这都是一种有限的“诠释学的螺旋”。第一,它不强调对文本原义无限制的诉求。第二,肯定存在一种共识域的融合,使得概念系统与文本间能获得相互调节。第三,螺旋结构具有一种方向性,强调概念系统的建构性的更新。这就是洛伦琛在《逻辑学与诠释学》一文中提出的新问题与新挑战:“通过一种逻辑—诠释学的思维训练,何谓一种新的启蒙的契机?”⑧一种新启蒙的契机是一种启蒙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综合,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尝试与努力。有系统的、可教可学的逻辑学与诠释学的融合提供一种效用,它能弥补早先各种启蒙样态的不足。这种思维的训练不应是对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模仿。
二、实践理性在方法论建构中让启蒙精神复归
在《启蒙与理性》一文中,洛伦琛对启蒙精神作了进一步的解读,并对其同时期的著名哲学流派进行了理论的对话,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维也纳学派等。通过这一对话的努力,爱尔兰根学派实现了几点目标:第一,在一种合理的思维方法的训练下,通过逻辑学与诠释学的努力,我们不会深陷于文本语词的泥潭中,不会使问题的实质因语词而模糊不清。以“启蒙与理性”一词的分析演示一种建构主义的方法论思考是如何进行的。第二,重新谈一种新的启蒙,为实践理性的复兴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第三,与维也纳小组、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对话,试图指出其理论中的不足,并对各派成员都关心的一些问题提出若干解决的方案。
在“启蒙”的条目下解析“启蒙”、“启蒙运动”、“实践理性”等核心术语,需要依据一定的论证步骤:一种专题化、理论化的论述和语言行为,它从最基本的命题开始。四种基本的步骤能形成一种理论化的命题,即术语、逻辑算式、定义、标记。其中术语的使用规范是论证的起点。对术语的使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建立在术语使用规则下的一种术语规定,这一规定使人们限制性地使用“启蒙”、“启蒙运动”、“实践理性”等词语。第一步,专名:启蒙一词,它强调对科学的信心和对改革的渴望。作为人类精神运动的专名,它所使用的语境、指代的时期是相对限定的,即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第二步,术语规定:对“启蒙运动”一词的术语规定,我们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依凭于该运动中典型人物的范例。只有一个人信奉科学精神,对宗教怀有敌意,并倾向于政治改革,那么他才能成为一个启蒙主义者。同时,这三个规定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派成员的基本条件,无论该人是作家、哲学家、科学家。第三步,“理性与启蒙的关系”:对于哲学的理性而言,我们不应在哲学的外部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闲聊,而首先应该是一种实践理性,哲学介入现实是一种实践的合理行动。如果谁承认自己是启蒙运动的合法继承人,那么他们的工作目标应该力图呈现所有科学的统一。⑨


三、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考



四、小结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从纵向和横向上获得理论架构的支撑。从纵向上看,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具有一种对确定性的寻求的传统,该传统不能回避一种科学的方法建构的要求,人类的知识所蕴含的命题性的公理都以此为论证的出发点。一种理想的思想试验与目标应该是,研究者自身运用理论理性厘清其研究的领域,并且用实践理性审视其对话的规范,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应建立一种反思的系统,在其基本概念与命题能得到足够的规范反思基础上,进行一种规范的、有充分根据的论证,其专业的内部理论建构,以及相关的有根据的价值论证。一种新启蒙的契机是一种启蒙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综合,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尝试与努力。在高举启蒙与理性的大旗下,爱尔兰根学派希望同时纳入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并实现一种可能的对话。从横向上看,方法论的问题首先变成语言及语言行为的问题。语言行为的整体被还原为一种对周围世界进行理论化表述的语言行为过程,它从最基本的命题开始,也从最基本的谓词项开始。同时,四种基本的步骤能形成一种理论化的命题,即术语、逻辑算式、定义和标记。自身概念系统在与传统文本的交互作用中能不断获得更新,形成一种有限的“诠释学的螺旋”。它不强调对文本原义无限制的诉求,肯定存在一种共识域的融合,使得概念系统与文本间能获得相互调节;螺旋结构具有一种方向性,强调概念系统的建构性的更新,形成一种逻辑—诠释学的思维训练。



注释
①Lorenzen, P.MethodischesDenken.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 1974,S.24.

③Lorenz, Kuno.“Prädikator,” IN Jürgen Mittelstraß, Hrsg.EnzyklopädiePhilosophieundWissenschaftstheorie, Band 3. Stuttgart 1995, S.315f.
⑩作为波普尔主义者艾尔伯特(H. Albert)同期的批判理性主义者,托匹茨(E.Topitsch)提到: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与思想机构仍然眷恋着一种自我解释的形式与世界观,这来自于前科学、前工业时期,尤其是古代的传统。对于西欧其他国家而言,在启蒙与科学工业化革命中,德意志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命运:它缺乏一种复杂而精致的资产阶级阶层,但他们具有一种经济权利的意识并要求政治权利。在德语区内,一种谦虚的市民文化影响着新教的伦理文化,不可能出现类似于英国与法国那种激进的启蒙,去重新形成一种对世界的形而上学—神学的新解释。这种情状同样在德国观念论上体现出来,它力图克服一种庸俗的、有害的启蒙,类似于德国宗教改革克服一种僵化的基督教正统教义。浪漫主义的观念论所具有的虔诚式的沉思冥想,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于德国大学、以及人文科学院系,并影响至今。参见Lorenzen, P.KonstruktiveWissenschaftsthorie,S.100-101.







责任编辑 邓宏炎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Reason and Enlightenment
Mo B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10002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reason and enlightenment is giving an important clue to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The renaissance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German academia in 1960s is to discuss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 new context of social history, especially to discuss the return of enlightenment spirit by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reason in a methodology. Erlangen School founded in 1960s had participated in this discussion, whose research outlines and methodolog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roblems: logic and hermeneutics, enlightenment and reason, viewpoints of constructivism philosophy of Erlangen School on the thought of Vienna Circle and Frankfurt School. A new opportunity of enlightenment would be a kind of enlightenment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is an attempt to work for the future. The unity between a systematic-teachable logic and hermeneutics coul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a variety of earlier state of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as an idea has indicated the feelings about the criticism of human being on history and reality. We are not only living in such a real life which could be traced and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heritage,but also can get the ideal beyond the reality,that is the real long-term and great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practical reason; enlightenment; constructive philosophy
2016-08-10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重点课题“1949年以来我国启蒙问题研究专题论文集”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