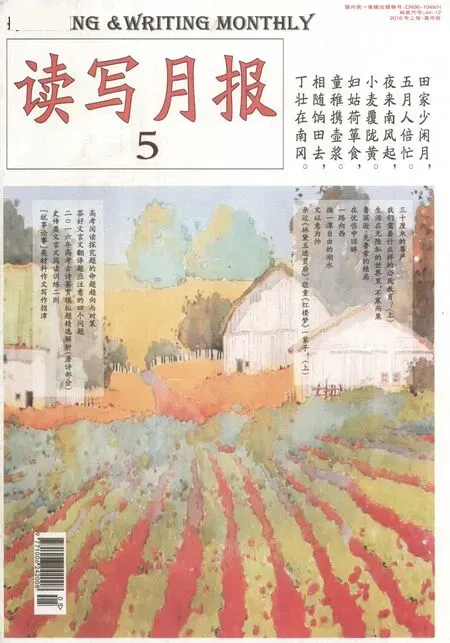鲁滨逊·克鲁索的结局
●米歇尔·图尼埃 著 王道乾 译
鲁滨逊·克鲁索的结局
●米歇尔·图尼埃 著 王道乾 译

“它就在那里!就是那里,你看嘛,在特里尼达岛的海面上,北纬9度22分。不会错!”
醉鬼一边说,一边拿他那乌黑的手指点着一张残缺不全的沾满油污的地图。他神情激动,语气肯定,翻来覆去地这么说,每说一次都引起围在我们桌子周围的渔民和码头工人一阵哄笑。
人们都认得他。他是享有特殊待遇的人。他简直成了本地传说中的人物了。我们叫他来和我们一起喝酒,是想听他声音沙哑地讲一点他的故事。他的遭遇是真正的冒险故事,同时也是很惨的,情况通常都是这样。
在海上不知有多少人一去不返。四十年前,他也在海上失踪。人家把他和同他在一起的其他船员的姓名都在教堂里登记了。后来也就把他忘掉了。
不想二十二年过去,他蓬首垢面、胡子拉碴、野里野气地又出现了,还带回来一个黑人。人家还不至于认不出他来。他讲起他那历险故事,不论在什么场合,听起来总叫人感到吃惊。原来他那条船失事后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留在一个到处有山羊和鹦鹉的荒岛上。要是没有那个黑人,岛上可真的只有他一个人了,他说黑人是从一帮吃人生番手上救出来的。后来一条英国双桅帆船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们回来了,居然还抓紧时间在加勒比人中间做了几笔得手的生意,赚了一笔小小的财产。
大家都跑来庆贺他。他娶了一个年轻姑娘做老婆,说是他的女儿倒差不多。他过的这种普通生活在表面上就把他那一段充满青枝绿叶、鸟雀鸣声、难以理解的意外插曲,在命运拨弄下的那一段往事,给掩盖起来了。
不错,是在表面上,因为随着一年年过去,确实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内部暗暗腐蚀着鲁滨逊的家庭生活。首先是他的仆人,就是那个黑人礼拜五打熬不住了。起初几个月,礼拜五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后来,他喝上了酒——开头,规规矩矩喝一点,接着就酒后闹事,越闹越凶。后来又出了问题,把两个姑娘搞大了肚子,圣灵救济院收留了她们,她们差不多同时生下两个小杂种,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双重的罪行,证据确凿,难道还赖得掉?
很奇怪,鲁滨逊拼命为礼拜五辩护。他为什么不把他送走?是什么秘密——也许有难言之隐——把他和黑人紧紧缠在一起?
最后,他们的邻居大笔现款失窃,对这件事甚至还没有怀疑到是什么人干的,礼拜五就不见踪影了。
鲁滨逊评论说:“混蛋!如果是为了逃走要搞钱,来找我不就完了吗?”
他这人不知谨慎,还说:
“他到哪儿去了其实我也知道!”
失窃的人抓住把柄非要鲁滨逊把钱赔出来不可,否则,就要他把贼交出来。鲁滨逊招架不住,只好赔出钱来了事。
自此以后,人们看到他变得越来越消沉,拖着脚步在码头上或海港入口那里荡来荡去,有时嘟嘟囔囔说:
“是了,是了,他回去了,肯定是回去了,这流氓现在一定是在那里了!”
确实是有一个很难讲清楚的秘密把他和礼拜五紧紧连在一起,那秘密就是他回来以后叫港口绘图员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上给画上一个小小的绿点。不管怎么说,这个小岛,毕竟是他的青春,他的一段美好的经历,他的不见人烟但又光辉灿烂的花园!可是在这里,在这阴暗多雨的天空下,在这讨厌的城市里,在这些商人和告老退休的人中间,有什么可指望的?他那个年纪轻轻的女人,有一颗知人的心,第一个看出他的痛苦,致命的奇怪的痛苦。
“你心里烦闷,我看得出。说呀,你在想它!”
“我?你疯啦?我想谁,想什么?”
“想你的荒岛,一定是!我知道是什么拖住你不让你明天就走,我知道,唔,就是我!”
他大声抗辩,大吵大叫,可是越是吵吵闹闹,她越是自信有理。
她深情地爱着他,不论什么事从不拒绝他。她死了。他急忙把房子田地卖掉,租下一条帆船,直驶加勒比海。又是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渐渐又把他忘了。但是当他再一次返回时,他比第一次出走变化更大。
他是搭一条旧货船回来的,在船上当厨师助手。他已经成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半截儿泡在酒里了。
他一说话,就弄得大家笑个不停。找——不——到!他那个小岛,拼了命去找,找了几个月,也不见踪影,找不到。像发疯似的去探险,到处去找,人搞得精疲力竭,还是一场空。他为重新找到那块自由幸福的土地,力气耗尽,钱都花光,那块福地好像被大海吞没,永远不见了。
“那地方是在那里嘛!”这天晚上他用手指指着地图还是反复这样说。
这时,一个老舵手走上来,碰了碰他的肩膀。
“鲁滨逊,愿意听我说说吗?你那个荒岛肯定一直在那里。甚至我可以担保:那个岛你已经找到!”
“找到?”鲁滨逊一时气塞,说不出话来。“可我刚才跟你说……”
“你找到了!在它面前你经过有十次也说不定。可是你认不出了。”
“认不出?”
“认不出了,因为你那个岛和你一样:也老了!是嘛,你看,花变成了果实,果实变成了树,绿树又变成死树。在热带,什么都变得快。你呢?找镜子去照照,傻瓜蛋!告诉我,你那个岛,你从它前面走过,它认得你?”
鲁滨逊并没有找来镜子照照自己。这个建议也是多余的。他的面孔是那么凄惨,那么狂暴,朝着所有这些人一个个看过去,他们又爆发出一阵更厉害的哄笑,可是笑声突然打住,这乱哄哄的场所一下子寂静无声。
附:
哲学的走私者
张畅
米歇尔·图尼埃(1924-2016)43岁时才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令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部由笛福家喻户晓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改编的作品,一举夺得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大奖——法兰西学院奖的殊荣。
在图尼埃的故事里,鲁滨逊不再是笛福的小说中那个征服荒岛、最终回归人类社会的勇士,而是抽离于社会、归隐自然的哲人。他敏感、忧郁,在航海日记中思考和批判,喜欢念《圣经》中的句子。为了抗衡与社会隔绝造成的孤独,鲁滨逊在荒岛上重新发掘人类社会建设所需的全部元素,思考如何确立作为人的价值体系,反思如何回归文明、重建道德,以及如何面对信仰的困境。难怪法语文学学者、翻译家柳鸣久将图尼埃称作 “铃兰空地上的哲人”。
三年后,46岁的图尼埃凭借《左手的记忆》获得龚古尔奖。他的成名作之一——《桤木王》虽是写二战,却避开了战争场面,选择讲述主人公迪弗热是如何从一个孱弱的小男孩蜕变成为德国纳粹服务的 “卡尔滕堡的吃人魔鬼”的。
《桤木王》,伟大的德语诗人歌德最神秘的叙事诗:“是谁在风中迟迟骑行?是父亲与他的孩子……”战争如同一架无情的机器,扭曲、毁灭着世间万物,作为士兵的迪弗热却只把自己当做旁观者。他利用干活卖力的名声使自己免受严密监视,在奥斯维辛,他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他叫它“加拿大”。
二战进入尾声,迪弗热最后一次抬头 “只看见一颗六角的金星在黑暗的夜空中悠悠地转动”,他感到“自己的人生历程将把他引向更遥远、更深奥的所在,引到更易受到攻击的黑暗世界,也许最终将走入桤木王那样遥远的令人无法追忆的黑夜之中”。这是桤木王命运的某种昭示,是迪弗热的命运,也是人类的终极命运。
图尼埃自称为“哲学的走私者”,擅长在旧有传说故事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把自己的哲学思考置于原本故事的语境,使故事呈现出全新的样貌,比如《礼拜五》。不过在图尼埃自己看来,他只是从头创作一本书,而不是重写一本书。一直以来,他都以简洁、清晰、具体为标准要求自己的写作。就像11岁的孩子都能读懂的那种简洁、清晰和具体。但他深知,作为一名哲学门徒,要达到这一标准何其困难。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隐约看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在同一时空中交汇、对话、迸发。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自身近乎苛刻的思考贯穿始终。表面上,他写一座荒岛 (《礼拜五》)、一名士兵(《桤木王》、一次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午夜盛宴 (《沉默的恋人》),实际上,他都是在对人之所以为人做最通透、彻底的思考。
(选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