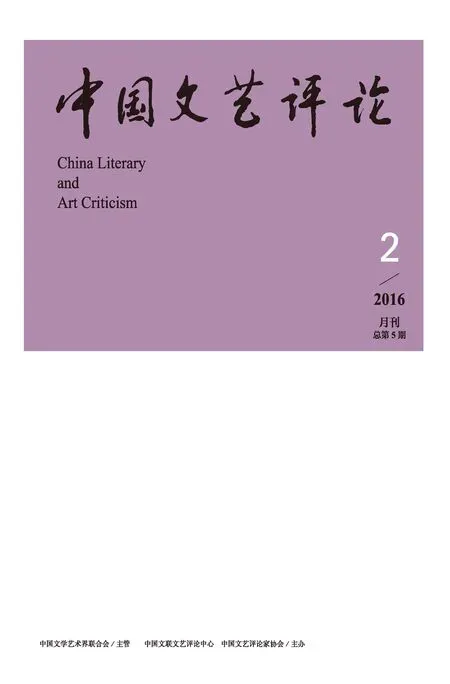历史剧如何呈现“历史的内在可能性”:昆剧《李清照》的启示
赵建新
历史剧如何呈现“历史的内在可能性”:昆剧《李清照》的启示
赵建新
一、戏曲舞台上的李清照
作为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女词人之一,李清照素来是剧作家们喜欢的题材。《声声慢》《如梦令》和《夏日绝句》等名篇佳构,人们一唱三叹,传诵千年;而她和赵明诚的爱情故事以及中年之后的颠沛流离,更让人咀嚼流连,扼腕长叹。正是李清照风华绝代的才情和漂泊凄婉的经历,吸引了众多剧作家的目光和笔触,创作出很多舞台作品,如中国京剧院版《李清照》(1980),南京市越剧团版《李清照》(1998),济南京剧院版《李清照》(2005)。此外,还有黄梅戏版的《李清照》电视戏曲片等。这些作品上演的时间跨度虽很大,但在剧作结构、情节编排、主题表达上都大同小异。
首先,题材内容上,几乎所有编剧落笔点都集中于李清照和赵明诚两人的爱情故事,然后根据李清照的生活经历把两人的爱情分为两段,前段是新婚燕尔、猜书斗茶青州归来堂十年的幸福甜蜜,后段是赵明诚外放莱州、湖州及至病故后李清照的颠沛流离。
其次,情节结构上,编剧们的惯常思维是,写李清照必写赵明诚,而要写一个古董收藏者的爱情故事,“夺宝”的情节似不可或缺,所以无论是京剧版还是越剧版,编剧都以某件文玩古董的争夺为线索来结构情节,塑造正反两派。
再次,主题形态上,这些塑造李清照的戏曲作品,在内容形态上几乎都采取了把朝廷、国家的政治矛盾和个人爱情婚姻生活相结合的方式,前景展现两人的爱情婚姻,后景则是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例如,在中国京剧院版《李清照》中,表面上情节线索是李赵两人的爱情婚姻,暗伏的则是蔡京和张汝舟为获得玉壶利用李格非、赵挺之的朋党之争,进而构陷赵明诚的政治背景;而济南京剧院版和越剧版《李清照》则把李赵两人的爱情生活与金兵南下、皇帝南逃的描写相互交织。这便构成了两层形态,外层是爱情,内层是政治。其实这也是中国戏曲的传统,才子佳人的爱情如果不能和济世报国的政治情怀相融,便显得过于风花雪月和轻忽缥缈。而二者的相互融合,既能利用爱情极大地增强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内容,又能利用政治改造和充实爱情故事,相得益彰。这种写作方式也衍生出双重主题:爱情悲剧和家国离乱,而剧作主题也能升华到“家国情怀”的境界。元杂剧如《梧桐雨》,明清传奇如《浣纱记》《长生殿》《桃花扇》,莫不如此。
上述各个版本的《李清照》在当时都有一定知名度,如中国京剧院版《李清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其保留剧目。越剧版《李清照》曾获得第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及十四项单项奖。济南京剧院版则获得第五届中国京剧节“优秀剧目奖”和“优秀编剧奖”。
以上版本的《李清照》,大多依据史书所记载的内容,以悲剧的形式编织情节、塑造人物,秉承了传统戏曲“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传统。但也有试图“另辟蹊径”者,2014年广东佛山市粤剧院排演的粤剧《李清照新传》,就没有按照以男女爱情写一代兴亡的传统进行创作,笔触仅限于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儿女情长。按说写什么不写什么,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去写,这是剧作家的自由,但这不能成为编剧编造荒诞不经之情节的理由。《李清照新传》从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甜蜜恩爱写起,写到因夫妻分离而相互误会猜疑,更编造了宋徽宗赵佶如何喜欢李清照、李清照又如何用计巧妙让皇帝知难而退、最后夫妻重归于好的情节。这样的胡编乱造,既不符合历史的可能性,也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可能性,只能对作品造成极大的伤害。
可见,单从剧作而言,以李清照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多年来选材和立意雷同,情节设计中规中矩,沉稳端正有余,灵动新颖不足,偶有“创新”却又流于恶搞,更不足取。
二、昆剧《李清照》对同类题材的突破
在同类题材戏曲作品鲜有佳作的情况下,北方昆曲剧院编创的昆剧《李清照》(2015,编剧郭启宏)一亮相便引人关注。
该剧共有四折,分别是“改适”“驵侩”、“讼婚”和“心警”。大致剧情为: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南逃杭州,病入膏肓,其弟李迒撮合朋友张汝舟与姐姐成婚。婚后张汝舟原形毕露,为霸占赵明诚留下的文物父乙彝竟毒打李清照。李清照不堪受辱,以骗婚、虐妇和谋财三宗罪状告张汝舟。一开始,张汝舟以“夫为妻纲”为由驳回罪状。后李清照改变策略,在公堂上揭穿张汝舟靠“妄增举数”骗取官职的秘密,状告张汝舟欺君罔上,终于打赢了官司。但是,按照“妇告夫,当坐,二年”的宋律,打赢官司的李清照却面临坐牢两年的悖论。虽然朝廷最后开恩,象征性地只让她坐了九天牢,但赵明诚的父乙彝却被皇帝纳为己有。晚境凄凉的李清照某日邂逅一正朗读自己词作的小女孩,不禁一阵情热,想收其为徒,孰料小女孩却不愿意,原因是“母亲说不要做李清照,因为她晚节不保”。一代词家顿时如坠深渊。
剧本为一剧之“本”,昆剧《李清照》的成功首先因为剧本的不落俗套。
第一,选材匠心,视角独特。郭启宏从改嫁落笔,本就发人之未发,继之又写再婚后的离婚,这对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是古典温婉、情意绵长之形象的李清照而言,简直就是石破天惊。郭启宏不像其他剧作家一样,从李清照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落笔,也不写与赵明诚恬适安逸的归来堂,甚至后面的离乱漂泊也推到了后景。他独辟蹊径,对李清照的再婚和离婚极尽描摹刻画,抛弃了以往剧作中李清照政治上“高大上”的写作套路,抛弃了朝廷党争中的忠奸斗争,也不写她在金兵南下时的民族义愤,而是把笔墨重点放在描写一桩离婚案,让主人公在再婚和离婚中凸显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已能引起人们的思考,而最终又以难逃道德悖论的悲剧收场,就更加发人深省。这种独特的视角和立意给剧作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例如,以往的剧作中,充满慷慨凛然之气的《夏日绝句》往往被阐释为金兵南下之际民族抗争之呐喊,但在昆剧《李清照》中却成功转换为主人公宁可身陷囹圄,也要争得人格尊严的一次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精神诀别。这种创作视角的成功转化,不失为当下我们所需要的一种创新。
第二,悬念集中,结构紧凑。关于戏曲的结构,历来有“一人一事”的主张。但笔者注意到,由于李清照题材的特殊性,很多剧作家在写李清照的时候很难写出她行动的主动性,很多时候竟有李清照是赵明诚之陪衬的感觉。而且,这种从小写到老的传记体笔法,要顾及主人公一生的际遇,势必就会加大时空跨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演员精彩的表演和导演高水平的舞台调度,整个戏就会给人疲沓冗长之感。这也是很多新编剧目难以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传记体的写法笔触遍及主人公的各个人生主要阶段,很难采用“一人一事”的结构,容易导致悬念不集中,散点透视,松散无力。而昆剧版《李清照》一反常态,不再采用传记体的写法,而是严格按照传统戏曲“一人一事”的原则,一人即李清照,一事即李清照讼婚张汝舟,把情节集中于李清照再婚到离婚的主体事件上,更显凝练。在写离婚官司时,编剧在悬念的运用上也颇具匠心,先是李清照以骗婚、虐妇和谋财状告张汝舟,但后者却均以“夫为妻纲”驳斥。孤注一掷的李清照无奈揭穿张汝舟“枉增举数”的秘密,最终把他告倒。孰料胜利者面对的竟是牢狱之灾,原告和被告同时入狱。紧接着,皇恩浩荡,李清照出狱,但为之舍命保护的宝物却被皇帝巧取豪夺。不由得让人感叹,这场离婚案,李清照到底胜耶败耶?
第三,观念的更新与境界的提升。一些编剧在写到李清照南渡时,尤其突出其动机是要向朝廷献宝。但导致剧作结构上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就是后来李清照好不容易追上了朝廷,却再也不提献宝之事了。实际上,李清照南渡就是逃难,躲避战乱。昆剧版《李清照》没有描写李清照的“献宝动机”,只是描写李清照拉着十五车宝贝到处颠沛流离,最后就剩下个父乙彝,本想守住它,对已故的赵明诚有个交代,但还是被皇帝巧妙地“抢”走了。在这里,编剧变李清照主动向皇帝献宝为皇帝夺宝,成功地避开了“忠君即爱国”的伦理陷阱。
另外,以往写李清照的戏中,很多编剧都写到李清照和小女孩的邂逅,当李清照要教小女孩写词时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很多人写到此处时,几乎都从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角度出发,让小女孩说出不学词是因为其母认为“词非女子所能,古今女子都不幸,自己不想当才女”。但到了昆剧《李清照》中,却让小女孩说出了“不做李清照,因为她晚节不保”的话。虽然李清照在一场离婚官司中赢得了人格,但却没有逃脱庸众之道德指摘和贬损。李清照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活”得卓尔不群,却在别人的口中“死”得如此不堪。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人物身处的道德困境借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之口推到观众面前,可谓振聋发聩,耐人深思。
三、历史剧更应呈现“历史的内在可能性”
昆剧《李清照》第一轮演出之后,有的专家便提出了一些异议,最主要的就是认为除了李清照改嫁、打官司之类情节,也应该表现她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应该把李清照的命运跟北宋王朝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笔者认为,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从历史人物的命运反映历史变迁、家国情怀,这确是历史剧创作的立意所在。但这并不意味必须搬用传统套路,相反,更需要独具匠心。
昆剧版《李清照》虽然没有正面写王朝更迭和政治斗争,但字字句句都渗透着主人公的离乱之情。李清照再婚又离婚的悲剧,不正是家国离乱的大时代在历史人物身上的真实缩影吗?而李清照在乱世中对人格、对情操的持守,不正是民族气节在历史人物身上的真实展现吗?
这又提出了历史剧创作中的一个理论问题:哪些是剧作家该写的,哪些是不该写的?其实,很多先贤大哲对此早有论述。亚里士多德曾对历史和戏剧做出了区分:历史是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戏剧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1]黑格尔在谈到艺术作品中的历史内容时也说过:外在事物的纯然历史性的精确,在艺术作品中只能算是次要的部分,它应该服从一种既真实而对现代文化来说又是意义还未过去的内容(意蕴)。[2]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可能发生的事”或者“带普遍性的事”,还是黑格尔说的“一种既真实而对现代文化来说又是意义还未过去的内容(意蕴)”,都是指的一种“历史的内在可能性”。这种“历史的内在可能性”虽已是历史,但又因其和当代人的精神意蕴相通而具有普遍性意义。
具体到昆剧《李清照》中,从李清照的改嫁和离异切入,比起为朝廷献宝之类情节,显然更与当代人的精神意蕴有相通之处。李清照的改嫁与离异,在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洪适的《隶释》、王灼的《碧溪漫志》、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事实大致清楚。但以往的剧作家们对李清照这段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如不是无意疏漏,就是有意规避,这也说明此节为李清照题材作品创作中的一块“硬骨头”。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版,第81页。
[2][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343页。而昆剧《李清照》却迎难而上,从李清照改嫁和离异的聚讼纷纭中展现其人格力量。正如编剧所言,“在我看来,正是再嫁和离异,突显出李清照独特的个性,张扬了她人格的尊严,也自然而然地与家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试想,没有金兵入侵,没有南渡避难,哪里有李清照的改嫁?何须刻意‘加强’什么‘时代背景’‘思想意义’?对于戏剧创作说来,重要的是再嫁和离异这样奇突的题材,骤现出强烈的戏剧性因素,期待剧作家去发现,去开掘,去想象,去化成文字,去推上舞台,自然,天赋、眼光和功力不可缺少。”[1]
应该说,这一写法同样抓住了历史剧所必有的“历史的内在可能性”,使剧中人的行动及其动机在历史环境之中得到自然展现,同时,这又使剧中的历史人物与当代人的精神同声相应、意蕴相通。以历史为题材的艺术作品的真正的客观性正是我们自己内心生活的内容和实现,“因为题材在外表上虽是取自久已过去的时代,而这种作品长存的基础却是心灵中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是真正长存而且有力量的东西。”[2]而李清照在改嫁与离异的行动中展现出的独特个性和精神魅力,正是黑格尔所指出的这种“心灵中人类所共有的东西”和“真正长存而且有力量的东西”,也是真正能引起当代人共鸣的情怀。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像李清照这样让剧作家感兴趣的历史人物有很多,诸如西施、王昭君、武则天等,他们已经成为相对固定的文化符号存在于历史之中,当剧作家以这些人物作为主人公进行艺术创作时,如果不能把人物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不去研究他们的具体动机和行动,不把他们当作一个真正、具体的“人”来看待,而仅仅满足于对某种文化符号的形象化阐释,忽视这种历史内在的可能性,势必会陷入创作误区,自缚手脚。
实际上,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品,内容往往不乏儿女情长和家长里短。黑格尔在谈到悲剧时说,悲剧情节的真正内容意蕴,也就是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是那些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而在这一系列的力量中,黑格尔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姊妹之间的亲属爱”,其次才是“国家政治生活,公民的爱国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3]剧作家只有自觉关注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探微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并给予了解之同情,才能从新的历史层面发掘出新的历史生活和历史主题,把历史剧的创作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我想,这应是我们赏析昆剧《李清照》所应获得的启示吧!
赵建新: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艺术》编审
(责任编辑:陶璐)
[1]郭启宏:《昆曲〈李清照〉余墨》,《光明日报》 2015年9 月28日。
[2][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354页。
[3][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