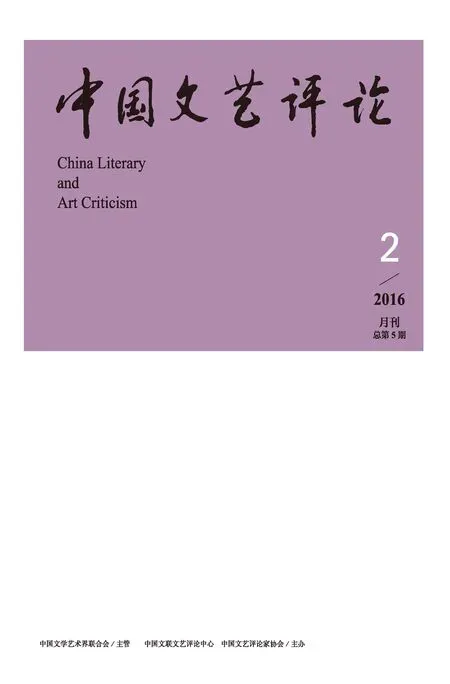“张火丁现象”溯源及启迪
傅谨
“张火丁现象”溯源及启迪
傅谨
张火丁是京剧界的一个奇观,20世纪90年代,就在京剧市场普遍低迷的背景下异军突起,在演出市场上表现出超强的号召力,形成所谓“张火丁现象”。她大约在1994年左右开始崭露头角,因举办第一次个人专场演出受到京剧界高度肯定与关注,1995年调入中国京剧院,2004年,在京剧院组建了由她个人命名的工作室。得益于工作室的灵活机制,她获得大量演出机会,并在其后的巡演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反响。2007年张火丁在北展剧场的演出和人民大会堂的演唱会,奠定了她作为当代最优秀的京剧表演家之一的基础。次年张火丁调入中国戏曲学院,2014年4月26日,张火丁暂别舞台数年后再度归来,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达到她个人艺术生涯新的高峰。2015年5月,张火丁在国家大剧院担纲“相约北京”闭幕演出,9月初应邀赴美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场演出,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她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戏曲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果从1995年算起,张火丁用20年时间,在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学院两个单位完成了她从一位京剧新秀到代表性表演艺术家的跨越。张火丁这20年的崛起历程,有太多值得研究与总结的经验。她在艺术上的悉心追求固然是其取得突出成就最核心的因素,然而假如我们看不到张火丁另外那些不循常理的方面,就无法真正理解张火丁,也难以深刻把握张火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
一
张火丁并非出生于京剧世家,但是她的家庭与戏曲渊源颇深。从目前能找到的公开报道看,她9岁时初登舞台,在廊坊工人文化宫的一场戏曲演出中串演剧中的孩童。在此之后她成为戏曲演员的梦想经历诸多曲折,1986年考入天津戏曲学校京剧科时已经15岁,比普通演员入门迟了数年。她跟随孟宪荣老师初窥京剧门径,1989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其后得到程派名家李文敏熏陶,尤其是拜师赵荣琛的经历,在她艺术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张火丁一直把她拜赵荣琛为师,看成她在艺术上“开窍”的关键。因此,赵荣琛或许是理解张火丁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赵荣琛是程砚秋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他和程砚秋的师徒关系充满了戏剧性。抗日战争期间,赵荣琛在济南承孙怡云学青衣,并且开始对程派产生兴趣,战争爆发后随山东省立剧院迁往重庆。他虽然仰慕程砚秋的艺术,却没有当面请谒的机会,居然通过书信往来成为程的及门弟子,抗战胜利后才在上海补办了拜师典礼,然而此时的赵荣琛在艺术上早已经非常之成熟。尽管京剧界带艺投师的现象非常普遍,但赵荣琛这段特殊经历非同寻常,所以,在程砚秋的著名弟子中,赵荣琛多少是个争议性人物。京剧界师徒间向来以口传心授(或按海震教授的论证,应称为“口传身授”)的方式传艺,假如比之那些多年得程砚秋亲炙的徒弟,赵荣琛是否能够得程砚秋艺术的真传,并非没有讨论的空间。但我们亦可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正由于赵荣琛与程砚秋相隔遥远,所以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与感悟模仿与学习程砚秋,他在程派代表性剧目的艺术表现中,就包含了更多他的深思熟虑。同时也正由于无从得到程砚秋的当面指点,他必须花费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接近程砚秋的艺术。在多数场合,这是赵学程的短处,然而优秀的艺术家总是能够化短为长,他学程比程的其他弟子难得多,然而也正因如此,他对程派艺术的思考与感受,恐怕也比旁人更为深切。
客观地说,张火丁从赵荣琛老师那里学的戏并不多。她1993年才拜师赵荣琛,1996年赵老师不幸离世,因而,她和赵荣琛的这段师徒情缘很短。但赵荣琛对程派的理解,深深影响了张火丁。京剧表演领域界有句俗语,叫“死学活用”,在某种意义上,张火丁的表演里有大量“死学活用”的突出表现,其中就离不开赵荣琛的影响。由于受制于客观条件,除了市场上流传的唱片之外,当年的赵荣琛甚至无缘看到程砚秋的演出。因此他表演的程派经典剧目不可避免地经常只是他“关于程派的想象”。一方面,因他极为心仪和崇拜程砚秋,他表演时无不在竭尽全力地追摹程砚秋,然而客观上,他的许多表演,包括那些程派经典剧目的表演,从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并不都很“像”程砚秋。然而赵荣琛之所以仍然得到程砚秋的首肯、接纳且偏爱,就是由于舞台上那些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能遮掩他的表演对程派表演艺术之精神的实质性的传承。
我理解,这就是张火丁所说的在赵荣琛这里“开窍”的核心内涵。尽管在此之前,张火丁通过多位老师的传授,已经基本掌握了程派最为流行的那些代表性剧目,在这段冗长而又枯燥的学艺历程中,她在“死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然而在赵荣琛这里,她所得到的启示,却使她得以超越了“死学”的层次,赵荣琛就是“活用”最好的范本,他和程派“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微妙关系,就在张火丁艺术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阶段,打开了她认识程派艺术的天地,让她豁然开朗,使她在表演上的气象与格局有了本质上的飞跃和提升。
二
赵荣琛对张火丁极其重要,然而,我们还不能仅仅通过赵荣琛这一把钥匙认识、理解张火丁。假如回到张火丁的“死学”的历程,那么,她在“音配像”里为程派剧目配像,同样对她的成长有决定性的作用。
“音配像”,以20世纪上半叶留存下来的大量京剧录音资料为依托,将录音配上表演制作音像产品,以保存京剧全盛时期名家的表演艺术遗产。经过一个阶段的研究和试录,从1994年起该项目始进入大规模实施阶段,至2002年止,共录制355部(出)京剧名剧,节目时间总长达500多小时。京剧音配像所收录剧目,多数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京剧舞台上的艺术精品,其中就包括程砚秋在其黄金时期留下的录音的配像。程派艺术虽受观众喜爱,但程砚秋留存下来的影像资料却极少,因此程派的“音配像”制作,对今人欣赏与研究程砚秋的表演艺术有特殊的重要性。张火丁就是在此时得到为程砚秋的录音配像的机会的,而且她有幸为程砚秋的录音配了八出戏,在所有程派音配像中,她担任的又是唱做最繁重的配像角色。
张火丁这一代演员的成长环境并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缺憾,就是在她学戏的年代,她的前一代已经与传统有相当大的隔膜。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堪称京剧的最后一个全盛时期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大师的表演艺术积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进入京剧表演行业的演员身上,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继承。时隔半个世纪后启动的京剧“音配像”工程就是要用现代科技手段与老艺人的艺术记忆相结合的方式,接续这个面临断裂之虞的传统。“音配像”这一形式,在人类表演艺术的传承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对于当代京剧表演领域而言,它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给予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表演艺术家全方位地学习和继承前辈艺术家表演精粹的机会。“音配像”之所以对演员的成长有特殊的意义,是由于在“音配像”的制作过程中要求配像者尽最大限度地努力重现录音者当年的舞台表演,因此,这就给予青年演员一个完整且真切地学习和模仿前辈表演艺术家的舞台风范的特殊机会。由于真切重现前辈艺术家的表演的需要,“音配像”的制作团队以国家的力量动员所有可调用的人力资源,一招一式地为配像演员介绍和示范前辈艺术家当年的表演,因而在为程派录音担任配像者的过程中,张火丁最重要也最难得的收获,就是比她同时代的青年演员们用更多时间,尽可能地完全按照前辈艺术家的表演路子演绎经典,由此近距离地、尽可能逼真地触及前辈们的艺术实践经验。表面上看来,“音配像”让那些在艺术本该相对成熟的青年演员完全以机械模仿的方式为前辈配像,并不符合一般的艺术规律。但张火丁这一代演员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个环节,在他们学艺期间,传统已经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支离破碎,“音配像”实在是他们补课的最佳路径。
“音配像”对张火丁的影响不同于赵荣琛。赵荣琛让张火丁知道怎么“放”,“音配像”让张火丁知道如何“收”。在这“收”与“放”之间,才有张火丁既不脱传统藩篱,又体现出鲜明个人风格的表演,才有人们所说的“程腔张韵”。
三
从2006年下半年起,张火丁领衔的京剧艺术工作室开始在全国各地巡演,并且因为取得越来越好的市场效益,受到各界的瞩目,有关“张火丁现象”的话题,也开始在各类媒体上发酵,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火丁是最具市场号召力的京剧演员之一,她的市场魅力,不仅超越大部分舞台艺术领域的表演,而且也比那些流行的明星具有更可长时间持续的市场需求与渴望。
张火丁在演出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其背景是戏曲演出市场整体上的低迷。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戏曲的市场危机就开始显现,戏曲界弥漫着失望与焦虑的情绪,业内人士对戏曲的市场空间与前景,普遍抱持着非常悲观的心态。相当多戏曲理论家认为戏曲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戏曲剧目和演出方式过于陈旧,缺乏新的、能激起当代观众兴趣的剧目和表演手段,“老戏老演,老演老戏”,更让观众厌烦。更极端的观点是认为戏曲是传统社会的产物,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新时代的观众有新的审美需求,因而必然抛弃戏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同时也不乏更具“哲学”意味的表达,认为戏曲艺术已经发展到顶端,因而走向衰亡是其必然结果。
当然,在戏曲实践领域,希望改变戏曲市场低迷现状的努力也在所多有。而如何改变市场衰退的趋势,解决戏曲与观众之间关系愈显疏离的难题,就成为行业内外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将戏曲危机的原因归因于传统拖累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各种提振戏曲市场的努力,都将重心放在新剧目创作上,放在要“为传统剧目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上。于是几乎所有剧团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新剧目上,即使偶有传统剧目,也必定要用符合“新时代观众审美意识”的方式加以大幅度改造,唯恐让人看出这其实是“老戏”。但是张火丁的演出,始终以程派经典剧目为中心,也就是说,她在演出市场取得的成功,完全依赖于传统剧目。特别需要补充的是,张火丁在表演这些程派经典剧目时,也从未想过要用什么“现代意识”和“现代手法”加以改造,因而我曾经提及她是“老戏老演,老演老戏”的典范。诚然,张火丁也有新剧目创作,她不仅有新编《白蛇传》,还有新的《梁祝》,甚至她还编演了《江姐》,还在粤剧大师红线女鼓励和指导下,根据越剧《祥林嫂》最后一场改编了程派《绝路问苍天》。然而她所新创的《白蛇传》和《梁祝》,从根本上说只是传统戏基础上的微调,无论是故事架构、人物关系还是情感表达,均没有脱离这些优秀保留剧目的传统格范,如果说其中有她的创造性开拓,主要也就在于她运用了程派风格浓郁的唱腔和她自己所擅长的传统手法来演绎这些经典故事。至于《江姐》和《绝路问苍天》,从题材内容上看,当然是对程派传统极大的突破,然而就其舞台形态看,完全没有刻意追求破格的迹象。张火丁仍然希望观众看到这是京剧,这是程派,丝毫不以这些剧目以及演出与传统之间的关联而有所忌讳,而观众也以非凡的热情回报了张火丁的选择。
张火丁通过她基于传统又拓展传统的演出,回应了用什么剧目才能把观众吸引回剧场,才有可能激活演出市场的难题。张火丁的回答完全不同于那个时代为大多数戏曲理论家认可的流行观念,我想这大概不是由于她对戏曲的前景与命运有多么深入的思考与深刻的认识,只是由于她成长在这个领域内,自然而然地从前辈身上继承了对传统剧目以及传统手法的稔熟与信任,她的演出无法脱离传统范畴。但是令人深思的是,正是她囿于传统的剧目和演出,却在不经意间获得了观众最多的肯定,使她在演出市场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那些搏命创作演出新剧目的剧团与演员。
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张火丁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张火丁的崛起是当代中国不同社会阶层渴望传统艺术回归的呼唤的集中投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在演出市场溃败的现实面前惨遇打击的戏曲界对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深刻怀疑,然而他们越是想摆脱戏曲的传统束缚,越远离戏曲本体,就越看不清前景。并不是所有新创剧目都无法为观众所关注,只不过偶尔有一两部作品侥幸得到了观众短暂的关注,人们的好奇心也往往很快就消退;当然,也不是所有传统戏都能够赢得票房,只不过优秀传统剧目的高水平演出,始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市场选择。
实践证明,戏曲与民族文化有深邃的内在情感关联,民众对戏曲传统剧目以及表现手法的兴趣与热爱,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决不会因社会发生的表层的变化而突然改变。但恰由于传统剧目一直不受重视,传统表演形态在演出中也愈益罕见,张火丁的出现,就成为诱发当代观众重新燃起对传统的情感依赖的催化剂,人们在她的演出中,重新体会到传统京剧之美,并且也找到了重新恢复文化自信的最好理由。
在一个理论纷纷强调创新的年代,张火丁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她“老戏老演”的道路,并且用市场的巨大成功,为传统戏的当代价值做了最好的证明。其实不仅张火丁如此,当下像王佩瑜、凌柯等有影响的著名演员,都因其坚持演出传统剧目而获得了相当好的票房回报,更不用说昆剧和许多剧种的商业演出中,最有市场成功率的多为传统经典。这个成功的经验,完全颠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戏曲界对市场偏好的判断,也在有效地校正人们对传统的偏见。
四
在张火丁的成长道路上,有一个特点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她始终把练功看成保持乃至提高艺术水平最重要的环节。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曲理论界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并且在戏曲表演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戏曲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宋元以来戏曲伶人们自洽的价值体系也逐渐被颠覆,戏曲演员实际上被纳入“知识分子”群体,因而以文人为基础坐标建构的“知识分子”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对戏曲演员的文化修养与社会责任感等多方面的要求。诚然,传统戏曲本身就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对民族文化往往有深厚的修养和深刻的理解。但这里所说的“文化”,却被有意无意地混同于通常所指的书面化的读书识字,所以对演员成长路径的理解中,奇怪地出现了认为“演员拼到最后是拼文化”“有文化才能成为表演艺术大师”等似是而非的观点,在这种论调的引导下,片面地强调演员读书识字,却忽视了作为京剧演员更基础、更重要的功法训练的必要性。因此,重文化轻功法的现象,在京剧界乃至多个传统艺术门类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而京剧的功法训练是如此艰辛,因而所谓“学文化”也很容易成为演员成长过程中偷懒的借口。
京剧的“四功五法”是其最重要的美学底蕴,属于“学文化”的范畴,离开了特有的功法,京剧艺术的魅力就无从依附。京剧之所以成为京剧,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其特有的“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它们才是京剧基本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语汇。离开了这“四功五法”,京剧就不成其为京剧;进而,掌握“四功五法”的娴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演员的表演艺术水平。假如说在大量新创作剧目中,戏曲特有的传统功法的作用不容易得到充分发挥,因而练功的意义就不是那么显豁的话,那么,传统剧目的表演中,功法的价值更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张火丁显然是一位对京剧功法训练意义深信不疑的演员,在这一点上,她比同时代多数戏曲演员都更清醒、更坚定。而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她对练功的特殊重视与她所取得的成就息息相关,数十年不间断的功法训练,为她高水平地演绎传统剧目,使那些京剧史上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在当代绽放出新的光辉,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在长期的表演艺术生涯中,张火丁总结形成了一套最适合于她自己的完整的练功方法。这套练功方法既源于传统科班的功法,同时又比传统科班和当代戏校同样强调的“基、毯、把、身”四大训练体系,有更丰富和更切实的艺术内涵。多年来张火丁对练功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不分寒暑,无论春秋。尤其在每次演出之前,她通常都会为自己设计一套针对性很强的、系统化的功法训练组合。张火丁的水袖功独步一时,达到了同行都赞叹不已的程度,但这恰是由于她有一套水袖功训练的特殊方法。她的水袖功训练,并不只是孤立单纯地训练如水袖花之类的一两个动作,以《锁麟囊》里“绣楼找球”一场为例,在演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火丁都会根据这场表演的需要,选取其中具有相对连贯性的一组水袖动作,加以无数次的反复练习。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武家坡》里“进窑”一场戏的身段,她同样会在演出前的很多天,就开始每天数十次甚至上百次地重复练习整组动作。她在练功时,当然也会注意台步、圆场、转身等基本动作和身段,但是除此之外,她不将动作分解为细部的训练方法也十分重要,由于她有这些创造性地从表演实践中选取的组合,“矩度既正,巧由熟生”(魏良辅《曲律》),使表演如行云流水般流畅,动作之间毫无联缀的痕迹,把观众注意力紧紧牵制在人物和剧情中,无由分神。
就像无数前辈大师一样,张火丁的成功又一次证明了京剧功法训练的重要性。这个简单之至的道理,本无须张火丁再予以证明,然而不幸的是,这个领域在理论上的混乱到了难以理喻的地步,张火丁反倒成了异类。
五
多年来,张火丁的处世风格经常被人们提起,尤其是她的冷峻和淡然,她的不善言辞,还有她的不喜应酬,等等。
张火丁崛起的时代,恰逢各类传媒急剧发展,媒体对大众的影响力逐渐在扩大,各类演艺活动无不依赖于媒体,以求实现其有效的传播。演艺界人士都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在公众中的曝光率,宁肯在各类游艺类“真人秀”里充当小丑,也要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存在。更有甚者,还不惜自我设计若有若无的绯闻和丑闻,为的只是“上头条”、博眼球。但张火丁好像生活在尘世之外,即使为演出而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她也总是选择最简洁的语言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是”或“不是”,每每让那些习惯于不耐烦地听艺术家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的记者们莫名以对。在这个人们通常认为“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张火丁这种常常让人感觉是有意“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态度,在当下社会中不易找到同类,在戏曲界同样极为稀见。
张火丁与其说不喜欢炒作,这不如说她不会和不愿炒作。她的生命中包含了对浮华与夸饰本能的排拒,这与她潜心于枯燥的功法训练、喜爱反复演出程派经典剧目的偏好,就是一体之两面。生活中的张火丁平实朴素,内敛自持,还是个开朗活泼的人,她待人接物稳重成熟,更无半分骄矜之气。当她低眉垂目时,她只是超然物外,心静如水地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在戏里,她才会在需要时瞬间爆发,忘我地投入戏剧情境。除了表演,她希望舞台之外的一切都远离公众,远离媒体,更没有什么制造话题的兴趣与能力。诚然,无论她是否愿意和喜欢,实际上她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媒体的聚光灯下,但由于她的低调,还有她的剧目选择,媒体很难找到太多可以让记者们充分发挥的题材。多年来有关张火丁的报道内容算不上丰富,她的票房最主要靠的是观众间口耳相传的口碑。然而,天道莫测,2004年她个人的工作室成立前后,在她身边却自然形成了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灯迷”团队,她的这些爱好者迥异于其他戏曲演员的粉丝却更为狂热。张火丁每逢有演出,这个群体便追逐她于各地的剧场,一票难求的奇迹一再重现。而张火丁也始终以其精湛的表演给观众超值的享受,逐渐把她营造成了时代的文化偶像。
在张火丁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民族文化偶像的过程中,最起作用的并不是传统的戏迷票友,也不是北京四九城那些习惯于在长安、“梅大”门口等待赠票的老派观众,而是城市写字楼中的白领阶层和他们的精神领袖。一批文化界具有特殊号召力、知识层次相对高端的精英,在相互间传递对张火丁剧场演出魅力的感受,不期然就成了她的拥趸。他们比社会其他阶层强得多的消化消费欲望与能力,使其有能力维持张火丁演出时的高昂票价,且不断创造新的票房神话,而张火丁的影响力正通过这样的途径被急剧放大。有趣的是,自从经历了对西洋音乐半懂不懂的盲目崇拜之后,更具民族气息的张火丁,就和昆曲《牡丹亭》一样,逐渐成为白领阶层填充其精神世界时最常被提及的关键词之一。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如此轻易地就在物质生活领域获得极大满足,却更为迅速地反衬出他们在精神领域的巨大空虚。[1]他们急于让心灵有所皈依,找到步入中年时停泊人生的港湾。京剧程派深沉幽怨的声音、传统戏剧古朴简洁的情感内涵、张火丁遗世独立的高蹈气质,都凝聚成一个超越于过度物质化的尘世的形象,于是她逐渐被形塑成了古典艺术中“青衣”的当代化身。而张火丁越是无为,就越激发出中产阶级的激情,他们想象中的“青衣”形象就越被强化,在喧嚣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她这样的角色恰好是繁华必不可少的补色,且日益显出夺目的光芒。
张火丁粉碎了当代传媒的自夸自傲,她从不匍匐在媒体脚下乞求关注,最后的收获却远远超出了那些炒作者的期待值。张火丁并没有刻意去迎合时代,相反,是时代选择了张火丁。
所以,张火丁的成功虽有赖于特定的机缘,背后也自有其情理。她在不经意间提供了既有独立人格,又得时代宠爱的艺术家的范本,鱼与熊掌看来并非不能兼得。
[1]“中产阶级”美学是一个复杂而又深刻的议题,就当代中国的审美领域而言,“中产阶级”的美学选择既浅薄又苛刻,它当然有质的要求,同时又附带了量的限制。如iphone、LV、周庄等都曾经进入过他们的视野,然而一旦这些符号化的对象成为普罗大众的消费品,就会很快被抛弃。所以,有人抱怨张火丁演出太少,设若她每年演200场,哪怕是100场,她也很容易滑出“中产阶级”的美学视野。
我们很难在这里完整地阐述张火丁的艺术,也无法全面剖析她成功的秘密,但我们看到了一条不循常理却臻于大成的艺术道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张火丁始终把京剧表演艺术的传承置于首位,没有被盲目创新的潮流裹挟;她始终坚持将技术训练置于首位,不相信艺术水平的提升有捷径可走;她低调处世,坚守了艺术立场的独立。从世俗的角度看,她的所作所为无不是成功学的负面教材,然而正因如此,她为京剧演员的成功开辟了一种新的路径,尽管这样的成功很难复制。张火丁不为各种五迷三道的所谓“新观念”所惑,坚持技术手段的完善与艺术水平的提升,京剧艺术才有可能继续居于让世界惊艳的高度。她通过自己的实践让人们看到,在喧嚣和脆弱的戏曲演出市场中,一个有见解、有追求的艺术家是怎样成功地维护了京剧的尊严和传统的尊严,为新一代成长中的青年演员提供了最为积极和健康的模范,而且,令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复兴与繁荣的前景充满信心。这就是张火丁的时代启迪。
傅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陶璐)
——随钟荣老师学习程派艺术的点滴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