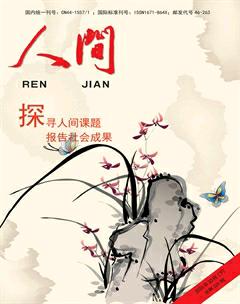佛教三大信仰群体与中国文化环境
冉顶平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佛教三大信仰群体与中国文化环境
冉顶平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佛教于隋唐时完成中国化。中国化的佛教带有中国特色,首先表现在对“至善”的追求强调“我命在我不再天”,修持不假外求;其次弥补了中国人成为“善人”的理论缺陷;最后其底层鬼神信仰亦显示出中国传统伦理哲学中的“务实”精神。由此中国化的佛教信仰群体可概括为信佛、信因果、信佛神三个层次。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等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是佛教在中国立足生根的根本。梳理此问题,对中国现存的其他形式的宗教的中国化,或可资借鉴。
佛教;中国化;文化环境;传统文化
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时的理论输入,到隋唐时达到鼎盛,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样式,此后禅宗一脉引领中国佛教1500余年,至今仍是主导中国人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文化源头之一。那么,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大文化背景下扎下根来?笔者以为,这不仅与佛教本身的文化内涵有关,也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气质关系密切,它们是双向互动、彼此契合的,或缺一方,我们今天便不能见到中国佛教如此浓厚的历史沉淀。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妄图走官方路线,但经过楚英王一案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于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1]由此,佛教一方面吸收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另方面也与民间的精灵鬼神相结合起来。纵观佛教在中国的这两千来年,与本土的道教类似,也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官方、再从官方到民间的发展过程。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不受统治者待见,而为了传道布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吸收中国本土的巫鬼方技。至魏晋南北朝时经中、印、西域无数高僧大德的努力,众多具有核心教义教理的经书被翻译到中土,由此很多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才注意到佛教的可资利用和精深义理,并一度成为“国教”。到隋唐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丰厚的哲学底蕴,完成了“中国化”,并且在此之间,中国佛教出色地解决了其“曲高和寡”的问题,把修禅悟道、伦理信仰及宗教神信仰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禅宗即是代表。至此,佛教信仰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成为了一种全民皆可接受的宗教形态。
纵观中国佛教历代以来的信仰实况,把中国佛教的信仰群体分为信佛、信因果、信佛神三个层次是可行的。由此,笔者便以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为基点,分别对中国佛教信徒对佛教文化的选取,以及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加以阐述。
佛教中的“佛”,即“觉悟者”,是佛教徒最高的追求目标。佛教的整套理论,无不是围绕着“凡人成佛何以可能”而展开的,于是便有了“四圣谛”、“三法印”。“佛”是体,是目的,而“四圣谛”、“三法印”是用,是理解的途径。佛教的“佛”,与儒家的“至善”和道家的“道”,在本体意义上具有极大的相通相似之处,即都是对世界终极真理的追求。从这一点来说,佛教的传入,为部分在儒、道文化环境下受挫的上层人士另辟了一条通往智慧的蹊径,填补了儒、道之不足。另一方面,佛教讲究的“自悟成佛”也与中国传统的“我命在我不再天”[2]相吻合。“四圣谛”首先讲了人生“八苦”,其次讲了苦的原因,即因果(十二因缘),再次讲了超越因果脱离苦海的可能性,最后以“八正道”道出了实现涅槃境界的具体方法。“因果”是贯穿整个佛教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线索,即人生来便在因果轮回之中,有因果轮回便有痛苦和烦恼,所以人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修持方法以超脱因果轮回,达到“寂静”的极乐境界。而在此过程中,修持者既不受外部环境影响,也不受他物援助,完全是一个自觉自律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自《周易》而始,便在讲“自我”应该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达到“无咎”的效果;儒家亦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从而把德的修习(对“善”的追求)落实到了个人身上;道教更是直言“我命在我,不属天地”[4],以“体道”的方式展开了对长生不死的探索。哲学界有“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之渭,其根据便在于东方哲学对“智慧”的追求总是,不同于西方人的“知识”源于上帝的恩赐。自然,佛教是东方哲学的一部分。
“因果”本是佛教解释成“佛”的一个理论架构,但在中国却为很大一部分佛教徒所直接信仰,即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道教更是全盘吸收并且在儒家观念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了一套“承负说”(“承负”,语出《太平经》),也就是不仅会“报”在己身,而且还会“报”在子孙后代身上。由此,因果报应成为了中国人最普遍的价值观念之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佛教因果理论中也是说得通的,是一种朴素的“普遍联系”观,不同的是,佛教最初建立的因果说只是“成佛”的解释工具,但当佛教到了中国后,却成为了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仰对象,并进而发展为“信佛等于行善”,而无有更高的为解脱烦恼的对“觉悟者”的追求意识。在中国的儒、道文化中,对人如何追求“道德”作了精细的论述,而对不追求“道德”的后果却少有理论建树。由此,佛教的因果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充当了一个反面教材,并且伴随着强烈的宗教神秘感,让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对因果伦理的信仰,虽然偏离了佛教信仰的本质,但却很符合普通大众的心理。这种心理关系到来世福报、今生幸福,以及自身与周围人事的可靠联系。当佛教的这种因果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家的伦理纲常形成互补的时候,就更增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于是,人们在“佛”的名义下崇信着“儒”。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们“向善”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秩序平衡、净化个人心灵,但最终仍然会和“儒”一样在尘世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恶”,从而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烦恼异常。所以,信因果仅能为世间的“恶”找到逻辑上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并不能把人从“恶”中拯救出来。只有真正的“佛”才能不为那些“恶”所动。
信佛的最低层次是信“佛神”。我们知道,从佛教的根本教义来讲佛教是反对有神论的,因为成佛不是靠神渡而是靠自渡。至今小乘佛教仍不崇拜偶像。虽然在众多佛经有很多鬼、人、神、罗汉、菩萨、佛,但那仅是一种哲学解释,而非实体化的信仰对象。然而在普通民众那里,人们并不需要这种复杂的解释,他们信佛根本不是为了成佛。从佛经中把那些观念的鬼、神、佛借鉴过来,实体化,供起来,再从它们那里求得他们需要的东西才是他们信佛的根本目的。这一宗教规律适用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宗教信仰,但笔者认为这在中国尤为明显,因为功利化、实用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特征。中国人历来崇拜着各种不同的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神的“职能”不同,所以求子的拜观音菩萨,经商的拜财神,读书的拜孔子……(中国多神崇拜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务实”精神等有关,在此不予赘述)而与自身生存生活无关的神,人们是不会去祭拜的。佛教众神进入中国,在内涵上并没有给中国的民间宗教增添多少光彩,仅是从数量上壮大了神族这个大家庭,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信仰选择。比如观音菩萨,除了名字来源于佛教、形象具有佛的气质外,人们就便不会再去关心她的得道之路,人们所在意的只是她的仁慈好施,以及所施何物。所以,在中国民间,往往有着佛道不分的现象。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说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佛教的传承毫无贡献,至少,在宣传上功不可没。佛教的这种“非佛教”化,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一致。
以上便是笔者对佛教为何能在中国立足生根的原因粗探。总而言之,就是佛教的宗教文化气质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很大的糅合空间。佛教作为一种典型的“温和型”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兼容并包的特质,是它们能够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并最终完成佛教中国化的前提。佛教不同的信仰群体,各取所需,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景象。
在此,我们反观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却显得不那么理想。天主教在唐时就曾传入中国,但未能立足。明末再次传入中国,纵然利玛窦、徐光启等人极力推行“本土化”,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虽然失败的外在原因(如中国封建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决裂)是其主导,但亦不可否认“上帝”的观念并未深入中国人的内心。试述其原因:第一,基督徒的命运握在上帝手中,与中国的“我命在我不在天”大相径庭;第二,基督徒的“原罪”决定了他们今生不可能达到“至善”,只有永无止尽的“洗罪”,而中国人通向“至善”的道路却现实可行;第三,基督徒与上帝和社会的关系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这与中国传统的“家族模式”相抵触,并且从中借鉴不到能够优化自身的要素;第四,基督徒意在来世,而中国人注重当下,信仰上帝对现实生活帮助不大;第五,唯一神的职能宽泛,不如中国众多的职能神具有针对性。这些,都与佛教的宗教文化气质相异。
[1]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89页。
[2]张松辉译注:《抱朴子内篇》,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0月,第519页。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73页。
[4]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8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第246页。
B949-G129
A
1671-864X(2016)10-0172-02
冉顶平(1988.09-),男,重庆奉节人,2015年于云南民族大学就读宗教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四川大学宗教学博士孔又专,研究方向:道教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