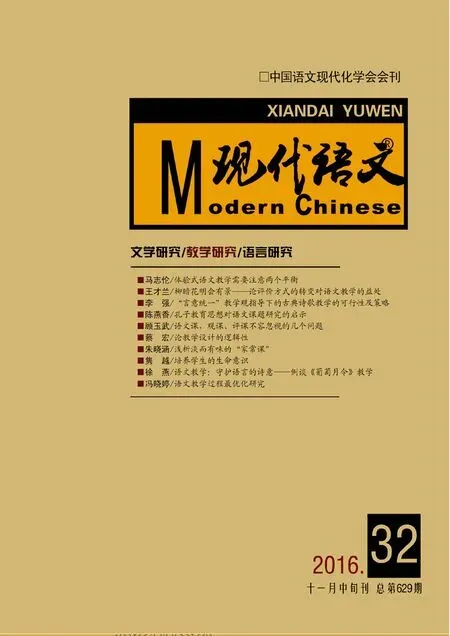语文教学:守护语言的诗意——例谈《葡萄月令》教学
◎徐 燕
语文教学:守护语言的诗意——例谈《葡萄月令》教学
◎徐 燕
当今时代,读图风行,文字阅读相对冷落。加之传媒语言、网络语言、市井俗语的多方渗透,汉语运用正日益简单化、粗糙化、随意化,语言的诗性不断被埋没。
早在18世纪,法国作家布封就说“风格即人”,20世纪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更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他们都把语言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文学语言不仅是符号工具、表现形式,其本身便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可以说,语言与“存在”同在,与人同等丰富。
然而,当下的中学语文教学,并未对语言的诗性有足够认识,更未能自觉有效地守护语言的诗性。老师们更多地关注内容、思想、情感,却往往忽视了语言本身的“美”。 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我们不难听到以下课例:
1.教韩少功先生的《我心归去》(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
作者写了法国的“家”和国内的“家”,这两个“家”,各有什么特点?作者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请于文中找出相关字词或自行概括,填写下表。

环境特点 作者感受法国的“家” 雅静 宽敞 优美 冷静 孤独 虚空国内的“家” 贫瘠 脏乱 温暖 亲切 激动 失望
2.教汪曾祺先生的《葡萄月令》(苏教版高中语文《现代散文选读》)
作者逐月介绍了葡萄十二个月的生长情况,根据文章内容,填写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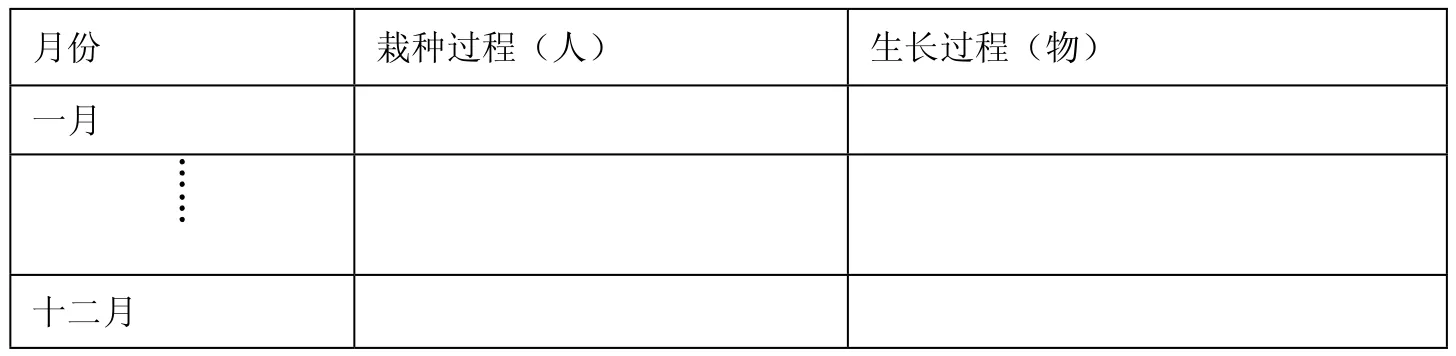
月份 栽种过程(人) 生长过程(物)一月十二月
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几乎 “一望而知”,没有曲折奥峭之处,教学却还匍匐在学生已知的能力层面,仅仅列取作品那可听可见的语义层面,简单地筛选信息、简化内容,却将文章本身精湛传神的语言弃掷不顾。如此,教学的无味无趣、单薄浅俗也就在所难免。
其实,读这一类文章,即便学生读懂了内容,也未必能深入文心,推敲作者语言表达的苦心孤诣、写作思维的电光石火,进而意与文合,读出那“雷转空山惊”的高峰体验。如果师生长期缺乏高水平的阅读审美体验,仅只盘桓在文章内容的表层,那么其阅读兴趣、审美能力都难以灌注活力,最终难免阅读的低水平重复和作文语言的伧俗简陋。
文学语言特别忌讳“抽筋剥骨”,斩断文脉。汪曾祺先生有个精辟的比喻:语言像树,树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 “如老翁携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所以,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就没有生命了。当文学作品被人为分解为几个段落、被删削得只剩下零散的词语、被剥离得只剩下筋骨构架、被直白地暴露出写作技法的时候,文学作品引人入胜的魅力何在?惹人沉醉的美何在?删繁就简的分析,删去的是文学的美感,简化的是生命的班驳。所以,依靠内容的精简、提炼、概括,期求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大概只能是缘木求鱼。引导学生关注文章的语言,字词的选用、句式的参差、文气的流转、声韵的抑扬理应成为语文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体会语言的艺术性和审美性理应成为语文教师的基本修养。
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认为,汉语的诗性特征,不在辞藻之华丽与否,而在于说出的言辞对未说出的东西所启发、所想象的空间之广度和深度。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言约旨远、隐喻性、画意性和音乐性。笔者拟从这四方面,考察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代表作《葡萄月令》。
这篇文章不以内容取胜,倒以语言见长。简淡平常,恰是作家汪曾祺创作上的自觉追求:我希望文章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不过,表面上的平淡随便,背后是作者的苦心经营。
首先,言约旨远,用意精深而下语平易。文学语言区别于口语,就在于它经过了作者的提炼加工,看似轻描淡写,实则举重若轻。请看先生描写“二月”的相关文字: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
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
“醒”、送”二字拟人,一草一木,在汪先生眼里都是有情的,都是活泼泼的生命。“软”则将娇嫩的枝条随着春风摇摆的柔美映人眼帘。“树绿了”,“土地是黑的”,着“绿”“黑”二字唤起读者直观的美感;“绿”写出了树木吐芽,洋溢着盎然生意,“黑”写出了土地肥沃,包孕着无限生机;并且两相映衬,构成春天的美丽多彩。而“碧绿”单词成句,置于句末,豁人耳目,舒朗中唤起读者的想象与美感。汪曾祺先生特别讲究语言的干练简洁,他用字精准,惜墨如金,力求每一个字都气韵生动,神气完足。这就是先生强调的“空白艺术”,“能不说的话就不说,……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
其次,隐喻性,以表示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象征)深远的意境。汪先生这样写给葡萄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先生把俗人眼中不堪的粪沟居然比作玲珑优雅的月牙形,别出心裁!但读来那粗俗甚至令人嫌恶的劳动立刻就有了诗意与美感。又如 “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凡俗的梨花在作者眼中如玲珑剔透的月亮,读来美不胜收。果园劳作,起早贪黑,农活粗重,况且,还背着“右派”的恶名。然而,再艰辛的劳动,再艰苦的处境,在先生的诗心慧眼里,竟都能展现出惊世的美。先生对生活滔滔汩汩的热望、对艺术一往情深的执着,令人倾心不已。
再次,画意性,即语言让鉴赏者在头脑中产生一幅状溢目前的生动画面。汪曾祺先生的语言凝练简远,极具画感。请看八月雨后的葡萄园:“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先生运用生动的比喻、贴切的形容词,把葡萄的形态、色泽、质地之美逼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仿佛热闹的葡萄园近在眉睫。
当然,画意不仅只是单纯形象的再现,画意的背后还隐藏着耐人寻味的境界。
请看先生笔下的“一月”: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雪中的果园,天地洁白、静谧安宁,安宁中潜伏着生命的跃动。读这段文字,让人从凡俗之境一下跌入一片虚静之场,洗净尘滓,澡雪精神。
最后,语言的诗性还表现在其音乐性。汉语音调有四声,优秀的诗歌、骈文甚至散文,其语音的轻重、清浊、平仄都有讲究,需得读来朗朗上口,悦耳动听。汉语句子不受严格的语法规律制约,因而组合自由、句式多样、形式灵活。请看一段为葡萄搭架备料的描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三句话句内“柱”“木”“粗”音韵铺叠,回环往复;句间平仄交错,波澜起伏;更兼长句短句错落,读来舒疾相间,真似嘈嘈切切,珠落玉盘。当然,语音的安排浸润了作者的情思和匠心。比如铺排的短句读来节奏明快,读者不难体会出作者劳动时轻松愉悦,津津有味的情态。
入选教材的文学作品,多是像《葡萄月令》这样语言惊人,字字闪光的典范之作,如若教学仅只在内容、思想方面兜圈,无异于买椟还珠,离博大精深的文心差得太远。真诚地希望语文课能立足语言品读,读出字句的精妙、读出语言的魔力,以此提升学生的阅读审美能力、写作表达水平。
[1]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2]汪曾祺.汪曾祺散文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徐燕 江苏省镇江中学 212017)